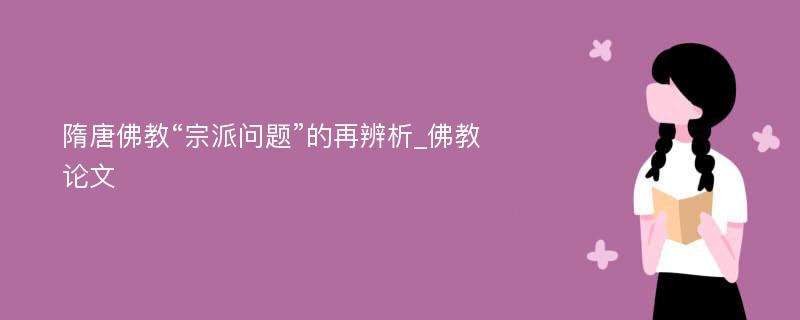
隋唐佛教“宗派问题”再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宗派论文,隋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存在形式出现了重大转型,其区分标志是形成了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为代表的独立发展的教团,也就是说,“宗派”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特点。这在学界一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尽管,对于佛教“宗派”的认定还存在着分歧,有关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时间、宗派的数量、特征以及各宗的形成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异说纷呈。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争议,无疑对中国佛教史的厘清有积极促进的作用。那么,究竟如何理解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争论?“宗派”能否作为隋唐佛教的存在特质的描述?如何理解隋唐佛教的门禁不严问题?
一、隋唐佛教“宗派”的特征及其存在质疑
对于隋唐佛教的“宗派”存在方式的质疑,大多是建立在众多学者对宗派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基础上。而对于佛教宗派特征的厘定,汤用彤先生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在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汤先生在其所著《隋唐佛学之特点》、《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中就中国佛教宗派问题提出和论述了许多观点,为大多数学人所接受或直接沿用。
汤先生根据佛教发展的特点,把佛教史上的“宗”区分为“学派之宗”和“教派之宗”,并指出:“两晋以来盛行的学派的‘宗’和到隋唐时教派竞起的‘宗’,两者的区分尚待研究。它们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点,主要的分别,似可说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①汤先生比较了“学派”和“宗派”的区别,把“宗派”的成立确定为隋唐时期,认为:唐代佛教的宗派,往往各宗有自己的庙、自己的禁律、自己的佛学理论、自己的历史、宗派意识,甚至拥有自己的全国性教会组织。②他还根据天台宗、华严宗等的特点,总结出了宗派的本质特征:“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三、时味说教,自夸承继道统。用是相衡,南北朝时实无完全宗派之建立。……迨及隋唐,而宗派确定矣。”③这一区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既说明了隋唐佛教之转型特质,也说明了宗派的本质特征。
中国台湾学者颜尚文把宗派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对隋唐佛教宗派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他假定佛教宗派之定义如下:“在佛教发展中,经某些教徒根据佛教主要教法,创造出独特的宗义和修行方法,并且透过讲著师承,使此种独特宗义流传数代而形成的独立思想体系或教团。”认为宗派的两项不可分离之基本因素是宗义与师承。在宗义师承关系发展中,又产生专宗寺院、组织制度等重要因素,而派别意识则由隐而显地贯穿在宗派的独立体系或教团中,并且产生宗祖、道统等强烈的争执。因此,宗派依其发展程度之不同,可区分为两种形式:一为学派式宗派,仅有宗义与师承关系及微细难查的派别意识之教义体系;一为教派式宗派,包含宗义、师承体系、专宗寺院、组织制度与强烈的派别、宗祖、道统意识等因素之教团。④他的这种做法,是把“学派”和“教派”视作佛教宗派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一方面关注到了“学派”和“教派”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佛教“宗派”是逐步形成的过程,因而其特质也是在互相影响中逐步建立的;另一方面,也容易混淆“学派”和“教派”的根本区别,从而把中国佛教发展史置于混沌不分的境地。王俊中指出颜的界定和区分可能不符合南北朝和隋唐佛教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还指出:“汤用彤尝试自‘宗’字底下析理出其杂多纷歧的历史面貌,但颜书的分类类型却又把这多元的历史面貌予以概念化与简约化了。性质极不相同的‘学派’和‘教派’全部统合在‘宗派’的概念底下,皆冠‘宗’名,造成同名而异指,似不如汤用彤先在名称上予以区分来得恰当。”⑤
蓝吉富在《信行与三阶教》中提出:“一个佛教宗派的形成,至少须具足下列条件:第一,须有特属于该宗的寺院;第二,在教义上,须有不同于一般佛教徒的独特体系;第三,该宗徒众及一般佛徒对该宗派持有宗派及宗祖意识。”⑥
虽然对宗派特点各呈己见,但对于宗派具有系统而殊别的宗义建设、连续而有序的师承法脉,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传法场所,并拥有一定的宗派自觉,这些是大家共同关注并认可的。而对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进一步展开质疑的,主要存在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中国佛教不存在宗派性,或者说,不以宗派性为特点;第二,隋唐时期不存在宗派佛教。
强调中国佛教不以宗派性为特点的,主要是以日本佛教为参照。在布施浩岳、中村元等学者指出宗派性的区别是中日佛教分界之一的基础上,蓝日昌对日本佛教的宗派性做了总结:“日本佛教的宗派性特别明显,僧侣的派系清楚,僧侣的传记或自称时常常把宗派名称标识清楚,寺庙的派系清楚而各有势力的竞争,还曾一段时间拥有僧兵而进行破坏性的战争,同一派系的寺庙有本宗与别枝的区别,各有从属关系上的相对的权利与义务,寺庙有直接的派系传承关系而不受政府的指挥,信徒与寺庙之间有非常紧密的信仰上的关系,日本在江户时代,通常一出生其宗派性就确定了。对日本佛教而言,宗派性是实而非虚。”⑦
与之相比,中国佛教尤其是隋唐佛教“入主出奴”的排外性不清晰,寺庙专属关系不分明,僧人的归属不明确。建立在前人对宗派问题的讨论基础上,中国台湾学者蓝日昌对隋唐宗派的存在提出全面质疑,其最关注的重点在于宗派观念,同时也检讨了近代以来学者们关注到的判教问题、法统问题、独立教义问题等。
在蓝日昌看来,近代以来关于宗派问题的探讨,是“一边建构隋唐的宗派历史,一边解构宗派的合理性,这种冲突在近代学者的论著中频繁的出现……”⑧他提出:“宗派观念的形成实有几个要素:一、要有群己的意识,也就是说要意识到我是某一宗派,彼为另一宗派,法会辩论时依据彼此不同的立场以进行义理上的争衡;二、要确立代传一人的传承观念,这样才能确立传法的权威性;三、要确立己宗的权威性及正统性,这样才能彰显己宗的殊胜性。”⑨以此为判断标准,蓝日昌质疑隋唐存在“宗派”,提出宗派正名始自五代与宋初,而形成则在南宋之时,因而宗派之说出自宋人,宗派观念与宋儒道统观念有关。蓝日昌对“宗派”理论的阐释可谓独树一帜,几乎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进一步以“寺庙继承与法嗣建立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判教与宗派成立的内在关系”以及“隋唐僧团是否具有独特教义和不同教规”等方面展开“宗派成立的内外条件之检讨”,⑩论证宗派不可能出现于隋唐初期,各宗派的祖师也没有创建宗派的企图。因而,以“宗派佛教”来定义隋唐佛教的发展不合历史事实。当然,他并不否认中国宗派的存在,只是认为宗派观念的出现及定稿是经过漫长的演变,宗派意识萌发于唐代中后期,其定论则在宋代。
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佛教尤其是隋唐以来佛教存在方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派为线索展开的。对“宗派”存在的质疑,不仅是对中国佛教史上隋唐以来佛教存在方式的历史事实的省思,而且是对百年来佛教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的挑战。那么,究竟百年来以宗派发展为线索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果真是缺乏学术客观性的臆想,还是质疑本身需要推敲商榷?要回答此问题,还需要回溯到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展开过程和质疑背景。
二、“宗派”问题的展开和质疑的背景
对于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纷论存在的原因,王俊中指出了三点:其一,中国佛教各宗缺乏明确且综合的数据记载,直至南宋时,天台宗人宗鉴撰《释门正统》、志磐撰《佛祖统纪》,才简略地提出有七宗之说,且两书都带有浓厚的天台本宗意识,时间已在十三世纪,只能说反映出南宋僧人的宗派意识。其二,日本遣唐僧使回国时,将中国佛教各家论疏传入日本,往往将各个经论系统都冠以“宗”名;或以后期日本宗派的发展来揣度早期中国的情形。其三,南北朝时中国一度盛弘的经论家,隋唐之后或不再流传,久之,其论疏在国内亡佚,却保存在日本专宗的寺院。清末民初,国人赴日甚火,不少汉籍回流中国,三论、唯识等论典在当时佛教徒的眼下,无不视为奇珍,凝然等人关于中国“宗派”之说,因此一度流行国内学界。但是,凝然的十三宗毕竟是以日本佛教的特有历史形态,辅以某些揣测而成。(11)
毋庸置疑,近代以来对于佛教“宗派”存在和存在方式的质疑,从根本上来自于我们对“宗派”的界定不明晰:“造成分宗数目差异的因由不全是在‘教义’与‘教史’的研究切入点不同,而是对‘宗’这个字学者们并未有精详而共同的使用规范。”(12)迄今为止,我们对“宗派”的使用,虽从汤用彤先生的论述之后,基本有了个共识,但这种共识并不是精准的。尤其是,由于汤先生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天台宗为典型的宗派形式而概括得出的,从历史上看,除了天台宗,各宗派并不具有如此完整而突出的特征;甚至这些特征的形成,也并不完全如汤先生所认定的那样,是在隋唐时期,因而,由这些特征去判定宗派,虽然为大家所沿用,但也常常有人存有保留意见。许多学者在沿用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了姑妄用之的策略,并不对宗派叙述做进一步的深究。
同时,后世对佛教宗派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艰难,甚至不断受到质疑,还在于对于“宗派”特征的概括和理解,打上了日本佛教教团生存方式的深刻烙印。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的整理,受到日本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近代有关佛教宗派的探讨,溯源于日僧凝然(1240-1321)所著《八宗纲要》的传入和关注。汤用彤指出:“戊戌后,石埭杨文会(仁山)因凝然所著《八宗纲要》重作《十宗略说》,从此凝然所说大为流行。”(13)可见,近现代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日本学者对于日本佛教发展状况的揭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的修订。
尽管“凝然所说大为流行”,但对于其说与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事实的吻合性问题,一直颇有争议,争议大多围绕着宗派的数量和名称。
中国佛教也存在着宗派,这在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大家的习惯性叙述,并未受到直接挑战;但中国佛教是否存在如凝然在应长元年(公元1311年)撰《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依中国佛教弘法次第所说的十三宗,这个问题在近代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宇井伯寿在《中国佛教史》中以“一时之方便”解释凝然“十三宗”的提法,(14)即使在凝然那里,也并不以为十三宗是“实指”,他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自认为十三宗是对诸师众多建立的“取广翫习”。不管是“一时之方便”,还是“取广翫习”,都表明此中国佛教十三宗之说,并非完整准确的叙述。中国佛教宗派究竟几宗,各家便自有其说,究其原因,是由于中日佛教自身的差异造成的。
日本佛教的生存方式与中国佛教有很大不同。从八世纪奈良时代佛教传入,日本佛教就有了宗派意识,至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各宗派分裂愈盛。每年度僧的额度分配至各宗,僧尼各自有固定的寺庙作为弘法的场所,寺庙产权可以直接由本宗弟子继承,僧侣基本上属于特定的宗派及弘法寺院。不同宗派之间的区别清晰,僧尼各据专宗经论而非难攻击其他门派。甚至,各宗之间有时起严重冲突。可见,日本佛教宗派之间排异性较强,僧侣、宗派、寺院、戒律、宗经之间的相关性明显,派系之间界限分明且常有势力竞争,彼此诤论从隋唐时期开始就从不曾断绝。而学者们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特征的界定,往往以日本佛教宗派的特点为依据,从而产生对中国佛教“宗派”特征完善性的质疑。
中国佛教的学术研究,在近代以来,确乎是在一边借鉴日本佛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一边剥离日本佛学研究对中国佛学研究的影响的冲突和纠结中展开的。即使在清算“宗派”问题时,这种纠结依然成为“宗派”研究的障碍,以至于依然使用日本学术范式套用的方式反对日式学术影响,而没有真正地从中国佛教发展状况出发来建构中国佛教发展的自身脉络。
此外,近代中国佛教史的整理,也受到了现代学术范式的影响。尽管宗教学提倡研究坚持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原则,尽量关注到各种宗教的特点,试图从各种宗教传统中概括、总结出具有覆盖力的“宗教”概念,但其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依然不免使大量的宗教学者在西方宗教的学术话语体系下看待宗教问题。创生型宗教的成立特点、一神教的排外性、西方宗教发展中的对抗性,深刻地影响了宗教学的学术范式,并因其在近代以来具有较为强势的学术话语权,也影响了对中国佛教的解读和诠释。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研究,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个烙印,强调宗派意识的自觉、教团生存方式的排外性和教团传承的独一性等,从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的结果。正如蓝吉富指出的:“即使是上述第二类宗派,(15)其与现代人的宗派观念仍有相当程度的距离。一般而言,古代中国人的宗派观念较淡。历史上各宗派的产生,往往是慢慢发展形成的,与现代人之号召信徒、制订宗门规矩、向大众宣布成立某某宗的情形大为异趣。此外,在组织形态及运作方式上,也往往与现代人所揣想者并不全然相合。”(16)学术范式的建构对宏观地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有积极的意义。但贴标签式的先入为主,往往容易遮蔽历史的真实,对复杂丰富的历史做简单化的归类或断论。
三、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基本看法
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重新厘定,需要就“宗派”描述对中国佛教的适用性作出回应。而“宗派”是否适合描述中国佛教隋唐之后的生存状态,首先在于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后的发展是否具有迥异于六朝佛教的态势,其次在于“宗派”能否概括和说明这种总体发展态势。
(一)宗派概念:“总结”抑或“套用”?
对中国佛教“宗派”存在加以质疑的理由,是否充足有力?“宗派”是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存在方式的“总结”抑或只是概念的“套用”?我们通过对隋唐“宗派”存在质疑的几个理由的分析来加以探讨。
质疑一,中国佛教史上尤其是隋唐时期并无对“宗派”的直接使用。
“宗”在中国古代有多种涵义,且历史上长期没有明确的宗派名称,这是个事实。也正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宗派”这个概念,而在于隋唐以后,中国佛教生存方式是否有了改变的趋向,这种趋向是否可以以“宗派”命名。
“宗派”并非从天而降,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学派林立分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来的。从学派之“宗”到教派之“宗”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17)正因为宗派佛教是从学派发展而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派佛教带上了“学派”的许多特征,如重义学,重辨析,重辩争;而对“学派”的进一步探讨和反省,也促使宗派佛教强调师承,乃至于建立法统,强调理论体系建设,强调冲突和会通。
汤先生的阐发给了我们理解隋唐佛教宗派的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即,隋唐佛教宗派的存在与否,首先是与六朝佛教的存在方式比较而言。如果我们承认隋唐时期佛教发生了重大转变,产生了与六朝佛教不同的独特的存在方式,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给这种独特性命名。于是,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宗派”的用法,而是“宗派”这个概念是否能概括隋唐以来佛教发展的一个路向,即自隋唐时起,中国佛教的发展路径有了新的拓展,这种拓展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可否认,与学派的思想纷争不尽相同的是,思想体系的独立建构、教团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不能涵盖隋唐佛教全体,却确实成为佛教发展的一个走向。我们用“宗派”来概括这种走向,对于思想史、宗教史的解析,有积极的意义。
质疑二,隋唐时期宗派观念不明显。
不管是智者大师,还是后来的玄奘,在自宗成立的时候,大多有根本佛教宣弘、佛典精准阐释的自觉,而不见得有创宗立派的自觉。这一点,不少学者都有明确的说明。即使在整个隋唐时期,宗派观念,尤其是排异性的宗派观念,也非大多数宗派的自觉。以殊别性的宗派自觉,乃至入主出奴的宗派排他性作为宗派成立或存在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预设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忽略了中国文化统合性传统,忽略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特点。
吕澂曾指出:“唐初的佛学是随顺隋代组织异说的趋势更加发展了的。依着当时著名学者的取材不同以及各有侧重之点,后来就形成了种种宗派,但是都带着点调和的色彩。”(18)这种“调和的色彩”,既反映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文化包容性,同时,也体现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特别之处。吕先生认为,在南北朝末期,佛学南北各家师说“逐渐有了综合调和的趋势,于是开始酝酿一定学派的结构”,有意思的是,他之后用了“此外”,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学派综合调和的趋势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与“综合调和”不太一致的趋势,即:“当时提倡某一种学说的人,常能在一地方固定下来,并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学徒的条件,这样,师弟传承络绎不绝,因而逐渐形成宗派,就大不同于前此流动不定的各种师说了。”(19)宗派意识之“存异”是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的“求同”的基础上展开的,故即使是宗派意识,也并非一味地突出门户之见,而是在强调殊途同归的同时,凸显己宗的殊异性。这种“求同存异”的过程是漫长的,宗派观念的求异性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自觉,而恰是在宗派内部、宗派之间的冲突和会通中逐步呈现的。正如葛兆光所说:“现在宗教史中关于佛教宗派的习惯性叙述,常常是依据佛教徒自己党同伐异的‘教相判释’而在事后追溯的结果,它总是把各种宗派的门墙划得太清,以至于后来的阅读者总会以当时佛教徒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派系上一开始就像汉界楚河那么清楚,仿佛井水不犯河水。”“中国的佛教各宗,从一开始只是学说宗旨略有差别,而并非一开始就是不可通约与逾越的门派,成为后一种宗教团体,并变得越来越有门户之别,则是后来被陆续建构的。”(20)
这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中国佛教宗派特点的总结,应关注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统合性,更应关注到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性。用典型性的结果特征来考量过程中的“宗派”,难免会忽略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长度,而以静态的点遮掩了动态的发展脉络。
质疑三,寺庙继承问题。
师承与寺庙继承的关联性,是否是宗派的根本特征?法统的建立和法统谱系的续继,是师承宗派化的一个标志。但在中国佛教中,至少在唐代,法统和寺庙继承,尤其是寺院经济的继承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我们通过对天台宗本山、玉泉等地的考察,对禅宗谱系的研究,均可发现:祖庭的住持和法统宗师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但这是否就是否认宗派存在的理由?或许应该反过来思考,宗派的延续性,到底是通过什么来保证的?中国佛教宗派的法统,不仅仅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承继一个“宗义”,一个能够真正契入佛意的“宗义”。
综上,我们在考察“宗派”问题时,尤其是在清理其他学术体系对我们真实研究的遮蔽时,或许不该再预设一个标准,而更应该从原典资料出发去概括、总结。推翻现有的对宗派特征的论证,来质疑宗派的存在,这是站不住脚的。
(二)隋唐时期是宗派佛教形成、存在的重要时期
那么,如果我们不以既有的“宗派”标准去厘定隋唐佛教的宗派特征,又如何去理解隋唐佛教“宗派”问题呢?事实上,前辈学者的叙述已经蕴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里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隐含的理念作为进一步研究隋唐佛教的线索。
无论是前辈学者对宗派佛教发展过程的揭示,还是对各宗历史的钻研,都蕴含着一个基本定位:宗派佛教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漫长的形成期。在这个漫长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中,隋唐时期出现了宗派佛教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与六朝佛教的发展相比,自隋唐起,中国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建立起了义理、修行、教团组织体系内在一致的综合系统,并逐步形成了融摄和排斥相统一的宗派观念,构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
之所以称之为重要向度,是因为宗派佛教作为一个主旋律,并不排斥中国佛教发展的其他分类系统,如法师-律师-禅师系统(21)、区域佛教发展系统。可以说,以宗派佛教命名隋唐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是化繁就简的一种学术角度,能够提纲挈领地反映中国佛教发展的路向,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他的研究范式。
从过程的角度看隋唐时期的宗派佛教,我们可以看到,宗派佛教在隋至中唐之前,更多的是一个不自觉的创造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宗派都有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教理系统,有了独特的修行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师承系统。但各宗的宗派观念还并不明晰。到中唐时期,由于各宗之间和各宗内部有了分歧乃至冲突,宗派观念日益凸显,终于在唐末以后形成了更为清晰的门户之见。因此,对于宗派佛教的研究而言,中唐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宗派内部、宗派之间通过学理的冲突和会通,逐渐引发出了宗派观念,并通过学理和判教等方式凸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史的发展,影响了之后佛教史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宗派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还处于一个建设期。在很大程度上,调和是主旋律,冲突是进一步调和、统一的方式和手段。也就是说,顺应着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是一个冲突和会通并存的过程,以会通化解冲突,成为中国佛教宗派发展的基色。这是考察中国的宗派佛教需要特别关注的。
注释:
①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汤用彤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2-373页。
②③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汤用彤全集》第2卷,第330、330页。
④颜尚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第4页。
⑤王俊中:《中国佛教早期“宗派”问题研究的相关探讨》,《谛观杂志》第81期,1995年4月。
⑥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6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⑦蓝日昌:《佛教宗派观念发展的研究·自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Ⅶ。
⑧⑩蓝日昌:《佛教宗派观念发展的研究》第13、17-86页。
⑨蓝日昌:《宗派与灯统——论隋唐佛教宗派观念的发展》,《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4期,2004年12月。
(11)(12)王俊中:《中国佛教早期“宗派”问题研究的相关探讨》注06,《谛观杂志》第81期,1995年4月。
(13)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汤用彤全集》第2卷,第380页。
(14)宇井伯寿:《中国佛教史》,李世杰译,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第209页。
(15)蓝吉富这里所说的是指具有宗派规矩与组织、信徒有宗派意识、且有特定修行方式的宗派。
(16)蓝吉富:《佛教史料学》,台北:东大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第194页。
(17)《汤用彤全集》第2卷,第372-373页。
(18)(19)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335、159-160页。
(20)葛兆光:《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
(21)葛兆光:《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