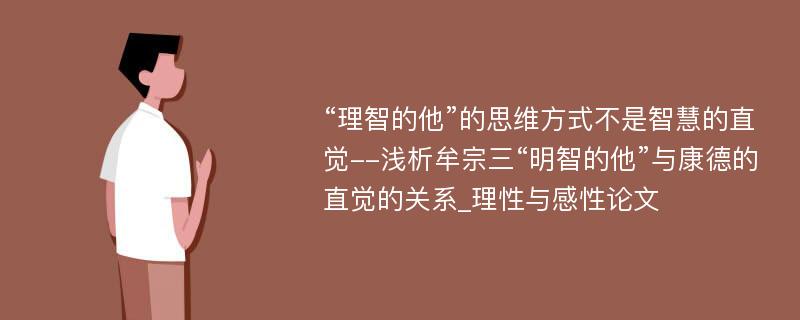
“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直觉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关系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非常重视“觉他”的思维方式问题,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康德不承认人类可以有智的直觉,儒家则承认人完全可以有这种能力,所以儒家超越了康德。牟宗三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人们一般都是从正面理解,目前尚无人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不同意见。我研究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觉他”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希望能够对正确评价牟宗三这一思想有所助益。
一、“觉他”的思想内涵
智的直觉的问题,是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正式提出来的。他认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智的直觉是没有彰显出来的,所以康德才断定人类不可能有这种直觉。“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智的直觉却充分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人类从现实上说当然是有限的存在,但却实可有智的直觉这种主体机能,因此,虽有限而实可取得一无限的意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0卷,第447页。下引牟宗三文献仅注卷数和页码)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人只是有限的存在,不是无限的存在。中国哲学传统则认为,人虽然是有限的存在,却可以同时取得无限的意义,或者说,人虽是有限的存在,但可以同时取得无限性。因为人有无限性,所以人完全可以具有智的直觉。
在《现象与物自身》中,牟宗三进一步肯定了上述思想。他回顾说,自完成《心体与性体》后,他发现该书未能充分注意智的直觉的问题,留下了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近十年来,他重读康德,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都译成了中文。在这一译述过程中,他正视了康德洞见之重大意义,见到知性之存有论的性格之不可废,并相信他能予以充分的证成,而这些康德本人并不能做到。“此中重要的关键即在智的直觉之有无。依康德智的直觉只属于上帝,吾人不能有之。我以为这影响太大。我反观中国的哲学,若以康德的词语衡之,我乃见出无论儒、释或道,似乎都已肯定了吾人可有智的直觉,否则成圣成佛,乃至成真人,俱不可能。因此,智的直觉不能单划给上帝;人虽有限而可无限。有限是有限,无限是无限,这是西方人的传统。在此传统下,人不可能有智的直觉。但中国的传统不如此。”(第21卷,第5页)在这一表述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牟宗三明确肯定了“吾人可有智的直觉”。康德预设了一个智的直觉,但又说人类没有这种直觉,只有上帝才有。这是康德学理的一大不足。要破除康德的成见,必先证明“吾人可有智的直觉”。依据中国哲学传统,无论儒家、佛家、道家都肯定了这一思想,否则成圣、成佛、成真人皆不可能。由此牟宗三再三强调,我们不能把智的直觉划给上帝,必须看到人虽有限而又可无限。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有智的直觉;因为人是无限的,所以可以有智的直觉。这样一来,强调“吾人可有智的直觉”,反对康德不承认人可以有这种能力,而将其归给上帝,便成为了牟宗三后期思想的一个主基凋。
牟宗三在肯定人类可以有智的直觉之后,对智的直觉的对象也有说明。这种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自觉”与“觉他”。牟宗三这样写道:“智的直觉既可能,则康德说法中的自由意志必须看成是本心仁体的心能,如是,自由意志不但是理论上的设准而且是实践上的呈现。智的直觉不过是本心仁体的减明之自照照他(自觉觉他)之活动。自觉觉他之觉是直觉之觉。自觉是自知自证其自己,即如本心仁体之为一自体而觉之。觉他是觉之即生之,即如其系于其自己之实德或自在物而觉之。”(第20卷,第258页)在这一表述中,“智的直觉不过是本心仁体的诚明之自照照他(自觉觉他)之活动”的说法,很好地表达了牟宗三关于智的直觉具有两类不同对象的思想。
智的直觉的对象首先是“自觉”。所谓“自觉”就是“自知自证其自己”,也就是自己觉察自己的本心仁体。在牟宗三看来,从理论上说,要肯定智的直觉,基础完全在于道德。儒家强调,本心仁体是每个人成就道德的根据。这个根据是每个人的本钱,遇事必然显现自己,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做,如何去行。恰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由于本心仁体必然显现自己,对于个人而言,只要你反身而求就能得到,中间不再需要其他环节。这种途径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直觉。因为这种直觉与康德所说的感性直觉不同,所以可以叫做智的直觉。这就是所谓的“自觉”。但光有“自觉”不够,还要有“觉他”。与“自觉”的对象是自己的本心仁体不同,“觉他”是对外部对象说的。这种外部对象,牟宗三有时径直称为“宇宙万物”(第5卷,第143页)、“山河大地”(第29卷,第305页)。牟宗三如此说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道德之心是一个活泼泼的实体,有着丰富的创生性。这种创生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可以创生道德之善行,决定人成德成善,这叫“道德实践地说”;其二可以创生宇宙万物之存有,使宇宙万物能生长、有意义,这叫“本体宇宙论地说”。前一条没有疑问,因为道德本体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成德成善。后一条则较为复杂。所谓道德之心可以创生宇宙万物之存有,使宇宙万物能生长、有意义,主旨是说道德之心有一种功能,可以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之上,使原本没有道德色彩的宇宙万物具有道德的价值和意义。道德之心是存有之源,山河大地、一草一木都系属于它而为它所统摄。宋明儒学喜欢讲仁即为一“生道”,在这一“生道”中,道德之心其极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如时雨之润,使天地万物有意义、能生长,涵盖乾坤而后已。特别有意义的是,与“自觉”一样,“觉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智的直觉,即康德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那种智的直觉。牟宗三认为,这是儒家思想非常独特之处,内涵深刻、意义深远,其合理性甚至超过了康德。
二、牟宗三证明“觉他”是智的直觉的基本思路
关于“自觉”与智的直觉的关系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详述。(见杨泽波,2006年)本文专门讨论“觉他”。牟宗三之所以认定“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不认可的智的直觉,是沿着下面两层关系展开的。
首先,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自己的诠释,其思路与学界通行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在康德哲学中,智的直觉是与感性直觉相对的一个概念。感性直觉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性的直觉,只有当对象刺激主体的时候,感性直觉才能发生。与之相反,智的直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本源性”,用康德的原话说,是一种“本源的直观”(intuirus originarius)(康德,第50页),特指不需要对象刺激,知性本身即可以提供经验、形成认识的一种直觉。这种意义的智的直觉人类不可能具有,或许只有上帝才能具有,当然对此我们是无法证明的。然而,牟宗三没有以这种方式,而主要是从不受影响、不受限制的角度来理解康德这一概念的。在他看来,人们的认识一定要受到范畴的影响,因此是一种受到限制和人为因素干扰的直觉。受此影响,我们只能认识对象的现相,即对象向我们显现之相,而不可能达到物自身。与此不同,智的直觉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不需要范畴,特指一种不受任何人为因素干扰、没有任何人为限定的直觉,即没有“屈曲性”、“封限性”(第20卷,第191页)的直觉。康德认为,我们人类并不具备这种智的直觉,我们的认识必须受到各种认识形式的影响,总有所变形。一旦可以证明人类确有智的直觉,那么我们就不再停留在现相层面,而可以直接抵达对象自身,认识物自身了。很明显,这是对于康德智的直觉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理解,与学界一般的看法有异。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楚的了解,否则尽管我们可以依据康德研究中的通行理解,批评牟宗三的诠释不符合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牟宗三此说的真正意图。
其次,牟宗三在将智的直觉作了自己的诠释之后,便以此为标准证明“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他所理解的智的直觉。这其中一个核心理由就是“觉他”的过程无需范畴。以是否需要范畴来界定是否为智的直觉,是牟宗三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已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并在西南联大办讲座时,专门讲建立范畴、废除范畴的问题。牟宗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按照他当时的理解,如果人类没有智的直觉,那么其思维是需要范畴的,但如果有了智的直觉,其思维便可以不需要范畴了,就如上帝那样。上帝是无限的存在,其思维是无限的,不像人类一样,必须借助范畴。不需要借助范畴,也就意味着不必受范畴的影响,所以其思维不必止于现相,而可以直达物自身。(同上,第195页)牟宗三后来强调“觉他”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在他看来,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并不需要使用范畴。“假定我们对于物自体可有一种智的直觉来直觉之,则范畴是否即能应用于物自体呢?假定我们对于智的直觉与物自体有明晰的理解,则对于物自体即使有智的直觉以觉之,范畴亦根本不能应用于其上。既是智的直觉矣,何须用范畴?”(同上,第155-156页)这就是说,如果有了智的直觉,我们便不再需要范畴了。牟宗三甚至有这样一个设想:“试设想我们实可有一种智的直觉,我们以此直觉觉物自体,觉真我(真主体,如自由意志等),觉单一而不灭的灵魂,觉绝对存在(上帝等),我们在此直觉之朗现上,岂尚须于范畴来决定吗?范畴能应用于上帝、灵魂、自由真我乎?康德自然知道不能用。在此等等上既不能用,何便能应用于物自体?在此等等上,不但因我们对之不能有感触的直觉,故范畴不能用,且亦不因我们对之有智的直觉,范畴即能用。”(同上,第156页)道德之心创生存有,觉润万物,难道还需要范畴,即“尚须于范畴来决定吗”?牟宗三的回答非常简洁明了:不需要。一旦我们有了智的直觉,便可以直接觉对象自身,范畴全无用武之地。因为不再需要范畴,人的思维也就没有了“屈曲性”、“封限性”,从而不再局限于现相,可以直达物自身了。为此,牟宗三还批评康德,说康德没有中国哲学传统的背景,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未能把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想清楚,措辞不谛,多有缠夹。
与无需范畴紧密相关的是无需时空。这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无需时空是由无需范畴引申出来的,虽然所指不同,重要性也不及前者,但思路并无二致。在牟宗三看来,“在无限心的明照下,一物只是如如,无时间性与空间性,亦无生灭相,如此,它有限而同时即具有无限性之意义。”(第21卷,第18页)人有两种心,一是有限心,一是无限心。对有限心而言,认识必须经过时空形式的中介;对于无限心而言,则可以不受这些形式的限制。因此,有限心展现的是受时空形式影响的样子,即所谓现相;无限心展现的则是物自身的样子,即所谓物之如相。换言之,感性直觉与时空有关,其对象为现相;智的直觉不与时空相关,其对象为物自身。有意义的是,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并不需要经过时空,所以其思维方式即是智的直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牟宗三还以康德论上帝为依据。“上帝的直觉是纯智的,因此它并不以时空为形式条件,上帝亦不在时空中(上帝无时间性与空间性)。它直觉之即创造之,即实现之,是当作一物自身而创造之,因此,其所创造者亦不在时空中(无时间性与空间性),时空不能应用于物自身,亦不能是物自身的必然属性,因此,康德遂主张时空之经验的实在性与超越的观念性,而否定其超越的(绝对的)实在性。”(第21卷,第110页)上帝拥有智的直觉,这种直觉没有时空性,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上帝造物并不通过时空的形式,其直觉就是其创造,而其创造的对象是物自身,不是现相。由此说来,区分现相与物自身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有无时空性。“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别其主要的记号就是时空性之有无”(同上),这段话清楚表达了牟宗三的致思路向:智的直觉与感性直觉有所不同,关键一环是时空之有无——有时空为感性直觉,反之则为智的直觉。道德之心“觉他”创生存有并不需要借助时空这种认识形式,所以“觉他”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
因为智的直觉无需范畴,无需时空,不受认识形式的影响,所以“觉他”没有用相。在牟宗三的观念中,有两种不同的感应方式,一是物感物应,二是神感神应。物感物应是说“既成的外物来感动于我也。物应者我之感性的心被动地接受而应之也,因此,此感性的心之接应亦只是一‘物应’耳”。(同上,第103页)意思是说,物感物应是外物感应于我,我的心被动地接受这种感应。这种感应感有感相,应有应相,与其相应的是对象的现相。神感神应就不同了,它完全属于另一种思维方式。“知体明觉之感应既是无限心之神感神应(伊川所谓‘感非自外也’),则感无感相,应无应相,只是一终穷说的具体的知体之不容已地显发而明通也。即在此显发而明通中,物亦如如地呈现。物之呈现即是知体显发而明通之,使之存在也。故知体明觉之神感神应即是一存有论的呈现原则,亦即创生原则或实现原则,使一物如如地有其‘存在’也。”(同上)神感神应是无限心不容已地显发而明通,这种显发和明通不受任何认识形式的限制,如如呈现,用无用相,与其对应的对象便是物之如相实相:“总起来,这就是王龙溪所谓‘无物之物则用神’也。物之在其自己即是‘无物之物’也。‘无物之物’者即是无物相之物也,亦即无‘对象’相之物也。‘用神’者其为用无封限无滞碍而不可测度也。物之用之神是因明觉感应之圆而神而神。明觉之感应处为物。此感应处之物既无‘物’相,即无为障碍之用,它系于明觉而有顺承之用,故其为用是神用无方,而亦是不显用相之用也。明觉感应圆神自在,则物亦圆神自在也。故物不作物看,即是知体之著见也。此是将‘物之在其自己’全系于无限心之无执上而说者。”(同上,第117-118页)这是对王龙溪“无物之物则用神”一句的疏解。在牟宗三看来,知体明觉是智的直觉。智的直觉无封限、无滞碍、不可测度,属于神感神应。神感神应最显著的特点是神用无方,是一种“不显用相之用”。这种“不显用相之用”也就是不受时空和范畴影响之用。时空和范畴是一种执,有执必有相。无需范畴、无需时空属于无执,无执即是没有用相。既然没有用相,当然也就不属于感性直觉,而属于智的直觉了。这一思想后来在《圆善论》中进一步得到加强,但致思方向没有根本性的变更。没有用相由此也成为牟宗三论智的直觉的一个重要理据。
三、“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
对于牟宗三上述思想,我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方面高度评价这一思想的合理性,认为这是牟宗三从其师熊十力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思想,预示着一个极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否则无法继承熊十力学派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对“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的观点,则持怀疑态度,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智的直觉。
根据上面的分析,牟宗三认定“觉他”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核心理由是“觉他”的过程无需范畴。从表面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十分清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觉他”的过程不需要范畴,那么其思维方式就是智的直觉;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觉他”的过程需要范畴,那么其思维就不是智的直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里有一个应该如何理解康德原文的问题。康德讲过,“一旦见不到这种时间统一性,也就是在本体的情况下,范畴的全部运用、甚至它们的全部意义都会完全终止了;因为甚至会根本看不出应当与这些范畴相适合的那些物的可能性”。(康德,第226页)牟宗三非常重视这一表述,以此作为智的直觉无需范畴的重要理据。按照牟宗三的理解,康德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对于本体我们没有感性直觉,没有杂多,既然如此,范畴无法整理感性经验,因而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这种理解在康德那里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是可信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这一理解无限度地扩展,直接以此证明智的直觉的重要标志即是无需范畴。有两种不同情况需要加以分别:其一,对本体不能有智的直觉,是因为我们对本体不可能有感性经验,范畴完全派不上用场;其二,智的直觉是无需范畴的,一旦能够证明我们的思维方式可以无需范畴,那么也就证明我们可以具有智的直觉。牟宗三没有将这两者分别开来,直接以前者证明后者,看到康德讲对本体“范畴的全部运用、甚至它们的全部意义都会完全终止”,便以为一旦我们能够去除范畴,也就做到了智的直觉,从而可以达到物自身(本体),不再局限于现相了。因此,牟宗三的这种理解本身是不无疑问的。
当然,即便我们暂时不计较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诠释的合理性,完全顺着牟宗三的思路走,将智的直觉理解为一种无需范畴,没有“屈曲性”、“封限性”的思维方式,但“觉他”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智的直觉,他的相关证明能不能立得住,仍然是值得商榷的。这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环节需要细加分辨。其一,在康德那里,范畴是先验的,用于在认识过程中整理感性经验的杂多。从这个角度看,由于道德之心创生存有不是康德意义的认识问题,不是以知性范畴整理感觉经验以形成认识,所以不需要康德所说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是正确的。其二,尽管“觉他”的过程不需要作为认识形式的范畴,但这并不等于说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可以完全凭空产生。这就是说,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可以不需要范畴这种认识形式,但不能离开范畴一类的东西。这里所说“不能离开范畴一类的东西”的意思是说,“觉他”创生存有,其本质是以道德之心为主体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这个过程不能缺少道德之心,尽管道德之心在这里不是作为认识形式的范畴出现的。其三,如果承认“觉他”不能离开道德之心,那么其创生存有,对于道德之心来说因为不需要范畴这种认识形式,可以说是做到了没有“屈曲性”、“封限性”,但对于创生的对象来说,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则仍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其过程可以不需要作为认识形式的范畴,但从其对象本身来看,是不是由此便没有了“屈曲性”、“封限性”,可不可以称为物自身,是有重大疑问的。
比如,牟宗三曾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挑水砍柴无非妙道”、“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第21卷,第117页)为例,来说明智的直觉是无需范畴的。一色一香、挑水砍柴、鸟啼花落在没有道德之心圆觉圆照的情况下,只是色香、水柴、鸟啼之自身,没有任何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一旦有了道德之心的圆觉圆照,便改变了性质,成为了中道、妙道、至道,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觉他”最基本的含义,对此不应有任何异议。问题在于,在牟宗三看来,由于自由自律的无限心不是认识之心,不受认识形式的限制,所以思维方式不是物感物应,而是神感神应。物感物应属于感性直觉,与其所对的是现相。神感神应属于智的直觉,与其所对的不再是现相,而是物之在其自己。这一看法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因为不是康德意义的认识问题,的确不需要作为认识形式的范畴,这自然是对的。但不需要认识的形式,并不是什么都不需要。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至少还需要中道、妙道、至道。尽管中道、妙道、至道不同于康德所说的范畴,但在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过程中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离开了中道、妙道、至道,道德之心不可能赋予一色一香、挑水砍柴、鸟啼花落以道德的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一色一香、挑水砍柴、鸟啼花落已经染有道德的色彩,不再是其自身了。这种“染有道德的色彩,不再是其自身”,当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积极方面说,这是道德之心赋予外部对象以价值和意义;从消极方面说,则是外部对象受到了道德之心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其本质而言,其实也是对于对象的一种“屈曲”、一种“封限”,所以绝对不能叫做物自身,只能叫做现相,当然是一种不同于认识之相的特殊现相。牟宗三把智的直觉界定为一种因为不需要范畴而没有“屈曲性”、“封限性”的思维方式,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觉他”的思维方式虽然确实不需要范畴,但仍然有其特殊的“屈曲性”、“封限性”,如此一来,如何能说“觉他”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呢?
“觉他”有无时空性的问题,也应这样看。在牟宗三看来,人既有有限心,又有无限心。有限心决定感性直觉,必须经过时空形式的中介;无限心决定智的直觉,可以不经过时空形式的中介。在自由自律无限心的创生下的存在是没有时空性的,即所谓“无时空性、无流变相”。因此,面对有限心所展现的是受时空形式影响的样子,即所谓现相;面对无限心所展现的则是物自身原本的样子,即所谓物自身。换言之,感性直觉与智的直觉之所以不同,一个重要标志是看有无时空性。感性直觉必须经过时空形式,而道德之心“觉他”并不需要这些认识形式,所以“觉他”是智的直觉。我对这种看法是存有疑问的。这里仅以时间为例加以说明。道德之心有感通觉润之功,其极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感应于孺子,即与孺子为一体,而孺子得其所,“感应于鸟兽、草木、瓦石,亦皆然”。(第21卷,第458页)这是牟宗三一再强调的思想。这个意思从理论上说,其实就是道德之心赋予万物以意义,创生万物之存有。因为这里谈的不是认识问题,所以与作为感性直觉形式的时间没有关系,这自然是对的。但需要注意,尽管“觉他”不需要借助作为感性认识形式的时间,但并不是完全可以脱离时间。这里仍以上面所说的“感应于鸟兽、草木、瓦石”为例。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就是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鸟兽、草木、瓦石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道德之心本身有时间性,所以在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之上的时候,也就将时间的属性加入其中,使得鸟兽、草木、瓦石在人的时间条件之中得以存在。牟宗三非常喜欢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第29卷,第310页)的说法证明智的直觉,但如果静下心来细心体味,不难看出,这句话刚好成为反驳牟宗三的证据,因为这后面一句本身就与时间脱不了干系。“四时佳兴”何以能够与人同?关键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一定是在时间中存在的,有其时间性。一旦成德行善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其内在的时间性便与天地四时合为一体,“四时佳兴与人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可见,道德之心创生存有是无法脱离时间的,尽管这种时间与作为感性直觉形式的时间有所不同。
没有用相的问题要稍微复杂一点,需要转个弯子。如上所说,牟宗三关于没有用相的论述主要是在分析王龙溪四无时讲到的。在他看来,四无中最重要的是“无物之物”。“在浑化之境中,仍然有物。但此物是无物之物,物无物相。王阳明亦说‘明觉之感应为物’,此物即是无物之物。无物相者是说此物既无为良知所知之对象相,亦无善恶意中之正不正相。‘意之所在为物’,此物是经验层上的物;‘明觉之感应为物’则是超越层上的物。若用康德词语说之,前者是实践中现象义的物,相应于有善恶相之意而说者,后者是实践中物自身义的物,相应于明觉之感应而说者。”(第22卷,第309-310页)浑化之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而化之”,将大化掉,大无大相。在这种境界中,当然仍然有物,不过这时的物再无物相,这就是所谓的“无物之物”。牟宗三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意之所在为物”,一是“明觉之感应为物”。“意之所在为物”之“物”是经验层上的物,“明觉之感应为物”之“物”是超越层上的物。在超越层上,只能讲神感神应。神感神应不再受时空和范畴的限制,感无感相,用无用相。因为不再受这些认识条件的局限,达到了无执无相,其思维方式当然也就不再是感性直觉,而是智的直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牟宗三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我坚持认为,王龙溪讲的四无只宜理解为道德之无相,不宜理解为存有之无相。道德之无相是说人的道德在达到一定境界后,便会出现无心为善而成善,无心为德而成德,一切皆是自然,一切皆是无执,外面不显道德之相的情况。王龙溪所说的四无正是指的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与存有是否有相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应该分别看待。牟宗三不是这样,他强行将这些材料运用到存有论上来,以四无来说没有用相,进而证明道德之心创生存有是智的直觉,其所得到的对象是物自身的存在。认真分辨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以道德之无相来证明存有之无相。道德存有是由道德之心创生的,这种创生就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象,使其带有自身的痕迹或色彩。这种痕迹或色彩本身就是一种相,并不是什么无相。道德之无相是无法证明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对象也是无相的。以此来说智的直觉,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理解。(参见杨泽波,2009年)
综上,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理解与学界的通行理解有很大不同。他着重从“屈曲性”和“封限性”而不是“本源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按照他的理解,智的直觉简单说即是一种无需范畴、无需时空、没有用相的直觉。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楚的了解,不然很难对牟宗三思想进行有的放矢的批评。但即使我们暂时接受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理解,抛开这种诠释与康德哲学基本精神是否吻合不论,他所列举的“觉他”属于智的直觉的理由,仍然很难成立。“觉他”就其本质而言,是道德之心赋予外部对象以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将自己的道德内容影响外部对象。这种情况从正面说是赋予对象以价值和意义,从反面说则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象。既然是施加了影响,对于外部对象而言就是一种“屈曲”、一种“封限”。虽然因为这里的主体不是认知之心,而是道德之心,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这些认识形式,其结果不是形成一般的现相,但不形成一般的现相并不等于不形成特殊的现相。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认识的现相,未必就是物自身,而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现相,仍然属于现相的范畴。以此反推,既然道德之心“觉他”的对象仍然是一种特殊的现相,属于现相的范畴,并不是什么物自身,那么其思维方式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牟宗三所理解的那种智的直觉。一言以蔽之,即便我们充分尊重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诠释,“觉他”也是需要范畴、需要时空(当然并非是认识意义的)、有所用相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其所理解的无“屈曲性”和“封限性”的智的直觉也不相符合。因此,“觉他”的思维方式既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也与牟宗三所诠释的智的直觉不相吻合,是不能叫做智的直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