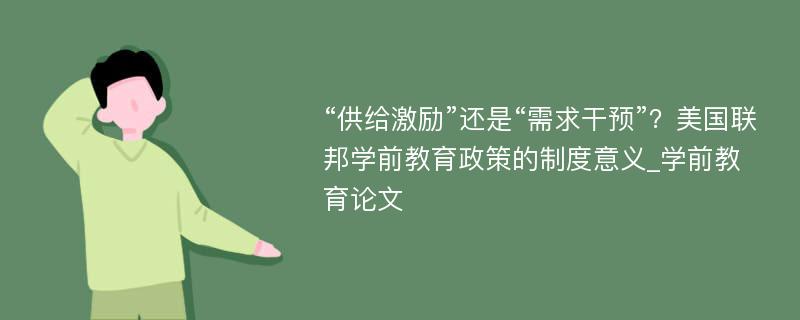
“供给激励”还是“需求干预”?——美国联邦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前教育论文,美国联邦论文,意义论文,需求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前教育公共政策一直存在两个落脚点完全不同的战略,即“供给激励”和“需求干预”。“供给激励”(supply-side incentives)是指通过激励地方政府和市场建设更多的学前教育服务机构(公办或民办),进而增加学前教育服务供给的战略,其产出以机构数和在园儿童数衡量。“需求干预”(demand-side incentives)是指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激励家长做出接受学前教育的决定,它的产出往往表现为满足条件的家庭接受服务的数量和比例。 世界银行在总结过去20年来公共福利的实施经验时,指出了影响服务分配效率的一个教训,就是本来应该把对目标对象(clients)的服务作为产出,结果在实施过程中,产出目标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对机构(facilities)建设的诉求,这是公共福利建设简单化战略的后果[1]。 和世界银行总结经验时所提及的国家不同,美国联邦政府学前教育供给模式采取的是“需求干预”。不过,美国联邦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采取这种“需求干预”模式,它也一直试图建立联邦学前教育体系。在过去近百年来一次次努力失败后,美国联邦政府反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看上去,好像美国联邦政府不知不觉中避免了“供给激励”的低效率模式,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实际上,这种选择背后有着深厚的价值观基础。因此,在大家对我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实施方式存在一些质疑时,去深入理解美国走过的道路,才能真正地全面理解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而不是仅仅表面上知道美国联邦政府现在的做法。 本研究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美国联邦政府在面对学前教育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时,建立完整服务体系的“供给激励”式努力不断受挫的过程;第二部分则分析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支持中低收入家庭学前教育需求的路径;第三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意义,说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应该注意到新公共行政的趋势,即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利用政策工具调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 一、“供给激励”:屡次受阻 和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适当的资源,只在一个家庭或者国家危难之时提供帮助,政府福利性的学前教育资助仅限于部分问题家庭(Cohen,1996)[2]。但随着社会发展,美国拥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就业率已经接近70%[3],这些女性面临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激烈矛盾,学前教育服务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 (一)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增加学前教育供给的思路 在美国,联邦政府举办的免费幼儿园一直是具有慈善性质、面对低收入家庭的。随着妇女就业不断增长,美国社会产生了将免费儿童中心扩展至所有人群的需求。于是,推动学前教育立法,就成为首先要完成的工作,国会一旦通过了关于教育的立法,联邦政府可以在预算中列出扩大免费儿童中心的经费,各州议会也会根据该法律,制定相应的规划。免费公共教育K-12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这种“供给激励”的政策推动方式遇到了阻碍。虽然经历了妇女解放运动,但是,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传统依然非常顽固,坚持政府投入的免费儿童中心只能针对低收入人群。从上世纪60年代起,女性主义、劳工领导、民权领导和儿童学前教育的倡导者不断游说国会,希望将学前教育作为所有儿童的权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联邦政府资助的儿童看管中心,将服务扩展到所有人群。半个世纪过去,这个法案曾经十分接近实现,但最终功败垂成,令人唏嘘不已。 (二)立法努力遭遇挫折 在全世界范围内,上世纪60年代都是社会福利最慷慨的年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在美国,1966年,由职业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组成的全国妇女组织诞生,美国妇女运动拉开帷幕,女性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1950年,拥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在劳动力市场只占1.9%,197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0.3%[4]。妇女就业渐渐被认为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现实。1965年,约有10%的3~4岁儿童进入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1970年,上升为25%。虽然开端计划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增长,但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学前教育项目已成为社会现实[5]。 经过多年的院外游说和社会发动,1971年,Harris民意测验发现64%的妇女和51%的男人支持建立更多的“儿童日间照看中心”[6,7]。妇女组织和劳工组织的代表都认为推动立法的时机成熟了。 1971年,广覆盖的学前教育法案(CDA,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被提交到国会。法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联邦政府资助的儿童看管中心,并对年收入在6960美元以下的家庭免费开放①,对高于此收入的家庭实行浮动收费。法案在参众两院引发激烈讨论,最终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但在白宫内部遇到了保守主义的阻挠,认为它削弱了家庭,违背了美国基本价值观。最终,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该法案,“轻率地投入财力支持儿童发展,会使政府遭受巨大道德批判,批评联邦政府倾向公共模式的儿童养育反对家庭为中心的养育模式”[8]。立法首次遇阻,强化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家庭观:幼儿的教育和保育主要被视为单个家庭运作的私人事务,不需要很强的公共责任。 (三)福利改革逼迫已有的“供给”体系不断收缩 美国联邦政府的学前教育服务,是带有强烈慈善色彩的、仅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免费服务体系,提前开端(head start)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将这种福利扩散至更广泛的人群时,受到了保守主义的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学前教育也一再受到来自财政、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不断变更目标群体的范围。 在福利社会的巨大债务压力下,自上世纪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观,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盛行,裁减福利成为减少政府债务的重要手段之一。1988年,美国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就业率为56%,很多人反对联邦政府资助贫困家庭的母亲使用补贴资金在家养育孩子。于是,国会通过了家庭支持法案(FSA),要求这些母亲参加教育、培训或工作,并将此作为接受福利的必要条件[9]。 1995年,31%的0-6岁儿童进入看管中心,年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家庭能够负担看管中心项目,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免费加入开端计划。但是,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但在贫困线以上的工薪家庭最没有能力支付看管中心的费用[10]。福利改革将依赖资助的家庭推向了劳动力市场,高额的学前教育成本使这些家庭在养育儿童和外出工作之中挣扎。 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普及性学前教育立法遇挫,以及慈善性学前教育收缩等经历,如果我们能够超越简单地“好”还是“坏”的评价,认识到保守主义的主张也有合理性,意识到多种政策目标之间可以存在矛盾,我们就会发现,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不断增长的需要,与保守主义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妥协空间,这种状况会激发公共政策告别简单战略,更加理性地、创新性地开发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 二、需求干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 在社会需求和保守主义传统的双重挤压下,美国联邦政府的制度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满足社会需求,支持女性就业,就要获得立法支持。如果迎合保守主义观点,则要面对众多家庭的需求得不到帮助的压力,任由这些家庭在工作和养育儿童间挣扎。于是,联邦政府不得不在保守主义的“主色板”上,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不断在这个主色板上“涂抹”,力求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维护平衡,实现社会互动。 当扩大供给的方式不可行时,美国联邦政府将政策转向需求干预。需求干预的政策工具一般是税收、补贴等经济干预手段,以及认证、监管等管理手段和社会组织、动员等社会管理手段。 (一)经济工具:对不同家庭的多类别补助 美国政府(包含联邦、州、地方政府)对儿童看管和教育的资助非常多样化和有针对性,大约四分之一是以税收补助的形式支持中上层家庭选择私人性质的儿童看管机构,四分之三的资助是以支出补助的形式广泛支持中低收入家庭。 1.税收补助 一个社会中,缴纳收入所得税者通常是中高收入家庭,通过税收政策补助家庭的学前教育支出,是联邦政府将政策支持给予“非贫困家庭”的主要渠道。比较有影响力的项目有两个:儿童看管税收抵免(CDCTC,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和未成年子女看管援助计划(DCAP,Dependent Care Assistance Plan)。前者按照家庭收入,以不同比例抵免联邦税收,后者对商业机构进行资助。凡参加该计划的企业,其雇员每人每年可有5000美元的税前收入用于儿童看管,免收入税和社保税。这样,雇主通过援助计划节省了社保税,雇员减少纳税收入。这对纳税额高的人群提供了较大利益。 2.支出补助 和直接供给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税收补助瞄准人群为中高阶层相比,联邦政府的支出补助在服务人群上比较模糊,虽然也有专门针对贫困家庭的补助,但也有一般性的、针对所有人的补助。 1995年以来,“开端计划”成为联邦政府资助金额最大,以单一税收和单一支出为基础的针对贫困家庭的儿童发展项目。而儿童保健和发展整体补助款(CCDBG,The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高危儿童保健(The At-Risk Child Care)、过渡时期的儿童看管项目(TCC,The Transitional Child Care)都从不同的方面为不同类型的贫困家庭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与以上以贫困家庭为对象的项目外,儿童和成人食品计划(CACFP,The Child and Adult Care Food Program)补偿合法经营的保育中心、集体日间照看的家庭和开端计划中心的用餐、零食和营养教育成本,这是一个针对所有家庭的支出补助。1994年,总会计署(GAO,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报告显示,联邦政府11个机构和20个办公室开展了90多个联邦资助的儿童看管项目[11]以上6个项目占据联邦政府80%的资助。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David M.Blau(2003)对美国当前的儿童养育和学前教育补助项目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发现对儿童养育政策的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补助的资金不足难以实现福利改革的目标、补助分配的不公平、使用补助购买的儿童养育服务的质量问题。对于改进儿童早期养育和教育项目的建议也分为两类:一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以低收入家庭为瞄准对象的项目补助,更多地强调家长的自由选择,就业导向大于儿童发展导向。二是由儿童发展专家倡导的强调普惠性和供给激励的补助方式、与养育质量(而非就业)结合更紧密的项目机制。最后,作者认为未来的儿童养育政策还将会继续在帮助母亲就业和增强儿童早期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争论[12]。 (二)管理工具:标准管制和认证 除使用经济工具支持家庭的学前教育需求外,管理工具是未被充分认识到的需求干预的政策工具。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经典经济学理论建设市场无交易成本,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交易成本大到“供求交易”无法进行。儿童看管就是典型的案例。没有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儿童看管的市场就会因为不信任而无法形成。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制和认证。管制工具主要有进入、价格和标准管制,认证则是行业协会或者政府用自己的信誉证明某机构已经达到管制标准[13]。1984年,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在会员、家长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颁布了一个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机构的认证标准。《评价标准》分十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包括目的、理论依据以及具体的评价指标。引入认证和监管,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就可以使一些原来不可能的交易活动发生,促成儿童看管的市场转化为有信心的实际的市场。 认证和评估是政府对于学前教育和看管服务质量进行管理的政策工具,它与多样化的资助同时发挥作用,可以在联邦政府不直接举办幼儿园的情况下,对多种形态的学前教育和看管机构进行监管,不仅实现了“管、办、评”分离,而且保证了多样化的业态,既有私立幼儿园、政府办的免费儿童中心,也有非营利组织举办的幼儿园;既有幼儿园,也有儿童看护中心以及经过认证的家庭看护,一个妈妈或者退休教师,只要通过了“认证”,就可以为社区内、邻里间3岁以下儿童的家长们提供放心服务。 上世纪60-70年代的“伟大社会”运动,奠定了美国联邦政府社会福利的基础框架,也带来了沉重的福利负担。1973年,社会福利支出合计高达GNP的17.6%,占各级政府支出的55.0%,占联邦支出的49.6%[14]。随后到来的经济滞涨和“失去的十年”,让美国各界意识到社会福利的代价。1981年2月,里根提交了《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之一便是大幅度消减社会福利开支。学前教育支出不再增加,但学前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在发生变化。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在全球的推行,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直接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是非常昂贵的服务,政府做好监管角色,可以提高家长和多种类型学前教育机构间的信任关系,改善市场供给的效率。 (三)基础性制度工具:跨部门预算 严格地说,跨部门预算并不是一个政策工具,因为它并不针对某个部门或者某类家庭,而是在国家层面上打通部门之间协作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预算系统,被称为关于目的及实现手段的选择系统[15],因此,联邦政府的支出预算是按照功能划分的,先列出预算,再决定由那个机构执行。 美国对学前教育的直接拨款较少,仅限于“处于危险之中”的儿童。美国滞胀危机后,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别缩水,社会福利政策对这类家庭的资助非常不足,受“挤压”的现象明显。“许多工作的工资都很低,或者正在裁员。许多中等收入家庭的父母都付不起一个月600美元的日间看管账单。”[16]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复苏方案中,会经常包含对美国社会庞大的工薪阶层家庭儿童看管的资助。这时,联邦政府对于家庭学前教育需求的干预工具,就是典型的跨部门预算,它目标指向家庭的学前教育需求,不仅通过教育,还通过劳工、就业和公益途径到达需要的家庭。 家庭需要的公共服务往往是跨部门的,但是,专业部门难免用自己的业务范围去“裁剪”社会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尝试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工作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只有实现了跨部门的预算机制,才能真正将各个部门统一到支持家庭的学前教育需求上来,才能实现学前教育政策服务于儿童,同时发挥对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的杠杆作用。 三、主要结论及制度意义 如果站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坏案例”。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妇女争取走出家门的上世纪60年代,到女性已广泛就业的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盼望的学前教育服务广泛覆盖的目标至今没有实现。 如果站在制度创新的角度看,美国联邦政府在没有直接提供学前教育的权利,也没有要求州政府提供的权利的情况下,在一个狭窄的制度空间中,联邦政府反而开辟了通过“需求干预”对家庭的学前教育进行支持的道路,具有两个不同于政府直接“供给”模式的制度意义。 (一)政策工具的创新直接影响政策效率 政策工具(Public Policy Instrument,Policy Tool)又称治理工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它深受公共选择经济学派的影响,把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及组织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管理技术上有所创新,而且也在政府治理的观念和制度上有所创新[17]。 近年来,新行政主义越来越强调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创新,美国联邦政府在支持家庭的学前教育需求时,所用政策工具涉及主要的工具类型,包括了管制、补贴、减免和社会动员等,也包括认证、多政策杠杆等。政策工具强调在行为分析基础上,依据人或者机构的动机,设计合适的政策工具,用政策工具激发个人和组织的合适行为,实现自动实施、精准化[18]。 合适的政策工具设计可以减少执行成本。广泛覆盖的免费儿童中心,作为联邦政府扩大供给学前教育服务的实施方式,政策工具简单、明了,但是,该实施方式与保守主义观念形成激烈对抗,也面对政府之间、政府与公共部门之间低效率的管理难题。因此,放弃简单化的实施方式,寻找更合适的实施工具就是行政理性的体现。 我们对于美国联邦政府学前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不是因为美国学前教育供给水平高、覆盖广,而是因为美国的学前教育发展在有限的制度空间内完成了政治妥协和技术创新。因此,对于政策工具的分析应当超越经验和事实层面上的片段式“借鉴”和“学习”,分析政策工具背后的制度意义,这是系统化制度设计的前提。 (二)妥协是政策工具创新的前提和跨部门合作的基础 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学前教育政策变迁,生动地展示了公共政策的本质——妥协,完美的目标设定远不如互相妥协更加符合社会认知的达成过程。保守主义家庭观是美国社会的传统,与广泛覆盖学前教育服务的福利观有明显的冲突,但是,基于刺激经济和帮助中低阶层家庭儿童养育的支出却符合保守主义的思想。教育部门作为专业部门,肯定会从儿童成长的角度思考制度设计,要求教育部门改变自己的思考范式,将学前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劳工福利政策结合起来并不现实。但是,美国广泛覆盖的儿童中心建设的立法过程屡屡受挫,却避免了用完美的目标去裁剪现实,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设计合适的手段,促进社会各组成部分的良性互动,“夯实”公共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在技术上,热衷于设计多样化的、恰当的政策工具,在直接政府供给之外,开辟了广阔的政策空间。 在我国,借助公众对学前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学前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先关注地位,也连续实施了两期行动方案。但是,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中的一些问题,却让我们看到了教育行政部门抑制行业发展冲动,学会在政策目标上妥协的迫切性。学前教育供给要增加,但也要重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小心翼翼避免对民办教育市场“挤出”效应。 无论是分权政体还是集权政体,政策工具的功能在于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目标,因此政策工具的特征必须与政策目标相匹配。和美国联邦政府相比,我国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在大力推进下,学前教育服务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但政策却比较简单和单一。简单化的实施策略实际上在透支政府的权威,来弥补政策工具的简单化带来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如与家庭合作、满足家庭多样化服务需求的能力都差强人意。 最近,财政部、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222号)明确将政府资金划分为“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和“幼儿资助”类项目资金,并用不同的方法管理两类项目,让我们看到了由供给激励向需求干预的转变迹象。学前教育公共政策,是良好愿望的表达,更是技术理性和不同目标间的妥协,不过度透支政府权威,学会创新政策工具,对实施中的问题始终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是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水平的前提。 ①1969年,美国的贫困线标准是4口之家的收入3,743美元,见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no.37,24 June 1971,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