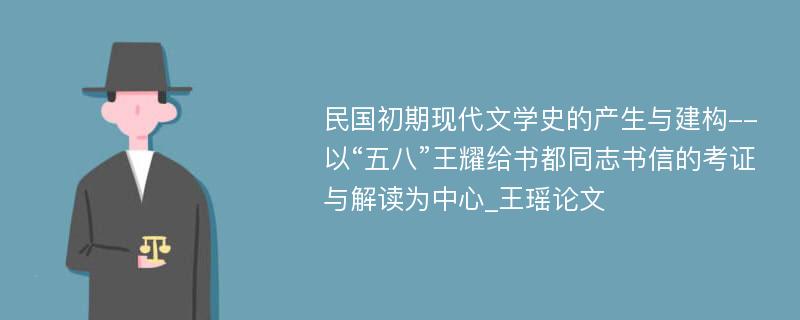
共和国初期现代文学史的生产与建构——以五月八日王瑶致“叔度同志”信件考释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国论文,文学史论文,信件论文,初期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十二月即印第二版,两版印数总计为八千册(第一版印五千册,第二版印三千册)。此书为王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讲义稿,“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①王瑶声称,此书严格按照一九五○年五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有关《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规定进行撰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中国新文学史稿》印刷之前(指的应为初版本),王瑶曾得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同事李广田、吕叔湘、吴组缃、余冠英等先生的鼓励和帮助,还在《进步青年》先期刊发过部分章节,这些章节包括《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等。不过,《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后,王瑶“不断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② 一九五二年一月,全国文艺界、京津高等教育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中,王瑶本人受到很大的“冲击”,撇开思想问题方面的复杂性不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这部著作,“新文学史班上我讲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的时候,虽然批判了那些内容,但又肯定了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③进而对他自己的思想观念做出反省,“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文艺修养太不够,没有能力做这样一件比较重大的工作;但根本上实在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我痛感到如果不认真彻底地改造自己,是什么工作也做不好的”④。八月三十日,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试图纠正王瑶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叶圣陶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吴组缃、李何林、孙伏园、林庚、李广田、臧克家、钟敬文、黄药眠、孟超、蔡仪、杨晦、袁水拍、王淑明、傅彬然、金灿然、王次青、唐达成。当天的日记中,叶圣陶这样写道谢: 此书为大学所通用,所述又为至关重要之文学,故特取为批评之对象。……综合诸人之见,大致谓此书立场观点不稳,编撰方法失当,为参考资料尚可,实不合称文学史。此事本未宜以个人之力成之,而王搜辑颇勤,成书甚快,以致种种失误。⑤ 从与朱自清、闻一多的亲密关系上来说,叶圣陶也会保护朱自清、闻一多的这个年轻且有为的学生。叶圣陶所说的“此事本未宜以个人之力成之”,可说抓住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要害”,新文学史的撰写不是一个人的“名山事业”。而《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大学所通用”的著作,其谨慎的程度甚为关键。王瑶受到的压力着实不小,曾有“王瑶要求专业,做不了灵魂师”的传言。⑥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时间最密切的信件,应该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之后王瑶与他人的通信,或许我们能够从中看出部分端倪。 一、王瑶致叔度信件的真正写作时间 翻检二○○一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八卷本《王瑶全集》,第八卷的书信选中,收录了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王瑶给“叔度同志”的一封信。王瑶在信件中谈的内容,正是有关《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相关问题。其实,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来看,此信的文学史料价值、现代思想史价值倒是值得重视的。这里先对此信做抄录,全文如下: 叔度同志: 来函敬悉。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问题,今年暑假高教部将在北京召集会议讨论,并订出“教学大纲”,届时各大学讲授本课的教师将皆来出席,想来定能有机会向您当面聆益。 谢谢您对拙著的关心。所提供的意见也对我帮助很大。其中有我也考虑到的,略说明我的意见如下: 1.《老张的哲学》就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论,恐尚略迟,合在一起叙述比较方便,因为此书并不高明。 2.湖畔诗人拙作中略有所述。 3.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 4.艾青《吴满有》是因为所写的人物发生了问题,我曾问过艾青同志,他不主张讲。 其余的有的是我根本没有看见过,或找不到,有的是故意省去了。您所提的《中国青年》我就没有找到,后来在张毕来同志的文章中才知道的(见《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承惠寄赠您辑的《中国青年革命文学论集》一册,敬此致谢。您的许多意见、材料和您将要送给我的书,无疑对我的工作将有很大帮助。 我工作的地方是北大中文系,与北大文学研究所是两个单位。文学研究所中没有现代文学组,由陈涌同志负责,另外还有几个刚毕业的见习研究员(助教),这一组成立后不久,他们目前的工作计划是研究重要作家的作品,首先进行的是下列八人:1.鲁迅2.瞿秋白3.郭沫若4.茅盾5.丁玲6.巴金7.老舍8.赵树理。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以后当然是可能增添研究人员和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的,但目前还谈不到(文学研究所中的同志不参加教学工作)。 耑此,即颂 王瑶 五月八日 此信列为书信选第二封信。在《王瑶全集》整理者看来,它是王瑶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写给“叔度同志”的信。从信件的相关细节来看,这封信的时间标注显然出了错,理由来源于几个方面: 其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初版时间为一九五一年九月,第二版的出版时间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也就是说,写信者“叔度同志”不可能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之前就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这部书籍。按照常识来推算,至少此信应该在一九五一年以后的某年五月八日写成,而不会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这天所写。 其二,王瑶在信中说“我工作的地方是北大中文系,与北大文学研究所是两个单位”,已经明确地说明,写此信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而他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时间,为一九五二年九月之后,“清华大学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先生的工作安排在北大中文系”。⑦这排除了此信写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日的“可能性”。 其三,信件里所说的“北大文学研究所”,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简称”,最初它隶属于北京大学,系北大的下辖研究机构,它成立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建构四大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时,北大文学研究所归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称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时,结合“北大文学研究所”拟重点展开对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赵树理等作家进行研究来看,此时丁玲并没有出现政治问题而卷入后来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件中,对她的作品进行重点研究,也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应有之义”。同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王平凡先生回忆,“北大文学研究所”实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创建了现代文学组,组长正是杨思仲(陈涌本名),他担任组长的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陈涌被错划为“右派”,现代文学组组长的领导职务亦被解除。王平凡特别说明,“回顾文学所的历史,他(指陈涌)是不能被忽略的重要学者”⑧。这也排除了此信写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的“可能性”。 其四,信中提及对艾青的长诗《吴满有》的处理问题。查《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不管是初版本还是修订版本,有关艾青的文学史叙述,根本没有涉及一九四二年以后的诗歌创作。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初版本的出版时间(一九五一年九月),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内容与此信的写作时间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修订再版本出版于一九五三年七月,改由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从王瑶给“叔度同志”的回信来看,“叔度同志”给王瑶写信时,他已经看到《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具体内容,从而才针对王瑶在处理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著作的第十七章《人民翻身的歌唱》之第二节《长篇叙事诗》)时,著作中没有谈及艾青的另一部叙事诗《吴满有》而提出了“异议”。《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脱稿时间,是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依据《王瑶年谱》,不过王瑶也有“今年二月初下册始脱稿”的说法),因“当时文艺界正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整风运动”“接着学校也展开了教师普遍检讨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当中他提及“限于自己的认识和水平,又感到不知究应如何修改”,下册的出版时间则延迟至一九五三年八月,“叔度同志”不可能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前读到《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相关内容。同样,这也否定了这封信写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日、甚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八日的“猜测”。 排除了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日、一九五三年五月八日、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写作此信的“可能性”,王瑶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给“叔度同志”写了这封信呢?看来,要确定这封信的真正写作时间,我们还得回到信件开头的这一句:“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问题,今年暑假高教部将在北京召集会议讨论,并订出‘教学大纲’”。查《人民日报》有关教育部制定教学大纲的会议,我们发现,教育部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就在严格规范高等学校各学科的课程教学,特别是课程的教学大纲制定本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举办全国综合大学教学研究座谈会,“会议拟持续近一个月”,这不正是王瑶信中所说的“暑假”吗?有关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座谈会将确定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英国语言文学、生物等专业计划,并修订《解析几何》《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等十六种理科课程的教学大纲和《中国文学史》《文艺学引论》等文科课程的教学大纲”⑨。《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显然也在这一范围之内,因为从王瑶信中所说暑假将在北京召开关于教学大纲的会议来判断,这封信写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已经确定无疑。显然,《王瑶全集》在编著时并没有从书信的具体内容来推断书信的真正写作时间,而是假定为“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二、信件细节:共和国初期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的生产与建构 王瑶五月八日给“叔度同志”信的写作时间确定之后,我们把它放置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文学环境中,还能细细窥探共和国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新文学史》)的文学史生产与建构的若干信息。 一是关于李辉英。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作家,李辉英的文学成就不容低估,他一九四九年前先后创作的作品有:《万宝山》(长篇小说,1931)、《两兄弟》(短篇集,1934)、《丰年》(短篇集,1935)、《山河集》(1937)、《北方集》(短篇集,1937)、《火花》(短篇集,1940)、《夜袭》(短篇集,1940)、《松花江上》(长篇小说,1945)、《复恋的花果》(长篇小说,1946)、《雾都》(长篇小说,1948)等。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课程讲义中,其实已经注意到李辉英的文学成就。《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初版本(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月)中,王瑶对李辉英评价颇高:“其中比较早的一个作家是李辉英,他的长篇《万宝山》是企图把日帝积年的经济掠夺来解释‘九·一八’之前的万宝山事件之成为人民反日斗争的大运动的,但并没有写得很成功。一九三三年他又回东北看了一次,写了短篇小说集《丰年》,序中作者向自己说:‘你该把那种书写闲情逸致的笔调,变为反抗敌人的武器!譬如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压迫,屠杀,欺骗我们弱小民族的人类事情。同时你也应该抓住现实社会的某一点,说上一些该说的话。’这书就是他所说的实践。其中《丰年》一篇写的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的故事,爱和平的老农夫孙三怎样从事实教训中由落后而认识了必须参加抗日的过程。《修鞋匠》是写东北的一个修鞋匠因日本橡胶套鞋大量倾销,而他不会修补,遂由愤懑而自发地反抗那干涉他摆摊子的警察。另一篇《乡下人》写青年学生的地下反日运动。题材都是有现实意义的,作者也有激昂的情绪,文字中用的吉林土白也适宜于表达当时的情状,应该是写得很好的,但作者的思想性不强,只能表面地介绍出现象,感人的力量就差了一点。”⑩李辉英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早期成员,曾与鲁迅有交往,也是北方左联的重要成员,按理说很有资格进入革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但此时李辉英身处非共产党的统治区,特别是他一九五○年离开东北大学前往香港后,还在一九五二年十月随香港文化界访问台湾(其实从后来大陆对李辉英的态度来看,他一直作为共产党潜伏在香港的文化人士而展开实际文化活动)。这在文学史家王瑶看来,李辉英的行为无疑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为避免《中国新文学史稿》书稿引来政治性问题,他不得不做出删除,在修订版中,彻底抹去了李辉英的名字,更没有提及他的创作情况(11),并特别标明:这是因为作家“政治上有问题”。李辉英七十年代对此也有自己的回应,“我想,倒怕是因为我已在这期间来到了海隅——香港了。一个离开了内地远适海外的文人,删除了与他有关的两段文学史上的文字,不也十分的公平么?”(12) 二是关于艾青的长篇叙事诗《吴满有》。《吴满有》创作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最初连续刊载于延安《解放日报》,是艾青在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创作中的代表性作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此书由三部分构成:《编者的话:关于文艺的“新方向”》、艾青《吴满有》、柯蓝《吴满有的故事: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这个版本的作者署名颇为奇怪,其名字为“艾青等”。在《编者的话》中,对长诗《吴满有》有这样的评价,“艾青的《吴满有》,被推作是朝着文艺的‘新方向’发展的东西,这是凡是读过《新华周刊》上解放日报社论的,都知道的了。这里,我们介绍了原文,希望读者读过这首诗以后,对于‘新方向’来个研究,得出具体的比较切实深刻的结论来,把‘新方向’三个字咬破。”“我们付印这个小册的第二个用意,正如解放日报所说:‘艾青的《吴满有》,从艺术体裁上说,完全是新的,既不同于历史上的诗、赋、词、曲,也不同于今天民间的唱本、小调,但是因为它有了群众的生活,用了群众的语言,吴满有和其他劳动群众就都能够加以理解和欣赏。’——是的,我们正在期待着这个小册子能够走到本区的吴满有和吴满有的无数伙伴们的手里去;倘因此而能稍稍引起他们劳动和创造的热情,那更是意外的收获了。”(13)放置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前后的作家转变来看,长诗《吴满有》也算是艾青得意之作。但吴满有身上的“疑点”(抑或说是“污点”),使诗人后来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写作过程中曾专门问及诗人本人可不可以讲这个作品。不过,艾青坚决拒绝,“他主张不讲”。这从侧面反映了艾青在中国新诗史、新文学史叙写中的自我规避意识,也是诗人回避政治敏感的一种自我保护。即使到一九五四年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艾青诗选》,他也没有让《吴满有》进入自选集中。臧克家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代序《“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也刻意回避了艾青的这首长篇叙事诗。这说明长诗《吴满有》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学史规范中,它潜藏的异质性和危险性不仅被诗人艾青所注意,也为文学史家王瑶所关注,同时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中被臧克家故意遮蔽掉。 三是关于新成立的北大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的“研究计划”。王瑶在给“叔度”的信中谈到,“他们目前的工作计划是研究重要作家的作品”,而被列入重要作家的,一九五四年三月成立现代文学组时就已经确定了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赵树理这八位作家。这或许是北大文学研究所这一学术机构在五十年代有关新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中的秩序建构,也是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秩序排列中“鲁郭茅巴老曹”的最初雏形。赵树理作为解放区重要作家,显然在新文学史建构的过程中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他的作品不仅列入解放区文学创作的重要展现(进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而且在共和国初期建构的大型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时,他也是当然的“编委”。赵树理列为重要作家,这也是我们面对一九五一年七月开明书店陆续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时可以看到的“细节”,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入选“新文学”序列的唯一作家(丁玲因成名于三十年代,不能列入解放区真正成长起来的作家)。王平凡先生在回忆北大文学研究所时,特别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14)它已经表明,这和意识形态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所中的同志不参加教学工作”已经表明,在北大文学研究所的所有研究人员,其实是专职科研工作人员。这些科研工作人员遵照文学所的总方针进行科研工作,“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最初成立北大文学研究所时,设置的研究小组共有八个:文学理论组,组长蔡仪;古典文学组,组长余冠英;中国文学史组,组长何其芳;现代文学组,组长杨思仲;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组长贾芝;西方文学组,组长卞之琳(15)。其实,各组研究人员在共和国初期的学术生产、体制建构、意识形态生产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四是关于老舍早期创作的“评价”。很清楚,“叔度同志”在致王瑶的信中,表达了他对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处置《老张的哲学》这部小说的方式的“异议”。王瑶在回信中说到,“《老张的哲学》就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论,恐尚略迟,合在一起叙述比较方便,因为此书并不高明。”这其实表明了王瑶的一种学术态度,他并不认可老舍早期文学创作有巨大的成就,对早期创作中如《老张的哲学》这样的作品,他保持着清晰的批判态度:“但笑料太多,描写也过于夸大,讽刺便有点失去了力量”。(16)这正是《老张的哲学》并不高明的地方。即使在一九八六年为《老舍选集》写序言时,王瑶仍旧回避了对老舍早期的文学创作的关注,文中重点评点的作品,其实还是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颇有特色的作品,包括:《月牙儿》《骆驼祥子》《小人物自述》《我这一辈子》等(17)。尽管后来的文学史著作(如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对老舍评价有所提高,但涉及他早期的小说《老张的哲学》等作品,文学史家们仍旧没有脱离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初版本中的那种定位:“早期写的长篇小说,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大都是写作者‘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其中虽然也有着作者‘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有着‘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的‘意思’,因为作者是那样‘抱住幽默死啃’‘油腔滑调’不免遗给作品以浮浅的毛病”(刘绶松)(18);“由于属于小市民层的‘命该如此’的看法,那么这一点‘委屈’和‘反抗’也就往往以小市民趣味的滑稽幽默态度出之,倒反削弱了反抗的力量,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他的初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丁易)(19)。 值得注意的是,此信的内容在辨别上还有一个小问题。信中“文学研究所中没有现代文学组”一句,显然是编者对原信件文字的“误植”。按照信件中所谈的“现代文学组”相关话题,应该为“文学研究所中设有现代文学组”,才真正符合北大文学研究所这一学术机构创办的基本情况,和信件中谈及的拟开展的“工作计划”。而这个“现代文学组”,正是由陈涌(杨思仲)具体负责。此前,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编纂工作中,陈涌因杂事没有参加(20)。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陈涌的确在鲁迅研究中颇为用功,先后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过《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意义》(1954年第11期)、《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1956年第10期)等高质量论文。 结语:未结束的考证 回到《王瑶全集8》收录的《致叔度》这封信的抬头上来,王瑶此信寄送的收信人“叔度同志”到底是谁?查部分文献材料,取名“叔度”的人有这样两位:卢叔度、刘叔(淑)度。卢叔度(1915-1996)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于中山大学,与王瑶的同学吴宏聪、陈则光曾为同事,他专治先秦文学和吴趼人研究,主讲诗经、楚辞、诸子等课程(21),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吴承学教授即拜于卢叔度门下,八十年代整理出版过《我佛山人短篇小说集》《最近社会龌龊史》《俏皮话》等书。卢叔度的研究趣味,似乎与王瑶这封信中谈及的内容无联系。刘叔(淑)度(1899-1985)的材料则颇多,她曾与鲁迅、郑振铎有交往,且还是许广平、高君箴的同学,也是著名的篆刻家,师从过齐白石,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附中教书,一九五八年退休于南京第十中学,后定居北京(22)。刘叔(淑)度从事的文艺活动,似乎与王瑶的这封信提及的内容并没有什么联系。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叔度同志”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高校里,显然是一位教授《中国新文学史》的大学老师,其详细信息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至于“叔度同志”是否参加了一九五四年七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综合大学教学研究座谈会,以及他是否与王瑶在会场中见面,甚至在会议期间谈论有关《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细节”,确有待研究界在今后的档案查检中,披露相关的细节信息。 ①王瑶:《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页。 ②王瑶:《修订小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 ③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④王瑶:《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王瑶全集7》,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76页。 ⑤叶圣陶:《叶圣陶集》(22),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⑥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8页。 ⑦《王瑶年谱》,《王瑶全集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⑧刘跃进:《尊重历史,编好文学所所志——王平凡访谈录》,《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⑨新华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举办全国综合大学教学研究座谈会》,《人民日报》1954年7月30日,第三版。 ⑩(1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50—251页,第231页。 (1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51页。 (12)罗孚:《东北雪,东方珠》,张双庆编著:《李辉英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6页。 (13)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 (14)王平凡:《深切怀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5)王平凡:《文学所往事》,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272页。 (17)王瑶:《〈老舍选集〉序言》,《王瑶全集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507页。 (18)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页。 (19)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71页。 (20)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大学大纲(初稿)》,《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第1页。 (21)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专家小传》,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22)王志民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284页。标签:王瑶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老舍论文; 艾青论文; 李辉英论文; 吴满有论文; 丰年论文; 北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