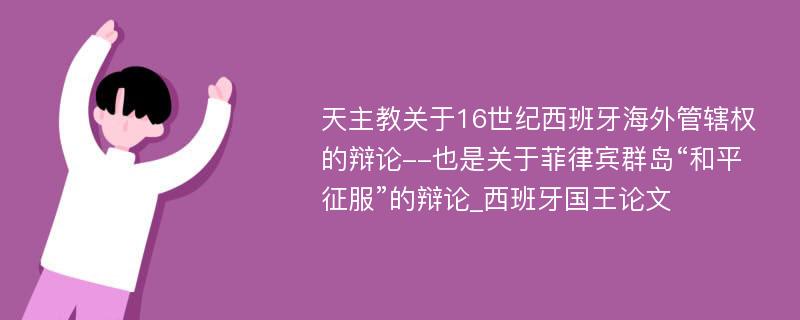
16世纪天主教会对西班牙海外管辖权的争论——兼论菲律宾群岛的“和平征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论文,管辖权论文,西班牙论文,会对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1-0122-07
许多殖民史家把西班牙对菲律宾群岛的占领美誉为“和平征服”。如研究西班牙海外殖民史的著名学者约翰·拉迪·费兰(John Leddy Phelan)把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占领比喻为“良心”与“剑”的征服[1](P221),菲律宾著名历史学家塞德(Gregorio F Zaide)也把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占领主要归功于“十字架”的胜利。[2](P156)的确,与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美洲初期对美洲印第安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的军事征服相比,西班牙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群岛宣扬的以传教为主的“和平征服”方式则少了许多暴力与血腥。一方面,西班牙在菲律宾实施的以传教为主的“和平征服”政策是对其早期以军事征服为主的殖民扩张政策的重大修正;天主教会在促使西班牙海外殖民政策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16世纪对西班牙海外管辖权与统治方式的理性思考与争论,对西班牙王室改变其海外扩张政策、制止殖民者的暴力意识和武力扩张起了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班牙海外殖民征服政策的改变并不能改变其海外殖民扩张的侵略本质。历史证明,教会所宣扬的“和平征服”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危害性,这种挟裹着殖民主义思潮、以天主教信仰和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征服”,对菲律宾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下至普通的菲律宾民众,上至菲律宾社会的文化精英,甚至包括塞德在内的一些菲律宾历史学家依然对天主教会和传教士流露出感恩戴德的褒扬,感谢他们带来了基督教信仰、价值观与拉丁文化,却对这种“和平征服”的性质缺乏全面与深刻的认识,这种普遍的“民族意识的模糊与倒退”是西班牙传教士对菲律宾实施“精神征服”与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3]本文将追本溯源,围绕近代初期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海外征服理论、16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对西班牙海外管辖权的争论,以及教会对该权力的“合法性”诉求,分析天主教会宣扬“和平征服”的实质与教会在西班牙海外殖民政策转变中的作用,从而探索菲律宾天主教化的深层次原因。
一、近代初期基督教世界的征服理论
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海外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扩张。新航路开辟后,为反击穆斯林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进攻,以及弥补因宗教改革而丧失的大量地盘,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欧洲天主教会急于向新世界扩张势力,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这场扩张运动的先驱。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接连颁布了四条通谕,不仅把哥伦布探险所至区域内一切已发现和未发现的土地赐给卡斯蒂利亚的国王,并且在佛得角和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一条分界线,以此来划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天主教国家海外发现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西、葡两国承担向海外殖民地派遣传教士的义务,负责修建教堂,并享有海外教区和教会机构高级教职的提名权。这四条通谕成为西班牙国王取得新世界土地的基本法律根据。[4](P571)
罗马教皇的通谕为何能成为近代初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占领海外领土的法律根据?这是因为,早期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征服理论是建立在中世纪以普世主义原则为核心的“基督教大世界”(Christendom)的观念之上的。即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神,一种灵魂拯救法和一个上帝;全世界同出一源,属于一个整体……不同民族都是基督教大世界的成员,都受到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5](P61)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这一原则也延伸到美洲以及当地的印第安人身上,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正统基督教世界认为他们拥有对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合理且合法的管辖权(jurisdiction)。首先,欧洲基督教世界认为,异教徒所占据地方都是“没有合法所有主”的“宗教上的无主地带”,而作为上帝在人世代表的罗马教皇有权把这种“宗教上的无主地带”分派给任何基督教王国的国王所有,因此分得这种地带的基督教国王就享有对这些地方的“合法”管辖权。第二,“开化论”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扩张提供了道德依据。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看来,基督教的海外扩张有其天然的、神圣的“合理性”,他们把欧洲的海外扩张与崇高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即把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扩张放置在神定的意图上,并视之为一项神圣的委托,他们的征服行动是本着“慈悲”与“善良”的目的,是为了把异教徒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对他们加以开化,使他们沐浴在基督教文明的阳光下,过上文明的生活,所以是“合理”的征服。正如17世纪西班牙法学家胡安·德·索洛萨诺-德·拉·塞尔纳概括的那样:“因为他们(指印第安人)如此野蛮……需要有人担负起管理、保卫、并教导他们的职责,使他们过一种有人性的、文明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因而他们应获得接受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能力。”[6](P296)这种从文明的角度来划分人种的优劣性,并因此把非基督教徒的印第安人污蔑为“野蛮人”的理论在欧洲基督教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土壤。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根据所谓的自然法则提出了“人种优劣”学说。该学说认为,按照自然法则,人们并非生而平等,因而,强者统治弱者是天经地义的。[7](P12)
新航路开辟后,随着海外广袤领地以及众多非基督徒民族的发现,为了给欧洲基督教世界提供海外殖民的合理说法,一些欧洲的神学家和法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如1510年,苏格兰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在亚里士多德“人种优劣论”的基础上著书立说,明确指出,印第安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劣种人,是“天然的奴隶”。[8](P192)西班牙神学家兼法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也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在其1554-1555年间的未刊论文《民
主变革》(Democrates Alter)中认为:“印第安人是天生的没有理性的野蛮人,应该由
天生高贵的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实行严厉的家长式管理。”[5](P300)此外,欧洲基督教
世界宣称的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为核心的“普世平等主义”,也为其海外殖民
扩张提供了“正义”之名。如塞普尔韦达就认为,前西班牙时期殖民地的社会与政治结
构中所存在的阶级划分、等级差别以及剥削压迫制度与专制主义是不文明、不公正的,
所以传播基督教,最终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废除奴隶制度”、“没有剥削压迫”
的基督教王国是禀赋神的旨意,是正义的行为。而西班牙国王作为上帝神圣旨意的捍卫
者和实践者,他所支持的海外扩张运动是为了把殖民地人民从“野蛮的专制统治”中“
解放”出来,是“正义”的“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这种理论在当时盛行的“乌托邦
”学说的推动下得到普遍支持。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秘鲁总督佛朗西斯科·德·托勒
多(Francisco de Toledo)就非常重视对当地土著社会情况的调查与研究,许多早期的西
班牙殖民官员以及传教士也热衷于对前西班牙时期菲律宾社会情况的考察与研究,都不
乏为这种理论寻找证据的动机。[9](P25)
但是,随着传教士对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暴行的揭露,尤其是这些暴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所宣扬的“慈悲”、“善良”、“文明”、“正义”的“开化”与“解放”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的暴行首先遭到一些具有温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多明我会传教士的谴责与抨击,而基于“教皇授权论”、“开化论”与“解放论”的基督教世界的征服权理论也因此在西班牙国内的天主教会、神学界和法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
二、对西班牙海外殖民权力的争论:对美洲的反应
多明我会传教士安东尼奥·德·蒙得辛诺斯(Antonio de Mondesinos)是谴责西班牙殖民者暴行和维护美洲印第安人权利的先驱。针对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s)以及许多委托监护主滥用权力,肆无忌惮地役使印第安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1511年,他在海地布道时就公开谴责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无疑是对印第安人的谋杀”[10](P156),并严厉地质问欧洲基督教世界“印第安人是不是人?他们有没有理性的灵魂?”[8](P198-199)蒙得辛诺斯的言论虽然遭到教会上层与王室的压制,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在西班牙国内和罗马教会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西班牙天主教会、神学界和法学界对西班牙在美洲管辖权力与统治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第一个话题集中在西班牙对美洲的占领是否合法上,归根结底是质疑“教皇授权论”,即罗马教皇是否享有对非基督教国家的管辖权力。1539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ctoria)在西班牙著名的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发表了题为“关于印第安人的陈述”(Relectio de Indis)的演讲,其中明确地宣称:“教皇没有享有对国家的世俗管辖权,他不能统治非基督徒民族及其领地,也无权授予西班牙君主统治海外领地的世俗管辖权力。”[11](P5)维多利亚根据进步的自然法观点,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为非基督徒的土著权利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大胆地将西班牙以教皇赠与为基础对美洲实行统治的合法性一笔勾销。
虽然维多利亚从“教皇无世俗管辖权”的角度否认了西班牙王室统治印第安人的合法性,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西班牙王室对印第安人的权利,而是竭力地从其他方面为西班牙王室寻找占领美洲的“合法性”。如他提出了“人间财富用途天定说”与“传播福音权力说”来论证西班牙王室对印第安人享有的权利,以及在几种特定情况享有对印第安人发动正义战争的权力。维多利亚的“人间财富用途天定说”认为:“西班牙人与蛮人一样,同属人类,凡人皆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同类。所以那些蛮人排斥西班牙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所以,西班牙人可以通商,分享公共财富。如果蛮人使用暴力,则西班牙人可以自卫……如果西班牙人想尽一切办法,仍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征服蛮人,占领他们的土地,必要时可以行使一切战争权利:剥夺他们的财产,俘虏他们,罢免及撤换他们的首领。”[12](P119-120)他在“传播福音权说”中认为:“基督徒有权到蛮人的地方传教,以拯救他们的灵魂……教皇是人间的精神主宰,有权把向印第安人传教的使命委托给西班牙人……如果蛮人阻碍西班牙人自由地传播教义,蛮人的首领以暴力阻止本族人皈依基督教,西班牙人可以使用武力来保障这种自由……根据这些理由,西班牙人可以行使战争权,占领土地,并任命新的国王……”[12](P119-120)维多利亚对西班牙海外征服权力“合法性”的寻求清楚地表明了天主教会对西班牙海外殖民扩张的真实态度。
争论的第二个主题集中在对印第安人的统治方式上,即由谁来对印第安人实施管理和统治,移民、贵族还是西班牙王室?根据1493年的教皇诏书,只有王室才享有对印第安人的管辖权,并且这种管辖权是与传教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被委托给其他西班牙人或通过委托监护制转让给个人。但在16世纪的美洲,委托监护制是一种主要的统治方式,它源于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的一种授地制度,16世纪初经过略加修改后移植到新大陆。依照规定,国王为了奖赏有功的拓殖者,将某一地区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委托”给他们加以“监护”,他们负有保护印第安人并使之皈依天主教的义务,(注:根据1512年12月12日颁布的《印第安法》(The Laws of Burgos)第3条和第12条规定,委托监护主有义务为受监护的人提供衣、食和住宿以及帮助他们接受基督教,并在传教士缺乏时,代替传教士为印第安人提供圣礼服务。参见Lesley Byrd Simpson,The Encomienda in New Spai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50.)同时拥有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和征用劳役的权利。但监护权本身不含有土地使用权、司法权,印第安人名义上仍是国王的自由臣民,土著村社拥有自己的土地,村社内部事务仍由酋长管理。委托监护制名义上是由委托监护主对印第安人实行间接的殖民统治,但在西班牙殖民美洲初期,委托监护主经常非法地行使管辖权,结果使监护制成为变形的封建领主制,委托监护主也常常与西班牙国王分庭抗礼,成为印第安人的实际统治者。[13](P82)在西班牙国内,赞成实行委托监护制的大有人在。如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塞普尔韦达就明确地宣称,应由移民中的贵族对印第安人实行严格的监护统治。但是,由于委托监护主对受监护的印第安人毫无节制地剥削和压迫,委托监护制遭到许多有良知的教会人士的谴责和反对。除蒙得辛诺斯外,在海地传教的多明我会神父拉斯卡萨斯也公开指责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并强烈要求西班牙王室废除委托监护制,由王室对印第安人实施直接的统治。拉斯卡萨斯谴责西班牙殖民者的实质并不是反对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权力,而是反对委托监护主对印第安人的残暴统治,主张由王室和传教士通过“和平殖民”的手段来维护西班牙王室在美洲的统治,但是他对西班牙殖民者暴行的谴责和对印第安人权利的呼吁成为促使菲力普二世于1573年颁布旨在约束殖民者暴行、规范殖民程序的《海外发现管理条例》的重要因素,这条法令对西班牙海外殖民政策的改变有着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后来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和平征服”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三、教会对西班牙殖民权力的争论与菲律宾的“和平征服”
在西班牙征服菲律宾初期,特别是在1565-1580年期间,虽然最早到达菲岛的奥古斯丁会神父也认为西班牙对菲律宾没有合法占领权,但他们对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讨论并没有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是主要谴责早期殖民者,主要是士兵与委托监护主对菲律宾人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暴力。[14](P254)委托监护制也是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一种主要殖民制度。1571年,列加斯比就开始在宿务实行委托监护制,把土地和菲律宾人分配给跟随他远征的有功之臣。随着征服的推进,该制度也在其他占领地实行。从1571至1572年,列加斯比共封赐了143名委托监护主。[15](P304-310)至1591年,在菲律宾共有257个实行委托监护制的庄园,监护着667612名菲律宾人。[2](P169)虽然法律也规定委托监护主有义务保护被委托监护人的福利,为他们提供教育并促进天主教的传播,但是,同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早期菲律宾人也同样遭受到委托监护主的侵扰与折磨。早期菲律宾奥古斯丁会传教士的书信、1573年上呈给西班牙国王的备忘录以及同年的《税收意见书》中就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委托监护主与士兵对菲律宾人的虐待与暴行以及因此对传教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15](P223-228,229-234,256-272,286-294)奥古斯丁会在备忘录里请求国王重新派遣有良知的、正直的总督来管理菲律宾,制止这些暴力,弥补已经犯下的罪行。备忘录引起了西班牙国王的重视,后来西班牙国王撤消了拉维萨雷斯(Lavezaris)的总督职务,并重新任命墨西哥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弗朗西斯哥·桑德博士(Dr.Francisco Sande)为菲律宾的总督。
但教会与殖民当局关于殖民政策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随着1581年多明我会神父、马尼拉第一位主教多明哥·德·萨拉查尔(Fr.Domingo de Salazar)的到来,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萨拉查尔在任马尼拉主教前,曾在美洲传教18年,是拉斯卡萨斯思想的狂热追随者。任马尼拉主教后,他不仅严厉谴责殖民当局对菲律宾人的虐待与暴行,而且也开始质疑西班牙国王在菲律宾实行统治的合法性。多明我会关于西班牙国王统治菲律宾的合法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西班牙国王是否享有对菲律宾人的精神管辖权;二是西班牙国王是否享有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
1582年,萨拉查尔主持召开了菲律宾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会议(Synod),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天主教传播的有关事宜以及过去和未来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合法性”。这次宗教会议使菲律宾的各个传教会达成这样的共识: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传播福音的基础上,传播天主教、实行和平征服才是西班牙在菲律宾实行合法统治的唯一方式。会后,萨拉查尔派遣阿隆索·桑切斯神父(Fr.Alonso Sánchez)回西班牙向国王汇报,因为他认为“菲力普二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天主教国家的国王,在确认征服菲岛的正义与合法性之前,他不能采取其他一切行动”。[11](P12)
在确认西班牙国王享有在菲律宾传播天主教的权力与义务,以及享有对菲律宾人精神管辖权之后,萨拉查尔开始思考西班牙国王是否享有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其中首要问题是关于税收问题。
税收问题是西班牙占领菲岛初期教会与殖民当局争论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到西班牙是否享有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的关键问题。在1573年奥古斯丁会的《收税意见书》中,教会就对殖民当局的高额税收提出意见与批评。奥古斯丁会在这份报告中认为:“每个纳税人3塔埃尔(tael)(注:Tael和maez是在前西班牙时期的菲律宾使用的黄金计量单位,1塔埃尔约等于1.5盎司,1马埃司约等于1/10塔埃尔。参见Blair and Robert,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3,P.192.)的税收是太高了,没有人能够支付。他们自己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因而常常逃入山里逃避税收。我们认为即使在衣食无忧、法律健全、社会安定的基督教社会,超过1马埃司(maez)的税收都是不人道的,何况菲律宾此时的社会情况呢?如果以后情况好转,生产提高,可以考虑提高税收。”“1马埃司税最实际的征收办法是允许菲律宾人用粮食和布来代替,如果士兵能辅之以其他方式谋生,这种税率是合适的……我们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他们,公正地对待他们,纠正对他们的虐待,教导他们信仰我们的教义。”[16](P428-429)但是奥古斯丁会的建议遭到以拉维萨雷斯为首的委托监护主的强烈反对,为此奥古斯丁神父拒绝为他们执行圣礼。[15](P301)在1586年马尼拉的宗教会议上,教会终于与委托监护主在税收问题上达成协议,即向每个成年菲律宾人征税10里亚尔,其中0.5里亚尔作为主教的薪水,1.5里亚尔作为西班牙士兵的补贴,2里亚尔作为教士的生活补贴,6里亚尔归委托监护主所有。菲力普二世批准了这个税额,并指示应允许菲律宾人以实物或香料来代替税收。[1](P233)
1589年,菲力普二世任命古墨兹·佩雷斯·达斯马雷纳斯(Gómez Pérez Dasmarinas)
为菲律宾总督,并指示他与主教共同商议管理菲岛的有关事宜。[17](P159)在税收问题
上,主教萨拉查尔与达斯马雷纳斯又发生了冲突。但此时的萨拉查尔已经变得比较现 实
,并且意识到委托监护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可能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废除,他所能做 的
只是论证西班牙国王对菲律宾享有合法的世俗管辖权,并制止委托监护主对菲律宾人 的
过度剥削。
在西班牙国王是否享有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问题上,萨拉查尔肯定了西班牙国王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但其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大多数菲律宾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或者是通过正义的战争。在菲律宾当时的情况下,萨拉查尔认为,应该允许菲律宾人自愿选择是否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因为西班牙国王没有向菲律宾发动正义战争的理由。他引用了多明我会神学家卡叶塔诺(Cayatano)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教会对教皇领地上的居民有理所当然的统治权;对教皇领地外的、但是反对基督教君主统治的异教徒有发动正义战争的权力;但是对那些教皇领地外的、既没有阻碍天主教的传播,又没有反对天主教国王的人民,天主教国王没有理由对他们发动正义的战争。菲律宾的情况就属于此类。[11](P15-16)萨拉查尔的观点得到多明我会神父米格尔·德·比拉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的支持,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菲律宾人的首领已经皈依了天主教,那么就应该保留他们对其原来下属的管辖权,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这种方法与西班牙国王在菲律宾的统治并不相冲突,而且还有利于推动天主教的传播。[11](P15-16)
1590年,78岁高龄的萨拉查尔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与比拉维德斯一起返回西班牙向菲力普二世汇报。经过漫长的讨论,1594年6月11日,菲力普二世作出裁决,除了保留已皈依天主教的菲律宾人首领的权利外,其他的决议完全与萨拉查尔的观点相反。1594年12月14日,萨拉查尔在西班牙去世,享年82岁。但比拉维德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他坚持向国王呈情,决心使国王改变决定。最后,菲力普二世匆忙召集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印第院开会,并在1596年10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同意萨拉查尔与比拉德维斯的观点。1597年2月8日,菲力普二世又颁布了一道敕令:命令菲律宾总督召集所有官员讨论殖民政策,首先,要求他们退还所有不应收的税金;第二,不能用武力威逼菲律宾人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应该允许他们作出自愿的选择。[11](P19)
1598年,被任命为新塞哥维亚(Nueva Segovia)教区主教的比拉德维斯带着西班牙国王的这道敕令回到马尼拉。同年四月,这道敕令开始逐渐在吕宋岛的各省宣布,一些地区的菲律宾人首领表示愿意率众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1599年,菲律宾总督特诺·德·古兹曼(Tello de Guzman)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多数菲律宾人普遍愿意接受陛下的统治。在新塞哥维亚教区的伊洛哥省,进展顺利,他们愿意接受您的统治。同样,在马尼拉奥古斯丁的辖区,也是如此。但在内湖省方济各会的辖区,暂时还没有结果,当地的首领说要一年后方可决定。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18](P253-255,P287)
可以说,西班牙国王的这道敕令是其海外殖民政策发生改变的又一重要体现,它对西班牙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迅速地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起了较大的作用。而教会,特别是多明我会关于“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管辖权”的争论对推动西班牙海外殖民政策的改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教会对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管辖权的争论以及对这种权力“合法性”的诉求,无论是其动机、本质还是目的,都是旨在维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教会在这场争论中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与温和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不可忽视的,与血腥残暴的军事征服相比,这种“和平征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传教士鼓吹的“和平征服”以及以天主教会为核心的殖民统治给菲律宾社会遗留下许多负面影响,成为制约当代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根源。
收稿日期:2003-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