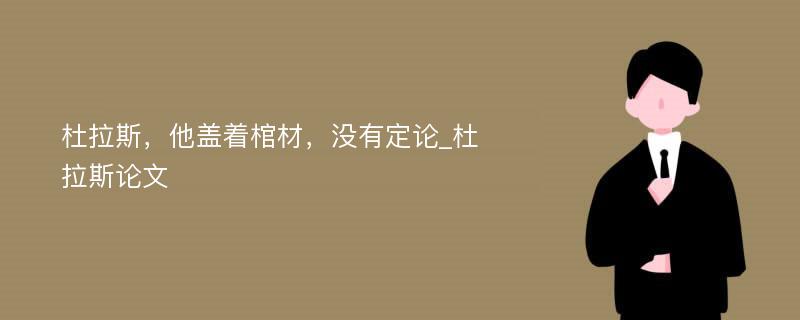
盖棺难以定论的杜拉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论论文,杜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文坛热点
1996年3月3日,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畅销全球的小说《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去世了。对于不论是生活还是作品都明显与众不同、经常出版标新立异之作、发表惊世骇俗之语且在晚年因酗酒不断与医院和死神打交道的杜拉斯来说,从这个她曾周旋其间且又常常诅咒它的毁灭的世界中消失,可以说是她能够制造的最大也是最后的新闻了。
一个创作期超过半个世纪、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学发展息息相关的多产文学家,退出了不一定总是辉煌灿烂但常常让世界注目的法国文坛。人们纷纷以赞誉文字、纪念文章论说她的死亡、她的创作,估价法国文学的损失,度量女作家去世留下的巨大空间。“新小说的象征”,“卓越而令人不安的文学”,“神谕的力量”,“文学的巫女”,“文字的女魔术师”,“异乎寻常的人物”,“无法归类的造物”等等评语纷纷见诸报端[①a]。法国国家电视二台及法德文艺电视台相继推出专题节目,纪念这位女作家。继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并在法国获创纪录的发行量后,杜拉斯再度成为传媒、舆论的 关注点,有关她的一切神话般地吸引着公众。
杜拉斯的所作所为在法国文坛可说是最无法归类、最不具典型性的。从法国共产党党员到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密友、社会边缘人物的喉舌;从“新小说”的同路人到“新浪潮”电影的先锋;从充满魔力的文学语言到有悖常理的对社会新闻的干预;从电台报刊上文学的、政治的高谈阔论到街头酒吧里与酒徒、流浪汉的畅饮狂欢,这一切都无法进入任何规范。而其颇具主观性的众多创作中对传统叙述语言的大胆冲击,对处于正常与病态之间人物的塑造,更是让那些据说能洞察人心尤其是作者之心的批评家们怀疑自己的理性与阅读能力,甚至为此竟在法语里创造出“不可交流性”(incommunicabilite)一词来界定杜拉斯作品的主题,把握其书中的人物(这同时也无奈地宣告了批评本身的无力)。此外,小说《情人》那巨大却又被夸张了的成功,电影《情人》那迅疾、广泛却又对原著有许多歪曲处理的推波助澜,使杜拉斯即便已入棺木也无法被真正把握。
玛格丽特·杜拉斯,原名玛格丽特·多那蒂约(Donnadieu),于1914年生于印度支那越南南部当时被称作交趾的地方。父母都是法国小学教师,受殖民主义宣传的影响,从本土来到当时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支那。或许是这不平凡的出生在她未来的意识深层中植根,使她对文化的差异敏感且宽容,对人类境况尤其是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中“人被抛到这个世界”的命题有着特殊的体验。人们大概也能由此读懂她许多作品中都出现的流浪主题以及她那总是把人物置放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环境、场所的处理。
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她的家属于白人殖民者的最底层,丧夫的母亲以微薄的收入养育着她和她的两个哥哥。贫穷的生活使他们与本地人的区别只在于肤色,只在于维持最后的所谓白种人的尊严。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杜拉斯对经济、阶级的差别有着比对肤色、种族、文化等更深切的感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曾长期信奉共产主义学说,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1944—1950),并且在初期作品中显露强烈的阶级意识以及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甚至在晚年又不断为最底层、被社会遗弃的人们摇旗呐喊。
一直到18岁为止,她的整个童年、少年都是在印度支那度过。这期间的家庭悲剧及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种种大小事件成了她日后创作的不尽源泉。她或者直接以此为背景写印度支那、印度乃至亚洲系列作品,或者以该地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为原型进行虚构背景下的再创造。可以说,在杜拉斯每一部作品中,都有她童年、少年时印度支那这段生活的影子;也可以说,没有印度支那,就没有杜拉斯。
1931年她回到法国读书,次年定居巴黎,在大学读了法律、数学、政治学,后去外交部任职。1939年与作家罗伯特·昂代姆结婚,后者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后,她开始了痛苦的等待与艰难的营救,并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狄奥尼斯·马斯科罗及终生密友、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战争的灾难,尤其是等待、营救关在集中营的丈夫的惨痛经历,被她记录在1986年发表的日记体小说《痛苦》[①b]中,由她担任编剧、曾获戛纳大奖的电影《长别离》对此也有形象、感人的再现。
1943年杜拉斯发表处女作《无耻之徒》,1950年发表成名作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从此便开始了写作生涯。其实,她的写作志向很早就表现出来,在印度支那法语中学读书期间她就向母亲表达过这样的志愿。她似乎无法独自承受个人及历史事件给她的心理、智力带来的重负,死亡与疯狂的诱惑又几乎仅仅次于写作的诱惑,以至于她的丈夫在向出版社推荐她的第二部作品时,竟对编辑说:“我先告诉您:如果您不对她说她是个作家,她会自杀的。”著名小说家雷蒙·格诺在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争取龚古尔文学奖不成的时候,也向杜拉斯建议:“写作,只于这个,别做其它。”另外,50年代初巴黎第五区共产党支部以“主观主义”将杜拉斯开除出党,更使她断绝了写作以外的其它念头。可以说,由此法国共产党少了一个不合规范的党员,而法兰西文学却多了一个以主观色彩浓烈独步文坛并日后让法国人感到骄傲的享誉世界的重要作家。
杜拉斯的早期创作基本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此一时期代表作品为使她差一点获得龚古尔奖、后被美国人拍成电影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①b]。小说讲了印度支那,讲了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白人家庭,尤其讲了母亲的故事。贫穷的母亲攒钱,借贷,从殖民当局那里买下了海边的一块不毛之地,她种下了庄稼,大海潮袭来时却被冲毁得一干二净,她不甘失败,在岸边筑起一道大堤,保护自己的庄稼,然而大水又冲垮大堤,再次毁灭了她的努力。她依旧不甘心,依旧借钱筑坝,播种庄稼,而太平洋依旧无情,继续摧毁她的梦想……在不停的修筑和摧毁之中,母亲表现出一种近乎荒诞的抗争,一种近乎垂死的绝望。最后,衰老多病的母亲不得不离开那块曾经疯狂地投入过的土地。小说有一种明显的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控拆,作家也不时地流露出对金钱和权势的愤恨,然而,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母亲悲剧的荒诞意义,是那同西西弗神话[①c]一样对人类境况的揭示。人们可以想象,作家对荒诞主题的发掘可能是受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不过《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源于自身的经历,不似当时流行的观念文学,更何况以萨特、加缪为首的存在主义大师们根本没有把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青年作家放在眼里。
杜拉斯的第二期创作是与“新小说”相映成辉的。被法国共产党开除、被存在主义拒之门外的女作家自然地加紧了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也自然地接近了企图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新小说”作家们。有必要说明的是,虽然评论界在她死后仍把她当做“新小说”的一员,她本人却从未接受过这一标签。客观地讲,她与“新小说”派只有两点共同之处:摆脱萨特所代表的文学干预生活的主流派影响;在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上进行新的尝试、探索。巧合的是,杜拉斯的创作高峰期、成熟期正好与“新小说”的蓬勃发展期同步,而该阶段又逢“新浪潮”电影流派问世。因而,在此一阶段完成许多重要作品的杜拉斯除了在小说上不断探索外,又常被邀写电影剧本,为她在70年代的戏剧、电影活动做了准备。
在杜拉斯的70多部小说、戏剧、电影创作中,给她的同代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当是她的成名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及80年代使她名扬四海的畅销书《情人》,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文学作品自身拥有的价值考察,最能够流传下来且具某种永恒价值的当是“新小说”时期的两篇力作:中篇小说《如歌的中板》和电影剧本《广岛之恋》。
发表于1958年的《如歌的中板》[①d]讲了一个最不适于讲的故事。小说取名于开篇的一个插曲。一位学钢琴的男孩固执地拒绝回答老师什么是如歌的中板的问题。母亲每周送孩子来学钢琴,孩子却根本不喜欢音乐;钢琴老师让他解释“如歌的中板”,他却根本不予理睬,只说:“我不知道。”在僵持中,从楼下传来一声尖叫,孩子母亲下楼去看发生了什么,街头咖啡店的女店主告诉她大概是一场情杀,一个青年男子杀死了一个女人。咖啡店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凑过来给她补充些情况。从此,这一男(工人模样的人)一女(弹钢琴孩子的母亲)经常在这家咖啡馆见面,一起谈论这场情杀,女人不断迫究细节,男人不断向她提供。但实际上男人并不比女人知道得更多,而女人也并不总是在听对方讲话。一个说着可说可不说的话,讲着似有若无的情杀背景,另一个听着可听可不听的语言和虚虚实实的细节,此外,小说不再有任何情节。一直到女人决定不再继续约会,而男人在最后一次见到她时说,“我要你死”,女人回答,“已然如此了”,小说就此结束。
《如歌的中板》打破了传统小说中人物、情节、行动的各种模式,也使批评家们像一般读者一样不自觉地在评论中用了很多问号:到底发生了什么?情杀的后面究竟是怎样的故事?男女主人公之间后来又怎么样?没有回答。情节的淡化,故事的似有似无,结局的开放,人物的模糊,行动的不确定等等,这一系列叙述语言及叙述方式的革新使人们把它列入“新小说”的代表作之中。然而作品除了像其它“新小说”一样让人费尽脑力以外,还让人产生一种不安。这就是杜拉斯的方式,在好不容易给她贴上标签以后,人们仍旧不能不折服于她小说家的才情、优美的语言及让人身心都有些不适的主要作用于感官的文字。那打破钢琴课僵持、打破常规生活寂静的尖叫似乎永远挥之不去,萦绕在耳边。
创作于1959年的《广岛之恋》属于另一个范畴。当时法国著名导演阿兰·雷乃要拍一部关于广岛的电影,他找杜拉斯写场影及对话,后者却写就了完整的一部电影剧本《广岛之恋》。相比之下,这个故事还有些情节,虽然情节大致只是个叙述的线索。1957年在广岛,一个日本男人和一个法国女人相遇了,这是一次婚外遭遇,两个主人公都有家室。男人是工程师,女人是电影演员,从法国小城讷韦尔来,拍一个关于广岛的宣传世界和平的电影,在电影即将拍完,她就要回法国时,他们相遇了。二战期间,法国女人曾经爱上一个德国兵,战争结束时,德国青年被处死,她也被剃光了头,躲在自家的地窖里不敢见人。在广岛,她想通过日本男人重新体验青年时经历的与敌对者的恋情。但是她终于明白在广岛是徒劳的,因为她的爱死在了法国的讷韦尔。她决定离去,日本男人苦苦劝留。作品的结尾是两个一直没有名字的男女互相以对方的地名称呼:“你的名字叫广岛。”“你的名字叫讷韦尔,法国的讷韦尔。”
对20世纪尤其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广岛是个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话题。那巨大的毁灭生灵的爆炸使广岛成了一种不需用许多语言阐释的象征符号。它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含义就是死亡。在这一背景下演绎爱情故事,其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效果可想而知。杜拉斯着力表现了爱情与死亡、个人历史与集体历史的对比与交织,使作品产生一种强烈的力度和感染力。她设计的片头特写让人无法忘记:两具裸露地贴在一起的躯体上流淌着两性欢爱的汗水,而这汗水又不断地与原子雨侵蚀人体后产生的灰尘、露珠重叠。
从《如歌的中板》到《广岛之恋》,两年的时间里杜拉斯使法国乃至欧洲的现代文学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震颤,而这两部作品也足以使她跻身于本世纪世界重要作家的行列。单独看《如歌的中板》,也许只能联系到当时的“新小说”探索,如果把这两部作品放到一起来读,我们几乎可以得到一个类似文学革命的启示。在这两部作品中,杜拉斯没有讲故事,没有解释议论,没有制造戏剧效果,也没有复制现实,她只让一声尖叫刺破沉寂或让被肢解般的身体占据整个画面。她把一对男女放在咖啡店或旅馆房间,这实际上非确定的空间就如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处所。于是,流浪、永远漂泊的意境就产生了。而走进这空间的是来无所来、往无所往的孤独男女。在他们之间演绎着的也远远不再是传统悲欢离合模式的爱与死的故事。在这里,惟一能给人以慰藉的是由那平白、中性的文字组成的对话语言,在这些看起来常常缺乏逻辑的对话中,每句问答都似乎是一种特殊关怀的流露,使对方感受到生存重负的减轻,每一个词都似乎变成一种抚摸,一种尽力不去碰痛伤口的对伤者的触摸,一种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
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在两年之间在两部作品之中诞生了。从此杜拉斯有了自己忠实的、无条件的读者群,也有了一些总想阐释不可阐释性的批评家,包括拉康、布朗肖等著名文论家。这以后直到1984年《情人》的发表,她又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亲自创作导演不下20部戏剧、电影,创造了以《副领事》(1965),《印度之歌》(1973)为中心的印度系列电影,塑造了一些极适于精神分析批评的女性形象,比如《劳拉·维·斯坦的劫持》(1964)。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前,她已获得许多荣誉(包括1983年法兰西学院授予她戏剧大奖),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乃至数十种语言,在法国大学里注册的有关杜拉斯的博士论文达50多个,这对活着的作家是十分罕见的。然而,真正使她名扬世界,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使她“名扬宇宙”的是小说《情人》。
《情人》的成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杜拉斯现象或《情人》现象,它把作品本身的价值及杜拉斯本人的影响漫画似地夸大了。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们把本应鼓励青年作家的文学奖打破常规地授予了已届古稀的杜拉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除了考虑到作品本身的价值及创纪录的发行量外,还同时在纠正他们34年前的一个错误:1950年,杜拉斯曾用同样优美的文字写过几乎同样的故事《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龚古尔奖评委们却因她是共产党员、是女性作家而拒绝给她这一荣誉。可以说,以龚古尔奖为发端,一场围绕《情人》的新闻炒作便开始了,而作家本人更是乐于参与其中并担任主角。先是渲染杜拉斯与著名导演阿诺合作拍摄同名电影,后又传言他们意见不合,分道扬镳,阿诺继续拍摄他所理解的《情人》,而杜拉斯又着手写另一部电影剧本《情人》。结果,商业性极强的电影《情人》1992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女作家也发表了她心目中《情人》的电影改编:《中国北方的情人》[①e]。这是典型的现代文化制作,目的是保持读者、观众及潜在的读者、观众的兴奋点,制造轰动的新闻效果,最终获得商业利益。我们无意怀疑女作家本人的诚意,但通晓现代社会各种经济、文化手段的杜拉斯不可能不意识到,成为新闻热点只会使她及她的作品的名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情人》是部准自传体小说。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及其它作品中叙述过的印度支那、母亲的悲剧、对两个哥哥的爱与恨,在该作品中再次出现。熟悉杜拉斯作品的人还能从中读出她的文学世界许多人物的原型、许多母题的来源。作者也有意暗示或明示给读者作品中自传内容的真实性:“我写过家里这些人的许多事。那时候,他们还都活着,他们,母亲和哥哥们。以往我写他们周围的事情,写事情的周围而不去涉及事情本身。”“在有关我童年的书中,忽然我不记得我讲过什么,没讲什么。我相信讲过对妈妈的爱,但不再记得是否讲过对她的恨;也不再记得是否讲过我们互相的爱和家庭里面可怕的互相仇恨。”[①f]然后,作者又告诉我们这不是重复,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一次无保留的坦白,对一段一直难以忘怀的隐情的坦白:“就我记忆所及,我将忠实地讲一段经历……我这里要做的,既与以往不同,又没什么大的差别。从前我讲的是清晰的阶段,被照亮的部分。现在我讲青春时代隐蔽的一段经历,讲那我本可以隐匿起来的一些事情,一些情感,一些事件。”(第12页)
整部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年迈妇人讲述青春岁月的基调下展开。而那经历就是她15岁半时与一个27岁中国青年的恋情。故事的核心也是开篇,是典型的杜拉斯风格: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邂逅在一个彼此陌生的地方。二三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湄公河的一条渡船上,一个中国男青年和一个法国白人少女相遇了。少女穿着破旧、寒酸,但举止随意自然,也透露着某种早熟的性感,她从当地人、穷人坐的大客车上走到甲板上;男青年衣着体面,温文尔雅,衔着一支英国香烟,从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里走出来。初步相识后,他们开始约会。女孩的感情很暧昧,男青年却不可救药地爱着。种族、年龄的距离和双方家庭的反对,使他们无法结合。一年半以后,少女乘船回法国的时候,他们也就分手了。
这并不是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阿诺导演的电影大概也因为原作缺少情节而只能在异国风光与性爱场景上大做文章。坦率地讲,就内容来看,《情人》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媚俗之作,它抓住了读者对异国情调的期待以及对名人隐私的好奇。更何况所谓少年恋情的坦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因为作家本人不论是在其后接受的采访还是写作中,都不断“修改”《情人》中的说法,为这段15岁半的恋情提供不同的版本。比如,《情人》发表不久,作者就在众多的场合一面强调自传内容的真实性,一面突出小说的虚构性:“明天,我可以重新写一本书,讲我生命线索中缺乏的这同一个环节。那本书将和另外一本,即这一本(指《情人》)同样充实……《情人》是一部小说。”[①g]实际上,她正是这样做的:1987年发表的《物质生活》及1991年发表的《中国北方的情人》都讲到了同一段经历,其中内容却有很大出入。
作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技巧。大家知道,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生命,而叙述在小说中是同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从这两点看,杜拉斯在《情人》中展示了大师级的手笔。语言的魅力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至。首先,它简洁、流畅,一个学过三四年专业法语的外国读者基本上可以不用查字典一气呵成地读下来。但是,简洁的文字后面却总像有很多的意义在躲躲闪闪,跳来跳去,行文之中又流溢出一种自然的节奏和韵律。另外,重主观、重感受的杜拉斯所使用的语言常常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对声音的描写:“城市的噪音很大,像是放电影时音量过高,震耳欲聋……木屐的嗒嗒声,像是敲在人的脑袋上……所有的说话声、脚步声宛如一声汽笛,引起了撕裂人心的喧哗,阴郁而没有回声”;(第36、37页)又比如启航与告别的场景:“启航的时刻来临时,轮船发出三声汽笛响。响声悠长,恐怖,全城都能听见……轮船再一次向人们告别,重新发出了它那可怕的长鸣。声音那样神秘,忧郁。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不光是远行的、离别的人啜泣不止,那些只是凑热闹、没什么明确目的、根本谁都没想的人也都流泪了。”(第105—106页)当然,那近乎神来之笔“空气是蓝色的,可以抓到手里”(第77页)更是让其他作家羡慕,让评论家们赞叹了。
杜拉斯在《情人》中的叙述技巧熟练到应付自如的境界。作品中青年男女一年半的爱情故事与少女的家庭故事并行演进,年逾古稀的女作家与如花似玉的少女不断重叠,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时空跨度和不断的场景转换,叙述中的时态人称也随之频繁变化。非凡的结构能力与叙述手段在杜拉斯笔下如行云流水般晓畅、自然,不留半点人工、做作的痕迹。
与叙述有关的是《情人》的自恋结构。整部小说叙述结构的基本点与出发点是一种自我观照。这自我观照首先表现为观看镜子中叙述者已经苍老、毁损的面孔并由此去对照经历那段爱情故事的年轻面孔,在这对比与交叉的观照中,时间似乎不再有意义,叙述者流露的是同一种顾影自怜,同一种自我陶醉。作品的第一段就借用虚设的场景中陌生男人的赞辞表达了这种情绪,这情绪弥漫着《情人》的开篇,笼罩着整部作品:“我有一副被深深的皱纹撕裂的、肌肤毁损的干瘪面孔,它不像某些线条纤细的面孔那样凹陷,它还保持着从前的轮廓,但质地全毁了。我有一副毁损的面孔”,“15岁我就有了一副享乐的面孔,那时我却不知享乐为何物……我的一切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光彩照人、疲惫不堪的面孔,与年龄、经历不符的有黑眼圈的双目”,“我时常想起这幅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从未对人谈起过的画面来。它的出现总是那样悄然无声,又总是那样让人赞叹不已。在所有画面中,只有这一幅使我感到惊喜,使我认识自己,使我如痴如醉”。(第20、21、1页)当然,这种自恋情结不只是精神分析家们所论的初级的对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的迷恋,它还表现为一种高级的对整个自我、自我的行为的欣赏、满足与认同。《情人》的行文中,后一种自恋更是贯穿始终,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段式来表述:1.我很满意自己是个作家;2.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在于我有过与众不同的经历;3.我既满意自己的现在又满意自己的过去。
源于那耳喀索斯神话的自恋情结(narcissiame),同俄狄甫斯情结一样,是西方文化的某种心理机制的重要内容。这种处于自然与病理之间的心理状态有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界限,也有它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自传作品的升华和超越。界限把握好的不论是在生活还是作品中都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同,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多少有这样的倾向;界限把握不好的实际上构成对他人的某种侵犯。在他人那里得到的不是认同而是抵触。杜拉斯在这一点上往往有越界的冲动。笔者曾经在电视上看到面孔苍老、干瘪的杜拉斯在氧气管的帮助下向记者和观众讲述类似《情人》中的那段故事,在极艰难的呼吸中讲述她15岁半怎样与一个中国青年恋爱。那故事依旧很动人,那神态依旧是自我欣赏,只是那画面有些残酷,让观众产生不忍之心。然而,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情绪在文学作品中就容易让人接受,因为文字给人想象的空间、提供净化的过程,更何况这文字出自一个大师级的女作家。如同在其它重要作品中一样。在《情人》里,杜拉斯悠然自得地冲破一切规范和禁忌,潇洒自如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驰骋自己的文采。从这一角度讲,杜拉斯确实有理由自怜自爱,而《情人》也确实是近几十年来用法语写成的难得的一本好书。
杜拉斯去世了。因为死亡,这个总是不合规范的女作家不会再给我们不厌其烦地讲她的印度支那了;因为死亡,她不会再就时事与社会新闻发表种种有悖常理的言论了;因为死亡,她也不会再以越界或不越界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她如何自我欣赏了。然而,她的作品仍在叙述着,叙述着一个女人对生活、对世界的体验,叙述着她本人及本世纪的很多人所经历的种种身心磨难,叙述着古老的永恒的关于爱关于死亡的话语。这被叙述的一切可能只是老生常谈,但,可以确信的是,她用来叙述这些老生常谈的语言和方式将使后来的任何模仿者显得滑稽、可笑。作为作家,杜拉斯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①a 见1996年3月4日《费加罗报》,3月5日《世界报》,第1635期《新观察家》及第2442期《巴黎竞赛报杜拉斯专号。
①b 中译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容译。
①c 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一译西绪福斯)因生前犯罪,死后受罚,推一巨石上山,推至山顶,巨石便坠,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加缪在论文《西西弗的神话》中把与荒诞人生作斗争比作西西弗推石上山。
①d 中译本《琴声如诉》(收入《法国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在书名的翻译上明显背离作者初衷,忽略了作品的先锋性与探索性,把《如歌的中板》传统化、规范化,纳入了言情的范畴。
①e 纪应夫译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华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①f 《情人》,王东亮译,刘自强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页、22页。以下在文中注明页码的均引自此书。
①g 见法国1984年9月4日《解放报》。
标签:杜拉斯论文; 文学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小说论文; 法国生活论文; 广岛之恋论文; 情人论文;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论文; 印度支那论文; 作家论文; 法国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