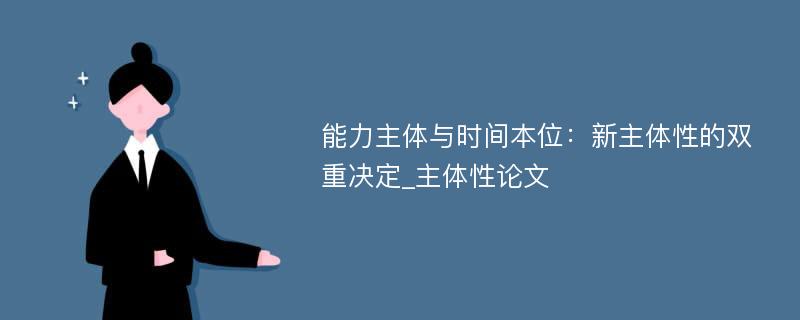
能力主体与时间本位:新主体性的两重断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本位论文,主体论文,两重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5-0111-06
西方反现代性的浪潮带来了对主体性的持续而猛烈的批判。批判的顶峰就是20世纪60年代福科对主体已经死亡的宣告。由于生活世界和理论逻辑都充分证明主体不可能死亡,也由于主体性事实上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是西方文化须臾不可离的思想原则,因此重建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诗学的头等重要的诉求。福科从70年代起开始反过来重建主体。戴维斯(Davis)、施瓦布(Schwab)、高更(Coquet)、沃特斯(Waters)、泰莱(Taylor)等一大批理论家批评家近年来都在致力于恢复主体性在当代西方学术思考中的地位。[1](P10)中国在20世纪的80年代曾经出现对主体性的热烈关注。李泽厚从康德哲学的背景出发,提出建设主体性的理论,在当时的哲学、美学、诗学领域和知识分子的心理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随后的90年代本应是主体性建设向纵深推进的时代,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90年代,主体性消失了。在知识层面上,主体性不再像在80年代一样成为被普遍讨论的热门话题。在价值学层面上,主体性不再是被自觉追求的普适性价值形态。反之,“一地鸡毛”,“躲避崇高”,“人生无梦到中年”,“哭也好,笑也好,活着就好”,诸如此类与主体性追求直接相背的心境、情绪、意向日益成为了人生的主色调。在知识主体的现实人生中,主体性作为生命品格开始了悄无声息的淡出。在稳定、沉寂、静默之中,人们告别对生命激情、创造活力的自我感受,转向对安宁、实在、舒适的外在家园的寻找,转向对外在的既有的一切的认同和接受。再也没有被压抑的愤懑、痛苦和自我超越的向往,有的只是疲累之际寻找宿处的渴望和无法找到宿处的凄然。“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主体只能带着一张旧船票去寻找栖宿的客船,或者在永恒依旧的涛声中去回味从前的夜晚。这是90年代前期的情况。到后期,则“客船”找到了,“我”也睡着了,梦幻中,各种旨在消解“中心”“总体”“本质”“主体”的“戏说”“搞笑”“宝贝”“口红”“下半身展览”便纷纷出场了,本能化的“食”“色”作为主角演绎出了极具特色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狂欢。
相对于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文化现实和中国传统精神结构中主体性本来就严重缺失的实际,考虑到当下西方的前沿性学术挑战,重建主体性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哲学诗学无法回避的核心课题。但是,另一方面,“重建”不是“重复”,而只能是“新创”。当代西方的主体性重建致力于以现象学范式取代笛卡儿的主客对立模式,其实质是新的[2]。中国的主体性也必须是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而作出的新的规定,是新的主体性。“中国”既与“世界”相对,又寓指与纯粹个体相对的文化“族性”。本文认为今日世界不存在纯粹世界性的问题。西方所讨论的“世界性问题”其实都蕴含了西方的文化立场。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在完全世界性的语境中提出和展开。中国当下的主体性不可能与西方当下的主体性等同。另一方面,今日中国的主体性虽然应该是建立在超群体性的个体性的层面上,但其作为问题的视角又必然包含超个体的中国民族性的规定。每一华夏子民都受着作为“中国”族性的现实制约,我们对自我主体性的建构无法离开我们身上的“中国性”。与“中国性”相对应,主体性也只能是当下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是当代西方学术的基本意向之一。中国的学术思考无法拒绝这一意向的合理性。不存在永恒。主体性也是如此。拒绝永恒与接受纯粹的解构无关。前者不排除当下建构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后者则把历史上的一切建构都加以封杀。绝对的解构是对解构本身的取消。解构的意义正在于有建构的存在。新主体性的追求既充分吸收解构主义的合理性同时又是对纯粹解构的拒绝。
新主体性因此致力于吸收和扬弃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主体性思想,以形成自身的理性建构。本文认为,今日中国的主体性建设要吸收和超越的主体性资源主要有四个方面:西方笛卡儿主义的主体性;福科、梅洛—庞蒂及其他反笛卡儿的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性;中国历史上的阳明心学等理论中所蕴含的主体性思想;80年代以李泽厚的论述为代表的主体性诉求。
针对解构主义的挑战,当代西方学者坚持主体有不可消减性(irreducibility)[3](P7)。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认为,主体性就是人性,是主体给自己建立的“一套既感性具体拥有现实物质基础(自然)又超生物族类、具有普遍必然性质(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能量与信息)”。[4](P140)本文的思考以上述两个论断为理论前提:一方面,认定主体性最终不可消减;另一方面,接受李泽厚从人性整体的角度定义主体性的思路。本文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对新主体性的具体构成内容给予论说。下文的两个断定即源自这样的理论追求。
断定一:超越欲望的能力构成
传统的主体性理论基本上都不对欲望的积微价值给予正面审视。它们或者完全否定欲望的意义,或者在它种形式的建构中遮蔽欲望的存在。中国古代的心学属于前者。王阳明的良知的建立是去欲的结果[5]。笛卡儿的主体性属于后者。在笛卡儿的我思中,欲望因为与身体感觉相连,与理性无关,因而属于被排斥的对象。这一面招致了梅洛—庞蒂等人的批判[6](P2-4)。但另一方面,笛卡儿的主体性属于认识论的建构,不涉及生存论;而他从认识论上确立的主客对立又可以被转移到生存论上。当这种转移现实发生之后,欲望作为主体的心理构成随之进入主体性之中,成为与客体相对的存在。笛卡儿的主体性在笛卡儿之后正因为欲望从生存论层面的潜入,招致了反现代性浪潮的猛烈批判,因为未受羁勒的欲望对个体身心和社会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论和李泽厚的主体性思想虽都对欲望有较多的肯定,但他们的肯定都是以潜在的形式进行的,其整体性的建构对欲望也仍是以否定为主;因为只是潜在的肯定,也就谈不上对欲望制约机制作正面的探讨。
新主体性直面欲望的存在,首先肯定欲望的意义,然后期望通过对更高身心机制的设立来建构主体的超越性。
在新主体性的视野中,欲望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欲望(desire)是个体生命存在的现实形式。生命的存在,以自身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为前提。失去交换,生命即停止。正是欲望促成了、保证了人与外界的信息能量的交换。欲望把主体所需要的信息、能量带给自身,把主体渴望排泄、转让同时又为环境所需要的信息能量移送给环境。
现代社会是欲望高涨的时代。欲望的高涨是生命个体性加强的结果。社会发展以生命个体责任性的加大为目标。在现代社会个体日益脱离传统与外界的天然联系,离弃原有的天然性保护,走向自身。为了承担自我被加大的生命责任,个体需要加快与外界的能量与信息的交换;生命走向自身造成个体身心的需要在质与量上同时发生变化;个体肉身的有限性、脆弱性使物质性要求异常突出;科技高度发展,又使交换频率的加快和交换方式的多样化得以可能。这多重因素的结合就造成了现代社会欲望的高涨。人们常用“人欲横流”来指摘现代人的欲望高涨。应该看到道德滑坡的背后有源发性的生存事实。
其次,欲望是个体生命自我发展的动力。欲望的动力意义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得到确认。欲望激活自我的生命潜力。无论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学的层面上看,人都具有丰富的潜力(potentiality)。欲望就如火种,点燃沉睡的生命潜力使之燃烧起来。所谓发展,实际上正是个体潜能的前所未有的显现状态。欲望促使个体置身于对自我构成挑战的生活情境,通过对生活情境的适应、征服从而提升自我生命的境界。欲望是尚未现实化的主体对外在目标的心理占有。欲望具有绝对的对象性。为着实现自身,拥有对象,欲望的主体就必须进入对象性的生活世界。这种生活世界在一般情况下是主体不愿进入,极力回避的,因为置身其中会暴露主体自身的荏弱,甚至因其相互的敌对性、排斥性,而使自我蒙受伤害、毁灭。中国古人“无欲则刚”的名言在中性意义上即包含了对此中原理的揭示。但是,不进入超我的外在生活世界,也就不可能有自我的提升发展。欲望在内在性(inwardness)的层面上使人摆脱惰性与畏惧,使人勇敢地投入外在的生活世界,从而获得自我的提升。欲望之“勇”在中国人的“色胆包天”一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叙说。
其三,欲望使个体生命无视外部世界的不合理性规定,使其在不断的自我提升中增强其主体性的品格。欲望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的不兼容性不仅使欲望的实现同具体的对象性情境构成矛盾,而且会因其与具体对象性情境之矛盾的普遍呈现使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生发出一种反欲望的机制。这样,欲望的实现就面临了双重抵抗。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反欲望机制在宋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中得到了最坚固的建构。在西方可与中国理学比美的则有中世纪的神学。欲望的被压抑是对个体生命本身的压抑;在这种压抑下,个体主体性无从建立。正是欲望的勃发、张扬,使严酷的社会性铁网被撕破,使个体生命得到解放。中国明代的浪漫洪流,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运动都是欲望作英雄性表演的场景。社会发展到今天,欲望的外在反抗性以及由之带来的主体性张扬已经不像历史上那样波澜壮阔,威武雄壮了;其规模、气势、意义都已渐趋弱化、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欲望的传统作用已经完全消失。西方的后现代实际上就是欲望掀起的新解放运动。至于在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历史的某些方面,比如受东方极权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压迫的地区,欲望的传统使命远未完成。欲望的外在摧毁性还应该大大加强。
其四,欲望在主体性建构中的重要性还可从自我意识的生成上确认。自我意识是主体性的重要成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我意识的生成来自于欲望的现实性否定。欲望把主体带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之中,欲望受挫使主体意识到自我与对象的区别,从而使主体萌生出对自我的意识。不经由欲望的现实作用与否定,自我意识就无从产生。
新主体性充分肯定欲望的意义但不在主体性的最高层面上定位欲望。欲望不能直接进入主体性之中,不能成为主体性的核心成分。欲望只能以潜在的被携带的方式进入主体性。其所以有这样的规定,理由在于欲望具有毁灭性品格。在这一点上,新主体性充分倾听反现代性浪潮对欲望的批判。欲望的对象性使主体置入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中。这一冲突既可能造成他者的不幸,也可能带来自我的毁灭。在“非非”的意义上,我们肯定欲望的排他性。但是这种肯定不能过渡到一般意义上,不能说欲望的任何排它性行为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当欲望导致自我毁灭的时候,欲望就成了反主体性的能量,更无法被接受了。历史上的主体性理论,比如中国古代的伦理主体,之所以不接受欲望,并非全错。
新主体性既要接受欲望又要避免欲望带来的灾难,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让欲望成为被携带的因素,由携带者制约欲望,达到用其善,去其恶的目的。可充当携带者的就是能力。能力(capability)包括现实行为得以发生和实际发生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能耐(ability),也包括尚未展现的潜能(potentiality)。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能力具有多样性、既可是实践的,行善的,思辨的,理性的;也可是认识的,审美的,想象的,超理性、非理性的。依靠能力的包容性,能力主体既超越理性主体,功利主体;也超越非理性主体、反功利的纯粹审美主体。对主体来说,能力具有绝对合目的性。从消极角度而言,它本身不具有欲望那种自伤和伤人的“劣性”,它只是在被欲望绑架引向对象性情境造成恶劣的伤害性效果时,才是有害的。但这种有害,是它没有被有效定位的结果,不是它本性的表现。“艺不压身”。能力本身不具有伤害性。从积极角度来说,能力既可以直接成为主体幸福的根源,也可使欲望实现因而给主体带来幸福。
能力可以携带欲望是因为能力可以超越欲望。能力与欲望有本质区别。能力是自体性的:能力的现实实现,是主体的自我心理体验。欲望是他体性的:欲望的现实实现,是对外在对象的占有。欲望区别于能力的他体性常使欲望在脱离能力的情况下恶性发展。人们常说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金钢钻却搅瓷器活的现象就是欲望脱离能力的恶性发展。当这种恶性发展逸出道德法律的规定,带来的就是可怕的结果。不幸的是,这正是今日中国常可看到的现实。
能力的自体性决定了它高于欲望,可以直接进入主体性中,成为构建主体性的主体成分。中国古人说:“有得于内,无待乎外”。能力体验带来的幸福满足感具有充分的合目的性。在此一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相比。欲望的满足也能给主体带来快乐。但欲望满足的快乐具有自身耗散性与外在指向性。欲望一当满足,其所伴随的快乐会马上耗散,主体或者因此而懊悔不已,或者因此而被推向对更丈目标的争夺之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29首对此有深刻的解读。能力因为是自体性的,能力的获得便成为主体完全能够自我驾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主体性不仅不消失,反会进一步加强。欲望的实现则不同,它的外在对象性使欲望主体受控于客体。其所争取实现的过程极可能造成主体性流失,甚至完全丧灭。历史上为仁人志士们痛斥的“奴性”“媚性”就正是这样的情形。
能力能够携带欲望也是因为能力与欲望紧密关联。一方面,欲望依赖能力。在正常情况下,欲望的产生和强化是因为有能力的支撑。不存在毫无能力支撑的欲望。当人的某一能力完全消失,欲望也就会消失。而当能力形成,与之相应的欲望就跟着产生。另一方面,能力也依赖欲望。能力不具备直接存在的实体性。能力要寄生在实现欲望的行动上。欲望的实现也是能力的实现。欲望既能把主体的潜能激活又能把主体推入实践并经由实践使主体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能力可以成为心理体验的对象,但当心理把欲望作为直接对象的时候,能力的体验是潜在的。当心理反过来把能力体验作为直接对象的时候,欲望的实现便转化成为潜在的过程。成为潜在的因素,只意味着主动性品格的消失,不意味着本身作为构成体的消失。经由自身品格的降低,欲望进入了主体性之中。欲望的多种作用得到发挥。欲望继续成为维护主体生命、提升生命境界、促使自我意识生成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因为受能力的制约,欲望的恶性被克服,只留下了它的合目的性一面。欲望经由能力的提携实现自身,能力则借助欲望获得自身的存在,实现其构建主体性的目的。依靠欲望的作用,主体于是顺利地成为能力主体。在能力与欲望的合一中,主体性于是得以生成。新主体性于是成为超越欲望的能力构成。
断定二:超越空间的时间性规定
人类历史上传统的生命建构本质上都是空间性的。西方的神学以永恒的天国作为生命的最终归宿。古希腊人头脑中恒在的奥林波斯山是最高的生命境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理想国均是永恒在场的世界。以天国模式和理念模式为基础,后世许多欧洲人包括以追求社会变革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编造了无数乌托邦神话。中国历史上虽没有永恒天国的设想,也没有相当精致的对永恒在场(理念)的哲学论证,但是中国人的永恒意识较之西方人更强烈。中国人头脑中的“天”、“道”、“理”、“心”、“三不朽”、“纲常伦纪”、“青山明月”都是永恒的空间性建构。中国民族用在巫术意识基础上生发的宇宙本体论和伦理本体论融合的永恒设想来范导、构建自我的生命,希望自我的生命在与社会伦理(纲常伦纪)宇宙自然(天道、日月)的融汇中获得永恒。中西的一大差别是,西方自现代性运动发生以来,传统的空间性建构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浪漫主义运动尖锐地凸出了此世生命的时间性。尼采、海德格尔一直到当代的后现代主义,一个基本的思想主题就是对浪漫主义的时间性体验给予哲学上的论证[7](P22-24)。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风靡当今西方世界,就在于它以对永恒性的彻底颠覆构建了它自身的最深刻的合理性。由于没经过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思维的颠覆性冲击,也由于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本来就具有结构上的超稳定性,当代中国人事实上仍在把空间性作为构建自我生命的理想维度。
新主体性将生命定位在时间性上,认定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觉接受生命的一次性,瞬时性,让生命的一次性、瞬时性经由自身的努力充分的显示出来;而不是以作为最终目的之虚幻永恒空间的建构来对抗时间。生命的时间性定位意味着完全接受西方自浪漫主义以来的反空间性的基本立场。但反空间性并不是绝对排斥空间,而是说要倒转传统的时空结构。传统的西方和东方也并不要求绝对的空间性,而是坚持时空一体论;将空间作为基本因素,置时间于空间的辖属之下。基督教神学认定永恒天国的获得需要在原罪的净化之后。原罪的净化是一过程,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性在这里是构建空间性的基础;但它的意义与必要性又受制于空间性。传统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经验性时间意识,总为时间的流逝而忧伤。“一尊酒醒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国古代诗人沉缅于此类时光流逝的伤感之中。但最终建立中国人生命意识的却又是空间。这一空间在理学家那里是“道”、“理”,在诗人那里则常是宇宙自然;因为“青山依旧在”所以能“一壶浊酒喜相逢”。
新主体性要求将传统的“空—时”建构倒转为“时—空”建构,以时间作为合目的性的基本因素,将空间作为受制于时间的成分。新主体性吸收历史上所有关于时空同一性的论证,包括辩证法所说的两者概念上的相互依存性。新主体性从时间本身来论证空间的存在。主体对时间性的领会、把握必然同时带来对空间性的领会、把握。时间的存在依从于人类整体性的意识对时间的觉知。既然有对时间的觉知,就说明“时间”有可以让主体觉知的“标志”。但从逻辑上说,时间本身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标志的,因为时间本身是流动的、无区别的。那么这一能让主体把握讨间的“时间标志”显然不是时间本身的,而是“外借”的。从何处借来呢?只能是从空间来,从拥有空间性的存在物来。可见,时间性内在地包含了空间性。时间虽然在目的论上超越空间,但它又是以空间为基础来构建自身的。
新主体性从时间之内求空间;要求在承认时间压倒性的基础上,让空间有其充分的展现。新主体性的这一要求导致“此际”在时间纬度上拥有本体论的意义。
此际不同于过去未来。此际是“时—空”结构,过去和未来都是“空—时”结构。在传统的生命哲学中,过去和未来都以牺牲此际为基础。艾略特有诗云:“现在时间和过去时间,/两者都寓于将来时间,/而将来时间又存在于过去时间。/足球在记忆中轰鸣。/沿着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朝向一张从来没开过的门,/里面有玫瑰的花园。”[8](P222)(拙译)艾略特虽被称为现代派诗人,但他此处表达的是传统的时空意识。其中,此际是被牺牲了的。此际的“牺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意义的剥夺:此际没有意义,只是为过去或未来作准备。基督教文化重视的是未来,此际的努力只是用来购买通向未来天国的门票。中国传统文化则如钱穆先生所言,重过去,向后看。“依照中国人的观念,奔向未来者是欲,恋念过去者是情,不惜牺牲过去来满足未来者是欲,宁愿牺牲未来迁就过去者是情,中国人观念,重情不重欲。”[9](P9)“牺牲”的另一表现是现实性的取消。这主要发生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历史上的精英文化提倡用此际生命的空洞化,即用纯粹的心理感受,来保持对过去的承纳。儒道所提倡的“静思”、“慎独”、“心斋”都有此偏颇。中国历史上抒情短诗极为发达也与此种心理有关。中国诗史上几乎所有名作都是在“恋旧”;所不同者,只是所恋的“旧”有别,或者“恋”的方式有异。后世文人对于空谈心性的批判也反过来说明了传统生命的空洞化有多么严重。空洞化的承纳使主体沉湎于怀旧之中,失去对现时生活的热情,取消对当下人生情境的投入。《长恨歌》中的后期唐明皇就是一个典型的怀旧形象。唐明皇灾变后的爱在中国文人的诗性建构中具有极高的地位。那种“芙蓉如面柳如眉,到此如何不泪垂”的回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的哀痛,“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执着,使很多人泪下。在失去此在性生命质量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怀旧性的爱的确伟大。诗中唐明皇自己灾变前后情感质量的巨大差异已经对此作了雄辩的论证:在马嵬坡变以前,他的现实此在的爱是苍白肤浅粗俗的,只是当爱已经化为回忆以后,其内涵的精神性品格才生长出来。但是中国诗性的这种非此在性结构未必就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比如爱情,难道就不能把唐明皇那种非此在的伟大转入到此在之中来吗?
此际不能为过去和未来作牺牲。生命的真正现实性形式只能是此际。所谓“过去”“未来”并不具有真正现实性品格,因为过去和未来都必须经由此际去创造去形成。离开此际,无所谓过去,未来。就人的身心结合所构成的生命的完整性而言,人总是生活在此际的;不可能生活于过去或未来。过去和未来作为人所能把握的时间纬度是经由人的心理想象来构成的。生活的此际性并不排斥作为心理活动形式的回忆和想象所具有的意义。被回忆的事与回忆本身应区分开来。被忆之事不具有现实性,并不等于回忆本身不具有现实性。唐明皇灾变后对杨妃的爱已经不具有现实性了,他已经不可能再去建立两人之间相互的富有诗意的现实肉体关系和精神关系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回忆作为心理活动也没意义了。事实上,唐明皇的回忆意义重大。《长恨歌》的千古魅力都是由唐明皇的回忆创造的。回忆作为心理活动本身是此在的。唐明皇的回忆也是如此。包括唐明皇之忆在内的历史上的伟大回忆所具有的悲剧性就在于它们总是以“被忆之事”和“忆”本身的矛盾分裂为前提。人类应为之努力的是去掉它们的分裂,让被忆之事与忆本身、与此际的生活本身相融合。乔伊斯名作《死者》中所描述的主人公去旅馆途中的回忆就是融合的情形。他正处于与爱人相恋的现实中,初恋时的幸福回忆这时涌上心头,把他此刻的爱感推向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胜境。此际不能为过去和未来作牺牲,就正因为此际具有能够囊括、承纳过去和未来的“母性”。此际的“承纳”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论证。此际的真正现实化,在于它的唯一性的获得:生命在这一时刻的经验具有它的不可重复的唯一性。此际的唯一性使它与“过去”构成区别,同时也就提升了“过去”的价值,使“过去”不可能被生命主体忘记。这是对比性的提升。更重要的还有“自身性”的提升。“此际”规定了它自身的“非此际性”:它在瞬间就由“此”转化成为“彼”,成为“过去”。它作为“过去”能够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正是因为它当年以“此”的身份出现时,曾经拥有辉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新主体性不认同当年的“沧海”“巫山”对于今日生活的剥夺,但是热烈欣赏“巫山”“沧海”当年的辉煌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不可消失性”。“过去”的伟大意义不就是它的不可消失性吗?这种不可消失性只能来自于此际的创造。此际的唯一性使生命的可能性被打开,于是可以刺激生命投向未来,以寻求更大的可能性。由此,“未来”同样被得到了。此际的获得是此际被“充胀”的结果。此际最大限度的被充胀离不开“过去”与“未来”的进入。过去、未来的因素以潜在的、隐约幽微的方式进入此际的生命,此际才被“充胀”。生命辉煌的瞬间正是过去因素和未来因素同时涌入的时刻。对未来的想象、期待,对过去的回忆,品味,它们与“我”此刻身处的情境汇合在一起,这才构成生命的此际性。在“此际”的这一构成中,生命拥有了过去与未来,但又超越了过去和未来。
生命的此际性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存在非常严重的误读。误读的突出表现就是“及时行乐”:以消费性享受来消除时间流逝引发的内心焦虑。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及时行乐”包含了对生命的时间性的充分觉知,但它并非对时间性的真正接受,而恰恰是企图以空间性的自然生命来对抗时间。在这种对抗中,时间被表象成了外在的入侵者,自我被定格为空间性的在者。这种对抗实际上是徒劳的,不能使主体获得肯定性的人生体验。
生命的时间性认同建立在创造性基础上的生命的碎片化体验。传统的空时性生命建构重视身份(identity)。身份实际就是内在的生命空间。生命的时间性击碎了身份,生命不再显现出完整的结构,而成为碎片的流体。从身份心理出发,碎片化是可怕的。追求现代性的西方人已经而且还在承受这种碎片化带来的打击。碎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将会越来越强烈。相对于传统中国式的生命建构来说,碎片化将是极为可怕的灾难。面对碎片化,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和应对。第一种态度是从传统心理出发,拒绝它。这种方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碎片化的必然性内在于人性自身的结构之中。承认主体生命的能力性、创造性、时间性建构,就必须接受碎片化;反过来,就只有回归古代式的灾难性生存。第二种态度是顺应生命的发展,接受碎片化;从生命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出发,挖掘能让我们承受碎片化的生命力量。其实如果我们不从身份层面要求生命,而是从“能力”层面理解生命,生命的碎片化并不可怕。早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济慈就倡导过碎片化的经验。他的著名诗学理论“否定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说”认定:在诗性创造中,身份是破碎的[10](P41)。济慈虽然感觉到了碎片化的伤害性,但还是欢迎它。济慈显然从中获得了幸福感。碎片化之所以并不必然是伤害性的,是因为它以能力的体验为基础和目的。济慈的碎片化如此,新主体性认同的碎片化也是如此。能力是主体身上较之身份更为深层的构成因素。它是主体性的最终存在。身份破碎了,能力还在。只要能力还在,主体就还在,生命就还在。正是身份的破碎,可以将能力的存在凸现出来,生命因此可以进入更为深层的自我体验之中。碎片化之所以并不必然是伤害性的,还因为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绝对排除生命的空间性。首先,碎片化在一定层面上将主体生命确认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碎片”是相对于“整体结构”而言的。只有内在构成因素丰富复杂的结构才会破碎。由单一的因素构成的物体是不会或难于破碎的。花岗岩就是如此。不会破碎的物体没有内在空间。人的生命易于破碎,恰是因为生命的内在构成具有复杂性,具有内在的空间性。生命的碎片化实际上就是生命的内在空间的外在时间性呈现。其次,“碎片”即使碎了,也仍然可以有同其他碎片的关联,纵然这种关联是微弱的,但它必竟存在。这种关联同样是空间性的。另外,“碎片”本身同样可以有、可能有内在分裂,也就是说有内在的空间性。事实上,正是因为有内在空间,“碎片”本身才有进一步破碎的可能。一方面,生命可以用“不断碎裂”来描述。另一方面,碎裂又是以空间性为基础并含有空间性的。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碎片化体验都能够给人以合目的性的幸福感。存在那种建立在纯粹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中的自我不是主体,而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自我完全困陷在外部力量的作用、撕裂之中,生命被撕裂成了碎片。这样的碎片化是绝对灾难性的,它无法转化成合目的性的幸福,因为在这种碎片化中主体失去了对自我能力的体验,主体完全瓦解了,生命落入了完全的死亡状态。摆脱纯粹经验主义的碎片化,主体在自我生命能力的层面定位,主体就由被动的撕裂走向主动的生存。应该说历史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完了他们的生存之旅。新主体性所认同的正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收稿日期:2004-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