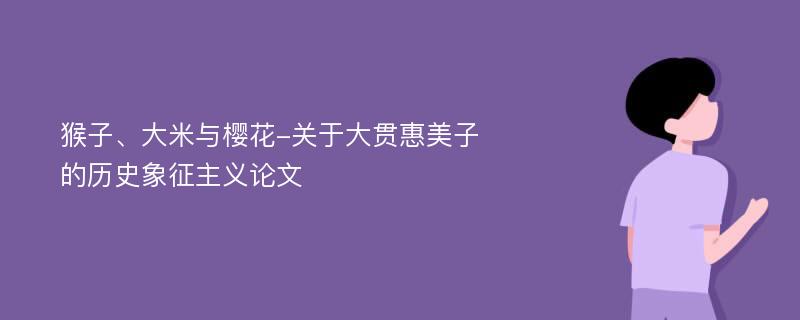
猴子、大米与樱花
——关于大贯惠美子的历史象征主义*
张沐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大贯惠美子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在她的诸多学术研究中,给予“物”的象征意义以极大的关注。她主张从历史中“物”象征意义的变迁入手,通过“物”的一词多义、政治势力的渗入与象征的非具体化等方面进行叙述。首先,她重点阐释了猴子、大米、樱花三个“物”在日本历史中的象征意义变迁。以此为基础,她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分析了“物”象征意义的变迁过程如何被国家利用,并通过表述集体自我的形式将文化与政治的民族主义建构为爱国主义,从而意识到在象征意义的政治化过程中,非具体化的象征有着独特的作用。她运用了制造日本天皇神秘感的例子,揭示了不可见的和无法听到的政治权力如何以一种“具体”的象征呈现。
关键词: 象征意义;历史背景;政治权力
一、引言:大贯惠美子与象征意义的建构
大贯惠美子教授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的威廉姆斯维拉斯讲座教授(Williams F . Vilas Professor),古根海姆奖获得者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她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专注于象征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共有16部独立著作,其中10部为英文专著,5部为日文专著。其所著的《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和《樱花、军国主义和神风特工队: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两部专著现已有中文译本,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大贯惠美子提出的“社会内力和外力关系讨论,要遵循每一个文化的历史和自己的历史脉络,但每个社会的历史又会出于外面历史力量的交汇点”这一观点是否自我矛盾[1];以及她通过为樱花辩护,从而在还樱花一个无邪的同时,也用这种无邪照见我们的当下。并且始终对“发明的传统”及其背后的脉络,保持一种清醒和理智[2]等论述,在中国人类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这两部著作之外,大贯惠美子教授的《猴子作为镜子:日本历史与神话中的象征性转变》(Monkey as Mirror: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Ritual)和《杀人之花,政治空间中的交流不透明性》(Flowers That Kill: Communicative Opacity in Political Spaces)这两本书对象征意义的变化和社会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指出了象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隐晦且不具体的。
在大贯惠美子对于“物”象征意义的研究历程中,她先是通过对猴子、稻米和樱花在不同历史时空下象征意义的变化,来叙述象征意义和社会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随后,在《杀人之花——政治空间中的交流不透明性》一书中,她对自己之前的研究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通过这次梳理,她意识到曾经对交流不透明性(Communicative Opacity)[注] 交流不透明性: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下,由于个人从相同的象征中描绘出不同的含义而导致的交流或相互理解的缺失,或者更常见的是由于他们头脑中对所描绘的含义缺乏清晰的认知。这就导致了所涉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缺乏交流的意识。(Ohnuki-Tierney, 2015 2) 的忽视。首先,大贯致力于让人们意识到这种交流的不透明性在利用集体象征性来促使不同社会群体被分隔的过程中扮演了的重要作用。正如西敏寺所言,“人民所同意的事情,和他们同意的事情的真实含义是不同的”[3]158。为此,她从政治扭曲“物”的传统象征意义入手,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何以成为政治民族主义直至演变为爱国主义。
2012年统计,全国有600座城市编制了城市防洪应急预案,占有防洪任务城市的95%,比2010年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很多城市着力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防洪排涝应急预案体系,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例如,北京市对下凹式立交桥、排水泵站、易积水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逐一制定应急排水抢险预案,提高了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长沙市在编制城市防洪预案和排渍预案的基础上,要求每个涉水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编制防汛预案,报市防指审批,并适时组织督察,以保证每个在建涉水建设项目的防洪安全。
为此,通过对象征,尤其是与政治权力相关的象征进行分析时,大贯惠美子发现非具体化的权力象征形成的交流不透明性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统治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即布迪厄说的“制度化的循环其实就是统治阶层的惯习在向下灌输”。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底层人民则会无意识地志愿支持上流社会惯习的支配,并把这认为是“合法的”和“自然的”。因此,一、象征性的权力是不可见的;二、单一系统内的信仰与价值受到了直接从运动中获益的人和被压制的人的共同影响;三、非独立的象征力量会因为一个外在的社会环境,从而来凌驾于个体的非言行力量之上[4]23,113,118,170,209。
二、象征的形成:“物”象征意义的变迁与背景
猴子、大米与樱花,是大贯惠美子在其学术生涯中给出的三个经典例子。通过这三个例子,大贯尝试以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不同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如何将一些不可感知的象征意义,通过“物”这样一个具体的形式得以展现出来。在论述中,大贯惠美子体现了其对于“物”象征意义变迁史的尊重。通过对“物”象征意义演变过程的详细叙述,细致地阐释了“物”被赋予特殊象征意义的逻辑过程。
研究导轨架结构,主要对标准节结构进行分析[1]。标准节由主弦管、斜腹杆、齿条、角钢框架、螺栓、螺母和销等组成,其端面尺寸有180 mm×180 mm、500 mm×500mm、650 mm×200mm、650 mm×650 mm、700 mm×700 mm、900 mm×650 mm等类型,同时,不同的类型的施工升降机,具有不同规格的标准节。因此,其结构十分复杂,参数又多,如果每设计一种导轨架都用三维软件重新建模,需要人工输入的数据很多,工作量大,很容易出错。而各种标准节主要组成部分基本相同,设计过程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的。
对于民族主义如何成为爱国主义的具体锻造过程,大贯惠美子认为“传统的再造”(refashioning of tradition)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都会涉及历史与现代的紧密关系的建构。并用自然化的方式,使得“历史的连续”替代了“历史的断裂”[7]。大贯惠美子没有选用“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和“物化”(reification)的概念,而是使用“传统的再造”,首先是为了强调连续和断裂的共存,“再造”即可以与个别文化现象,也可以与整体文化相关。再者,历史连续性中是有变迁的,“再造”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的能动性。这进一步强调了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能动者的积极参与[7]298-299。在这一基础之上,大贯尖锐地指出,美学往往会掩盖上述的自然化过程,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把当下和“纯洁”的过去连接起来,进而忽视了历史过程中令人讨厌的“污染”过程。例如樱花在军国主义时代的象征意涵,就是典型的国家对历史上樱花丰富象征意义的利用[7]304-305。
新型消能减震复合墙板试验与模拟的骨架曲线、滞回曲线如图4所示,其试验平均值与模拟值得到的关键点数值对比见表2。由图4和表2可知,不同位移下的试验结果与有限元模拟分析结果相差很小,误差基本在20%以内,有限元模型能较好的反映构件的性能,表明数值模型基本是正确合理的。
护理前两组心理健康指标汉密尔顿相关指数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试验组心理健康指标汉密尔顿相关指数的改善幅度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春风过柳绿如缲:有关部门好好查一查,把赚到的赔偿金都弄到哪里去了?还有音集协收了钱真的交版权费了吗?
在对猴子、大米和樱花的象征意义变迁进行叙述分析之后。大贯惠美子在厘清一个“物”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象征意义变迁的过程与逻辑的同时,更进一步意识到象征意义会被国家和政治势力重新建构。为此,大贯在她后续的研究中对国家与政治势力如何逐步渗入到象征的建构中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受到格尔茨的影响,大贯首先从象征意义与集体认同的关系入手。将认同作为被社会群体依据“假设给予”(assumed given)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品质特征[9]250-269。她认为以象征意义为基础的集体自我认同,存在着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选择的解释路径也不尽相同。其中,大贯认为在与自然相关的集体认同中,如何选择性地表述最为重要,土地和血缘则是最常见的集体自我的象征。而血缘和土地在产生象征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断向外衍生的过程。例如土地的象征性就会延续到土地所产的农产品和在这片土地上所饲养的动物之上,即从“我们的土地”(our soil)到“我们的食物”(our food)。而实际上,这种“我们的食物”(our food)更加近似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10]128-130。
与此同时,在一个群体遇到他者时,集体自我认同的选择,即重申我们是谁就显得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也极易发展成为文化与政治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其高度依赖国家层面深入的、内在化的教育文化性的保护。区分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是大贯非常强调的一点。她认为前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个体带有自愿性质的喜欢、爱和对国家的归属感。而政治民族主义则是由国家协调整合在一起的,致力于去宣传“意识形态”,并利用统一的体制和结构来承诺或是证明权力[10]130-131。通过国家目的的宣传,政治民族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不同,则是更为强调一个个体对民族,对国家乃至于对一个团体的忠诚性,进而成为一种“政治性的附属”(political belonging)[10]132。
三、象征的建构:从文化与政治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
在对樱花如何成为军国主义象征意义变迁的阐释上,大贯细致地举出了樱花在日本不同时期的具体象征意义,并解释了每一次樱花象征意义变化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社会变迁。大贯惠美子对樱花的叙述是从其在日本古代为生活、青春与活力庆祝的寓意开始。她指出樱花最初的象征等同于稻米,是日本农业生产力的象征。因为农业社会的美学影响,樱花美学扩展到其他美丽的人和事,包括妇女的生育能力以及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7]39-49。大贯同时也发现樱花在日本历史上就具有一词多义。在日本古代传说中,樱花就有着“无比光荣又无比悲哀”(unparalleled glory and unparalleled sorrow)的含义[8]21。樱花表征与生死之间更有着极其微妙的平衡,当樱花表示生、死和再生等的其中一个阶段时,它总是预示着其他两个阶段,当这种平衡如果稍加打破,就会把生命力和再生象征转为死亡。樱花又因为其花期的短暂性,成为生命短暂的象征。生命的短暂又和日本文化中怜悯短暂的美学产生密切的关联[7]50-55。这一系列传统的象征意义在军国主义时期被日本官方加以利用。在大贯看来,军国主义时期把樱花等同于为天皇牺牲,与靖国神社附近种植大批樱花有着紧密的关系。靖国神社作为一个为阵亡武士招魂的场所,在那个年代变成了祭祀忠魂的场所,落樱则成了为天皇牺牲军人的象征。樱花象征意义与军队之间的紧密联系,更通过将樱花在日本军徽中的重要角色和军队歌曲等形式进一步地加以强化[7]126-129。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过程中,樱花的象征意义不仅被用作军队的军国主义化,更深度地融入了国民的军国主义化中。在大贯看来,樱花象征被利用到国民的军国主义化中,主要通过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再到军国主义的演化路径,例如在教科书《樱花读本》中,先通过对樱花、富士山和升起的太阳体现文化性的民族主义,而后通过日本经典的民间故事“桃太郎”的剧情相结合将其与极具政治性的太阳旗升起相关联,进而出现了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玩具兵和军舰等形象。此外,校歌、流行歌曲、流行喜剧也与教科书一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并引领民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工具[7]146-175。
日本文化中的猴子,在大贯惠美子眼中是第一个可以展现象征意义如何与时代背景相联系,并随之改变的重要例子。最初在日本,猴子被认为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但这一理解,随后又认为会是一种对人与动物边界的威胁,并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替身。时至今日,猴子更多的被视为娱乐人类的小丑,猴戏通过对最基本社会文化设想的挑战,来引起人们的嘲笑[5]226-228。猴子之所以在古代日本被认为具有神圣性,主要和比克猿(Saruta Biko)与太阳女神(Sun Goddess)的神话故事,以及作为山神的使者的传说[注] 猴子在日本传统宗教的山神信仰中,被作为”sanno shinko”。由于这个信仰,猴子的功能被指代成了“猴神”,或者“saru gami”,从而成为人和众多神灵之间的信使(Ohnuki-Tierney, 1987 43) 息息相关。由于古代日本将太阳女神视为日本人的先祖,同时在日本原始宗教的万神殿中山神又是最重要的神灵。二者的神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到了猴子身上。进而使得猴子被认为具备让马匹保持健康和治愈病马的超能力[5]42-48。但是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猴子由于尝试打破人与动物的边界,被认为是人的“替身”(scapegoat),进而备受歧视。在大贯惠美子看来,被日本社会认为猴子作为替身的含义源自于日本的一句传言即猴子是“少三部分毛发的人”(a human minus three pieces of hair)。这则传说表达了猴子作为一种低等的动物想要成为人类,以至于被嘲笑。然而,日本人对这则传言的理解却使得猴子被描绘成了不受欢迎人的代表,进而受到奚落[5]59-60。到了当代日本,猴子先是更多地用以展示日本文化,出现在众多的旅游纪念品上,成为新日本“现代”与“进步”姿态的代表。再者,与中世纪时猴戏是作为魔术师(Trickster),并带走人身上不祥之气的仪式性表演不同。在东京出现的一些新型猴戏表演中,猴戏更多是一种小丑表演,由驯猴师和猴子共同来制定,这样的表演既满足了人比动物更高等的设想,又回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分层中的原则[5]72-73。
这三个例子虽然变化的历史各不相同,但归纳来看,都是利用一个具体的“物”,并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从而使得复杂的象征能够以这样一种既直接,又不断变化的方式得以呈现。从人神媒介到替身再到小丑,猴子敏锐地展现了出了日本文化中自我与他者概念的转变过程。通过追踪猴子象征意义的变迁,我们能够察觉到日本社会思维结构的转变[5]74。大米虽只有一个含义,即日本集体自我的象征。但是这种“自我”经历时代的变迁,是通过日本人“作为自我的稻米”来检验。即许多稻米代表了许多自我。而这样的象征化过程,比一个简单的一词多义符号象征更为复杂和能动[6]156。而从樱花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象征及其意义不是孤立地分割开来的。樱花象征意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不同象征之间构成了一定的相互关联性,即象征是一个过程与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70。
大米在日本的重要性,最初是与日本人对于宇宙起源与传统宇宙观的理解息息相关的。在日本古代重要的祭祀活动如新尝祭、大尝祭和稻收日中,稻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日本古代最为重要的大尝祭中,稻米就是最重要的祭品。这些祭品通过祭献后的人神共食,并与大尝祭中人灵魂与身体更新的仪式过程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身体与灵魂上宇宙观的交换[6]54-57。此后,稻米和稻田与自然象征也紧密相连。在日本的版画中,反复出现稻米和稻作农业的主题。这不仅代表着稻作农业本身,并且代表了更抽象的东西,最显著的就是其标志着一年四季[6]107。在日常生活中,稻米会用作家庭生者与死者的共食,乡村社区成员的分享,同时也是人与神之间共食的物。米的这种共享性,更是衍生到了与米饭相关的“物”,例如饭勺就成为家庭主妇权力的象征。而清酒则引入一系列社会交换的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共享食物类型,以至于单独饮酒会被认为是最孤独的事情[6]113-115。由于稻田成为“我们祖先土地”的象征,农民们坚持用自己的种子来种植水稻,使得稻米稻田的双重隐喻强化了集体自我认同。在日本历史上,稻米更是被用来区别其主体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之间的关系。以农业作为日本表征把非农人口边缘化了,猎人的仪式就被认为是和农业对抗,并将这种特殊族群变为替罪羊。使得其在日本国内被赋予不纯洁的属性[6]116-117。到了近代之后,稻米在日本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其具有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功能。尤其是当接触西方之后,日本的对外关系趋于复杂化,大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场景中起到了既区分日本与西方,又区分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作用。在将日本与中国进行区别时,日本人的独特性就表现为日本的稻米是神米。并贬低中国米是“下等”,“吃中国米就会衰弱而死”[6]125。比较日本人与作为“他者”的西方人时,采用了稻米对立于肉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肉食是西方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此,在明治维新之后,一些人主张毫无顾忌地模仿西方,主张放弃稻作农业而饲养动物。并且认为只要日本人继续只吃稻米、鱼和蔬菜,他们的身体就不能跟吃肉的西方人竞争。时至今日,虽然米饭的量在高级烹饪中的量越来越少,但是在日本饮食中,米饭始终存在。即使如日式牛排这样深受西方影响的菜肴,在呈上的时候,米饭依旧是作为“就职”(主食)对立于菜作为“复职”(复食)[6]127-130。
四、象征的选择:具体化与非具体化
“物”的象征意义会被国家和政治势力曲解,进而去满足其政治性的目的。但与政治权力相关的象征意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并非由具体的“物”来展现。在一定的条件下,非具体化的象征有着独特政治魅力。政治权力的象征具体化与非具体化,在大贯看来与政治领袖象征的具体化密切相关。为此,她选择了欧洲与日本的政治领袖之间进行对比。在大贯看来,不同的宗教背景是影响欧洲的君主和独裁者与日本天皇,对于是否要用具体的“物”来象征权力的关键。欧洲的君主和独裁者之所以需要通过演讲、画像、标志、纪念碑、仪式和游行等具体化的象征来代表他们的权力。是因为欧洲有着“君权神授”(The Royal Power From God)的传统,君主们更需要强调其与神灵的关系,即君主与独裁者是被上帝所选择的,而非上帝本身[10]189-196。与欧洲不同的是,在日本,“非具体化”的象征是用以体现具体权力的。因为日本神道教中“魂”的思想,对于天皇的“非具体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魂”是神道教中神圣性的基础,而神的“魂”是不可以见的。这就使得神道教需要去隐藏这个神的“魂”,进而在神道教中很难将神具体化。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道教万神之中的一员,也就使得天皇“魂”的具体化受到了日本“魂”概念的阻碍[10]165-166。尽管天皇在出席公共活动中可以被看到,但是他始终站在远离日本民众的地方。至于出版的天皇骑着白马戎装照,却更多是在国外传播[10]167-174。
在大贯看来,以欧洲统治者为代表的政治领袖,通过将其权力具体化能够巩固他们的权力,并增强他们驯化人民的可能性[10]200-201。与之相反,日本天皇更倾向于通过图像和一些仪式过程强化天皇体系的象征,欧洲那样强化个体的君主形象在日本的政治哲学中是不可接受。为此,与欧洲君主的身体制度化不同,日本国家致力于防止将个体天皇的“身体自然”(body nature)具体化,从而努力去建构基于整个天皇体系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10]181。日本与欧洲的这种政治象征具体化的不同,最直接的影响结果就是在二战战争罪责的归因上,日本与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虽然在总体上日本宣传为天皇而战。但当重新检视这段历史则会发现,日本很少在战争时期提到天皇。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虚无”(nothingness),“黑盒”(dark box)或者是“一层不可见的网”(layers of an invisible net)而战。与之相反,尽管德国在战争中的一些行为是需要全体国民共同负责的,例如反犹主义。但人们依然能非常清晰地将德国的战争责任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直接关联。与纳粹党在战后的土崩瓦解不同,美国在战后认定天皇无需对战争罪行负责,进而保留了天皇的体系[10]180。因此,大贯惠美子总结认为象征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有一些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含义,另一些则只有单一意涵。包括非具体化的零信号物(zero signifier)与美学意涵等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交际的不透明性”。但这种“交际的不透明性”却往往被受到其影响的社会行动者们所忽视[10]203。
五、评论
从通过文献梳理对猴子、大米与樱花等“物”在日本历史上象征意义变迁过程的研究开始,大贯惠美子教授用了几十年的心血来探究“物”的象征意义与其所处时代间的紧密关系。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贯教授对于影响物象征意义的背景因素有了更为深入与抽象的思考。在其较早的两部著作《猴子作为镜子:日本历史与神话中的象征性转变》和《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中,她对于象征意义变化的论述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人类学色彩,偏重于史料的收集与叙述。到了《樱花、军国主义和神风特工队: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一书中,她对象征意义变迁的社会背景有了更为清晰的分类,尤其是通过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对比,直至爱国主义的建构。这一研究犀利地揭示了政治势力对于原本“纯真”的民族文化象征如何进行腐蚀。而在2015年出版的新书《杀人之花:政治空间中的交流不透明性》中,她更是提出了“交流的不透明性”这样一个极为抽象化的概念,而通过对她之前研究的重新梳理,大贯将她对象征意义研究从可见的具体“物”衍生到了不可见与不可听的零信号物。并进一步阐释了,她对于政治势力渗入象征意义的建构,并遮蔽人民的感知所带来的担忧。
大贯惠美子的这一系列研究也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早在写作《猴子作为镜子》时,大贯惠美子将结构主义分析与日本历史中的民间传说和文化分析相结合就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尝试[11]。到了“作为自我的稻米”一书中,大贯惠美子的研究则被认为是一种对历史人类学传统的继承,尤其是被认为是对利奇提出的“内部性文化辩论”(internal cultural debates)的实践[11]。而她对于爱国主义的研究,更被认为是在安德森·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并且更具挑战性地用回溯性路径来揭示日本的民族主义属于朦胧的“天皇体系”[12]。在大贯惠美子后期对于物质文化及其意义与价值转变的研究中,大贯惠美子笔下的樱花被认为运用了类似于西敏寺关于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架构。而她关于美学意识形态的关注,更被看作了是对布迪厄的“惯习”“区隔”和“误识”思想的一种回应[13]。
大贯惠美子的研究视角,在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独特的。不同于其他的人类学家,大贯非常强调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动态变化对于象征意义变迁的影响。在她的这四本著作中,她均是采用了一个宏观的历史视角作为切入点,以一个“物”在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变迁作为研究的主线。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的影响在大贯惠美子的研究中也是有着非常显著的体现。“物”象征意义之间的对比,贯穿了她几乎所有的研究,这其中既有同一个“物”在不同历史时期象征意义的对比,也有不同的“物”在统一历史时期的对比。此外,大贯惠美子教授在其研究中,更是注重与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对话,她尤其强调文化是运转中的一个动态过程,当文化的“核(core)”裂解和转化时,文化会形成和复制自身。为此,在大贯看来可以与后现代主义中对大分裂(great divide)的反思进行对话,她强调要对人类学这一学科和文化的概念本身进行一个历史学化,只有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历史因素的重要性,才能避免陷入大分裂新的伪装之中,从而将世界分为中心与边缘,并使得人类学家的研究陷入剥夺他者的共时范式[15]。虽然大贯惠美子这种重视历史因素对于文化影响的研究路径在人类学家中是独树一帜的,但她的研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同一历史时期,其他因素对于包括象征意义在内的文化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大贯惠美子对于历史影响的理解,极大地偏重于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对于非人的因素,例如气候变迁等自然因素则缺乏更为深入地分析,从而使得她的研究路径稍显片面。
参考文献:
[1] 石峰.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的历史世界——兼及历史人类学的相关讨论[J].世界民族, 2012(5).
[2] 张经纬.上海书评——她为樱花辩护:评《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J].澎湃新闻,2017-02-27.
[3] Mintz,Sidney.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M].New York:Viking,1985.
[4] Bourdieu, Pierre.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
[5] Ohnuki-Tierney, Emiko.The Monkey as Mirror: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Ritual[M].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6] 大贯惠美子.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空的身份认同[M]. 石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7] 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M].石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 Field,Norma.The Splendor of Longing in the “Tale of Genji”[M].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9]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10]Ohnuki-Tierney,Emiko.Flowers That Kill: Communicative Opacity in Political Space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1]Kelly William, Reviewed Work(s): The Monkey as Mirror: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Ritual by Emiko Ohnuki-Tierney[J].Ethnohistory,1990,37(1):76-78.
[12]Goodman Roger.Reviewed Work(s):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by Emiko OhnukiTierney[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994,50(3):651-652.
[13]Doak,M. Kevin. Reviews of Books: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esthetics in Japanese History[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3,108(5):1431-1432.
[14]Danely Jason.Book Reviews: Flowers That Kill:Communicative Opacity in Political Spaces[J].American Ethnologist,2016,43(2):392-393.
[15]Ohnuki-Tierney Emiko.Historicization of the culture concept[J].History and Anthropology,12(3):213-254.
Monkey ,Rice and Cherry blossoms -Historical symbolism of Emiko Ohnuki -Tierney
ZHANG Mu-y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 Professor Emiko Ohnuki-Tierney is a world-famous anthropologist. In her academic researches, she pays high attention to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ings”. She advocates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 change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ings”, especially from the polysemy of the “things”, the infiltration of political forces and the non-externalization of symbols. First of all, she focuses on the symbolic changes of the three “things” in Japanese history: monkey, rice and cherry blossom. Then, she analyses how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ings” is used by the state under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as the patriotism through the collective self. After that, she realiz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symbolism, the symbol of the “Non-externalization” has a special role. She uses the example of creating the mystery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to show how invisible and inaudible political power can be presented as an “Externalization” symbol.
Key words : Symbolic Meaning;Historical Background;Political Power
收稿日期: 2019-02-09
作者简介: 张沐阳(1991- ),男,浙江台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9)04-0113-06
[责任编辑:刘兴禄]
标签:象征意义论文; 历史背景论文; 政治权力论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