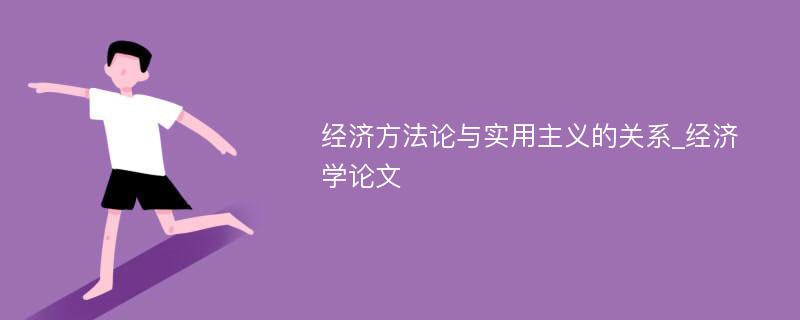
经济学方法论与实用主义思想之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实用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初,狭义经济学方法论只是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应用,然而科学哲学本身正在经受急剧变化,更具开放性。如今经济学方法论的工具箱越来越多样化,近年来复活的古典实用主义思想(包括皮尔士的实效主义、杜威的工具主义)以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也都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走向。新实用主义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结合,还引发了经济学话语分析的转向和经济学修辞学研究的产生。
一、实用主义思想兴盛的源起
经典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后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兴盛而衰落。近几年,它以新实用主义的形式重新回到了主流哲学的怀抱,并且是思想界增长最快的哲学框架之一。实用主义盛行的起因在于,它似乎能够为摆脱当代元科学研究的困境提供出路。当代元科学研究的困境是:一方面,基础主义的辩护困境在于“绝对确定性”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激进相对主义具有可怕的解构功能,能让一切都化为乌有。有人喜欢走极端:要么坚持科学理论具有客观的、绝对可靠的经验基础(即基础主义),要么承认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并无独特地位可言,甚至承认所谓科学只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磋商或谈话的活动。为什么非得非此即彼呢?实用主义企图找到一条合理的中间路线,为走出困境提供一种希望。它既反对坚持绝对确定性的基础主义,但是又承认科学确实拥有其特殊性。实用主义所预设的科学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实用主义是反基础主义的,它反对人类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也包括科学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但是它保留了科学(例如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知识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一观念。因为价值判断本质上是经验的,像科学一样具有实践性、社会性、语境性,并且具有认知或理论特征,原则上受科学方法的控制,这已经成为实用主义的中心原则。换句话说,实用主义相信,价值判断和科学陈述一样,同样遵守实用主义的座右铭。科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解决生活实践问题,在社会科学、伦理及价值判断领域同样体现着科学的这种特殊品性。
第二,实用主义模糊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此相呼应的有,哈金(Hacking)和卡特赖特(Cartwright)的实验实在论,加里森(Calison)的以实践为中心的观点以及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阵营中科学实践观的日益流行。在“社会学式对科学的研究”中实践的维度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在经典科学哲学中截然分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模糊。对于实用主义来说,严格区分“知道”(认知)与“做”(实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两者是相互渗透的。
第三,实用主义强调社会性。认知的社会性是一种普遍特性。实用主义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科学像人类生活一样,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社会性是我们的认知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而实践就是桥梁。传统认识论脱离了人的实践因而无法回答个人信念如何反映客观世界,而实用主义则重视实践行动、效用观念,这样使它能够幸免于难,并且又可以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理念相互接轨,科学共同体可以根据实际效用取得“共识”、达成一致。对于实用主义来说,人类知识产生于人类实践环境诸因的博弈过程中,虽然多因素互相缠绕但是却又引人入胜。
二、古典实用主义与经济学方法论的联系
古典实用主义以皮尔士和杜威为代表,他们的思想是基于上面所提到的核心原则。皮尔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很大,文献也很多,这里只集中讨论一个明确的案例,以说明古典实用主义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尤其是克拉伦斯·艾尔斯的经济学。他们之间有着清晰明确的联系。可以这样说,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杜威,而不是来自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克莱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在他的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1944)和《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1961)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他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制度主义中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美国制度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义在美国学界曾取得过支配性的地位。但在1940年代以后,制度主义逐渐被坚持新古典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取代。艾尔斯一直坚持着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将其系统化,建立了一个明晰的理论体系。
艾尔斯吸收了凡勃伦对演化的经济系统的解释,他最大的贡献是关于价值的技术理论或制度理论的系统阐述。阿兰·G.格鲁奇说:“艾尔斯关于价值的技术理论或制度理论,是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贡献,这更多地归功于杜威而不是凡勃论。”①艾尔斯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经济生产的物质力量的发展和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的演化关系密切。他将经济也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时,须将经济视为整体、动态过程来理解。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每一个人类文化都是“技术”与“制度”这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的不稳定的结合。技术与工具价值的力量是向前、动态与进步的,而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力量是滞后的、静态的和阻碍的。这两种力量代表了不同文化的两极,它们相互交织,它们之间的张力解释了任何特定社会的可观察的特征,而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源自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艾尔斯对“经验技术”与“仪式价值”的二分法(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务虚的)是他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基础,它直接来源于杜威的工具主义。那么,什么是“仪式价值”呢?那就是由文化风俗、制度化的等级、地位和权威所体现的。艾尔斯说:“正是从约翰·杜威那里我首次知道了认知的方式就是‘工具性’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一种以不间断的连续性运行的过程,并贯穿于所有社会的活动之中,并对所有的社会具有相同的意义。”②人类认知的过程就是杜威提出的“工具性”的务实过程,而不是作为文化风俗等“仪式价值”所表征的务虚过程。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③
艾尔斯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层面的探讨也来自杜威的工具主义价值理论。人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工具性的试错过程。在经济生活中也同样需要找到供给过程的有效途径,这只能通过与科学知识产生的相同的工具性过程而得以揭示。经济演化过程与经济活动中最为有效的供给效应,也与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一样是一种工具性的延续过程。在经济决策中所选择的评价,对价值分配的评估,应和科学研究方法一样,是工具性地证明了的评价。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的判断标准。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科学是技术的一种模式的人。对艾尔斯来说,正如杜威和其他的实用主义者一样,科学所具有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实用效果,“科学信念的作用效果比其他偶像的作用的效果要明显得多,科学并不触及上帝,但它确实能触及俗世生活”④。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是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的应用。工具主义一词的含义,经济学方法论中经常混淆不清。科学哲学中的工具主义主要是皮埃尔·迪昂提出来的,认为理论仅仅是预测的工具,只是对经验观测做预测的“工具”,并不是对真实世界的表征与诠释。另一种工具主义主要是启蒙运动后产生于西方的工具理性思想,认为理性包含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任何给定的目的,这一思想在后现代思潮中受到强烈的批判。杜威的工具主义则认为不仅仅手段,目标也具有理性的价值,与人类生活过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伦理道德领域里面工具理性的价值也是存在的。
最初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被博兰(Larry Boland)指认为科学哲学中的“工具主义”,从而引起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持久争论。后来尼尔·德·马奇(Neil de Marchi)和亚伯拉罕·赫希(Abraham Hirsch)经过广泛分析研究与辩护,提出弗里德曼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实质上是杜威的工具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应用:“‘所包含的概念应该被认为是在观察和整理现象时所使用的假设,因此应该由作用于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来检验’,这正是弗里德曼的立场,也是杜威工具主义的核心立场,当人们使用它以努力理解过去的经济经验以及预测未来的结果的时候,理论应该根据它具有多大的帮助作用来判断,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要根据它是否导致新的洞见来判断。”⑤
可见,在处理方法与实践、理性工具与目标的关系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在广义上说就是杜威意义上的工具主义。正如皮尔士也提出的,理性认知与理性目标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目标里面必然包含着研究事物,而研究事物必将会放入工作、生产和分配中,在当代知识经济时代尤为明显,实用主义必然要在认知与经济活动中建立联系。皮尔士为了强调他的观点的特异性(与詹姆斯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精细区别,他更偏向于科学性),更喜欢使用“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个词。如同经济学方法论家试图应用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这些公认观点来争论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问题一样,实效主义也许在方法论上是一种新的解释向度,因为它也可以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它与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是经济学的知识哲学。
皮尔士除了在实效主义思想上对杜威的启示和对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影响外,不得不提到他另外的有趣贡献,其实也可以看成经济学方法论对认知哲学和实效主义的反向的影响和应用。皮尔士将他的思想应用于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认知范畴的广泛的问题,这一观点在杜威的思想中得到延续并产生了新的洞见,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相反,皮尔士采用经济学理论对认知的成本—收益分析则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与实效主义思想的联系。
皮尔士利用当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条件来分析科学共同体的认知的成本—收益问题,也就是关于科学共同体如何分配它的资源以达到认知的最高效率的问题。他于1879年写了《关于研究的经济理论的说明》,这一论文最近受到广泛关注,是最早关于科学共同体对科学资源分配的分析,其实也就是他说的研究的经济学进路,或者称为科学经济学,这一点在另外一文中有具体的论述。⑥
皮尔士认为理性地决定在给定的时间、资金、精力的情况下,如何获得关于知识的最有价值增长是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最基本问题,并提出对策,即用成本—收益分析理论评价科学共同体的集体研究计划,以便在实现科学目标时最优分配有限的资源。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将各种项目的总效用和总成本之间的差别最大化,利用当代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条件作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假如对于一个项目来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可以增加对这个项目的计划与资源的投入;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就减少资源的投入。这样就可以为科学资源的分配、科学认知劳动的分工作出理性而实用的决策。这种分析科学共同体的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集体认知的有效产出的路径在科学经济学中非常流行。
但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皮尔士在方法论上是反对个体主义的,利用博弈论分析科学共同体有效产出的基切尔关注的是个体认知的重要性,认识效率是作为个体科学家理性的自利行为的相互博弈的结果。皮尔士则反对个体主义,将科学研究团体看成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他讨论的是宏观层面上的计划者的问题,在理想层面上科学共同体所作出的认知计划,而不是微观意义上的博弈过程。从皮尔士的研究可以看出,哲学思想与经济学方法论之间相互影响,难分难解。
三、新实用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是通过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工作,罗蒂的思想将古典实用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某些方面融合起来。罗蒂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显而易见。
新实用主义反基础主义并且反对追求确定性,强调知识总是处于实践和人类的利益之中,质疑传统认识论的表征主义(相当于“机械反映论”)理念,强调科学的社会性、理论负荷性及不充分决定性,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走向一致。罗蒂被称为“美国的尼采”,他提出“实用主义,我认为提供了后现代主义所有的辩证的优势却避免了自相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的修辞”⑦。
罗蒂思想最大的冲击就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中心教条的批判,这一教条被称为“镜喻”,认为人类的心智“像照镜子一样地反映”世界,按照“镜式”隐喻标准划分的表征体系具有一种客观性或特权性。要获得准确的反映或表征,就要对镜内所发现的表征做一个特权的分类,这些特权的分类基础就成为知识的基础,而知识论又是文化的基础。但是罗蒂认为“如果在镜中没有享有特权的表征,那么它就不再有必要成为决定我们的信念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试金石”⑧。
对罗蒂来说,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景与语境,没有超越的哲学立场以评判其他立场。我们寻求思想与行动方式的描述,永远没有一个“基础”,这些描述相对于所有文化传统而言,既不优越,也不会超越它们之外。他对科学的态度与古典实用主义一样,反对把科学看作获得真实表征的方法。他的立场远远超越了科学知识的研究,更有力地冲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如果科学与认知没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如果研究只有情境与视角,那么有什么理由有可能赞同我们的社会、政治及认知制度?在一个没有“第一哲学”与客观“基础”的世界里如何为自由、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辩护呢?
罗蒂的立场为:“努力做到我们不再崇拜任何事物,我们不把任何事物奉为准上帝,我们将所有事物,我们的语言、意识或共同体,看作是时间与机会的产物。”⑨从这里可以看出,罗蒂把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在一起。他说“一个依然能够规范行动的信念,应该依然被认为是值得为之坚持的信念,而人们十分清楚这种信念是由并不比偶然性的历史情境更为深刻的原因所引起的”⑩。
罗蒂的思想为将科学研究(特指“社会学式的科学研究”)当作话语或修辞学研究打开了大门,这种研究集中于人类的交谈(conversation),“除了交谈的约束,没有关于研究的约束,不存在从客体、心智或语言中导出的全面的约束,而只有由我们的同行研究者话语所产生的零星的约束”(11)。对于罗蒂来
说,科学知识是特殊的社会交流、交谈的结果。将科学广义地看作一种劝说,而这种劝说应当应用修辞学分析工具进行考察。
尽管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抵制新实用主义中的后现代思潮,为经济学方法论确定规范性的标准。但是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温特劳布(E.R.Weintraub),他采用受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以及SSK影响的思路来研究数理经济学的历史。
温特劳布最近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抨击是以罗蒂为自己的后盾。在他的文章里,他提出要把抽象的方法论从经济学里开出除去。他对方法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关于特殊领域中所进行研究探索的程序方法,一种是经济学学科中的特殊课题:那就是试图通过提供普遍性的理论说明来对特殊的经济理论进行评价。基于这样的分类,他提出方法论家所追求的那种普遍性的基础知识,并用这种知识去改造经济学家的做法是不对的,问题是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知识,方法论家并没有任何特权地位可以使他(或她)有资格对经济学家评头品足或进行“指导”。方法论家在理想中所追求的与现实完全一致的那种“永恒真理”我们难以接近,“相反,新实用主义者相信,我们是从我们创造的概念中构建我们的世界”(12)。我们构建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依据自然和现实进行分类的方法。温特劳布提出的实用主义目的把新实用主义更普遍的观点引入经济学中。
温特劳布对方法论的抨击与罗蒂对笛卡尔以来认识论的抨击一致。罗蒂认为,认识论的困难在于,并不存在可以与情景隔离开来的孤立的观察者,在进行观察时也没有光亮的镜子,相反,认识是对解释的解释,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解释、什么是独立的现实。真理并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一个纯粹的自然,真理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应付生活。罗蒂把知识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相互解释的信念网络。对知识的评价与判断必须根据信念之间的相互一致和支持程度来整体地加以判断。
知识对于皮尔士、杜威和罗蒂来说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正如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按照解释学观点提出的,文本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文本的建构与稳定都依赖解读者的“解释共同体”,而温特劳布就引用了费什的“解释共同体”的思想并引用到经济学中。他把一般均衡理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其他专业化领域均视为“解释共同体”的领域。
鉴于对实用主义与费什文本建构理论思想的吸收,温特劳布提出,方法论家不可能在根本上左右经济学家的实践改革,因为两者不属于同一解释共同体。来自方法论的批评都外在于经济学,因而难免会隔靴抓痒。“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理论,就像对通货膨胀率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内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建构通货膨胀理论。”(13)
可以看出,不仅经典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古典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思潮也渗透进了经济学的文献,凡勃伦—艾尔斯对经验技术与仪式价值的虚实二分法是整个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基础,它直接来源于杜威的工具主义,皮尔士—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正如皮尔士与杜威一样,艾尔斯也认为科学的务实性在认知上是独特的,它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处理生活世界事务的工具意义是务虚的仪式价值无法比拟的,因此代表经验技术的科学及文化制度实实在在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抽象的仪式价值则阻碍社会的发展,虚实之间的张力解释了任何特定社会的可观察的特征,而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源自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艾尔斯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建立在反基础主义的实用主义基础之上,杜威的工具主义为不同文化的规范评价提供了一个明确标准。因此,制度经济学如果不为政策制度提供指导,它就没有完成它的科学的任务。但是制度文化中有仪式(虚)和工具(实)两种文化,本身是有裂缝的,因此会引起“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这已经引起双方广泛的争论。一方是用工具主义价值原则为制度主义强硬路线作辩护,另一方为各种文化相对主义作辩护。前一种观点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还是无法不陷入某种“基础主义”,当然是指工具主义的实践与评价基础,具有规范性的一面。第二种观点受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不提供任何规范性的评价标准,而应保持中立性。
新实用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衍生出了一些相应的经济学话语分析路线,其中典型的是经济学修辞学研究,由麦克罗斯基(D.McCloskey)这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开创,经济学修辞学代表了在经济学和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及话语分析这三种声音之间的结合。
不仅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兴盛,今天的科学哲学也在经受着急遽的变化,它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由此导致经济学方法论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开放与多元化。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不久前我们开始注意到,国内学者柯华庆对于“实效主义经济学”早就有独到的认识。笔者惊奇地发现,柯华庆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简要地说,他的重要论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概括出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所采取的方法=皮尔斯实效主义重视解释与预测效果的推理逻辑。(2)他将用于经济的实效主义逻辑加以模式化。(3)根据实效主义哲学及其逻辑方法,认为实证经济学体现了科学的三个功能,即描述、解释与预测。现在加上更加重要的第四功能:控制。这个功能使得描述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结合起来,从而引出实效主义经济学。(4)基于逻辑与数学功底,柯华庆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博弈论的最大优势在于纳什均衡与一致性预测使得预测与控制成为可能,也就使得实效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成为可能。(5)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相结合,要让实效主义经济学真正用于提高政策与法律的实效,提出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具体方案与有益的政策建议。(6)更有难以估量的潜在理论价值的是,提出邓小平的哲学是典型的实效主义,而实效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等重大论断,并且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逻辑辩护。(14)这是将实效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起来的极有启发力的一种理论反思。
注释:
①Allan G.Gruchy,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Augustus M.Kelley Pubs,1972,pp.89-90.
②Ayres,C.E.,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1978,p.29.
③Ayres,C.E.,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1978,p.99.
④Ayres,C.E.,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1978,p.279.
⑤Hirsch,A.and De Marchi,N.,Milton Friedman:Econo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54.
⑥陈群、桂起权:《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知识经济学》,《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
⑦Rorty,Richard,"Is Truth a Goal of Inquiry?:Davidson vs Wright,"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45,No.180,1995.
⑧Rorty,Richard,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212.
⑨Rorty,Richard,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2,189.
⑩Rorty,Richard,Contingency,Irony and Solida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2,189.
(11)Rorty,Richard,The Consequence of Pragmatism (Essays:1972-198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165.
(12)Weintraub,E.R.,"Methodology Doesn't Matter,But History of Thought Might," In S.Honkapohja,ed.,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s,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pp.268,272.
(13)Weintraub,E.R.,"Methodology Doesn't Matter,But History of Thought Might," In S.Honkapohja,ed.,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s,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pp.268,272.
(14)柯华庆在2010年11月1日召开的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改组仪式暨“法律经济学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实效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后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