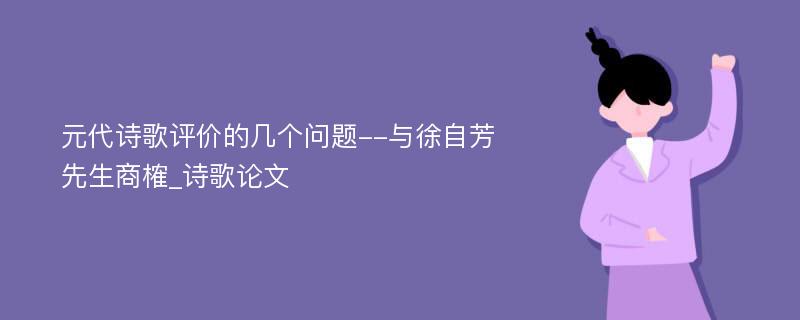
关于评价元代诗歌的若干问题——兼与徐子方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诗歌论文,评价论文,徐子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206.222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 期刊发了徐子方先生的大作《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笔者一向注意元诗——这个被人冷落的研究领域,能见到有关元诗的论文,自然十分喜悦。徐先生将元代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对元诗进行了评说,其中有些见地为不移之论,有些问题窃以为尚需做进一步的探讨。所以这里就评价元代诗歌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兼与徐先生进行商榷。
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时序》篇曾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也讲:“凡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版。)人们公认元代文学的代表就元曲,即元散曲和元杂剧,但这不等于说元代的文学仅仅有散曲和杂剧。所谓代表,是指散曲和杂剧的成就比元代其它文学创作更加突出。仅就传统的诗歌而言,我以为若要对它进行中肯的评价,首先要关照它产生的时代特点。徐先生的文章也说到了元朝的时代特点,但我以为叙述的不够准确,所以这里略作补充与更正:
首先应该看到,元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五代以来辽、金、西夏与宋王朝三百多年来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元王朝是一个空前强大、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个新王朝“起溯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注:《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第二,元王朝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文化传统,元朝的国制、体制、礼制、法制都承接了历代的王统与道统。以汉法治国是元朝的基本国策。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在他即位时就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注:《元史》卷四《元世祖忽必烈本纪》一。)“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注:《元史》卷四《元世祖忽必烈本纪》一。)至其建立大元帝国,更明确声称:“绍百王纪统,”(注:《元史》卷七《元世祖忽必烈本纪》四。)宣布“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注:郝经:《临川文集》卷三二《立政议疏》。)终元一代,正如《元史》所言,从忽必烈时起“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注:《元史》卷一七《元世祖忽必烈本纪》十四赞语。)
第三,元王朝是当时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最频繁、最广泛的王朝。是时,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天文历法、中医药、纸币钞法、驿站牌等都在此时传入中亚以致西欧,而域外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相应地传入中国,如欧洲的数学,回回的历法、医学、火炮、纺织、宝石,尼泊尔的范金术和建筑等。
第四,元王朝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而又尊重各民族风俗信仰自由的王朝。终元一代没有强迫其他民族必须遵从蒙古族的习俗和传统。这是一个各民族文化相对自由交流融合的时代。汉民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其他民族也吸收了汉民族的文化。而汉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在当时最具先进性,故少数民族汉化的现象在此时也最为明显。
第五,元王朝是一个实行种族统治和民族歧视政策的王朝。它将域内的民族分成蒙古族、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由于蒙古族享有种种特权,这就使元王朝从它的诞生起就埋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终其一代,各民族不断进行反抗元王朝统治的斗争和起义,就是这一政策执行的后果。
第六,元王朝在元祐年前基本上取消了科举制度,一大批汉人儒士流于市井,再加上那时城市经济相当繁荣,市民文艺发展,通俗文学中的说唱、戏曲、散曲、小说和民间文学就乘时而兴,一大批文人加入市井的创作队伍,推波助澜,更使俗文学的发展波涛汹涌。在此情况下,散曲和杂剧即成为元代文学的主流。这样,就大大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从而元代也就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大转折的时期。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样式——元代的诗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它必然要具有不同于其它时代的特色:
首先,元代取消了前代以诗赋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就是其恢复科举考试以后,也不再重视考试者的文学才干,而是“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元代主试者认为“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因而把“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注:《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这也就是说传统的诗歌在元代再不能作为考取功名的工具。元代的诗歌已失去了它曾经具有的功利性,它已完全成为诗人们抒发情性的纯文学创作,再也见不到过去那种应制诗了。
第二,正因为元代诗歌摆脱了功利性,诗人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地域辽阔的国度,他们笔下的诗歌就更加自由地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其中元代诗人所讴歌的边疆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大大扩展了传统诗歌的表现内容,同时也为诗歌增加了不少新的语汇。这些诗歌虽可说是前代边塞诗的延续,但其精神面貌却并不相同,人们只要打开耶律楚材、萨都刺、虞集、袁桷、柳贯、宋无、王继学、陈孚、员炎、许有壬等人的诗集,对此便会一目了然。
第三,元王朝地域辽阔,多民族杂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使汉族的诗歌深得少数民族的喜爱,这样一些汉化较深的民族文士也加入到了汉文诗歌创作的队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只要翻看一下顾嗣立所编的《元诗选》,浏览一下目录,就可知元代诗坛活跃着一支少数民族创作汉文诗歌的队伍。这是其它朝代所不曾有的特别的文化现象。我曾对这支队伍的组成进行过专门的考证与论述,(注:门岿:《元代西域诗人及其创作》,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 门岿:《论元代女真族和契丹族诗人及其诗作》,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门岿:《元代蒙古族及色目诗人考辩》, 见《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 )这些少数民族的诗人以他们优秀的诗作为元代诗坛增加了不少光辉。
第四,元代诗歌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发扬。当唐诗宋词将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顶峰之后,诗坛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继承前代的成就并将其发扬光大。历史已做了规定,任何事物都不会永远发展,当它成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走向衰亡。传统诗歌到了元代,已经没有再创新的可能,所以人们大可不必为元以后的诗没有创新感到遗憾。我们只要看到元代诗歌以唐诗宋词为大旗,为楷模,使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得到延续,就可以说元代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事实上也是如此,元诗承前启后,维护了发扬了唐诗宋词的良好传统。元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链环。
第五,元代文学是俗文学大发展的时代。元代诗歌既处于那样一个环境中,就不能不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与唐诗相比,宋诗明显地多议论化、哲理化和散文化,元诗要扭转宋诗的倾向,继承唐诗的传统,同时又受俗文学影响,只有向浅显一路挺进。不管元代诗人学唐还是学宋,他们都有意无意地随着时代的风气将诗歌作得比唐宋更加直白、通俗,甚至干脆采用散曲的新形式,写出全新的诗歌。散曲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就是元代诗人向民间诗歌学习的结果,是元代诗歌平民化的硕果。传统的典雅的诗歌变化为通俗直白的散曲,正是元代诗坛的重大成就。
第六,元代诗歌受时代文风的影响,不仅向浅显化道路发展,而且更与通俗文学合流、融合,这不仅仅是散曲的出现标志着传统诗歌失去了独占文坛鳌头的地位,就是散曲也成为最流行的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还有在杂剧中出现的更加通俗的宾白诗,这一切都说明在元代,诗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已被杂剧这种综合的艺术所“包容”(这里借用徐文中的用语)。元代的诗人有相当数量同时是散曲家,反过来说,元代的散曲家、杂剧家无一不是诗人。
元代诗坛的这些特点十分鲜明。到此就不得不对徐子方先生的论文进行一番讨论:
第一,徐文把元代科举的兴废看作划分元代诗歌前后两期的标志,以为科举的有无左右着元代诗歌发展的进程。对此,我不敢苟同。科举不过是封建社会诸种选官制度中的一种,固然唐代设立诗赋科目以考进士,对文人研究诗艺、创作诗歌有推进作用,但绝不能由此就说,有无科举关乎着诗歌发展的命运。在没有实行科举的时代,诗歌不照样取得光辉的成就吗?不照样涌现出了《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那样杰出的诗作吗?元代初年是没有举行科举,可是并不是由此就没有出现诗人和诗作。元代中期实行了科举,也不能说因为实行科举后,诗歌就有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和变化。况且元代实行科举时曾明言“罢诗赋,重经学”,此可以中书省臣的奏章为证:“今臣等所拟将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元仁宗览奏赞同,并下诏说行科举时“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注:《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向来论述元代诗歌分前后两期,不过是从元代诗歌本身风格稍微有所改变而言,而这种改变与是否实行科举并无关系。要说科举与元代文坛的密切关系,那不在传统诗歌方面,而是在新兴的散曲和杂剧。大批读书人一时丧失了传统的进身之阶,他们已无处去考取功名富贵,被迫流于市井,使他们加入到民间艺人的创作队伍,这就大大促进了元代俗文学的发展。
第二,徐文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戏曲与诗文相互冲突、此消彼长说。他说:“戏曲和传统诗文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两种生活观念和艺术追求,从整体上看,起码在元代二者还不是互相包容的关系,元曲大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等绝少染指诗文创作,而刘因、赵孟俛、虞集等诗文作家同样没有涉足戏曲领域。戏曲和诗文在文坛上的发展势头也是互相冲突,此消彼长的。”(注:引文皆见徐子方《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这种论说很值得推敲。
1、如果说戏曲与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 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定,那么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包容的问题,不仅元代不能包容,就是其它任何时代也说不上互相包容。如果一旦有包容,一种文体势必就要被另一种所取代,势必有一种文体要消亡。但也应看到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有巨大的涵盖力,它的体式可以融合诗词文赋等所有文学形式的创作成就。对于传统诗歌,它可以将有关的语句或整首诗改造或原样搬入剧中一定人物的唱词或宾白之中。一部《西厢记》其中融入前人多少诗词,历来的注解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而中国古典戏曲一向被人们称为“诗剧”,剧中每一唱曲无不是一首精美的诗,而其宾白中又有多少各种各样的诗!(注:门岿:《论元杂剧宾白诗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见《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依我所见,元代的戏曲与诗文只有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冲突;我以为元代的戏曲与诗文是同步前进,各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此消彼长。
2、中国古典戏曲是诗剧,中国古典戏曲作家都可以说是诗人。 不善于诗者,绝不可能创作中国的古典戏曲,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徐先生说元曲大家绝少染指诗文创作,我以为这种结论太绝对化了。元曲家中有不少人都曾进行诗歌创作,现以事实为证,如号称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既有杂剧《梧桐雨》,又有词集《天簌集》存世。而白朴的好友侯正卿,除作有杂剧《燕子楼》外,还有《艮斋诗集》十四卷传世,是著名的长寿盲诗人。南戏大家,《琵琶记》的作者高明著有《柔克斋集》,今仍可见其诗作。若从文献记载来看,则元曲家大多有诗文创作,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注: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名宦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注: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增补吊王实甫曲。《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马致远则自称“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注:马致远:《黄钟·女冠子》,见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86年版。)至于关汉卿的世交故友、杂剧家梁进之,则有人赞扬他:“行文高古尊韩、柳,诗宗李、杜流,填词似苏、柳、秦、周。”(注: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增补吊梁进之曲。)其它,像锺嗣成赞誉宫天挺“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赞睢景臣“吟髭燃断为诗魔”,赞赵良弼“醉后挥毫写旧诗”,记范康“诗题雁塔写秋空”,说沈和“五言尝写和陶诗,一曲能传冠柳词”,(注:钟嗣成:《录鬼簿》之钟嗣成吊诸戏曲家曲。)等等,就是锺嗣成本人除了作有《录鬼簿》及七种杂剧以外,同时“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注:《录鬼簿》附录之无名氏《录鬼簿续编·钟嗣成传》。)
3、至于徐说刘因、赵孟俛、 虞集等诗文作家没有涉足戏曲领域,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是有相当数量的诗文作家都在关心着当时的戏曲动态,并发表他们独特的见解。涉足戏曲领域与否,不只是要看他们有无戏曲作品,因为有戏曲作品,自可以称为戏曲家,就谈不上涉足不涉足的问题。就以徐先生所说的三个诗文作家而言,起码有文献可征赵孟俛与虞集都曾对当时的戏曲界发表有著名的论见,以致不断被人们所引用。赵孟俛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矣。”(注:朱权:《太和正音谱》之《杂剧十二科》引赵孟俛语,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 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虞集说:“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对元曲给予了肯定,此外他还对戏曲理论家周德清的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注:周德清:《中原音韵》之虞集序,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 册。)其它诗文作家如元好问、卢挚、胡紫山、冯子振、刘时中、仇远、杨维桢、陶宗仪、顾瑛等和当时戏曲界都有种种联系。胡紫山的《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等文,不仅论说了戏曲的演唱,而且也讲述了杂剧作家赵文益能作剧、演剧,还能作诗。(注:陈多等编:《中国历代剧论选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杨维桢的《周月湖今乐府序》、《沈氏今乐府序》、《优戏录序》等文更对杂剧家关汉卿、庾吉甫、马致远、白朴、王晔等人的创作成就或有关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注:《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至于仇远和杂剧家李致远的交往,卢挚和刘进中、胡紫山等一大批文人和杂剧演员们的交往与词曲赠答,在他们的文集和夏伯和的《青楼集》中多有记述。顾瑛的《制曲十六观》对当时戏曲编剧也有指导性的意义。(注:秦学人等编:《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陶宗仪的《辍耕录》更记述了金元戏曲多方面的资料。这些都已尽为人知,又怎么能够说诗文作家没有涉足戏曲领域呢?
4、 徐文说“延祐之后元杂剧的衰落也就必然导致传统诗文力量的增强”,徐先生把元代诗文和戏曲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互相冲突的关系,此消彼长的关系,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是不符合元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须知元代的戏曲包含有杂剧与南戏两种形式,元杂剧的全盛繁荣是在大德前后,元南戏的复兴是在至正年间。整个元代戏曲的发展轨迹,在杂剧来说是一个“凸”字形,在南戏来说是一个“凹”字形。有元一代戏曲都处于一种持续发展,不同剧种此起彼伏的局面。徐文论述元代戏曲只及杂剧而不及南戏,显然是不全面的。杂剧的衰落正是南戏兴起的一种原因,说杂剧的衰落必然导致诗文力量增强,这还是从科举有无决定着元代戏曲兴衰推导出来的结论。元初取消科举,是将大批读书人推向了市井,促进了杂剧作家队伍的迅速发展,但这绝不是元杂剧兴盛的唯一原因。同样后来科举的举行,也绝不是元杂剧衰落的原因。元代诗文前后期除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前后期的诗文作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思想与艺术价值也难说有多少高低之分。总体来说元代诗歌的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的态势。诗文与戏曲在元代前后时期始终是并行的,受传统思想牢笼的文人不屑于戏曲,这在元前后时期都没有分别;能向民间学习,注意新兴戏曲的文人都关注着戏曲,这在元代前后期也没有什么分别。一句话,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元代戏曲的兴衰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不受戏曲的兴衰所左右,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徐先生所谓的元代诗文与戏曲互相冲突、此消彼长论,不过是将科举的作用夸大,从而对元代文学发展加以臆测所得出的结论罢了。
第三,徐文说“元代前期诗文作家以遗民诗人为主”,并说以刘因、赵孟俛为代表。何谓“遗民”?从广义上说先朝所生,大部分时光在另一个新的朝代或时代度过的人皆可被称作“遗民”。但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界限,就是:“遗民”绝不能是出生在新朝的人;决不是指出仕新朝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凡在新朝为官者,绝不可再称为“遗民”。假如用此两条标准来衡量刘因与赵孟俛,则他们都算不上“遗民”!刘因生于1249年,此时金朝早已被蒙古灭亡,他一出生就处于蒙古政权统治之下的河北,而徐文据学术界的一种观点,把蒙古时期也算做元朝的范围,(注:元朝历史有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者,有从蒙古灭金算起者,有从元朝建立国号算起者。徐子方文则采用蒙古灭金的说法,可见其文第一部分第二段之叙说。)那也就是说刘因出生在元朝,他怎么能够被称为“遗民”呢?况且他在至元十九年也曾应召入朝,官承德郎,授学宫中,并不是未曾享用元禄之人。至于赵孟俛,徐文中就已说他以宋室王孙的身份仕为显宦,颇为当时“遗民”所轻。显然,赵孟俛根本算不上“遗民”。徐子方先生在文章的行文中虽然一再强调赵孟俛是“遗民”,可是他恐怕也只是想尽力为自己文章的“以遗民诗人为主”的论点强拉人证,就在他的行文中自己也说:“元初‘学宋’的诗文作家主力仍在由南宋人元的一部分遗民那里,张炎、林景熙、汪元量、谢翱、郑思肖等可为集中代表。其次,戴表元、赵孟俛这些非遗民同样有着类似的艺术表现。”(注:引文皆见徐子方《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这里他明明是把赵孟俛称作“非遗民”!这种行文的矛盾绝不是什么笔误,只能说徐先生对赵孟俛是否“遗民”或者把握不定,或者对什么人才可以被称为“遗民”,还不大清楚。如果刘因、赵孟俛都不能说是“遗民”,那么徐先生的论点可就找不到依据了,那还能够成立吗?
第四,徐文说:“元代后期的诗文作家,应以延祐间‘元诗四大家’为起点”。(注:引文皆见徐子方《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说这四人特点都是倡导学唐,这“起点”二字倒是颇让人难以理会,也颇值得斟酌。徐文之所以如此说,还是受他“科举决定文学发展”观的主使所致。他道:“元代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正统权威逐渐树立,文人于诗文方面的着力也在加深,他们逐渐看出诗歌的正宗在唐而不在宋……于是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由宋转向了唐”,“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后期的诗歌竟也有了一点起色。”(注:引文皆见徐子方《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依照徐先生的说法,好像元代诗坛的宗唐之风是在延祐以后才因科举的恢复而逐渐形成,由“元诗四大家”才开始提倡诗歌学唐,也正由此元诗才有了一些起色。为此,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徐先生的论说到底是否正确。首先来看元好问,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诗文大家,为“一代宗工”,(注:李瀚:《元遗山集序》,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元好问全集》卷五○。)时人评其诗文说:“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注:《大德碑本遗山先生基铭》,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元好问全集》卷五○。)“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注:徐世隆:《元遗山集序》,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元好问全集》卷五○。)他曾编《唐诗鼓吹》选76家唐人诗以教弟子。(注:《唐诗鼓吹序》,见《元好问全集》卷五三。)这充分说明元好问并不是专尚宋代诗文之人。元初北方诗人受他的影响,也绝不是宗宋,恰恰相反,他的门生弟子多数宗唐,如郝经、王恽等人无不明确提出了诗歌宗唐的主张。就以徐先生文所论的刘因和赵孟俛而言,刘因是北方诗人中最早推崇唐代诗人李贺的,他以人呼他为“刘昌谷”而自豪。赵孟俛与他的好友戴表元同样是宗唐的诗人。当今学者邓绍基在他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和他所辑的《元诗三百首》两书中曾反复申说了戴表元的“宗唐得古”之论与赵孟俛诗文皆宗唐的观点。(注:《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元诗三百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其它诗人如姚燧、马祖常、袁桷等等也是宗唐者。这怎么能说元诗是到延祐科举时由四大家不满前期宋金遗响,转而才开始倡导学唐呢?学唐、宗唐是元代诗歌的一贯之风,元好问已开其端,其弟子继而扬其波,元前期诗人们已看到宋诗诗风的弊病,故而纷纷越宋取唐为楷模。不过他们各有所好,各有所学,并不是一味宗主盛唐罢了。元人诗歌学唐兼顾魏晋,词学宋,文则学唐宋兼顾秦汉,整个元代文坛是一个向前代优秀文学大学习大继承的时代,是一个万木千花竞自放的时代。
徐先生的大作探讨了元代诗歌的分期与评价问题,引起人们对元代诗歌做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其文章的主旨之一。他说:“我们不能因为先人之见而无视元诗所创造的成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话说得是很对的,本文即是就元诗若干问题想做一些深入的探讨,不过限于篇幅,也不知把要说的问题说清楚没有,欢迎徐先生与同道们批评,本人愿聆听各位先生高论。
收稿日期:1999—06—21
标签:诗歌论文;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论文; 元代建筑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元朝科举论文; 读书论文; 录鬼簿论文; 元史论文; 徐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