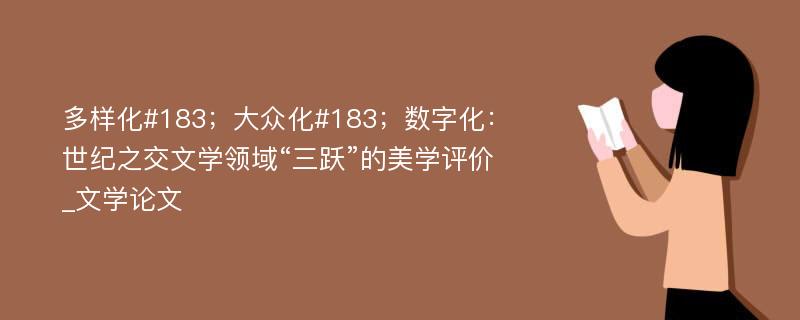
多元化#183;通俗化#183;数字化——对世纪之交文学领域中“三个跨越”的审美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领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近十年来我国文学的总体评价评论界一直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毁之者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金钱和权势的双重挤压下,文学作品日益显得空乏平庸、粗鄙恶俗,以至道德沦丧、艺术衰微,已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末路歧途;誉之者则感到它在实现自我、回归文学自身和书写当代人的生存困境等方面,较以往都有许多新的实验和突破,应该被视为当代文学继承和发展“五四”文学传统的新的跨越。下面我想着重从文学探索的审美价值取向方面做点评估,作为对世纪之交文学命运的一种思考。
一、在文学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外化走向自身的转换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颠覆了以往审美创造中的“不胜负担之重”以后,又生成了艺术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艺术实践中逐步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审美创造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一体化的创作方法,在文艺领域里出现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发展态势。如主旋律和多样化,高雅和通俗,精英和大众,政府和民间,计划和市场等等,有效地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和创造空间,从而有利于作家艺术家们能够更好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追求来进行创作实践——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回归,也有先锋派的余绪;既有纯文学的坚守,也有消费文化的兴起;既有传统程式的再现,也有新新人类的实验……因缘时会,不失为世纪之交新旧文学的一次有声有色的展示和预演。
然而九十年代文学就是在进行这种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外化走向自身的艺术转换过程中,因为缺少自觉的精神准备和审美追求,往往在纷纭繁复、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和现代思潮面前失去了对于社会人生和艺术品质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辨和审美观照的能力,误以为文学创作只要消解了以往的那些宏大叙事、主题意义之类的外在压力之后,就可以在超离社会、放逐精神的自由自在的艺术想象中实现其“预支快乐”了。其结果正像人们所说的,当它致力于颠覆了以往审美创造中的“不胜负担之重”以后,又生成了艺术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例如在近年来被人们称之谓“另类写作”或“个人化写作”的作家作品中,他们虽然在注重“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和揭示“世俗本色的生存状态”方面,有时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鲜的生活信息和情感经验,并在文学叙事和写作姿态上进行了有益的实验;但由于他们常常自得于把创作中的人文关怀消解成所谓“主体退隐”的零度写作,把审美活动中的情感展现张扬为欲望宣泄的“文本狂欢”,从而便无力把这种自恋式的写作姿态和物欲化的叙事快感提升为有意味的情感形式。因为在艺术创造中真理和美德不仅赋予人生以意义,也赋予艺术以品格。如果一个人对人类的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大问题、大意义都没有热情和爱憎,他还怎么能够“把美带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又怎么能够在审美领域里实现迈向新世纪的历史性跨越呢?
二、通俗文艺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得大众喜闻乐见的欣赏习惯和兴趣爱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同;另一方面,通俗文艺粗鄙化、庸俗化的创作倾向,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泡沫和艺术垃圾
九十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审美现象,就是以影视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艺得到了迅速强势的发展,其传播的广泛和影响的深入已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资源。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大量资金艺术人才的不断涌入,大众文艺在审美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从一直被人们瞧不起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一下变得横行文苑,连一向自视很高的文人雅士们也不得不倒过来附庸“俚俗”,以求得自己“高雅”文艺的生存和发展。这样一来,一方面大众文学的审美特点,即大众喜闻乐见的欣赏习惯和兴趣爱好便不能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同,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用高雅文艺的审美规范去贬低大众的欣赏习俗,也不会用“纯文学”的那些价值意义之类的要求去取代它的娱乐性、消闲性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大众欣赏中的低级趣味和市场化的恶性炒作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俗文艺粗鄙化、庸俗化的创作倾向,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泡沫和艺术垃圾。例如就以当下影响最大的影视文学来说,无论是新编戏说、还是言情论道,其审美价值能够在娱乐的同时又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的,却并不占多数;而那些陈腐不堪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观念,令人审美能力日益衰退的生拉硬扯和胡搅蛮缠,以及所谓情节破绽、性格硬伤等等,则比比皆是……这样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为大众文艺的欣赏活动毕竟属于艺术审美的范畴,它和一般的消闲娱乐——如体育竞技、赌博冒险等不同,不是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而是作用于人的情感和心灵。由此我们便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大众文化的“职业道德”就是拒斥一切思想性,专门给人疲惫的身心“捶背挠痒痒”的。所以尽管今天的大众文化已经使那些“曾经令我们的先人过得十分舒服的一切趣味、窍门和好玩的玩法一股脑都在中国复辟了”,而我们却无论抱有什么“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良心”也是无从逾越的。这样一来,大众文化不是注定要永远背着复辟传统腐朽文化的黑锅而没有出头之日了吗?其实,记得西方的一位比较通情达理的文艺理论家曾经这样说过:艺术家和公众双方如何“把教益和娱乐”调和成一种可口的“艺术点心”——既不能放进过多的教益和过少的乐趣使它难以消化,又不该只有乐趣而没有教益让它缺少营养——从来就是通俗文艺创作所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像现在的大众文艺欣赏这样,动不动就会被弄得家喻户晓、万人倾巷,就更应该重视其审美导向的问题了。
三、数字和网络加速了文学国际化的进程。这一过程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接受最严峻的历史性考验和洗礼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以更加自觉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心态来弘扬民族的文化传统,寻找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定位,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先进的文化潮流
世纪之交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人们在谈到文学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到科技文化对于人文文化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参与。这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显示出文学演进中的另一种形式的跨越。
其一,是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对文学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文学作为人们“情感的显现”,本来就是人类感情交流的一种最好的方式。而当现代化的信息革命日益冲破了国际间长期形成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壁垒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所曾经预言的“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愿望,便正在逐渐变成现实。所以在新的世纪里,国际间的文学交流和融合必将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当然,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接受最严峻的历史性考验和洗礼的过程。这里既有从未有过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避免的强势文化的渗透和介入。但无论怎样,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文化整合和文化冲突,无疑将会给人类文明和艺术创造带来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我们便不应该再采取什么闭关自守或文化殖民的心态——在批判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同时,又做着所谓“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美梦;而应该以更加自觉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心态来弘扬民族的文化传统,寻找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定位,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先进的文化潮流。
其二,网络化多媒体的出现,还使得审美文化正经历着从语言中心(听觉)向影像中心(视觉)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将导致审美活动中的美感经验和审美方式的一次全新的体验和变异——以往文学创作中语言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的距离感和虚幻感将被打破,人们可以在计算机房或演播厅里制造出任何一种以假乱真的理想蓝图和人间奇迹,从而使得文艺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有可能被无限制地扩大和滥用。而且除此之外,当影像作品一旦被高科技的自动化快速大量廉价地复制出来以后,艺术产品的过剩和原创价值的稀释,必将使人们心灵化、个性化的创造激情和灵感受到伤害,从而进一步显示出科技进步和商品经济对于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部门的某种敌对姿态。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学实践,我国文艺领域中的这“三个跨越”既显示了当代文学在迈向新世纪时的开拓进取,又暴露出探索过程中的许多迷失甚至陷阱。个中得失,且待来者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