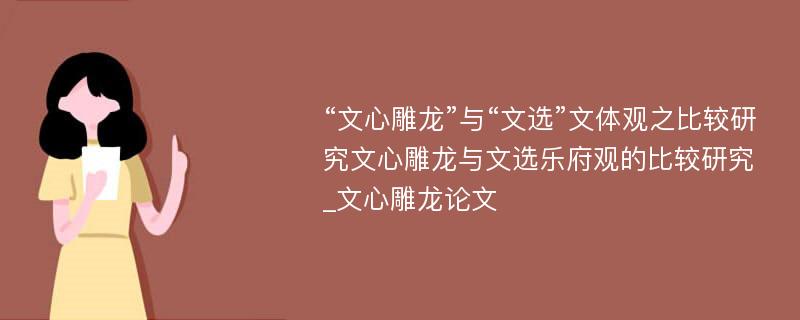
《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观比较专题研究——1.《文心雕龙》与《文选》乐府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选论文,乐府论文,文体论文,专题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4)11-0017-013 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时代最早而又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其中不但有文学总论、创作论和鉴赏论,而且还有几近全书一半篇幅的文体论。和刘勰几乎同时的还有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选文大家,就是昭明太子——萧统,他编纂了一部流传至今最早的诗文选集——《文选》。《文心雕龙》和《文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两朵奇葩。两书的作者生活年代相近,彼此之间也有交往。他们都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梁时代,刘勰曾在昭明太子身边担任过东宫通事舍人,深为萧统赏识。关于他们之间的文学观念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前辈学者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笔者拟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入手,分析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 《文心雕龙》共论及了三十四大类文体,其中在《辨骚第五》《明诗第六》后边专列《乐府第七》,对乐府诗进行了专题论述。刘勰在篇中曾说:“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他在这里明确说道,自己是继承刘向《别录》中把歌诗和六艺略中的诗分开的做法,单独列《乐府第七》,聊备《乐篇》。由此可见,刘勰并不是将乐府和诗完全割裂开,把乐府作为独立文体和诗、赋等并列来讨论,而是注意到了乐府和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乐府作为诗的一个大类别来讨论。 《文心雕龙·乐府第七》开章即点明乐府的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这句话本之《尚书·舜典》。刘勰认为,乐府就是用宫、商、角、徵、羽五音来配合歌咏,用六律六吕来配合五音,即他后边说到的“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乐心”之“诗”。这里虽然强调了乐府配乐歌唱,但其立意之本仍是作为“乐心”的诗,所以又说:“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从这里不难看出,《文心雕龙》提到的乐府诗,虽然强调入乐的重要性,但归根结底仍然落脚在诗的辞句上。在刘勰看来,乐府已经发展成为诗中比较重要的一大类别,能够配乐歌唱的就是歌诗,不能配乐的就是诗,即徒诗。刘勰并非没有认识到歌诗也是诗的一种,只是由于刘向在整理典籍时把作为儒家经典的《诗》和歌诗分别开来,将诗分在六艺略中,而将歌诗分在诗赋略中,受此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单独论述了乐府诗。实际上,刘勰主要是从音乐教化的角度来讨论乐府。但是因为歌诗是配合音乐演唱的,作为音乐的核心唱辞,这些歌诗的辞句就显得特别重要,正所谓“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也。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也就是说,《诗经》的所有诗都是可以歌唱的。只是到了后代,由于《诗》被提高到了儒家经典的地位,而乐曲又多亡佚,所以才变成了徒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云:“‘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意思是诗、歌本来是一体的,只诵其辞就是诗,咏唱其诗就是歌。刘勰也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他的论述和刘向、班固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作为“宗经”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无疑也反映了儒家传统的教化观念,所以他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在他看来,这些有教化作用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自魏晋以来一直没有雅正之音,连曹操、曹丕、曹睿等魏之“三祖”创作的乐府诗也有不合经典的缺点,认为其“诗声俱郑”。所谓“诗声俱郑”,也就是过于追求靡丽之音,而忽略了传统的雅正之乐。刘勰是从是否符合典雅合经的角度对曹操、曹丕、曹睿的乐府进行批评,认为他们的诗歌不够典雅,过度抒发怨恨,不符合儒家“哀而不怨”的优秀传统,破坏了音乐的教化作用,走上了世俗音乐的邪路。刘勰在《乐府第七》篇里没有提到南朝宋、齐时期的乐府,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魏晋以下的诗歌辞句和音乐曲调都走上了俗乐的路子,偏离了中正、典雅的正道。 刘勰在重视乐府诗音乐教化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有些乐府诗并没有实际配乐演唱的情况。比如他说道:“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刘勰认为,曹植和陆机都写有很优秀的乐府诗,这些乐府诗没有请乐工配乐,也没有实际的配乐演唱过,世俗人就认为它们不合曲调,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世俗人没有深入思考的缘故。他在这里实际上又强调了乐府也就是歌诗与诗、音乐的关系,有些诗虽然是按照乐府创作的,但是在实际配乐演唱的时候,也要经过乐工加工,适当增减文字以便配乐。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书·乐志》中入乐的诗和《文选》选录的同样的诗,其中文字都有差异,就是因为入乐时根据需要增减文字的结果。因此,乐府诗既可以由乐工配乐演唱,也可以不配乐演唱,是否配乐演唱并不影响这些诗称作乐府诗,有些没有配乐演唱的乐府诗是文人模拟乐府诗写作的。这正如宋代的词,有些虽然是按照词牌填写,但也并没有入乐演唱,但不影响它们仍被称作词。 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一》解题对乐府诗歌配乐的关系有比较透彻的论述,其中说道:“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1]也就是说,乐府的歌辞,有的是先有音乐而后写作的歌辞,也就是诗,比如曹魏的清、平、瑟调歌曲;有的是先有诗而后谱曲,比如清商、吴声等曲调;还有些是只有歌辞,是后人的拟作,但却未必被乐工谱曲,所以只有歌辞而没有乐曲。郭茂倩关于乐府歌辞的论述可以说是对刘勰乐府观的继承和发展,而后人对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收录有些完全没有配乐的歌辞颇有微词,实际上是没有完全领会乐府的真谛,也缺乏对诗乐关系的准确把握。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乐府第七》中对刘勰的乐府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古者诗歌不别,览《虞书》、《毛诗序》、《乐记》则可知矣”。“然观《艺文志》所载,有乐府所采歌谣,有郊庙所用乐章,有歌咏功烈乐章,有帝者自撰歌诗,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诗,有杂歌诗,此则凡诗皆以入录。以其可歌,故曰歌诗。刘彦和谓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殆未详考也。及后文士撰诗者众,缘事立体,不尽施于乐府,然后诗之与歌始分区界。其号称乐府而不能被管弦者,实与缘事立题者无殊,徒以蒙乐府之名,故亦从之入录。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统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管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远之若曹陆依拟古题之乐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题之乐府,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淆溷也”[2]。黄侃这段话分析透彻,充分厘清了乐府与诗、乐的联系和区别。 乐府由音乐机关的名称转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正是在魏晋以后刘勰生活的时期,所以刘勰特意把乐府诗作为诗中相对比较独立的文体单独论述,从文体发展和分类的角度来说,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虽然把乐府诗作为诗中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单独论述,但他并没有完全割裂乐府与诗的关系,他认识到有一部分文人的创作虽然没有配乐演唱,但是这些作品一旦经过乐工配乐,增损辞句,马上就可以成为脍炙人口的歌诗。这一认识对后代的诗歌创作和发展有深远影响。比如唐代,乐府的名义有了更广泛的指称,特别是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如果配乐,完全可以演唱,如果不配乐,则可以当作诗。从这个意义来说,宋代的词和元代的散曲,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乐府,如《东坡乐府》《小山乐府》等。但宋词发展到大量文人创作时期,又有若干词作实际上并没有被演唱。 随着历史的发展,乐府的含义也在不断演变,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黄侃根据刘勰的乐府观,又进一步对乐府和诗的关系进行了解说,并在此基础上对乐府进行了分类,实际上总结了乐府的四个发展阶段:“今略区乐府以为四种:一乐府所用本曲,若汉相和歌辞,江南东光乎之类是也。二依乐府本曲以制辞,而其亦被管弦者声,若魏武依《苦寒行》以制《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制《秋风》,是也。三依乐府题以制辞,而其声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乐府旧题,自创新题以制辞,其声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陈陶》诸篇、白乐天《新乐府》是也。从诗歌分途之说,则惟前二者得称乐府,后二者虽名乐府,与雅俗之诗无殊。从诗乐同类之说,则前二者为有辞有声之乐府,后二者为有辞无声之乐府,如此复与雅俗之诗无殊。要之乐府四类,惟前二类名实相应,其后二类,但有乐府之名,无被管弦之实,亦视之为雅俗之诗而已矣。”[2] 除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诗外,在《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中,刘勰把“轩岐鼓吹,汉世铙挽”也“并总入乐府”。鼓吹即古代管乐和打击乐合奏的军乐,也就是铙歌,挽歌就是丧事所用之歌。 与刘勰《文心雕龙》类似,《文选》在选文时也对文章进行了文体分类。萧统把文体分为三十九类,而将乐府作为诗的一个类别进行编排。根据《文选》的文体分类标准,其中收录的乐府诗作为诗的二十四类之一,分别收录在李善注《文选》六十卷之卷二十七、二十八,五臣注《文选》三十卷之卷十四。其中有无名氏《古乐府三首》(分别是《饮马长城窟行》《伤歌行》《长歌行》;五臣本四首,多《君子行》一首)、班婕妤《怨歌行一首》、魏武帝《乐府二首》(《短歌行》《苦寒行》)、魏文帝《乐府二首》(《燕歌行》《善哉行》)、曹子建《乐府四首》(《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石季伦《王明君词一首》、陆士衡《乐府十七首》(《猛虎行》《君子行》《从军行》《豫章行》《苦寒行》《饮马长城窟行》《门有车马客行》《君子有所思行》《齐讴行》《长安有狭邪行》《长歌行》《悲哉行》《吴趋行》《短歌行》《日出东南隅行或曰罗敷艳歌》《前缓声歌》《塘上行》)谢灵运《乐府一首》(《会吟行》)、鲍明远的《乐府八首》(《东武吟》《出自蓟北门行》《结客少年场行》《东门行》《苦热行》《白头吟》《放歌行》《升天行》)、谢玄晖的《鼓吹曲一首》,共计十家四十首(无名氏算一家,五臣注本四十一首)。 《文选》选入“乐府”类的诗,有很多是没有配乐演唱的。萧统不纯粹是从音乐的角度来收录“乐府”诗,他更重视的是文辞,这也是《文选》作为文章选本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在论及《乐府第七》中“子建士衡,并有佳篇”时说道:“案子建诗用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调·怨诗》)及《瞽舞歌》五篇而已,其馀皆无诏伶人。士衡乐府数十篇,悉不被管弦之作也。今案《文选》所载,自陈思王《美女篇》以下至《明都篇》,陆士衡乐府十七首,谢灵运一首,鲍明远八首(谢玄晖《鼓吹曲》,乐府所用),缪袭伯以下三家挽诗,皆非乐府所奏。将以乐音有定,以诗入乐,须有增损。至于当时乐府所歌,又皆体近讴谣,音邻郑卫,故昭明屏不入录乎。”[3]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在继承黄侃论说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则诗辞非必不可入乐,惟视乐人能否使就谐合耳。”也就是说,《文选》所选录的“乐府”诗歌,有很大一部分并未实际配乐演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配乐演唱时需要根据曲调增损字句,乐工害怕繁难就没有配乐。但这并不影响这些诗都是依照乐府诗创作而形成的一种乐府,特别是没有入乐的乐府,几乎都是按照乐府旧题而创作的。 除“乐府”类外,《文选》“挽歌”类收录的有缪袭伯的《挽歌一首》、陆士衡的《挽歌三首》、陶渊明的《挽歌一首》,“杂歌”类有《荆轲歌一首》《汉高帝歌一首》、刘越石的《扶风歌一首》、陆韩卿的《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这些类目在《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中也有论述,但都总括在“乐府诗”的题目之下。此外,《文选》“杂诗”类收录的《古诗十九首》,据有的学者考证,这些诗也属于歌诗,至少部分诗确证可以属于歌诗[3],也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乐府”,而《文选》将其归入了“杂诗”。 《文选》收录的乐府、挽歌、杂歌、杂诗等,在《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中都被列入了乐府诗,造成这些分体归类方面差异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儒家传统的宗经性文学批评著作,他的立足点是教化,所以重视文章以及一切文学体裁包括音乐的教化作用;而萧统则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待乐府诗,分类更加细致,所以他将乐府与挽歌、杂歌、杂诗分别作为诗的一种类别。第二,《文心雕龙·乐府第七》实际是为了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而将乐府单独讨论的,这并不意味着刘勰割裂了诗和乐府的关系,他仍然是将乐府诗也就是歌诗作为诗的一个大的类别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和萧统的观点是相通的。第三,《文选》作为一部诗文选集,蕴含着编选者的文学思想,体现了编选者的文学好尚,萧统在《文选序》中明确了其选文标准,即“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文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文人创作,提供文学创作范本,选编时更多是从诗歌内容和文辞角度入手。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与《文选》两书对乐府的处置在细节方面略有差异,其中既反映了刘勰和萧统相似的文体观念,也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体细分观念。《文心雕龙·乐府第七》对诗中的乐府歌诗单独讨论,主要是出于对音乐教化作用的重视。由于世俗都喜爱俗乐,而魏晋以来的歌咏情性的诗歌越来越多,连庙堂雅正的音乐都受到了冲击,而伴随音乐演唱的歌辞即诗,在刘勰眼里自然也江河日下,越来越绮靡淫艳,因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对乐府诗也进行了探讨。也就是说,《文心雕龙》论乐府诗是由于论乐而及于配乐演唱的歌辞即能演唱的乐府诗。而《文选》作为文章选本,最关心的是文章的辞藻,所以对是否入乐并不是特别关心。只要诗篇文辞雅正,思想性、艺术性又比较高,就可以入选。在诗的具体分类上,《文选》更多的是从功能上来区分,因此《文心雕龙》中所论述的乐府诗在《文选》中被细分成乐府、挽歌、杂歌、杂诗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