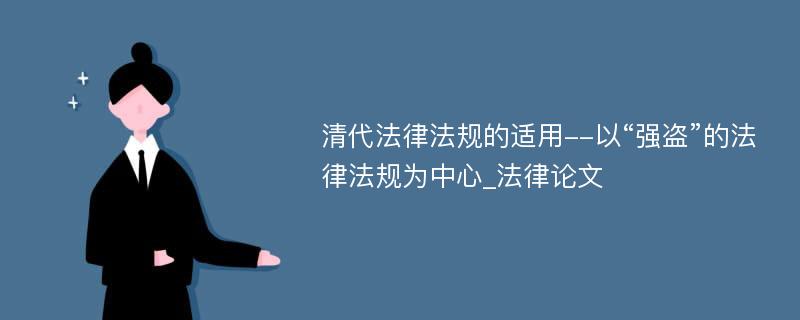
清代律例成案的适用——以“强盗”律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例论文,强盗论文,清代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9)08-0131-10
清代法律规范由律、条例、事例、则例、成案、章程、禁约、告示等不同法规形式所组成。在这些不同的法规形式中,什么样的法律规范可以成为司法官吏断案的依据?各种不同性质的法源之间的效力如何?尤其是律、条例、成案的法律效力如何?对此,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给予关注,但在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而弄清三者的关系则涉及法律适用。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既关系到法律的条文规定,又关系到实效问题。“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①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强盗”律例及成案分析,以弄清律、条例、成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剖析当时立法与司法领域的特点。
一
以《清史稿》为代表时“以例破律”派认为:“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②从清末至20世纪末,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学界通论。瞿同祖、张晋藩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明确提到过,清代例的效力大于律。③但是近年以来,许多新一辈的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苏亦工认为:“明清官方处理律例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以律为主导,条例为补充、辅助和变通”,那种以例代律的现象是不普遍的。④何勤华分析了清代律例适用的七种情况,认为虽然“以例改律、以例破律的情况,在《刑案汇览》、《驳案成编》中还是比较多的”,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在清代例的地位高于律,只能“例”对律文的“盲点”进行了补救,因为“在清代,律是基础,例是补充,一般情况下,当某个案子呈送到审判官面前时,他首先适用的是律,只有在律文明显落后于形势发展或没有律文可适用时,才会适用例。那种认为例的地位高于律、在律例并存之情况下首先适用例的观点,与清代的审判实践并不相符”。⑤吕丽也认为清代的律例关系是“例以辅律,非以代律”。⑥张晋藩则把律例关系表述为:“一般说,清朝政局稳定时,刑律的国家大法地位往往得到统治阶级较充分的认可和尊重。律的地位与效力理所应当地优于例。相反每当出现内忧外患,统治阶级考虑更多地摆脱大法的严格约束,依靠例的灵活形式和便于使用的特长,实施广泛有效的刑事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律例地位倒置,以及例的效力高于律的真实状况”。⑦总结新世纪学者的观点,其都反对把清代律例关系表述为例的地位高于律,认为律例关系是律为主导、例为补充的关系,而这种观点有被普遍认同的趋势。
从“强盗”律例来看,如果说律例关系是“律主例辅”,那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否定“例”对“律”的优先效力,就不符合史实了。尤其是何勤华的观点,与强盗案例裁断的事实相差太远。《刑案汇览[三编]》共收入强盗案例104个,其中纯依律文判刑的只有第57案和第103案两个案例,此外第67案是依谕旨赦免,第18、27、42、44、67、97案或是驳案,或非强盗案,不涉及强盗量刑。除了这9个案件之外,其余95个案件都是结合例文的规定予以量刑的。比如第99案,李克详等一伙五人抢得财物将事主打死。此案如果依律判决,五犯皆应斩决;如果依例判决,五人中“法无可贷”者斩枭,“情有可原”者发遣。刑部核覆此案时引了一条律、两条例。一是律文中时“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二是例文中时“寻常盗劫未经伤人之伙盗,如入室助势搜赃,一经得财,俱拟斩立决,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其止在外瞭望接递财物,并未入室搜赃,无凶恶情状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发遣”。三是例文中的“强盗杀人,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决枭示”。⑧最后定刑时将李克详按例拟为斩枭,其余四犯按例拟为发遣,可见是依例处罚。这里刑部明显有律可引,但他们没有“首先适用律”,而是适用了例的规定。其余案例也与此案相同,有的引了律文,有的没有引律文,但最后的定刑都是综合律例的规定,优先适用例文作出的,没有一案是在例文有新规的情况下仍坚持依律定刑的。
此外,还可以通过律例的变化,来考察这些案例是否随着定例的变更而变更量刑。强盗处刑最大的变化是律文规定“凡强盗,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康熙五十四年到咸丰五年(1715年-1855年),例文规定将情有可原盗犯免死发遣。《刑案汇览》与《续增刑案汇览》收录的是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案例,共100案,该段时间内“情有可原”例有效;《新增刑案汇览》所收4个强盗案例,是同治十年至光绪七年(1871年-1881年),这段时间“情有可原”例废止,恢复律文“但得财皆斩”的规定。分析《刑案汇览》与《续增刑案汇览》收录的100个强盗案例,其中窃盗临时行强34案,例文规定其处刑与强劫不同,不涉及情有可原免死发遣;另有26案是探讨投首、留养、蒙古例、不行分赃等情况的处刑的,因未录全案,也没有提到情有可原发遣;其余40个记录较完整的处刑办法的强劫案件,或直接援引“情有可原”条例,或依据此例将案犯免死发遣。《新增刑案汇览》4个案件无一援引“情有可原”例将案犯发遣,其中第3案张三目击伙犯拒伤事主,自己并未动手,若在“情有可原”例有效时期,当免死发遣,而此处仍拟斩决。⑨可见司法实践是紧随例条变更而变更量刑的。
再如,雍正九年(1731年)规定,捕役为盗虽非造意为首,以为首论,不准免死减等(强盗条例266.55)。《成案续编》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案例,即依据此例将“虽系听从同行,初次为盗,转纠不及三人,亦未伤人”,本应情有可原发遣的营兵8人斩决(营兵与捕役同有捕盗之责,类比)。⑩司法官员亦步亦趋跟随定例判案,这是清代行政体制的必然要求。如果司法官员以“律”为据,拒绝适用中央的新定例,就会有漠视君权的嫌疑。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下,对君权的漠视会得到什么下场,即便不是局内人也可以猜想得到。所以,即使从清代的行政机理去推,那时的律也不可能具有高于例的效力。《清会典》对律例之间的关系有明确解释:“有例则置其律,例有新者,则置其故者”。(11)当律与例调整的对象相同时,律例关系其实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新法的效力大于旧法。清代司法官员也都清楚律例之间的关系,“有例应照例行,无例方照律行”(12),乃是司法官员的原则。
或许有学者可以勉强承认在律例冲突时,例的效力高于律,但是他们认为“以例破律”的现象并不普遍。然而,从“强盗”律例看,例文对律文处刑的改定是相当大的。律文对于强盗处刑的规定其实非常简单,一是不得财满流,二是得财皆斩,三是临时拒捕皆斩监候。清代前后制定有强盗处刑例文105条。对于律文第一点不得财满流,定例区分伤人、未伤人,伤人者首犯斩监候,从犯满流;未伤人者,首犯发遣,从犯满流。对于第二点,不得财皆斩,定例大部分时间区分“法所难宥”与“情有可原”,其中有加至斩枭、减至满流、分地域、分盗劫对象、分犯罪主体等等,较为具体。对于第三点窃盗拒捕皆斩监候,定例要分首从、是否伤人、所持器械是否是凶器、从犯要分是否加功等等,处刑从斩立决、斩监候到烟瘴充军、极边充军不等。可以说,强盗例文对于律文的处刑规定,不是局部调整,而是全盘的改定和细化。如果审判强盗案件,只看律文不看例文,最后作出的处刑判断十有八九将被驳回。因此瞿同祖先生说:“我们研究清代法律必须研究条例,不能仅研究律文,否则不但了解不全面、不了解其变化,不了解其法律的具体运用,还会发生错误,将早已不用的律文当做清代的法律来论证。”(13)虽然一条强盗律不能代表整个清代律例的情况,但是窥一斑而见全豹,可见整个律例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具体细致。其他例文的改变不如强盗律例多,从清律436条、清末付诸实施的例文已有1892条来看,例文在很大幅度改变了律文。
既然“例”的效力大于“律”,而例文对于律文规定的改变又很大,那么是否就是例的地位高于律?笔者认为也不尽然。从法典的角度看,律文所设定的结构、原理、概念是例文所依赖的根基,律例在法典中的地位还是可以用“律主例辅”来形容的。之所以制定了大量的条例,而在法典中仍以“律”为主导,一是“诚以律为一代不易之大法,例乃因时损益之定制,律不可不严,过严则不能垂之久远;例不可过宽,过宽又无以绳百司民人;例所以补律之不及者也”。(14)当例的处罚重于律时,统治者往往强调这是暂时变通之法,待形势好转,即复成法,不敢背擅改律法、加重刑罚之名,故可以从思想层面来解释律的主导地位。二是从实践层面来说,虽然定例繁多,但多是一事一例,抽象水平极低,没有自己的法律理论体系,其概念、理论、体系皆是依赖于前代律典创设的框架。失去律文的支撑,例文就成为一部庞杂的法条汇编,谈不上是法典了。如强盗案件的处刑虽然已被例文大部分改变了,但是律文所创设的强盗与抢夺的区分、窃盗转化为强盗等基本概念,还有强盗区分得财与不得财等基本原则,仍被例文所遵循的。如果不从一条律和整部法典看,例文依赖律文所设立的理论框架会更明显。思想层面的尚古及垂久远观念,加上实践层面的抽象水平低,造成定例虽多,但仍改变不了法典中“律主例辅”的局面。当然,这种意义上时“律主例辅”,不是因为“律”决定了大多数案件的量刑,而是因为“律”体现和表达了当时刑法的一些根本原则与思想。
从“强盗”律例分析,可以看出清代律与例的三层关系。第一,法理学的“法的位阶”概念,是指不同等级主体制定的法,效力等级不同,等级高的主体制定的法,效力高于等级低的主体制定的法。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效力高于国务院制定的法规,所以法规不能与法律相抵触。然而,律例之间并不具有这种因“位阶”导致的效力差异,二者都是皇命钦定,同属中国古代最高位阶的法律,地位相等,效力相当,所以例可以与律冲突,律不具有优先于例的效力。第二,从新法与旧法的角度看,律是旧法,例是新法,当二者相冲突时,例的效力大于律。第三,从在法典中的地位看,律主例辅,律占据核心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在具体量刑方面的效力大于律,律在法典中处在核心的地位。
二
成案,顾名思义,即已成之案。“成案”一词不仅指司法领域的办过案例,还可以指其他行政领域办理事务的先例。比如,《宋州从政录》载虞城县禀文:“前因惠民沟横河,业经奏请兴挑,将次完竣。饬查附近沟河有无淤塞,应遵照成案,动用民力挑挖,顺沟通河,以除水患。”(15)此处的“成案”是指先前疏通河道之办理方案。再如,“道光五年(1825年)间,复据候补运副吴臣敌等具禀,近日丞悴各员候补无多,请照成案,仍将宁、嘉二分司缺,归入同知、通判班内,一体委署”。(16)此处时“成案”是指浙江先前委署官员的办法。《晋政缉要》有“兵部咨一件厘定修制军装等事”。兵部“谨查来册,并考稽成案,因各省之情形,酌物料之坚脆,核定应修应造之期,分别定限,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命下,臣部纂入则例”。(17)此“成案”又为兵部责令各省修治军械之旧例。总之,清代所谓“成案”,并非仅指司法案例,各个行政领域过去形成的办事方案,都可称为“成案”。从这个角度讲,“成案”即先例。
学界谈清代的成案,通常是指司法领域中的已成之案,即所谓司法案例。(18)清代司法实践中,成案是否具有法源效力?这个问题学界有许多讨论,总体来说,都认为有一部分成案具有法源意义,但是成案究竟在多大程度有法源意义,却存在争议。(19)苏亦工认为:“绝大多数的清代案例或判例并不必然享有法源的地位。只有个别判例譬如某些成案,有时可以被接受为一种法源。但成案的地位很不可靠,其适用的方式更接近成文法的引证方式,而不是英美判例法的归纳方式”。(20)何勤华则认为:“实际上,在清代司法实际中,成案的适用还是非常普遍的”。(21)而王志强认为:“如果从形式上成案的独立规范性角度而言,成案在司法实践中显然又具有相当独立的效力”。(22)显然大家争议的焦点在于成案在多大程度上有法源意义。
《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序言讲:“律例为有定之案,而成案为无定之律。例同一罪犯也,比诸重则过,比诸轻则不及,权轻重而平其衡,案也,律例也。同一轻重也,比诸彼则合,比诸此则否,汇彼此而析其义”。(23)成案的作用在于衡量轻重,也有补律例之不足的寓意,故“律之所不能尽而有例,例之所不能尽而有成案”。(24)成案既有加减刑罚的作用,又有补律例之不足的效用,但所有的成案最终定罪都是律例规定的内容。下面结合清代强盗案件司法实践,具体分析在什么情况及多大程度,司法官员会引用成案作为自己判决的依据。
本文搜集的有处刑规定的强盗案例共195件,其中援引成案的有13件,占总数的6.7%。(25)其中照案者有7案,不准照案者有3案,不准照案而追究违例援案者责任的有1案,照案改例的有1案,不准照案而照新定例的有1案。由此可见,司法官对两案情节相似性判断失误,不但会导致拟断错误,还要追究违例援案者的责任。
清人对于援引成案的态度有两点:一是“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著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26)二是“如有轻重失平,律例未协之案,仍听该督抚援引成案,刑部详加察核,将应准应驳之处,于疏内声明请旨”。(27)也就是说,原则上断案只能引律例正条,但是如果律例正条所定之刑与案情实未允协,可以援照成案上请。这两点看似矛盾,实际上放到清代行政体制中去理解,还是合于情理的。皇帝是最高立法者,也是最高司法者,对于显失公平(情法未协)的案件,皇帝在司法过程中予以改判或重新定例,允许司法官援照成案,甚至比照律例加减定拟,再由皇帝批交法司对最后判决予以审核,这正是实施其立法与司法合一的权力体现。从理论上说,这种灵活的处置有利于实现更实际层面时“情法平衡”。然而哪种情况是“轻重失平,律例未协”,却没有明确的标准,司法官对这一点的把握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故违定例,滥引成案”之窠臼。
清代司法官员在实践层面如何援引成案?是为解决什么问题援引成案?试分析如下。
《成案汇编》第3案《在洋行劫声明情有可原驳案》,《刑案汇览》第35案《行劫衙署伙盗接赃免死发遣》,第60案《海江盗劫分别情有可原》,是确认洋盗、沿海滨江盗犯、行劫衙署盗犯是否适用“情有可原”条例。清律规定强盗犯罪不分首从,清初例文将行劫衙署等六项强盗犯罪及响马强盗的刑罚提高至皆斩枭,康熙年间又规定将江洋大盗照响马例办理,康雍时期定例将强盗区分“法所难宥”与“情有可原”。那么这些原例中皆斩枭的大盗,是否也可以区分出“情有可原”者,将他们免死发遣?例文对此很含糊,在司法实践中多引成案将此类犯罪也区分“情有可原”。所以这几个案例援引成案实际是解决定例(情有可原之例)适用问题的,不涉及创制新的处刑规定。此外,《刑案汇览》第25案《临时谋杀事主仍照临时拒捕》,是行窃时被事主发现,起意杀人灭口,争议的焦点是适用窃盗临时拒捕杀人条例还是谋杀人律,也是关于适用条例的问题。
《成案汇编》第18案《盗首虽经捆缚事主》,《刑案汇览》第6案《拒伤事主分居亲属与事主同》,第39案《首盗冻毙事主伙盗免死发遣》,第55案《既经入室虽不搜赃亦应斩决》,是解决情节认定问题的。《盗首虽经捆缚事主》是关于强盗自首的,清代规定伤人盗首不准自首,即伤人盗首自首不减刑,该案就是探讨“捆缚事主”是否算“伤人”。刑部认为:“此案盗首高周村子因事主李增惊觉喊叫,用强按缚其手,即系伤人,虽系闻拿投首,例难宽宥”,予以驳回重拟。该省引据成案称:“乾隆九年(1744年)八月内,刑部议覆河抚硕审题盗犯李奇山行劫荆保家一案。内开该抚既称李奇山系此案盗首,虽捆缚事主,并殴打事主之妻,尚未成伤。”后李奇山投首,该省照未伤人盗首例,将该犯拟以发遣,刑部照覆,奉旨依议。今周村子与李奇山情事相同,“应仍依前拟”发遣。这是一个省抚以成案为据拒绝刑部驳案的例子。然而,此案双方争论的关键点是“捆缚事主”是否算“伤人”,这是一个情节认定问题,不涉及改变原有处刑规定。《拒伤事主分居亲属与事主同》是对“分居叔父、堂兄是否算事主”的身分认定问题,如果分居叔父不算事主,盗犯就以罪人拒捕论,如果算事主,盗犯就以拒伤事主论。最后依照成案,分居叔父、堂兄等也算事主,盗犯以拒伤事主论。《首盗冻毙事主伙盗免死发遣》也是一个情节认定问题,例文规定强盗杀人者斩枭,但是此案事主因逃避强盗,“奔至附近岩洞藏匿,受冻身死”,非强盗直接杀死,是否应认定为强盗杀人,例文不详。刑部奉批查考成案,发现以前有因遭强盗而失足落水的,有因遭强盗而惊慌失足落河溺毙的,皆照强盗杀人办理,于是此案也照强盗杀人办理。《既经入室虽不搜赃亦应斩决》是关于入室未搜赃是否可以归入“情有可原”的。与本案最近的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例,规定入室助势搜赃者斩决,未入室搜赃者情有可原发遣。此案案犯虽入室未搜赃,该省援照乾隆二年(1737年)成案将该犯拟以情有可原。刑部认为:“查办理盗劫之案,总以入室不入室为断”,“盗犯既系入室,非系搜赃即属助势”,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且该抚所引成案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例之前的成案,“殊属违例”,要求“查取错拟及违例援引成案各职名,咨送吏部查议”。显然此案也是情节认定问题。《临时谋杀事主仍照临时拒捕》是行窃时被事主发现起意杀人灭口,应该适用窃盗临时拒捕杀人条例还是谋杀人律?该抚据成案临时拒捕杀人条例。解决情节认定,本质上说也是定例适用问题,不涉及创制新的处刑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8个为解决律例适用问题而引用成案的案件,只有《既经入室虽不搜赃亦应斩决》未照成案判决,其余各案均照成案判决了。
《成案汇编》第11案《哄开大门入内行强不准援案宽减》,第14案《先窃后强持刀恐吓事主赃已满贯不便拟遣》,是关于临时行强是否可以减刑的。律文规定临时行强处刑与强盗同,有的司法官则认为临时行强开始时只是窃盗,因事主发现才决意行强,与自始即立意行强者犯罪恶意不同,故有的案例将临时行强杀人拟斩监候。《哄开大门入内行强不准援案宽减》即依据这样的成案将罪犯拟以斩监候,遭驳。《先窃后强持刀恐吓事主赃已满贯不便拟遣》则是临时行强情节显著轻微,仅是用言吓阻,并未对事主动手。该省引据成案将案犯发遣,遭驳。《刑案汇览》第62案《洋盗案内买赃摇橹定账定例》是关于接买盗赃二次的犯人的处刑,原例接买盗赃一二次枷杖,三次以上近边充军。嘉庆十年(1805年)核覆闽省朱贯章一案,认为原例处刑过于宽纵,将该犯发遣。这次该抚引此案,将接买二次的犯人拟遣,刑部认为这样办理不妥,重新定例:“三次以上,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二次者发近边充军;一次者杖一百、徒三年”。本案照新例发近边充军,未照成案。《洋盗强盗年幼拟流应行刺字》,《洋盗投首免其从前窃劫各案》,虽是关于处刑变更的,但皆因律例规定不清,不是因为律例与事实“轻重失衡”。《洋盗投首免其从前窃劫各案》是关于自首犯人以前所犯之罪没有首明,是否赦免的。《洋盗强盗年幼拟流应行刺字》是关于年幼盗犯杖流是否刺字的。清代窃盗刺字十五岁以下免刺,强盗刺字未有明文,故此引成案。这5个案件只有《洋盗强盗年幼拟流应行刺字》照案判决,其余均没有照成案判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强盗案件中引成案作为依据,所要解决的事项大多是一些律例规定含糊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律例对适用范围规定不明确,或是律例对情节界定不明确,或是律例对处刑规定不明确。其中因定例与案“轻重失平”,欲引成案改定例之刑的只有《哄开大门入内行强不准援案宽减》,《先窃后强持刀恐吓事主》,《洋盗案内买赃摇橹定账定例》。这三案也不是对处理强盗案件的主要量刑作出更改,只是处理一些边缘性的情况,而最终均没有依照成案判决。可见,虽然例文规定,“如有轻重失平,律例未协之案”可以引成案上请,但由于缺乏“轻重失平”的客观标准,实践中敢于这么做的人并不多。如果地方官真这么做,要冒很大的风险,等待他的很可能是被刑部驳回所带来的错拟处分。所以,大多数引据成案的案件,只是探讨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律例有明文规定的事项,依律例拟断是最安全的。
综上所述,强盗案件中确有一些案件在判决中引据成案,但是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大多是一些边缘性的问题,比如法律适用问题,或边缘情况的处刑问题,处理强盗案件的主体规则还是由律例来规定的。所以成案在有关强盗案件的法律渊源中,只占一个很边缘位置,它决不能与律例相提并论。或许现代社会中最高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与清代成案的地位有些类似。司法解释主要也是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司法解释无权更改法律规定,而成案可以“轻重失平”的名义提请皇帝更改。当然,本文所论述的只是强盗案件这一种情况。强盗犯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律例方面的规定细致周密,给成案留下的空间不多。可以说,制定法是清代法律渊源的主体,成案所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成案作为法律渊源,发挥的作用并不大。这一观点与清代成案汇编类著作盛行现象,似乎有些矛盾。其实,笔者认为,清代成案汇编类著作主要有三方面作用。
一是学习用,仅供司法官员、幕僚、讼师等有断审需求的人学习之用。“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28)这是把成案比作范文,可临摹不可硬套。胡肇楷也指出:“律例为治世之书,而文简义深,非参观成案无以通变而妙其用”。(29)成案是前人所办案例,只读律例不读案例不能活用法律,但是不读律例只读案例、生搬硬套,结果必多错误。
二是套用。清代律例繁多,掌握不易,所以各级司法官及其幕僚往往从中取巧,熟悉若干个成案,然后拟断案件时一一照成案套用,往往就可以应付大多数案件的审判。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律例如古方本草,办案如临证行医,徒读律而不知办案,恐死于句下,未能运用。徒办案而不知读律,恐祗袭腔调,莫辨由来。直隶省习幕大都以办案入手,亦犹读时文而随解题旨,苟能不忘其本,相辅而行,未始不可融贯。特恐仅以一二成案为式,于全部律例置之不讲,则无源之水,其涸可待。故习幕者固宜多办案,尤宜熟读律”。(30)这就说明当时幕友多从办案入手学习,往往有以成案为范式,而不读律例的。这种套用成案的办法显然是违法的,但是从最后结果去看,拟断引律合于范式,上司也无从查考。
三是作为法源引用。能够用为法源引用的只是极少的成案,如《刑案汇览》所说的“例无正条、援引比附加减定拟之案”。(31)这些成案都是刑部通行的,原本是可以在修例时补充入例,从律例修订的情况来看,道光以后几乎进入停顿状态,虽然同治九年有过修订,但此后“刑部既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32)的状况,使这些通行成案处于微妙的地位,以致出现“彼黠胥猾吏旁立睨视,徐出成案寘几上曰:某年某省某案,前官议如是,则面赤唯唯,不敢复言狱事”(33)的怪现象。
因为有上述三个方面的用途,才共同筑就成案汇编类著作的流行,因此并不能就简单地用清代成案类著作盛行的情况作为成案是重要法源的论据。
最后谈一下判例与判例法的问题。许多人把清代成案看作是判例,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个混合法体系,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34)何勤华还以为“从《大清律例》以及清代保留下来的判例汇编中可以看出,中国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判例法乃至判例法体系。在清代,已经存在一种判例法的形成机制:国家审判机关(主要是督抚、刑部和皇帝)将判例(成案)认可适用,并将其定为例,使其通行全国,获得普适的权威,成为判例法,进而将这些例按照国家大法(大清律)的体系分别附于其后,成为一种判例法体系或制度”。“清代不仅存在着判例(成案),存在着判例法(定例),且还存在着判例法体系(大清例的体系)”。(35)这显然是将清代时“定例”也作为判例法,并且列出了一个由判例到法典的判例法生成机制:判例(成案)——判例法(通行)——附律之例。笔者认为,且不说“判例”一词在当代法学尤其是普通法体系中具有的特殊含义,清代成案实不适宜称为“判例”,也不能说“大清例”在形式上是实实在在的成文法,与非成文的判例法不同,即使清代的成案可以称为“判例”,可以忽略“例”是成文法的一个形式要素,由判例至判例法之间的道路,以清例而言,也并非如其所描述的那般顺畅。
在西方的判例法中,法律规则是由法官的判例所创设的,也就是说,法律规则不是任何其他个人或机关制定的,而是从判例中归纳得来的。清代的确有许多定例是在司法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但它不是从案例中归纳得来的,而大多是皇帝(或由他本人亲自提出,或由其他臣僚建议皇帝认可)针对新情况制定的新办法。比如,康熙末年,东南沿海洋盗活动频繁,为了惩治这样的江洋大盗,安徽巡抚叶九思在审理一起洋盗案件时,建议将江洋行劫大盗照响马强盗例,斩决枭示。这一建议获康熙认可,准为定例。(36)这里,巡抚提出一个新的办法建议,皇帝认可了这个办法,这明显是一个制定法产生的过程,与由判例归纳出法律规则有本质的不同。人们误认为皇帝在办案过程中制定的定例是判例法,原因在于皇帝集最高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他的立法行为与司法行为紧密相联。但是笔者认为,皇帝的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合一,与判例法体系中法官运用判例创设规则不同。判例法中的法官审断每一案件必须在已有判例(规则)的基础上,推演出合于公平原则的结论,而所推演的这个结论又成为日后其他案例推演的起点。也就是说,法官只是法律原则的推导者,不是创制者,他无权随意创设新规则;皇帝则可以随意创设新规则,他可以不受以往规则的影响随时改变规则。这是制定法律与推导法律的区别。在强盗条例中,最主要的处刑条例,如康雍时期区分“情有可原”,咸丰时期恢复“不分首从皆斩”,又如将针对特殊对象、地区、犯罪主体的强盗加至斩枭,窃盗拒捕的处理等等,这些规则都是新制定的,它背后有鲜明的制定主体——负有治世之责的君臣。这些规则构成了处罚强盗犯罪规则的主框架。的确有少量规则是在司法实践中经由判例确认的,但是这些规则是根据制定法推导出来的,在地位上是次要的,在数量上是较少的。不能因为有它们的存在,就把整个清代定例说成是判例法。判例法本质上与制定法相矛盾,也与清代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不兼容,它不可能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清代处理强盗案件的主要法律渊源是律和例,律例如果有冲突,用例不用律,用新例不用旧例;在律例规定模糊、欠缺或显失公允时,可以引用成案上请。
三
律与例是清代法律的主体,“律者,一成而万古不易者也,其与时势之推移,不能相应,此无如何者也。而条例,则世轻世重,准社会现象以为衡”。(37)条例的动态变化而富于灵活性,对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律进行了补充。以明示罪名安排法律条款,使罪名之间有了一定逻辑。罪名体系是按照一定体例、规则、秩序组合而成的罪名立法框架及表述方式,而条例又对罪名系统进行完善和补充。在“律例之法有尽,而法外之意无穷”的信条下,“由成案而观,则知以法断事,而事有不符,以事拟事”,从而达到“法无不尽”(38)的效果。
根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动态法包括法律秩序、规范等级体系、规范法学与社会法学等部分,那么“探求规范效力的理由,并不是像探求结果的原因那样,是一个regressus ad infintum(无止境的回溯);它终止于一个最高规范,这个规范是规范体系内的效力的最终理由,而在一个自然的体系中,是没有最后或最初原因的地位的”。(39)在这个规范体系中,有静态体系和动态体系,静态体系是建立一定的权威,而这个权威可以依次把创造规范的权力授予某些其他的权威,进而构成动态体系的各种规范。清代“为政之道宽猛贵乎相济,过宽则有废弛之患,过猛则有刻核之伤,二者各有流弊,皆当先事预防,以期政归平允”。(40)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静态体系与动态体系之间的关系,在针对犯罪进行惩罚的同时,注意到惩罚本身存在的警世功效。
分析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法律,要基于当时的社会,而当时社会的社会组织、政治体系、经济结构,以及大多数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都是影响该法律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该法律的深入研究,既是对前人文明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为后人行为抉择提供思想的启迪。
将相关的律例及成案汇集一起,结合相关的史料进行分析,可以因循律例修订、增删、改并,而了解其制定的历史背景,探讨隐含在其背后的、已经不太为现代人所知的立法目的。应该说,这是宏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正是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使我们有利于深入理解传统。在对一些律例或罪名研究的同时,既弄清该律例或罪名的因袭发展,又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在当时立法中起指导作用的思想观念和基础理论,将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研究的深入。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中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在许多地方已经与中国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国情,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有许多精华。在当前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改革与完善我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呼声甚高,许多学者鄙夷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崇拜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希望通过移植以达到完善今天政治法律制度之目的。但笔者认为,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也是现代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资源。
法是文本表达与社会实践的综合体。文本法体现着政治理念和统治思想的理想化追求,实践法则是法的运用和实际操作。《大清律例》作为时代的产物,其文本体现的精神和价值势必在实践中得以丰富和拓展。中国传统法律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其执行过程中以皇权为转移的“综合式”治理。君主借助司法充分地游刃于法律之间,从而无往不在地施展其政治技巧,以达到其驾驭全局的目的。
应该承认,清代在法律承袭与修订过程中,基于维护统治秩序,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变革。这种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41)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的国力与政治都曾经向强盛的方向发展,出现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然而“盛世”并不能掩盖危机,传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弊端,在新的情况下越来越显现出来,以至于“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42)清代法律的承袭与修订不能摆脱这样的状况,形成了“清世曹司不习吏事,案牍书吏主之,每检一案,必以属书吏。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43)的循例办事制度。“例者,一成之法,永远可以奉行。案者,一时之事,轻重可以出入也。故杀人一也,而谋故分。处分一也,而公私别。一部而彼此两歧,一司而前后兼异。苞苴既入,则援案以准之,而不能指为瞻徇。要求不遂,则援案以驳之,而不得目为挑剔”。(44)在高度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情况下,统治者很难依靠自身的体制革除弊端,最终还是走上了法愈多而弊愈多的循环怪圈。
注释:
①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导论第2页。
②《清史稿》卷142《刑法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86页。
③瞿同祖:《清律的继承与变化》,载《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另参见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32页,对二书的引用。
④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46页。
⑤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⑥吕丽:《例是辅律 非以代律:谈〈清史稿·刑法志〉律例关系之说的偏面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
⑦张晋藩:《清朝法制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0页。
⑧⑨(清)祝庆琪、鲍书芸、潘文舫、何维楷编:《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册,第124-125页、第585页。
⑩(清)同德:《成案续编》卷4《强盗》,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同心堂刊本。
(11)光绪《清会典》卷54《刑部·五刑之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12)(清)徐栋:《牧令书》卷17《刑名上》引无名氏《刑名总论》,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本。整句曰:“欲理刑名先明律例,律乃一代之章程,例为应时之断制,有例应照例行,无例方照律行。律例俱无,则用比照,比照宜的确不得游移。”此段文意与《大清会典》相通。
(13)瞿同祖:《清律的继承与变化》,载《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
(14)王锺翰:《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15)(清)王凤生:《宋州从政录·批虞城县覆禀》,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本。
(16)(清)不著撰者:《治浙成规》卷4《委署同通等缺查照原议章程办理》,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刊本
(17)(清)海宁:《晋政缉要》卷7《修治军装》,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山西布政使司刊本。
(18)还有一种狭义的成案,是指钦命通行各省,遵照执行的成案。这种成案其实已经获得了定例的效力。本文将它作为定例看待。此处所论之成案是指广义的已成之案,不包括通行在内。
(19)参见[日]小口彦太:《清朝时代の裁判にぉける成案の役割にっぃて——刑案汇览をもとにして》,《早稻田法学》57卷3号,1982年;《清代中国の刑事裁判にぉける成案の法源性》,《东洋史研究》45卷2号,1986年。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第55-56页,215-217页。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王志强:《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0)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17页。
(21)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2)王志强:《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3)(清)许梿、熊莪:《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熊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版。
(24)(清)许梿:《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续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版。
(25)其中照案者有:《成案汇编》第3案《在洋行劫声明情有可原驳案》,洋盗是否分别情有可原发遣;第18案《盗首虽经捆缚事主》,未经成伤闻拿自首仍准减等案、盗首自首,曾捆缚事主,是否照未经伤人盗首自首拟遣;《邢案汇览》第6案《拒伤事主分居亲属与事主同》,事主之分居叔父、堂兄是否算事主;第25案《临时谋杀事主仍照临时拒捕》,临时谋杀事主适用临时拒捕例还是谋杀人律;第35案《行劫衙署伙盗接赃免死发遣》,行反劫衙署之犯是否分别情有可原发遣;第39案《首盗冻毙事主伙盗免死发遣》,强盗行劫致死事主[光避冻死]是否按强盗杀人处刑;第77案《洋盗强盗年幼拟流应行刺字》,强盗年幼拟流是否刺字;等共有7案。不准照案者有:《成案汇编》第11案《哄开大门入内行强不准援案宽减》临时行强成可否减为斩候;第14案《先窃后强持刀恐吓事主赃已满贯不便拟遣》,临时行强情轻可否照案发遣;《刑案汇览》第67案《洋盗投首免其从前窃劫各案》,投首盗犯以前行劫之案是否赦免;等3案。不准照案而追究违例援案者责任的有《刑案汇览》第55案《既经入室虽不搜赃亦应斩决》,入室未搜赃是否归入情有可原。照案改例的有《刑案汇览》第60案《海江盗劫分别情有可原》,滨海沿江行劫是否分别情有可原。不准照案而照新定例的有《刑案汇览》第62案《洋盗案内买赃摇橹定账定例》,接买盗赃二次是否照成案发遣。此处所列第几案,是原书所收强盗案例前后排序所得序号。
(26)光绪《清会典事例》,卷852《刑部·断罪引律令》附律条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27)光绪《清会典事例》,卷852《刑部·断罪引律令》乾隆八年事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28)(清)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引成案》,清同治十年(1871年)慎间堂刻本。
(29)《新增成案所见集总编·序》,转引自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215页。
(30)(清)盘峤野人:《刑幕要略》附《赘言十则》,光绪十八年(1892年)浙江书局刊本。
(31)(清)祝庆祺等:《刑案汇览[三编]·凡例》,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2)《清史稿》卷142《刑法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87页。
(33)(清)许梿:《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续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4)参见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阐释》,《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汪世荣:《判例法在中国传统法中的功能》,《法学研究》2006第1期。
(35)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6)(清)吴坛撰,马建石、杨育棠校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37)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2页。
(38)(清)孙纶:《定例成案合鐫序》,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刊本。
(39)[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40)《皇清奏议》卷46载熊学鹏《诗慎改律令疏》,罗振玉根据清内府藏抄本刊印,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41)[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陈镇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42)(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变法中》,上海书店2002年版。
(43)(清)罗惇曧:《宾退随笔·记书吏》,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7年版。
(44)(清)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0《吏政十一·吏胥》载尹耕云《胥吏论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图书集成局精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