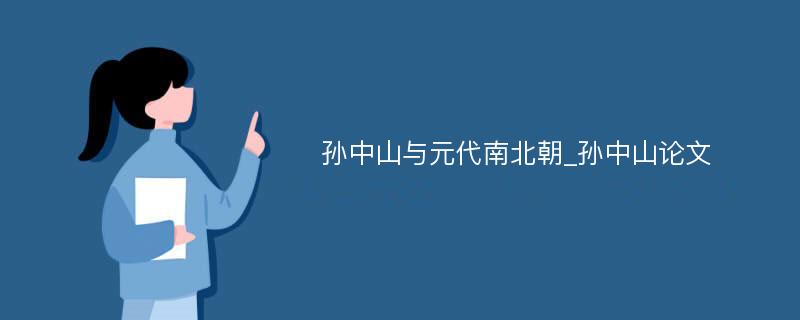
孙中山与民元南北议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5-0559-07
1911年末至1912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2个月的议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次议和谈判,简称民元南北议和。这次议和,与辛亥革命成败有密切关系。过去国内对这次议和的评论,贬多褒少;孙中山被说成是反对议和的左翼代表;让权袁世凯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衡诸历史实际,这些评论不尽合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此做些评论。
一、南北议和格局的形成
民元南北议和,是当时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南北议和在几经曲折之后,最后达成协议,也是诸多社会力量互相妥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归根到底,是由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过去把民元南北议和说成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不无一定道理,但存在片面性,即把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片面地夸大了。不顾情势,把议和的责任全归咎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是不公平的。
首先,最早倡导议和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在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又充当了导演的角色。英国是当时外国在华势力最大的国家。革命党人首义地在英国势力范围,纷起响应的地区,主要也在英国的势力范围。战火的蔓延与扩大,势必对英国的利益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因此,他们迫切希望革命战火早日熄灭,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早在武昌起义不到半月,当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向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四国银行团提出一年期1200万两的贷款时,四国银行团的惟一要求就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1](第765页)。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革命烽火遍及全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惊呼:“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朱还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2](第60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11月26日汉阳之战进入最激烈阶段之际,朱尔典感到“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于是立刻会见袁世凯,陈述了英方意见。袁当面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同时,授权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将此意向转各黎元洪[2](第73页)。英驻汉口总领事葛福秉承朱尔典的电示,立刻着手斡旋,终于很快达成在武汉地区停战三天(12月3-6日)的协议。12月4日,停战刚才实行,袁世凯又会同唐绍仪起草了议和大纲,仍然是通过朱尔典授权葛福“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款被接受”。其中第一款即为“目前的停战期限届满后,延长十五天”[2](第133页)。此后停战一再延续,直到达成协议。这样,在英使导演下的停战,就成为辛亥革命由军事斗争走向议和谈判的转捩点。
同样,在议和谈判中,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的意向,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北议和的谈判,英国驻华使节充当了牵线人。议和谈判的地点也是在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厅。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的寓所,同样是由英方精心安排,住在英国资本家李德立的家中。为了促使南北和谈成功,在英国的串通下,英、日、美、德、法、俄6国公使于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共同决定,议和谈判开始前,即由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分别向双方代表递交同样内容的照会,强调“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2](第167页)。这简直就是对议和双方代表下命令,哪是什么照会?
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共和制,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每当谈判出现波折,总是英国势力在发挥协调作用。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包括美、法等共和制国家,开初皆不赞成。由于南方革命党人坚持不屈,执意实行共和制,大多数国家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东邻的日本,由于担心中国改变政体会影响本国政局,仍然坚持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并准备对中国实行强力干涉。议和谈判因此一度停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此多方疏通,并由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代表英国政府表态:“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2](第172页)日英是同盟之国,日本见连英国都不支持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才“暂时表示同意,以观日后演变”[3](第336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国内各地吁请共和的压力下,也于12月28日由隆裕太后发布懿旨,同意政体问题“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4](第155页)。这样,停顿了8天的议和会议,才在12月29日恢复。通过连续3次会议,最终就召开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清帝退位,是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重要条件。面对这个问题,袁世凯自己不便开口,又是外国势力为之搭桥架梯。1912年1月,南方革命党人已一再表白,只要清帝宣布退位,实行共和政体,就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是,如果按照双方协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非3个月不能成事。因此最简捷的办法是由清帝顺应各方共和要求,自行宣布退位。在这种情势下,英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后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首先建言:“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1](第830-831页)结果,在他的策动下,上海商会首先向清廷摄政王等发表通电,汉口商会等继起响应。段祺瑞等42名高中级军官也通电赞成共和,要求清帝退位。清廷接到各方来电,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接受退位后的优惠条件,于2月12日正式宣布退位。
其次,袁世凯赞成议和,尽管别有用心,但他作为议和一方的主持人,也是议和的促成者。没有袁的主持,议和是无法进行的。如所周知,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实为革命党人起义之赐。如果不是武昌起义,至少他不可能如此快速东山再起。袁氏心中明白,清廷起用他,是因为有一支受他控制的北洋军。因此,他只有保存北洋军的实力,才有他的地位。他决不愿孤注一掷,让北洋军与革命军拼个同归于尽。议和则是保存北洋军的最好办法。何况,袁利用南北议和,正可左右开弓,揽取权利。这样,议和对于袁氏来说,又何乐而不为。
从清方来考察,议和导源于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武昌首义之初,清廷中的顽固派不识时务,一意主剿,“以为武昌一隅,大兵一到,指日可平”。但是,袁世凯却认为:“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5](第269页)故他一出山,就使出剿抚两手,一方面谕令冯国璋率军大举进攻汉口,一方面又派遣刘承恩“办理招抚事宜”。刘一再致书黎元洪,表示只要接受招抚,“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5](第278,281页)。他们以实行君主立宪做诱饵,企图要求民军“和平”放下武器,放弃民主共和,遭到革命党人的严辞拒绝。汉阳两军决战,尽管北洋军最后获胜,但已造成北洋军的巨大损失。如果每次战役都这样硬拼,北洋军势必遭到灭顶之灾。特别是此时全国已有14省宣布独立,三分天下已占其二,未独立各省也不断发生起义。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种形势决不是靠武力能平服的,招抚亦失去效力,惟一办法就是与民党停战议和。
至于议和方针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唐绍仪南下前,已经有所策划。据赵秉钧谈,在唐南下前,洪述祖即向唐绍仪建议,“乘此机会,仿照英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其进行,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创建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指唐绍仪)为新国内阁总理”[5](第289页)。这个办法得到了唐绍仪的首肯,估计唐也征得袁氏的同意。所以,在议和的第二次会议上,唐绍仪才敢于公开说:“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并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4](第77页)此后持续一个多月的南北和谈,尽管有过多次曲折,而大旨未出上述范围。虽然在议和过程中,袁氏装模作样,一再申述主张君主立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即使在唐辞去代表职务之后,唐通过梁士诒与袁通声气,仍继续从事促和活动,“秘密私电往返,均从促成共和着手”[5](第292页)。
第三,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促进议和中亦发挥了重大作用。上海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江浙等地的大资本家都集中于上海。他们以张謇为代表,为了使自身经济利益不受破坏,并谋求进一步发展,很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有一个和平环境。张謇等人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眼见革命起义之后,实行民主共和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很快转变为拥护共和。先是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就运用他们的地位与影响,在南北间穿针引线,竭力促成议和。他利用与袁世凯的旧谊,“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持落日,要来扶起朝阳”[4](第41页)。并且与南方革命党人商妥,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就一定举他为总统。他告诉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袁氏“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4](第42页)。袁世凯之舍弃君主立宪,倒向民主共和,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劝说是分不开的。
张謇身为清末状元,受到清廷恩宠。他在转向共和时并没有忘记旧情。为了促使清帝体面退位,一面劝说革命党人许以清帝退位后给予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又恳劝清廷看清大势,顺应潮流。他在致清内阁电中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希望清廷“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4](第41页)。这纸电文情词恳切,对促使清廷退位,导致议和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更有进者,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是采用了张謇的代拟稿。唐绍仪之出任北方议和代表,也是通过赵凤昌从内部通款曲,“请为国家戮力,南来协商大计”[6](第78页)。后来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出任内阁总理,这种折衷至当、兼顾南北的主意,同样出自赵凤昌。赵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位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对此,孙中山、黄兴拍掌赞同,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7](第196-197页)。凡此都可表明,这批人在议和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南方革命党人赞同议和,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南方革命党人对议和的态度,以汉阳失败、南京光复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袁世凯出山后,推行招抚政策,以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等为条件,诱劝革命党人放下武器。革命党人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断然拒绝招抚,反劝袁世凯趁此机会弃暗投明,“共扶大义”[5](第281页),“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8](第71页)。由于双方的要求差若天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汉阳被冯国璋攻占后,革命党人经过这次实力较量,已知单凭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不是易事。但清朝的军力,也只有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如果能把袁世凯争取过来,推翻清朝统治并不困难。所以,当袁世凯通过英使朱尔典提出议和时,对革命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因而盘恩过江来到武昌时,孙武等人立刻同意停战。军政府都督的印盖被黎元洪带走,不妨仿刻一颗代替。各省代表会议也相应通过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不久,黄兴又致电汪精卫,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9](第94页)。这些足以说明,通过停战议和,建设共和民国,已是革命党人的普遍愿望。即使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亦在所不惜。
考究革命党人趋向议和的根由,最根本的是实力不足,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增长到足以战胜敌对力量的程度。特别是在军力与财力上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不得不另筹出路。另外,也有认识上的错误。他们把思想认识的转变,看得太简单,以为清帝退位,共和建立,就算革命目的达到,实在太天真了。
二、孙中山与南北议和
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酝酿停战议和之际,孙中山尚在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直到12月25日,他回到上海,南北议和已正式开始一个星期。因此,前段和议,他未能实际参与。在此后的南北和谈,他显得非常关心。1912年1月2日,他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即致电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10](第6页),足见他对议和的进展十分关注。
孙中山此时的中心思想,在于争取共和政府早日成立。因为他在欧美从事外交、借款活动,均很不顺利,原因就在于革命的中央政府尚未建立,外交承认自然无从谈起,借款更无从着手。而当时要解决的燃眉之急是财政困难,别无办法,惟一的指望就是向外借款。至于如何才能使国家早日统一,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筹划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在摧毁旧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和谈,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再举袁氏做大总统。基于这种策略,孙中山对议和并不反对,对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也很赞同。他的态度是,总统可以“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簿[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的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11](第547页)。
前已提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孙中山反对议和的观点。这种观点,实导源于1917-1919年间孙中山自撰的《建国方略》。其在《有志竟成》一节中说,当1911年12月回到上海时,中外各报皆说他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他的回答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12](第246页)这段话因为是六七年后的回忆,不十分准确。查对孙中山当时与《大陆报》主笔谈话,明显有较大出入,孙当时是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耳。”[11](第573页)如果把六七年后说的话作为孙中山反对议和的依据,显然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议和前后孙中山的言行,恰恰表明,孙中山不是反对议和,而是赞成和议的。对于举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也始终表示支持。先拿议和来说,他在回国前,对议和即持赞成态度。1911年11月21日,他与《巴黎日报》记者谈话时即表示:“现在革命之举动,实为改良政治起见,……以平和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1](第562页)12月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又对胡汉民、廖仲恺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11](第570页)孙中山归国之后,几天之内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第二天就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10](第5页)1月14日,孙在复直隶、河南谘议局电中重申:“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解职之条件,……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10](第20页)1月29日,在复伍廷芳电中复强调:“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共和之目的。”[10](第50页)这一系列言论表明,孙中山对议和是一贯赞同的,如能不劳兵力,实现共和,可为世界开一未有之先例,何必用兵。
再来看选举袁世凯当总统。早在1911年11月16日,他就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惟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11](第547)这时南北和谈尚未开始,只是黎元洪在11月12日复袁世凯的信中有此表示,目的在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所以孙认为只要合宜也是可以的。后来回到香港,在和胡汉民等谈话中,他更进一步表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1](第569页)。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孙中山对举袁世凯之得失利弊是经过深思熟虑,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在12月29日被各省代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因怕袁误会,当天即致电袁世凯表白:“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1](第576页)袁世凯果然因孙被举为临时大总统而深表不满。孙中山又于1912年1月2日复电袁世凯再次申明:“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10](第5页)后来,在具体讨论议和条件时,袁世凯还是有些担心总统落空,孙中山又做了多次重申,强调“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10](第38页)。这些言论一再表明,孙中山为了以和平手段,达共和目的,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始终一贯。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孙中山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诺言。
当然,孙中山并非一意寄望于和谈,对武力统一同样有所准备。如在1912年1月初,即拟订了六路北伐计划,并致电陈炯明:“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0](第7页)到了1月下旬,由于在讨论清帝退位时一再拖延不决,孙中山担心和议破裂,复致电黎元洪做好北伐准备,指出“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10](第41页)。在致伍廷芳电中则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今曾提交参议院,尤极愤激,誓以同心共去共和之障碍。”[10](第43页)当时真要开战,最大的困难是财政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孙中山在致陈炯明电中对真情有所吐露,他说:“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10](第41-42页)当时在无款可筹的情势下,为了弄到借款,曾努力向日本财界求助,甚至不惜以出卖东三省权利来换取日方的支持。在接洽借款中,孙对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派来之森格说:“革命政府的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假如军队财源不能尽快解决,将完全到达破产境地。万一此数日内没有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则将陷入许多军队离散,革命政府瓦解之命运。”[13](第106页)由于财政极端困难,北伐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只有议和,解决清帝退位,建设共和政体,才是较好结局。孙中山赞成议和,情愿让位于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三、议和的成败得失
关于南北议和的成败得失,前人有不认议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袁停战议和,是否应该?假如不与袁议和,革命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
为了辩明上述问题,首先有必要做点理论探讨。停战议和就是与敌对势力妥协。多年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妥协成为与革命对立的贬义词。实际上,不加分析地对妥协一概否定,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妥协通常有两种: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这类妥协当然必须反对。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谋求暂时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求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平息国内叛乱,苏维埃政权代表曾与德奥集团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尽管因此丧失了大片土地,却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摆脱了国际战争,使新生的革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对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争取抗日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妥协都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妥协,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应予肯定。
辛亥革命时期的停战议和,对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也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这个原则就是民主共和。民主共和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是革命党人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议和中,革命党人始终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最后,通过南北议和,也实现了民主共和。应该说,这对革命党人是个很大成功。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最终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飞跃,大大地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停战议和,国内许多地区的战火得以停止,遏制了战火向其他地区蔓延,因此避免了战争的巨大破坏,使广大人民减少了战争灾难,无疑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带来了许多好处。这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益的。
战争是一场生死之争。敌对双方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势必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战争本身造成的将士的死亡,物力的消耗,不用说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由于停战议和,人力物力的损失自然因此大量减少。这也是非常明白的。
停战议和无疑是敌对势力之间的一种妥协。既然妥协是双方的,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这种情势下,对革命党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不少后遗症。辛亥革命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反封建不彻底。除了给清朝皇帝满蒙贵族势力以许多优惠外,最大的祸害就是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得以保存下来,并窃据要职,继续欺压人民,致使革命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华民国仅保留一块空招牌,还招来了1915年和1917年的两次帝制复辟。而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这股北洋军阀,后来经过多次斗争,直到1928年,通过大革命才最后消灭。
如果不停战议和,辛亥革命是否会有更好的一种结局?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做分析。实事求是来说,当时封建势力已经腐朽透顶,清朝统治已经人心丧尽,要推翻它是大势所趋。它必然垮台,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势力是一种新生力量,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有强大生命力。但在当时仍很弱少,无论在军力、经济力以及社会影响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反动势力的地步。这就导致妥协的必然性,只可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不可能经过一次斗争就把封建势力彻底摧毁。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复斗争了近50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复斗争了80年;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包括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前后也延续达90年。中国的革命党人当然比英、法、美资产阶级势力更弱少,又何可能靠一次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呢?何况,当时外国的侵略势力都支持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资产阶级上层也在为袁帮忙。因此,依据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妥协具有必然性。如若革命党人不顾时势,反对妥协,势将如孙中山估计的,革命势力会立刻瓦解。假若出现这种局面,革命很可能以失败告一段落。其结局将会更坏。诚如孙中山后来说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14](第126页)。
收稿日期:2001-04-08
标签: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唐绍仪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