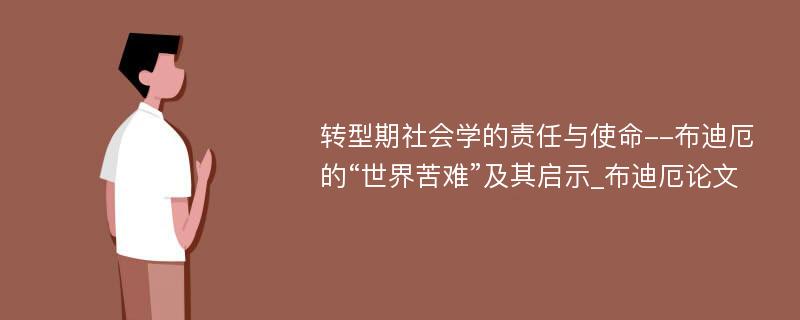
转型时代社会学的责任与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难》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苦难论文,使命论文,启示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随着布迪厄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国内,以及众多运用他的概念与理论进行的理论的或经验性的研究陆续发表,布迪厄的学说,如场域和习惯的理论以及象征资本、符号暴力和参与性对象化等概念,还有他所强调的实践与反思的社会学立场等,在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已经广为人知。然而,这些概念、理论多属于布迪厄早期和中期的学术思想,晚年布迪厄的思想其实经历了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学术与政治立场更加锋芒毕现,进一步确立了他作为一名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的牢固地位。作为布迪厄晚年的一本代表性著作,《世界的苦难》( La misère du monde) 构成了这个转型的重要标志。尽管这部煌煌巨著看起来似乎因过于“沉重”而令人却步,但了解这部著作,对于我们理解晚期布迪厄的理论乃至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学术生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与布迪厄的其他著作相比,《世界的苦难》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也许首先并不在于它所具有的理论性如何,而更在于蕴含在这种学术实践之中的价值关怀和它所产生的社会性及政治性的效果。为什么研究社会疾苦?当代社会有着怎样的疾苦?疾苦的根源何在?怎样去揭示这些社会疾苦?所有这些方面,都源自布迪厄始终恪守的“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的学术立场,凝结于布迪厄身上所体现的科学、政治和知识分子公民之使命的完美统一的伟大精神。正由于此,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情境中,布迪厄关于社会疾苦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其中所体现的学术操守和道德关怀,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无疑更具有某种现实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世界的苦难》
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是布迪厄晚年主持的一项重大的学术活动。这个研究项目历时三年之久。1993年,作为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世界的苦难》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隆重地呈献给了世人。此书一出,立刻登上畅销书榜,并在当时法国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平等、种族歧视、社会团结等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当代法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英文版于1999年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面世,取名《世界之重: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分别由政治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布迪厄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世界的苦难》与其早期和中期的作品相比,显得相当特殊。这不仅在于它的形式,更在于其内容所蕴含的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与其22位合作者,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细致深入的生活史个案,为读者展示了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在形式上,这部著作大多数篇幅是对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的经理人、农民、中学生、老人、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 hustler) 、右翼分子及支持者,也包括那些基层的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法官等各式人等的访谈。而且,为了尽力展示蕴含于其中的“荒谬”,同时也为了避免刊诸书面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访谈内容尽量保持了未加雕琢的原始形态。(注:一旦投入对社会疾苦的研究,那些日常的苦难极大地触动了研究者,在与德国作家格拉斯的一次名为《来自下层的文献》的对话中,当格拉斯问及为什么不运用一些文学技巧,让描述带些反讽的幽默时,布迪厄表示,研究者在直接记录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亲耳聆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感到极大震惊,因而很难超然于外,以至于在实际的编排中,不得不舍掉了那些令人感到过于悲伤的案例。然而即使这样,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看似十分普通甚至平淡无奇的案例,却蕴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暴力性”。而为了还原这些故事中的暴力性,需要避免文学化,而以这种极端实际的方式加以呈现。另外,这样做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布迪厄表示,他“感受到此刻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国家犯下了滔天暴行,难以用纯粹的概念分析加以解释,手中掌握的批判资源都不堪以对付这种政治制度造成的后果。”( Grass & Bourdieu, 2000) )实际上,布迪厄和他领导的小组所做的这些访谈本身就是这些研究者运用“社会学技艺”在实践中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创造性过程。正是通过研究者的社会学解读,这些主要来自于底层的日常生活的片断和讲述被赋予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厚重感。
二、布迪厄的学术与政治
理解布迪厄的这个研究,必须了解布迪厄的政治立场和实践。布迪厄虽然多年来都身居法国知识界的核心位置,但他矢志不渝地坚守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注:或者用布迪厄自己的话来说,他属于“左派中的左派”,布迪厄使用这个称呼意谓与已经变节的法国社会党划清界限。)无论是在他等身的著作中,还是在实际的行动中,布迪厄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保持着对政治的积极介入。严谨的科学精神与政治激情交织在一起,虽不及福柯那样彰显,但却深沉而执著,始终贯穿于布迪厄的学术实践和生命历程之中。而且,如果说布迪厄惯常的介入政治的方式相对低调而内敛,那么在布迪厄晚年则显得越来越激进而张扬。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布迪厄成为公认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围绕新自由主义批判这一主题,先后有《抵抗行动》(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和《反击》( Firing Back: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两本小册子,以及政治评论集《干预:1961-1991》( Interventions: 1961-1991) 等出版(卡尔豪恩、华康德,2003)。布迪厄于2002年1月23日去世后,《世界报》以头条报道此事,称他为反对自由市场正统与全球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华康德等学者(2003)在悼念布迪厄的一篇文章中对他评价说,“作为福柯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布迪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的忠实辩护人。”
在布迪厄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之间有着一种彼此交融的关系。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在华康德看来,布迪厄所倡导的反思社会学,始终遵循着涂尔干的立场,深切地关注着社会学的道德意义和政治蕴含(布迪厄、华康德,1998:52)。按照布迪厄的理解,作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和“慈悯”的工具,社会学具有一种除魔祛魅、揭示社会隐秘、破除社会宿命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各种形式的神秘化和符号支配,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关系的种种神话,揭示行为必然性和所谓社会法则背后隐含着的历史关联,而一旦人们掌握了有关于此的必要知识,就可以从政治上瓦解它们(布迪厄、华康德,1998:56、278)。可以说,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十分突出地体现了布迪厄赋予社会学的这种艰巨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疾苦的大规模调查,是布迪厄学术生涯晚期从事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也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
三、社会疾苦的形式
关于什么是社会苦难,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界定。(注:在法文版原著中,布迪厄用的是misèry一词。按照Donald Reid的理解,布迪厄使用这个词,是为了避开社会学与抽样调查惯用概念的局限。在法国的传统中,这个概念用来刻画物质上与心理上的痛苦,晚近用来描述被剥夺的社会学现象,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像性关系等方面( Reid, 2002) 。布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也指出,如果把物质贫穷作为度量疾苦的唯一尺度,会使我们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社会体制所具有的痛苦性质的方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疾苦在医学人类学中已成为一个相当正式的研究传统,如在当代医学人类学代表人物Arthur Kleinman那里,Social Suffering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这里,布迪厄对“社会疾苦”概念的运用虽然也充满了病理学的隐喻,但其最终的落脚点更多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不是身体意义上的。不过,正如Kleinman(1996)所指出的,《世界的苦难》深化了对痛苦的社会分析,建构了“社会疾苦”这种新的研究对象。)但是,阅读这部著作中每一个故事,就会感受到其中无不流露出的痛苦。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有种种具体的表现,甚至有评论称这部著作是当代法国社会苦难的百科全书。了解什么是社会的疾苦,当然最好是去细读这部著作中每一段具体生动的故事。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这些细微具体、隐含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社会疾苦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
其一,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表现为内在矛盾形式的“位置痛苦”( positional suffering) 。
比如,布迪厄和研究者们揭示出,对于那些为弥补市场经济不足而承担着所谓“社会功能”的警察、基层法官、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人员来说,在他们致力于应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疾苦时,在国家赋予他们的繁重的、无休无止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十分有限的方式手段之间存在矛盾,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必然会感受到这种张力,体验到这种“双重困境”( double binds) 和政府体制之内存在的“制度的自欺”( institutional bad faith) 带来的痛苦。
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学校也陷于矛盾境地。教育体制承担着社会公平的功能,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集体失望和潜在的社会排斥的永久之源。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给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是又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提供任何保证。那些在学校和劳动力市场接连遭遇失败的青少年具有一种在社会阶级的等级体系中“底层化”( subproletariat) 的特征。在市场原则主导的教育体制下,学校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所谓“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分化,这种分化由于污名化机制而不断加剧,实际上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教师、学生感受到这种结构性矛盾:学校中充满了失序、紧张、甚至暴力,学生心理脆弱、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教师承受着多方面压力,为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所困扰。
另外,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还提到了一类存在于家庭代际继承关系之中的痛苦。布迪厄指出,当代社会,不管有无可能实现,父母都将自己的期望补偿性地投射到子女身上。无论成败,许多人对父辈的期望和自己所能达到的成就之间的差距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与社会流动、教育体制、种族歧视、阶级结构和女性地位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世界痛苦的一个重要社会来源。比如,对于那些新一代外来移民来说,他们与父母一代产生了显著的断裂和冲突。他们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他们与过去、宗教、家族有着某种断裂;但又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之中,而是遭到更强烈的歧视,这种地位双重性给这一代移民造成心理上的焦虑和背叛感。
其二,一种集体性和社会性的解组,表现为伴随着集体衰落的个体的悲惨际遇。社会怨恨、种族歧视、工人阶级衰落等问题明显地属于这种社会疾苦的形式。
布迪厄和研究者们发现,在法国外来移民聚居区的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与交往遭到破坏,正常的邻里生活不复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微琐事分歧,都可能成为本地人和移民之间产生摩擦的导火索。暴力行为时常光顾这样的地区,本地居民搬离,公共设施撤出,外裔族群和整个社区经受着社会排斥和污名化的过程。种族歧视、社会怨恨不断积聚,导致了对极右排外主义的政治支持。(注:在布迪厄看来,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布迪厄、华康德,1998:278)。因此在实际的调查之中,他尤其关注到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怨恨心态及其生成机制,并将勒庞( Le Pen) 为首的法国极右势力的抬头的原因归结为于此。不过,对于这种政治立场,布迪厄视之为一种对痛苦的反应和表达。)在黑人聚居区,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沉默的暴力,合法的劳动市场衰退,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兴起。社会信任被严重破坏,每个人只能依赖自己,生活变成了一种日复一日的生存技艺。这些地区常规的规范机制缺失,陷入一种霍布斯所讲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演变成一个自相残杀的闭合的循环,遮没了以往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毒贩向自己的母亲兜售毒品,兄弟反对兄弟,穷人反对穷人,整个贫民窟共同蹈向一种集体自杀的陷阱。更具悲剧性的是,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演变成为一套“事物的秩序”,甚至剥夺了黑人对社会排斥的感知意识。
工人阶级经历了一场集体的衰落。工人分裂成产业工人和临时工两个群体,老工人们无法传授他们那一代长期为之生存和竞争的技艺与经验。劳工运动消失殆尽,工人中间充斥着不信任和躲躲藏藏的暗地行为。在新一代工人中间,缺乏政治意识,缺乏统一的集体性的政治语言,他们只是考虑现实的谋生问题。仅有的反对态度,也只是针对那些他们认为挡住他们道路、阻碍他们机会的“老家伙们”。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大工业的衰落,冒出林立的小公司,雇员很难成立工会,维护自身权益。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令工人们只能屈服和沉默。而管理者通过种种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群体,鼓励形成围绕管理者的群体,强化特殊主义、增加人们之间的妒忌和敌对。这些策略消解了工人们之间的社会连接。“过去工人团结起来对付监工,而现在是工人反对工人。”( Bourdieu, 1999:331) “没有谁能帮助谁,每个人只顾自己”(同左:319)。随着整个工业区的衰落,工人个体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命运,职业生涯断裂,生活陷入危机状态。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离婚、酗酒、自杀等现象十分普遍。(注:在Simon Charlesworth(1999)所撰的《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一书中,这些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心态,在工人普遍“失语”的形象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
四、社会疾苦的政治根源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社会疾苦呢?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并没有就此综合地给出明确结论,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布迪厄对此的分析。比如,在住房供给等问题上,布迪厄指出,考虑到197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背景,(注:布迪厄指出,在法国,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从1970年代开始,以1980年代中期社会党领导人加入这个阵营标志完成。布迪厄在《世界的苦难》中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花招实际上表达的都是高级国家精英的观点和利益。)“国家的退出”( the abdication of the state) (同前:181)以及公共设施服务的枯竭,必须为外来移民聚居区的衰败负主要责任。华康德在对黑人贫民窟勾勒的“反面乌托邦”( Dystopia) 的黯淡景象中也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市场与国家双重退出”(同前:152)的过程,或者说一个“美国政府有意为之的城市放弃政策”(同前:132)的过程。
“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地,也不想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同前:183)。在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下,国家精英鼓吹市场的原则,而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后果都被推卸给了那些承担社会职能的公共服务部门。在布迪厄看来,那些承担着社会职能的人员也感受到身处“双重矛盾”之中的痛苦,也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造成的。在谈到社会福利的时候,布迪厄则指出,福利形式从集体福利到针对个体的救济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从直接针对分配结构的政策向简单地纠正资源分配不平等效应的政策的转变,这种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国家救济形式,“加上工联主义及组织群体弱化等原因,将一群具有动员潜力的人们转化成由碎片化的、孤立的穷人组成的、充满异质性的乌合之众,用官方说法,即弱势群体。”(同前:184)
其实,在布迪厄对社会疾苦的研究中,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社会疾苦,在其背后都有着某种共同的政治性根源。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个世纪之前涂尔干在社会转型中找到了失范的原因……,而今天,布迪厄则发现苦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运作。”( Reid, 2002) 如果说,在《世界的苦难》这部著作中,在这一点上布迪厄表达得还相当含蓄和零碎,那么在布迪厄后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十分明确。在一篇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檄文中,布迪厄明确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套旨在破坏可以阻止纯市场逻辑的集体结构的行动纲领”,使社会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状态( Bourdieu, 1998) 。该书英文版在英国出版之后,布迪厄接受了《社会主义评论》的采访。当采访者问及为什么近些年来许多人日子越来越难熬的时候,布迪厄的回答直截了当:“主要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和我称之为‘国家的退出’的政策。”( Bourdieu, 2000)
布迪厄晚年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也正是由于他看到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这些问题,才力图通过政治的手段来矫正这个有可能将世界重新引入灾难的危险趋向。在他看来,20世纪末期“欧洲人民面临着历史转折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斗争的成果,为了争取工人和市民尊严的各种知识的、政治的战斗成果已直接受到威胁”,这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倒退的可能性,“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为掩护使复辟正当化”(华康德,2003)。这里所说的威胁,也就是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行其道。
通过《世界的苦难》一书,布迪厄不仅指出了新自由主义转向是造成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根源,而且,也表达出对由此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的忧虑和关切。比如,他把对法国极右势力政治支持的上升看作种族歧视、社会怨恨的结果,而这些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所导致的社会不满和社会分裂的重要形式。布迪厄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称作“保守的革命”或“进步的复辟”,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回复到过去,却伪装成进步的姿态,把倒退说成进步。”( Grass & Bourdieu, 2000) (注:布迪厄将新自由主义革命称作一场“复辟”或者“倒退”,是因为他看到某种历史的相似性。理解他的这个说法,需要回到博兰尼所说的那个“大转折”的时代。十九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兴起。当自由放任、拒绝一切外在干预的市场资本主义挟国家之霸权,试图把单一的经济原则强加于社会整体之上,雄心勃勃地力图建立起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支配原则的市场社会时,却带来剥削加重、环境破坏、经济波动、社会动荡等种种苦难,而由之造成的最严重后果莫过于二十世纪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极权主义政体诞生等人类文明的危机,自由市场体制的神话自身也陷于破产(博兰尼,1989)。又一个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再次处在新的历史关口,面临着由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带来的严峻挑战,原教旨主义复兴、恐怖主义流行、极右势力抬头、民粹主义泛滥、文明间冲突上升、贫富分化加剧,如此等等。历史似乎在重蹈悲剧性的覆辙,而并非已经在福山那洋洋自得的理论自负中终结于所谓自由市场加代议民主的理想模式(福山,2003)。虽然经济自由化和市场转型似乎是为解决博兰尼面对的那场大转变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必经的道路,但是这种转型并不必然带来它所许诺的美好前景,而是非常可能塑造出坏的社会模式。事实上,它也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不满、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不断生产出新的不平等,并导致集体价值衰落和社会整合的消解。这些正是布迪厄所揭示当代世界社会疾苦最深重的表现形式。)许多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看到或者预见到了新自由主义泛滥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但布迪厄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怀着悲悯的情怀,运用社会学的技艺,在社会世界的日常生活领域向公众展示了这些社会疾苦的存在,并揭开了屏蔽这些社会疾苦的权力机制,从而给新自由主义以最深刻、最扎实的回击。
五、研究的目的与方法论
布迪厄之所以倡导这项研究,还有一些直接的原因。他痛心地看到,当代政治领域逐渐走向封闭,各种常规化的政治仪式和科层化的政治操作,已经遮蔽了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且不断积聚的歧视、不满、怨恨和苦难。政府领袖们被一些乐意于借助民意调查一类的“社会巫术”进行治理的技术官僚所左右。这些人不懂得自己无知到何种地步,对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缺乏了解,通过貌似科学的手段和集体性的话语制造出掩盖社会疾苦的政治幻象。这种“蛊惑人心的伪科学”(布迪厄、华康德,1998:262)不仅无益于揭示社会问题,反而对现实具有一种压制性的政治效果。媒体屈从于内外部的压力和竞争,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不加反思,给出一些轻率的描述和结论,对社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之一的Patrick Champagne以专门的章节分别批判了在对于社会问题的理解上来自于媒体和技术官僚的官方立场,揭露了媒体记者和专家们的民意测验所建构出来的“社会问题”的虚伪性。)在知识分子中间,一部分陷入沉默,另一些人则热衷于到处抛头露面,喋喋不休地讲着人们不愿意听也听不懂的套话,实际上妨害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性。而此时此刻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却被排斥在政治世界之外,得不到合法表达的机会(P627)。
在布迪厄看来,新自由主义转向造成种种社会疾苦,但这些疾苦及其根源却被“巫术化”的社会调查、被媒体权力等机制掩盖了起来。面对这种恶劣的状况,布迪厄表示,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绝不能袖手旁观,而要积极介入。他主持这项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就是为了揭示出被那些社会机制屏蔽的社会疾苦及其运作机制。他用一种社会病理学的比喻来阐明自己的研究目的,那就是“把难以名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使它们可以用政治的手段来加以治理”(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1998:265)坦诚地讲,这项研究不仅是科学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这个研究就是要让那些对社会疾苦麻木不仁的技术官僚们意识到社会当中不断积聚的苦难和不公正,让被压制和扭曲的声音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得以表达,从而为通过政治手段对社会病患加以疗治提供必要的条件。
而为了揭示这些社会疾苦,就需要走进普通人群,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与轨迹,重构他们被掩盖、被歪曲的历史。在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中,布迪厄彻底抛弃了早年他还经常使用的统计方法,采用的是一种深入访谈的形式。因为在他看来,“一般而言,如果进行沟通交流,没有什么比同时关注从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生发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真实也更切实的方式了”(P607)。这项研究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265)。在布迪厄看来,访谈中的对话,不仅是一种具有偶变性的互动结构,而且隐含着形塑它的社会空间结构。因此,研究过程是在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情境知识的基础上,采用被访者的语言、观点和立场,以特定的生活史的形式将所有对个体而言可用的素材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加以理论建构。
在对社会疾苦的研究中,这些从事调查的社会学家,彻底突破了所谓宏观与微观的虚假对立,以社会学的专业想象力,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捕捉着那些个体命运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微妙关联。这些有关普通人的文本,按照英译者的理解,与其说是访谈,不如说是一个个短篇的民族志。的确,在阅读书中的案例时,给人的印象是这些素材细腻深入,却无处不闪耀着研究者专业的洞察力和灵感。比如,在北非移民聚居区,通过对当地居民的访谈,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邻里日常生活中抱怨与纠纷等“私人政治”背后深刻的社会意涵。“我们不再有邻居,我们互相不说话”(同前:26)、“人们不怎么来往”( People weren' t very sociable) (同前:42),这种邻里关系的解组、怨恨的积聚,最终导致种族歧视和对极右排外势力予以支持的政治倾向,“一听到是移民,我就按捺不住自己”(同前:100)、“我要投票给勒庞”(同前:111)。
为了在研究实践中捕捉到这一点,布迪厄倡导一种苏格拉底助产术式( maieutics) 的研究方法。首先,在研究的实践中,研究者要进行一种“参与性对象化”,理解并考虑到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对研究造成的影响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培养“社会学的技艺”。只有具备了这种“技艺”,才能做到在研究现场随机应变,把握好提问的机会和尺度,帮助被访者讲述他们的真实状况和想法。布迪厄(1998:265)自信地指出,正是突破了所有正统方法论的清规戒律,才使得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捕捉到了所有官方科层调查根据事先的定义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总之,布迪厄在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反思性的立场。(注:在1997年出版(法文版)的Pascalian Meditations一书中,布迪厄批评民意测验以及学究取向。提出在研究实践中,需要注意到提问者的意图与被访者非学究取向的固见之间存在的隔阂所具有的效应。在《世界的苦难》中,研究者持续不断地反思,就是力图使调查关系中存在的固有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交流过程中的扭曲得以控制。实际研究中需要一方面避免引入学究偏误,另一方面协助被访者实现自我理解、自我关照。( Bourdieu, 2000:59) )理解这部著作的方法论,有一句话非常关键:“真正做到从材料出发,需要以在实践中对形塑这些材料的社会逻辑的把握为基础,进行建构活动”(P617)。
六、简短的结语
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布迪厄把《世界的苦难》留给了世人。不管布迪厄把当代社会疾苦的根源归结到新自由主义转向是否冤枉了新自由主义者,不管这个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怎样的争议,都无可否认这部著作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正如关于此书的简介中所言,这部著作最主要的贡献是,不仅提供了一套分析社会生活的独特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种实践政治的方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集“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于一体的经典研究,面对时代变迁的主题,承担起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或许,就此而言,这部著作的英译本所取的带有几分文艺性的主标题——“世界之重”用在诸位作者身上要比用在封面上更为贴切:They carried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their shoulders。
强调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尤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面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社会学究竟提供怎样的产品,是每一个专业人士必须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这不仅事关在这个需要社会学一展身手的时代、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公众中树立什么形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考验着当代中国社会学有无严肃地面对这场深刻转型的魄力和能力,也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学者的学术操守和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