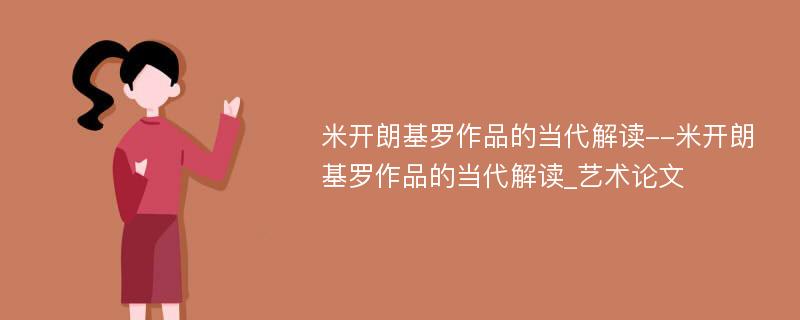
闻鸡鸣而怆然涕下——米开朗琪罗作品的当代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鸡鸣论文,当代论文,米开朗论文,作品论文,怆然涕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彼得雕像中寄寓的人生体验
被后世称之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雕塑巨匠米开朗琪罗,晚年致力于为耶稣的门徒彼得雕塑一座“超人类的纪念碑”。这其中缘由,恐怕有着丰富且复杂的潜台词。
米开朗琪罗从不肯把自己在雕像中寄寓的思想告诉任何人(比如米开朗琪罗那尊著名《摩西像》,有人问起,他总是不屑一答:“干你们的活,执行我的命令。至于弄清我脑子里的思想,你们永远不可能做到。”他的作品究竟是表现了惩戒还是宽容,几个世纪以来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弗洛伊德曾以心理大师的笔触,专门撰有数万字的长文《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来探究米开朗琪罗在摩西像中寄寓的理念)。
思想无法用语言完整准确地表达。老子有言: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当我们对任何一件艺术珍品用文字说明解释时,只会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地冲淡缩减了其本身涵蕴。雕像本身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罗》(武文胜、万亭编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披露:米开朗琪罗的晚年与耶稣最喜爱的信徒彼得一样,不止一次因听见鸡鸣而痛哭流涕。
初始接触米开朗琪罗之“闻鸡鸣而怆然涕下”,望文生义,第一感觉是一种珍惜时间珍爱生命,与“闻鸡起舞”是异曲同工的表达。
米开朗琪罗有诗句云:
可怜,/可怜!/我被已逝的生活抛弃……/我有过太多等待……/时光飞逝,/我已垂垂老矣。/我不复能在死者面前忏悔和自省……/哭也徒然,/没什么不幸能与失去的时间相比……
对日月如梭时光飞逝的恐慌,每逢“鸡鸣天亮”新的一天开始,都会产生时光虚掷老之将至的悲哀。昨日犹如东逝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罗》里,描绘了米开朗琪罗“工作狂”的劲头:
他说:“我为了工作而精疲力竭,从来没有人这样工作过。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他什么也不想。”
“……他甚至想雕刻整座山。如果要建造某个纪念性建筑,他会经年累月地跑采石场,挑选石头、修筑道路运输石头。他事必躬亲,样样自己动手,过的简直是苦役犯的生活,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在他写的信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我几乎连用餐的时间都没有,没有时间吃饭,十二年来,我累垮了身体……’”
“……干起活来像拉磨的马。没人明白他这样自虐的原因,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适可而止地工作,谁也不明白他这样自讨苦吃是为了什么?”
在波伦亚忙着为尤里乌斯二世塑铜像时,米开朗琪罗和三名助手只睡一张床。睡觉时衣服靴子都不脱。有一次他腿肿了,只好将靴子割开,脱靴子时,腿上的皮也被扯了下来。
米开朗琪罗的传记作家瓦萨里,还记载下这样一个细节:
“……整个罗马城都入睡了,他睡不着觉,半夜里起身打夜工。用凿子开始工作。他用硬纸板给自己做了一顶头盔,中间插上蜡烛,戴在头上。这样既起了照明作用,又腾出两只手可以不妨碍工作。一天夜里,瓦萨里去看望这位老人,他独自呆在凄凉的屋子里沉思,面对着他创作的《哀悼基督》。
瓦萨里敲门,米开朗琪罗站起身,拿着蜡烛去开门。瓦萨里想要看看雕像,米开朗琪罗的蜡烛掉在地下熄灭了。屋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米开朗琪罗的所有杰作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乌尔比诺去找另一枝蜡烛时,米开朗琪罗伤感地对瓦萨里说:‘一切都快消失了。我太老了,以至死神常来拽我的裤腿,要我随她同去。有一天,我的躯体也会像这支蜡烛一样倒下去,像它一样,熄灭我的生命之光。’”
人生苦短,生命不再,当一个人的生命帷幕即将拉上,恐怕任何人也难免陷入悲苦恐慌的情绪之中。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罗》一书里这样描述米开朗琪罗:“他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整个世纪的光荣都体现在他身上。对意大利而言,他是天才的化身。不仅艺术家将他视为超人,王公们在他的权威面前,也得礼让三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卡捷琳娜·美第奇向他致敬;科斯梅·德·美第奇大公想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米开朗琪罗到罗马的时候,以王公贵族的礼节对待他;科斯梅大公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平起平坐与他亲密交谈;科斯梅大公的儿子则像晚辈一样,把帽子拿在手中毕恭毕敬。他的晚年像歌德、雨果一样为荣誉所环绕。”
求仁得仁,夫复何求?对于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老人,他还有什么人生抱憾,为什么还要“闻鸡鸣而怆然涕下”呢?
二、死何足惧,只是可怕奴隶生活的终结
米开朗琪罗(1475-1564)高寿八十九岁,当达·芬奇于1519年去世、拉斐尔于1520年去世后,米开朗琪罗又筚路蓝缕步履蹒跚地走过了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而言,米开朗琪罗并不惧怕死亡。
当死的意念一天比一天更阴暗地笼罩着米开朗琪罗时,他对瓦萨里说:“我的任何想法,无不刻有死亡的印记。”“当我的过去重现在眼前,我这才认识了人类的谬误与过错。喔,虚伪的人世,谁若相信了你的谄媚和虚妄,必为自己的灵魂备下悲痛忧伤的苦果。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最明白。你经常许诺你没有,也永不会有的安宁和福祉……因此世上羁留最久的人,是最不受恩宠者;出生后旋即死去的,才是上天选中的娇子。”
米开朗琪罗还说:“我是被迫的,我的艺术是在敌对的环境中成长的。”
米开朗琪罗在他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我的生命,在波涛险恶的海上,由一叶残破的小舟渡到了彼岸。在那里,大家对于虔敬的作品和冒渎的作品下一个判断。由是,我把艺术当作偶像,当作君主般的热烈的幻想,今日我承认它含有多少错误,而我显然看到一切的人都在为着它的苦难而欲求……既非绘画,亦非雕塑能抚慰我的灵魂。”
这个长寿老人的晚年,经历了身边一个个亲人和朋友离他而去的苦痛。
1534年米开朗琪罗在纪念父亲之死时写道:“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的变化和欲念的改变……今后的日子里不必再面对专制与暴政,需要和偶然也不可能再操纵你……想到这些,我怎么能不羡慕呢?”
米开朗琪罗最喜爱的助手——弗朗切斯科·达马多雷别号乌尔比诺死后,米开朗琪罗给瓦萨里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乌尔比诺死了,这对我是极残酷的折磨,却也是上帝赐予我的极大恩惠。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使我也能存活;他一死,教我也懂得了死,并非不乐意而是很乐意死……比死更难以忍受的,是让我苟活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上,在数不清的烦恼之中。我身上最精华的部分已随他而去,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
米开朗琪罗已经厌倦了这个充满谎言多灾多难的人世,只愿速去不愿留。临终时,米开朗琪罗要求人们让他回忆基督的受难。晚年,他几乎是倾注全力颂扬基督的受难。受难升华为一种精神遗产。
生命终场的帷幕即将拉上,米开朗琪罗孤零零地独自留在暗夜之中。在驾鹤西去之前,米开朗琪罗反省人生,甚至感觉到不能对自己说,已经做了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一切来安慰自己。
米开朗琪罗向上帝发出绝望的呼号:“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谁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
米开朗琪罗不畏惧死,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结”,是一种解脱!
米开朗琪罗临终的遗言,发出的竟是这样的呼喊:“不再活着!不再是自己。逃出天地万物的桎梏!摆脱自己的幻觉。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复为我自己吧!”
谁能相信这是举世瞩目声名显赫的一代巨匠的声音?米开朗琪罗居然不愿成其为米开朗琪罗!
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其实,截然不同两极取向的话却是殊途同归,本质上阐明的是一个意思:不愿做现实中那个逆来顺受的自我;希望成为理想中那个我行我素的自我。
三、米开朗琪罗的“著书都为稻粱谋”
在米开朗琪罗长寿的一辈子,没休息过一天,没享受过一天真正的人生。这位雕塑家毕生辛勤忘我的创作,完成的只是一些他所不愿意画的宗教壁画,竟然没有一件作品是真正表达自己心目中的伟大构想。
渴望自由的米开朗琪罗,总是从这副桎梏转到另一副桎梏,从这个主子转换为另一个主子。尤利乌斯二世去世后,新任教皇利奥十世照样竭力控制米开朗琪罗,让他从颂扬前任的事业中转换过来,为他自己的家族树碑立传。利奥十世之后,又是克雷芒七世。
所有的教皇如出一辙,他们只是把艺术和艺术家作为他们自我煊耀自我标榜为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工具。文学艺术成为权势的婢女。
克雷芒七世登上教皇宝座后,曾于1521年4月29日授意他人写信给米开朗琪罗说:“新教皇克雷芒七世崇拜你所作的一切,他把他所有的爱来爱你的作品。他讲起你时那么慈祥恺恻,一个父亲也不会对他的儿子有如此的好感。”1521年12月5日又写信说:“如果你愿到罗马来,你要做什么便可做什么……你在新教皇治下有你的名分,你可以做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
克雷芒七世意图让米开朗琪罗为他建造美第奇教堂和他家族的陵园,要他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还要就近监督他。克雷芒七世还建议米开朗琪罗参加教派,这样就可以让他享有一笔教会的薪俸,三倍于别的主子给他的数额,还送米开朗琪罗一座邻近圣洛伦佐教堂的房子。
米开朗琪罗当然明白,天上不会平白无故地掉下馅饼,他从接尤利乌斯二世定金中已经尝足了苦头,这些定金犹如卖身契,就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米开朗琪罗决心放弃豪宅,拒绝薪金。米开朗琪罗的朋友们觉得他的举动简直不可理喻:难道金钱地位还会咬人?有朋友写信劝他:“听说你拒绝你的薪俸,放弃你的住房,还中止你的工作,在我看来这纯粹是疯狂行为。我的朋友,我的伙伴,你这是在和自己作对……”(1524年3月24日Fattucci致米开朗琪罗的信)
人生活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上,物质是生存的基础。谁能把这种“布衣傲王侯”的劲头持之以恒?
教皇的司库当真按米开朗琪罗的请求撤销了他的薪俸。在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一统下,可怜的人儿,几个月后就陷入了绝境。米开朗琪罗不得不重新申请他曾拒绝的钱。起初他还有点不好意思,羞羞答答地写信给教皇的司库:“亲爱的乔凡尼,既然羽笔总是比舌头更大胆,我就把近来屡次想对您说,却又没勇气亲口说出的话写信告诉您:我还能得到月俸吗?……即使我确信不再有薪俸,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安排,我将一如既往地尽力为教皇工作。”
人家想给米开朗琪罗点教训,便故意装聋作哑。两个月以后,米开朗琪罗还是没有得到一点回音。而他的生活越来越困窘,他只得再次提笔给教皇的司库写信:“经过仔细考虑,鉴于教皇如此关注圣洛伦佐教堂这件作品,且主动给我一笔月俸,想让我更有条件加快工程进度,那么我若不接受月俸便无异于延宕工期了。所以我改变了主意。迄今不曾申请薪俸的我,现在,出于一言难尽的理由,我要提出申请了……您能否从答应我的那天算起,把这笔钱给我……请告诉我,何时能拿到这笔钱?”
米开朗琪罗曾无比感叹地说了这样的话:“我为教皇服务,完全是不得已。”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地球人谁也没有能力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生你养你的星球!
这是米开朗琪罗的“著书都为稻粱谋”?!
雕塑家格依贝尔蒂在其回忆录里,讲述了安茹公爵手下一位德国金银匠的故事。此人的技艺,“足可以与希腊的古雕塑家媲美”,到了晚年,却目睹耗去他毕生精力的作品,只不过是王公贵夫人们头上的装饰、手中的玩物。全部辛勤工作换回的是终身徒劳。他跪下悲天怆地地呼喊:“主啊,人是天地的主宰,万物都是你的创造,别让我再误入歧途,除了你,我再也不追随其他人了!可怜可怜我吧。”然后,他把所有一切全部散给穷人,从此隐居山林,了其余生。
罗曼·罗兰说:“米开朗琪罗如同那个可怜的德国金银匠一样!到了晚年,痛苦地看到他的一生犹如虚度,他的努力全是徒劳,他的作品不是未曾完工,便是遭到毁坏,等于一事无成。”
米开朗琪罗曾为尤里乌斯二世铸造了一尊铜像,1508年2月落成。这尊倾注了米开朗琪罗心血的铜像,在圣彼得罗尼奥的正门前仅仅立了不到四年,1511年12月,尤里乌斯二世的政敌班蒂沃利党人就把此铜像砸毁,用其碎片铸成了大炮。随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统治者的更迭,米开朗琪罗那些为当政者所用的作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随之灰飞烟灭,我们今人对此铜像,“仅闻其名,未谋其面”。
这就是“为统治服务的艺术”的必然命运?
四、两个时代反差形成的巨大裂缝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罗》里,还有这样一段描述:“米开朗琪罗忧郁成性,他在自己周围营造了一片空虚。最糟糕的还不是孤独,而是和自己过不去。他总是否定自己、反对自己、摧残自己。他有天才,却长着一颗背叛这种天才的心。有人说这是他的宿命。命运使他激烈反对自己,阻止他实施任何伟大的计划。这所谓的命运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在政治上、艺术上,在一切思想和行动上都优柔寡断……他开始、开始,总到不了头,既想又不想……什么事他都要反复考虑,辗转不安,刚做出选择又开始怀疑,直到生命结束……”
与米开朗琪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另一雕塑家朱利亚诺。他走的是另一极端:太自我陶醉敝帚自珍了。朱利亚诺每完成一件作品,别人还没说什么,他自己先赞不绝口。米开朗琪罗说:“这是他的幸福。我自己之所以十分的不幸,正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创作的任何作品都不能使自己完全满意。”
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可能超越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局限吗?
米开朗琪罗1514年承接下弥纳尔教堂的基督像,但直到1518年,四年过去了,他还没能开始动手。米开朗琪罗在日记中写道:“我痛苦死了……我总在犹豫不定,我真不知我该如何下手……”1510年,米开朗琪罗与西也纳教堂签订了契约,承诺三年后交出成品。可是直到五十年以后的1561年,他仍在为完不成作品而痛苦。
我国的先锋批评家崔卫平曾说:“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的时候,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一个思想的第一秒之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刚才相反的意思。因为我们站立的位置,是两个时代的反差形成的巨大裂缝。”
这是一个勇于探索、勤于思索的艺术家的特征。
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产生巨大反差的两个时代交替之际。萨伏那洛拉既领改革的前潮也步专制的后尘;路德既要求自领启示的权利也不同意其他信徒拥有这个权利;同样,天主教既反对宗教改革也接受人文主义的世俗教育。这就是米开朗琪罗生活的时代背景。任何两种制度交替、两种观念交锋的时代,必然使人充满矛盾和困惑。
罗曼·罗兰说:“米开朗琪罗犹如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哈姆雷特。”
别林斯基在评论到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时说:“这种精神的分裂,缘自思想的深刻。越是深刻的思想,这种分裂来得愈是惨烈。驴子是不会精神分裂的,因为他不会思想。”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中有着丰富的心理内容。
这是一个先驱者探索的悲哀。也是一个思想者思考的悲哀。
五、米开朗琪罗的“避席畏闻文字狱”
1490年,米开朗琪罗十五岁。宣教士萨伏那洛拉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对《启示录》进行宣讲。他看到这个矮小羸弱的宣道者,全身透着圣灵之气,在讲台上用可怕的腔调猛烈抨击教皇,将上帝血淋淋的宝剑悬挂在意大利的上空,不禁吓得浑身冰凉……佛罗伦萨发抖了。人们在街上乱窜,发疯似地又哭又喊……米开朗琪罗也没能逃脱这种惶恐情绪的感染……萨伏那洛拉下令焚烧散布“虚荣和邪说”的书籍、装饰品、艺术品,直到萨伏那洛拉去世,他一直是艺术家中最具异教色彩的一个……两个敌对的世界展开了对米开朗琪罗灵魂的争夺。
1495年,各党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米开朗琪罗的哥哥利奥纳多因相信预言而被追究;萨伏那洛拉四面楚歌,最后被宗教裁判所焚死在火刑柱上。
这场幼年时的激烈动荡,把米开朗琪罗吓坏了,他逃离了佛罗伦萨,一直逃到威尼斯。对此后发生的一切,米开朗琪罗噤若寒蝉不置一词,在他的书信中,也没留下这一事件的任何痕迹。只是在此后不久,米开朗琪罗雕刻了《耶稣之死》。
米开朗琪罗雕刻《耶稣之死》,寄寓了对那个时代“无所不在的恐怖”。米开朗琪罗也许是通过作品向世人宣告:那个热血青年的米开朗琪罗从此死去!
米开朗琪罗不敢对抗人世间政治和宗教的权势,他在书信中总是流露出对自己对家庭的担忧,唯恐一时冲动,说出反对某个专制行为的大胆言词而惹火烧身。他时时刻刻写信给家人,嘱咐他们多加小心,别多嘴多舌,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逃。
1512年9月,米开朗琪罗在致弟弟的信中说:“要像流行瘟疫的时候那样,尽早逃命……性命比财产重要……安分守己,切勿树敌,除了上帝,别信任何人,不要议论任何人的短长,因为事情的结局无法预料……最好独善其身,不要介入任何事端。”
米开朗琪罗这种恐惧心理敏感得有点神经质,亲人和朋友们都在嘲笑他。米开朗琪罗伤心地说:“你们别嘲笑我,一个人不应该嘲笑任何人。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所以他比别人更有理由恐惧。”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为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形成了一套秩序森严的等级制度,把上帝作为绝对权威。一切文学、艺术、哲学,都得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地依据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进行制裁,甚至处以死刑。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起步冲决这“黎明前的黑暗”,还处于“五更寒”的最严冷的时刻。
这是米开朗琪罗的“避席畏闻文字狱”?
哈维尔说:“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恐怖的理由,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失去东西。”这涉及到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极权专制的时代,个人有没有软弱的权利。顾准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与其号召大家都去做海燕,不如承认大多数人都是家雀的现实,并维护家雀的基本权利。”现当代的学者,对当年文艺复兴时代,一批科学家屈服于中世纪黑暗的软弱,进行了重新认识:究竟我们应该赞许那个为坚持真理而被烧死的布鲁诺,还是庆幸那个以妥协赢得继续研究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伽利略?这是一个人生悖论的永恒命题。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罗》一书中,如实记录了米开朗琪罗的软弱和恐惧:
他软弱,他总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实在太谨慎了。这个“使所有人,甚至教皇害怕的人”,却害怕所有的人。他在王公贵族面前很软弱,但却比任何人都看不起在王公贵族面前软弱的人,把他们称作“为王公贵族负重的驴”。他多次想躲开教皇,却始终没走,且十分驯服。1518年2月2日,大主教于勒·梅迪西斯猜疑他被加莱人收买,托人送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米开朗琪罗在回信中却卑躬屈膝地说:“我在世界上除了专心取悦于您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务了。”有时,他也反抗,说话态度好似强硬起来,但最后总是他做出让步。一直到死,他都在自我挣扎,却无力做出抗争。他被中世纪宗教审判所的血腥吓坏了。
……他会突然惊慌失措,由于恐惧在意大利乱窜。1494年,他被一种幻象吓得逃出了佛罗伦萨。1529年,佛罗伦萨被围,他受命承担城防重任,而他又逃跑了,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想逃到法国。稍后,他又觉得这种行为很可耻,决心弥补,便返回到被围的佛罗伦萨,一直坚守到围城结束。佛罗伦萨沦陷以后,许多人被流放,他又吓得魂不附体,竟去巴结那个刚刚处死了他的朋友巴蒂斯塔·戴拉·帕拉的法官瓦洛里。米开朗琪罗在侄儿告知他有人告发他与流亡者私通,他在回信中作着这样的辩白:“我一向留神着不和被判流亡的人谈话,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将来我将更加留意……我不和任何人谈话,尤其是佛罗伦萨人,如果有人在路上向我行礼,在理我不得不友善地和他们招呼,但我竟不理睬。如果我知道谁是流亡的佛罗伦萨人,我简直不回答他……”
更出格的是,米开朗琪罗因为恐惧,还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情:他否认他受到过Strozzi一家的照顾。他的信中说:“至于人家责备我曾于病中受Strozzi家的照顾,那么,我并不认为我是在Strozzi家中,而是在Luigi del Riccio的卧室中,他是我极好的朋友。”(Luigi del Riccio是在Strozzi家服役。而米开朗琪罗与Strozzi关系实际上非同一般,他曾送给Strozzi一幅作品《奴隶》,现收藏在法国卢浮宫)。
……他怕,同时对自己的惧怕感到羞愧。他鄙视自己,因厌恶自己而病倒。他想死,大家都以为他快要死了。但他死不了,他体内有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每天周而复始,痛苦则日甚一日。如果能无所作为该多好,但是办不到,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必须行动。他行动吗?行动了,但却是被动地行动。他像但丁笔下的罪人,被卷进激烈而矛盾的感情旋风之中。他不得不受苦。
米开朗琪罗在日记里写道:“哦,哦,我真不幸!在我过去的日子里,没有一天属于我自己。”
被逼迫说假话,不得不去谄媚讨好瓦洛里,颂扬洛伦佐和乌尔比诺大公,他痛苦羞愧得快要崩溃了,他只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把一切毫无作用的狂怒发泄在工作中。
那场罗马的劫难和佛罗伦萨的动荡,势必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理性的彻底破产和崩溃,使许多人从此一蹶不振。连昔日著名的先驱者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也堕落成为一个追求享乐的怀疑主义者。
1531年2月24日,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致信米开朗琪罗,这是罗马浩劫后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通信。他在信中说:“神知道我真是多么庆幸,当经过了多少灾患,多少困苦和危险之后,强有力的主宰以他的恻隐之心,使我们仍得苟延残喘,我一想起这,不禁要说这是一件奇迹了……此刻,我的同胞,既然出入于水火之中,经受着意想不到的磨难,我们且来感谢神吧,而这虎口余生至少让我们去追求苦中求乐。只要幸运是那么可恶那么痛苦,我们只当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吧。”这真有了“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意味。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还在诗中写道:“我已到了这种地步,/哪怕宇宙崩裂,/我也无动于衷。/我嘲笑一切……/我觉得我已不是那场浩劫前的巴斯蒂阿诺,/我再不能还原为过去的我。”
那一时期,米开朗琪罗绝望得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诗中写道:“如果允许自杀,/那么满怀信仰,/却过着悲惨的奴隶生活的人,/最应享有这个权力。”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罗》一书中说:“现在是懦夫的时代,他们在痛苦面前瑟瑟发抖,大叫大嚷地索要幸福的权利,而这种幸福往往是建筑在他人的不幸上。
将来,多少个世纪过去之后,总会有一天——如果我们的这个尘世还能保存在人类的记忆中的话——总会有一天,未来的人类会俯身在这个种族绝灭的深渊旁,如同但丁俯身在第八层地狱的火坑边望着,心中怀着感叹、厌恶和怜悯。”
六、雕塑像其实是刻画自己
米开朗琪罗在雕刻美第奇宗室的像时,其实是在雕刻他自己绝望的形象。当人们提出他的尤利乌斯和洛伦佐与他们本人并不相像时,他话中有话地回答道:“十个世纪以后,谁还能看出像不像?!”
这些雕像,倾注着米开朗琪罗的思想。底座上的四座辅像:《昼》与《夜》,《晨》与《暮》,仿佛是在给两座主像做着诠释,倾诉着米开朗琪罗内心丰富而复杂的潜台词。
意大利诗人乔凡尼·斯特罗兹看了米开朗琪罗那座寓意深长的《夜》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夜,为你所看到妩媚地睡着的夜,却是由一个天使在这块岩石中雕刻成的;她睡着,故她生存着。如你不信,唤她醒来吧,她将与你说话。”
米开朗琪罗说过这样的话:“睡眠是甜蜜的,成为顽石更是幸福,只要世上还有罪恶和耻辱的时候,不见不闻,无知无觉,于我是最大的欢乐。因此,不要惊醒我,啊,讲话轻声些吧!”
黑暗的夜就是让人睡觉的,但愿长睡不愿醒!
米开朗琪罗在另一首诗中还写道:“人们只能在天上睡眠,既然多少人的幸福只系于一个人身上!”“在你圣洁的思想切勿迷惘,相信把我从你那儿夺走的人,由于心怀恐惧,并不能从他的滔天罪行中获取丝毫享受。些许欢乐就能使情人们无比快乐,从而平息欲念;而不幸则使希望膨胀,欲念增强。”
米开朗琪罗这颗痛苦的灵魂,虽然那么战战兢兢深藏不露,但在内心深处却是满怀热烈的共和思想。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有时候,在知己朋友面前,或情绪格外激动时,这种思想会在火热的言词中流露出来。米开朗琪罗曾为多纳托·吉阿诺蒂雕塑过一尊胸像,就是这个吉阿诺蒂在《关于但丁〈神曲〉的对话》一书中,披露了米开朗琪罗这样一个细节:朋友们议论到布鲁图和卡西乌谋杀了恺撒,为什么但丁在《神曲》的地狱中,却把恺撒安排得比他们两人更深一层。米开朗琪罗马上为弑君者辩护道:如果你们仔细地读一读前几章,就会看出但丁非常了解暴君的天性,他知道他们该受到上帝和人类何等样的惩罚。他把他们归入“对他人施暴”一族,即打入地狱的第七层,将他们投入沸腾的血海之中……既然但丁这样认为,那就不可能不认同恺撒是该国暴君,布鲁图和卡西乌杀他属正义行为的说法。因为杀死暴君的人并不是杀了一个人,而只是杀了一头人面野兽。所有的暴君都丧失了人所共有的人类之爱,他们已失去人的本性,而只有兽性。他们显然对同类没有任何爱心,否则不会成为强取豪夺他人之所有,也不致成为蹂躏他人的暴君……显然杀死暴君并未犯杀人罪,既然他没有杀人,而只是杀了一头野兽,因此杀死恺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并没犯罪。首先他们杀掉的是每个罗马公民依照律法坚决要杀的人。
赏析米开朗琪罗的前期作品,直到《基督审判》时期,米开朗琪罗都把上帝描绘得极其严厉,是审判者而非爱的化身。
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塑造了一个“开天辟地”“全知全能”型的人类主宰形象。刻画了上帝动辄迁怒于人类的暴戾属性。他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充满毁灭的惩戒,而不是爱的福音。在创造亚当、夏娃的画面上,上帝的手与亚当的手若即若离,这可能是米开朗琪罗的一个象征手法。当亚当、夏娃因冲决愚昧被逐出伊甸园时,夏娃面露羞愧,而亚当则满面怒容,表露着一股反抗情绪。
在诺亚方舟大洪水的画面上,米开朗琪罗刻意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在灾难面前的互相扶持和相依为命,以此控诉降临这一灾难的上帝之不近情理和没有爱心。
在这一时期,米开朗琪罗勃发着强烈的反抗精神,画出了许多具有大胆异教色彩的作品。如《被鹅狎戏着的丽达》《被爱神抚摸着的维纳斯》等。
米开朗琪罗这一时期的绘画,究竟是宗教信仰式的,还是人文主义式的?米开朗琪罗在他的画中暗藏玄机。在倡导人权、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无疑在画中寄寓着自己深邃的现实思考。
米开朗琪罗在其早期的绘画中,一再表明自己反抗上帝的决心。米开朗琪罗仿佛是把他作品中的上帝,刻画成一生都在胁迫他的教皇的化身。这个时期,米开朗琪罗对上帝的理解,就是一个严厉而不近情理的暴君。
米开朗琪罗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对痛苦人生的感叹:
“可怜,/可怜!/回顾以往,/我找不出一天曾属于我自己!/扭曲的希望,/虚妄的欲求/——我现在算是认识到了——/把我羁绊。/哭、爱、激情燃烧、悲哀叹息(没有一种致命的情感我不曾体验过),/都远离了真理……
可怜,/可怜!/我不知何去何从;/我害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啊,上帝,让我弄错吧),/我看到,主啊,/我看到了永恒的惩罚,/因为我明知有善却去作恶。/我只能希望……”
“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对“今是而昨非”的忏悔,细思之,把米开朗琪罗的人生经历与彼得的命运际遇比照,就让人意识到其中更深一层的涵蕴。
七、“闻鸡鸣而怆然涕下”的深一层寓意
我查阅了《圣经》上彼得“闻鸡鸣而怆然涕下”的典故(译文取自《圣经的智慧》,韩凌编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得知彼得原先是渔夫,是耶稣最初收的六个门徒之一,也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个。
最后的晚餐以后,耶稣看出彼得已经有些动摇,知道他可能会有退缩的行为,预先安慰他:“等你悔悟的时候,一定要去坚定你兄弟们的信心。”
耶稣被捕后,门徒大都逃跑了。彼得不走,远远跟着耶稣,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想看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看门的使女认出了彼得,指着耶稣问彼得:“你不是这个人的门徒吗?”
彼得惊慌失措地摇了摇头说:“我,我不是!”彼得胆子小,害怕会受牵连。
仆役们生起了炭火,彼得正站着烤火,一个差役转过头问彼得:“你不是他的门徒吗?”说着冲耶稣呶呶嘴。
彼得使劲瞪了他一眼,压低声音说:“你说的什么话,我不是!”
旁边站着大祭司的仆人,就是被彼得砍伤耳朵的马勒的亲戚,盯着彼得又看了看,觉得自己没认错,对彼得说:“我亲眼看见你和他一起在客西马尼园子里!”
彼得真的恼了,忍不住大声吼道:“你们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正说话的时候,外面鸡叫了。
耶稣转过身看着彼得,眼神中包含着无限的体谅和期待。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出院门,失声痛哭起来。
身处黑暗之中,面对看不到摸不着的茫茫未知,人类大概天生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当“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后,一切都变得清晰可辨了,回首看自己恐惧下的诚惶诚恐卑躬屈膝,会油然生出痛恨交加的悔之莫及。
米开朗琪罗另外还画过一幅《圣彼得受钉刑》。米开朗琪罗在画面上画了各色人等,他们面对一个圣徒为上帝殉道的场面,每个人都心不在焉“心怀鬼胎”地打着各自的小算盘。米开朗琪罗将彼得的目光画得直视观画者,仿佛在拷问每一个灵魂。
米开朗琪罗完成的最后一件雕塑作品是,佛罗伦萨大教堂里的《耶稣降下十字架》。那个扶着耶稣下十字架的老人,米开朗琪罗给他画上了自己的嘴脸:一脸懊丧,满面悔恨。
米开朗琪罗的传世之作中,蕴含着多少等待我们后人去解读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