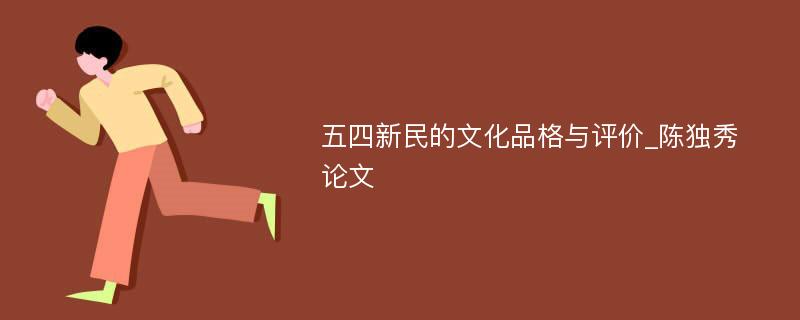
五四新人的文化性格与评孔开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格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孔开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3)03-0116-06
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不仅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国初年的排孔,也不同于历史上 尤其是近代史上的排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排孔,着眼于政治批判,文化附属于政 治,即便是在民国初年也是将孔子偶像作为封建帝制的政治偶像来批判的,这样,对于 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孔子之道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刻的文化清算。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就不同了。复古与帝制复辟运动来源于政治领域,也基本上通过政治的方式予以最 终解决。除此之外,留给人们思考的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话题:孔子之道充当奴役人们 思想的精神枷锁,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帝制复辟与猖狂进攻民主共和的反动工具,其 文化奥秘何在?五四时期的评孔批孔当然是如同一些专家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批 孔的深化,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深化恰恰来自于评孔批孔的角度转换,即由政治的批判 变为集中的文化批判。
一
陈独秀首先展现出辛亥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激进而富于战 斗的文化性格。其斗争的锋芒所指,是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核,亦即封建主 义的文化巢穴。针对袁世凯政府鼓吹“提倡国粹”,陈独秀即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 发表文章指出所谓的“国粹”,其基本精神不过是“忠孝节义”而已,其实就是“奴隶 之道德”。鼓吹“国粹”,就是要使封建主义文化“谬种流传”,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 族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败亡。他说: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 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 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 ,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 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注:陈独秀 :《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33—35、68—72、73—75、 94页。)陈独秀指出,儒家的“三纲”说教,是“奴隶之道德”的根源。因为“三纲” 说教,使人失去了主体精神,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痛恨袁世凯“洪宪帝制” 丑剧,将尊孔复古视为中国文化的灾难。洪宪帝制的覆灭,在陈独秀心中激起中国文化 新生的波澜。他借用“春秋笔法”,将1915年与1916年划断,视1915年为古代史,而对 1916年赋予新希望。陈独秀寓意深刻地指出,1916年是中国文化“除旧布新”的开始, 呼吁“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极力促进中国之新 生,中国文化之新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 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注: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5—6、33—35、68—72、73—75、94页。)。
针对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叫嚷定孔教为“国教”,赋予孔教以宪法的地位,鼓 吹以孔子之道为“立国之精神”,陈独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陈独秀指出,所谓孔教 ,不过是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护身符,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他说:“中国帝 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 ,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异者 也。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适者皆目笑存之,本 无辩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 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陈独秀揭示了孔教与封建帝制的内在关联,指出, 鼓吹孔教,就是反对民主共和。他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 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 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 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 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注:陈独秀:《 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33—35、68—72、73—75、94页 。)深入到孔子之道的文化特质里揭露孔教与专制主义的内在关系,从文化上排斥孔子 之道也就有了学理的依据。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 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由于“三纲”说乃是孔教之根本教义,因此,孔子之 道与国民教育精神的非相容性也就一目了然,而主张“废孔”也就有十足的理由了(注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33—35、68—72、 73—75、94页。)。陈独秀指出,不仅不能定孔教为国教,而且应该扫除孔子之道对于 国民的精神笼罩,为此,“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 之孔庙而罢其祀”(注: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 6、33—35、68—72、73—75、94页。)。陈独秀并不是将孔教作为一种宗教来反对,而 是将它作为有碍于社会进步的一种文化来反对,把它作为一种锢蔽人心的一种迷信来反 对,因此,他坚决地指出,只要是骗人的东西,不管它身穿什么外衣,都要统统予以反 对;不论它是不是自古相传的信仰,只要它是腐朽的、不合理的,就要统统推倒。这样 ,陈独秀评孔批孔的战斗性和深刻性,就体现在揭露孔子之道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和 主张破除“偶像崇拜”上,这正是既超乎前人,而又在思想上极其闪光的亮点。
陈独秀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将排孔的视觉转到文化上来,以及表现出来的坚韧的 战斗精神,不仅影响了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新人,而且明显地影响了新文化阵 线的他的战友们。
二
继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批判儒家“三纲”说教的文章后,易白沙发表 《孔子平议》的长文,直接批判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易白沙从揭示孔子学说内在的缺 陷易于为封建专制主义所利用出发,揭露了孔子学说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天然联系性。他 将孔学与封建主义的耦合揭露无余,从而揭破了“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孔 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独夫专制 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注: 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他指出,孔子的宏愿,“ 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但是,由于孔学自身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因而被历代封建 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白世之傀儡”(注:易白沙:《孔子平议》下 ,《新青年》,第2卷第2号。)。
李大钊从日本回来后,即投身于陈独秀发起的批判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旧文化的斗争 中。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相呼应,李大钊发表了朝气 勃勃的冲击中国旧思想旧文化的美文《青春》。他认为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 将中国的发展导入了死胡同,“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 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他呼吁“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 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注:李大钊:《李 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0、204—205页。)。《青春》与《敬告青年 》的视点切入、思想观点、豪放激情、旷达文风一脉相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双璧。但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则对李大钊评孔批孔的彻底性估价过低,认为,虽然李大钊在 此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要比他自己的过去更为激进,显得“要严厉得多”,但 是,他“没有对孔子的传统加以彻底的批判”(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7、42页。)。这是不切事实 的。针对康有为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将孔教写入《宪法》的鼓噪,李大钊表现出同陈独秀 等人一样彻底的战斗精神。他认为,“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 ,“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乃“怪诞之事实”。因为 ,“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 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 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 ,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此孔子之纪念碑也,此孔子之墓志铭也”;何者为孔子之 道?何者为非孔子之道?必如何始为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必如何则否?此质之主张规 定此条之议宪诸君,亦将瞠目而莫之所应。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 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自取其效力之告白也”(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甲寅 》日刊,1917年1月30日。)。李大钊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四天后,又发表《自然的伦理 观与孔子》,指出:“余谓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 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 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则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而何也”?“余谓孔子为历 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 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 利用资以为护符也。”(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 年2月4日。)批孔开新,李大钊的态度十分坚决,论述深刻,在打破孔子之道的精神桎 梏上没有回旋,也没有半点儿含糊。
三
当然,只有态度的坚决,绝对产生不出深刻的思想。深刻思想的产生,来自于研究问 题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运用正确的方法。由于李大钊掌握并运用了唯物史观来破孔子 之道,因此,李大钊虽也像陈独秀一样,批判孔学的伦理道德,但是,李大钊比他的战 友乃至同时代人都要深刻,因为他探寻了孔学的伦理道德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而找到了破除孔学的伦理道德的最根本的途径。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 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 、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孔子的学 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两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本身的权威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 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 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 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 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要彻底铲除孔子之道对于人们的精神束缚,就得动摇 孔子学说千百年来所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 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 、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 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 ,第178—179、181—182页。)
思想的共鸣,是思想者之间的思想共鸣。通过对中国封建主义、儒家学说与家族制度 的分析研究,吴虞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两千年 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注 :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7、176、171、98、167页。)。 吴虞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正是支撑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孝”与“礼” 则是旧伦理旧道德的核心。因此,吴虞的战斗利器直指儒家伦理道德的孝和礼。吴虞指 出,在封建家族家长制下,因宗法血缘关系而建立起子女“孝顺”父母的家庭伦理,在 社会中又放大为臣子为帝王“尽忠”的社会伦理;由于封建国家不过是父权家长制家庭 的放大,因此,一国之君主,也就是一国之家长,而一国之臣民只能像孝顺其父母那样 来效忠于君主,这样,从家庭到社会,“孝”与“忠”就成为束缚人的伦理观念。吴虞 认为,即使在旧时代,对于“孝观念”以及“孝养方式”的提倡,真是“糊涂荒谬极了 ”(注: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7、176、171、98、167页 。);更何况是在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它与人们的精神需求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必须彻 底抛弃旧时代的“忠孝”伦理,塑造新的国民。吴虞指出,孔学所主张和鼓吹的礼教, 较之忠孝伦理有更强的道德制约性,因而其危害性也就更大。吴虞批判吃人的礼教说: 为了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 ”!“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 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就是现在的人,或 者也有没做过吃人的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干净净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 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 骗我们的,讲礼教就是吃人的呀”(注: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63—67、176、171、98、167页。)!吴虞从人性的高度抨击孔学的伦理道德,是很有 战斗力的。
有的论著虽然肯定“吴虞对儒家文化的排斥与批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态 ”,但是,又指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吴虞并未来得及认真思考”,“吴虞对儒 家文化的批判没有得出积极的结论”,“结果,原本激进的非儒主张并未得出什么更为 先进的结论”(注: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 页。)。这个评价显得不那么公允。所谓“积极的结论”和“更为先进的结论”,我的 理解是,指吴虞没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来批判孔学,也还没有明确地具体地指 出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吴虞的要求未免过高,也近似于 苛刻。一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前,文化新人都是借助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武器与中国 旧文化决斗,他们在那时还不可能运用更为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关于中国文化的发 展方向与出路问题,不可能得出“更为先进的结论”;但是,如果缺少了这时的环节, 绝不可能有此后揭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文化批判,从而得出“更为先进的结论” 。这就是说,吴虞对于孔学的批判以及所达到的水平,不可能超越历史所能给予的既定 条件,他对于孔学的批判已经达到了其时文化新人与旧文化斗争的平均水平,是值得珍 视的。二是吴虞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批判,虽然打上了时代烙印,是“匆忙的”,但却是 极其严肃认真的;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时,也是找到了前进的大方向的,即走出 中世纪,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轨道。他说:“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 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今译笛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 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 万事,惟此为大已吁!”(注: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7、 176、171、98、167页。)这也是五四文化新人在抨击中国旧文化时运用西方民主主义文 化作为参照系的共同认识,在那时当然是进步的。
还有论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探寻吴虞非儒反孔的学术渊源,这对于认识吴虞的学 术思想理路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仅仅判定吴虞的学术“内源”,得出“吴虞非儒 反孔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传统文化内部的非正统、反正统思想因素”(注:吴效马:《 论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传统学术渊源》,《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就未免顾 此失彼了。从吴虞对李贽等反判儒家正统思想的高度评价来看,吴虞的确存在非儒反孔 的学术“内源”;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吴虞就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吴虞了。应该说 ,吴虞非儒反孔的学术渊源以“内源”为基础,以“外源”为依据。所谓“外源”,即 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正因为吴虞主要的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装, 他才得以跻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流,并赢得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和“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注:胡适:《胡适文存》卷四,东亚图书馆,1928年,第255 、259页。)的称号和相应的历史地位。
四
鲁迅参加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流中来,比陈独秀、李大钊要晚一些。但鲁迅一加入 到破除中国旧文化思想笼罩的行列,就以他颇有文化特色的杂文和很有吸引力的小说,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揭穿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指出中 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统治者在“仁义道 德”的伪装下,干着嗜血食肉的吃人勾当。他借小说的主人公的口吻说道:“我翻开历 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 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里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注:《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5、432页,第124—125页,第137、 135—136页。)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的批判,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促进了人们对毒害其思想的旧文化的反思。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力地声援了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受这篇小说的影响,吴虞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写下 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论文。吴虞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 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 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 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 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注:吴虞:《吴虞集》四川人 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7、176、171、98、167页。)
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站在民主与科学的角度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有所不同的是,鲁迅 更多地则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向着封建文化猛攻。在《我之节烈观》的文章中,鲁 迅谴责了封建主义“贞节”道德给妇女造成的苦难:“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 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 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因而他呼吁道:“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 都受正当的幸福”(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5、432页 ,第124—125页,第137、135—136页。)。在1925年发表的《寡妇主义》的文章中,鲁 迅继续声讨了强加给中国妇女的落后的道德。如果说《我之节烈观》批判的是封建的夫 权主义,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痛斥了封建的父权主义对于孩童的无情折磨 。他揭露说:“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 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他呼吁:“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 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样,便是父 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注:《鲁迅全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5、432页,第124—125页,第137、135—136页。)这 篇文章的主题,我认为应该是对于上一年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 的深化。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常翻滚在鲁迅心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决不能让旧时代的 伦理道德再毒害甚至吞噬我们的后人。
对于鲁迅的评价,一方面存在着超越层次的无限拔高,一方面又存在着对于鲁迅作品 的“误读”。例如,西方有研究者称,鲁迅“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 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 ”(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479页。)。关于“全盘否定”论在这里姑且不论,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阴暗论 ”没有真实的依据,倒可以得出“希望论”:鲁迅一方面对于以“吃人的礼教”为代表 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坚决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充满希望。鲁迅所进行 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充满希望”的心理活动的表露,前者以后者为基点和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具有民主主义文化觉悟的文化新人,同忧同感,心心相通 ,为了满足社会进步对于新文化的精神需求,他们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 共同的心理基础,结成一个“开风气之先”的进步的文化群体。
收稿日期:2003-01-20
标签:陈独秀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李大钊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国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