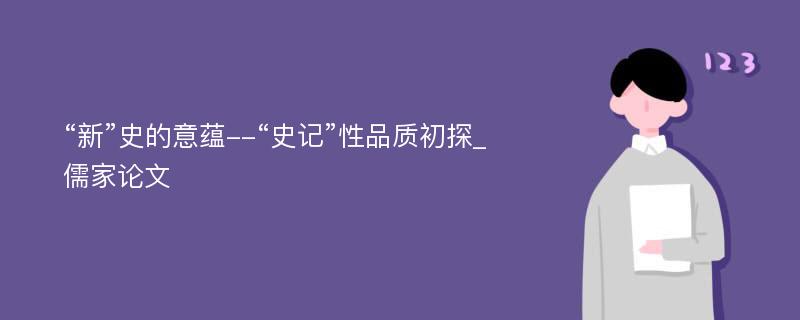
一种“新”史的意蕴——《史記》性質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史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題及略述“史”在知識譜系中之位置
本文以“新”史名篇,“新”之名,對舊而言。所謂舊史,是經學興以前的古史系統,《莊子》裏面曾用“舊法世傳之史”來指稱。① 太史公著《史記》于舊史雖有一定之因襲,卻絕不同于舊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可以成爲“‘新’史”。
今日言經史,我們總會本能地將“經”、“史”對應到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的經和史,這是因爲“四部”分類法是中國歷史上沿用時間最長且最有影響力的一種圖籍分類方法。此法肇端于六朝,其先以甲乙丙丁四部統屬群籍,甲部對應六藝及小學類著作,乙部對應諸子類著作,丙部對應史記類著作,丁部對應詩賦總集類著作。其後,《隋書·經籍志》接受這一方法並將乙、丙兩部對調,于是,便成後世流傳不變的“四部”分類法。
在“四部”分類法之前,最有影響力的便是前文所云劉向、歆父子所發明的“七略”的分類方法。所謂“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数略、方技略。② 在“七略”中,顏師古《漢書注》云“輯略”爲“諸書之總要”,故《漢志》去之,如此則圖籍之分類爲六類而已。“七略”中無後來所謂的“史部”,與之相應的《史記》存于“六藝略”《春秋》類之屬。
目錄學將《七略》作爲其開端,只是就圖籍分類而言。若以知識譜系而言,絕不可以說在《七略》之前没有知識分類。蒙文通先生在“抉”經學之“原”時便點明了代表早期不同知識類型的三類人,即《莊子·天下篇》中所說的“舊法世傳之史”、“搢先生”、“百家”。③ 這種知識分類方法似乎也得到了司馬遷的認可,他曾在《史記》的論贊部份說過: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④
又《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備乎……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史記》文中所說“薦紳先生”即《天下篇》所說的“搢紳先生”。“搢紳先生”多爲“鄒、魯之士”,即儒者,司馬遷曾說過“儒者以六藝爲法”可證。⑤ 從引文可以看出,《五帝本紀》論贊部份只有“儒者”、“百家”,而《天下篇》所云舊史則缺席。可是,若考慮司馬遷本人“太史公”這一“史”的身份,這個問題便不難理解。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的“史”與“舊史”是有所區別的。而恰恰是這一區別的存在,纔讓《史記》一書的性質複雜起來。
二、《史記》是一部子書?
《史記》被歸入史部是發明四部分類法以後的事情,從唐代以後《史記》的這種部居就一直被沿用,直至今日。可是,如前文所述,四部分類法是六朝時開始使用的一種圖籍分類方法,此前在《七略》分類法,《史記》被列入“六藝略”《春秋》類之下。這一時間的間隔和部居的錯位,引起了學者們的充分注意。因此,《史記》的性質問題便被一再提及,而大多數觀點都力圖“糾正”四部分類法對《史記》的誤置,進而突出《史記》“子”書的性質。臺灣學者李紀祥先生曾斷言:
將《史記》還原爲《太史公書》,一如正文所述,《太史公書》是一部“子書”。無論是從史公“成一家之言”的自道,或其稱先秦史官文本時用了“史記”一詞;以及太史令在漢代是一天官屬性,不任“撰史”之司;都可以顯示《太史公書》的家言子書性質。⑥
李先生的結論基于以下事實:第一,司馬遷曾明確表示作《史記》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⑦,則《史記》的性質當爲“家言子書”;第二,司馬遷稱述先秦史官所掌之文本爲“史記”,則其書之性質必有別于是,即非史書性質;第三,太史令在漢朝職掌天官,不司“撰史”,故其書當非史書。案李先生所舉證據,皆是事實。司馬遷稱先秦史官所掌之文本爲“史記”,有文本可證,如“(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⑧、“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其行”⑨ 云云。至于太史令在漢朝不司“撰史”者,司馬遷本人曾自道“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云云。⑩
可是,即使李先生所說的證據皆屬實,仍不可以說《史記》是一部子書。
既然提到“子書”,我們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子書”的確切意涵。就筆者淺見,上文所云“子書”至少可有三種理解:
第一,“百家言”。前文筆者曾提及,蒙文通在《經學抉原》中以敏銳的目光發現《莊子·天下》中區分了三類人:舊史、鄒魯搢紳先生、百家。太史公司馬遷接受了這種分法,所以在《史記》中經常出現“百家”、“薦紳先生”等提法,只是不見舊史。“薦紳先生”便是“以六藝爲法”的儒者,因此“百家言”便是與“六藝”對應的學說。
第二,“諸子學”。劉歆在《七略》裏面區分了“王官學”和“諸子學”,所謂的“王官學”便是“六藝”,“諸子學”乃是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與“六藝略”和“諸子略”並列的還有“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因此,與“諸子學”相對應的乃是包括“六藝略”在內的其他五類。
第三,“子部”。晋荀勖《中經新簿》定四部分類之法爲甲、乙、丙、丁,其中諸子屬于乙部,至《隋書·經籍志》始定經、史、子、集四部之法。因與本文無關,故不贅言。
將《史記》視爲“子書”似乎是將其與“諸子學”對應。可是,如果考慮到前文所提及的“七略”分類法是司馬遷之後的事情,那麼“子書”似乎又可以對應“百家言”。難道“諸子”不就是“百家”麽?顯然不是。這兩個概念若仔細推敲,還是有所區別的,而這個區別顯然不只是時間先後而已。
首先,二者最明顯的區別是,“百家言”中不包括儒家,而“諸子學”則包括儒家。如上文所述,在司馬遷的知識分類中,儒者即“搢紳先生”,是修習“六藝”的人,所謂“儒者以六藝爲法”是也。《七略》首創“諸子略”,其中包括儒家類,詳可參《漢志》。
其次,在《七略》的體系中,與“諸子略”相對應的,最重要的是“六藝略”。《漢志》雖未明言“六藝”爲“王官學”,但卻暗示了二者之間的關係。在《漢志》中,明言諸子皆出自王官,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然又云“今异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則《六經》與王官之間的關係不難推定。六經爲王官學,在後世基本上可謂定論,這一觀點在章學誠“六經皆史”這一表述中達到極致,其根源則在于劉歆之《七略》。可是,從種種迹象上來看,司馬遷並不接受“六藝”爲“王官學”這一觀念。如果說非要在司馬遷所理解的知識類型中塞進“王官學”這一概念,那麽它可以指稱古史官所掌之“史記”。在《太史公自序》中有“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的說法,《索隱》云“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六藝”有別于“史記”,且司馬遷作《史記》曾自比孔子作《春秋》,又作《史記》爲“成一家之言”,則“六藝”非王官學無疑。
所以,《史記》顯然不是一部“子書”。即使退一步說,將“諸子學”替换爲“百家言”,那麽《史記》亦不是“百家言”。在司馬遷本人看來,著《史記》所效法的是孔子作《春秋》,如此一來,《史記》便似乎有了“六藝”的性質而成了一部經書。當然,《史記》到底是不是一部經書,這還要看司馬遷本人的看法。
三、司馬遷之“志”
從司馬遷本人的表述來看,他將自己著《史記》比作孔子作《春秋》之傾向非常明顯。在《太史公自序》中便有: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居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于是卒述陶唐以來,卒子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三段引文皆提到《春秋》,第一段引文更有“足于麟止”之說,按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于此,猶《春秋》終于獲麟然也”(11),《春秋》獲麟絕筆,司馬遷亦卒于武帝“獲麟”,其意圖昭然若揭。亦無怪乎上大夫壺遂將其比作孔子作《春秋》,並刁難云: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職守,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明何?(12)
這句話隱含著將司馬遷作《史記》等同于孔子作《春秋》這一前提。壺遂的刁難可謂尖銳,如果《史記》與《春秋》具有同樣的性質,就意味著司馬遷必須承認當世爲亂世。司馬遷顯然不願意犯如此低級的“政治錯誤”,故反駁云“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所以“君比之于作《春秋》,謬矣”。如此一來,司馬遷本人似乎又反對將《史記》與《春秋》相提並論。可是,孔子作《春秋》于“所見世”尚且“微其辭”,司馬遷此辯解爲什麽就不可能是爲了避免“政治錯誤”的一種權宜性的修辭呢?
所以,要弄清楚《史記》和《春秋》的關係,還需要清楚司馬遷本人的意圖。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最後一篇爲《自序》,是本書之序言,明確寫作之緣起,提示全書之內容。在《太史公自序》開篇,司馬遷叙述了自家的族譜,一般說來,顯親揚名乃是孝之大者,這本不足論。可是,若仔細玩習司馬遷的筆法,卻能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按《自序》開篇云: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晋……自司馬氏去周適晋,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錯……錯孫靳……靳孫昌……昌生無澤……無澤生喜……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司馬貞《索隱》云:
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13)
從司馬遷所述譜系來看,其先出自“程伯休甫”是毫無疑問的。可是,“程伯休甫”到底是重之後還是黎之後?司馬遷混而言之在“重黎世序天地”之後,似“程伯休甫”爲重、黎之後。且不說司馬貞所云重、黎“二氏二正,所出各別”(14),即爲昆仲,亦各有所出,不當混而言之。裴氏《集解》引應劭之說,以“程伯休甫”爲“封爲程國伯,字休甫”,則“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必是奪爵廢國而非指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守”,因爲文中明確表明“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蓋程國被廢後,程國之後流爲司馬氏而“世典周史”。可是,“程伯休甫”到底是誰之後?據司馬談臨終前與司馬遷所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15)。
文中所說“余先周室之太史”照應前文“司馬氏世典周史”,此爲“程伯休甫”之後。又文中云“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則可斷定“程伯休甫”爲南正重之後無疑。所以,司馬談纔“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黄子”,其中“天官”、“《易》”、“道論”皆屬于廣義的“天官”事。司馬貞《索隱》云司馬彪、干寶以爲司馬氏是“黎之後”,蓋誤以爲司馬談不滿足于掌天官而欲著史續“祖”之祖爲司地的北正黎,其實司馬談所云“續吾祖”之“祖”乃是“世典周史”的司馬氏。
司馬遷在文法上混言“重黎”,乃是不願意區分“司天”與“司地”兩種職能。“司地”範圍甚廣,要言之便是“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之“治民”。明于此,纔能理解司馬遷對《春秋》之態度,也纔有可能理解司馬遷本人對《史記》性質之定位。
司馬談修習“天官”、“《易》”、“道論”等“天”學後,爲漢太史令,掌天官卻“不治民”。司馬氏曾世典周史,而周太史所掌“建邦之六典”(16) 皆是治民之用。所以,令司馬談至死仍耿耿于懷的便是他一生只“司天”而未“司地”。當然,這裏所說的司馬談所企望的“司地”並非真的是親身輔弼君主治理民衆,而只是修史,所以囑咐其子司馬遷“無忘吾所欲論著”,因爲史所記載的主要對象便是與天道相對應的人事。司馬遷也確實繼承了乃父這一遺志,同時更因襲了司馬談糾合天道和人事這一思想,所謂“究天人之際”是也。
司馬遷爲何如此推崇孔子作《春秋》?他如何定位《春秋》?
壺遂在質問司馬遷爲何在治世著《史記》時,曾先試探性地提問道“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司馬遷在回答這一提問時,曾對《春秋》的性質作了如下表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17)
《春秋》“長于治人”,這是司馬遷理解《春秋》性質一個絕佳的表述。(18) 所謂“治人”之“人”並非特指某一階層,而是可以泛指包括君臣等身處高位的所有人。其不言“治民”者乃是因爲“民”則嫌不包括身處高位之人,後文有“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可證。所以,“治人”也即是“掌天官,不治民”之“治民”。所以,在司馬遷看來,《春秋》首先是一部“治民”之書,其所以推崇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孔子爲“不治民”的史官提供了一個可资效法的榜樣。
如此說來,《史記》便是一部具有“治人”性質的書。問題是,《史記》是不是一部與《春秋》一樣純粹以“治人”爲目的而作的書?這便需要回到本節開始時討論的問題——司馬遷叙述家族譜系有意重、黎並提,用意何在?
前文曾提及,在《五帝本紀》論贊中,司馬遷提到了兩類人——百家和薦紳先生,和《天下篇》相比,“舊史”是缺席的。當然,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論說者司馬遷本人的史官身份——“掌天官,不治民”。也就是說,“掌天官”這一身份對于司馬遷來說是預設的,是理解司馬遷著《史記》這一行爲的前提。事實上,司馬遷推崇“治民”,卻並不反對知“天”。《史記》“八書”中有《天官書》,專門記述天道運行之事。其本人亦通曉變占之法,曾自云“太史公推古天變”云云。(19) 在《天官書》中,司馬遷有云:
夫天運,三十歲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相續。
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此兩段文字結合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則可知:就司馬遷本人的意圖來說,《史記》一書之性質絕非只是“治民”可以涵括。司馬遷說自己“欲以究天人之際”也並非誇大之詞。
總言之,《史記》和《春秋》並不是兩部性質完全相同的書。如果說,《春秋》是一部“治民”(政治)的經典,那麽《史記》則又有知“天”(哲學)這一維度,至少司馬遷本人的初衷是這樣的。
四、三種知識類型與《史記》的性質
讓我們再回到《莊子·天下篇》,來看一下文中關于三類人的劃分以及與此劃分相關的諸問題。按《天下》云: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蒙文通先生對此文曾作過如下解讀:
周季之學,類別有三:舊史爲一系,魯人六藝爲一系,諸子百家爲一系。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孔子語宰予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此皆古代史籍之可考見者也。《呂氏春秋》說:“太史令终古出其圖法乃奔如商,殷內史向贄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是三代迭興、圖史不墜。史公謂:“諸侯相兼,史記放絕,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則列國又各有舊法世傳之史,至秦而夷滅蛊矣。(20)
《天下篇》所說的“舊法世傳之史”既爲“舊法”且“世傳”,則爲古史之遺響無疑。這一類人雖生活于“道術將爲天下裂”的周季,但在他們身上仍然保留著古史官之遺蕴。按蒙文通先生之說,這類“舊法世傳之史”即是掌列國史記之史官。文中所說的“鄒魯之士、搢紳先生”顯然是不同于“舊法世傳之史”的另一類人,他們是能“明”《詩》、《書》、《禮》、《樂》、《易》、《春秋》的一類人。按古史掌邦國之墳典,《詩》、《書》、《禮》、《樂》亦在其列,此處將“明”《詩》、《書》、《禮》、《樂》之人說成是“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必是經孔子删削之後的“六經”,而非章實齋所說的“六經皆史”意義上的古代先王政典。至于文中所說的百家,更是發生于周季禮崩樂壞之時。所以,蒙文通先生所說“舊史”、“六藝”、“百家”爲“周季之學”洵爲不易之論。既然經孔子手訂的《六經》和百家之學皆爲晚起之學,那麽此前的知識類型就只有舊史一種無疑。按照章學誠的說法,周季之學的興起源于官師分離(21),此前學皆隸屬于學官,則史爲唯一的知識類型。要而言之,“舊法世傳之史”、“鄒魯之士、搢紳先生”、“百家”這三類人所代表的是三種不同的知識類型。
《天下篇》緊接著這三種區分,便開始叙述知識類型轉變的歷史情境。按其文云: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壁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知識類型的分化源于知識整體性的喪失。同樣,之所以會出現“百家眾技”是因爲“道德不一”。與此相應的歷史情境便是“天下大亂,聖賢不明”。事實上,很難說知識的分化是因爲“天下大亂”還是“天下大亂”是因爲知識的分化,又或者這二者本身就是一體之兩面,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所以,可以說從古史到“舊法世傳之史”、“六藝”、“百家”的轉變,揭示出來的是生存境域的轉變,轉變的結果在這裏被稱爲“天下大亂”,但更多的時候是被稱爲“禮崩樂壞”。
到司馬遷生活的時代,這三種知識類型依然是構成整體知識形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所以,在《史記》中,我們也會經常看到“薦紳先生”(“儒者”)、“百家”、“史記”等提法。所以,如果我們要追問《史記》一書的性質,除上文從“天/人”這一角度切入之外,還必須弄清楚《史記》與當時三種既有的知識類型的關係。
首先,《史記》與“史記”的關係。按上文所引蒙文通先生的說法,列國之史記便是“舊法世傳之史”。司馬遷父子任太史令,雖“掌天官,不治民”,但仍有機會見到中祕所藏之圖籍簿册,即《自序》所說的“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太史公司馬談臨終前曾以“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22) 爲憾,所謂“史文”即列國之“史記”,列國之“史記”經“論載”而後可成《史記》。司馬遷在叙述孔子作《春秋》的過程時曾有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23)
在司馬遷看來,“史記”和“舊聞”是孔子作《春秋》的素材,孔子同樣是“論”列國之“史記”而成《春秋》。所以,《史記》與“史記”之關係便可等同于《春秋》與“史記舊聞”之關係。
其次,《史記》與“六藝”的關係。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對“六藝”和“六經”的使用,有著微妙的差异。相較之下,司馬遷更喜歡用“六藝”一詞。仔細對比《史記》中“六藝”和“六經”用法的,不難發現:在司馬遷的文法習慣中,“六經”更多指文本意義上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典;“六藝”則更多是指教育方式,且“六藝”所包含的內容更加廣泛,不只是六部經典文本而已,還包括其他與經相關的傳、說、記等輔經而行的文本。(24) 在《五帝本紀》中,司馬遷次序黄帝等五位帝王,其論贊部份有云: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
這裏的“薦紳先生”顯然就是“儒者或不傳”之“儒者”。傳經學的“薦紳先生”難言五帝,是因爲他們不相信《大戴禮》,而《尚書》之記載自堯始而無黄帝之記載,故而黄帝的問題就很難在既有的經學系統中得到解决。所以,既有的經學系統並不是一個絕對完備的知識形態,比如上文因爲“《書》缺有間”,所以要瞭解黄帝之事迹就不得不時時參考“他說”。這個“他說”可能包括《國語》、《左傳》、《大戴禮》等非“正統”六藝文獻,也可能包括百家,甚至可能“遺聞”。這種以“他說”補充“六藝”之說的方式,被司馬遷本人稱爲“拾遺補藝”。總而言之,在三種知識類型中,《史記》與六藝之間有著最爲深刻的關聯,無論在事實層面還是在價值層面。可是,“六藝”作爲三種知識類型中的一種,就注定了其知識系統的不完備性,因爲總是存在著與其性質不同的知識以及對相同對象的不同表述。于是,《史記》便有了“補藝”的可能。
第三,《史記》與“百家”之關係。如上文所引,司馬遷次序五帝,因“六藝”所載闕如,所以不得不藉助“他說”。可是,“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所以司馬遷要“整齊百家雜語”。
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總結《史記》與三種知識類型之間的關係並歸結如下:司馬遷著《史記》融合三種知識類型而構成一種可以被接受的統一的知識形態,用司馬遷本人的話說便是因“史記舊聞”、“厥協六經异傳,整齊百家雜語”。
總而言之,從性質上說,《史記》仍然是一部史書,這是由其作者的身份——史官——决定的。但是,《史記》“史”的性質與列國“史記”則有所區別,因爲司馬遷有意識的將幾種不同的知識類型整合爲一種統一的知識,來紹述傳統古史。
五、餘論
第一,司馬遷之後不久,劉歆整理秘藏圖籍並分門別類,將《史記》列入“六藝略”《春秋》類下。這種分類方法,既混淆了《史記》和“六藝”之間的界限,也混淆了《史記》和“史記”之間的界限,更混淆了“六藝”和“史記”之間的界限而一並歸爲“王官學”。這樣一來,司馬遷著《史記》的意圖以及當時的不同知識類型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晦暗難明。
第二,從種種迹象上看,司馬遷並不認爲“六藝”(“六經”)各個文本之間存在著一個相同的本質的規定。他對“六藝”的本質和同一性的認識完全是基于“六藝”的現實功能——教育方式。可是,《史記》對統一的知識形態之追求本身,卻極有可能對我們理解經學之本質有所啟發。
第三,借鑒司馬遷理解“六藝”的方式,或許對我們理解“六經”有相當的積極意義。
注释:
①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67頁。
②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701~1784頁。
③ 蒙文通:《經學抉原》,《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第50頁。
④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6頁。
⑤ 同上,第3290頁。
⑥ 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入“史”考》,載《文史哲》2008年第2期。
⑦ 《史記》,第3319頁。
⑧ 同上,第509頁。
⑨ 同上,第1350頁
⑩ 同上,第3293頁。
(11) 《史記》,第3301頁。
(12) 同上,第3299頁。
(13) 《史記》,第3285頁。
(14) 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有“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以及“顓頊氏有子曰犁”之說法。
(15) 《史記》,第3295頁。
(16) 《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92頁。
(17) 《史記》,第3297頁。
(18) 《春秋繁露·玉杯》有“《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參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6頁。
(19) 《史記》,第1344頁。
(20) 蒙文通:《經學抉原》,《經史抉原》,第50頁。
(21)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4頁。
(22) 《史記》,第3295頁。
(23) 同上,第509頁。
(24) 詳可參筆者博士論文《經史之間的〈春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