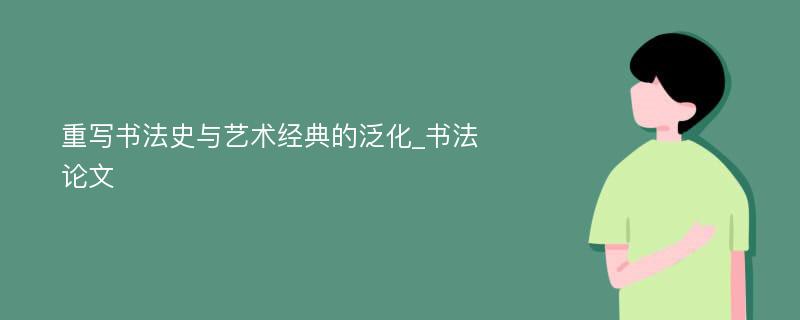
“重写书法史”与艺术经典的泛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写论文,书法论文,艺术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典的范围和价值内核如何确定,既关乎艺术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也关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品格的形成与升降,对此不可不审慎。经典问题在近些年成为书法界争论的话题,主要是因为书法经典的标准和界限的泛化乃至消失,传统经典——以“二王”书风为中心的帖学传统的绝对中心地位在逐步衰落,变成多元书风中的一元;书法的界限不断延伸,除了清代碑学思潮所强调的六朝碑版、墓志造像,随着20世纪的考古大发现,殷商甲骨文、秦汉简牍帛书、吉金文字、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等等,甚至被以往书法史所“遗忘”的“前人的一切文字遗存”,都成为当代书法取法和研究的对象,其中有不少书迹还被作为“经典法书”编入中国书法全集,纳入到不断重写的书法史中。
经典法书是理解“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关键,经典的泛化必然导致书法艺术界定的困难,带来书法取法、审美取向和评价机制的全面变革和调整。传统经典的衰落和新的经典的确立,不仅仅涉及书法内部的审美趣味、艺术观念和文化价值的转变与调整,也折射出整个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价值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建,所以,书法经典的泛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
一、经典的泛化与“艺术史的危机”
从清代阮元的“南帖北碑论”开始,碑帖并行的观念打破了帖学独尊的传统,人们逐渐认同“二王之外有书”,在崇尚碑学的风气推动下,北碑的代表书家郑道昭也曾被尊为与王羲之相抗衡的“书圣”。晚清以来,随着甲骨文、竹木简牍、敦煌遗书等的发现,传统书法史的经典标准和写法因新的材料和观念的出现而开始动摇。甲骨文、陶文刻符的发现改写了先秦书法史的神话叙事模式,简牍帛书等的发现改写了两汉书法史石刻书法一枝独秀的格局,敦煌遗书、西域残纸的发现改写了魏晋以后书法史的士大夫精英主导倾向,经典书写和民间应用书写双线并进①。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多书迹出土,改变人们对书法史的印象与理解,甚至对书法史原有的构架和解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重写书法史”似乎变成了不容置疑、与时俱进的学术使命。
在当代“重写书法史”潮流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导性的趋势:打破“经典书法史”,重写“民间书法史”。认为以往的书法史是一个由“二王”、颜柳欧赵等等“帝王将相”、名家大师构成的经典史,在这之前、之外,还有着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由无名氏、贩夫走卒、匠人武夫等“人民群众创造的书法史”。今天,书法已经成为“人人都可参与的”大众艺术,书法史理应是由名家书法与非名家书法、文人书法与素人书法、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共同构成的复线型历史。毫无疑问,书法的取法范围和审美趣味的多样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打破经典书法的垄断,促进书法艺术的多元发展②。但仔细审视,所谓的“多元发展”并非事实,“重写书法史”其实不知不觉变成了单纯的“重写群众书法史”、“重写民间书法史”,这种倾向正在取代传统的经典书法史,成为新的霸权。
材料和观念会限制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如果说早一千年发现甲骨文、简牍书法和西域残纸,那么书法史的写法的确会是另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贵族与庶民、文与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书法史再怎么变,也不会在一千年前就出现“经典书法史”和“民间书法史”的“双线型的书法史”景观。清中期的阮元梳理出来的另一条对抗“二王”传统的“碑派”或“北派”书法传统,也还是一个流传有序的精英团体,而非平民或无名氏的民间群体。所以,“民间书法史”的出现只能是一个现代现象,不可能出现在千年之前,甚至在康有为的时代也没能成为主导。那么,为什么要到20世纪后期才出现这种崇拜民间书法、打倒经典书法的潮流呢?这不是新史料的发现就能解释的,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出现已经超出了书法的范畴,涉及到对整个现代文化格局的理解,尤其是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结构的转变问题。在传统社会精英结构解体、文人书法审美精神衰落、普罗大众主导文化标准的时代,经典书法史的现实支撑已然崩塌。新的民主政治召唤新的审美范式,大众审美意识和市民趣味必然要投射到书法史上,希望在历史中找到表达自我的经验和合法性根据。所以说,书法经典的变迁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结构解体的结果,也是当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边缘文化对传统主流文化消解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书法,当今整个文化领域(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都面临着一个经典的泛化和重新界定的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在艺术界早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辩,还催生了种种“艺术史危机论”和“艺术终结论”。
传统的艺术史主要以各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包括艺术大师和民间巨匠)创造的经典作品为记录对象,恪守着“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藩篱。但是,今天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主流不再仅仅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和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以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大师作品,随着消费主义和信息化图像时代的到来,更多的艺术史家开始关注广告、摄影、电影、电视和各种工艺品、商品包装等等。另一方面,受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各种解构“中心”“霸权”的潮流促使西方的艺术史家不得不将视野拓展到“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遮蔽的范围之外的艺术形式。原始土著的朴拙和自然气息成为修改陈旧、封闭、死气沉沉的贵族艺术史的兴奋剂,大量亚非拉和大洋洲的艺术进入西方艺术史课堂和研究所,艺术成为体现不同阶层、性别和民族的文化身份的象征,艺术史研究领域变成了文化政治较量的战场。总之,就像可以把“前人的一切文字遗存”作为当今书法取法的对象一样,似乎所有的人类创造的“视觉形象”都可以纳入到艺术史研究和记录的范畴。
尤其是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和商业化对文化的无限渗透,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渐消弭,“艺术在生活化”,日常生活被塞满了艺术品格;同时,“生活在艺术化”,从都市景观到个人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被美学包裹起来,装饰无所不在③。虽然人们今天依然承认达·芬奇、拉斐尔作品的经典地位,但它们与15世纪意大利的某件手工艺品、20世纪某超市的食品包装盒可能以同样篇幅被写进艺术史教材。“人人都是艺术家”,也意味着“人人都不是艺术家”;什么都是艺术,也意味着艺术什么都不是。当一切的废物都可以当成艺术品来展示时,也就意味着无论多么高贵的艺术作品都同样可以被当作废物。“如今对视觉艺术家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这种极端的开放性的一个后果是:成为一件艺术品即使它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不再受到可能面临的谴责”④。
当今学界对艺术的定义、艺术品的评价和艺术史学科的发展目标不再有基本的共识。原来这一切都可以将经典作品做标准,但随着这种标准的丧失,艺术史研究者和批评家陷入到一个悖谬的境地,一方面,“如果当代艺术史家不能超越传统审美经验的范畴和对艺术作品的规定,那么他们就会丧失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合法性身份和基本的发言权,同时也面临着被学科自称要分析和研究的对象——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所抛弃的危险”⑤。但另一方面,由于当代艺术史家放弃传统审美经验的范畴和对艺术作品的规定,放弃艺术所应秉持的高雅与低俗、审美与生活的界限,那么,他们同样会丧失关于艺术和文化的发言权,因为当“标准”和“共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有发言权,专家就失去了意义,人人都可标榜为专家。在这种混乱的格局中,商业的逻辑、权力的法则可以更加轻易地渗透到艺术的自治领域。
二、重写艺术史的“政治修辞”
艺术史的重写到底是遵循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历史事实,还是基于现实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需要,这是理解经典泛化问题的合理性的关键所在。
“民间书法”被许多书法家和研究者视为一场书法史上的多元化审美变革,他们强调:民间书法具有经典书法所不具备的诸多审美特征,比如它们没有经典书法那么多的法度要求,能体现出“字中之天”;也不像经典书法那样过度追求完美,而是在“奇肆放逸”的“不规整”中,充满各种“奇思妙想”和耐人寻味的“意趣”;没有经典书法陈陈相因的传承束缚和审美疲劳,往往能给人以无比的新鲜感和刺激,让人惊叹“原来字可以这样写”,体现出自由创造的无拘无束!这些特点看起来非常符合“陌生化”、“审美距离”、“个性化”、“自由创造”等美学规律。
但也有学者认为“民间书法”不是基于历史事实和审美规律,而是基于现实需要而建构出来的,是一种文化政治修辞策略。如果民间书法真的那么富有艺术创造性和审美意味,为什么可以将历史上的那些曾经被边缘化、被鄙弃和遗忘的东西重新奉为宝贝与经典,而不直接将当下同样充满“字中之天”的书迹——如发廊招牌、拆迁告示、工地标语这样随处可见的真正的民间书法作为取法的对象,这样岂不更方便,更自然⑥?果真如此,那么,皓首穷经,“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还有必要吗?一切的刻苦学习和文化修炼意义何在?谁还会崇敬那些经过无数代人锤炼、被历史千淘万漉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和文化创造?虽然“民间书法”提出者说,他们并不否定传统经典的伟大和完美,但人们有权在经典书法和民间书法之间自由选择,这是他们的民主权利!然而,这样的“自由”和“民主”只会鼓动人们去投机取巧,放弃一切高尚的人类抱负,不再为困难的和遥远的目标而奋斗和牺牲,都追求最不费力的东西,并被片刻的欲望所引导,沉溺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赵孟頫说:“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跋定武兰亭》)而今“可鄙”的反倒是赵孟頫了,他哪里见过在今天比比皆是的“朝学执笔,暮入国展,暴得大奖,旋称大师”的现象。
“民间书法”概念是利用审美规律的一种政治修辞,利用人们的“崇古”、“陌生化”等心理来实施变革。这种思路至少可以追溯到康有为。1888年,四度落榜的康有为深感于常规的功名仕途无望,于是改变策略,在京广结名流,希望通过徐桐、翁同龢等权臣得以“民间布衣”身份直接向太后、光绪上书,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上书失败后,在沈曾植的建议下,1889年康有为开始搜集、研究金石碑刻,著成《广艺舟双楫》,极力推崇碑学,甚至说魏碑“虽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将自己的政治变革意图和愤懑情绪寓于其中。1896年康有为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受到进化论的启发,决定模仿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构建“孔子改制创教”的理论系统。翌年,《孔子改制考》完成,倡言六经为孔子“托古改制”所作。按康有为的自述,《孔子改制考》的写作始于1886年,此说虽遭学界质疑,但其“托古改制”思想的萌芽未必晚于此时,这在《广艺舟双楫》中昭然若揭,通过碑学来“托古改制”,打破帖学经典迷信,完成对帖学传统的改革不正是这样的思路。“以古为新”、“言古切今”,康有为在古典、民间与进化之间找到了一条两全之策,其政治智慧虽然未必为今人理解,但其中的逻辑方式却被继承了下来。近代以来,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新的权势崇拜”——西潮崇拜,以西方为标准,以“新”和“现代”为尺度,西方的、新的、现代的就是“好的”、“正确的”、“美的”、“高贵的”,对这种思路的弊病学界已经进行了挞伐。但是人们忽略了另一种崇拜:中国人在不断地数典忘宗、打倒曾经居于中心地位的圣人和经典的同时,开始迷恋和神化“新的”古与经典——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边缘“群众”和“无名者”的古籍、古典。“古”的对象不同了,而“以古为徒”的心似乎并未改变,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古人的各种阴魂被不断召唤乃至“发明”出来,重新以“历史真实”的名义为现实正名,为今人创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仅面临着古老的庸俗,把好的等同于古老的或现实的,还面临着进步的庸俗,把好的等同于新的或未来的”⑦。
“经典书法”首先是一个审美、艺术和文化概念,而“民间书法”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以书写者社会身份来划分书法史是现代民主意识的一种投射,并非如有的学者所称的那样是基于“信史”的观察。被归入民间书法范畴的许多写手都不是所谓的“民间匠人”和平民百姓,相反,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写甲骨文的占人和书写国家重器上的铭文的臣属,都是商周时代掌握文化的最高知识分子。汉魏两晋南北朝为朝廷宗庙书写碑文和为王公贵族书写墓志的也都是最著名的一些文化精英,甚至由皇帝、太子和国家重臣亲自撰制⑧。“民间”这个概念在当代美术和文学研究中也在使用,文学史家陈思和明确地强调了其中的政治色彩,他将“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写作”视为一种反抗国家权力控制、追求自由自在的形式,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形态拥有“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是一种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⑨。书法界在运用这个词时无疑更强调其民主性优点,忽略了其阴暗面。而且,文学界和书法界对“民间”的具体代表的理解也不同。陈思和等是以“民间写作”来批判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民间写作”是指被压抑但又能充分体现个人自由和人性欲望的文字;而“民间书法”恰恰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书法,从郭绍虞、郭沫若、金开诚到当代的民间书法倡导者几乎都是这么界定的⑩。
从经典书法的角度去规定民间书法和从民间书法的角度去规定经典书法,都会简化对方。在民间书法向经典书法发起“边缘”向“中心”挑战的过程中,二者的位置发生了颠倒,这正好验证了福柯的理论:任何一种边缘的设定,都无疑是一个中心再置的过程。经典书法和民间书法一视同仁的观念是对价值高低的取消,以政治的平等来抹煞在艺术和文化价值上的本质差异。现代民主革命在文化上造成了一个极端结果:从“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孔子)的古典模式转向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的现代模式。文化的掌管者、立法者和解释者凭借的不是“智慧”,而是出身和政治身份(阶级、族裔、性别等等)。然而,对于经典来说,其创造者的政治身份不是关键,其本身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三、历史主义的“解经”逻辑
“重写书法史”的诉求体现了现代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这与建立在神话和信仰基础上的古代经典崇拜必然发生冲突。现代思想中的历史主义观念及其阐释学思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经典的态度和理解方式。
经典的发生和古代的“圣人崇拜”传统紧密相关,经典背后的依据是人类对自身群体中的价值高度和人格理想的崇拜(11)。汉代以来的古代中国,一直有着“尊经”、“宗经”的传统,以圣人来确立艺术典范和道统秩序。古代书论就常常从黄帝之史沮诵、仓颉造书的传说开始,言其“存载道德,纪纲万事”的“垂法立制”意义。经典历来被视为是承载了超越时空的普适性价值和万世不变之根本大法,相应地,阐释、传承经典的人也被纳入到一个极其严格的精英统绪之中。古人叙述书法史非常讲究师承、源流和书家的品第座次,即便有的经典之作是民间的无名氏创造的,也往往要附会在名人身上,这就是受古代圣人崇拜传统以及“人书合一”观念影响的结果。
现代人逐渐改变了对经典的神化和迷信态度,经学史家周予同指出,中国的经典“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要认识经典的本来面目,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治史的办法来治经”(12),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人对经典的理解和研究方式。现代启蒙观念认为,要祛除对经典的“迷信”,首先就是要还原经典的“本来面貌”,经典的存在有一个“历史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经典其实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特殊的趣味、偏好和价值观念,后来被权力放大成普适性价值,进而变成统治性的大经大法。经典的塑造逻辑不外乎是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真理性),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权力性)。从宋之陈傅良开始,明之王阳明,清之袁枚、章学诚、龚自珍,民国之章太炎,都主张“六经皆史”,而梁启超则进一步宣布“六经皆史料”,经典的永恒性不断遭到质疑。在章学诚看来,六经不过是三代圣人传“道”之“器”耳,三代之后的“道”,非六经所能尽也(《文史通义·原道中》)!故六经不过是特定时代的思想,不可奉之为颠扑不破之永恒真理,读书人当通今而不泥古。章学诚“所以最重视‘道’正由于他把‘道’看成一种‘活的现在’(living present),而不仅是像多数考证学者一样,把‘道’当做‘古典的过去’(classical past)也”(13)。他通过“尊史抑经”的方式,逐步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这一理论开创了两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一是,对于经典最重要的不是信仰,而是解释,这与西方现代解释学是相通的。如尼采所说,哪里有什么“本质”和“本体”,有的只是“意义”,意义是人附加的,因此,惟一的行为就是解释,人在对经典的“历史化”、“语境化”解释中不断生成意义。这种观念在西方经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进一步发挥,形成了统治当今学界的主体阐释学传统(14)。二是,从“历史真实”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经典。尤其在西方现代科学武装下的新史学的检测下,“圣人崇拜”的经典传统基本上都是“神话”,无信可取。于是,人们逐渐从“信经”转向“疑经”、“释经”。到了后现代主义泛滥的今天,“亵渎经典,解构神圣”已然成为文化造反派的民主宣言,而极端主观化的现代解释学正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
以《兰亭序》为例,从唐太宗开始,其至高无上的经典地位无人敢质疑,“不道《禊帖》不知书”,《兰亭序》是历代书家顶礼膜拜的圣经。但从阮元到今天,围绕《兰亭序》真假的论辩就未曾停息。特别是1965年,由郭沫若发起,高二适、商承祚、徐森玉、启功、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诸多学界、书法界名流参与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空前大讨论,史称“兰亭论辩”。郭沫若将考古发掘的东晋王谢墓志笔法与传世东晋法书特别是《兰亭序》相比较,发现二者相去甚远,指出《兰亭序》的笔法更贴近唐以后的楷法,进而又由书法延伸到文学,认为这篇文章亦是后世依托,所以《兰亭序》完全可能是隋唐人的伪作(15)。其他质疑者也大多从这一思路出发,列举了更多的东晋前后或同时期的墓志、砖文、简牍、残纸、写经等,证明东晋时通行的“民间书法”都含有隶书笔意,与传世《兰亭序》行楷书体不类。虽然近三十年来,许多研究者认为将民间通行书体与代表世族风流的王羲之书法相比较是一个误区,但对《兰亭序》的真实性的质疑仍在继续。“兰亭论辩”的大多数学者从考古学、文献学角度探讨《兰亭序》的真伪问题,还是比较“学术的”,但随着争论的扩大,就有人将问题上纲上线,要通过否定《兰亭序》来揭开“二王”神话的“迷信外衣”,还原王羲之书法作为“粉饰治具”的“本来面目”,进而将整个帖学传统视为只有“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软绵绵的人”所继承的“迷信”传统(16)。所谓“二王”正统论不过是唐太宗“罢黜百家,独尊羲之”的结果,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道统论和极权主义的延续与流毒。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解经”——经典的“解魅”和“解构”过程,印证了周予同的概括,经典在“学术的”处理下,解除了其“宗教的”信仰光环和神秘色彩,被还原成了一个“政治的”谎言。直到今天,质疑《兰亭序》经典地位的主要理由依然被定格在“帝王雅趣和封建文人俯首逢迎”的政治逻辑之上,人们更关心王羲之是怎样被“神化的”、历代的“崇王”观念是怎样被政治绑架的,从艺术、审美和文化价值上去理解“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经典的真正意义的人越来越少。
当今艺术史研究更关心经典作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那些非经典作品,由“意义和思想的基础问题”转向“由博物馆和市场支持的狭窄的专业化”的“学术规范”,培养的研究者多是重知识和数据的“知道分子”与“专家”,而非重鉴赏和修养的“艺术家型学者”。充满激情、想象力和生命情调的艺术世界,被“沉闷的社会科学”带入与美隔绝和远离人生意义的学术加工厂和文化死水,艺术研究者蜕化为机械工人。“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17)。由于非经典的艺术品大多缺乏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突出的审美价值,传统的纯美学和纯艺术研究让位于社会历史批判和权力哲学话语,艺术的审美和教化、净化功能被忽视,研究者不再关心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而是把所有的视觉形式都视为权力的表达和政治符号,艺术研究的目的在于社会批判,在于探寻艺术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话语霸权、性别歧视、阶级压迫等问题。
其实,“治经”和“治史”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经典”存在的基础是“信仰”与“教化”,而历史的基础是“真实”和“认知”。“史之贵实”,因此治史者强调事实判断高于价值判断,求真是最重要的史德;而“经之贵义”,治经者强调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经典存在的合理性不在于真假,而在于通过确立价值典范、树立高贵精神、创造完美艺术来提升人性,促进文明,美善社会。经典首先是一个寄托理想、安顿心灵的空间,吸引人们的不是某个事实,而是经典所承载的对人类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美好情感和崇高精神。将经典历史化、政治化的结果就是消解了经典的存在基础,简化了经典的丰富意义,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去质疑经典,无异于用理性取代信仰,用哲学代替宗教,用真代替善与美,用“现实主义”代替“理想主义”,用“可信者”代替“可爱者”。“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及他们的信徒都坚持认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合理的和现实的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与之相反,黑格尔宣称,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而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18)。经典的信史价值的取消,是否意味着其哲学、政治、道德和美学价值的全无?求真是历史学的美德,但以真来代替美与善则是历史学的霸权!
这种历史主义观念还导致对经典的解释主观化和相对化,使篡改经典、发明经典和利用经典成为合法性行为。人们不再抱有对经典的敬畏之心,甚至自以为高于经典——“我比作者本人理解得更好”;或者把经典的高度降至“我在”的层次——“我只能按我自己的水平来理解你”。以我观六经,六经皆着我色,我有多高,六经就有多高!用这种“读者中心主义”的极端主观化方式去阐释经典,必然矮化经典,难以真正理解经典。人们普遍相信没有“正解”,只有“误读”,没有“本义”,一切都是读者的“附加义”。从晚明开始的那种主观、臆断地理解、临摹经典法书的方式被今人视为“创造性思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王羲之”!但谁能保证你追摹的是王羲之,而不是投射在王羲之法帖上你自己弯曲的倒影?我们确实找不到“正解”,但不意味着没有了“惟一的”正解,就可以随意解读,放弃“更好的”解读。解读必然是多元化的,但那些多元的解读能一视同仁吗?历史上有无数的《论语》注解,可为什么只有何晏、皇侃、朱熹、刘宝楠、康有为、程树德等人的注释最被推重?上帝死了,人们以为“怎么都可以”,可没有“人”能取代上帝的位置;最高法官缺席后的狂欢不等于“自由”,没有了地狱审判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所欲为。
仇兆鳌《杜诗详注》序:“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情乎有余思。”这种回到本义的阐释态度在当代阐释学中已经被视为水中捞月,历史主义告诫我们不可能超越时空,“像作者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其实,“本义”的确不可求,但只有循着追求本义的精神才能尽可能地靠近杜甫,而靠近杜甫就是靠近高度,应该怀着敬畏高度的心情,“小心”地去理解那些伟大的经典,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经典的引导下往高处走,从而使学习经典成为一个修身的过程(19)。千百年来,中国人在那些经典法书中反复临摹,一笔一画,精雕细琢,仿佛在攀登一座座天梯,我们越是持久地接近她们,我们越发感觉到她们的伟大,诚如卡尔维诺所言,是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帮助我们理解了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
对经典的崇拜和信仰并不意味着把自己变成教条下的思想奴隶,不要误以为经典崇拜就是缺乏创造力的表现,是精英主义的诱惑。别忘了,人类的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合奏,而非极权者的独唱,正是人类那些伟大的经典在反复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由,实现创造与超越。对于那些伟大的思想文字和艺术作品,我们少一点自以为是,就会多一点精神的上升空间。
历史永远在重写的过程中,但正是这不断的重写使那些永恒的东西得以沉淀。因此,历史的变迁不会成为改变经典地位和标准的动力与依据,相反是检验经典的最好方式。我们所批判的不是历史学的求真意志,而是对经典历史化的相对主义观念。“经者,要也”,经典是指那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书籍和作品;“经者,常也”,经典所承载的是那些具有普世性的常道、常理、常法。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之名是不能滥用的,因为经典是由人类的圣贤所创,为绝大多数民众所尊信奉行,是全社会通行的常行之道和终极关怀。不同领域所尊奉的经典,不管是哲学、历史、文学还是艺术,虽然各自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但也遵循着经典的这种共性。能称之为“书法经典”的首先是那些被历史确立下来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书,那些法书不仅仅是历代学习书法的人都应取法的“径路”(法度、规范),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中国人关于人生意义、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和审美追求的常理与常道。经典的范围的确在不断地变化,会有新的作品进入经典的家族,它们将和以往的经典一样,继续刻画人类进步的坐标。但不管怎么变化,经典总是“反复灌输着相同的、永恒的人文主义价值。它们使我们想起相同的、人类经验的永恒特征”(20)。经典作品具有持久的魅力和永恒的审美意味,而不是短暂的新奇和刺激。相信经典,其实就是相信人类还有一些不可逾越、不可随便践踏的基础、共识和规范。
注释:
①陈振濂:《近代三大发现对书法新史观建立的积极影响》,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②沃兴华:《书法问题》,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④阿瑟·C.丹托:《美的滥用——美学与艺术的概念》,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⑤常宁生:《扩展的视野——西方当代艺术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转变》,见《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⑩白谦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页,第107—114页。
⑦(18)Leo Strauss,"What can We Learn from Political Theory?",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69,Iss.04,University of Notre Dame,2007,pp.520-522,p.527.
⑧华人德:《评帖学与碑学》,见《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
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
(11)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见陈壁生编《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5—56页。
(14)王晴佳:《章学诚之史观与现代解释学》,见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载《文物》1965年第6期。
(16)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载《文物》1965年第10期。
(17)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页。
(19)刘小枫:《“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载《读书》2005年第11期。
(20)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标签:书法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作品书法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兰亭集序论文; 信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