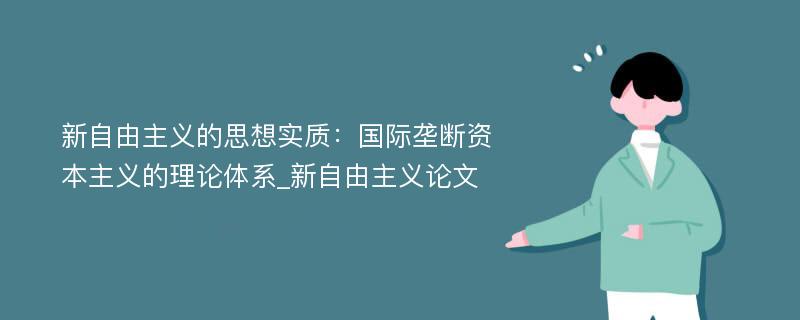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本质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的。这是一次以信息革命为主要技术特征,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控力量的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主控的这次全球化运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即这种模式既要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又要能够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接受。后冷战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迫切需要,而国际垄断资本正是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向他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这一模式。而从推行的结果看,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后台的美国却再次强化了世界霸权。
一、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衍生物
第一,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对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现象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列宁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自由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①他还进一步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②可见资本输出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也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③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资本输出的这种剥削性质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并且形成了新的世界剥削模式。
第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垄断资本要越过国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谋取高额利润。为了迅速达到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事实上,面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怎么可能和它们“平等”竞争呢?这种“平等竞争”无异于小鸡与老虎的竞争。但作为“老虎”的国际垄断集团非常欢迎这种理论,大肆吹捧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鼓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将这种不平等竞争比作是,“相当于组织一场足球比赛——举这个例子是谈一个很多人都了解的运动——由奥林匹克冠军对一个幼儿园队,但规则相同”,而事实上,“不应用相同的规则进行这场比赛。”④
第三,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金融自由化不断地转嫁自身的问题和危机。其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欠发达国家没有完善的金融风险规避机制和监管体制,加上自身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面推行,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比如,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金融危机往往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而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发展中国家“过于迅速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⑤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惟一最重要的原因。
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⑥这种资本的投机本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坦泽尔所言,“重要的是要揭露当今全球化的动力和为此服务的资本的绝对统治,它力图对付停滞和经济危机,造成少数富人暴发到空前的程度而多数人一贫如洗。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奴仆,根本的出路不在于改革甚或撤销它们。我们所要的是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全面彻底的改造,以人的优先取代资本优先。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看到所需要的全球金融机构。”⑦由此看出,国际垄断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入资本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出发的。
二、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教条到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
新自由主义最初是学术领域内的一种学说、思想,一种改革方案,逐渐嬗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征服世界的一种右翼意识形态,这种演变与经济全球化的勃兴紧密关联。由于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经济理论,又是一种政治立场,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单纯从经济学的向度是很难吃透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的。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层面上首先是一种经济学教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和40年代,它主要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主张,要求给予个人以尽可能大的经济活动自由,实际上是要实行最大限度的私营企业制度。这套理论“重构致力于转换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斥责通过政府开支和税收来调节商业周期的波动的方法;认为应当在国内外市场上放松乃至取消政府对公司行为的调控;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要求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项目。这种重构被称为新自由主义。”⑧从这些具体的政策主张来看,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典型的19世纪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
20世纪上半叶,苏联社会主义与美国的长期对峙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采取国家管制主义的模式。这种两级的对抗加剧了资本家阶级的恐惧,他们害怕本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心理上要对工人阶级表现出缓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在政策上要对福利国家的作用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肯定。因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和忽视平等的主张在经济政策层面受到理论界的反对,在意识形态上也备受冷落。1947年哈耶克在第一次“朝圣山学社”大会的致辞中说:“如果那些我认为把我们团结起来的理想——就那些理想的名称而言,尽管自由这个概念已为人们过分滥用,但它仍然要比其他术语更妥切——要有任何复兴机会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着手进行一项巨大的知识工作。这项工作关涉到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要把某些在历史时间的过程中添附在传统自由理论上的观念从这种理论中清除出去;二是要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问题。”⑨可见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时代”并未偃旗息鼓,而是仍然对其理论进行不屈不挠的捍卫,使之系统化的自我修炼时期。
第二,凯恩斯主义遭遇困境,新自由主义便由“异端”变为“正统”。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长期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造成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无法回天,“这意味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维持阶级调和的体制——追求充分就业、提供社会福利措施——而不得不急转弯。弗里德曼为这种新动向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谴责政府干预引起了危机并坚决主张回归到30年代起受到强烈质疑的‘自由市场’原则。于是弗里德曼的‘古怪’理论便成为正统,而凯恩斯主义则成为异端。”⑩为了应对英美经济出现的衰退,新自由主义以“里根—撒切尔主义”面相首先在英美取得一定的成功。这使新自由主义由一种经济学教条转变为一种政策主张。英国撒切尔夫人发起的私有化运动和里根政府推行的“反通胀、反赤字”政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一种经济理论上升为具体的政策实践。
新自由主义的勃兴,推动了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反滞胀”的改革浪潮。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等等。里根、撒切尔的改革体现了经济发展中最迫切、最急需的效率取向和动力要求,激活了一度衰微的发展动力,将国家经济从长期低迷的周期上拉了回来,起到广泛的示范效应,成为9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源头。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这次成功变革,帮助发达国家走出了困境,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入了新一轮以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新的历程。
第三,后冷战时期,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暂时“空场”,新自由主义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填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在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大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渗透,严重侵蚀着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主权安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消了原有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在价值观念上向“西化”靠近。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转入低潮,西方意识形态领域认为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这时新自由主义不但成为一种标准的转型模式,而且成为巩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成果的重要手段,因而得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极力推崇和吹捧,具有一种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色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极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和谋求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华盛顿共识”的引导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助推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导向开始了新一轮改革。而此时“华盛顿共识”的出台并迅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发达国家经过80年代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信息技术进步,这些国家的大公司要求摆脱国内市场的束缚和开拓国际市场。同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扩张也为资本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条件。虽然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巨大的优势,但它们仍然感到在资本流动、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限制,要求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以获取一个更加宽松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华盛顿共识”正全面体现了这种要求。其次,90年代初期恰逢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社会主义的挫折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暂时“空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上经济繁荣之路,而新自由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空场”。最后,不论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官员,还是进行改革的政治家而言,“华盛顿共识”都是一个清晰、简单的政策导向,便于理解和实施。
三、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总是与一定的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总和称为是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统治阶级“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点之一在于:前者鲜明地宣布了自己的代表对象和不代表的对象,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诉求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真正能抗衡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崭新的意识形态,为广大劳动者争取自身合法利益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两极分化的社会现状的深刻揭露和反思的结晶,另一方面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合理成分的扬弃。二者的结合,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和权利,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描述了大量工人阶级受到残酷剥削的事实,“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观,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12)他同时还披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许多女工、童工的悲惨状况,“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开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些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性堕落。”(13)童工也是一样,“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4)
马克思曾指出,“只要阶级的统治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着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5)换言之,意识形态只有在消灭了自然分工,消灭了阶级统治的前提下才能走向灭亡。所以,只要世界上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制度间意识形态的纷争依然存在。目前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散布“意识形态终结”、“淡化意识形态”等论调来迷惑人们;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借助全球化的旗号作掩护加快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速度,以达到称霸全球和主控世界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两面性有足够的认知。
第二,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资本和富人的利益,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16)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产物,是资本和富人的代言人。美国学者塔布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并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更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实现资本的阶级意图方面,却是成功的。它们那些未加宣布的目标,诸如在提高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家和地方上层部门的支配能力方面却增强了。”(17)可见,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都是以更多更贫困的穷人为代价,制造出财富更多更集中的富人。
第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潜藏性。新自由主义视国家为万恶之源,主张弱化国家功能,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弱化,而是仍在对经济进行干预。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万能”为神话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用意是把有关主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国家丧失组织社会的能力。只有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扫荡干净,这些国家的资源才有可能被他们所利用,服务于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认真而虔诚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意识形态本质就掩藏在科学性和价值中立性之下,往往不易引起重视甚至被忽视。其实,每一种新的经济学说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意识形态的助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决策行为联系密切,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斯蒂格利茨曾这样写道,“我相信,以非感性的方式观察和思考问题,在进行有关何者为最佳行动路径的决策之前,抛开意识形态并审慎地对待证据是非常重要的。”(18)可见,对于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说,抛开意识形态的纷扰,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理性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无情的现实却把斯蒂格利茨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当我在华盛顿任职期间,包括我在世界银行的任职,我看到诸多决策经常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得以形成。其结果是,很多方向错误的行动方案得以实施,这些行动方案并没有解决面临的问题,但是符合大权在握者的兴趣或信仰。”(19)斯蒂格利茨通过自己在独特位置上所察觉到的事实说明,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研究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这说明,经济学不完全是实证的,不都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它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新自由主义,必须对其意识形态性保持高度警觉。
注释:
①②③《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6、377、378页。
④[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王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⑤[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页。
⑦[美]迈克尔·坦泽尔:《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见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⑧[美]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王泰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8期。
⑨[英]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4-555页。
⑩[澳]尼克·比姆斯:《弗里德曼:使社会倒退的“自由市场”设计师》,李春兰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
(1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1页。
(12)(13)(14)《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6、287、28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17)[美]威廉·K.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18)(19)[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17、17-18页。
标签:新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