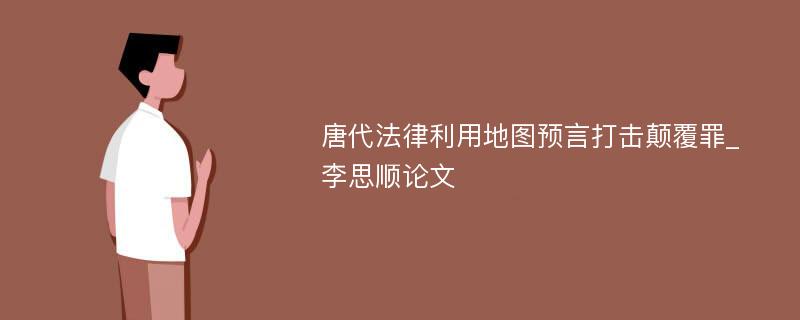
《唐律》对利用图谶进行颠覆犯罪的打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835(2005)03-0063-05
一 关于图谶
图谶,包括谶谣、谶言等形式,是利用中国汉字的同音、部首、拆分等方法,预言社会重大事件的文字、图形等,是一种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许慎《说文解字》言:“谶者,验也”,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暗示[1]。“谶”,也被称为“符谶”、“符命”,是指能够预测来事的神秘图记和文字符号,其有图有字者,称为“图谶”。图谶大多都失传,有的也仅存其文字。我们现在所说的“谶”,主要指的文字谶。明郭孔太《书传正误》对谶谣的解释是:“谣中杂谶,天监志公诗谶、陆法和书谶,谶而杂于谣也”,也就是说谶语、童谣、诗谶、诗妖、书谶等均属谶的范畴。
谶谣之根源源自人们缺乏了解世界的知识和能力,无法解决解释社会和自然现象,以为人间的一切吉凶祸福乃至朝代变更都体现了神的旨意,都是出于不可违抗和改变的神的安排。人们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知心理,用唯心主义的方式解释外部世界,猜测、揣摩神的意志,寻踪神的意志体现的迹象,特别是在灾害频繁、社会矛盾激化的特殊时期,人们更加渴望能够推断未来,于是神秘莫测、生涩难懂、言之不明、甚至不知所云的种种谶谣、谶言就以一种神秘、怪诞、虚幻的神密面目出现了。谶言从其发展来看,先秦的预言、占卜是后来谶纬的早期起源,但二者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即先秦预言、占卜,比较直白而有缺少理论的支持,即使用阴阳卦象进行预言的解释时,也仅限于对卦辞、爻辞、卦象、爻象本身的解释。而汉代以后的谶纬是在阴阳五行学、天人感应学等—定理论基础上的、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框架,其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论说起了主要作用(注: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君权神授论的天人感应理论,实质上就是宣扬汉王朝的君权是决定于天的意志,他以为通过观察日月星辰、风雨变化乃至各种动物的活动都是预测人间事事的兴衰,乃至社会变更、改朝换代的征兆。其在《天人三策》有这样的对白:“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盏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大字本.中华书局.1975年9月版))。
图谶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往往造成人心浮动,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是一种严重威胁封建王朝统治稳定的言论和信息。因此自汉末开始,官方对利用图谶进行威胁封建统治的打击可谓不遗余力,但在唐代之前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和法典化(注:唐代之前各封建王朝的法律条文现已无法可考,据程树德先生《九朝律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等考证隋唐之前尚无专对图谶犯罪之特别法律条款。)。《唐律》不仅将此类犯罪归入法典,而且就立法水平来说,《唐律》相应规定及处罚的内容和精神无疑是代表了中国封建法律的最高水平,现结合具体案例将《唐律》相关条款作一简单分析。
二 《唐律》对图谶犯罪的打击
《唐律》将利用图谶、散布不良言论的行为作为一种最严重的犯罪归人“十恶”之第一条,即“谋反大逆”。
“十恶”是指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十种最严重的行为,是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即是最不能饶恕的严重犯罪,同时也是处罚极为严厉的一种犯罪行为,大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注所谓“乃立十恶,以惩叛逆、禁淫乱、沮不孝、威不道。皆斯义也”[2]。其中谋反行为排在第一位。
谋反,就是指“谋危社稷”[2]。社“为五土之神”,稷“为田正”,“社稷”在这里即是指皇帝所代表的统治秩序,也指皇帝本人的安全。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十种犯罪行为之首,谋反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人实施或阴谋实施针对皇帝本人和以皇帝为首的统治秩序造成危害的行为。该条款将所有可能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不论是预谋还是现行,包括言论)都囊括其中,对其统治不利的图谶犯罪当然不会例外。
(1)《唐律》对利用图谶进行颠覆活动的行为的处罚规定。《唐律》第248条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该条款并非针对图谶犯,若被定性为谋反,就如上条规定进行处罚,在实际案例中,事涉图谶案件也往往都会被定性为谋反,详见篇后案例分析。
首先,对犯有谋反及大逆罪行的罪犯本人,处罚是适用《唐律》中规定的最高刑罚——斩首刑;直系亲属中年龄十六岁以上的男性父子亲属,处以《唐律》中次一级死刑——绞刑。
其次,直系亲属中年龄十五岁以下的男性父子亲属,以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孙、兄弟、姊妹等近亲属都被罚做为官奴,那将意味着从法律上不再被认为是有行为权利的“人”,而是“视同畜产”,即和牲畜一样,从而失去了“人”所享受的权利。血缘关系较远一些的伯叔父、兄弟之子,不论是否在一起居住,都被处以流放三千里的处罚。
除了对犯罪人及家属严厉刑事处罚以外,还会对犯罪人处以财产刑,其家产,包括奴婢、部曲、资财、田宅都会被并没官。
(2)《唐律》对图谶犯罪专有条款,按情节和危害程度不同,在立法中做了区别,比如作为虽然有利用图谶犯罪的言论,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行为,虽然也按谋反处罚,但处罚力度要较真正谋反罪行轻。
《唐律》第6条疏曰:“若自述休征,言身有善应;或假托灵异,妄称兵马;或虚论反状,妄说反由:如此传惑众人,而无真状可验者,自从袄法,谓一身合绞,妻子不合缘坐。”
这里列举了五种具体的犯罪表现,有此五种犯罪表现,而又没有实质性的犯罪行为的,虽然没有具体实施谋反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但在处罚上,由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相对处罚要轻,仅对犯罪者本人处以次一级死刑-绞刑,亲属不连坐,财产也不被没官。但都要以谋反大逆论处。也就是说只要利用图谶、谶谣等方法散布了对当朝不利的信息、言论,都以造反谋逆论。
另外《唐律》中对制造、传播、持有“妖书、妖言”也区别了几种不同情况,分别处以不同的处罚。
首先,对制造不利于当朝统治者书籍、言论的犯罪人,不论具体犯罪行为危害如何,都处以次一级死刑——绞刑。
《唐律》第268条规定:“诸造袄书袄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於不顾者。”“休”,是指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徵(即吉兆),当有天下等等(注: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说的“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咎”,指“妄言国家有咎恶”,在这里是指捏造、议论、传播当朝统治者已经或者是即将出现衰败、失道、灾异等等的言论,从而造成人心浮动乃至社会动荡的行为(注:同上董氏所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遗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对危害程度的判断是依照言论传播范围确定的。“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4],其疏曰:传用以惑众者,谓非自造,传用袄言、袄书,以惑三人以上,亦得绞罪。意即如果向三个人以上传播,即“满众”,其罪与制造妖言相同,就要被处以绞刑,不满三人的予以流放三千里的处罚。
可见,传播“妖言”范围大小不同,决定了处罚程度。如果达到了“惑众”程度,罪同制造者,处以绞刑;达不到“惑众”程度,即减死一等,流放三千里。这里不包括同在一起居住的亲属。因为中国古代多是大家族聚居,如果将同居的亲属也包括在传播范围内,那么将大大扩大打击范围,反而会造成社会动荡(注:见《唐律》第268条疏云:若是同居,不入众人之限;此外一人以上,虽不满众,合流三千里。)。
对于并非意欲动摇其封建统治,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轻微的妖言犯罪,对象预言天气旱涝灾害的言行及留有图谶的行为如何处罚,《唐律》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由于预言天气变化、旱涝灾害的书籍和言论属于“自然科学”一类,不涉及政治问题,对当朝封建统治者而言没有直接的威胁,故可以从轻发落,但因其也充满玄异、天象等变化,并且有被“滥用”于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故处相对较重的杖刑一百。私自藏有前人所做的袄书,虽然是收藏性质,并没有用来“诽谤当朝”,也没有传播他人,也被处以徒二年的处罚;如果所藏有的妖书是属于前面所说的预言天气变化、旱涝灾害的“非政治性”书籍,对当朝统治者无害者,杖六十(注:见《唐律》第268条其注云:“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言理无害者”,谓袄书、袄言,虽说变异,无损于时,谓若豫言水旱之类,合杖一百。“即私有袄书”,谓前人旧作,衷私相传,非己所制,虽不行用,仍徒二年。其袄书言理无害于时者,杖六十。)。
(3)要说明的是“图谶”本身并不是一种犯罪,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里设有专门观天预测灭祥吉凶的官吏,在官学里也设有专门学习观天象的学科,但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禁止民间进行此类活动。以唐代为例,秘书省设有太史局,官吏设置令二人,掌管观察天文、稽定历数的职责,定期报告所见到的灾祥,并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泄露所见天文天象,否则治罪。《大唐六典》卷10太史令条载:“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之事。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侯焉。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其注云“观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3]。
另据《唐律》第109条漏泄大事条:“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其疏议云:“非大事应密”,谓依令“仰观见风云气色有异,密封奏闻”之类。
现存日本养老令杂令第八条也有同样记载:
“凡秘书、玄象器物、天文图书,不得辄出。观生不得读占书。其仰观所见,不得泄漏,若有微祥灾异阴阳寮奏讫者,季别封送中务省,入国史。”
《唐律》第110条私有玄向器物条:
“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书、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
其疏议曰:
玄象者,玄,天也,谓象天为器具,以经星之文及日月所行之道,转之以观时变、以占吉凶者。私家皆不得有,违者,徒二年。若将传用,言涉不顺者,自从“造袄言”之法。私习天文者,谓非自有书,转相习学者,亦得二年徒坐。
(4)综观中国历史,图谶之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严格限定为非官方不得学习、传播、使用,以防止其他政治势力利用图谶宣扬不利于当朝封建秩序。但也没有一个封建皇帝对歌颂当朝的言论进行过制止,即使是用了图谶、祥瑞的形式也都没有被做为犯罪,相反为了宣扬其统治合法性往往是欣赏甚至是纵容这样的行为。如《汉书》王莽传载: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则天垂拱四年夏四月条: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
总之,《唐律》对利用天命思想,传播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的打击是严厉的,但较之其他封建王朝动辄具五刑、夷族、凌迟处死,其在法律上也没有采用一味地严酷打击,而是依据其言论传播范围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处罚,从这点上说,《唐律》不仅相对其前代法律是个进步,就是相对明、清封建相关法律也较为合理、温和。
三 相关案例分析
则天延载李思顺谋反案,见《通典》卷289刑法七守正:“汾州司马李思顺,临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韦秀告称:思顺共秀窃语云,汾州五万户,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好设斋戒。”大云经上道:“理复思顺好,李三五年少。”思顺恰第三,兄弟五个者。监察御史李恒等奏称:“据思顺潜谋逆节,苞藏祸心,研核始引唐兴辩占,复承应谶。请从极法。”奉敕依奏者。司直裴谈断:处斩刑,家口籍没者。主簿程仁正批:合从妖处绞。只向韦秀一人道状,当不满众,合断三千里者。裴谈又判:请依前断录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却议者。有功议曰:谋危社稷,罪合反条。自述休征,坐当妖例。反依斩法,妖从绞论。律着成文,犯标定状。状在事难越状,文存理无弃文。若违状以结刑,舍文而断狱,则乘马何俟衔勒,遏流岂用堤防?今判官处以反谋,勾司批从妖说;不耻下问,窃欲当仁。李思顺解大云经,韦秀称其窃语私解,明非众说。窃语不合人知,虚实唯出秀辞,是非更无他证。纵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征。既异结谋之踪,元非背叛之事。即从叛逆,籍没其家,便是状外弃文,岂曰文中据状。请依程仁正批,妖不满众,处流三千里者正。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请议者。右台中丞李嗣等二十人议称:请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画一者。守司府卿于思言等六十三人议称:依徐有功议者。录奏,敕:思顺志怀奸慝,妄说图谶。唯其犯状,合寘严刑;为其已死,特免籍没者。缘有功议,遂免破家。
此案中韦秀举报李思顺按图谶之说解释大云经,认为大云经上所云“理复思顺奸,李三五年少”与李思顺姓氏、排行等情况相符,于是自认为是有贵人之图谶,当为大富贵等等。针对此案,监察御使李恒认为是潜逆谋反,应处以极刑。司直裴谈认为根据谋反条,首犯处斩刑,年满十六岁以上父子皆应处绞刑,近亲属籍没为官奴。主簿程仁正认为:李思顺所犯之罪非谋反大逆,而是应该以妖言不满众论处,而且其只向韦秀一人说过,未满三人,属于《唐律》“不满众”之规定,建议处以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司刑丞徐有功认为此案且只有韦秀一人做证,无有其他证据,事实真相难以说明。即使真的是李思顺自己认为符合大云经上云“祥瑞”,也只是自述休徵,仅此而已,无其他谋反之状,是符合《唐律》规定的妖言之法——“若自述休徵,假托灵异,妄称兵马,虚说反由,传惑众人而热真状可验者,自从妖法”,而不能以谋反罪论处,主张按照主簿程仁正的意见,应该处以“妖言不满聚,科流三千里,家口不缘坐”的处罚。
从案件的结局来看,虽然最终以妖言不满众结案,虽然李思顺身死,但如果不是徐有功力争,此案很可能定性为谋反大逆,按照《唐律》谋反入属于十恶之首的大罪,不仅本人处斩,家属也要没入官奴,可谓家破人亡。
武则天时瀛州李仁恒等37人谋反案,《通典》卷289刑法七守正载: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恒等37人,被告称谋反。曹断: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执曰:“玄淑里正元得户人缘祖纷争,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唤,或将奔叛相牵。反逆须有同谋,奔叛宁无协契?无谋无契,口语口陈,即以实论,颇亦苛酷。抢口元无影响,星文本自参差,纵使实有反言,只恨换其宗姓。因恨称有,正是口陈;徒侣绝无,明非实反。贼盗律云: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流三千里。疏云:口陈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状,并是口陈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实之计。忝居商度,用此当宜。如不使推,请从鄙见。如将未允,终须重推。录奏,敕依。得宗君哲状,称:无反可寻,请依徐丞见,流三千里。奉敕依,会赦免。”
此案中,瀛州李仁恒等人,因为有已有之旧怨,于是相互攻击对方想要谋反大逆、谋求叛国等大罪,本是无中生有的相互栽赃陷害,目的仅是要陷对方于不利,而希望官府将对方治罪,所谓假官家之手报私家之仇。地方法官不问具体情况,将两家都以谋反罪名结案,都判处双方首领斩刑,并处家口缘坐。徐有功认为在此案中,虽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谋反、叛国,但都拿不出对方谋反、叛国的实质性证据,按律应该是属于“口陈不肖之言”,并没有真正策划和实施过谋反行动,按照《唐律》规定,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应该处以流放二千里。
和上个案例一样,地方法官将此案定性为谋反和叛国的十恶重罪,因有徐有功此案得以改判,同样是先扩大罪名而后改正,使两个家族免遭杀戮。由此推断,当时地方法官往往将妖言等轻罪被扩大为谋反大逆罪,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
贞观年间茂州童子张仲文妖言案,唐《会要》卷39议刑轻重载:
贞观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张仲文忽自称天子,口署流辈数人为官司。大理以为“指斥乘舆”,虽会赦犹斩。太常卿摄刑部尚书韦挺奏:“仲文所犯,止当妖言。今既会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怀州人吴法至浪人失置鲍陈,口称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舆,咸断处斩。今仲文称妖,乃同罪异罚。卿乃作福于下,而归虐于上耶?”挺拜谢趋退。自是宪司不敢以閗。数日,刑部书张亮复奏;“仲文请依前以妖言论。”上谓亮曰:“韦挺不识刑典,以重为轻,当时怪其所执,不为处断。卿今日复为执奏,不过欲自取删正之名耳。屈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谓之日:“尔无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我,可申君所请,屈我所见。其仲文宜处以妖言。”
此案中,张仲文“自称天子”,并任命了几人为所谓“官司”,是自认为该成为皇帝,应该属于“妄说己身有休徵”,虽然已经实施了“自称天子”的具体犯罪行为,但并没有其他的大逆具体行为,所以应该归入“首造妖言”之罪。“指斥乘舆”之罪是指捏造、发布、传播针对皇帝本人的言论,属十恶之大不敬罪之一,此二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此案如果不是两位执法官不惜触犯皇帝坚持己见,就会以“指斥乘舆”罪结案,所犯之人就会被判处死刑,性命难保。
由上面案例看,尽管《唐律》对利用天命犯罪的规定可谓详尽、合理(相对其他封建法典而言),但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案件的官吏都会本着“从重不从轻”的原则,往往会加重处罚,并不完全按照法律条文的本意去判决,从这点来说,《唐律》这部代表封建法典最高成就的法律在实际中往往是成为具文。
五 总结
同其前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唐朝统治者对图谶以及天象等神秘之学也并非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将其纳入了封建统治秩序,用法律的形式对此类行为进行了规范。在对此类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时,并没有采取一味的残酷打击、无限扩大的方式,而是根据对封建秩序危害程度大小、犯罪人主观意识等具体情况,设立了轻重不同的罪名及处罚级别。不仅是对以前封建王朝统治经验的总结,也对后来封建王朝的封建法典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如大明律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都明显地吸收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经验,又根据时世有所变动而成。
收稿日期:2005-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