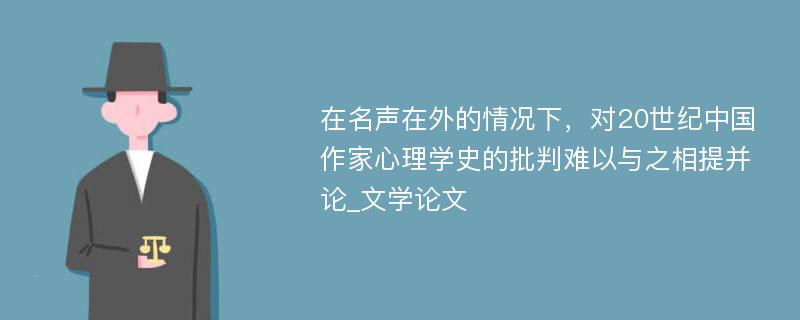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实难副论文,盛名之下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以下简称《心态史》)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书后记称“力图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切入,对本世纪中国作家的心态类型、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描述,以期进一步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723页。)。遗憾的是,通观全书,似与预期目标相距尚远。
平心而论,此课题有一定特色:该书纵览百年中国文学,关注文学思潮、时代心态,相对于以往的某些作家心态研究,近乎“长时段”;洋洋洒洒58万字的篇幅,力图包罗万象,兼及台港,也算宏篇巨制;特别是从作家传记、回忆录等已有成果中搜集、辑录了相当可观的有关作家心态的史料,使后来者免去不少搜寻之苦,类似史料长编;但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却拙于分析,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
该书封底将此书誉为“国内第一部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入手,分析描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心态类型”的专著,但愿这纯属广告用语,而非学术史定位。若以研究中国作家心态时限长达百年论,确无先例;就选题的开创性而言,此书并非拓荒者。除时段不同(一为现当代,一侧重当代),疏密有别,深浅有异,价值判断分歧,孟繁华完成于1995年的博士论文《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也尝试“从作家心态的曲折变化入手,梳理并描述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注:《梦幻与宿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页。),在选题上与之极相类。两书主要运用的实质上都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心态史》后记也透露出:“由于我们一直特别注重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对于作家个人的尤其是生理心理机制方面的材料发掘不够”)(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632页。)。孟著虽出版在后,但大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刊物上,早为学界关注。遗憾的是,《心态史》作为一个国家级课题,却对国内同类课题缺乏必要的了解,致使部分章节低于孟著水平且重复,而未能有所超越。
其实该课题大有可汲取、可借鉴的成果。除孟著,除书中提及的李辉关于巴金、周扬、冯雪峰等人的心态描述,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关于鲁迅的心理推断,以下研究似不应忽视: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诸作开始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总体研究,尤其是他的《丰富的痛苦》一书,实质上已从对中国作家心态“点”的解剖进入了“史”的展现;孙郁《百年苦梦》一书,对20世纪中国文人(大都是艺术气质很浓的文人)的心态也作了心心相印的描述。在钱理群、孙郁的笔下,作家复杂的心态弥散出诸种不确切性的光芒,而研究者则费尽心力地用文字捕捉,那“难言”与“言说”间的话语魔力恰是语言不无简化、轻率的《心态史》所欠缺的。
又如王晓明的论著《潜流与漩涡》对20世纪十余位中国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所作的体认深刻的分析;再如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神话》一文对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注:《当代西绪福斯神话》,《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作者颇有新意地发现了史铁生因残疾心态而生的类宗教精神(《心态史》“主体生理机制与作家心态”节中也有一段谈及史铁生残疾心态的类似论述,想是不约而同,否则理应注明出处)(注:《心态史》抄袭了《当代西绪福斯神话》第42页。);吴俊另著有《鲁讯个性心理研究》一书,对鲁迅的负罪感、虚无意识、被虐与攻击心理、性爱心理以及暮年意识都有着不无偏颇、却发人深思的阐释……上述研究的深度以及透露出的诸多学术生长点,使学界有理由要求此课题在广泛汲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推进。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读毕全书,却发现其思维水平不时从前述更具文学心理学意味的深度思考,降至作家经历、心态的浅表记录。且部分章节概念芜杂,持论偏颇,史实有误。以下分别析之。
一
该书并非没有将平面化的描述提升为更有价值的“理论形态”的自觉,但涉及理论层面的概括往往不能做到逻辑自足。用以分门别类的概念或重叠,或不平行,以致不能准确地说明“希望作出的是什么区别”。
如书中依据主导心理动机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导心态类型分别概括为:政治型心态(书中又称其为“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人文型心态、超然型心态。被该书归入政治型心态类型的作家计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郑振铎、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夏衍、老舍、闻一多、朱自清、冯雷峰、沙汀、艾芜、周扬、胡风、丁玲、艾青、何其芳、李广田、赵树理、孙犁以及建国后活跃于文坛的郭小川、贺敬之、柳青、欧阳山、梁斌、峻青、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洁、梁晓声等;归入人文型心态类型的作家计有: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以及活跃于新时期文坛的莫言、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归入超然型心态类型的作家计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林语堂、张爱玲以及活跃于新时期文坛的杨绛、孙犁、汪曾棋……(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3页。)
融入时代潮流的作家其创作是否必然从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动机出发?如鲁迅,如朱自清;而郑振铎虽曾亲历上海工人反对“四·一二”屠杀的游行,也有与开明书店同仁联名致信国民党抗议暴行之举,但“从主导心理动机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来看”,将其归入“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类型似有不妥。“五四”时期,他便反对在文学中渗入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动机(而非如书中所言主张“以文学为武器”),认为“如果作者以教导哲理、宣传主义为他的目的,读者以取得教训、取得思想为他的目的,则文学也要加上坚固的桎梏的危险了”(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30年代无论在北京编辑《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时,还是主持燕京大学中文系之际,他都“谨守文学本业”,并扶育了北方一片远离政治、埋头写作的文学风景。
周作人与林语堂无论在“五四”时期还是《论语》时期都是同气相求、互为呼应的同道;汪曾祺一再强调自己是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若说他“超然”,也显然一脉相承于沈从文乃至周作人……然而都被概念硬生生地撕裂了。又如钟阿城的心境庄禅影响颇深,何以非归入人文型心态而不可归入超然型心态?
我意该书列“人文型心态”不妥,因其涵括面太大,书中被归入超然型心态的林语堂、张爱玲、杨绛、孙犁、汪曾祺等都可纳入。还不如改用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都曾标举的“自由主义”一词来得贴切。
特别牵强的是,该书又据“中行、狂、狷这样三种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潜在影响”,推导出如下论点:“富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政治型心态,正是‘狂’者文化心理的体现;超然心态体现的正是‘狷’者风范;至于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人所向往的不偏不倚的文化心态,颇类乎于传统文化所期望的中行人格。”(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1页。)按照书中的逻辑推导,人文型心态的莫言应为“中行人格”,然而众所皆知莫言的创作心态放纵恣肆、无规无矩,判其“中行人格”岂不荒谬!而按书中的逻辑推导,政治型心态的朱自清应属“狂者”,然而40年代文坛却都尊崇守分有所不为的他为“狷者”,即便40年代中叶他终于“跟着时代走”,步履依然谨慎节制,他依然“以无党无派为操守”,依然狷而不狂。类似的“张冠李戴”还有徐志摩、郑振铎等。所以出现上述混乱,纯因概念抵牾,指涉互缠,涵义不清。
如此归类在书中不一而足。如该书涉及“文革”时期作家的虔诚心态,将其具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苦衷式(如周扬、郭小川、邓拓);2.自责式(如沙汀、赵树理);3.负罪式(如巴金);4.感恩式(如臧克家)。于是,“自责式”与“负罪式”指涉互缠;“苦衷式”与“感恩式”概念也不无重合:如书中所记,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周扬出狱时,“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何尝不是出于“自责”、出于对领袖英明的“感恩”?又如,郭小川在干校期间又何尝不以其诗作、书信,表现出某种类似于臧克家的感恩式心态?该书论及“文革”时期作家的自杀现象时,更是失之繁琐:将邓拓的自杀称之为“证苦衷”之死;而将傅雷、周瘦鹃、李广田、闻捷的自杀称之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死,指出“上述一些作家的相继自杀,却没有一人是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也不仅仅是由于政治高压而导致的幻灭,也不是邓拓以及中国古代的屈原那样一种‘证苦衷’之死,而是表现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以死抗议邪恶的精神”(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503页。)。于是,不区分倒还清楚,越区分越使人糊涂:邓拓之死何以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李广田、闻捷之死何以不是“证苦衷”?
该书虽有追求“系统”的自觉,却缺乏求系统应具的理论概括、逻辑运演的能力,故每每以一些教科书式的不无简单化的条条、点点敷衍。殊不料,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反而因类似的机械解析,剪不断,理更乱。
二
在该书“进一步探讨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时,立论言说也不无空泛、偏颇。如第五章结尾在探讨中国作家文学心态的失衡与丁玲、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悲剧时,除归咎于“政治原因以及当时他们个人言行的某些不当”外,又称“创作心态的失衡,又与作家个人的素质有关。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应有博大的宇宙襟怀,凌空高蹈的文化眼光,和超尘脱俗的生存策略。只有如此,才能风雨由人,处世不惊,才不至轻易为一时一地的功利所匡拘,才能避开纷繁世俗的干扰,保持一种通达开阔的创作心态,才有可能写出一流文学巨著。曹雪芹就是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设法保持了这样的心态,创作出了伟大的《红楼梦》的。在50年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与孙犁,也正因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样一种可贵的心理素质,故而才会有《茶馆》、《铁木前传》这样的优秀作品的产生”(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14页。)。文中暗含着对胡风等人不谙“生存策略”的遗憾。对作家宣讲生存策略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未知上述“生存策略”是否包括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责任,是否包括修剪作家的独立人格以适应严酷的政治环境?若是那样,纯属不平等的平衡术。总觉得上述立论对作家心态、文学现象缺乏必要的“体贴”,而近乎空口说大话。关纪新著《老舍评传》以“树欲静而风不止”为喻,极其生动地说明了在那特定历史时期,作家心态要避免政治风雨的干扰谈何容易!不是吗?即便如书中赞赏的“具备了这样一种可贵的心理素质”的老舍与孙犁,终未能在“文革”风雨中“处世不惊”,而分别有沉湖之举、自杀之念。老舍的血恰恰反证了此路不通。
该书自称持整合价值观的取向,我也注意到了书中观念的多元,但整合价值观应意味着客观的史实与复杂的倾向在多种联系中充分得到学术尺度下的尊重,意味着论述的相对平正、公允,遗憾的是,体现在书中的却常是一场思想内哄。更令人不安的是,杂语喧哗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刺耳,那便是部分仍未舍弃偏“左”的理论立场,未舍弃不无僵硬的阶级政治尺度的执笔者所持的论调。
在论及萧红前后期小说创作时,该书称:“正是与感情的寂寞,生活的困苦,病魔的折磨有关,萧红这时的创作思想也出现了某种偏差。她的笔下再也没有了《生死场》中那样的对恶势力绝不妥协,勇敢斗争的英雄人物,而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消极倾向,这在这一时期她写的《呼兰河传》中有集中反映。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否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而将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有反映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有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49页。)对于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等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赵园《地之子》的评价却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称《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的愚昧,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冯歪嘴子倔强的生命里面,又表现出中华民族潜伏在下层人民中的无穷伟力”;杨义称“萧红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精神丝缕难以割舍地牵系着已逝的光阴、遥远地故土,说明她的心灵中有一种难以拂去的寂寞之感,并在寂寞中忧郁地参悟着人间的生老病死、前尘后影,以直觉逼近‘哲学’。她借这类作品宣泄胸间哀戚,也在这类作品中达到了艺术上新的高峰”;赵园则看重《呼兰河传》的“非模式”写作,并因《呼兰河传》等小说的命意与结构样式,将其视作“新时期某种探索的前导”(注:参阅《地之子》第13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版。)。对某部文学作品的评价可以众说纷纭,但应是学理探讨,而不能是政治批判——如该书因《呼兰河传》的“非阶级斗争模式”而上纲上线“为作者否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
这类阶级政治话语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本书中。如称沈从文的作品艺术价值可取,却“缺乏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8页。)。在执笔者眼中,只有当作品直接指涉阶级政治时似乎才具“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至于超越阶级斗争的人生体悟、文化思考则不具“进步意义”。正是为此类泛政治语系所蔽,以致未能发现沈从文作品越来越显示出的对人类的卓特贡献。
也是由于执笔者取庸俗社会学的眼光而非文艺心理学的视角,该书在论及艾青的忧郁时,泛政治话语替代了学术话语。《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视“艾青式的忧郁”为“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与艾青个人气质的一种‘契合’”,并认为“这浸透了诗人灵魂、永远摆脱不掉的忧郁,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个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文艺心理学的视角看,诗人某种博大、深刻、忧生忧世的忧郁气质,恰是优秀诗作赖以产生的动力源。然而该书却在准确地道出了这是时代的忧郁、历史的忧郁之后,又节外生枝判其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并一厢情愿地称“在奔赴延安之后,艾青的忧郁才一扫而光”。(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48页。)思想改造(书中名之为“思想锻炼”)的铁扫帚若真有此彻底的神效,那么,本不该如执笔者那么激赏,而应惋惜:诗坛从此少了一个有着独特艺术气质、艺术个性的诗人。
同理,正是因着某些执笔者至今未能逸出阶级斗争、思想改造年代铸成的历史心理障碍,致使不时出现对那个时代心理不加分辨,不加剖析,反而备加赞赏的认同。如书中赞誉“新中国成立后,废名终于从孤寂迷乱的心境中走出。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时代,再度唤起了他的创作热情。……在中国人民支援埃及抵抗英法侵略的时候,他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年老的病人,竟要求‘到埃及去做一名志愿军’。从这不切实际的要求中,我们或许仍可见出废名个性的怪异,但他的心地无疑是真诚的……自信心也使废名不像巴金、曹禺等人那样背负上沉重的心灵重累,而是以坦然潇洒的心态,面对了伟大的新时代。”(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07页。)实质上,废名建国后的热狂心态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建国前“口吐疯癫之语,手舞足蹈不止”的迷狂的或一形式表现。他的好友卞之琳曾谈及他晚年的“激进”,说他“不假自己的独立思考,几乎‘闻风而动’,热肠沸涌,不能自己,于是乎旧时的妙悟、顿悟、擅发奇论甚至怪论的思想方法一旦与感人的新事物结合,我看不免有不少离谱的地方。”一个颇具病态心理学意味的个案,却被执笔者政治整容为一个欣逢盛世、枯木逢春、心态“坦然潇洒”的典型。
三
作为一部心态史,该书对史料却缺乏尽可能详尽的占有,缺乏认真的考辩梳理,甚至“六经注我”,信手拈来。由于论据的欠可靠,致使部分观点缺乏坚实的支撑与导引。
如书中对邵洵美称其曾负责接待萧伯纳并出席了那次宴会这一说法未加辩析的引用,疏忽了当事人的证言必须经过验证(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61页。)。事实上这一史料显然有误已有倪墨炎等识者指出。又如谈及丁玲南京3年的软禁生活,称丁玲“丝毫不为所动”,“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丁玲就是这样,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风范”(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41页。)。这也有违史实。本来丁玲的“南京三年”作为作家心态史的材料恰可透视丁玲在这艰难、尴尬的境遇中的复杂心态,包括她的脆弱与刚强、颓唐与昂奋、麻木与挣扎、苟且与坚守;然而那人性的伤痕、生命的血色却因书中概念化的矫饰荡然无存。
更轻率的是书中对一些至今颇有争议的材料的采用。该书称“文革”之初,浩然与李学鳌“曾敏感地意识到这场革命中所隐藏着的龌龊与黑暗,曾利用‘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地位,合谋暗中保护过老舍、杨沫等作家”(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513页。)。20年前“争议浩然”时,对于浩然与迫使老舍自杀事件有无直接的关联,并未达成共识;1998年底,又因浩然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问,谈及老舍之死而争议再起。有人认为,“从浩然自己这段回忆中,可见老舍之死确与他有所关联:1.他声称派了一个人去保护老舍,为何老舍还是被打了?2.他把老舍送到专政机关派出所,老舍是否以为浩然宣布其为‘现行反革命’是一种保护而不是罪加一等?明明是红卫兵打伤了老舍,为何浩然还要说老舍打红卫兵?浩然此前与老舍一直关系不好,老舍能理解一个政见不合者这种突然而来的‘特殊保护’么?……3.他又赶到派出所批评老舍,还叫老舍‘明天到机关开会’,老舍对这个批判会的恐惧感是否极大?这种种压力除了挨打是红卫兵施行的,其它都是来自浩然啊!”(注:参阅朱健国《“争议浩然”再争议》,《新经济周刊》1999年6月28日第15、16版。)……所以不厌其长地援引别一种说法,意在指出浩然有可能是老舍的保护者;也有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甚至有可能对老舍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种可能出入甚大,而《心态史》在缺乏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的前提下贸然断言,未免有失文学史著作应有的慎重。
至于书中缺乏史料支撑,臆断周扬“建国后,一直忍辱负重,代表中共中央,具体执掌着中国的文艺舵轮,忠诚地按照党的布置,积极领导和组织了一次次文艺批判运动”(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468页。)(引文中着重点为笔者所加),则明显有违史实。以上批评,用语太直。且一味针贬不足,而没有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成就。这并不等于笔者认为此书无所长、无可取,而是由于那些优长已有一些识者指出,故不再赘言,只要不是溢美之辞,想来不会因笔者的批评而遮蔽。
所以严格,很大程度上鉴于它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对此属望者殷。尽管课题式申报、集体运作容易产生一些体制性弊端已成共识;尽管名不符实的大型课题也非个别;但这不仅不能成为谅解该书缺陷、降低国家级课题应有的学术水准的理由;相反,恰恰表明,对此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课题进行严正的学术批评,已是学界重建学术规范的亟需。
标签:文学论文; 老舍论文; 中国作家论文; 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呼兰河传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中央编译出版社论文; 丁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