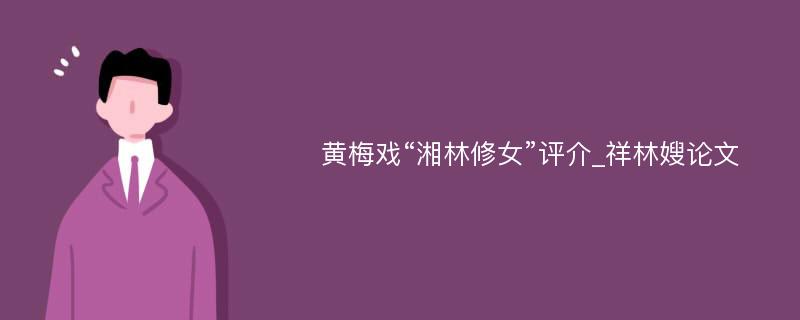
漫评黄梅戏《祥林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梅戏论文,祥林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江苏省首届青年戏曲节上,由江苏第一泉黄梅戏剧团(盱眙县)演出的《祥林嫂》引人瞩目,“小团演大戏”,确实不易。而我观摩此剧,关注的则是它与原著《祝福》的关系。编导者苏位东、朱国芳声称:“我们只能忠实于原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注入什么新的东西。……我们要求自己尽力做到的只能是不要歪曲它,更不能有任何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改编经典名著的创作思想,十多年来似乎已很少听说了,有的多是“超越”,“以现代意识重新解释”,“关键在于挖掘新的时代意义”等等。在我看来,既然是经典,就是久经考验,由历史筛选出来的精品。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仅因为它与当时的人们相通,也与当代的人们相通,仍具有当代的时代意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所以对动辄便要赋予新的意识、新的观念的改编经典巨著的创作思想及作品,笔者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比如对于《红楼梦》,在我看来改编时“忠实”尚唯恐不能,更遑谈“超越”、“新意”?正因为笔者长期抱有这样的保守思想,所以特别欣赏黄梅戏《祥林嫂》编导者的小学生态度。的确,在经典名著面前,首先要谦恭,尔后才有所获。若倨傲在前,充其量不过是哗众取宠。一时哄闹固然能在脸上贴金,但那“金”色是终究要褪的。表面文章做不得,就因为归根到底总是徒费心血。
(二)
那末黄梅戏《祥林嫂》是否真正做到了忠实于原著了呢?
衡量这个问题的标准,要把握人物形象及其所体现的题旨是否符合原著,而不在于某些细节。相反,由于从文学转换为戏曲,在某些细节方面依照舞台艺术的表现规律,必要时还应当作某些调整。我注意到,黄梅戏《祥林嫂》至少在两个细节上有些改动:一是祥林嫂被迫改嫁贺老六,在拜天地时,原著写祥林嫂头撞香案而昏厥,演出则以人物反抗不能时的精神恍惚使仪式得以顺利进行,而把撞香案挪至洞房中撞床沿。我在观摩时并没感到什么别扭,从编剧技术上考虑,这样一挪动,倒便于表现祥林嫂与贺老六心灵上的撞击和冲突;同时也便于表现贺老六壮年成婚不可避免的野性,使之与祥林嫂昏厥后贺老六的自抑形成较大反差,使贺老六的忠厚性格更加突现、更加丰满。况且撞香案与撞床沿,同样都能表现祥林嫂的抗争,于人物形象无损,当然若仍依原著让祥林嫂撞香案,也并非不可,但洞房一场就很难有戏可演:贺老六将昏过去的祥林嫂抱进洞房,下面就只能由贺老六独自一唱到底,戏剧行动单调、无味。所以我以为编导在这一细节上的改动是成功的。
另一个细节的改动是,原著写的是贺老六死于前,阿毛死于后,演出则将这两件事合于同一天发生。这样的改动在戏剧行动上增强了不幸事件对于祥林嫂的冲击力,同时也省去了一些场次,更简炼,更明了,也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我们更应关心的是忠实于原著的实质内容。
祥林嫂是鲁迅笔下的一个不朽的典型,她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去开掘,但有一条基本涵义是必须把握的,那就是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揭示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势力对于妇女的戕害。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时指出,封建宗法社会有四种权力系统: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的男子普遍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而中国的女子则还要加上夫权的束缚,因此女子是处于最底层的被压迫者。鲁迅写《祝福》,将祥林嫂设计为一个寡妇,这就使人物处于底层的底层。与普通女子相比,寡妇更为族权、神权、夫权所不容,因为丈夫不论死于何因,都是妻子的罪孽所致。寡妇的命运也因此就更悲惨,她所含有的典型意义就更具血腥味。但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更在于,他将祥林嫂的悲剧不仅归结于封建宗法势力作为人的外在力量对于人的生存、自由、人性的压迫,更归结于它作为观念、作为意识,渗透于人的骨髓、融化于人的血液,而成为人的自我戕害的力量否定自己。这正是鲁迅所最为痛心疾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性的本质之一。封建宗法势力的残酷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远甚于它仅仅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剧不仅在于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更在于有价值的东西自认为应当被毁灭。这正是鲁迅创作《祝福》的初衷。
基于对原著这样的理解,我以为黄梅戏《祥林嫂》的改编是成功的。编导在表现祥林嫂夫死子亡一连串不幸的基础上,着力描写人物自我的罪孽感。“扫帚星,克夫命”,从鲁四老爷的侮辱,变为祥林嫂的自我认定。编导抓住“手”来做文章,鲁四老爷说:“……你嫁两个,死两个,晦气。寡妇做事不干净,东西沾了你的手,祖宗、菩萨怎么肯吃!”于此祥林嫂无力辩白,也未曾想到辩白。她在磨房中痛苦地自叹:“这话儿说得我战战兢兢地怕,好似那乱针儿尖尖利利地扎。手啊手你何时得罪了菩萨,竞变得不干不净,腌腌臜臜。……看起来只能是多干活儿少说话,苦海里行船你与我慢慢儿地划。”当柳妈给她看花纸,那上面画着一个嫁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正在被分尸,一锯两半,她惊恐和悔恨,而这惊恐和悔恨正表明了她对夫权(死后到阴间她也得属于丈夫,所以才要分尸)、神权(罪孽者到阴间要受鬼神惩罚)的深信不疑:“阎罗殿,阴森森,阴森地府列鬼魂。青面獠牙多凶狠,张牙舞爪吓煞人。恨只恨,当初寻死未撞准,落得个,罪孽步步愈加深。眼睁睁,死后还要交恶运。……”
拼命干活,可以使她生存下去,却无法使她驱除压在心头的罪孽感。带着罪孽,虽生犹死,于是如何赎罪便成了她生存的前提。所以当以柳妈告诉她:到土地庙捐条门槛便可赎清罪孽,她竞猛然在绝望中看到了生路:“我能苦,我能挣,挣得钱来赎罪名。只要罪孽能洗尽,苦死累死也甘心!”“土地庙里去打听,捐条门槛作替身。千脚踏万人跨我也能忍,为只为死后不进地狱门!”既然捐门槛能赎罪,赎了罪便能象正常人那般地活下去,祥林嫂捐了门槛后的喜悦是难以言喻的。编导者在表现祥林嫂的喜悦时特意加了她和柳妈的一段戏:祥林嫂告诉柳妈:“门槛已经捐上了,真的,又粗又长……。”柳妈以为她又要唠叨阿毛的死,打断她的话头:“又来了不是。”祥林嫂快乐地表白:“不,我是说我该早点去捐。”这里编导者匠心独运,以祥林嫂一向用来表达失子之痛和侮的一句话“我真傻,真的……。”(凡读过《祝福》的读者都记得这句话,因为它将祥林嫂的痛苦和侮恨表达得最淋漓尽致),来表达她赎罪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其实赎罪后的喜悦,恰好从反面衬托了人物在赎罪前的罪孽感的沉重。正面文章反面做,编导者是聪敏的。
祥林嫂的悲剧是以死来归结的。但与其说祥林嫂死于一连串不幸的生活遭遇,不如说死于罪孽感的不能解脱。当鲁四老爷宣布祥林嫂捐了门槛也不能碰香炉、烛台、供品时,也便等于宣判了她的罪孽永不能赎补,也便等于宣判了她的死刑。祥林死了,她与婆婆相依为命;老六死了,阿毛死了,她仍能在鲁家干点粗活……。但祥林嫂终于未能苟活下去,就在于她的“罪孽”被宣布永不能赎补。如果说祥林、老六、阿毛的死多少带有偶然性,祥林嫂的死却是必然的。封建宗法势力,无论作为客观存在还是作为人物的主观意识,都不能容许她活下去。为了表达原著的这一题旨,黄梅戏《祥林嫂》的编导者,除了通过人物的戏剧行动(诸如上述),还着意开拓人物的心理空间,在结尾加了一场阴曹地府的戏:祥林和老六要争夺祥林嫂,四个小鬼为他们分尸……。这是祥林嫂临死前的意识活动,让我们分明感到了祥林嫂自我罪孽感的沉重,对表达原著(以及演出)的题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倘若没有这段戏,祥林嫂死于鲁四老爷们的一片祝福声中,我们看到的情景、得到的启示,无非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然而这决不是祥林嫂这个典型形象的全部,更不是她的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
(三)
为了更鲜明更准确地表达出祥林嫂的典型意义,这出戏似乎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改进:
其一,贺老六和阿毛的死,对祥林嫂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对祥林嫂致命的打击却是鲁四老爷在祥林嫂捐门槛赎罪以后仍宣布她“不干不净”,不能碰烛台、供品。演出没有注意到这两次打击轻与重的区分,体现在人物造型和表演上,祥林嫂在老六、阿毛死后二进鲁家时,已生华发,举止迟缓,显出老态;这样一来,在被鲁四老爷宣布永不能赎罪而赶出鲁家后,便无法在造型和表演上造成更大的反差。鲁迅描写祥林嫂二进鲁家时仍是壮实的,什么粗活、重活她都能干,只是在精神上显得萎顿、麻木,始终生活在亡夫失子的痛苦之中。所以演出时,祥林嫂二进鲁家,不应表现她的老态,可以在造型上以头发散乱、衣衫不整(但也要注意适度),在表演上以精神恍惚、两眼呆滞,来表现人物的疲态,及至赶出鲁门,人物赎罪不能、再无生的欲望时,再表现她的老态。这样可使前后造型、神态的最强烈的反差,留于最能体现原著和演出的题旨的地方,起到强化人物典型意义的作用。作为导演和演员,某些重要的细节是要时时扣紧主题的,犹如做文章,务使字字句句勿有离题之嫌。
其二,演出结尾对祥林嫂临死前意识活动的表现,用意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表演上,四小鬼窜上窜下,显得没有章法,尤其没有注意到须突出祥林和老六。从这段戏的内容和创作意图来分析,应以祥林和老六为中心,分为两组,以舞蹈的形式来展开。可借用传统戏中的某些舞蹈和表演技巧,如跳判之类,来表演二夫分尸的情节,以此加强人物的精神压力。此外,这段戏既要狰狞可怕,又要富有形式美,使这段戏既具有点染、强化人物思想意义的作用,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这段戏的表演一定要精采,使之成为终结全剧的“豹尾”。
(四)
戏曲舞台的时空自由,是戏曲艺术以有限写无限的优势。五十年至八十年代,新编戏曲剧目往往忘掉这一优势,以分幕制代替分场制,从而使自由时空变为固定时空。这本是向话剧靠拢的结果。但是八十年代的话剧舞台正与戏曲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在时空处理上反而向传统戏曲靠拢,先是有“无场次”,进而在分幕的每一幕中,将演区切割为若干小演区,依剧情需要,轮流或跳跃使用各个小演区,借助追光或区域光,将时空流动起来,丰富了舞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使固定时空难以或无法表现的不同时空的事件,能够集中在同一幕中表现,显得更为简炼明了流畅。九十年代,戏曲新编剧目吸取了这一经验,以不同的形式重又回到时空自由的观念上来,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黄梅戏《祥林嫂》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它巧妙地使用若干梯级平台,或合为同一时空,或分为几个时空,相当自由灵活。
写戏、导戏的人都知道,第一场戏最难写。因为有许多背景要交代,否则观众看不懂,剧情也难开展。《祥林嫂》这出戏,一开头需要交代:祥林嫂守寡,与婆婆相依为命,卫老二怂恿婆婆卖掉祥林嫂;贺老六壮年未婚愿意花钱买祥林嫂为妻;祥林嫂得知此事,惊恐,不安,至死不从,决定逃跑……。这些情节背景必须一一交待,但又不能采用传统戏的“自报家门”加以叙述;倘分若干小场次,戏就会显得“拖”、“瘟”。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几个平台,将演区切割,借用追光和区光的变换,以若干小演区将上述发生在不同时空的背景事件,一一表现。这样一来,不仅笔力集中,而且情节开展流畅。导演在运用切割演区手法的同时,还利用幕外音将不同时空加以复合。如贺老六在正面平台出现,在唱腔中表达了急迫成家的心情,紧接着幕外响起祥林嫂惊恐的叫唤声:“妈!你不能这样!祥林他九泉之下也会……。”手法相当简炼老到。
但有一点须提出的是,当几个平台合为同一时空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妨碍演员的表演,要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演员伸展手脚。譬如第六场,祥林嫂上山寻阿毛,以若干平台为山冈,这当然很不错。但平台太多,演员上上下下显得很忙乱。我的看法,应当将舞台中央的那块大平台撤掉,留有足够余地让演员以身段(借用传统戏的程式)来表现爬山、行路,人物的焦急除通过唱和白表现外,在这场戏中,更要注重以身段来表现。这是全剧中难得的一个施展身段表演的场次,不能以写实的上山下山动作轻易地滑过去。在身段设计中,要注意难(耐看)和美(好看),但要忌繁,不能琐碎。这样一来我相信这场戏可为全剧增色不少。
(五)
以一个县级小团上演根据名著改编的大戏,况且在此之先,不仅有越剧(已作为该剧种的保留剧目)、电影的成功,而且有多个其他剧种改编上演,可见该团的领导以及编剧、导演、演员的魄力和雄心,这是令人欣慰的。但从整体看,演员阵容的实力尚不够强大。主演毕春梅的戏,以前我从未看过,无从比较她的进步和退步。从饰演祥林嫂看,这位演员在把握人物的基调方面还是较准确的,人物幸与不幸遭遇后的几次变化,从内心到形态都能把握到位,层次清楚。需要注意的地方,除我在上面提到的二进鲁家复又被逐在疲态与老态的表演方面需作适当调整外,在唱腔方面,还需注意更为细腻的处理,这是基本功还有欠缺的表现。贺老六在洞房一场,初始的野性还表现不足。不必有损害人物善良忠厚品格的担忧,因为只有野性表现得到位(当然不能表现为粗暴),才能使祥林嫂撞床沿寻死更为合理,同时也才能使老六在祥林嫂昏厥后的自抑与前面的野性显出更强烈的反差,由此也才更能鲜明地表现出贺老六的善良和忠厚。这是表演中的辩证法,不可不懂。
在音乐设计上,幕后的伴唱非常动听,各角色的唱段也不错,但有的唱段似乎离传统味道远了些,使爱听黄梅戏的老观众感觉不过瘾,另外,主要唱段不突出,似乎有主、次平分秋色之感。
以上所提的,毕竟是琐碎的技术性问题,何况也未必提得合理。即使这些都是问题,也是瑕不掩瑜。
衷心祝贺黄梅戏《祥林嫂》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