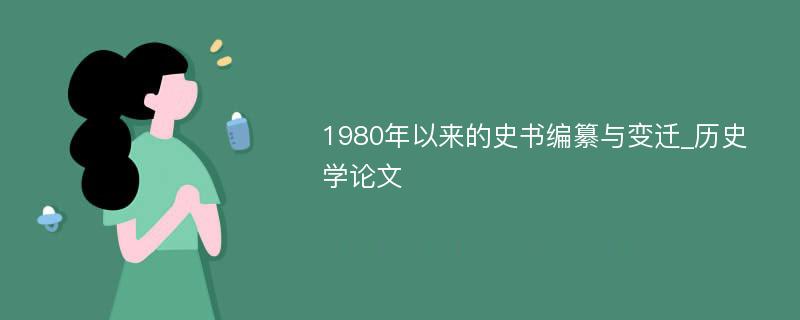
史书编撰与1980年以来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45至1980年:史书编撰的两大支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7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史书编撰方法立足于以下三个支柱 :结构史学,量化研究和心态史。
结构史学立足于精确的社会研究方法,其原则是在假设社会上存在着同质的社会阶层 的基础上重建诸社会群体。它运用的标准既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范畴(如在生产过 程中的地位),也有行政管理部门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如社会—职业分类标准。这种方 法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是由相对均质的社会群体构成,而每一个人则在某一群体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认同其本质特征。对于一个农业工人或者是一个城市食利者而言, 历史学家给予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如何代表或表现出其所认同的社会阶层的属性,而不是 他们的个性或特殊性。
而量化分析的方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则由诸如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 )和埃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这样的历史学家加以厘定并确立,并于60 年代和70年代臻于完善。它立足于下述三重观念:
——数据的使用赋予历史学的知识以更多的科学性并由此而减少其非确定性因素。埃 马努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70年代就认为,历史学家只要 装备有计算机,并由一系列数据支持,就可以成为科学家。
——历史学家通过使用经过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规则辨析后的数据,可以用以衡量其它 历史现象或史实,甚至可以用其界定出非确定性的阈值。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历史学家将 对法国18世纪人口发展演变的数据化分析方法大规模地运用于教区人口出生死亡登记册 的统计与分析上。
——数据的使用使历史学家得以理解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拉布鲁斯及其传人通过 对16世纪和18世纪期间的大量价格数据的分析进而研究经济危机等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便是诸多实例之一。对诸如识字率这样的文化数据的分析,对诸如17世纪和19世纪期 间使用避孕方法的人数统计这样的有关私人生活的人口学数据分析,则是历史考据学者 运用数据分析方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典型例证。
“心态史”研究得益于“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 弗尔(Lucien Febvre)的研究成果,并且深刻影响了法国历史考据研究,尤其是是该学 派提出的“心态分析工具”的概念,值得一提。某一文明或某一时代的心态分析工具, 是指所有用于认识世界,思考世界并改造世界的的知识范畴,认识范畴和情感范畴。吕 西安.费弗尔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拉伯雷的案例,并说明在16世纪,若以心灵分析工具分 析当时人们的观念,就会发现不信神论和无神论是无法想象的。许多学者从中深受启迪 ,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便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中世纪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 和关于炼狱的想象。
在上述三大支柱以外,还需补充另一个对历史时间的结构严谨的描述方法。这种方法 既吸取了结构的概念,也给予量化分析以特殊地位,同时还将文化的维度整合于其中。 根据这种方法的层次排列,经济现象居于首位,因为经济活动至少部分地导致了社会的 产生,而对此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文化方面和文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年鉴》杂 志直至1994年,其副标题仍然为《经济·社会·文明》,后来才改为《历史学·社会科 学》)。这里主要的参考坐标便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论地中海文 明》一书中提出的三重时间维度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将发生历史事件的短暂时间置 于历史时间的长河中加以深度考察。布罗代尔于1958年发表于《年鉴》的著名文章的标 题就是《长时间历史阶段》(一译“长时段”),而长时间历史阶段的概念便成了法国历 史考据学的核心时间概念。它的重要性可从以下两点中见出:
一、借用布罗代尔有关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的术语“思想牢笼”,我们可以说凡是长 期持续的东西,和非长期持续的东西相较,必然带有更为厚重的历史积淀,这就说明了 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时间的长短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70年代的研究课题即可证明:长 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研究(参见关于法国和英国农业生产/生产率发展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人口迁移的形式,针对长时期内自然气候演变史和环境演变史展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此项研究的首要特征即是排除人类对气候和环境的作用因素而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学 家当时所发现的自然决定论的框架中加以考察)。
二、“长时间历史阶段”是一个有助于我们沿着杜克海姆(一译“涂尔干”)(E.Durkeim)在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之际重新思考社会学时的逻辑,重新思考人文科学 范畴的概念。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中心学科,因为它从时间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 ,在此基础上方可纳入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维度。这种围绕着历史学来建立社会 科学的模式也是对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回应(参见其于1958 年发表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一如布罗代尔关于长时间历史阶段的文章)。布罗代尔 以长时间历史阶段的概念代替结构的概念,并强调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的历史性。
二、80年代和对历史研究两大支柱的批判
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的特点是,法国史学界比其它国家的史学界更加广泛地质疑历史 考据学的两大支柱。头脑最为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发现结构分析方法和量化分析方法 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197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明显地表达了这种不安。第一篇文章题为 《过去与现在》由英美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撰写,他在文中批评抽 象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注重结构而忽略历史事件本身,注重模式而牺牲有关史实的叙述。 耐人寻味的是,此篇失之浮浅的文章竟在史学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因为不少历史 学家对历史学过于遗忘个人的作用及个人行动的自由而忧心忡忡。第二篇文章由意大利 历史学家卡尔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撰写,他猛烈抨击了他所称之为“伽利略 ”范式的研究方法,换言之,即历史学家寻求历史规律和阐释规律的方法。他的批评主 要集中于那种试图将历史系列化,试图使其呈现出规则性的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的方 法,抨击有些历史学家将运用此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加以普遍应用,以便建立一种因 果关系的阐释史实的范式。金兹伯格认为,此种研究方法源于精确的科学,然而历史学 的史料是不可以用此种推导方法化减通约的。他建议建立一种“指数范式”,此种范式 并不寻求建立规则性联系,而是用于解释一些指数,即历史学家们认为有意义的史实和 必须加以阐释的史实,一如某幅油画的局部或16世纪某个磨坊主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 。总而言之,必须以刑警的调查研究的逻辑取代科学家的逻辑。
这些“纠偏”的立场导致了(或准确地说伴随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三大批判运动的出 现。
1.对数据的批判:
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对于数据有时近于天真的信任受到严肃的质疑。首先是因为很 显然,社会科学里的数据和精确科学里的数据不具有同样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前者, 数据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常常是妥协的结果,在这个谈判的空间里,其有效性是相对的 。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企业的破产。经济史学家长期认为这是经济景气的可靠指 标,而历史学家们近来却证明,何以企业破产的数量只是部分地反映经济景气的指标,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企业界或与企业主谈判的结果,而且由谈判各方共同 决定在什么时机决定通过增加破产企业数量来整顿经济,或相反,通过降低企业破产数 量来保护企业。
其次是人们意识到数据在长时间历史阶段内的可靠性常常很低,因为随着被衡量的现 实的改变,衡量的尺度也失去了价值。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两位统计员试图测 算法国1800年至2000年的就业人口的例子便很能说明问题。他俩的研究结果遭到历史学 家们的严厉批评。历史学家们认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概念无法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 加以衡量,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1800年和20 00年就业人口的百分比置于同一条曲线上是混淆事实的做法,因为这里衡量的并非同一 个事物。
2.对社会历史的批判。
上面提到的对社会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在英国以“社会历史学”为代表,在德国则以“ 结构史学”为代表)在整个欧洲都受到猛烈批评。
人们主要指责它将社会中的个人视为装在弹子盒中的玻璃弹子: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 被严格界定的群体,这样便可将社会视为所有群体的总和。这种方法尤其被运用于地方 志或城市市志的研究当中(参见孚雷Furet和多玛尔Daumar关于19世纪巴黎人口的研究) 。人们之所以批评此种方法,是基于下述两项原则。
(1)首先,一个人不能被简约为人们赋予其所隶属的社会群体的特征。
相反,每一个人都能运用来源于其分别隶属的不同人群的资源(如家庭的,职业的,友 人的,教会的资源)。若要理解他在政治方面或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抉择,就必须重建这 个复合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每一次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唯一的,都是为其所特有的。
这种意识自80年代起就在不断增强,不仅在史学界,而且在社会学界,大家都在质疑 将人们的行为动机简约为某种经济利益计量的研究方法。因而所有将其简约为经济利益 计量的研究形式均受到批评。形成悖论的是,一方面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大 举进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并试图证明经济利益计量决定论乃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普遍性原理,可以说明每个个人的特征。例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凯 瑞.贝克(Gary Becker)就曾论证说,人们的社会行为(结婚,离婚,犯罪)都源于某种实 用利益的考虑。同样,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试图证明理性游戏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各不 相同的历史情境,如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对立集团的林立现象和中世纪香槟酒集市贸易的 组织问题(参见阿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的研究)。针对这些将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归结 为“经济人”的研究方法,近些年来,学界不少学者批评那些认为个人行为仅仅是由经 济计量所决定的观点,批评那些根据人们的社会集团属性或阶级属性来解释个人行为的 做法。事实上,上述被质疑的方法由于严谨有余,由于其所认为的相同社会群体中的个 体具有同质性,个人行为具有同一性,因而令人信服,然而由于这些方法无视历史现实 和社会现实具有的异常丰富的多样性,它们同时亦具有欺骗性。曾经对历史学界部分历 史学家有过巨大影响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其研究成果亦受到批评, 因为他的关于“文化外观”的概念将个人的趣味,将个人文化上和休闲上的选择与特立 独行的策略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无法充分考虑到决定个人选择的异常多样的而 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行为动机。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阿尔贝.赫施曼(Albert Hirschman )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经济利益的概念只是在18世纪初以前才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 而且带有功利主义的内涵,因而批评者们强调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严格的历史规定性。这 样便为对古代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大量多样性理性动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道路,尽管这种 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历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个别学者对 所拥有的知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史料加以阐释和运用的问题,也就是对文化要素的“接 受”问题。米歇尔.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在其《日常的虚构》(1980)一书中 就是这样批评心态史研究方法的。他认为此种方法过于死板,因为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不 能由一次特定的某种思维类型来定性,况且思维系统是一个在与其它系统的交流中,以 及在对这些系统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系统。这种“接受理论”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 要成果便是在1980年前后围绕“大众文化”展开的争论。长久以来,历史考据学者常将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加以对立并认为各有其同一性,各有其内在逻辑。然而大量的研究 表明,这种内在的逻辑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的关系 错综复杂,根本无法加以截然区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尔罗.金兹伯格在其重要著作 《奶酪与蛆虫》一书中,通过对意大利宗教裁判所于16世纪对被指控为异端的磨坊主梅 诺乔(Menocchio)的审讯记录的研究,揭示出此磨坊主的文化结构是一个复合结构,它 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融合了多种文化要素,包括神话,迷信,古老的民间信仰,神学知识 和科学的基本常识。人类社会不仅仅截然分为富人与穷人,文化也不仅仅截然分为大众 文化与精英文化。
(2)此外,个人也决非孤立的存在。
一方面,他在某一对他而言是给定的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家庭网络),另一方面, 他也根据其需要和具体情境维护,改变和利用这一网络。这一来自美国社会学界的社会 网络概念自最近15年以来在社会历史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超越 上述结构史学的方法,并将社会活动者本人置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中心来加以研 究。
3.对模式的批判和对历史叙事的回归。
1980年至1990年间,人们常用史学的危机一词来描述当时怀疑主义和质疑一切的研究 氛围。这种氛围使人们进而反思历史学的地位及其科学性。当时的一部关键性的著作为 研究古希腊—罗马史的专家保罗·维内(Paul Veyne)所撰写的,自1971年起陆续出版的 《如何编写历史?——历史学认识论问题评论》一书。该书猛烈抨击了种种赋予历史学 以科学地位的企图。保罗·维内认为,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关注对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 的历史史实的研究,因而历史学家必须严肃对待这种性质。因此,历史学事实上毫不留 情地排斥那种建构在规律性基础之上的因果式推理,因为历史史实绝不会重复发生。这 种观点导致了两种后果。首先是对历史知识的某种相对主义认识,认为历史知识不属于 真理性范畴,而是与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和历史学家的选择密切相关,历史的真实因而 是无法企及的,历史学家只是在重构历史事件的情节,在撰写真实的小说而已。其次, 历史学知识的进步并不取决于永远属于主观范畴的历史知识的累积,而是取决于历史学 家反思历史问题的触角的延伸。具有创新意识的历史学家往往是对史料提出前所未提出 过的问题的人。保罗.维内常常以米歇尔.福柯的研究成果为例,说明他是如何在研究知 识和权力的历史性对峙的框架中思考个人与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发前人之未见的。我们 在此强调的是这种对历史科学的激烈批评与《年鉴》学派多年来关注的史学问题在某些 方面的不谋而合。保罗.维内的立场在法国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在于他的研究受到了哲 学家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的有力支持。利科尔在1983年发表的著作《时间与叙 事》中,以哲学论证的方式证明,历史学属于叙事的范畴。他甚至论证说,费尔南.布 罗代尔的历史学模式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尽 管奠基于著名的三个历史时间维度的结构之上,依然属于依据一些历史事件的情节建构 起来的叙事(情景叙述)范畴。这些批判不仅对今天在美国和欧洲历史考据学界占主导地 位的有关历史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念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而且对史书的编撰,对突出 历史叙事的贡献,对弘扬历史叙事的作用,皆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最近的一个例子便 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塔凯特(Timothy Tackett)所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 作。他在分析国王于1791年6月逃往瓦伦事件的后果时,认为有必要将其著作的一半篇 幅用于对逃亡事件本身的详细叙述,而这在10年或20年前简直是无法设想的。
三、个人、地方、事件
作为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宏观历史研究视野的反动,近几年来的历史研究深深打 上了对个人历史研究的关注的烙印。也许我们应从历史学家的这种转向(包括整个社会 科学界的转向,只有经济学为例外,因为自19世纪以来,系统地研究个人经济行为已成 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见出西方社会个人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的趋势,因为时至今日,对 作为一个既具整体同一性亦具特殊个性的个人的权利的尊重已成为重中之重的要务,无 论是就现在而言,还是就将来而言(退休,环保等),莫不如此,当然集体与政权机构的 权利相较而言却在削弱。历史考据学领域亦不例外,而且愈来愈倾向于认为对个人历史 的研究最有助于释清社会体制问题与社会运作的问题。
(一)个人和微观史学
自1980年至今20多年,史学界对个人的历史,尤其对其社会阅历的关注与日俱增。目 前占上风的观点是,鉴于社会现象的高度复杂性,历史学家若想对其有所理解,则必须 进行深入细致而且立足于一时一地的研究。甚至连那些极限性的历史情境也倍受史学界 的高度重视,因为它们能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理解社会的运作机制。正因为如此,混血 人群的问题在拉丁美洲才被研究得特别深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问题已然预示了 我们社会的未来,而且更为突出地揭示了当今人类学问题的根本机制(如联姻问题,跨 文化问题,体验不同文化差异的方式问题,社会统治和族群间关系的联系问题等等)。 同样,史学界,尤其在法国史学界,人们愈来愈注意研究奴隶问题。对此现象的理解不 仅与目前人们重新审视白人和黑人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一政治氛围有关,而且也与某种极 限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有关,恰恰是这种极限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的例外性特征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人身依附的诸种形式问题或抑制与反抗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种对个人历史的关注表现为对传记作品和自传的重新发现和解读。曾几何时,宏观 历史研究方法盛极之日,恰为传记类作品信誉尽失之时。然而米歇尔·福柯和阿兰·科 尔班(Alain Corbin)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建个人历程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传记类作 品的样式也为之一新,因为乔瓦尼尼·勒维(Giovanini Levi)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皆从 理论上告诫我们警惕任何形式的“传记性幻觉”:须知,若历史学家试图在某个人的生 平中重建内在逻辑联系而忽视偶然或巧合的因素,那么他将面临学术上不小的风险。但 是,人们对于传记作品的关注恰恰是因为,较之于对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研究而言,对个 人历史的研究更易于重建历史情境,重建个人所拥有的所有可供选择的机会,以便理解 这个个人作出决定其一生的决定的缘由或此种缘由的缺失。
微观历史研究的方法则为这种对个人历史的特别关注提供了说服力与理论内涵。这种 对个人历史的选择与重新思考社会历史的勃勃雄心并无矛盾之处。相反,这种选择恰恰 源于人们对社会历史研究特别忽视人际关系的重大作用这一点的不满。微观历史学者认 为,为释清人际关系的重大作用,惟有可能对其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的非常地方性和局 部性的史实,才会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真实,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构成。个人之所以占据 研究的中心位置,不仅由于他是社会的原子,是社会不可再简约的构成元素,而且还由 于在最好的情况下,学者能够掌握有关他的历史的详尽资料。这种微观历史学研究方法 与自70年代末年起便同时出现的数种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在德国有Alltagsgeschichte ,即生活史或日常生活经验史研究,在意大利则有microstoria,即微观历史研究;在 英国有thick description,即由克利弗·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的阐释性人类 学对史实进行“厚”描述的方法,还有在法国于90年代初由《年鉴》杂志提出的新的社 会史观(我们在下文中会继续对此加以讨论)。尽管其形式多样,然而微观史学的研究方 法近年来在欧洲历史考据学界已经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点,不 仅在于其对地方局部性史实的特别关注,也在于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前,大 多数学者的共识为,我们的社会奠基于经济活动之上,而现在,研究重点已转移至社会 问题,因为对社会问题的把握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体制,而且社会问题亦应被视为 用以解答社会其它领域中提出的问题的钥匙。因此今后史学的前沿学科即为科学的社会 学史,艺术的社会学史和经济的社会学研究。
60年代的社会历史研究所选择的目标为将社会历史的数据加以组织以便将其优化整合( 如行业问题,生产中的地位问题,财富的水平问题),然而它却完全忽视了个人行为问 题和在每每特殊且各不相同的情境中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问题。今天学者们的参照模 式已不复为经济学或社会学模式,而是人类学模式:人类学深入细致的史实描述所达到 的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与历史学家简化的图解式的研究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消弥这 一差距,微观历史学家们提议界定其研究领域的范围,以便将不同系列的档案文献加以 叠加比较,并最终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再现同一个个人的历史。此种完整的历史研 究不再是空中楼阁式的研究,而是脚踏实地的研究,旨在重建人们亲历的历史。这样做 并非为了再现“客观发生的”历史进程,而是为了重建个人社会经验的多样性。
这个社会经验的概念至关重要。在德国的社会生活史及日常经验史研究中,它甚至具 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内涵。这股思潮在德国为左翼历史学家所推动,他们指责结构史学研 究沿着黑格尔和韦伯的传统路径,对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社会阶层的历史倍感兴趣,却忽 略了被历史学遗忘了的人群,尤其是妇女。他们提出应该着重理解的,不是社会阶层或 团体,而是个人及其社会经验。这些历史学家们认为,每个个人生平阅历都是独一无二 的,每个人都建构其自身的价值系统:人民并非被动的被统治者,人民有行动的自由和 创造的自由。德国左翼历史学家们所参照的法国模式并非布尔迪厄,而是塞尔多。社会 生活史及日常经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要弄清楚为何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心安理得 地接受专制政体的统治,无论它是纳粹专制政体还是前东德的专制政体。这些历史学家 们试图解开德国政治的表现形态和工人的世界观之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夫·吕德 克(Alf Ludtke)的研究。他的分析揭示出,之所以德国工人能够适应于纳粹专制政体, 实在是因为工人们所认同的政治表现形态与纳粹的政治表现形态相去并不甚远,而纳粹 也在个人局部领域内而非从工人阶级整体出发给予工人一些自由的空间。
最为坚定的微观历史学家们认为,只有微观历史层面和个人层面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层面,因为正是由此而派生出宏观历史问题(如体制问题,社会阶层的意识问题等等)和 社会关系的总和问题。兹举例说明。莫里兹欧·格利波迪(Maurizio Gribaudi)在研究2 0世纪初意大利都灵市工人人口问题时,其出发点本来基于如下的观点,即这一社会阶 层乃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构成,因而都具有同质的工人文化素养(如阶级意识, 政治观点,与工作的关系等等)。然而他的研究结果却呈现出与出发点不同的结论:工 人阶层当时具有十分明显的多样性,因为每一个被研究的工人家庭都依据其所拥有的资 源而显示出其自身的经历,其自身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所采取的特殊对策及其所遭遇的 生活中的偶然变故。至于激励工人的群体意识形态,以及工人与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关 系,与其说是共同的社会地位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毋宁说是非常外在于此的因素造 成的,尽管这种因素具有“工人阶级”的同一性的表象。格利波迪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结 论说,若要理解社会阶层或群体,则需自研究个人和家庭始,而不是相反。
微观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受制于两大难题:
1.就史料而言,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史料最为丰富的个人(如卡尔罗·金 兹伯格所研究的磨坊主梅诺乔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曾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在案 ;同样,乔瓦尼尼·勒维的研究专著《非物质遗产》中的那个本堂神父,也是如此)。 这些个人因而是非典型性的,他们能够作为普通社会的代表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 而微观历史学家们则回答说他们既属例外又是普通人,换言之,他们的特殊性恰恰凸显 了普通社会被推向极端条件时的运作状态。然而无论如何,个别案例与普遍规律的关系 问题依然被提出来。以往受到涂尔干和西米昂启迪的历史考据学者们则是通过将个案的 多样性和特殊性置于其共同性之下考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使个案得以划分为 不同的系列供学者加以比较。
2.微观历史研究的分析是否有助于重建社会历史?
将考察社会的眼光反转过来,不再是自上而下地而是自下而上地考察社会,其理由虽 然不无道理,然而它是否就排斥社会也是由集体或群体的现实存在(宗教信仰,意识形 态,社会体制)所构成的这样一种观点呢?通过对社会网络的分析而形成的研究方法有助 于我们理解从微观向宏观的过渡,由个人向集体的过渡,这也是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获得 历史学家,而且也获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青睐的缘由。然而就研究个人行为的内在逻 辑而言,这种方法显然有利于对个人所作的微观历史研究。
(二)对历史事件研究的回归
如果说宏观历史研究与长时间历史阶段相联系,那么微观历史研究则与短时间的历史 阶段以及与历史事件(此处指社会生活的某一特殊时刻)相联系。首先,就历史资料而言 ,历史事件由于其特殊性的缘故往往导致许多与之有关的文献档案的产生。其次,由于 历史事件的非同一般的特点,作为一种反常时刻,比一串平淡无奇的时刻更能有助于我 们对社会的理解。这种对事物的新的认识说明了何以历史考据学者愈来愈关注于社会新 闻。总而言之,我们在此再度看到了“既属例外却仍不失为普通”的研究原则的运用, 只是此番不是运用于对个人的研究,而是运用于对历史事件的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短时间的历史阶段(一译“短时段”)从未在历史研究中消失。我们不 可忘记布罗代尔立足于长时间历史阶段的三重时间结构理论恰恰旨在帮助我们认清每一 个历史事件所承载的巨大的时间厚度,无论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统治,还是1571 年发生的勒邦特战役,莫不如此。然而不管这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一个王朝的统治) 还是一个例外的事件(如勒邦特战役),它们无疑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因为都是由于不 同时间性的特殊组合而产生的),但是它们同时亦总是相同的事件,因为它们都可以被 归纳为已知的不同时间性的组合作用的结果。有鉴于此,历史学家赋予长时间历史阶段 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优越性便倍受微观历史学家们的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优越性妨碍 了对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1940年至1945年德军占领下的法国”这样的短时间历 史阶段课题的研究(后一课题近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恰恰是一个极其特殊反常的 事件,有助于我们认清法国的一些深层次的本质特征)。应该说,微观历史学家们在此 类问题上有时的确言之有理。
这一赋予历史事件的新的认识论功能显示出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 此以后历史学家们便对历史事件的历史作用深信不疑。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历史 研究正在逐渐从历史时间决定论向被人们称之为“随机性”理论过渡,换言之,偶然性 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决定论者眼中,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因为它对历史长河的流向并无 影响;对偶然性论者而言,情形正相反,历史事件对历史长河有影响,因为历史长河的 流向恰恰取决于该事件的结局。每一历史事件表明社会历史有着多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而真正发生的历史只是其中某一种可能性的实现而已。这种将历史表述为多重发展方向 而且偶然性在历史对多重方向的选择中具有一定作用的观点,正在诸多领域的历史编写 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新的科学史的编写,基本沿用了与微观历史研究中某些 方面相同的思路:这样一来,科学史便表明,科学的发展演化并非由科学真理的不断被 发现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一些偶然性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取决于 科学界诸方人士的谈判与协商的结果。这就使科学史也演变成了“社会结构过程”的历 史。
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建议
《年鉴》杂志竭尽全力对各种编写历史的新方法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然而同时,杂 志对史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所侧重。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实践转折点
这一看似晦涩的术语指称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旨在将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范 畴”(参见贝尔纳·勒伯蒂Bernard Lepetit)来加以分析,换言之,就是认为对社会文 化特性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不可能来自于其外部的理论的甚至是哲学的分析,而是来自于 对该社会文化特性和社会关系的具体运用的研究。某一个人或某一社会阶层是如何界定 自身的,是如何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公布其社会文化特性的?问题在于始终从关注于具体 事实着手,研究在某些确定的情境中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这种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就是“ 社会角色”和“实践”。
“社会角色”概念的提出旨在与宏观史学的决定论决裂,并将自由与自主的权利归还 给历史舞台上的真正角色本人。事实上这一历史角色拥有与其可支配的多种资源(家庭 的,情感的,社会关系的和智力的资源等等)相对应的多重选择的可能性,他因而使用 这些资源以便适应社会并对他所面对的具体情境作出反应。在这个观察的背后出现了另 一个难题,即社会以何种方式保持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假如拥有真正的选择自由的历史 角色这个层次是一个正确的分析层次的话,那么如何解释社会并不构成一个在永恒的争 战中各自分散并对立厮杀的简单的集合体这一点呢?这个问题令我们联想到17世纪和18 世纪政治哲学家们就此所进行的带根本性意义的思考,而在今天,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 答。恰恰是这一点解释了何以历史学家如今特别关注有关社会协商的诸问题,如个人之 间订立的明白无误的或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的性质问题,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国 上下相对地同仇敌忾的深层原因问题,再如美国历史学家借助于博弈理论以便理性地理 解每个人是如何通过个人的利益考量与他人谈判协商并相安无事的问题。这里对如何将 历史角色纳入社会空间的问题,和对是什么导致了社会保持为一个整体的问题的双重思 考说明何以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关注政治问题。以往曾为历史考据学边缘化了的政治史研 究,重新成为历史学家们的思考重点,因为历史学家们认为政治史可以在今天重建最具 总揽各种社会组织形态能力的分析层次。
“实践”概念的提出是因为需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是因为将其视为过程而不是一种 固定不变的特性。因此,科学史趋向于放弃思想史而转向科学实践的历史,因为这将更 有利于理解科学真理是如何形成的。学界重新表现出的非常明显的对法律的关注也应该 在这个视野中加以考察。使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倒不是作为行为准则的人为法,而是实 践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文本与对文本的阐释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种关系都假 设历史上不同角色之间的谈判与协商,而各个角色的实践活动与对其权利的使用比规范 本身更为重要。
(二)分析尺度
任何一种分析尺度都不对其它分析尺度具有优越性,正如宏观分析尺度对微观分析尺 度而言不具优越性一样。重要的是运用不同的尺度作一种双重假设:一方面,在历史学 领域内,与某些物理学系统和数学系统(如经典几何学未予表示的不规则碎片形)不同的 是,每一种分析尺度都有助于作一次环境的改变,有助于显现出差异;另一方面,每一 种分析尺度都有助于产生出社会问题方面的意义。
西欧国家的形成的历史便构成了一个分析尺度的范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宏观历史 研究在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时总强调其两个特征:其一、国家即使在其孕育阶段,就已 经打上了其后才有的理性的烙印;其二、国家是自上而下地建构而成的,是由服务于国 家的官僚精英们强加给社会的。不久以前,历史学界微观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尤其是 围绕着网络的概念的方法,开始发展起来。微观史学批评宏观史学的方法,认为在长时 间内国家的权力更多地建立在王国内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支持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 在官僚制度及其官员的基础之上。此外,国家的地方政权很弱,所以国家始终被迫与对 手进行谈判并作出妥协。
这两种观点各自都有部分的真实性。如果说微观研究方法特别有助于通过社会群体理 解国家的起源,那么,它在思考国家所具备的,对于个人行动而言必不可少的“稳定的 ”集体形式时,却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假如我们不去研究17世纪绝对王权和“国家利 益”这一双重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这一在局部的微观研究中无法理解的双重观念,那 么我们便不能理解这一时期国家形式的飞跃发展。同样,在18世纪下半叶,对自由经济 的政策的飞速发展的分析离不开对地方局部层次的分析,因为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人们 会发现存在着对自由经济政策的强烈抵抗和自由经济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实践。然而伴 随着人口引进政策的实施的法国经济的这种深层次的变革,无论如何都是自上而下,由 开明的官僚和精英们通过与商业贸易界人士的协商与协议而加诸社会的,而其所依据的 原则,却是来源于宏观史学的原则。
(三)表现形态
这个概念目前在西方历史考据学界,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特别流行,其意义及其运用 也多种多样。而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与传统的倾向于将具有结构实体的现实世界与作为 表现形态(意识形态,文化)的主观世界加以对立起来的历史考据学有所不同的是,现时 的历史考据学则强调将这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同层次的世界统一起来的相互之 间的联系。在此视野中,即使我们尚无法给出表现形态一词的确切内涵,它亦已经获得 了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在此提出我们以为是至关重要的三种用途。
1.在60年代,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就所使用的社会历史研究的范畴问题发生了一场严重 的争议。
诸如罗朗·穆斯尼埃(Roland Mousnier)这样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使用研究对象所属 的范畴(或曰表现形态):如果说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社会由不同社会等级(教士,贵族 和第三等级)所代表,那么,这些等级范畴便是用以分析这一时期社会的准确范畴。而 诸如拉布鲁斯这样的另一些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这些内源性的范畴乃是一些意识形态的范 畴,他们还认为在每一社会内部是难识其庐山真面目的,因而必须使用来自其外部的范 畴来分析,特别是运用社会阶层的概念来分析。而今天历史学家们的视野与此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应该对社会赋予自身的表现形态和社会形象加以关注研究,同时注意到所有 的表现形态系统,而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强加于人的表现形态,而且还应注意到 以下的双重概念:
其一、任何表现形态都在表征社会的某一方面,而非其全部,而且是以间接的方式加 以表征的。
其二、这种表现形态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并由此进而对社会群体产生作用。
例如,1695年的人头税制度就是路易十四统治中期官僚精英们用以表征当时社会的十 分等级化的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象,若象夏尔·罗瓦索(Charles Loyseau)那样以绝对王权主义的法学家的眼光考察这一问题,那就只能是非常片面地把握该社会的全貌。然而他对该社会的理解仍不失其重要性,因为这种以社会地位等级的方式对一个盛行摹仿和攀比的社会所作的表征,必然会对社会中具有生机活力的部分产生影响。对这一点,启蒙时代诸多思想家已有描述,而诺贝尔·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在其著作《宫廷社会》一书中亦有相关论述。
2.社会表现形态有助于在微观史学研究和宏观史学研究的分析范畴之间建立起联系。
众人皆认同的社会表现形态(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社会集团话语)能够产生出群体 的文化特性。为史学界所深入研究的一个案例即为“喧闹”案例(这个词语指尤为16世 纪的法国的青年团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当老夫娶少妻时,年轻人以大声喧哗 的方式表达其对此所持的反对态度)。历史学家指出,这种表现方式有助于年轻人产生 某种群体意识,而这种意识在社会的构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3.社会表现形态有助于避免史学研究中的混淆年代的错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好地理 解古代思想的范畴。
我们不妨从经济现象史和经济思想史中举一些例子。在研究17世纪和18世纪的经济学 文本时,我们会饶有兴趣地发现,甚至连亚当.斯密的文本也都暗示有某种“正常的” 或“合适的”的经济行为的存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经济学范畴无法理解这些概念。然 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对18世纪大众心目中的“道德经济学”的研究 却表明,这些概念属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表现形态的一部分,而这种表现形态不仅非常 合乎逻辑,而且对人们实际的经济行为产生过影响。若我们研究17世纪和18世纪对商品 加以分类的文献和依据某些集体组织对商品质量所作出的评估对其进行排名的文献,我 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不将这些文本纳入当时社会和经济的等级化的表现形态 中加以考察的话,这些文本不会有什么意义。而1695年根据社会经济等级排列而设的人 头税制度也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特殊例证而已。
目前历史考据学又重新关注整体性历史学研究了,或曰“世界历史”,一如2000年在 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所表明的那样。这种重新关注的现象有时似有人为之嫌, 然而它却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使我们得以将微观历史研究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地方史志 研究纳入更为开阔的整体性历史研究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而整体性历史研究所关注的恰 恰是将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各种局部性地域性的社会实践加以比较。其次,它向比较研究 敞开了大门。往日马克.布洛赫曾力主进行比较研究,而今天,比较研究作为最有潜力 的研究途径之一,可以使我们避免微观研究的主观性并将能微观研究成果的意义加以扩 展。王国斌(Bin WONG)最近于《年鉴》杂志(2001年)发表的文章,就使用了地域的概念 来分析中国和东亚诸国的不同历史命运,是一篇独具慧眼的成功之作。他将西方的概念 用之于亚洲的社会历史空间(反之亦可),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地中海诸国和亚洲诸国 各自历史进程的独特性,而不至于落入简约化的文化主义的窠臼。他由此而证明了我们 所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中国历史学家还是欧洲历史学家,彼此都有充分的理由互相解 读对方的文明史并相互切磋探讨。
本文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于2004年7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举办的中法历史文化暑期班讲座内容之一。感谢葛涅先生授权本刊发表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