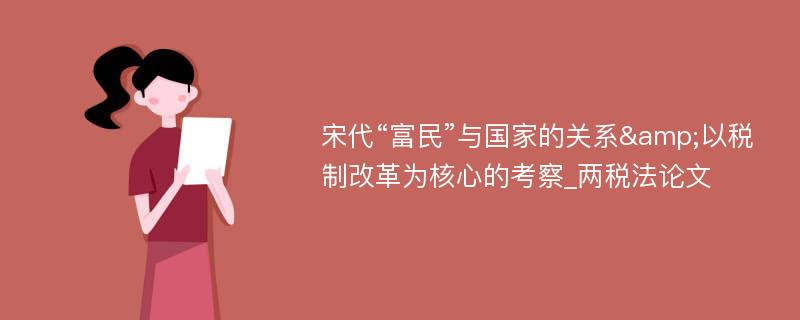
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制论文,宋代论文,关系论文,为核心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5)03-0019-09 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学界已对两税法改革的背景与目的、两税的内容及其由来、实施情况、作用和影响等方面作了深入探究。①笔者通过仔细、反复阅读中唐两税法改革内容,发现“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②中的“资产多者”,就是林文勋教授近年来倡导并致力研究的“富民”阶层。③不惟中晚唐,两宋时期国家赋税征收和职役征派,仍以民户土地资产作为计征标准。五等户制的完善与行用,④即是其明证。这就是说,自中唐至两宋,从国家税制规定来看,“富民”阶层因其占有资产较多,一直是向国家纳税的主体,这与我们对唐宋“富民”的相关认识,即“富民”是社会中间层和稳定层,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此,进而引发我们思考,如以税收制度及征税对象为研究视角,或可为我们探讨宋代“富民”与国家关系提供新的认识。 一、从人丁税到资产税 中唐以前,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源于人丁。租庸调以均田制为基础,规定每一成年男丁每年需向国家缴纳粟二石,无粟之乡,输稻、麦三石,是为“租”;“调”则根据本地乡土所产,缴纳絁、绢各二丈,绵三两,或者布二丈五尺,外加麻三斤;每一丁每年还需为国家服役二十天,若不服役,可以按“每日三尺”标准输纳,叫做“以庸代役”。⑤这种税制的征收计量单位为“丁”。以丁定赋,以“人丁为本”就是其主要特点。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税制弊端越来越明显。首先来自人口增长压力,民户每增加一位男丁,理论上就意味着国家授受土地要随之增长,但很显然,耕地增幅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以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关于土地授受的文书证实了唐代在西州、沙洲地区推行过均田制,但其授受田亩数额却远较文本所载“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要少得多。⑥在人口不断增加而土地开垦有限的现实面前,唐代均田百姓不能足额授受田土非常普遍。其次,国家关于授受田土(口分田)不能买卖的禁令也不可能完全遵循。百姓为渡过家庭生产或消费危机,不得不出卖土地以救急,先是世业田,进而扩展到口分田,豪强巨室则往往趁机贱买,土地买卖和兼并以此为契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不断扩大。在土地买卖和兼并迅速扩大社会背景下,一些豪强巨室“田连阡陌”,一些民户却贫困无“立锥之地”。但在国家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现存税制下,无田百姓仍得承担国家赋税,结果自然只能导致贫弱民户的大量逃亡。于是,唐玄宗时不得不依靠宇文融进行检括田户,但历史发展趋势强猛而不可遏止,其效果自然有限,并未能舒缓土地兼并和人口逃亡带来的国家财政危机。 安史之乱后,“丁口流离转徙,版籍徒有空文”⑦,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财政危机和对原有税收制度的破坏,官府不得不依靠各种科敛以满足财政所需。改革前“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泣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⑧,最终催生了建中元年(780年)的两税法改革: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费,申报出入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⑨ 杨炎的建言以诏令方式在全国颁行,标志着以户税(“居人之税”)和地税(“田亩之税”)为主干,分夏秋两季进行征收的国家赋税制度的建立。 两税法将中唐以来包括租庸调、户税、地税和各项杂税在内的诸多税收合并在一起征收,简化了原有税制;居住于当地的主户、客户、商人都被纳入征税范围,又扩大了赋税征收面,从而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是,新税制规定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国家不再以人丁,而是以“贫富”,即资产多寡作为赋税征收依据。陆贽为此总结两税法改革原则为“惟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这是两税法与租庸调最大的不同,同时也是新税制的最大特色。在这种新税制下,“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⑩,开始为人所共知并普遍接受,中国赋税制度史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作为在均田制崩溃、原有租庸调税制遭到破坏以后官府推行的一项新的税制,两税法变革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唐开天之际,社会经济获得持续发展,出现盛世局面。此时,不仅农业获得了大发展,百姓存粮增多,手工业、商业亦取得长足进展,迎来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随着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社会贫富分化也在急剧加大,出现了一大批的豪富群体,即“富民”阶层。(11)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富民”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又非国家官员等特权免税群体,已经具备良好的税源基础。但在国家原有以人丁为纳税依据的税制下,他们只用负担很小的纳税税额。相反,失地百姓本无更好经济来源,与“富民”人丁承担同样的税额,其不合理性已非常突出。因此,两税法确立以资产多寡为纳税多少的依据,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相符合的。“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既凸显出“富民”在国家税制改革中的重要位置,又达到了国家力图使百姓负担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立法目的。因此,相较于以往的租庸调税制,两税征收方式无疑是一种更为合理、公平和有效的税收形式。 两税法改革,以资产多寡作为纳税依据,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下社会贫富分化结果的认可,即对“富民”阶层崛起的认可。“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它指向的主要是财富占有者中的“富者”,而非“贵者”——“贵者”仍有一定的优免权。蕴含在这背后的逻辑昭示着“富民”阶层的兴起,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分化的结果。对此,学界已有林文勋教授等深入探讨,兹不赘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资产多者”进入执政者视野,既反映出“富民”力量的勃兴,也说明政府对这一新兴阶层的重视。两税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在富民阶层力量兴起以后,国家对“富民—国家”关系的规范与调整。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并没有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权观念,个人私有产权的发展极不充分。两税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财产权不完整和无保护的状况——以资产多寡定税,前提就是对财产私人占有合法性的确认。所以,逆向思考之,中唐通过两税法改革进一步确认了个人私有产权,也就是认可了富民财富占有的合法性。这样,税制虽然以富民为纳税主体,却为富民进一步寻求经济利益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根据近代西方国家与税收理论的相关认识,税收是国家与民众双方权利的让渡和权责转移,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富民以向国家缴纳赋税的方式表达了对帝国统治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并进而从这种合法性认可中得到国家对其自身财产的保护;国家则通过收取富民缴纳的赋税,以正常施政并维持国家政权统治,同时对纳税人予以国家保护。双方的这种权利与义务的让渡,让彼此关系显得融洽、稳定而持久。当然,在这场由官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两税法改革中,国家才是制度变革真正发挥作用的力量。也就是说,从两税法税制改革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富民—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力量为主导的。通过税收转让部分财富,使富民与帝制国家之间呈现一种共赢互惠格局,从而确定了以国家为主导的“富民—国家”关系。 二、资产税链条中的富民及其逃税、避税行为 宋代沿用两税法,但唐宋两税已有较大差别。(12)宋代二税田赋的征收,仍是资产税制。关于这一点,可由五等户制观之。“宋代制订乡村五等户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征派不同类别的徭役,同时与税制也有密切的关系。”(13)据已有研究,宋代乡村中的上三等户都是富民(14),且富民队伍不断壮大,分布范围很广,富裕程度很高,“中人之家钱以五万贯计之甚多,何足传之于史”(15)?“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16)。富民是国家纳税的主体,在宋人笔下有非常具体的反映,“凡有家产,必有税赋”,“两税履亩,乃是常法”(17),“有田则有赋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则赋役有轻重,亦常理也”(18),“夫有田则有赋,有力则有役,民未甚病也”(19),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宋代的两税征收原则仍是主要据地出税。那么,占有社会土地财富60%-70%的富民阶层(20),自然也就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据宋人程珌所言,宋代赋税征纳过程是“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21)。显然,这里的“巨室”就是广泛占有田土的富民,农夫则是租种富民田土的佃农。佃农通过租佃富民土地从事耕种,并将其中一部分产品以地租的方式交予富民,双方形成一种租佃契约关系。富民因为据有田土,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于是又将佃农缴纳的部分产品以赋税的方式上缴于国家,从而形成“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的场景。在这样的经济生产与产品分配模式下,小农与富民、富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22)。正因为富民可以“上当官输”,满足国家财政所需,又能“为天子养小民”,自然就被视为“州县之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下之所赖也”。关于富民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宋太祖有着清醒地认识,“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23)。这既表明帝制国家统治者对其统治权力的极度自信,认为“常岁科配,皆出富室”(24)的富民阶层,对其统治权力并未构成实质威胁,只要他们能够据实纳税,自然就是国之良民。受这样思想的指导,相较于宋太祖要处理帝制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其他弊端,诸如节度使专兵等唐末五代之弊,以土地财富和平地换取武将交出兵权,“杯酒释兵权”就显得理所当然。这同时也是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所推行的现实土壤。 因此,对于可以为国家输纳财富的富民群体,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士大夫群体以及统治者倡导呼吁实行“保富”就是一种正常的时代呼声。(25) 从赋税与百姓关系的角度来说,税收会减少百姓的经济收益,人们必然会对此有所反应,如逃税或避税,这在古今中外皆为理所当然。两税法改革虽然从一个层面上确认了富民对土地财产占有的合法性,从而促进了富民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但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向国家缴纳赋税多一分,就意味着富民田主的收益少一分。因此,和被视为良民的记载相比,宋代富民田主逃避赋税的记录同样突出,这样的富民常被目之为“豪横”(26)。 富民之不据产纳税,也常见于史籍。“今势家巨室,以不输王赋为能,相习成风,而有司惟困弱小户是征”(27)。甚至有豪民为抗拒缴纳赋税,将里正拒之门外,如“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输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28)。面对这种情形,有的地方官府直接将豪民名下的赋税均摊给租户,“富民之无赖者,不肯输纳,有司均其数于租户,胥吏喜于舍强就弱,而攘肌及骨”(29)。有的则采取以暴制暴方式解决,如胡顺之接任浮梁县令后,不仅怒斥“豪横”臧有金的暴力抗税恶行,“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耶?”当再三督催而不得时,“令里正取藁,以藁塞门而焚之”,同时又将臧氏家族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尽痛杖之”。自此以后,“臧氏租常为一县先”(30)。臧氏不交赋税就等于直接对抗官府(国家),一旦遇到胡顺之之类的强势官员,当然会遭受官府的弹压。类似情景,其他时空之下,间或有之,当非孤例。 相较于直接对抗官府,有些富民逃避税赋的方式非常巧妙。他们或在登录籍簿时直接隐匿资产,或以诡名而多立民户、子户、佃户方式隐匿田产户等。(31)富民的这一选择,与他们吃透了地、赋、役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关,“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故贫者鬻田则赋轻,而富者加地则役重”。(32)田土必须登籍于国家税册中,才能成为纳税和为国家服职役之依据。故而,欲逃避赋税,最佳的方案莫过于在源头上,即登录土地籍簿时就不据实登录——以多为少,或直接以有为无,既可免赋役征纳,亦可减少官府涉入。 不论富民以何种方式隐匿田产,都不是其单独的个体意志与行为,而是与基层组织头目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宋代,和赋税征纳相关的丈量田土与籍簿登录等环节,由于国家力量有限,常常是由基层组织头目,如里正、户长、乡书手和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贴人等进行具体操办。这些乡胥乡役人员作为纳税依据登录的具体执行者,在核实田土占有情况与登录作为纳税依据的籍簿时,其地位非常重要。因此,那些试图逃避赋税的富民,在田土核实以及以之为基础制订纳税依据的簿籍登录时,常常与这些乡职胥吏勾结在一起,通过他们上下其手,以遂其私。接受了豪富者贿赂或好处的乡职胥吏人员,常常在田土核实与籍簿登录过程中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他们对于豪民田土登录,常以多为少,或以高为低,以遂豪富逃避赋役之奸。这种逃税方式,非常隐蔽,故而也是一部分豪横富民逃避赋税的常用方法。不仅豪横富民与乡胥人员狼狈为奸,甚至就算依规输纳赋税者,由于与胥吏交结,得以“斛输斛,斗输斗;若众民户,则率二斛而输一斛,又或不啻。”(33)其中的复杂性,就更难以言说了。(34) 此外,两税法改革强化了土地私人占有的合法性,进入宋代以后土地买卖与交易已经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就是这种土地交易频繁的反映。国家对于土地交易的态度,不仅由以前的“抑兼并”变为“不抑兼并”,而且“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35)。“官为之司契券”,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税收的正常征收,客观上也是对土地产权的进一步保护。与此相关,这就要求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和土地关联在一起的土地赋税要随土地买卖进行推割。对地权变更与赋税负担的推割,主要也由乡司县吏等负责具体执行。在这一过程中,豪横与乡司也经常会勾结在一起,从而土地买卖及占有与赋税税籍变更不实,也随之出现,最终导致赋税负担的转嫁,加剧了一般小民的赋税负担。对此,宋代官员已有非常清晰地认识: 今夫一户之赋,官知其为赋之多少,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如此,则增损出入,惟其意之所为。官吏虽明,法禁虽严,而其势无由以止绝。且其为奸,常起于贸易之际。夫鬻田者,必穷迫之人,而所从鬻者,必富厚有余之家。富者恃其有余而邀之,贫者迫于饥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赋。有田者,方其贫困之中,苟可以缓一时之急,则不暇计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以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36) 贸易之际,产业的增损出入,直接关系到日后的赋税缴纳数额。理论上,应是赋随地移。但贫民迫于饥寒出售家中地土时,因救急之迫切,往往不得不接受富者提出的“少入其赋”的附加条件;富者为自己田土“免于赋役”,常以“收其少半之直”的“贱售”方式出让“数亩之地”,贪图小便宜的贫者往往中计。田土交易中的这两种情形,不仅扰乱了土地交易市场,国家赋税登记也因之“淆乱”。这一状况,自北宋前、中期起,就日益严重。具体而言,为保证国家财赋的如额征收,在官府督责之急的强权压力下,由于富户诡名挟户、诡寄田产等行为,“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从而造成土地占有与赋税负担的严重不平衡。这种现实,直接造成了社会动荡与不稳定。 另一方面,上述情形的普遍存在,也造成了对国家财赋的严重侵蚀,导致国库赋税收入的减少和地方财政运转之艰难。(37)据宋英宗治平年间修订的《治平会计录》记载,当时天下“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38)。南宋绍兴十年(1140),户部上言:“国家平昔漕发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万,和籴之数又在其外。而近岁上供之数才二百八十万,除淮南、湖北凋残,最甚蠲放之外,两浙号为膏腴沃衍,粒米充羡,初无不耕之土,而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究其原因,“此盖税籍欺隐,豪强巨室诡名挟户,多端以害之也”(39)。再以范围更小的局部地区来看,如华亭县,“浙右壮邑,岁入苗号逾十万石,实六万七千有奇,而县官岁督,才三万八千止。盖自绍兴经界,迄今百年,官无版籍,吏缘为奸,隐匿诡寄弊幸非一”(40)。 这些弊端,事实上形成对富民—国家之间稳定互惠关系的强烈冲击。出于正常统治的考虑,任何一个国家与政权对于这样的“豪横”均难以容忍。宋代国家的政策应对,既有对“豪横”富民的逃避赋税行为加以打压,也有对地方官员以及胥吏与豪横勾结贪腐行为予以惩处。但笔者认为,结合宋代若干史实记载,宋廷调整与富民的关系,最重要的举措仍然来自于不断完善和深化税制改革本身,借此实现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和对社会公平的促进。 三、深化税制改革与进一步厘正“富民—国家”关系 宋廷对豪横的打压,有严惩赋税逃避者,如上文所引浮梁县胡顺之对臧氏之举措;有严惩吏胥与豪富为奸者,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诸多例证。(41)下面主要讨论宋代国家是如何完善和深化两税税制改革,以及由此反映出国家处理与富民关系的深层意蕴。 富民阶层隐性逃避赋税行为主要来自对土地田产等登录环节。因此,对富民占有田土进行清丈,并据实登录纳税籍簿就显得非常重要。但北宋前期的籍簿整顿工作,并未进行田土清丈这一环节,而是沿用自前代通行的“自实法”——民户自己向官府申报所占田土状况,官府则据民户“自实”情况建立国家赋税籍簿系统。这样带来的问题,就聚焦于百姓实际占有田土的多寡,官府事实上很难准确知之。尽管税租簿等籍簿一年或三年进行更新,但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富民阶层在籍簿登录与更新过程中,通过与吏胥进行勾结,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籍簿管理的混乱,从而导致赋税不均。不过,鉴于宋初国家赋税尚能满足财政所需,社会关系仍较为稳定,籍簿登录与实际占有田土不实,以及赋税不均尚未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北宋仁宗时期,财政开支持续增大,田赋收入却有缩减趋势。官府财政收支的背离,表明富民阶层逃避国家赋役的状况正日益普遍化。宋廷上下对“豪横富民”主导下的田赋不均现象严重后果产生了共识,部分官员提议要清丈田土,实行方田。对此,宋廷的做法较为审慎,先是郭谘、孙琳首创了千步方田法,在洺州肥乡县进行试点,“四处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42)。欧阳修对千步方田法予以了高度评价,“括定民田,并无欺隐,亦不行刑罚,民又绝无词讼”,建议扩大试点。随后郭谘均蔡州,田京均无棣,蔡挺均聊城、高唐,掀起了一次清量田土的小高潮。但可惜的是,方田行动最终因“重劳人”而罢。(43)嘉祐(1056-1063)时,包拯为三司使,也曾派人到各地清丈田土,随后也以“天下不能尽行”为由而草草收场。(44)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清丈土地的敷衍了事,固然与清丈田土耗费成本较大有关,但“富民”阶层隐蔽于文献背后的种种抵制与反对,显然也有极大关系。这也表明,在围绕赋税分割的利益博弈中,“富民”群体正在日益破坏与国家双赢的互惠局面。 宋神宗与高宗时期,宋廷进行了两次由官府主导的大规模田土调查与清丈工作,是深化和完善两税田赋制度的重要改革。 1.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因患田赋不均,在王安石主持下推行方田均税法。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此次方田均税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确定了方田单位;二是确定了方田时间,为秋季收成之后的九月开始推行,或“岁稔农隙”推行;三是确定了方田的组织体系,先是由县司官员主管土地丈量工作,后来选任专职方田官,每方差派大小甲头,连同方田户一起方田;四是确定丈量土地类型与分等原则,如土地分“陂原”与“平泽”两大类,对土质又区分“赤淤”或者“黑垆”,然后根据土地肥瘠程度,划分为五种等级,分别课以不同税率;五是设立了方田田土地标,“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六是确立了方田田亩色等公示制度;七是根据方田丈量结果,编制民户田土信息的方帐、户帖、庄帐,官府以契印认可,再据此编制版籍。(45) 2.经界法。经界法是宋高宗时推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田土调查与清丈工作。绍兴十二年(1142),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书言经界不正之害,经高宗首肯后,次年率先在两浙路推行。李椿年的经界法与北宋方田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设置了专门机构“措置经界所”,根据田土高下划分田等,编置成资料登记册等。但经界法与以往方田最大的不同在于,编制了更为细致的土地资料籍簿——砧基簿。 编制砧基簿之前先要“画图”,“画图”或由田主自实自绘,或请人绘制,还须注明亩脚数字、四至、地势、肥瘠、税率和税额等,然后田主和佃客在“画图”上逐丘计亩脚,依次押字,保正长则在地图四至押字,责结罪状,申报经界措置所,等候差官覆实。这些图页集合起来,就构成“草图”。地方政府再将草图照謄成四份“正图”,每页加盖一印章,一份发还田主,其余三份,按照乡、都、保装订成册,“一本在县,一本在州,一本纳转运司”,以之作为田土产权证明书、推割文件与备查档案。(46)正图就是砧基簿。砧基簿对田土资料登记的翔实程度显然要远甚于以往方田时推行的户帖制度。经界之后砧基簿的推广,导致了南宋户帖制度的逐渐消亡,户帖为砧基簿所取代。(47) 宋廷进行的这两次大规模清丈田土和整顿土地与税籍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方田法从熙宁五年到元丰八年十二年间,先后在开封府界、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推行,大致上长江以北除京西路都已波及。(48)“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49)。经界法自绍兴十三年(1143)两浙路首行,到绍兴十七年(1147),除沿边或地广人稀的两淮、京西、湖北等路及福建漳、泉、汀等州外,东南经界大体完成。之后在四川地区推广,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除沿边泸、叙、长、宁等州外,川蜀其他州府也已进行完毕。宋孝宗以后,如朱熹等一些地方官员,仍不断在福建等未经界等地推行经界法。 这两次大规模田土丈量和调查工作,一方面清理出大批隐漏田产,另一方面又根据调查情况,将每一田土所含的具体信息,包括田主姓名、面积四至、土地色等、高下肥瘠,甚至纳税税额等,一一作了登录,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土地信息登记簿册。这些地籍簿册在北宋时为户帖、至南宋发展为更加细密的砧基簿。北宋时的户帖主要是民户自执的土地产权信息执照,官府一般依据民户户帖建立专门作为征税依据的税租簿。户帖为民户土地单一凭证,税租簿乃是统计一县内民户户帖信息制成的纳税簿册。砧基簿则不同,它既是民户土地执照,也是土地信息登记表,还是纳税征税依据,一定程度上和税租簿有交叉重合。砧基簿除民户自有底本外,还有三册,“一本在县,一本在州,一本纳转运司”(50)。方田和经界对田土占有与地籍图册和税租簿三者的对应衔接,有效地弥补了自两税法改革以来国家税制方面的缺漏。并且宋廷的这两次大规模田土清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私两利”——大量为富民或豪强所隐占的田土借此重新登录到国家版籍系统中,国家则借此增加了田赋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田赋不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宋廷主导的丈量田土、税籍籍簿登录等工作,同时也是国家在赋税问题上进一步厘正与富民关系的重要举措。 两税法改革以来,国家税制原则由人丁转向资产,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富民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富民藉税制改革得到了国家对其占有财富与私有产权的认可和保护,双方由此建立了共赢互惠关系。但就如前文所述,在获取收益一定的条件下,百姓每多缴纳一分赋税,即意味着自己收益减少一分,因此逃避赋税不可能得到真正根治。尤其是国家税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些相关环节的缺漏,为百姓——主要是“富民”逃避赋税提供了方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逃避赋税行为高涨。富民阶层在宋代的逃避赋税,对国家财政损害尤大,赋税负担的转嫁又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因此,如果不从完善国家税制建设本身深化税制改革,单凭国家对逃税避税行为的打击,不仅会加剧国家行政成本投入,而且不利于国家财政的持续稳定增长,进而侵损和动摇国家统治基础。这样,我们看到,宋廷并未重新更改税制,而是继续秉承两税法税制原则,即仍以田土资产多寡作为征税标准,但其重要推进之处在于,宋廷对两税税制的主要缺漏进行了修补,进一步完善了两税税制。宋廷进行以方田和经界为手段的深化税制改革,就是其将之进一步往前推进的实际举措。蕴藏于其后的逻辑显示,宋廷对富民阶层在国家财赋构成中的重要性认识并未改变,仍认为他们是国家主要税源,仅从调整和深化税制而言,也表明它并无意更改或破坏其与富民之间构筑的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共赢互惠利益格局。 富民阶层对宋廷此举的反应并不一致。李椿年在浙东、王之望在四川推行经界时,均不断有“富民”上京诉其扰民,以此表示对深化税制改革的阻挠与反对。事实上反映出豪横富民与国家之间仍在不断进行博弈。但富民阻挠税制改革与国家展开博弈的手段并不高明,也不猛烈。他们以向上级官员或朝廷“诬告”的方式表达对主导执行丈量田土官员的不满,冀图朝廷罢免改革官员;或者通过与乡胥人员、地方官员勾结的方式反对改革推进,或者在改革推进过程中继续舞弄各种手段,使清丈工作难以开展进而影响籍簿登录等——但是,富民并未因此揭竿而起,公然叫嚣,反对帝国的这一压制自己持续富庶的政治举措;恰恰相反,两宋期间民乱暴起者,多非富民;相当多的富民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的建设之中,且乐此不疲,自以为理所当然,对帝国的持续性发展和稳固,起到了固本强根之绩效。(51)而宋廷对于“富民”们在阻挠税制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小动作,常常不以为然,并没有采取断然镇压等手段。这也表明,国家在厘正与富民阶层关系的税制改革过程中,虽然一些豪横富民的行径较为恶劣,但宋廷并不认为整个“富民”阶层都是与其对立的异己力量,富民也未因帝国的限富举措而叫嚣变乱。富民所采取与国家博弈的小手段,也是在国家统治秩序的规范之内。 因此,宋廷藉方田与经界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的推进,所反映出来厘正与富民阶层关系的新举措,仍是延续着两税法改革以来的“国家—富民”关系而来。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富民与帝制国家之间并非此进彼退、相互对立的两极,二者仍然是包容于一体,可以共赢互惠、共利并存的统一体。 两税改革,乃至持续到宋代进行的方田与经界法,都是属于唐宋帝国主导的不断完善田土资产税为目的的税收制度。在这一税制下,“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成为人所共知的税收制度。该税制的不断完善过程,反映了富民阶层不断被纳入以国家为主导的“富民—国家”新型利益关系格局之中,最终成为向国家纳税的主体对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群体。另一方面,新税制的核实,反向证明了国家对富民占有财富的认可,又为富民阶层的进一步扩充力量提供了法权基础。总体而言,尽管富民与国家之间围绕财赋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与斗争,但二者的博弈事实上都是在帝国许可的范围之内,并且为了防止富民利用税制漏洞,宋廷不断强化和完善税制改革,从而构筑起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富民—国家”共赢互惠体系。宋代富民阶层力量较之唐代明显壮大,以及以富民为主体创造的高度发达经济,无不表明,新税制的推行并未成为限制富民发展的羁绊,相反,由新税制变相确立和认可的私有产权,将宋代富民与社会经济带到了全新的高度。 ①参见陈明光:《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 ②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华书局,2006年,第722页。 ③参见林文勋、谷更有著:《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所著《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相关论著。 ④根据民户资产划分不同的户等制度,并非起始于宋。早在唐代,就已经有沿袭前代“三等九则”制而制定的九等户制。九等户制到宋代演变为五等户制,而其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是以全体乡村民户为划分对象,后者则是在主客相分基础上对主户的划分。参见邢铁:《户等制度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6《食货六》赋税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106-108页。 ⑥参见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西嶋定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实施情况:以给田文书、退田文书为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⑦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3《田赋考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65页。 ⑧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8《杨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20页。 ⑨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8《杨炎传》,第3421页。 ⑩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华书局,2006年,第722页。 (11)林文勋、谷更有著:《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3页。 (12)李剑农指出:“唐代两税的户税与地税,是资产两税,宋代两税则仅仅只是田地二税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重印本,第204页);另请参阅梁太济《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代两税的异同》(原载日本《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今据氏著《两宋阶级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邢铁:《户等制度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14)漆侠:《宋代经济史(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83-303、371-374、565-581页;柳田节子:《宋代乡村的户等制》,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第189-270页。 (15)吴萁:《常谈》,台湾艺文印书馆,1964年。 (16)苏辙撰,曾枣庄等校点:《栾城集·三集》卷8《诗病五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页。 (17)《袁氏世范》卷3《治家·税赋宜预办》,国家图书馆藏宋本,第19页。 (18)《历代名臣奏议》卷259《赋役》,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3404页。 (19)程珌:《程端名公洺水集》卷9《书金华义役册后》,四库全书影印本。 (20)薛政超:《唐宋以来“富民”阶层之规模探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1)王柏:《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页。 (22)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 (23)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祖宗兵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24)《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41,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 (25)关于保富论的具体论述,请参阅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3—327页。另见林文勋:《中国古代的“保富论”》,《历史教学》2006年第12期。 (26)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台北《新史学》4卷4期,1993年12月。陈智超:《南宋二十户豪横的分析》,收入邓广铭、徐规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善军:《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27)王柏:《鲁斋集》卷5《送曹西滁序》。 (2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6《胡顺之》,中华书局,1989年,第109页。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丙申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2189页。 (29)《宋史全文》卷26上,淳熙四年十二月甲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7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丙申,第2189-2190页。 (31)参见王曾瑜:《宋朝的诡名挟户》,《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4-5期。 (32)《苏轼文集》卷8《策·策别安万民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页。 (33)《陆九渊集》卷8《与张春卿》,中华书局,1980年,第105页。 (34)参阅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刁培俊等《“税赋弊源皆在乡胥之胸中”——南宋中后期东南路分乡司在赋役征派中违法舞弊的表现及其社会内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5)《历代名臣奏议》卷54《民事上》,第764页。 (36)《苏轼文集》卷8《策·策别安万民四》,第261页。 (37)参阅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4-136页。 (38)《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第98页。 (39)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9,绍兴十年六月戊子,中华书局,2013年,第2814页。 (40)袁甫:《蒙斋集》卷14《华亭县修复经界记》,四库全书影印本。 (4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惩恶门·豪横》,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473页。参阅前揭陈智超、梁庚尧、王善军等已有研究。 (42)《宋史》卷326《郭谘传》,第1053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4,庆历三年冬十月丁未条,第3482页。 (43)《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第99页。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八月己丑条,第4590-4591页。 (45)《宋史》卷174《食货上二·方田》,第4199-1200页。另可参见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等论述。 (46)《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3840。 (47)刘云、刁培俊:《宋代户帖制度的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宋朝部分时空下还出现有鱼鳞簿和鱼鳞图,当也是配合方田经界而设者,且得以普遍推行,参阅王曾瑜:《宋朝的鱼鳞簿和鱼鳞图》,原载《中国观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1期,今据氏著《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8-581页。 (48)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210—211页。 (49)《宋史》卷174《食货上二·方田》,第4200页。 (50)《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40。 (51)20世纪以来,有关讨论,相当繁复,兹不赘述,较近研究,请参阅王世宗《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刘馨珺《南宋荆湖南路的变乱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9年,1994年,并黄宽重《宋代变乱研究的检讨》,收入氏著《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有关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请参阅美国学者韩明士(Robert P.Hymes)《官宦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台湾学者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原载《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入邢义田、黄宽重、邓小南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黄宽重《人际网络、社会文化活动与领袖地位的建立——以宋代四明汪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张文《济贫恤穷活动与宋朝民间社会的兴起》(《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