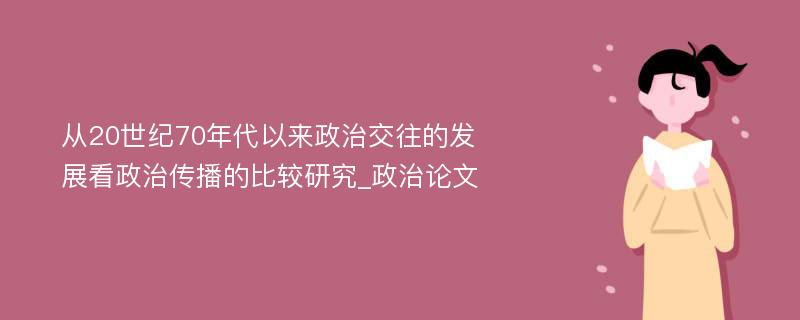
试论政治传播学的比较研究——从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发展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政治论文,试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8-0021-05
自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以来,其竞选团队擅用互联网力量组织传播活动的经验,几乎已成为世界各地媒体传播或公关营销人士的学习案例。在全球化的今天,来自美国的政治传播专家们被各国政府高薪聘请,指导协助政府进行有效的政党竞选、政治传播或危机管理。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已突破了原有的仅关注选民个人行为的媒体效果研究,逐渐向大众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系统性角色研究扩展。①在这样的研究趋势和实践中的美国化倾向下,本文着重强调政治传播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呼吁政治传播比较研究应当在全球化时代获得学界更多的重视和关注。这里,本文对政治传播的定义引用美国学者Graber的论述,即“对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产生鲜明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②比较研究则指“对两个或更多不同地理或历史定义的系统进行比较,这些系统中与研究兴趣相关的现象则植根于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之中”。③
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横纵向拓展
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转折点。因为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对媒体与民主政治体制的宏观结构性关系的考量,政治传播学获得了一次重生。正如Graber所指出,政治传播学始终是建立在媒体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断之上,即“信息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机制、以及所有这些存在的社会大环境有鲜明的政治效果”。④但是,自从李普曼(Lippmann)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政治传播研究的议题之后,政治传播学对于媒体效果研究的核心却一直在变化之中。从早期传播学奠基人的研究活动中不难看出,70年代之前的政治传播重在从微观领域研究和分析媒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选民行为的影响;70年代之后,对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则逐渐占了上风,从横向和纵向上都对媒体个人效果研究进行了重大拓展。⑤
横向拓展:争辩“媒体抑郁论(media malaise)”
政治传播学的横向拓展主要由70年代以来关于“媒体是否是造成公民对政治冷漠的元凶”的争辩为代表。在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的基础上,70年代的传播学者们开始把媒体的个人效果研究与影响媒体内容的结构性因素研究相结合、把媒体对选民的个人效果研究与媒体对政治家的个人效果研究相结合,从而大大拓展了政治传播学的视野。作为这股研究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抑郁论”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媒体在美国的流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这种理论认为“由大众传媒和政党竞选主导的政治传播行为阻碍了公民参与,使公民对公共事务缺乏了解,对政府失去信任,对政治活动失去兴趣”。⑥1968年,学者Michael Robinson主导的一项受众调查显示,完全从电视新闻中获得政治信息的人要比只从电视新闻中获取部分政治信息、或者不从电视新闻获得政治信息的人更加愤世嫉俗地对待政治和公共参与。⑦这项调查使水门事件之后的美国人更加相信,电视是导致投票率下滑、公民对政治“抑郁”、失去兴趣的主要原因。到了90年代,“媒体抑郁论”在传播学界几乎已成为一种不需要证明的共识,大众媒体被打上了对公民参与政治具有负面作用的标签。⑧1997年,学者Cappella和Jamieson出版了产生广泛影响的Spiral Of Cynicism一书,他们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数据指出,现代媒体对政治信息的报道不再是一个个单纯的“事件”,而是经过了媒体的“战略性构建”,人们越多接触这种被战略性构建过的信息,就会越反感政治,更加愤世嫉俗,因为人们能够从这些信息中理性地分辨出政治家们的真正动机,从而拒绝参与到这样的政治过程中。⑨
然而,“媒体抑郁论”并非无懈可击,它也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和反思。正如学者Norris所指出,“媒体抑郁论”的最根本缺陷在于其对受众的假设。“媒体抑郁论”中的受众完全被动地接收政治信息,没有能力作出理性的信息选择。Norris对美国以及欧盟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状况和媒体使用状况进行调查后指出,人们接触媒体未必只带来负面效果,相反会有正面效果。她的研究显示,如果人们越接触媒体,得到的政治知识就越多,就会更加信任和参与到政治中。这种积极的“正面循环”效果可以由受众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来解释,因为那些本身就很积极参与政治的受众会积极地选择接收媒体传播的政治信息,从而更加积极参与政治。⑩她指出,针对公民对政治失去兴趣和信任的现象,与其责备作为传播者的媒体,还不如更多思考政治制度本身的深层次问题。
不过,新闻媒体是否应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下滑负责至今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学者Norris的“正面循环”理论虽然一定程度上批驳了“媒体抑郁论”,但其本身也不断遭到学术批评和发展。其中重要的一点批评是,Norris的“正面循环”理论没有考虑到媒体对政治家行为的影响。学者Meyer指出,媒体时代的政治家们已懂得如果按照媒体的要求管理自己的形象,从而导致了政治体系为了适应媒体舞台的要求而“戏剧化”。他认为,当民主政治体系有赖于公众的支持、而公众的支持又有赖于他们从新闻媒体获得的信息,民主政治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传媒的影响,成为一种被传媒“殖民”的政治。(11)公民也因而更加难以获得真正的政治信息并参与公共事务。
纵向拓展:媒体的系统角色
对传媒的系统性角色以及受众的个人心理过程的研究是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纵向拓展的最重要体现。就大众传媒的系统性角色而言,“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和“霸权模式(Hegemony Model)”是两个产生深远学术影响的理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中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传模式”,认为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权力的不平等对媒体的传播内容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12)他们指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这些“过滤”机制包括:媒体产业的所有权和利润追求;广告成为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信息来源主要被控制在金钱和权力手中等。
与“宣传模式”将大众传媒完全看成是统治精英的宣传工具不同,“霸权模式”认为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斗争、妥协、达成共识的变动中的领域。学者凯尔纳(Kellner)从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理论出发,分析认为统治阶级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和统一的,而是在不断的斗争和商议中形成霸权的意识形态,因此大众传媒的系统性角色也不是“宣传模式”所强调的完全被动的宣传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商议过程,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改变或抵制统治精英。(13)
全球化潮流强化政治传播比较研究的价值
在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横纵向发展背景下,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当代政治传播研究最有价值的视角之一。比较研究的兴起与政治传播学转向宏观研究的历史机遇相契合。早在1975年,学者Blumler和Gurevitch就指出政治传播学界缺乏比较研究的视角,并呼吁建立政治传播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经过90年代的蓬勃发展之后,比较研究在当今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已逐渐成为一股潮流。(14)正如学者Hallin和Mancini所指出,比较研究在概念构建和因果推论方面具有重要学术贡献。(15)它在回答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主要学术问题和应对全球化对政治传播学的挑战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概念构建:来自全球化的挑战
媒体环境和政治环境既是政治传播研究的背景、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它们的变化对媒体内容和媒体效果都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现代政治传播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上世纪末以来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和后果。政治传播学的很多理论和概念都建立在对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中的现象研究基础之上,而这些概念可能将随着全球化浪潮过时,急需理论创新。(16)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正在逐渐趋同,朝着学者Hallin和Mancini所称的“全球同质化”演变。(17)这种政治传播的趋同过程被学术界用全球化、现代化或者美国化来概括。相比美国化强调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单向影响,全球化的概念更加着重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传播体系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18)现代化的概念则在外界影响的基础上,强调一国自身的内部发展也是各国政治传播逐渐趋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国际媒体产业的日益集中化,也加剧了媒体机制融合的速度。虽然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媒体产业的集中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十年,新一轮的媒体产业化和媒体市场开放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19)另一方面,各国的文化差异和结构性差异仍然对政治传播研究有重要影响。正如Graber指出,文化差异是21世纪政治传播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政治传播实践有巨大的差异,尤其是非美国文化之下的政治传播研究至今仍比较缺乏。(20)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比较研究因其对“共性和异性的强烈敏感度”而对政治传播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21)它不仅能够提醒研究者们避免简单的模糊概括和推论,也能够鼓励研究者们超越一国一地的具体经验而去探索更加普遍的规律。Blumler等学者称比较研究是“黑暗中的一跃”,它使研究者们越过自身所处之地的局限,注意到那些在自身社会系统中不曾被注意到的现象,或者通过与其他系统的比较而获得一种新鲜的视角来观察自身社会系统中的传播现象。(22)比较研究可以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检验那些由西方社会体系建立起来的、曾被认为是普世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从而避免直接套用传播学理论和概念的简单假设。(23)例如,自9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各国政党竞选中的政治传播比较研究逐渐增多,虽然美国模式几乎被认为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统一模式,但实际上欧洲各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尽管与美国趋同、仍有相当大的区别。(24)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不少学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强烈批评一概以美国模式为中心的政治传播研究范式。(25)
因果推论:社会现象的系统关系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者们就媒体对公民参与下滑是否负责的问题以及媒体的宏观系统性角色反复讨论。虽然学界在媒体对于政治演变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上早有共识,但就媒体和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长期存在争议。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比较研究更加擅长于回答社会现象之间因果推论的研究课题。目前在政治传播学领域,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还是内容分析、问卷调查和试验。但如同Norris所指出,这些研究方法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26)内容分析是用来分析政治信息的最常用研究方法,但是样本的选择可能很难代表所有新闻媒体,内容分析的结果也无法代表受众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接受状况;(27)问卷调查可以了解受众的观点态度,但这只是受访者在调查那“一时一地”的观点态度,并且难以掌握受众的媒体消费的不同详细状况:试验的研究方法则面临着如何将试验结果合理地推论到整个现实世界中的问题。(28)
然而,比较研究因其着重于从系统性的角度观察和解释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而对因果推论的课题具有特殊价值。要证明一种社会现象是另一种社会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比较这个社会现象同时存在和不存在的结果。(29)所以,因果推论要求研究者们分析在同一个社会系统或者文化背景中很难被发现的一些系统性变量。比较研究善于发现宏观制度因素的影响,成熟的比较研究并非仅仅是对不同社会系统和文化背景中单一分散的社会现象进行比较,而是关注为什么这样的社会系统和文化背景会产生这样的社会现象,从而进行宏观的比较和推论,揭示不同政治传播实践的制度性原因。例如,学者Jeffrey Alexander通过对美国报业历史的分析得出结论,工人报纸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是新闻专业主义强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个结论却遭到比较研究的质疑,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北欧,工人报纸和新闻专业主义都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30)
案例分析:英美政党竞选传播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此处以英美两国政党竞选传播的比较研究为例,简析全球化浪潮下比较研究对于政治传播学术发展的价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Semetko等学者就依据可能影响新闻传播在政党竞选中作用的系统性因素,设计研究框架并对英美两国的政治传播进行了对比。(31)这个研究框架中包括的系统性因素有:政治和政治家的社会角色,新闻记者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一般态度;竞选运动的专业化水平;媒体竞争的程度以及媒体的商业化或公共服务倾向。结果显示,英美两国的政治传播有明显的区别,尤其在竞选运动的电视报道方面。英国的电视报道仍主要以政党、政治话题为中心,媒体对政治相对尊重;而美国的电视报道则更多地以记者的个人评论为中心,竞选本身则被娱乐化成“赛马(horse-racing)”。也就是说,美国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干预更深,美国政治的“媒体化”程度更浓。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英国的政治传播以及政党竞选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朝着所谓“美国化”的方向演进。随着撒切尔夫人首次将“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从美国引入英国,以及布莱尔带着“电视神童(TV genius)”的昵称登上权力的最高峰,媒体在英国政治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美国化”。学者Blumler和Gurevitch运用早年Semetko等人提出的研究框架,对英美两国的政党竞选传播现象分别进行分析,界定两国的异同之处,并对作为比较基础的研究框架本身提出修订,从而对“美国化”的概念进行反思。(32)他们的研究表明,英国的政党竞选传播确实有“美国化”的倾向。一方面,英国政治家像美国同行一样“专业”对待新闻媒体和选民。这体现在政治化妆师和公关专家地位的提高、新闻管理得到更高重视、传播因素和传播从业者对政策制订的影响加深、政党形象逐渐符号化成领导人的个人形象等。另一方面,英国媒体也更加独立和强势地参与到政党竞选的过程中,和美国媒体类似,出现在竞选报道中的一些著名记者或评论员甚至比政党候选人本身还要耀眼。但是,两位学者同时指出,英国政党竞选传播中仍存在“美国化”无法解释的特征。这包括两国政党竞选的资金来源不同、媒体商业化程度不同及其对政治报道的影响、竞选报道的数量、竞选报道内容的多样化程度、主流新闻界的创新和发展等。
更进一步的是,Blumler和Gurevitch对比较研究框架本身提出了修订。首先,两位学者肯定了一些比较项在当今仍需要重视甚至需要加强,比如竞选运动的专业化水平(政治化妆师、公共关系、政治营销等)、新闻媒体对政治过程的干预、新闻从业人员对政治及政治家的基本态度(批判、实用主义、抑或基本上实用主义偶尔批判)。其次,两位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比较项需要加入到研究框架中,包括政治文化(对多样性拥护或抵制的程度)、非主流传播渠道的控制管理以及非英美体系之外的制度因素。
结论
比较研究对政治传播学来说意义重大,但成功的比较研究并不容易做到。研究者稍有不慎,很可能使整个研究失去意义。所有有意义的比较的一个基础就是“被比较的事物是真正可比较的”。(33)一般说来,被比较的两个国家或体系不能太不相同或者太类似;如果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维度的,只对其中之一进行比较而不提其他,也会给研究结果带来风险。就政治传播学而言,比较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难度变得更大,因为国家和社会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独立、封闭的系统,研究者们通常比较难界定真正被比较的对象。(34)不过,尽管有这些限制和缺陷,本文认为,比较研究仍然应在未来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中获得更多的重视。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政治传播学发展已经越来越依赖比较研究的发现和成果。
[收稿日期]2009-07-25
注释:
①⑤Mcleod,J.M.,Kosicki,G.M.,Mcleod,D.M.(1994) The expanding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effects',in Bryant,J.,Zillman,D.(eds.) 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pp.123-162
②(20)(27)Graber,D.A.(200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aces the 21st Century',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479-507
③(22)(33)Blumler J.G.,McLeod,J.M.,Rosengren,K.E.(1992)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Blumler J.G.,McLeod,J.M.,Rosengren,K.E.(eds.) Comparatively Speaking: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Across Space and Time,Newbury Park,London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pp.3-18
④Graber,D.A.(1993)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cope,progress,promise',in Finifter,A.W.(eds.) Political Science: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Washington DC: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pp.305-332
⑥⑦⑧⑩(26)(28)Norris,P.(2000) A Virtuous Circle: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⑨Cappella,J.,Jamieson,K.H.(1997) Spiral of Cynicism: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Meyer,T.(2002) Media Democracy:How the Media Colonize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12)Herman,E.S.,Chomsky,N.(1988) A Propaganda Model in 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New York:Pantheon Books
(13)Kellner,D.(1990)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Colorado and Oxford:Westview Press
(14)(21)(29)(30)Gurevitch,M,Blumler,J.G.(2004) 'State of the art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poised fro maturity?' in Esser,F.,Pfetsch,B.(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ories,Cases,and Challen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25-343
(15)(19)(23)(25)Hallin,D.C.,Mancini,P.(2004a) 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Pfetsch,B.,Esser,F.(2004)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orient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in Esser,F.,Pfetsch,B.(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ories,Cases,and Challen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24
(17)Hallin,D.C.,Mancini,P.(2004b) 'Americanization,globalization,and secularization:understanding the convergence of media system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 Esser,F.,Pfetsch,B.(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ories,Cases,and Challen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5-44
(18)Thompson,J.B.(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24)Blumler,J.G.,Gurevitch,M.(1995)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
(31)Semetko,H.A.,Blumler,J.G.,Gurevitch,M.,Weaver,D.H.(1991) The Formation of Campaign Agenda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rty and Media Roles in Recent American and British Elections.Hillsdale,N.J.:Erlbaum
(32)Blumler,J.G.,Gurevitch,M.(2001) 'Americanization reconsidered:UK-US campaign comparisons across time',in Bennett,L.,Entman,R.(eds.) Mediate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80-407
(34)Esser,F.,Pfetsch,B.(2004)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the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a changing world',in Esser,F.,Pfetsch,B.(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Theories,Cases,and Challen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84-410
标签:政治论文; 传播学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媒体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传播效果论文; 全球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