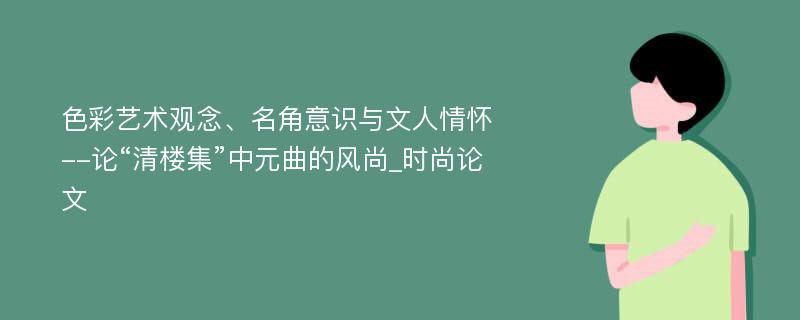
色艺观念、名角意识及文人情怀——论《青楼集》所体现的元曲时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角论文,元曲论文,青楼论文,文人论文,情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尚”,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时代的风尚”。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各种风尚,那些为大众认可并趋同的即成为“时尚”。“时尚”的媒介是传播,“时尚”的方式是流行,“时尚”的率先体现者则是爱好和趣味。
关于元曲成为时尚,胡祗遹《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云:“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陶宗仪《辍耕录》云:“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朱经《青楼集·志》云:“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周德清《中原音韵》云:“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缙绅及闾阎,歌咏者众。……”这些关于当时元曲如火如荼演出活动的记载,即反映了当下时态人们对作为文学艺术形式之一的元曲成为一种时尚的热衷和认可。
对于时尚,大众是参与者和趋奉者,作家是发现者和表达者,理论家则是总结者和评判者。作为元曲作家兼理论家的夏庭芝敏锐地发现了时尚,并且以史笔写作了《青楼集》这样一部独特的著作。《青楼集》(注:本文所引《青楼集》,均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是记录元曲艺人而且主要是女艺人的生活和表演情况的。从《青楼集》所采用的传记体例和所呈现的话语兴奋点,可以看出:在关注女伶的生存状态时,夏庭芝格外在意指出她们的色艺水平,非常注重评价她们的艺术地位,并且始终将她们纳入到文人的视野加以观照,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这是对青楼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文人对“才”的本能关怀,更重要的,从中能够真切感受到当时文化情境中元曲的时尚脉动,体现了时尚的兴味所在。因此,《青楼集》是属于时尚的,并且主要从色艺观念、名角意识、文人情怀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元曲作为时尚的具体理解。
一 色艺观念
艺人,在中国古代有多种称谓,如“优伶”、“倡优”、“娼优”、“歌妓”等等。虽然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技(伎)艺类活动,但按《夷坚志》的说法,属于“伎之最下且贱者”,自古以来就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被视为玩物,过着低贱的生活,并且随着历史的烽烟而香消玉殒,不落痕迹。仅有的关于他们的记载,“或者因为他们以‘优谏’指斥君王的过失而引起了史家的注意,或者因为相反,是因为他们受到君王过分的宠爱而导致亡国,值得史家记载下来作为后代帝王的教训”(注:杜卫、傅谨《审美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他们在艺术领域内的杰出贡献反而湮没无闻,他们的才华也被异化为专事淫亵之举的能力。对于历史上那些默默无闻的艺人来说,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概括他们的成就与风貌当比较恰切。
所谓“风流”,对于女性艺人(女伶)而言,主要是通过色艺来实现的,“色艺俱佳”是评价女优的基本审美标准,相沿成习,已成传统。在中国古代,由于卖艺的同时无法避免卖身的特殊性,女艺人往往被等同于娼妓,艺妓往往不分,所以《青楼集》的命名体现出明确的妓女意象:“青楼”一词让人“一望而知是记述妓女的事迹的”(注:周妙中《〈青楼集〉和它的版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实际上,“艺”和“妓”还是存在区别的,所以历来对艺人之色艺与娼妓之色艺的评价并不一样。究其原因,当主要缘于二者的职业规定性。艺人(主要是女伶)之色艺首先是为适应表演的需要而受到关注的,色通过艺即技巧而展开,因之首先在舞台上获得实现,是观众评价其艺术修养甚至表演水平的一种标准或者审美参照物。娼妓之色艺则是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决定其商业活动的能力,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乃金钱的等价物;在二者的关系中,色是根本,艺是附属物,又往往是色的先行者,其价值指向显然是实用的商业的而非审美的目的。在中国古代,优伶艺人仅仅有“艺”是不够的,卖艺的同时往往需要卖“色”,而“色”的内涵相当宽泛。对于女性艺人而言,则不仅包含作为创作媒体的容貌、体态乃至气质等因素,还有为达官贵人提供“性”服务的内涵。所以,由“性”构成内在要素的“色”始终因为契合于审美心理的自然需求和文化需求而成为欣赏者的首选标准。
在元代,一个不具备“色”的艺人同样是很难生存发展下去的,所以元代文人在论述女伶之表演时往往首先谈到她的“色”,如胡祗遹 “九美”说第一条就是“资质浓粹,光彩动人”(注:胡祇遹《黄氏诗卷序》,《紫山大全集》卷八,四库全书本。)。因为,元曲作为一种表演性非常强的舞台艺术,本身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不仅在富贵人家的厅堂演出,首先要在瓦舍勾栏进行表演,色艺与演技丝丝勾连,具有为市井社会认可与追逐的普泛性,因之也率先成为艺术欣赏的世俗需要和审美内涵,其中的“色”逐渐演变成为“艺”的重要构成因素,并且通过“艺”获得洋溢和体现,这样对于艺人自身条件的要求就更加严苛。这一点,作为元曲鉴赏者的夏庭芝显然已现实地体认到了,并且与许多因袭传统的文人一样认可色艺俱佳的审美观念,这是他“有感”之心理基础,同时也是激发他写作《青楼集》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记述女伶的身世和才艺时,进入他视野的首先是女伶们的色艺。如曹娥秀:“赋性聪慧,色艺俱绝。”,聂檀香:“姿色妩媚,歌韵清圆。”周人爱:“京师旦色,姿艺并佳。”王金带:“色艺无双。”王巧儿:“歌舞颜色,称于京师。”龙楼景、丹墀秀:“俱有姿色,专工南戏。”赵梅哥:“美姿色,善歌舞。”汪怜怜:“美姿容,善元曲。”金莺儿:“美姿色,善谈笑。”事事宜:“姿色歌舞悉妙。”李真童:“色艺无比。”等等。她们在当时声名鼎盛,领一时之风骚,成为人们追逐与崇拜的名角,首先缘于她们的“色”。
夏庭芝笔下的女性虽亦不免卖身的经历,但在作者笔下,她们首先是演员而不是娼妓,她们的生存方式也主要来源于“观者挥金与之”的勾栏瓦舍,这决定了对她们的观照态度首先是艺术的或者说是审美的。这从夏庭芝始终将色与具体的元曲表演特点联系起来论述即可以见出。他的言语兴奋点多落在女伶擅长的技艺方面:她们的表演特色、她们的艺术履历,并且记述态度公正客观,不带有任何猥亵和游戏意味,体现出不同于一般也不同于以往的开阔的艺术视野。在夏庭芝眼里,艺人之“艺”处于次之的地位,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是格外重要的,缺少了“艺”;“色”亦无所附丽,毫无价值可言。《青楼集》记载了那些主要以“艺”见长的女演员,并且对她们炉火纯青的“艺”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如朱锦绣:“高艺实超流辈”而“姿不逾中人”;喜春景:“姿色不逾中人,而艺绝一时”;陈婆惜:虽“貌微陋”,但“谈笑风生,应对如响,省宪大官,皆爱重之”;般般丑:虽容貌不佳,但“擅词翰,达音律,驰名江湘间”。此外还有,诸如陈破惜:“貌微陋”;王玉梅:“身材短小”;平阳奴:“眇一目”;王奔儿:“身背微偻”;和当当:“虽貌不扬,而艺甚绝”;等等。甚至有“朱娘娘”之尊称的一代艺人之杰珠帘秀也有“背微偻”的毛病。元代以前,文学史上人人眼目的多是些才艺俱佳尽善尽美的歌妓形象,而唐代公孙大娘类姿色平平却技艺超群者如风毛麟角;不是她们没有存在过,而是因为她们没有进入到文人的视野。夏庭芝对于“以艺见长”者的充分认可,有个人价值观念开明的原因,又可以见出人们对一种时尚艺术的偏爱。正是这种偏爱,才促使人们更看重演员的表演技艺,而对其形貌气质上的微瑕表现了宽容大度的心理趋向。这种对演员与娼妓色艺的明确区分,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表演艺术逐渐脱离青楼文化而趋向审美的艺术走向。对于中国古代戏曲批评而言,《青楼集》的意义则在于,其促进了中国古典戏曲表演理论的开放视野,以后的表演理论在论及演员修养时也尽量避免了唯色为第一的片面化,给予艺人之“艺”以充分的关注。
由于这样的艺术时尚,元代女艺人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性。这不仅表现在她们与文人士大夫关系的开放、自由、亲密,这种开放、自由、亲密与唐宋时期文人与歌妓的关系具有了本质的不同,尤其体现在以她们为代表的市井阶层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明显增加的参与份额。元代文人与普通民众对元曲艺术的趋之若鹜已为众所周知,值得注意的是,艺术观念发生转型的同时日常生活观念的细微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开放、兼容和尊重相概括。如《青楼集》的记载,女伶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无视国家法令使用“酒器皆金玉”(如张怡云等),也可以依从个人的意志追逐并嫁给文人士大夫(如金莺儿等),她们甚至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逞才使性,与当朝显贵斗智斗勇。如顺时秀与王元鼎相好,参政阿鲁温亦对其属意,就问:“我何如王元鼎?”顺时秀回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巧妙却是直接地拒绝了阿鲁温。那么,元代社会较以往甚至以后有所开放吗?当然不是。元曲艺人社会地位的引人注目,实际上来自于蒙古贵族汉化过程中的疏漏以及他们喜爱歌舞表演的民族习性,当然还有市井社会的进一步成熟。这一切,促成了当时社会风气的相对开化。
其一,蒙古人是喜欢直观先验地看待事物的,加之汉化步伐的时缓时急,所以直到入主中原多年,必要的礼仪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政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直到至元八年(1271),才正式使用了朝仪。由于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不能同步,执行也不能做到有效,加之监察制度的不完善,元朝的许多规章根本没有得到认真实行。如朝廷禁止官员宿娼,规定一旦发现,宿娼之官吏与娼妓一起“坐罪”,可实际上,元代社会宿娼成风,官员们的宿娼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而在民间,由于各民族杂居,受到少数民族自由开化观念的影响,北方地区的伦理规范相对松弛,官商通婚之类并不受限制,甚至在汉族家庭中还出现了“收继婚”这种原始的婚姻形式。
其二,世世代代生活于大漠荒原的蒙古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舞和戏乐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扫平欧亚占据中原后,处于权力顶端的蒙古贵族当然不会改变这种民族习性,反而要尽力张扬挥洒这种享乐追求,加之热衷于宴饮和狩猎,所以元代的宫廷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歌舞娱乐。据说当时宫廷中最盛行的皇家舞蹈是规模盛大而华贵的“天魔舞”:“行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绣帘齐卷熏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注:萨都剌《上京即事》之三,见《雁门集》卷三,叫库全书本。)吐蕃、回回等族的音乐歌舞以及汉族人擅长的杂技也纷纷进入到宫廷中表演。而元曲以它的歌舞兼长和故事性同样得到蒙古贵族的喜爱,《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了元代宫廷团拜时“音乐家和梨园子弟演剧以娱众宾”的事情。当时的许多著名演员进入宫廷供奉,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记载:“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影响所至,当时许多有名的汉族权贵如东平侯严平、史天泽等亦将欣赏歌舞和戏曲表演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三,自唐宋以来,市民社会逐渐生成并且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作为市民的重要分子,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三姑六婆,当他们进入文人的文学描述视野时,都无法与以色艺事人的艺人娼妓相比。唐宋传奇、宋词乃至元曲的成就均与这一市井群体的参与密不可分。正是他们的积极介入,新生的文体才不断成熟,叙事艺术才终于脱离了历史的拘束而进入审美的视界,中国古代的市民艺术才获得蓬勃发展的机遇。可以说,色艺观念是伴随着市井艺术的发展逐渐为我们认知的。因此,艺人乃至以色艺为主的娼妓的活动逐渐社会化、审美化,其在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的凸现,加强了社会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他们获得了空前的尊重和理解,社会角色也愈加重要起来。因此,当元代社会为以色艺事人的女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和施展才艺的特殊空间,她们较前代艺人享受到了更加宽松的伦理自由和更少的规范限制,尤其是她们通过勾栏瓦舍从事的表演,使她们与芸芸众生更加切近,增加了为整个社会所瞩目为时尚所关怀的机缘,市井百姓喜欢她们,豪强势要愿意亲近她们,而各类文人也刻意与她们相往还,或附庸风雅,或寻求慰藉,或欣赏才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元代女伶们的生活呈现出相对宽松的存在状态,表面上显示出社会地位的有所提升。实际上,对于事人者和被侍奉的人而言,这一切的前提都取决于声色之娱的当下目的,所以,归根结底女伶们只是时尚的代表享乐的标志,她们与元代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社会互为表里,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的产物。
元代女伶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是特殊文化情境的偶然结果,所以在元代的典章制度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优伶生活处境的悲惨。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仅次于娼妓,如《元典章》规定,“乐人只娶乐人”,其他人不准与乐人结婚等等。《元史·顺帝纪》还有“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以及不准佩带“金面钗钏”等规定。《元史·刑法志》中有:“诸民间弟子,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这种对正经人家子弟的申戒真正饱含的是对优伶的鄙视。一般的士大夫和文人也多是从欣赏歌舞和寻求慰藉附庸风雅的目的出发与艺人交好的,怜香惜玉者即使如白朴也不免轻薄无聊的心理。而从《青楼集》的记载可以看出,多数女伶是将归于文人士大夫为妾视为最佳出路的。实际的情况却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在世时,女伶也只能居于“别馆”,如翠荷秀:“自维扬来云间,石万户置之别馆。石没,李(翠荷秀)誓不他适,终日却扫,焚香诵经。”他们去世或者厌弃了她们的时候,女伶就只好重操旧艺或出家为女道士了,这一点,夏庭芝关于女伶归宿的记载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如喜,春景:“张子友平章,以侧室置之。”金兽头:“湖广名妓也。贯只歌平章纳之。贯没,流落湘湖间。”王奔儿:“金玉府总管张公,置于侧室。……张没,流落江湖,为教师以终。”李芝秀:“金玉府张总管,置于侧室。张没后,复为娼。”汪怜怜:“(涅古伯经历纳之)数年涅没,汪髡发为尼,公卿士夫多访之。汪毁弃形容,以绝众之狂念,而终身焉。”李真童:“(归达天山同知)后达没,复为女道士,节行愈厉云。”等等。女伶这种不幸结局托出了色艺观念的轻薄内涵,同时也是她们受到社会歧视终将被排斥到伦理生活之外的鲜明印证。
二 名角意识
表演是青春的艺术。在色艺观念的支持下,艺人尤其是女艺人的艺术生命往往非常短暂,表演的竞争往往成为了生存的竞争。在元曲表演的舞台上,观众对名角的表演格外倾心,作家愿意为名角创作剧本,戏班或勾栏也愿意网罗名角招揽观众,《青楼集》的作者夏庭芝在为演员作传时也仅仅关注那些“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成为“名角”是多数女伶最大的心愿。
在中国古代缤纷多姿的艺术表演中,并没有出现“名角”的概念。但是,名角的意识源远流长,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表演艺术的发展,并在艺术的繁荣和流变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名角”既是演员走向宫廷寻求发展的身份依据,也是具有商业性质的艺术演出的必然要求,同时还往往是时尚的标志和聚焦点。缺乏名角意识的艺术显然不能发展为时尚,这是为艺术规律所证明了的。成为13世纪艺术潮流的元曲时尚渗透着强烈的名角意识,这一点在胡祇遹著名的“九美”说中已有印证,他的“九美既备,当独步同流”的著名话语,较早为元曲表演理论乃至实践领域中的名角意识做了总结。而《青楼集》的写作亦缘于夏庭芝让一代名伶留名青史的美好心愿:“庶使后来者知承平之日,虽女伶亦有其人,可谓盛矣!”据此,名角意识显然已经相当成熟与自觉。首先,在夏庭芝的笔下,成为名角已不仅仅是抽象的“资质浓粹,光彩照人”、“举止闲雅,无尘俗态”等,还具体为内在气质、神韵乃至修养与演技的勾连关系,如顺时秀“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天然秀“风神靓雅,殊有林下风致”,其“闺怨杂剧为天下第一”;等等。作者虽没有明确指出这样的个性风神对艺术的直接影响,但将其作为名角女伶的特殊质素强调出来,显然是将其作为名角意识的重要构成要素来看待的。其次是演员的文化修养,这是构成名角的另一个层面的重要因素。夏庭芝不止一次提及女伶的文学修养,如说她们“亲文墨,通史鉴,教坊流辈咸不逮也”(“赵真真”条),即是对名角与普通演员卓然不同之处的指认。如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梁园秀“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般般丑“善词翰,达音律,驰名江湖间”;等等,明确指出她们的艺术修养与她们成为名角的自然关系。而许多“独步古今”的名角不仅以她们独具魅力的身体艺术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元曲艺术,还在其他艺术形式方面有所擅长,如珠帘秀就有诗集编成,胡祇遹在为之作序时对她“以一女子,众艺兼备”的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注:胡祇遹《朱氏诗卷序》,《紫山大全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元代散曲中多的是吟咏女伶之作,其审美对象几乎是当时擅场的元曲名角。如赵明道的散曲《明姬》赞美一位色艺双绝的吴地歌姬,说她“燕赵驰名,京师作场”,接着进一步以“雷声声梁苑,禾惜惜都城,苏小小钱塘”作比,夸她是“四海名扬”的名角,“堪写在宣和图上”,在青史留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曲时尚推奉的所谓“名角”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首先是空间意义上的。成为名角的女伶大都在某一地域内特别知名,如朱春儿“得名于淮浙”,平阳奴、郭次香、韩兽头等“皆驰名金陵者也”,廉前秀“武昌湖南等地,多敬爱之”;而刘子安之女关关,人称“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湘湖间”。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元曲作为时尚的广延的地域性。而许多女伶通过四处作场式的巡回演出作为成就其声名的方式,不但可以增加个人的知名度,助其成为名震四海的角色,客观上也完成了对一种时尚的推扬。如连枝秀,“浪游湖海间。尝至松江,……后又飘然入吴”;再如珠帘秀、顺时秀,《青楼集》虽然没有记载,但从其他资料中可以知道,她们后来都到了杭州。作为已经成就了声名的名角,她们对于元曲时尚进入南方地区必定是做出了难以描述的贡献的。
出现在夏庭芝笔下的女艺人共有119位,为《青楼集》绝对的主体。无论是“见而知之者”,还是“闻而知之者”,都是“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受到普遍认可的名角。尽管夏庭芝没有使用“名角”这一概念,他对于演员的记录中时时处处渗透了“名角”的意识。具体说,这种意识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一)直接对女伶的艺术水平作出评价。夏庭芝在简要概括了演员的表演特征后,往往迅即对其表演特色作出评价,这种评价是简约的、概括性的,体现为一种惯性切入的话语模式,表达出他对名角艺术特征的欣赏和认同。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珠帘秀:“元曲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天然秀:“才艺尤度越流辈;闺怨元曲,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顺时秀:“元曲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孙秀秀:“京师谚曰:人间孙秀秀,天上鬼婆婆。”于四姐:“尤长琵琶,合唱为一时之冠。”张玉莲:“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等等。应该说,这种评价既是夏庭芝个人时尚观念的体现,也是历史对行将逝去的时尚的一种追忆式表达。《青楼集》是在元末问世的,当元曲时尚渐成历史云烟之际,女伶们的色艺表演经过时间的过滤,依然成为激动夏庭芝心灵的亮点,并促成了《青楼集》的最终问世,既是对一种时尚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女伶艺术实践的充分认可。
珠帘秀、顺时秀在当时影响很大,是享誉一时的名角,许多文人对她们的评价都很高,关于她们的文人题咏也比较多。珠帘秀,流传至今的就有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胡紫山[沉醉东风]、冯海粟[鹧鸪天]等,从不同角度歌颂了她的色艺双绝。另外《绿窗纪事》、《辍耕录》等有关于她的记载。如对于顺时秀,王实甫、白朴等均有题咏;还有诗歌,如张光弼《辇下曲》:“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可见名角在当时影响之大。
(二)对女伶擅长的多方面艺术才能加以强调。从《青楼集》的记述可以看出,成为名角的演员虽然在某个领域特别出色,但并不只是在某个固定的角色行当中活动,她们往往擅长多种艺术形式,体现出较高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具体说,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1)擅长的杂剧行当种类多,能够承担类型迥然不同的多种角色的艺术表演。毫无疑问,杂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青楼集》涉及的女伶多为杂剧演员,并且在作者的叙述中占据着其他艺术种类演员无法比拟的话语优势,这表明杂剧在元曲时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杂剧艺术的丰富性在表演中首先是角色行当的丰富,对演员来说,擅长多种类型角色的表演是其艺术水平高低优劣的标志,《青楼集》虽然没有具体论述角色行当的审美特性,却注意将之作为女伶的多种艺术特长特别介绍出来。如珠帘秀:“元曲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天然秀:“才艺尤度越流辈;闺怨元曲,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顺时秀:“元曲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等等。这表明,许多演员对多种类型角色的成功的艺术把握,恰恰是她们成为名角的重要因素。(2)独擅某一种类的技艺,无人或少有人可以比拟。“曲并非开始于元,而是到了元时臻于极盛。”(注:黎东方《细说元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这种“盛”规定了今天所谓元曲内涵的极其丰富,即它不仅包含有杂剧一种艺术形式,还囊括了散曲、诸宫调、慢词、院本等艺术形式。《青楼集》准确捕捉到了这种对于元曲内容的规定性,将其他艺术形式的元曲演员也纳入视野。她们能歌善舞,技艺超群,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往往对某一种艺术样式或角色行当格外精通,并因此声名鹊起。如刘燕歌:“善歌舞。”秦玉莲、秦小莲:“善唱诸宫调。艺绝一时,后无继之者。”孔千金:“善拨阮,能慢词,独步于时。”李娇儿:“花旦元曲,特妙。”等等。(3)精通经史,擅作诗词曲,表现出较高的文化品位。在中国古代,纯粹的艺人往往是不识字的,她们的表演主要依靠单纯的技艺培训和心口相传的记忆功夫。女性艺人因为性别原因,所需要的相当的文化储备实际也非常有限。因此,如胡祇遹提出的所谓“心思聪慧”的概念在表演领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对表演技巧的熟练把握,还包含·了对表演内容的领悟能力和体验程度。《青楼集》恰恰从这一层面重视到演员的文化修养。元代女伶或者通晓经史,或者能够创作诗词歌赋,这构成了她们生存的一种手段,创造了她们与文人对话的机缘,还是她们包装自己促成名角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樊香歌:“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经史。”梁园秀:“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等等。夏庭芝还特别记录了知识修养较好者所具有的敏捷才能,“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的名角张怡云,一次“佐贵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恰到好处地续吟了曲子,还聪明地为曲子安排了曲牌,而且用意深远。在作者的叙述策略中,张怡云类名角不仅足以与名公士夫对话,而且显示了不让须眉的豪迈气度。
(三)遵奉者多,后继有人。中国古代口口相传的艺术传承特点注定了师承关系的重要意义。名师出高徒,自古如是,以名师作为号召,也是表演艺术领域相沿成习的艺术传统。那些为一时风尚所尊奉的名角,往往出自名师的培养,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如赛帘秀,为名角珠帘秀的高徒,虽双目失明,但在舞台上“出门入户,步线行针,不差毫发,有目者莫之及焉”,亦为一时所重。名师还往往成为女伶作场时的一种招牌,有些女伶干脆以师傅的名字嵌入自己的艺名,既昭示自己的师承,也隐含名师对自身艺术成就的肯定,如赛帘秀(珠帘秀的徒弟),以及小顺时秀(荆坚坚,顺时秀的徒弟)、小天然(李娇儿,天然秀的徒弟)等。以名角或名师相号召虽然具有角色意识乃至商业利益诸方面的考虑,但首先是与其表演技巧的纯熟程度相关的,许多女伶因此扩大了影响,成就了独步一时的名角地位。如燕山秀,是“珠帘秀之高弟。旦末双全,元曲无比”;荆坚坚,“擅唱。工于花旦元曲,人呼为‘小顺时秀’”;李娇儿,“姿容姝丽,意度闲雅,时人号为‘小天然’”;等等。很明显,在以名角之艺名对女伶表演进行艺术概括时,夏庭芝虽没有特别说明,但首先表现出对名角艺术风格的认可,这是一种时尚的认可,而且是倾向于女伶的演唱风格而言的。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元曲是以“演”和“唱”为特征的,叙事性很强的元杂剧往往以“旦本”或“末本”相标志,不仅规定了演唱的特质,而且也强调着演唱的重要性。其“一人主唱”的演出体制对于演员的艺术功力有极高的要求,演出的成功与否往往与歌唱技艺的水平关系密切,这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夏庭芝在对元曲演员的艺术进行评价时,特别注意提及她的演唱水平,如赛帘秀“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唱”;朱锦绣“元曲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赵真真“善元曲,有绕梁之声”;专工贴旦的回回人米里哈“歌喉清宛,妙入神品”;李定奴“歌喉宛转,善元曲”;等等。王国维关于真戏剧首先是“以歌舞而演故事”的论断在《青楼集》中得到了部分印证。
以上主要针对演员的“艺”分析了名角意识的构成。实际上,《青楼集》中所反映的名角意识也饱含了对色的定位。在提及女伶的色时,夏庭芝往往是色艺并举的,这是传统思维定势的延展,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主观上刻意标举“艺”并不能掩饰“色”在审美接受时的能动作用,在评价女伶的艺术水平时,“色”已经历史地成为了其中的必要构成因素。
三 文人情怀
女伶自身的色艺是重要的,但仅有色艺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独步天下”的名角,无论古今,机遇对于演员的成功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宋以来,由于市民社会的逐步成熟,文人的市井趣味不断强化,文人之于艺妓的关系也日益重要起来,可以说,唐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近古市民文化的发达与影响密切相关。艺妓作为市民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创作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不仅勾连着一个来自雅文化的创作群体——文人,而且在中古向近古的文化转型中帮助他们,完善他们,甚至激励他们,促成了转型的完成;反过来,文人以及由文人组成的仕宦阶层也乐于将这些艺妓引为自己的红颜知己,精神同道,因此而乐于关注她们,提携她们。有关这一点,已获得了当代许多学者的充分认可。
在元代,获得文人尤其是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文人的青睐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从事元曲演出的女伶们来说,这是她们声名鹊起的基础,更多的时候是她们获得普遍认可的依据。可以说,这是青楼文学主题在元代的延伸,同时也是文人作为文化中心思想在市井艺术领域的凝聚与体现。
夏庭芝本身是个文人,他对女伶的关注是饱含着文人趣味的,这使他始终热烈地将目光投注到文人尤其是那些身为显宦的汉族文人与女伶的遇合关系方面,甚至刻意阐释彼此之间的佳话与逸事。如顺时秀“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小娥秀甚得张子友平章“爱赏”,“中朝名士,赠以诗文盈轴焉”;天然秀有“林下风致”,“高洁凝重,尤为白仁甫、李溉之所爱赏云”;樊事真,“周仲宏参议嬖之”;周喜歌“字悦卿,貌不甚扬,而体态温柔。赵松雪书‘悦卿’二字,鲜于困学、卫山斋、都廉使公及诸名公,皆赠以词,至今其家宝藏之”;于四姐“尤长琵琶,合唱为一时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诗赠之”;等等。显然,文人的青睐与否、赏识与否,直接关涉到对女伶艺术才能与地位的认可,而与之交往的文人愈多,女伶的名气就愈大,文人也就会更加趋之若鹜。如珠帘秀作为遐迩闻名的名角,获得后辈尊为“朱娘娘”的巨大声名,与她精湛的艺术造诣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著名文人对她推举的结果。关汉卿、胡紫山、冯海粟、庾天锡、卢挚等都有诗曲相赠,对她的演技和容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再如,张怡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诸名公题诗殆遍,而画家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都为他创作“怡云图”相赠。而且,她的住处还是文人雅集之地,当时的名宦姚牧庵、阎静轩乃至史天泽都光顾滞留,这在当时是一种来之不易相当难得的殊荣。
文人之于女伶的态度不断进入夏庭芝的视野,作为比较重要的因素被反复提及,固然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嘲风弄月传统的遗绪,更多的,则来自于元代文人特殊的人文情怀,这同样是一种时尚的反映。自古以来,儒家对于士人和优伶之间的等级关系就有严格规定。《礼记·乐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明确指出,文人是靠修德立业,是高贵的,优伶靠专门的技艺谋生,是低贱的。在这种观念下,优伶被视为玩物、贱人,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而与优伶或娼妓相处,往往被视为文人的恶行之一。一些正统的文人对此是嗤之以鼻的。但是,多数时候,文人并不把赏优嫖娼看作一件严肃的事,反而以风流潇洒自任,将之作为文人情趣的点缀,加之“唐宋以讫前明,国朝不废女乐”(注:章学诚《妇德》,见《文史通义·内篇》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于是,以文人和歌妓之遇合为描写对象的所谓“青楼文学”便愈加发达起来,各种艺术题材如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等,都因为名士与妓女的风流韵事而格外妩媚妖娆起来。文人因为美人而有了灵感,美人因为文人而获得了永恒,《青楼集》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的例证。
元代有与以往不同的文化语境。这是一个独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规范一度混乱无序,伦理规范始终相对松弛,感官享乐被充分认可,文化价值趋同于世俗化。这个时代促使文人的目光向下,不得不放弃“骚雅”的标格,混迹于主要由进身无路所构造的市井社会生活。所以作为13世纪的时尚代表,元曲既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也给了积聚已久的文化压抑以集体释放的机会。而且,这不仅仅是民族歧视问题,也不仅仅是边缘处境问题,还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起作用,就像一位学者所言:“面对中国文学过分严肃以至于到了僵化程度的传统,文人们内心的深处那些隐秘的情感要求无法得到一条顺畅的发泄通道,……尤其是在文人们不仅受到内在的道德戒律的压迫,同时还受到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压迫,就像元代初年‘士失其业’的时代,……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轻松之途。”(注: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最典型的是关汉卿,他能独担风流之名,以“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任,并且宣称:“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注: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见《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这是需要大破大立的勇气的。联系他的为人,审视他的元曲作品,可以发现,其中显然含蕴着一种激切的情绪,一种包含着逆反与破坏因子的情绪,这种逆反和破坏不仅来自于他的失意、困窘,还来自于他对那个社会的批判、指责,更多的,来自于长期文化压抑所导致的深层心理的发泄。作为一个落魄文人,关汉卿辈首先是人,他们不但需要摆脱贫穷,更需要摆脱压抑,那种来自于灵魂为自己的自负和骄傲控制的压抑,这种由诗书礼乐制造的压抑已经使他们窘迫了近千年了,他们需要一个适度的土壤宣泄,而元代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土壤,他们为什么不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呢!因此,这是文人群体的一次群体大释放,元代社会给了他们千古难逢的机会,元曲则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于抒情达意的多种形式。
但《青楼集》所涉及的主要是元代的另一类文人群体。他们多数不能归属于“沉抑下僚”之辈,主要是活跃于社会上层的文人雅士和成为高官贵吏的仕宦文人,如赵松雪、胡紫山、张子友、史天泽等。由于身份的高贵、地位的特殊,及他们对艺术的参与和干预,他们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往往影响了勾栏瓦舍的选择,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时尚的方向、范围以及内涵。例如史天泽在真定的戏剧活动对促进其成为元曲创作与演出的中心即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而如胡紫山,其对优伶乃至元曲的青睐则显示出从人本视角的独特关怀。在《赠宋氏序》中,他指出,“百物之中,莫灵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优伶们的艺术表演不仅为芸芸众生带来了生命的“欢适”,还提供了审美的表达:“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注:胡祇遹[木兰花慢]《赠歌妓》,见《紫山大全集》卷七,四库全书本。),“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这些见解尽管极稀薄却也极细微地表达了对市井人生的体谅与关怀,联系元曲中较少宋词中那些私语性的“高处不胜寒”之句,则胡紫山的观点在某种层面上表达了当时部分权宦的共同心理与思想,而这也正是他们能够顺应、发现、推波助澜,将方露“尖尖角”的元曲推导为代表文学主流与表达时代精神之时尚的动因。
如果将关汉卿之属归为跻身于市井的一类文人,这一群体则属于寄情于市井的另一种类型。较关汉卿类书会才人而言,他们少了些边缘处境的窘迫,多了些社会中心的感觉,他们脱离了窘迫的物质境遇,却可能蒙受着另一种来自种族的压抑,所以他们同样需要心理的补偿,渴望精神的丰盈。他们和关汉卿辈承受的文化积淀是相同的,面临的文化语境也是类似的。对他们而言,元曲表演不仅仅是优容闲雅与诗酒风流的点缀,同样是挣脱精神羁绊所必须拥有的缓释琼浆和宣泄渠道,所以,他们也格外看重在欣赏歌舞表演中与女伶们建立起来的遇合关系,并且将之作为一种别样情怀的寄托而投入了真切的精神关注。如赣州监政全子仁起初对“时贵多重之”的刘婆惜并不看好,但在一场戏剧性的“表演”完成后,即对之格外称赏,“顾宠无间,纳为侧室”:
时宾朋满座,全(子仁)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子仁)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裣衽进前曰:“能容妾一辞乎?”全日:“可。”刘应声日:“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全(子仁)大称赏,由是顾宠无间,纳为侧室。
这里所体现出的元代文人与女伶的彼此认同,显示了诗酒风流之外的别样魅力,表达了另一种文化情境中难以捕捉的人文情怀,即对于彼此才艺和人格的充分认可,以及由此而来的宽容、理解与亲和关系。应该说,这种亲和关系是双向的,包含着互动的因素。当文人的目光向下并且发现了这群“资性明慧,技艺绝伦”(“顾山山”条)的女性时,这群禀赋了时尚的新奇和生动的女性也在追逐着文人的目光。他们的相遇是历史性的。其价值不仅在于规定了元代文化语境中特殊的精神运行轨迹,还给我们提供了直接并且切实地捕捉从抒情艺术到叙述艺术的转换时段,这些女伶以怎样的热情创造了舞台,又怎样以她们的身体和身体的艺术理解和慰藉了整整一代文人群体。由于这些来自民间与市井的女伶的引领,元代文人或染指于元曲创作领域,感受到日常人生的喜怒悲欢,或寄情于元曲欣赏,寻求生命的舒展永恒,为人生打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性结构的鲜亮底色。没有这些女伶及其所从事的元曲艺术,一代文人的情怀将无所寄托。
余论
《青楼集》的作者夏庭芝,我们所知甚少。他是元末著名文人,出生于“乔木故家”,一生“黄金买笑,风流蕴藉”,不以功名为意;其“慕孔北海,坐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以故闻见博有,声誉益彰”(注: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5页。)。元末社会动乱时,“资产荡然”,即便如此,“凡寓公贫士,邻里细民,辄周急赡乏”,自己则“优游衡茅,教子读书,幅巾筇杖,逍遥乎林麓之间,泊如也”(张鸣善《青楼集·序》,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第6页。)。显然,历史视野中的夏庭芝是一个淡泊名利、潇洒蕴藉的风流文人。
关于本书的写作动机,夏庭芝这样说:“呜呼!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仆闻青楼于方名艳字,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虽详其人,未暇纪录,乃今风尘澒洞,群邑萧条,追念旧游,慌然梦境,于心盖有感焉;因集成编,题曰《青楼集》。”(夏庭芝《青楼集·志》,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第8页。)似乎,经由岁月的砥砺,凸显于夏庭芝记忆中的只有那些领一时之风骚的元曲艺人,而且主要是女艺人。的确,在元代之前,女伶虽然在表演艺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还没有像元代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真正从民间而来,又回到民间而去,在市井人生的大舞台上演绎生存的悲欢喜乐,完成了她们自身意义的回归,同时参与创造了领一时风骚的元曲艺术。她们是元曲表演的主体,她们的艺术魅力光芒四射,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男演员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从现存的元曲文本即可以获得部分印证。如现存的杂剧剧本中,旦本占多数,举凡我们经常称引的优秀文本,如《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等等,多为旦本,甚至杂剧艺术的每一个行当如驾头、闺怨、绿林等等都由女伶们独领风骚。显然,她们的色与艺是元曲演出的魅力所在,始终为时尚所关注,不仅激动了一代文人的情怀,在“风尘澒洞,群邑萧条”之际也是最值得忆念的,她们是值得文人为之留名后世的。
但是,仅止于此,似乎不是全部。在《青楼集》问世之前不久,另一部记录元代作家状况的戏曲理论著作《录鬼簿》悄然面世。它的作者钟嗣成大约生活在1275年至1345年的历史时段,显然早于夏庭芝;戏曲史上没有留下他们交往的记载,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有目的的影响也难以确证,但以两人分别写作了反映元代作家和演员的著作这一现实来看,他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志同道合。《录鬼簿·序》这样写道:“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并有意为那些地位卑贱的作家张目,称那些天才的元曲作家为”鬼”,指出:“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称颂和欣赏溢于言表,体现了与众不同的果敢和强烈的平民意识。夏庭芝没有如此真切的言志话语,但他在《青楼集·志》中对杂剧流变过程的精辟总结和关于其“厚人伦,美风化”功能的肯定,同样说出了他目光向下的理由。所以,他才不仅仅为女伶作传,还有为男优作传的打算:“至若末泥,则又序诸别录云。”云云,凡此,昭示出其平民意识与钟嗣成或不谋而合或彼此呼应。他和钟嗣成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曲的时尚所在,以独立不移的创作与已经浮出水面的平民主义审美理想契合对应。如果说,《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是出于让那些怀才不遇的“不死之鬼”青史留名的目的而写作,展现的主要是作为“主景”的一代文人的精神求索的话,《青楼集》的作者夏庭芝在将目光投向“青楼”的同时,彰显的则主要是作为其人文背景的一代文人的精神面貌。他们的立足点不同,却都将元曲作为话语的中心,表达了一个时代。从此,不是同样可以体会到元曲的时尚地位和价值?
正因为如此,在《青楼集》的编选和创作过程中,夏庭芝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客观公正的,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元曲作为时尚的基本风貌。如他有关一百多位演员活动区域或成名区域的记载,涉及了大都(京师)、山东、江淮、金陵、江浙、淮浙、湖广、维扬、湖州、武昌、京口、松江等许多地方,而大都、江浙、江淮、金陵等地演员数量的集中,从地域角度反映出大都和江浙地区演员队伍的庞大,透视出元曲流行范围的广阔,以及其成为时尚的真实性,又进一步确认了大都为元曲繁荣中心的成说。李昌集更据此得出戛戛独论:由于“京师名妓代有人出”的事实,“大都一带北曲的中心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元灭南宋后,民间文化圈的事实是大都和江浙一带两个‘北曲中心’并存”(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又夏庭芝对女伶擅长的表演技艺种类的记载,根据粗略统计,大约有十种之多的艺术形式构成了元曲艺术的丰富内涵,如杂剧、院本、南戏、诸宫调、慢词、小唱等,这其中,又以杂剧独领风骚。因为在他提及的110多名女伶中,有60多位专门从事或同时擅长杂剧的各类角色表演,在所参与的各类艺术样式中占有最大的比例;而他对演员杂剧表演特色的描述也往往注重她们对多种角色的擅长,角色艺术分类的细致并发展为演员的艺术专长,只有在这种艺术充分发展并在艺术实践中独领风骚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如在对众多女演员的记录和描述中,夏庭芝的笔端不见一丝一毫嘲风弄月的怀抱,也没有涉及一点淫邪低俗的言行,有的只是对于她们艺术才能和个性风采的概括和总结,除此之外,就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对女伶们的深刻的同情、高度的理解,以及由衷的赞美。他将一代女艺人的言行、经历乃至演技都交给了历史,也就是交给了未来。这种让历史来评说的态度本身就包含了表彰甚至提升的含义,是前代的《教坊记》(注:唐代崔令钦编著,记录了艺人生活琐事与逸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之类无法比拟的,也是后代的《鸾啸小品》(注:明代潘之恒作,记录了戏曲演员的生活与演出情况,见《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一类难以追步的。
(收稿日期:2002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