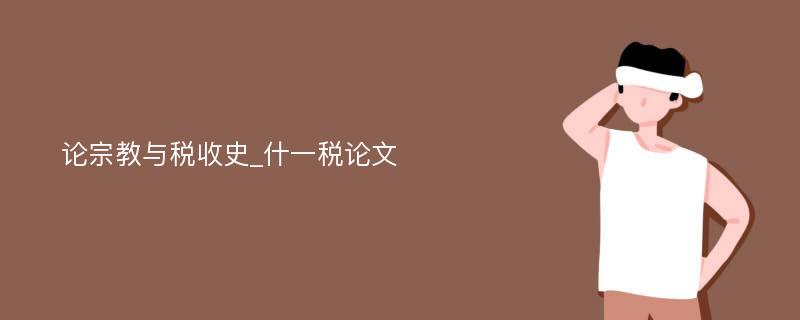
宗教与赋税史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税论文,宗教论文,史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封建社会是宗教发展的“黄金时代”,正如恩格斯在论及天主教时所指出的“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政府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它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不仅如此,在封建时代,宗教还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它们依靠国家特殊的赋税政策充塞“圣库”,并为宗教的扩张充当助推器。
一、什一税:一种最基本的宗教赋税
封建时代,教职人员多为寄生性的社会成员,其个人生活及宗教活动所需仰赖教徒的贡献,小则为私人捐纳,大则为国家的财政拨付,再有便是寺院地产经营的收入等等。“什一税”是其中由教俗两界共同拟定的一种最基本的宗教义务,是寺院最稳定的一项经济来源。
“什一税”并非始于中世纪,其古例见诸埃及、巴比伦、犹太、希腊和罗马等民族,将个人财产或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给国王或祭司的惯例。六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会利用《圣经》所载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向居民征收什一税。八世纪末查理大帝在敕令中对此有特别强调:“凡一切财产的收入,不论是由破坏和平或其它任何罚款以及国王一切收入,都应抽出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和教士”。(注:查理大帝“关于萨克森地区的敕令”(780年左右)) 世俗帝王为什么要做如此规定?这是政教两种权力相互结合的需要。796 年查理大帝曾致信教皇利奥三世:“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这就清楚地道出世俗政权为何要赋予教会征收“什一税”这一特权的根本原因。
查理曼的政策在他身后得以继续遵行,“什一税”乃成为封建剥削的一项重要构成。它有大什一税(粮食)、小什一税(蔬菜)和血什一税(牲畜)之分。“什一税”的税额并不是绝对的十分之一,而是经常越出这个标准。“什一税”的征收主要由教区神父负责。收来的“什一税”分做四份,用来上交主教、救济穷人、维持神父及其助手的生活和修缮。
在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教会一样征收“什一税”,但获取方式与西欧相异。它从公国财政收入中提取十分之一的实物或税款,故称“国库什一税”,且分贡品什一税、诉讼什一税和商业什一税等类。这种“什一税”是俄罗斯正教会与大公政权分享封建地租的早期形式,其实质与西欧诸国无异。
“什一税”对封建劳动者来说是一项假名宗教义务的经济负担,但在教会势力处在上升期时,无人敢对此有所非议和诘难。十三世纪初的英诺森三世教皇曾傲言西方:“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且是整个世界”。但是,当教会势力盛极而衰时,对“什一税”的指责便群言四起。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期间德国农民便普遍要求废止“什一税”。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也曾反对罗马帝国的税收政策,并憎恶税吏。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马太,出身税吏,耶稣与之交结成为他人非难的口实。可以说,犹太人当年对罗马帝国税收政策的痛恨与中世纪西欧国家对“什一税”的不满,根本原因是一致的。但是,“什一税”毕竟是一种宗教赋税,而不是一般的封建赋税,因而其废止之声虽出,然行之犹缓。直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欧才陆续废除“什一税”,而英国一直征收到1936年。
伊斯兰教亦有一种“什一税”——“天课”。穆斯林相信,这是“奉主命而定”的。《古兰经》中劝诫教徒要施舍、要完纳天课。(注:马坚译《古兰经》58:12、13;9:60;9 :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伊斯兰教曾具体规定:教徒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应按规定税率纳课,商品和现金纳1/40,农产品纳1/20—1/10,驼、牛、羊和矿产各有不同税率。多数情况下,乃以1/10征取, 故有人称“天课”为“什一税”。“天课”由伊玛目(注:伊玛目: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教长。)负责征收,原则上须缴实物。“天课”的用途在《古兰经》中有所规范:“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账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旅途中穷困者”(注:马坚译《古兰经》58:12、13;9:60;9: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故此,“天课”习称“济贫税”。“天课”的设立体现了宗教共产主义精神,这在佛教与基督教中亦可见到,但它并不能真正消除社会中的贫富差异。
二、人头税:推行伊斯兰化的一柄利剑
人头税,亦称“人丁税”、“丁税”,是以人作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税。这一税种在古代世界曾普遍实行。由于它不考虑纳税人的财产状况,后在各国渐被废除。中国清初推行的“摊丁入亩”在赋税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即体现在第一次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头税。
伊斯兰教在扩张过程中,遍征人头税,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宗教赋税,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古兰经》第九章载:“当抵抗不信真主及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缴纳丁税。”(注:马坚译《古兰经》58:12、13;9:60;9: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由此可知,伊斯兰教向异教徒征收“人头税”是为了使他们屈从或改宗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曾将通过契约而征服的地区内的居民,分为两类:一是多神教徒,他们只能在死亡或皈依伊斯兰教之间进行选择;二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经人”),他们如欲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必须缴纳“人头税”。
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这一体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宗教的扩张与领土的扩张并行,所谓“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为推行“两化”,阿拉伯人一方面奉行刀剑政策,另一方面又辅以强制性的经济手段,前曰“圣战”,后者征收“人头税”。穆罕默德逝世后,其历代后继者们继行推行“两化”政策,终将阿拉伯帝国推向极盛。随着征服对象的变化,“人头税”的征收也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扩大到中亚的佛教徒、北非的柏柏尔人、西亚的波斯人(袄教徒)、南亚的印度教徒等。从史书中可以发现,征收“人头税”确乎伊斯兰教扩张大业中一柄不闻杀戳之声的锋利刀剑。史载,哈里发欧麦尔二世时期(公元717—720年)允许中亚本地居民在改信伊斯兰教后就不缴纳贡税,于是大量佛教徒变成了穆斯林。(注: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 》第68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时,情形亦大抵如此,不少基督教徒弃“天主”而归依“真主”。德里苏丹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穆斯林政权,它的统治者菲图兹·图格鲁克就推行“人头税”政策一事曾颇为自得地声称:“我鼓励我的异教徒的臣民信奉先知的宗教,我宣布凡能背诵教义,变成了穆斯林的人得以免除人头税。这个通告传到了大部分人民的耳朵里,大量的印度教徒都提出请求,并获得了加入伊斯兰教的荣誉”。(注:(印度)恩·克·辛哈等《印度通史》第二册,第463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征收“人头税”何以能起到迫使大批非伊斯兰教徒改变宗教信仰的巨大效果呢?法国学者昂里·马塞一语中的:“被征服人民之所以皈依伊斯兰教,不是缘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少纳捐税”。(注:昂里·马塞《伊斯兰教简史》,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由此我们认为,伊斯兰教的“人头税”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典型地体现了经济对政治的能动作用。但是,对这一作用的评价不可绝对化。异教徒在包括“人头税”在内的巨大经济压力下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起初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当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人的统治弱化或完结时,这些居民的宗教信仰还会有新的变化。以西班牙为例,“光复运动”使之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统治,西班牙人的宗教信仰从此又回到了以基督教为主的轨道上来,伊斯兰教渐亡。北部非洲乃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构成,但直到今天,这里有些部族只在名义上信奉伊斯兰教,而实际上依旧遵从他们祖先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注:(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第23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因此, “人头税”政策只是伊斯兰化的助推器。
不过,从宗教传播的角度看,以“人头税”政策促进宗教的扩张不失为伊斯兰教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之成因当归于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根本体制。“人头税”的推行依靠国家的力量,并服务于宗教与政治。这个关系只有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下方能成立。
三、寺院经济与赋役豁免权
历史上,寺院经济一度十分发达,尤以中世纪为最。以基督教为例,早在七世纪时,欧洲有些国王、贵族为了拉拢教会,而拨赠教会大量土地。那时不少教会竟拥有七千至八千处庄园,而拥有二千处以下庄园的教会只能算是小领主。中国唐代佛、道两教的寺院经济规模亦盛。如唐高祖625年2月15日便赐少林寺地40顷,唐代宗762—763年赐全国诸寺、砚田达千余顷。而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即845 年)灭佛(佛教谓之“法难”),所没收寺院土地即达数千万顷。寺院汇集天下之巨财,但却拥有部分或完全的赋役豁免权。
寺院所特享的赋役豁免权,其指有二:一曰免除财产税,二曰免除丁役、丁税。中世纪的基督教两者皆免。伊斯兰教对其清真寺的地产——“瓦克夫”明确规定免缴财产税。对中国的寺院经济,不同朝代针对不同寺院所赋予的赋役豁免权各有变化,有时丁课俱免,有时免丁纳课(如唐代),有时则丁课俱缴(宋代僧侣们为此纳“助役钱”代役)。寺院所取得的上述或大或小的赋役豁免权原本基于世俗政权对宗教的扶持与利用,以期对方对封建统治提供精神支持。但这种做法不免积久成弊。
一方面,天下财富日益为寺院所占有,而寺院对这些财富的消费多为非生产性的筑寺、造像或其它宗教活动,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则天时曾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其“所费以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注:《资治通鉴》卷205。)由此可见一斑。 又由于寺院经济规模大,加之享有不同程度的赋役豁免权,从而妨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僧侣拥有免役权助长了出家之风,不仅造成国家劳动力和兵源的匮乏,而且大大减少了国家的丁税收入。《魏书·释老志》有载:“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在日本,鉴真东渡前,“自度”、“私度”之风炽盛,其由亦在逃避政府的赋役。唐代宗时都官员外郎彭偃曾主张令僧尼“就役输课”,“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匹;其杂色役与百姓同”,他还估算,这笔收入“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注:《旧唐书》卷127页。)
僧侣们大多不事生产,靠他人供养,靡耗的是国家税收。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就此做过推算,公元778年间, 唐政府为了供养官方僧侣,必须动用一百万名农民所纳税额;公元780年, 国家为供养佛教僧侣,可能要动用全部正常税收收入的五分之一。(注: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第5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寺院经济的流弊必然刺激世俗政府调整它曾赋予寺院的那些赋役豁免权。唐初行“均田制”,僧侣们亦为受田对象,“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注:《大唐六典·户部》。)但政府只要他们纳税而免其丁役。到宋代,这一规定得到改变,僧道不仅要纳地税,而且须服丁役,后者可纳钱代之。在法国,中世纪的天主教长期享有赋役豁免权,但1302年,国王为筹足军费,亦不得不向教士抽取“什一税”。
由此可见,国家对宗教寺院赋予赋役豁免权这一政策具有两面性,一则是对宗教的扶持,二则又以不妨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丁役征募为前提。如此,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一特权具有可变性,从而我们对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的认识便更深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