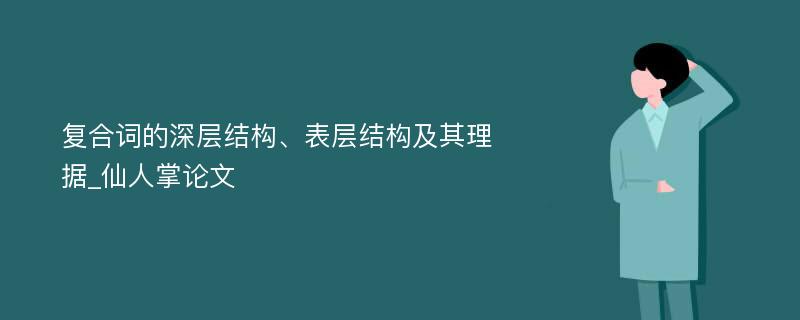
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及其理据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合词论文,结构论文,表层论文,理据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 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2)03-0041-05
一
汉语中有些复合词,常常显得有些荒谬,不合逻辑,无理据可说。这其实是这些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句子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学说。笔者以为,其实不但句子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复合词也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例如:
复合词 父母官 钟鼓楼
深层结构 偏正结构 并列结构
表层结构 偏正结构 偏正结构
“父母官”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一致的,都是偏正式。“钟鼓楼”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却是不一致的,深层是:钟楼+鼓楼。这是两座建筑物,钟和鼓分别放置在这两座建筑物的里面,而不是一座楼同时放置钟和鼓的建筑物。所以是并列式。而其表层:“(钟+鼓)+楼”。当然是偏正式。
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不是一回事情,而且有时是一致的,因此在分析复合词的时候,其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不能混淆的。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词语理据》中说:“‘口罩’,既可以理解为宾动结构(‘罩口’的倒装),又可以理解为偏正(口上的罩、遮口的罩),还可以理解为主谓结构(口被罩住)。”其实,作为表层结构,“口罩”只能分析为偏正结构,其中心语素为“罩”,“口”是修饰性语素。这个“罩”是名词性语素,“口罩”的词性等同于中心语素的词性,是名词,不可能理解为主谓结构或宾动(动宾)结构。但是在其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上,“口”和“罩”可能有三种语义组合的方式:
A.偏正结构:“罩”为名词性语素,戴在口上的罩。
B.主谓结构:“罩”为动词性语素,口(被)罩住了。
C.动宾结构:“罩”为动词性语素,罩上了口。
在这三种逻辑关系中,只有A转化为一个表层的名词, 其余两种逻辑关系只是转化为短语或句法结构,例如:
他的口被口罩罩住了。‖他的口被手巾罩住了。
口罩罩住了他的口。‖手巾罩在他的口上。
B和C类用法并没有词汇化,其结构和意义并没有进入“口罩”一词,所以“口罩”的结构不能分析为主谓结构或宾动结构。同类的词语还有:“眼罩、灯罩、床罩”、“枕套、被套、沙发套”等。
混淆了一个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就很难正确理解其表层结构。例如《汉语的词语理据》中一例:“‘使节’的中心成分是‘使’而不是‘节’,‘使’是使者,‘节’是符节,古代使者持符节作凭证。它的内部形式应是‘持节之使者’,而不应该是‘使者持的节’,所以‘使节’结构方式不是偏正,而应该是‘正偏’。”在古代汉语中,“使”首先是一个动词,是派遣、命令、出使的意思,然后转化为名词,表示使者。“使节”的深层结构其实是:手持符节出使到他国去。其结构模式同“司令、将军”是相同的,都是动宾式名词,由动作而转指人。汉语中的正偏结构,其实是后补结构,通常只是:A.谓词性语素+补充成分,如“扩大、说明、打倒”等。B.名词性语素+量词性语素,如“车辆、马匹、船只”等。
两个名词性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意义也有复杂的一面,例如:
A.酒瓶——装酒的瓶子。
B.瓶酒——用瓶子装的酒。
其表层结构同深层结构是一致的。但是,也有这样的现象:
A式B式
棒冰(上海)冰棒(南京)
盒饭(中国大陆)饭盒(新加坡)
沙锅鱼头鱼头沙锅
A式和B式是同义形式。“我吃冰棒”等同于“我吃棒冰”,“我吃盒饭”相等于“我吃饭盒”,“我吃沙锅鱼头”等于“我吃鱼头沙锅”。A式的表层结构是偏正式,B式的表层结构也是偏正结构。B式的表层结构是不能分析为后补结构的。如果硬是把B式分析为后补结构(正偏结构),那就是用意义分析来代替了结构分析,而在构词法的分析中,是不能混淆意义内容和结构方式的,是不能用意义内容替代结构方式的分析的。
所以说,只有正确把握深层结构,才能看清并妥善处理表层结构。
二
大量的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一致的,分析其表层结构就可以直接推导出其意义来。例如:“心上人、意中人、知心人、知情人、人民币、人情味、同心结、连心锁、连理枝、比目鱼、日光灯、文字狱、文字禅、乡土气、植物人、木头人、鬼门关、国字脸,瓜子脸、鸭蛋脸”等等。这些复合词的理据性是很容易把握的。
由于大多数词语的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结构关系是一致的,是人们所熟悉的,比较习惯的,它就成了一种强势格式。这一来,语言的使用者和研究者很容易忽视另类现象的存在,那就是:有些词语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
深层结构同表层结构相矛盾的复合词,如果是成批量地出现的,至少是有一定数量的,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理解并不困难,寻找其理据性也还算方便。特别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之后,例如,(A+B)+N式——表层结构为偏正关系,深层结构为并列关系。例如:管弦乐(管乐+弦乐)、青红帮(青帮+红帮)、上下文(上文+下文)、中西医(中医+西医)、东西方(东方+西方)、青白眼(青眼+白眼)、教职工(教工+职工)、错别字(错字+别字)、阴阳历(阴历+阳历)、中西餐(中餐+西餐)、南北朝(南朝+北朝)、南北货(南货+北货)、红白喜事(红喜事+白喜事)等等。再如,(A+B)+V式——表层结构为附加式样,词根加上后缀。 例如:指战员(指导员+战斗员)、教职员(教员+职员)等等。由于这些模式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于是人们往往就忘记了其中深层和表层彼此矛盾的现象。
如果这一矛盾只是出现在个别的或极其少数复合词之中,这就会给语言学分析方面带来麻烦,也往往会误导语言的使用者。例如,“花生”,其表层结构仿佛是主谓结构,或者是状中结构(花着生,品种齐全)。其实深层结构是一个复句:花落了(落入地下),然后生出果实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花生被作为生育的象征其实是建立在对表层的曲解的基础上的。这是复合词表层结构多义性的非深层结构意义的产物。
这类复合词的理据存在于其深层结构之中,因此只有揭示出其深层结构,才能把握它的理据性。忽视了它的深层结构,仅仅从其表层结构出发,就会陷入困境。例如,“肉骨茶”是新马华人所喜爱的食品,中国大陆的旅游者在品尝之前,往往以为是一种加上茶叶烹饪的食品,如同“奶茶”、“酥油茶”“咖啡茶”、“人参茶”等一样。这是“肉骨茶”的表层结构误导的结果。在表层结构中,“肉骨茶”只能分析为偏正关系:“茶”是中心成分,“肉骨”是其修饰成分。依据这一表层关系,其意义似乎也只能是:“肉骨的茶”。其表层是很难分析为并列结构的:肉骨+茶。其实,它本来是:同时供应两种食品——肉骨汤和工夫茶。这两者当然是并列关系。在其深层结构中,“肉骨”是“汤”的修饰成分,“茶”的修饰成分是“工夫”。“肉骨”同“茶”没有语义联系,两者不发生结构关系,两者不能相互构成直接成分。
词语的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结构关系的不一致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只有揭示出其深层结构的特殊性,才能发现其理据性。例如,“蛇人”是养蛇、玩蛇的人。“蛇头”不是蛇的头,而是特指一种人。“蛇岛”上蛇特多,或以蛇为特色。“兽医”、“鱼医”、“植物医生”,修饰成分表示的是受事。“儒医”的修饰成分表示的是医生的身份。但是,“蛇医”是给被蛇咬伤的病人进行治疗的医生。其表层结构是偏正结构,“蛇”是“医”的修饰成分。但是,蛇不是医生,医生也不给蛇进行治疗。这是因为,在其深层结构中,“蛇”同“医”并无直接的语义联系,在其结构上不能构成直接成分。“医”只同“病人”发生结构关系,“蛇”亦同“病人”发生语义联系。
三
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的产生,是有其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
其内部原因指的是语言系统内部的因素对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化的制约作用。例如,复合词音节的长短是有严格要求的,是最受限制的,压缩复合词的音节数量是复合词产生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压缩过程,往往会改变复合词的表层结构方式。例如:
A.白条子
B.绿条子、红条子
表层结构都是偏正关系,“白、绿、红”等颜色词都是“条子”的修饰成分。但是在其深层结构中,却是:
C.绿(白条子)、红(白条子)
“绿”和“红”同“条子”不发生结构关系,彼此不是直接成分。在这一过程中,“白条子”中的“白”消失,其中的低等级成分的“条子”在表层结构中上升了一个等级。
“仙人棒、仙人球”和“仙人掌”,表层结构似乎是相同的,都是偏正关系,仿佛其中的“仙人”分别是修饰“棒、球、掌”的。其实,“仙人掌”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一致的,而“仙人棒、仙人球”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不一致的,其深层语义是:“仙人掌科中的形状像棒的植物”,或“样子像球的仙人掌(仙人掌科中的一种植物)”。
“师母”是常用词语,普通人是完全明白其含义而从不思索的。但是它却叫语言的研究者困惑。有一个海外研究生问我:“‘师母’分析为偏正结构,那该是老师的母亲了,然而却是老师的妻子呀!”研究词语理据的语言工作者认为:“‘师母’,意为师傅或老师的妻子,把它看作偏正结构(师的母亲)是错误的,看作并列结构(师和母)却又不能尽如人意。”这里首先有一个结构关系同语义内容之间的非等同性、不一一对应性问题,结构总是简单的,其所蕴涵的语义内容和类型总是多种多样的。把偏正结构的语义内容统统都归结为领属关系,这未免简单化了一些。例如“东坡肉”,恐怕是只能分析为偏正结构的,但是其语义内容可决不是苏东坡身上的肉!这个麻烦其实是其深层结构同表层结构的矛盾所引起的。“师母”的表层结构是偏正关系,不是同位关系。可是其含义不是老师的母亲,而是老师的妻子。其意义内容同结构关系很难对得上号,不好解释。要想比较合理地解释其中的奥秘,就得深入到它的深层结构中去——老师的妻子,我的母亲(比喻式尊称):
A.是我的老师的妻子。(不是老师本人,不是老师的妻子。)
B.我尊称为“母”。(我尊我的老师为“父”。父和母是相对称的。)
在其深层结构中,“母”同“师”不构成直接结构关系。同“师”有结构关系的是“妻”,但是,“妻”字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在其深层结构中,是有一种同位关系的,那就是:“师妻”(老师或师傅的妻子)和“母”(我的母亲)的同位,然而“师傅”(老师)并不同“母”(母亲)构成同位关系。从深层结构转化为表层结构之后,由于压缩(省略),其同位关系就很难为人所接受。
现代汉语中有两个“给”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介词。在句子的深层结构中,本是:“他给给她一本书。”但是,在其表层结构中却是:“他给她一本书。”深层结构中的两个“给”字因为相同语音的连续而省略或重叠了。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复合词中。例如,“大姐夫”一词,有两种切分方式:A.大姐‖夫,B.大‖姐夫。其意义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似乎不能因为切分后的意义基本相同,就认为两种切分同样都是合理的。这正如:A.爸爸的‖爸爸的爸爸,B.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两种切分的意义基本相同,但不能认为两种切分都是合适的。虽然“大姐夫”的两种切分可以指同一个人,但是A式是从其配偶角度来限制修饰的,而B式则是从他自身利益来限制修饰的。
与“大姐夫”同类的,再如:大姑妈——大‖姑妈,大姑‖妈。大舅妈——大‖舅妈,大舅‖妈。大姨奶——大‖姨奶,大姨‖奶。
但是,有的似乎并不是两种切分都可以的,例如:
表姐夫——表姐‖夫 表‖姐夫(?)
姨姐夫——姨姐‖夫 姨‖姐夫(?)
外孙女婿——外孙女‖婿 外孙‖女婿(?)
因为具有姨表关系的只能是姐妹本人,而不是她们的配偶,所以后一种切分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前一种切分也很难成立,因为“姐夫、舅妈、姑妈”等结合是固定的,是为社会所广泛接受了的。外孙是男人,他也不可能有丈夫(女婿)的!
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再分割。其中的语素不能独立地接受修饰或限制,例如“布头”,“小布头、新布头”,修饰的是词,不是其中的某个语素。如果要修饰其中的语素“布”就得说:“新布布头、土布布头、麻布布头、印花布布头”等。再比较:
大气压←大气‖气压
可以认为,表层的“大气压”在其深层其实是“大气气压”,从深层向表层转化的时候,因为两个“气”字的连续出现,为发音方便而省略了其中的一个,于是造成了这种表层结构的重合。“印花布头”可以认为是“印花布‖布头”的重叠省略。
因此,似乎也可以认为:
大姐夫←大姐‖姐夫
表姐夫←表姐‖姐夫
姨姐夫←姨姐‖姐夫
堂姐夫←堂姐‖姐夫
外孙女婿←外孙女‖女婿
侄女婿←侄女‖女婿
这也是语言系统美不胜收的原因所引起的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矛盾。
有些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由于社会的演变,构成复合词的理据的环境消失了,也会导致一些语素意义的变动,相应地出现了深层结构同表层结构之间的矛盾。例如:“胡说、胡搅、胡搞、胡来、胡闹、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胡作非为、胡搅蛮缠”等等。其表层结构都可以分析为偏正关系,其中的“胡”字是不讲道理、蛮横无理的意思。在其共时平面上,这一分析没有错。但是究其产生的原始含义来说,这“胡”字指的是胡人,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些复合词的结构本是主谓式:“胡”为主语,其中的动词性成分是其谓语。这些词语中都有民族偏见的因素。但是汉语在发展,在现代汉语中,“胡”已经从民族的称谓,逐步转化为形容词性语素了,那就不必、甚至不能再分析为一个表示民族的名词性语素了。
四
复句式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也往往不一致。汉语中,有些复合词,居然是一个复句的紧缩,或者是紧缩的复句。例如:“花生”,其实是:花落了,果实生出来了。或:花落了,生出果实来了。第一个分句的谓语省略了,第二个分句的主语省略了。在其深层结构中,“花”同“生”是没有结构关系的。两个汉字竟然是一个复句,真的不可想象。这可以叫做“复句式复合词”。
三字格中的复句式复合词比较多。例如,“生死恋”,其意思是:“生(活着)相恋,死也继续相恋。”这就是一个复句。要构成一个复句,按理说,起码得有四个汉字(其实是“语素”!),于是复句式三字格都是省略复句。例如,两个分句的主语是相同的,而省略其中之一的:“鬼见愁”——两个分句的主语都是“鬼”,第二个分句主语承前省略了。就是:“鬼见了,鬼也发愁。”两个主语相同而全都省略了的,例如:“随身听”——主语是某人,省略了。他随身带着,随时都可以听。
两个主语不同的,省略其中之一的,例如:
人来疯——第二个分句省略,指小孩。可以是条件复句,也可以是因果复句。
胃痛宁——第一个分句的主语是“胃”,第二个分句主语是“人”,省略了。
夜来香——第一个分句的主语是“夜”,第二个分句的主语是“花”,省略了。
两个主语都省略了的,例如:
开门红——某人开门,门外是一片红。
三字格复合词中,谓语也是可以省略的,例如:“龙虎斗”。其实是“龙争虎斗”,是一个并列复句。第一个分句的谓语省略了“争”,因为与“争”和“斗”是同义词,承后省略。
表层结构往往是省略的结果。省略之后的表层结构常常是多义的,例如“老来俏、老来瘦、老来福、老来穷”等,其深层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分句的主语相同而省略了的复句。但是就其表层结构而言,如果分析为偏正结构,应当说是合适的:老来‖俏、老来‖瘦、老来‖福、老来‖穷。
表层结构的多义性,很容易造成误解。例如因为“龙虎斗”的表层结构是主谓结构,本来是:“龙”和“虎”的联合短语作主语——“龙争虎斗”(像龙和虎那样地争和斗),但是,“龙虎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其表层的主谓关系却变成了:“龙”为主语,它去同虎争斗。“介词+虎”作状语,介词省略了,没出现。“龙同虎去相互争斗”于是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于是就出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虎同义意象相反的龙和虎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另类文化意象。
其实,许多复句式复合词,就表层结构而言,分析为偏正结构是比较适合的,例如:人来‖疯、龙虎‖斗、鬼见‖愁、开门‖红、夜来‖香、随身‖听、胃痛‖宁、老来‖俏、生死‖恋等等。既然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不同的层面,对其结构分别采用不同的分析方式,也是应当的吧。
词汇学是语言学中比较落后的一个部门。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寻找新的视角,需要加强方法论原则的建设。本文的目的是:寻找词汇学研究的新视角,探讨复合词研究的方法论原则问题。
(一)乔姆斯基提出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是语法学的概念,构词法本可以认为是语法学中的一个部分。在汉语中,复合词、短语和句子,在其结构方面是很一致的,是互通的。因此把原先用于句子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扩大到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方面,我们以为是行得通的。
(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存在着复合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不一致现象,仅仅就表层结构往往很难真正把握住复合词的结构方式。因为,表层形式中的语素同深层结构中的语素不完全一样,深层结构中的结构关系常常不能在表层形式中得到真实的表现。这就是一些词汇学家反对运用句法结构模式来分析复合词的理由。但是,复合词表层结构分析所遇到的麻烦,并不能证明复合词的表层结构就是不可运用句法模式分析的。所以在复合词的分析中,引进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三)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引进复合词的分析之后,不仅要求给复合词确立合理的深层结构,而且要研究从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运动中的规律规则。从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转化中,制约因素有语言世界本身的,也有非语言的,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因素,应当区别对待。
(四)在复合词的研究中引进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其实就是复合词结构分析从纯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的一个开端。
我们相信,复合词研究中的新视点的引进,是有利于复合词研究的科学化的。
标签:仙人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