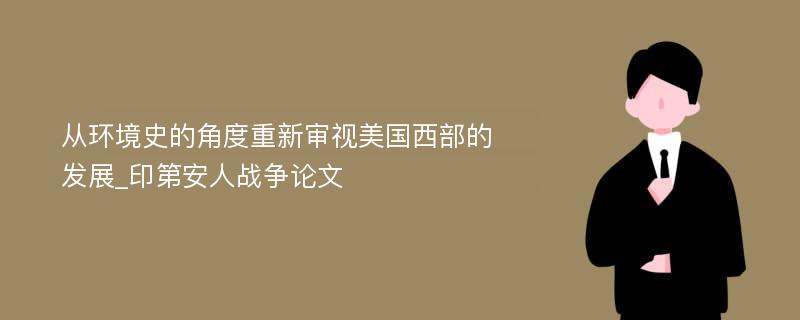
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西部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西部开发论文,重新审视论文,角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2-0107-12
西部开发是美国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在短短的百余年的时间里,北美大陆从一片蛮荒变成了千里沃野,在不断西移的移民潮背后,崛起了小麦王国、畜牧王国、矿业帝国、数以千计的定居点和现代化的城市。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西部开发,就没有今日的美国。传统上,人们总是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美国西部开发,认为“如果人类要走向文明,就必须改变其周围的环境”①。美国西部的环境变迁被看做是文明战胜野蛮、科技战胜蒙昧的一个胜利,甚至历史学家也以赞许的语气描述西部开发:“他们征服了荒野,征服了森林,并把土地变成丰产的战利品。”②
然而,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西部开发却是一部深重的灾难史,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北美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数以千万计的旅鸽、野牛、海狸、白尾鹿等物种相继灭绝或濒临灭绝,大片的原始森林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土壤的盐碱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结果,上一个世纪30年代西部大草原的沙暴(Dust Bowl)为北美西部开发画上了一个终结号。世界粮食组织的代表曾经将美国30年代的大沙暴与公元前3000年中国西北地区森林被砍光和地中海周围的植被被啃食殆尽并列为人类历史上的三大生态灾难。③ 也正是由于剧烈的环境灾难,才使一向认为资源无限、机会无限的美国人幡然醒悟,率先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西部开发,就会发现它所走过的实际上是一条从破坏到保护的U型曲线。因此,研究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环境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客观地认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 新世界动植物资源被破坏和旧世界物种的入侵
北美大陆是一片资源极度富饶、物种十分丰富的地区。当17世纪初白人刚刚登上这片大陆的时候,这里简直就是动植物的宝库。东西两边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东边的森林一直绵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这些树都长得异常高大,波士顿地区早期的记述中称:“该地区的树木长得又高又直,一些树干在抽枝前就高达二三十英尺。”④ 新英格兰和西海岸的一些松树甚至高达250英尺,树龄在4000年以上。⑤ 在东部林区还生长着很多可食用的野果和浆果,如樱桃、葡萄、黑霉、水越橘、覆盆子、草莓、桑葚等。生存于东部森林中的动物物种也非常丰富。据估计,当时北美东部一片10平方英里的森林里,可以生存5只黑熊、2~3只美洲豹、2~3只狼、200只火鸟、400只弗吉尼亚鹿、20 000只灰松鼠。⑥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1624年所著的《弗吉尼亚通史》中,对于新大陆的描述极尽夸张之能事,他说,当冬天来临时,“整个河面都被天鹅、大雁、野鸭及鹤类笼罩着,我们天天都食用上好的面包、弗吉尼亚豆、南瓜、柿子、鱼类、水禽以及各种各样肥得流油的野兽”⑦。当欧洲人刚刚来到北美时,海狸的数量估计在1000万~4000万只之间。⑧ 美国东南部的森林里还生活着大约4000万只白尾鹿。旅鸽这种在20世纪初期灭绝的物种在欧洲人到达北美时,数量大概有50亿只,相当于现在美国所有鸟类数量的总和。中部草原上最典型的动物就是野牛,从阿巴拉契亚山西麓到落基山脚下都能见到这种动物的身影。“当第一批欧洲人抵达北美中部的大平原时,他们发现庞大的野牛群在那里闲逛。这些野牛群,其数量最少也有4000万头左右,很可能总数达到了6000万头。”⑨ 除了北美野牛外,与这片草原气候相适应的其他物种还有鹿角羚、长耳兔和草原鼠等,数量也都非常多。除了这些草食性动物,草原地区最主要的肉食性动物是狼和郊狼。据估计,在白人到达草原前,草原上至少生活着150万只狼。⑩
然而,在美国向西部的开发中,这些动植物资源都遭到了疯狂的破坏,从而使得西部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遭殃的是森林。在北美历史上,一度曾经出现过方木边疆。英国海军将眼光瞄准了北美东海岸生长着的高大树木,结果“新英格兰的森林成为维持英国海军力量的一个关键因素”(11)。海军测量员在每棵被选作海军军舰用木的树上都标上箭头。除了海军用木外,东部优质的木材还是制造地中海酒桶的上好材料。当时的锯木厂效率低下,只用上等的木材,其他次等的都浪费掉了。许多北美人夏天耕种,冬天就转入伐木营去砍伐树木。除了专业的伐木业外,农民为了开垦耕地,建立农场,更是不分好坏地肆意清除树木,通常的办法是环剥法,即在树下将树皮环剥一圈,使大树枯死;更具有危害性的则是放火焚烧,有时候这种火会蔓延成森林大火,失去控制,将很大范围的森林都统统烧光。除了农民毁林开荒外,取暖用柴也是造成北美东部森林迅速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1826~1827年冬天,仅费城一地就烧掉了11平方英里的森林。(12) 当时一个新英格兰家庭一年的平均用柴是30~40克德(cord),相当于4800立方英尺的一堆木头,至少要1英亩森林才能提供这些木材。正是由于如此大规模的浪费和肆意砍伐,北美东部的森林消失得很快,一般一个镇建立15年后就会面临木材短缺。1749年访问新英格兰的瑞典生物学家皮特·卡尔姆(Peter Calm)对于美洲人浪费木材的现象深感吃惊:“难以计数的木材实际上在这个地区被用做烧柴而浪费了,整个冬天的日日夜夜,即几乎半年的时间里,在所有的房间里,火都不停地燃烧着。”“我们在瑞典和芬兰对于我们森林的敌视也没有这里更大: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将来。”(13) 正是由于白人的肆意破坏,到1800年,新英格兰南部3/4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森林。随着东部森林的消失和西部开发,铁路用木、建设用木和工业燃料用木的数量都大幅度增加,大湖区的森林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西部主要的木材来源地。1856年,芝加哥取代阿尔伯尼成为全国的木材交易中心。在木材交易的盛期,芝加哥的晒木场上常年晾晒着500万立方英尺的木头,这些木头需要砍伐25万棵大树,覆盖上百英里的范围。(14) 1876年,加拿大木材商约翰·利特尔(John Little)撰文称,大湖区的伐木者“不仅两头点燃蜡烛……而且还把蜡烛一切为二,四头同时燃烧,以加快木材耗竭的速度”。当时他还遭到当地《西北伐木者》主编的攻击,可仅仅10年以后,连该报也不得不承认:“以前认为不可耗竭的白松和霍威松(horway pine)木材的末日即将来临了。”(15)
随着森林一道消失的还有这里原来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火鸡在17世纪还在新英格兰地区成群地活动,当时一只40磅的火鸡可以卖4先令;可到18世纪,就很少见到了,以至于连名字的来源都忘记了。到18世纪末,鹿在北纬44度以南已经很难看到,殖民地史学家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wan)记载道:在缅因地区,“麋鹿这种大型动物,以前还数量很多,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一只了”(16)。甚至连旅鸽这种数量达到50亿只的动物,也没有逃脱灭种的命运,野外的最后一只大约是1900年死于俄亥俄,全世界最后一只旅鸽“玛莎”1914年也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里孤独地死去。
丰富的毛皮动物资源曾经使得毛皮贸易成为北美历史上堪与农业开发并提的一种边疆开发形式。毛皮贸易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竞争状态,最明智的办法是在其他竞争者到来前尽量捕猎,把一片空白留给对手。例如,19世纪20年代后,哈得逊湾公司总裁辛普森针对有争议的落基山西南部地区而要求他的员工:“该地区海狸资源非常丰富,基于政治原因,我们应该设法尽可能快地努力去猎光它。”(17) 这就是海湾公司所采取的著名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疯狂的灭绝式捕猎,导致这些珍贵的毛皮动物在多处灭绝。1640年,海狸在哈得逊河流域和马塞诸塞海岸一带绝迹;到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海狸几乎完全消失;到1831年,海狸在北部大草原上也灭绝了。北美东南部的弗吉尼亚鹿和草原上的野牛也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命运。18世纪四五十年代,查尔斯顿每年平均运出17.8万张鹿皮。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贸易盛期,每年大概要捕杀100万只鹿。(18) 到19世纪末,曾经数量庞大的弗吉尼亚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由于需要满足西北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的牛肉饼供应,梅蒂人到1850年就已经把马尼托巴地区的野牛都杀光了。在1873年以后,随着野牛皮制革的成功,野牛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捕杀,在1872~1874年,每年被杀死的野牛高达300万头。结果,在短短的数年内,野牛的数量从原来的上千万头锐减到200余头。1889年1月调查的结果是:在勺柄地带有25头,科罗拉多山脚下20头,黄石河到密苏里河之间10头,大霍恩山附近26头,黄石公园200头。(19)
美国西部开发不仅是本地动植物资源遭到疯狂破坏的历史,也是物种变迁的历史。“生态学上的偷乘者是随着最早的居民开始来临的。”(20) 在殖民者向美洲移民的船上就搭载了旧世界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在1609年,当弗吉尼亚才刚刚奠基时,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发现,他们所储藏的食物几乎被数以千计的老鼠给吃光了,因而不得不靠打猎、采集和印第安人的救济而过活。(21) 除了老鼠之外,在新世界繁衍的旧世界的动物还有猪、马和牛。猪由于适应性强、繁殖率高而颇受早期殖民者的欢迎。马的祖先原来在美洲,可后来在这里灭绝了。马又重新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了这里,有些马走失或被放野,成为北美草原上的野马。在有些地方,野马数量变得如此多,“从而使它们实际上成了令人讨厌的家伙”(22)。牛也是同殖民者一道来到新世界的首批移民,它们与猪相比,更有优势:可以消化掉人所不能消化的粗纤维,将它们转化成人类所需要的奶、肉和皮革,牛因此也深受殖民者青睐。在18世纪初期,根据约翰·劳逊的观察,卡罗来纳的牛已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一个人就可以拥有1000~2000头牛”(23)。蜜蜂也是被殖民者从旧世界引入的新物种之一,在17世纪20年代,它就随着移民们来到了弗吉尼亚,并迅速在北美东部繁衍起来。印第安人称蜜蜂为“英国苍蝇”(English flies),认为“它们向内陆的推进是白人临近的前兆”(24)。蜜蜂在1792年蔓延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除了上述这些动物之外,其他像鸡、鸭、羊等家畜和其他的昆虫和野生动物也都在美洲安下了家。
旧世界的植物也是在新世界安家的首批生命之一。除了欧洲人带到美洲的农业品种外,不经意来到的还有野草。据瑞典植物学家彼德·卡尔姆的研究,大多数欧洲野草早在1750年就在新泽西和纽约扎根了。(25) 在17世纪后半期,至少有20种野草在新英格兰安家落户。车前草被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Englishman's foot),意即英国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可见到这种植物的影子。另外,像白三叶草、蒲公英、肯塔基六月禾、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等也都在北美扎了根。(26) 19世纪初,当杰斐逊总统任命生物学家古斯蒂斯(Custis)探查雷德河地区时,古斯蒂斯在那里发现了16种欧洲物种。(27) 在今日的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其中177种明确地来自欧洲。(28) 上一个世纪初对圣华金河地区的调查表明:引进的植物在草地类型中占到了植物品种的63%,在林地中占66%,在灌木中占54%。(29)
除了这些动植物品种外,殖民者随身携带的旧世界的微生物和病菌也一道侵入美洲,给印第安人造成致命的威胁。
二 西部开发史是一部人为的自然灾难史
物种变迁和本地动植物资源遭疯狂破坏仅仅是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一个方面,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征服自然、文明战胜野蛮的观念的指导下,美国西部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生态悲剧。除了动植物资源外,西部的土地、矿产和水利资源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几乎每个西部行业的兴起都伴随着对环境的巨大破坏。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西部山区的采矿业。矿业边疆所信奉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早期的淘金实际上都是在印第安人土地和公共土地上的非法采矿,淘金者为了赶在别的竞争者到来之前尽量多地获取财富,根本无视自己的行为对自然的破坏。数以万计的淘金者分散在从太平洋海岸到大草原以西的山区乱开滥挖,“许多人的双手,把这一片原来无疑是很美丽的风景破坏成为一系列难看的深沟。峡谷中丛生的松树,尤其是积雪长时间不化的山坡上的松树,已经完全不见了。树桩已经因寻找燃料而被挖出,遗留下土壤流失的丑陋疤痕。由于开矿和研磨而堆积的黄色废矿石一堆堆散布在圈起来的山坡上”(30)。
在矿业边疆中,对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当数一些大公司所惯常采用的水力采矿法。这种方法用高压水龙头洗去矿脉上面所覆盖的表土和沙石,然后再进行开采。被水流冲刷下来的沙石随着废水流进河道,使河流的沉积物增加,“在河谷下游成千上万亩肥沃的土地,被上游水力采矿浚流下来的垃圾毁坏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水利采矿所冲刷下来的沙石在有些山谷中堆积高达100英尺,甚至连玛丽维尔(Maryville)和尤巴城(Yuba City)也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抬高河堤来阻挡洪水。尤巴河的河床每年抬高1/3英尺,萨克拉门托河河床每年升高1/4英尺。(31) 1878年的一次决口把萨克拉门托和玛丽维尔变成了汪洋中的孤岛。根据工程师的计算,到19世纪90年代,水力采矿所带来的沙石在这里共掩埋了39000英亩的农田,并对另外的14000英亩农田造成了部分损害。然而荒唐的是,当农场主状告采矿公司要求赔偿时,采矿公司的理由竟是:他们有权往河里倾倒废沙石,而且他们采矿在先,农场主应该意识到这种后果!(32)
大草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消失的地方,也是生态灾难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野牛的灭绝仅仅是大草原生态灾难的预演。随着牧人和农场主的进入,更大的生态灾难还在后面。在美国内战后的20年里,大草原目睹了开放式放牧事业从快速崛起到灾难性结束的全部过程。从60年代开始,许多白人牧场主就在西部草原上非法圈占土地,从南部赶来小牛,在大草原上饲养。“到1880年,养牛业已经在整个大草原深深扎下了根。”(33) 西部开放式的牧牛业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它存在的基础是广阔的所谓无主土地和牧草的自由占用。片面追求眼前利益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牧牛数量的疯狂增长,严重超过了草原的载畜量,在1880年后短短的5年时间里,怀俄明的牧牛从无到有,发展到900万头的存栏量。
就在草原上的牛越来越多时,形势逐渐向着不利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牧羊业的兴起,草原上羊的数量越来越多,对牛的牧草构成严重威胁;草原上可供自由放养的土地越来越少,农业边疆不断向西部推进,更使大批的牛向原来已经拥挤不堪的牧场集中;天公不作美,1885~1886年的冬天是一个狂风呼啸的严冬,冻死了很多牛,而第二年的夏天又炎热干旱,牧草生长不善,根本满足不了牛的需要。忍饥挨饿的牛面对的1886~1887年的冬天又是西部草原上为数不多的严冬之一,气温下降到零下68华氏度,这年冬天“南部牧区高达85%的牛群,或饿死,或冻死……接着,1886~1887年传奇般的冬季,残酷地狠狠抓住平原不放,搞得人畜都恐慌。等到解冻之日,篱笆旁,深谷中,瘦骨嶙峋的死牛堆积如山。北部平原牛群的损失估计高达40%~50%”(34)。牛价下跌和恶劣的天气使得无数牧场主破产,连著名的斯旺牧牛公司也在1887年因连续亏损而倒闭,开放式放养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
然而不幸的是,1886~1887年开放式牧牛帝国的崩溃并不是西部人疯狂破坏自然的结束,恰恰相反,更残酷的破坏和更严重的灾难还在后面。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草原所需要的内外条件都逐渐完备:铁丝围栏的发明,农业机械的改进,旱作农业种植方法的应用和耐旱作物品种的推广,为草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草原上迎来了新一轮的湿润周期和日益看好的市场行情。从1865年到1905年正好是一个多雨的周期,而欧洲市场上对美国小麦的需求有增无减,1880年,有1.53亿蒲式耳小麦卖给了英国,获利1.91亿美元。小麦的利润相当可观,“如果碰上好年成,种小麦的利润就相当于畜牧业10年的收入”(35)。就在科技进步为美国人扫清垦殖大草原的障碍的同时,美国人的自信心也在膨胀。从专家到普通农场主都相信“雨随犁至”(Rain follows plough)。提出“雨随犁至”这一著名观点的C.D.威尔伯甚至狂言:“上帝没有制造永久的沙漠,人是进取性的,因而,除了人类允许或忽视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沙漠。”(36)
虽然在科技进步和大好的外部环境下,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发西部草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西部的生态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降水少,春夏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其次,虽然美国人狂妄地认为“雨随犁至”,然而,西部的降水非常不稳定。整个西部开发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旱作农业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丰水年份,这种耕作模式创造了奇迹。然而,当干旱年份到来之时,这种方法就不灵验了。根据对西部树轮的分析,学者们发现:从1406~1940年有11个持续10年以上的干旱周期,10个持续10年以上的湿润周期。(37) 再次,西部开发是一种典型的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是建立在传统的征服自然观念之上的,奉行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1936年成立的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了这个区域的定居情况后认为:“一种强烈的投机心理……一直是开发驱动力。大部分居民大概都想为他们自己建立家园和农场,但是很多人的目的却是想投机获利。这一点受到了公共土地政策的激励,在一种扩张主义决策的指导下,它几乎不考虑这个区域长远的稳定。”(38) 在这种掠夺自然、征服自然的法则的指导下,每个农场主所考虑的都只是眼前利益,都天真地相信西部资源无限、机会无限,明天会更好。甚至到了大沙暴肆虐的1936年,堪萨斯一位名叫艾达·沃特金斯的农场主还信心十足地宣称:“我猜仁慈的主正想把我们重新带领到希望之地。5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片沙窝的荒漠之中,而现在,充沛的雨水将把我们带到高山之巅,而不远处就是富饶的迦南之地,小麦飘香,繁荣重新降临。”(39) 这种滥用科技、盲目乐观、违反自然规律的胡作非为的结果,必然是严重的生态灾难和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此外,原来的市场和气候条件正在逐渐消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相对丰沛的降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支持了小麦经济的繁荣。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席卷全球的大危机沉重打击了西部农业,农产品价格直线下跌,以加拿大西部草原为例,从1928年到1932年农业收入下降了82%,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原来的18%下降到5%。大危机对于“依赖资源的产业意味着灾难,而对于几乎完全仰仗于一种资源的经济则预示着完全的崩溃”(40)。而30年代相对较少的降水和高温更使西部的情况雪上加霜。从1930年到1936年,美国整个大陆除了缅因和弗蒙特外,年降水量都比正常年份低15%以上。除干旱外,还有罕见的高温,1934年,内布拉斯加的最高气温达到华氏118度,艾奥瓦115度,伊利诺伊100度。(41)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终于出现了美国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30年代的沙尘暴。30年代第一次比较大的沙尘暴发生在1934年5月9日,从蒙大拿、怀俄明席卷而来的风沙以每小时超过100英里的速度一路咆哮着吹过达科他,携带着3.5亿吨沙尘卷向东部城市。当晚,芝加哥落沙1200万磅,平均每人4磅;5月11日早晨,波士顿受到风沙的袭击,第二天,连东南部萨凡纳的天空也变成了灰色,300英里外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船只也有沙尘飘落。(42)根据美国土地保护局的统计,整个30年代,能见度不到1英里的天数,在1932年有14天,1933年38天,1934年22天,1935年40天,1936年68天,1937年72天,1938年61天。(43) 如此大规模的沙尘暴肆虐的结果是大草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堪萨斯西部、科罗拉多东南部、新墨西哥的东北部、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交界的勺柄地带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1000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暴中心(Dust Bowl)。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44) 严重的沙暴还使得草原上的大批牲畜渴死或呛死,并导致风疹、咽炎、支气管炎等疾病在草原上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1939年,《达拉斯农业新闻》哀叹:大草原,原先是鹿、野牛和羚羊的家园,现在则成了沙暴和联邦工程管理署的家。(45)
美国历史学家马林曾经将西部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西部独特的气候,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批判了马林的这一观点,指出:“生态学家在30年代所辩论的尘暴,是美国在适应自然的经济体系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失败。”那种个人主义的、以掠夺自然为基础增殖个人财富的文化价值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大平原委员会1936年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名为《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中指出,沙暴的产生是一系列美国传统观念的作祟,“他们认为大自然是被使用和进行开发的某种东西;自然可以随意按人的便利去塑造。从表面上看,这是事实……然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已经说明,自然基本上是无伸缩性的,它要求遵从……现在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在于使大平原上的农业经济适应周期性的雨量不足而不是充足的雨量,是适应风刮过干涸、松弛的土壤的破坏性影响,而不是首先去适应暂时的小麦或牛肉的高价格。这是我们的方式,而不是自然的,我们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46)。
三 印第安人成为西部开发的生态牺牲品
美国向西部的不断拓殖,也是不断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侵占他们土地的过程,最后,土著人战败,被赶进了白人划定的保留地,过着屈辱和悲惨的生活。美国西部史就是一部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史,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已经广为人知,毋须多言。不过,如果我们从环境史的角度看待西部开发中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就会发现: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印第安人的生态灾难史。土著人拥有白人所需要的两种东西——毛皮和土地。由此形成了两个种族之间两种不同的交往关系,即毛皮边疆和农业边疆。在农业边疆中,白人从印第安人那里需要的只有他们的土地。所以,自从殖民地时期起,垂涎于印第安人土地的殖民者就否认印第安人的土地主权,殖民地的领袖温斯罗普鼓吹:“对于新英格兰的土著人来说,他们没有占据任何土地,既缺乏任何固定的居所,也没有哪种家畜来改善土地,所以,他们对这些土地除了自然权利外没有其他权利。”(47) 1817年,甚至连美国总统门罗在向国会的报告咨文中也公然声称:“地球是被交给人类来承担它所能够的最大限度的人口的,除了维持自身需要和生存外,任何部落和种族都无权阻止其他人对土地的占有。”(48) 而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同那些该死的森林一样,必须当做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49)。由于白人背信弃义窃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引发的战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而一贯的结局都是随着美国边疆的不断向西部推进,印第安人不断战败,土地被剥夺。
毛皮贸易不同于农业边疆,农业边疆中“那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的印第安人’的口头禅,从来没有被应用到毛皮贸易之中”(50)。毛皮贸易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51)。“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这边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那边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友谊’的唯一基础。”(52) 为了能得到持续的毛皮供应,这种经济形式需要保存北美毛皮产地的原始状态,与农业边疆那种大规模的砍伐森林、改天换地的情形相比,可以说是在北美诸多经济形式中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的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保护环境和与自然和谐的。毛皮贸易以其特殊的方式同样在北美历史上制造了惨烈的生态灾难。
首先,毛皮贸易所导致的许多珍贵毛皮动物的加速灭绝,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由于白人来到后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物种的灭绝,印第安人所依靠食物的断绝,许多部落陷入了饥饿的境地。早在1642年,纳拉甘西特湾地区的印第安人酋长梅安特努莫(Miantonomo)就敏锐地看到了白人到来所造成的生态变化:“我们的祖先们拥有很多鹿和毛皮,我们的平原上有数不清的鹿,林子里有数不清的火鸡,我们的池塘里也满是鱼虾和水禽。而这些英国人占据了我们的土地,他们用大镰刀割去了草,用斧头砍倒了树木;他们的牛和马吃掉了草,猪弄坏了我们盛产蛎蚌的海滩,而我们却只能忍饥挨饿。”(53)
其次,毛皮贸易在给毛皮动物造成灭顶之灾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印第安人是否可以定义为“生态的居民”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印第安人的确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生态伦理传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准则去苛求他们符合我们的规范。可是自从卷入毛皮贸易后,印第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白人猎捕毛皮资源的杀戮工具,这“显然背离了他们原有的价值观”(54)。一旦涉足毛皮贸易,印第安人猎杀动物的性质就变了,“随着毛皮贸易的加剧,卷入其中的土著部落开始了从为生计而捕猎向着为海湾公司而捕猎的转变,杀死的动物远远多于他们本身所需”(55)。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每年猎获的毛皮一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需要为依据,如地处弗吉尼亚鹿密集地区的克里克人在卷入毛皮贸易前,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25~30张鹿皮;可卷入毛皮贸易后,平均每年要猎杀200~400只鹿。
再者,白人从毛皮贸易中得到的是丰厚的利润,而印第安人从中得到的则是耻辱和灾难。欧洲工具的到来的确改变了一些部落的生活,使他们获得了暂时的富足。然而,卷入毛皮贸易却使不少土著人逐渐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依赖欧洲商品,从而增加了自身的脆弱性。毛皮贸易还使白人文化中的恶劣因素传入印第安人部落之中,侵害土著人的身体健康和道德观念。“毛皮商人走在最前面,探查最好的土地,把白人的工具和罪恶带给印第安人,以削弱印第安人自给自足经济,为后来的移民铺平道路。”(56) 在白人的所有商品中,有两样最为土著所青睐,对他们的危害也最大:一是枪支,二是酒。土著人最早从法国殖民者尚普兰那里领教到了枪支的威力。自此以后,枪支便在土著人中泛滥起来。“对于一个自己的敌对部落拥有火器的部落来说,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个个都感到不高兴,不可避免地会向竞争者宣战。”(57) 枪支的到来,不仅加快了猎杀的速度,使珍贵的毛皮动物加速消亡,而且还大大加强了土著冲突中的杀伤力。卷入毛皮贸易中的各部落为了争夺交易中间商的地位、欧洲商品和毛皮,相互侵入对方的领地,从而爆发冲突。而冲突爆发后,则更加依赖欧洲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形成恶性循环。据估计,从1620年到1750年的130年间,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有3.6万人死亡,其中有1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占死亡总数的25%。(58)
酒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著名的毛皮商小亚历山大·亨利称:“酒是西北地区的万恶之源。”(59) 在19世纪30年代的野牛皮袍贸易中,“酒是最主要的商品……而且,这些游牧部落虽然需要许多刀子和枪支,但对酒精的渴望是没有止境的”(60)。等真正到达印第安人手上时,每加仑酒平均兑4倍水,实际上每加仑酒可以卖到16美元或者兑换5张牛皮袍子。19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画家卡尔林就曾经听说过600名苏族的武士用1400条野牛舌仅仅换了几加仑威士忌。(61) 饮酒的另一个害处是导致土著人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退化。1753年10月3日,易落魁人酋长向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长官和派来的调查员痛斥白酒带来的危害:“你们的商人们现在除了朗姆酒和面粉外,火药、铅弹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带来。朗姆酒把我们都毁了……这些奸诈的酒贩子,一旦让印第安人饮酒上瘾,就会让他们把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当掉。总之,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毁掉。”(62)
白人踏上美洲的土地后,不仅从印第安人那里拿走了毛皮和土地,破坏了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带来了旧世界的各种传染病菌,包括天花、肺炎、流感、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等,其中以天花对土著人的危害最为深重。传染病的流行使印第安人面临着灭顶之灾。1616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流行了3年之久,深入内地20~30英里。此后,天花就经常在北美各地爆发,其中1633年在北美东北地区爆发的一次最为惨烈,受感染者死亡率高达95%。频繁的疾病打击,使得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减少,在17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新英格兰土著人口的数量从7万多人下降到了不到1.2万,东北部曾经强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Abenaki Indian)的人口从1万人下降到了不到500人。有的学者估计,天花等传染病造成了北美80%的土著人死亡,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5%左右。(63)
针对白人到来后北美所发生的剧烈的生态变迁,许多学者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哥伦布在西印度的出现,是数以百万计的土著美洲人和南北美洲野生动植物的接连不断的灾难的开始。”(64) 而马萨诸塞殖民地长官约翰·温斯罗普却对印第安人的灾难幸灾乐祸,他在1634年5月22日写道:“土著人几乎都死于天花,这样上帝就赐予我们拥有我们财产的权利。”(65) 而一个法国人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加赤裸裸:“接触这些野蛮人后,有一件事我不能对你隐瞒:显而易见,上帝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让给新来的移民。”(66)
四 环境保护主义的缘起
就在美国西部开发凯歌高奏之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认识到所谓的“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生态变迁以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灾难性破坏,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呼吁政府制定措施保护环境,从而掀起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导致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产生和民众的自然观念改变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从国际环境看,浪漫主义对西方传统自然观念的反思,为人类突破机械的自然观、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能。“近代以来,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对象关系模式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笛卡儿—牛顿的机械自然观基础之上的。”(67) 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许多浪漫主义者不惜远涉重洋,到美洲来寻找灵感。(68) 浪漫主义作家们歌颂自然的作品成为改变世人观念的第一素材。
第二,对边疆消失的担忧和资源破坏的反思。随着边疆的消失,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美国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和可以随意浪费的了,意识到了保护的重要性。早在1864年,著名学者乔治·帕金斯·马什在其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名著《人与自然》中,针对美国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批驳道:“地球仅仅是给予了人类使用,不是消耗,更不是肆无忌惮地浪费的权利,人类把这一点遗忘的太久了。”(69) 马什被称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之父,其著作也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源泉”(70)。
第三,生态学的发展为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美国最著名的生态学家克莱门茨提出了“顶级群落”的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大草原上各种生物之间的依存和演化关系。1913年,英国建立了生态学会,著名的生态学家A.G.坦斯利担任主席;1915年,美国人也建立了生态学会。1935年,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标志着这门学科逐渐走向成熟。生态学的发展让一批专家学者认识到了自然界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感到了机械主义自然观的狂妄和灾难性后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呼吁人们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先驱。
第四,美国环境主义先驱们的不懈努力在动员群众、扭转人们的环境观念方面功不可没。在美国,真正以欣赏的目光歌颂和赞美自然的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如华盛顿·欧文、帕克曼、惠特曼等人,其中以亨利·梭罗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作为浪漫主义学者,梭罗深受超验主义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的影响,不仅出版了著名的生态学著作《沃尔登湖》,而且还在他最后的10年里,留下了200多万字的观察康克德森林的随笔。他的《沃尔登湖》成为生态伦理学的经典名著,美国《环境主义者书架》对它的评价是:“这部著作激励了无数自然主义者和倡导返回大地的人们。”
面对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变化,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呼吁保护自然的第一批先驱。《美国的鸟类》一书的作者约翰·J.奥杜伯恩(John J.Audubon)曾经因赞美大自然的美丽而一度成为19世纪早期环境保护的领袖人物,他在20年代到俄亥俄去搜集标本的旅途中,所见到的满眼都是西进运动对环境破坏的痕迹,他深深地感到:“贪婪的锯木场诉说着悲哀的故事,在一个世纪内,美国的森林将会荡然无存。”(71) 画家乔治·卡尔林(George Caltin)是第一个从仅仅悲叹转变到呼吁保护的人士。在目睹了印第安人也疯狂地捕杀野牛的场景后,他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的设想:“在未来岁月里,对美国来说,它所保护和呈现给它的文明化了的市民和世界的是多么美丽和激动人心的标本啊!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72) 亨利·梭罗也是那个时代呼吁保护的先驱之一。1858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呼吁在马塞诸塞的每个城镇都保留一片500~1000英亩的森林,“在那儿,永远不应有一根树枝当柴烧,它为大家所有,为传授知识和消闲之用,男人和女人们可以在这里得知自然的经济体系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梭罗疑问:“在某些土地被赠与哈佛学院或另一个机构时,为什么不能将另外一些土地授予康科德做森林或越橘林用?”(73)
在民间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政府的联合努力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美国保护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它“始于19世纪后期,在进步主义时期开花结果,新政时期走向成熟”(74)。虽然保护主义者都感到美国资源过快消耗和浪费的威胁,感到了保护的必要,但在如何保护,尤其是保护的目的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出现了以约翰·缪尔为首的非功利主义保护和以吉福德·平肖为首的功利主义保护之间的斗争,但最终还是以平肖为首的功利主义保护原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缪尔继承了梭罗等人的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传统。1892年,他倡导建立了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并出任主席,直到1914年去世。对缪尔来说,“大自然既是供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也是供人们崇拜的庙宇”(75)。自然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自然的原始之美,因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保护并不需要带任何功利色彩。而吉福德·平肖则属于“明智地保护,明智地利用”一派,他声称:“保护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76)“保护意味着在最长的时间内给最大多数人以最大限度的好处。”(77) 吉福德·平肖主持创建了美国林业局,并把他的环境保护主义观念贯彻到了上一个世纪初期美国的林业保护之中。
森林资源日益衰竭的状况引起了美国朝野的特别关注,所以,森林保护成为当时的首要目标。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植树法》。1891年,美国的土地法经过修改,授权总统可以从公共土地中划定森林保留地(forest reserve),哈里森总统在该法通过的当年就分别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划定了1239040英亩和1198080英亩的森林保留地。深受平肖和缪尔思想影响的老罗斯福总统更是当时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总统。他不仅再度扩大了国家森林保留地的面积,还设立了5个国家公园、4个动物保护区和51个鸟类保护区。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威克斯法》(Weeks Act),授权联邦政府购买林地以保护可航运的河流的水源供应。1929年,胡佛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对国家森林进行保护。
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建立。在缪尔的努力下,1903年,约塞米蒂谷被从加州纳入国家公园系统,从而奠定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基础。1908年,缪尔又领导了著名的反对修建赫奇赫奇水库的环保运动,虽然没有能够阻止国会在1913年最终批准修建大坝的法案,但通过这场运动却唤醒了民众的环保意识。缪尔去世后,在另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斯蒂芬·马瑟的领导下,美国国会最终在1916年通过了《国家公园法》(National Park Service Act),建立起了国家公园管理局(NPS)。1919年,大峡谷也被开辟为国家公园。
上一个世纪30年代肆虐的沙尘暴引起了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1933年3月,建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CC);1933年5月,设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对田纳西地区进行综合的治理和开发;1934年7月,罗斯福又拨款1500万美元筹划在西部建立风沙防护带;同年,国会还通过了《泰勒放牧法》(Taylor Grazing Act),其目的是“通过制止过度放牧和水土流失而防止对公共放牧土地的危害,保证土地的正常使用、改善和发展,并稳定依靠公共土地放牧的畜牧业”(78)。1936年,政府成立了“大平原调查委员会”(Great Plains Drought Area Committee),授权对大草原的生态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该委员会调查了占美国40%面积的土地,在其提交的名为《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中指出:13%的土地已经遭受轻度退化(即植被价值退化了25%),37%的土地遭受重度退化(比原来减少了26%~50%),34%的土地严重退化(退化程度达50%~75%),16%的土地极端退化(退化程度达76%~100%)。报告最后的结论说:“在美国土地占据和利用的历史上,或许再也没有比西部牧场更加黑暗和悲惨的章节了。”(79) 根据大平原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邦政府购买了被沙暴严重破坏的600万英亩土地,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奠定了当今希马龙国家公园的基础。(80)
进步主义时期联邦和地方政府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出台,一系列森林保留区、国家公园和国家纪念地的建立,无疑奠定了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是功利主义的保护,其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人类的持续利益,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如缪尔所主张的那样保持自然的原貌,因此,在保护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反自然的行为。而且,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生态状况在这个时期仍然在继续恶化。针对由所谓保护而产生的新的生态灾难,尤其是大沙暴和生物调查局的行动,一些有远见的生态学家对于上一个世纪初期的功利主义保护原则逐渐提出了质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尔多·利奥波德。他在40年代创立了著名的大地伦理学说,他后期的主要思想集中在他的遗著《沙乡年鉴》之中,他在该书中写道:“在Home Sapiens(人的生物学名称——引者)仍然扮演着征服者的角色,他的土地仍处于奴隶和仆人的地位的时候,保护主义只是一种痴心妄想。”“当某事物倾向于保护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之美时,它就是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81) 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像缪尔一样,利奥波德的理论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接受,但到了1962年,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在该书中,作者写道:“控制自然是一个傲慢自欺的词组,始自生物学和哲学的最原始时期,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是为了人类的方便才存在的……如此原始的科学使用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在转而用来对付昆虫的同时,也转而用来对付地球。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令人惊恐的不幸。”(82) 卡逊的著作引发了新一轮的环境保护主义高潮,有人把她比作环境保护中的斯托夫人。在这股大潮下,梭罗、缪尔和利奥波德等人的思想重新得到重视,生态保护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词汇。1964年,美国通过了《荒野法》,标志着美国政府放弃过去功利主义的保护原则,开始着手建立荒野保护体系。如今在黄石国家公园最流行的保护观念是:“大自然知道如何是最好的!”(Nature knows best!)
结语:以史为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美国的边疆开发由于集合了当时最主流的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也最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三百年边疆开发的历程实质上是三百年环境破坏的历程,是过去几千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前我们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片面地夸大人对自然的能动性,把人类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片面地以产量的增长作为考察的依据,不考虑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因此,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美国的西部开发应该终结于上一个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沙尘暴,它标志着西部花园神话的彻底瓦解和延续了无数代人的传统的自然观念和生产方式的终结。也正是由于边疆开发中的致命破坏,才使乐观的美国人幡然醒悟,率先采取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措施,从而向着新的人与自然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提出,原本十分冷寂的美国西部史领域一下子热闹起来,许多学者针对美国的西部开发,对我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许多建议。其实,美国西部开发是建立在资源极端丰富和对印第安人的无情掠夺的基础之上的,是殖民主义大扩张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虽然美国西部开发的确有许多很好的经验,然而它们却并不适应中国的情况,如果说有什么可供我们借鉴的话,大概就是从疯狂破坏环境到走向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了。
人类应当记住:不是地球并不属于人类,而是人类属于地球。诚然,人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从自然中获取生活必需品,通过劳动,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进行改善。我们反对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者彻底否认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存权利的那种偏激观点。但是,其他物种同人类一样也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随意践踏地球上的环境和生灵万物。汤因比曾言:“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是我认为,在允许贪婪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毁灭。”(83)“对人类而言,没有必要放弃必需的物质富裕,但是,从环境保障的观点看,不必要的奢侈是恶行,避免浪费和节约才是美德”(84)。
美国人能够从破坏自然中醒悟,提倡保护自然,相信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炎黄子孙也有能力在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采他山之石,在当前的西部开发中摸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科学发展之路。
收稿日期 2008—04—25
注释:
① 杰罗姆·O.斯蒂芬:《美国西部史:新观点,新领域》(Jerrome O.Steffen,The American West:New Perspectives,New Dimensions),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② 罗德里克·纳什:《荒野与美国人的精神》(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版,第27页。
③ 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美国西南部平原》(Donald Worster,The Dust Bowl:The Southern Plains in 1930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④(11) 威廉·克朗农:《大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William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 and Ecology of New England),纽约:希尔-王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2、110页。
⑤ 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页。
⑥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页。
⑦ 查尔·米勒编:《北美环境史地图集》(Char Miller,ed.,The Atlas of U.S.and Canad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鲁莱奇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页。
⑧ 哈罗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Harold 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经济史学家因尼斯的估计是大约1000万只,而生物学家欧内斯特·塞顿(Ernest Thomson Seden)的估计是大约4000万只。
⑨ 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⑩ 安德鲁·伊森伯格:《野牛的灭绝:1750~1920年间的环境史》(Andrew C.Isen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A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50~192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12) 查尔·米勒编:《北美环境史地图集》,第26页。
(13)(16) 威廉·克朗农:《大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第122、105页。
(14)(15) 威廉·克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3,200、202页。
(17) 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商人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Daniel Francis,Battle for the West:Fur Traders and the Birth of Western Canada),埃德蒙顿:赫蒂格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45页。
(18) 谢波德·克雷克三世:《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现实》(Shepard Krech III,The Ecological Indians:Myth and History),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60页。
(19) 安德鲁·伊森伯格:《野牛的灭绝:1750~1920年间的环境史》,第143页。
(20)(25)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3页。
(21)(22)(23)(28)(29)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年到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许学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190、185、171、160~161页。
(24)(26)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细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Alfred W.Crosby,Germs,Seeds,Animals: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2、38页。
(27) 丹·弗洛里斯:《自然的西部:大平原与落基山区环境史》(Dan Flores,The Natural West: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Great Plains and Rocky Mountains),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30) 拉尔夫·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54页。
(31) 卡罗琳·麦茜特:《哥伦比亚版美国环境史指南》(Carolyn Merchant,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2) 理查德·怀特:《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我的:新美国西部史》(Richard White,It's Your Misfortune and None of Mine:A New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33) 雷·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周小松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下卷,第343页。
(34) 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下卷,第一分册,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
(35) R.道格拉斯·赫特:《沙暴:农业社会史》(R.Douglas Hurt,The Dust Bowl: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尼尔逊-豪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页。
(36)(39)(41)(43) 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美国西南部平原》,第81、33、12、14页。
(37) 安德鲁·埃森堡:《野牛的灭绝:1750~1920年间的环境史》,第18页。
(38)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第275页。
(40) J.康威:《西部在联邦中的历史》(J.Conway,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Region in Confederation),多伦多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01页。
(42) 唐纳德·沃斯特:《大自然的财富:环境史与生态观念》(Donald Worster,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44)(45) 唐纳德·沃斯特:《沙暴:1930年代的美国西南部平原》,第29、35页。
(46)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第278页。
(47) 威廉·克朗农:《大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第56页。
(48) 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天空下:美国西部的环境与历史》(Donald Worster,Under Western Skies: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Wes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49) 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下卷,第28页。
(50) 哈罗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第144页。
(51) A.B.麦克洛普:《加拿大的过去:W·L·莫顿论文选集》(A.B.Mckilop,Contexts of Canada's Past:Selected Essays of W.L.Morton),多伦多: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88页。
(52) 理查德·丹尼斯:《鲁伯特地区文化史》(Richard C.Danis,Ruberts Land:A Cultural Tapestry),滑铁卢:威尔弗雷德·劳里埃3v&th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53) 威廉·克朗农:《大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第162页。
(54)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55) 皮特·纽曼:《海湾帝国》(Peter C.Newman,Empire of the Bay),多伦多:麦迪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8页。
(56) 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第100页。
(57) 布鲁斯·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Bruce Alden Cox,ed.,Native People,Native Lands:Canadian Indians,Inuit and Metis),渥太华:卡尔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58) 邱惠林:《论印第安民族的衰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81页。
(59) 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商人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80页。
(60) 安德鲁·伊森伯格:《野牛的灭绝:1750~1920年间的环境史》,第104页。
(61) 威廉·克朗农:《大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第216页。
(62) http://www.ohiohistorycentral.org/ohc/history/h_indian/life/furtrade.shtml.
(63) http://www.thefurtrapper.com/indian_smallpox.htm.
(64) R.F.达斯曼:《环境保护》(R.F.Dasamnan,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霍博肯: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84年第5版,第53页。
(65)(66)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第213、218页。
(67)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68) 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69) 乔治·帕金斯·马什:《人与自然》(George Perkins Marsh,Manand Nature),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70) 丹尼尔·G佩恩:《荒野的呼唤:美国的自然主义作品和环境政治》(Daniel G.Payne,Voices in the Wilderness:American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71) 罗德里克·纳什:《荒野与美国人的精神》,第97页。
(72) 卡罗琳·麦茜特:《哥伦比亚版美国环境史指南》,第146页。
(73)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第101页。
(74) A.L.里奇·欧文:《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中的环境保护》(A.L.Riesch Owen,Oonservation Under F.D.R.),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Ⅶ页。
(75) 苏姗·阿姆斯特朗、理查德·博茨勒编:《环境伦理的分歧与合流》(Susan J.Armstrong and Richard G.Botzler,ed.,Environmental Ethics: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18页。
(76)(77) 吉福德·平肖:《为保护主义而战》(Gifford Pinchot,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2、48页。
(78)(79) 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天空下:美国西部的环境与历史》,第44、47~48页。
(80) 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期间美国的环保主义政策,可以参见A.L.里奇·欧文《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中的环境保护》一书的相关章节。
(81)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216页。
(82)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83)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7页。
(84) 岸根卓郎:《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