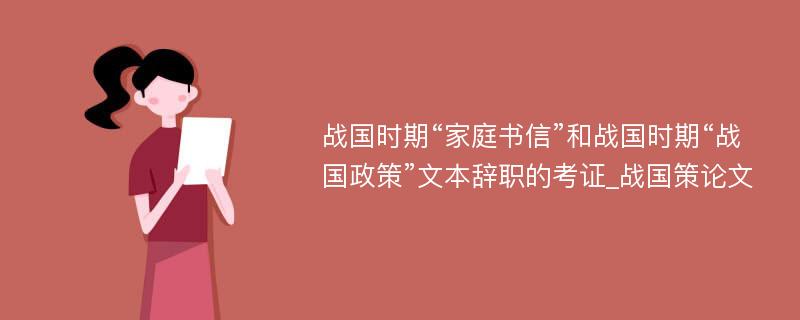
《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文相关辞主问题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策论文,家书论文,战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策》文自高诱注时已涉及辞主问题,其后代有其人,以至于今。特别是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以为司马迁所未见,便将其与《战国策》、《史记》相参照,对帛书的一些“无主辞”予以归名,对《策》文的相关辞主更名。但如此做法,无论是对材料的性质、文学与史料的观念、文学与史料关系认识的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论证方法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学者对帛书辞主的变动,主要是将十五章“无主辞”归名苏秦。原因如杨宽云:“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四章苏秦资料,起首皆未署名,惟其中有六章游说者自称秦或苏秦,其为苏秦所作无疑。帛书第二十二章‘谓陈轸’云云,内有‘今者秦立于门’,而《史记·田世家》改属于苏代,并改作‘今者臣立于门’。帛书第二十一章‘献书赵王’云云,《赵策一》第九章作‘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而《史记·赵世家》改属于苏厉。《史记》中,其他类此者尚有多处,皆当加以校正。”①其他学者如曾鸣云:“帛书四这篇文字,确很重要,首先与帛书一至三有密切关系,另外,它是苏秦治齐交五年中的详细记录。也是他为燕反间的确实证据。”②唐兰认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除了这十四章外,还有四章也与苏秦有关。除了第二十章是后世拟作,此外三章,也应是真正可信的有关苏秦的史料。”③但即使苏秦为燕反间于齐为事实,自称“秦”之人为苏秦,也不能断定帛书一些“无主辞”即为其所作。帛书有与《战国策》、《史记》相同内容的“无主辞”材料,后者人物非苏秦,即可说明这一点。如帛书二二“谓陈轸”者自称“今者秦立于门”,《史记·田完世家》作“苏代谓田轸”,自称“今者臣立于门”。
具体而言,帛书四部分内容亦见《战国策·燕策二》。二者最大区别在:帛书为“无主辞”,《燕策二》为“苏代”;帛书言“臣秦拜辞事”,《燕策二》无。缪文远云:“据帛书,献书者自称其名为‘秦’,则此‘苏代’当作‘苏秦’。”④但帛书中的“秦”是否即为本字?是借代还是实指?为什么帛书与《策》文不同?帛书比《策》文篇幅长得多,且文章结构也大相径庭。《燕策二》已经有人改动,选取了其中几段材料,组合成一篇文章并加了主名。
帛书五内容同时见《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辞主不能改动为苏秦。首先,同归《燕策一》内容,帛书作“人有恶苏秦于燕王”,《燕策一》作“苏代谓燕昭王”,《苏秦列传》作“苏秦见燕王”,差别较大;其次,《史记》记载苏秦材料,基本上采用了与今本《国策》拟托苏秦之名而成的相同材料,只不过为了体例统一的需要,将材料予以排序。这类材料不具备真实史料价值,钱穆曾言:“《史记·秦传》载秦说齐国辞,皆本《国策》,其辞皆出后人饰托,非实况。”⑤所以,根据拟托苏秦之名游说各诸侯王合纵的长篇《策》文,以及《苏秦列传》推断其事迹,既不可行、也不可信。
帛书一六为“无主辞”,《战国策·魏策三》为“朱己”,《史记·魏世家》为“无忌”。整理小组注释云:“《荀子·强国篇》杨倞注引《史记》作朱忌。朱与无形近而误,己与忌通,疑当以朱己为是。”⑥出现这种情况,或是材料来源渠道不同,或是在一篇材料基础上,人为改动。帛书“无主辞”可能为“底本”,其他材料据此改动时加了主名。
帛书二○为“无主辞”,《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均作“苏代”,整理小组定为“无主辞”。原因如唐兰所说:“此篇似摹拟苏秦的口气所作,《燕策》和《史记》均作苏代是错的。此与有名的苏秦合纵八篇,张仪连横诸篇,以及其它,当都是战国末纵横家的拟作,气势都很盛,跟真正的苏秦文笔,宛转而有条理,风格截然不同。”⑦也就是说,整理小组认定前十三章为“真正的苏秦文笔”,但此篇因气势很盛而定为拟作,理由过于牵强。
帛书二一为“无主辞”,《战国策·赵策一》为“苏秦”,《史记·赵世家》为“苏厉”。整理小组据《赵策一》定为“苏秦”,唐兰对改动理由予以陈述⑧。《战国策》中三苏事迹混乱,有时甚至互为对立面,而且三苏材料,有许多为传闻故事,因之很难说《赵策一》、《赵世家》何者为是。综合观之,帛书应是原貌。
至于历代学者对《战国策》文辞主的变动,主要集中在“三苏”(苏秦、苏代、苏厉)及“苏子”。具体可分为:1.改模糊的“苏子”为某人。如《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之“苏子”,高诱注以为“苏代”,姚宏、鲍照同其说。《楚策三·苏子谓楚王》,鲍照以为“苏秦”。《楚策二·女阿谓苏子》,缪文远以为“此苏子当指苏秦。⑨”《燕策二·客谓燕王》之“苏子”,郑杰文以为“苏秦”⑩。2.改“苏秦”为“苏子”。如《东周策·苏厉为周最谓苏秦》,《西周策·楚请道于二周之间》,《齐策三·楚王死》,《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等,鲍照改“苏秦”为“苏子”。3.改“苏代”为“苏秦”。如《燕策一》、《燕策二》多篇出现的“苏代”,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改为“苏秦”。《秦策二·陉山之事》、《齐策五·苏代说齐闵王》、《赵策四·五国伐秦》、《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燕策二·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的“苏代”,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以为皆应作“苏秦”。4.为“无主辞”加辞主。如《魏策二·五国伐秦》“谓魏王”者,鲍照注、吴师道《战国策补正》以为苏代,徐中舒、杨宽、缪文远均以为苏秦。何建章引徐中舒、唐兰之说,以为“徐说或是”(11)。郑杰文以为《东周策·谓薛公》辞主当为苏秦,《秦策三·谓应侯曰》为苏代,《秦策四·说秦王曰》为黄歇,《赵策三·说张相国》为鲁仲连,《魏策二·五国伐秦》为苏秦(12)。5.变“苏代”为“无主辞”。如缪文远以为《魏策二·苏代为田需说魏王》之“苏代”,“疑皆旁注字混入正文”(13),《韩策一·公仲数不信于诸侯》之“苏代”,“或后来所附”(14)。其他变动情况,不一一例举。
对《策》文辞主做如此变动,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如《秦策一·张仪说秦王》,《韩非子》做“初见秦”,鲍照注本删“张仪”。自古至今,学界有韩非、吕不韦、范雎、蔡泽、张仪,张仪作而韩非袭用之,以及“纵人为齐、燕说秦”之说(15)。因为许多情况不明,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证明自己观点的空间,各自也能找出一些证据来立论。“可是都没有直接证据能确切定为某人,还当各依本书为是。”(16)此《策》文应是模仿横人口气作的揣摩游说的无辞主、无题目的一篇练习稿。其中“臣”不是确指,而作为练习游说之辞的惯用语,《战国策》中俯拾即是。“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是设置了“说”和“听”的语境,也是创作练习游说辞的惯用手法。“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是当时行文的一种套语。《墨子·非命上》、《孟子·公孙丑下》、《战国策·楚策四》都有类似说法,只不过《国策》夸张多了。“愿大王有以虑之也”,特别是“大王试听其说”,是游士模拟创作游说辞的熟语与标志。文中之所以两次出现重复,可能是有人连缀不同材料而成,故《张仪列传》未采用。《国策》辞主为张仪,有几种可能:1.本为托名张仪而为辞;2.先有此文,后加张仪游说背景;3.编《国策》者所加;4.注释入正文。此类《策》文,辞主不仅不可随便改动,内容也不能轻易增删。如《燕策一·宋伐齐》不能据帛书二十删结尾几句。因为这样的思路,是认为帛书为“真”,故“自‘燕昭王善其书’至章末,帛书无,《策》文当据《史记》录入,所言俱不符合史实,当据帛书删。”(17)
再如《燕策二·客谓燕王》,前为“客”后为“苏子”。缪文远等均认为“客”与“苏子”属同一人,且在认定了苏秦于前284年被齐车裂前提下,将“客”、“苏子”均改为苏秦。但《策》文客谓燕王的首句,与苏子谓齐王的首句重复,似不应出于同一人之口。其时间跨度自“三覆宋,宋遂举”,一直到“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显然是讲述故事的口吻。要将“客”与“苏子”考实为苏秦,既不符合史实,也非文章原貌。再如《燕策二·赵且伐燕》。缪文远以为“此‘苏代’盖策士虚拟,嫁名之者”。却以为《齐魏争燕》“苏子谓燕相”“当是苏秦使人告燕相”。(18)主观随意性太强。此类情况,非止一端。
对帛书辞主改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整理者先设定了如此前提:苏秦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反间于齐,帛书为“苏秦的原始资料”,且为司马迁所未见,所以变“无主辞”为“苏秦”。但出土文献为“真”,不代表记载之事必为“真”。至于历代对《策》文辞主的变动,原因更为复杂。
帛书二十四章的二十章为“无主辞”,《策》文也有许多“无主辞”,开创了一种新的行文体例。帛书“无主辞”,《策》文、《史记》加了辞主,从文章形态的演进而言,帛书为原始。帛书内容见于《史记》者有八篇,至少说明这部分司马迁已见。假如果真为司马迁所未见,而其下葬时间又在汉初,更能说明帛书为原貌,不能据《国策》、《史记》变帛书。帛书是与《国策》性质接近的材料之一,所记不一定为史实。用帛书、《策》文、《史记》互证,是将性质相同、来源渠道或不同的材料强为之类比。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材料,可以作为真正的材料来“核实”其他材料。在材料“真”、“假”难辨,事实不明情况下,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帛书出土后仍悬而未决,难以定论,也不好“拨乱反正”。梁启超曾云:“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19)如关于苏秦、张仪行事,先秦文献《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臣道》、《吕览·知度》等有零星评点式记载。银雀山汉墓竹简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以为二人开始“俱事鬼谷先生”,《张仪列传》还以为苏秦比张仪先死。当代许多学者对苏秦、张仪年辈予以推断。如范祥雍称苏秦为张仪的前辈(20),但唐兰(21)、杨宽(22)、徐中舒(23)以为苏秦晚于张仪。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24),事迹更为扑朔迷离。其为燕反间于齐,帛书、《国策》未详其事。《苏秦列传》则记因与易王母、文侯夫人私通,恐诛,乃说服燕王,使之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这两点学者也许以为小说家言,未引起重视。事实真相,今日仍不明。
另外,关于三苏长幼,《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自言“嫂不以我为叔”。但此《策》文类小说,不能做真实史料。《史记·苏秦列传》则言“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唐兰云:“《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25)在注释十他还引用了《魏策二》之“苏代为田需说魏王”,“田需死,昭鱼谓苏代”,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证明“苏代游说诸侯较早,在前四世纪末期,已来往于楚魏燕齐各国,苏秦的事迹要晚得多”。但缪文远针对“苏代为田需说魏王”云:“苏代,相传为苏秦弟,然苏代事本在若有若无间。”(26)针对“田需死”云:“此章与史实不合,乃晚出拟托之作。此章载苏代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则已类于戏剧矣。”(27)《策》文载“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但据《韩非子·内储说下》,犀首死于田需前,用《魏策二》材料来证明苏代活动则不妥。以《战国策》、《韩非子》、《史记》观之,记载苏代活动材料远比苏秦多,其事迹早至燕王哙(前320-前312年在位),晚至燕武成王(前271-前258年在位),时间跨度有六十馀年。但以现有资料,苏氏兄弟序齿难以确定。《国策》中他们有时互为对立面,有时又坚持儒家主张。相关的基本事实不清,就不能贸然改动帛书、《策》文辞主。
再从性质看,帛书、《国策》不是史官实录、记载的材料。1.尽管“战国纵横,史职犹存”(28),但战国之前,史官除“君举必书”(29)及记载诸侯国聘问、祭祀、兵戎等重大事宜,还有“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故有《世本》、《牒记》、《历谱牒》、《五帝系谱》(30)。“牒者,纪系谥之书也。下云‘稽诸历谍’,谓历代之谱”。至战国“废文任武”(31),各诸侯国即使有史官,也很难履行上述职责。故《七国考》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七国云扰,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度,荡然不可复征。”2.史官记言主要是具“教诫”(32)性质的“先王之制”、“先王之训”、“先王之教”、“先王之令”,还有“嘉言善语”、“治国之善语”(33),《策》文显然不具如此性质。先秦“史记”记事的体式,应像《春秋》、《竹书纪年》、《编年记》、《史记·秦本纪》部分材料。即某年、月、日、某地、某事,《战国策》则完全不是这样。纵横家大多出身社会底层,且都不是史官。《策》文应该不是史官的记载,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司马迁感叹“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犹甚”,虽未将“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的“权变”之类《策》文前身材料当做“史记”看待,但又称“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34)3.许多《策》文为传闻故事,而先秦同一模式的故事会不断变化。如《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说顷襄王者为黄歇,《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善谋第九》均以为黄歇上书秦昭王,《文选·辨亡论》李善注引“楚、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校”以为“顿子说秦王”。《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劝其勿入秦者为“苏秦”,《史记·孟尝君列传》为“苏代”,《说苑·正谏》为“客”。这说明不仅司马迁与刘向所见材料不同,刘向本人所见材料也不同。此故事又与《赵策一·苏秦说李兑》基本相同。向宗鲁云:“窃谓本书不记姓名为得,《齐策》以为苏秦,乃传闻失实,史公知其误,改为苏代,子政不敢臆断,故止称客,若《赵策》所载,则误中又误矣。”(35)《齐策四·先生王斗》王斗之语,与《齐策四》公孙弘、鲁仲连语差不多,《说苑·正谏》以为淳于髡。《赵策三·平原君谓平阳君》公子牟告应侯之语,《说苑·敬慎》以为告穰侯。《战国策》与《韩非子》相同的故事有三十馀条,这些材料绝大多数见于平时收集备用的故事集——《说林》及《内、外储说》。其中与《国策》相同的材料,二者辞主等方面多有不一致者。如《燕策一·燕王哙既立》自燕王哙立叙述到燕昭王即位,其间“苏代为齐使于燕”。《外储说右下》一作“苏代为齐使燕”,另一作“苏代为秦使燕”,徐中舒以为“秦”指“苏秦”(36);说燕王者,《燕策一》为“鹿毛寿”,《外储说右下》作“潘寿”;引禹之事说燕王者,《燕策一》作“或曰”,《外储说右下》作“潘寿”。而最大变化是《韩非子》仅为短篇故事,《战国策》则成为一篇完整叙事文。这样的传闻故事,有些情况早已不明,若没有新材料出现,后人就更不清楚了。若以为帛书中出现“秦”或“苏秦”字样就考实为“苏秦”,那么,先秦流传的类似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是否均为实指?先秦典籍中提到的人与事,有其人未必有其事,有其事未必其人所为。4.游士揣摩的练习之作也占《战国策》一定的比例。刘向《战国策叙录》以为“权变”之人,“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将“中书”的部分材料当作个人创作看待。《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也许初具后世“别集”性质。5.《战国策》为材料汇编,若按材料性质分类,可分为不同的“类”。《策》文的形成过程、来源渠道不同,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背景与结果,或其中一项是否为后人附益都未可知。其中同一《策》文,版本不同就会有变化。如《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鲍本无“顷襄王二十年”至“臣闻之”一百十字,有“说秦王曰”四字,或许鲍本别有所本,或许依照他《策》体例改动。《秦策五·谓秦王》谈“始”与“终”一段,与“顷襄王二十年”谈“始”与“终”一段材料,意思基本相同,所以“顷襄王二十年”为模拟游说辞。《齐策五》只有一篇“苏秦说齐闵王”,且为《战国策》文篇幅最长者。缪文远言:“姚宏云:一本无‘苏秦’二字。……鲍彪改‘苏秦’为‘苏子’,吴师道以为‘苏代’并非也。”(37)除了上述原因,战国中、后期拟托创作成为一种风气,《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许多拟托之作,《战国策》也有许多虚构、拟托的作品。《策》文不仅拟托人物,还虚构了事实、地理、时间、事件。如拟托苏秦之文,《秦策一》极力鼓吹“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齐策五》又宣言“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为志,则战功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像“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38)之类现象,从史实看存在真实性的疑问,但若从文学创作看,正好说明人们模拟苏秦之名撰作游说辞。
就史实而言,《策》文大多以当时的“新闻事件”为背景或话题,人物、事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但史料不等于史实,更不能将传闻当成史实,将文学人物当成历史人物。退一步说,若帛书二十七章中的十五章果真为苏秦的书信、谈话,那么苏秦分别自赵、齐、梁献书燕王,其书信应在燕,自赵献书齐王,应在齐。不管在何国,这些书信应在朝廷,属于国家最高秘密,一般人不得而知,要将分散在燕、齐两个朝廷的苏秦书信收集到一起,难度太大。假如前284年乐毅攻破齐都临淄与苏秦反间有关,至前279年齐田单反攻燕,尽收齐之失地,历经多年战乱,即使有这样的书信,也难以完整保留下来。因为朝廷文件与游说之士的揣摩练习之辞,与人们口耳相传,有人收集、整理的传闻或故事,性质应该完全不同。
注释:
①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论上篇”第9页。
②曾鸣:《关于帛书〈战国策〉中苏秦书信若干年代问题的商榷》,《文物》1975年第8期,第28页。
③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见《战国纵横家书》附录,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29页。
④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98年,第944页。
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苏秦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286页。
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61页。
⑦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纵横家书》附录,第138页。
⑧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139-140页。
⑨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463页。
⑩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11)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861页。
(12)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第129-132页。
(13)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713页。
(14)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839页。
(15)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缪文远《战国策考辨》、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所引各家之说。
(16)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17)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923页。
(18)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960页。
(19)梁启超:《古籍真伪及其年代》,台湾“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
(20)范祥雍:《苏秦合纵六国年代考信》,《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4辑,第1-25页。
(21)唐兰:《苏秦考》,《文史杂志》1卷,1941年12期。
(2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23)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1期。
(24)《史记·苏秦列传》。
(25)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130页。
(26)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713页。
(27)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731页。
(28)《文心雕龙·史传》。
(29)《国语·鲁语上》。
(30)《史记·三代世表·序》之《索隐》。
(31)《战国策·秦策一》。
(32)《国语·鲁语下》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语肥也?”韦昭注:“语,教诫也。”
(33)《国语·楚语上》“教之语”韦昭注。
(34)《史记·六国年表·序》。
(35)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第212页。
(36)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第137页。
(37)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362-363页。
(38)《史记·苏秦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