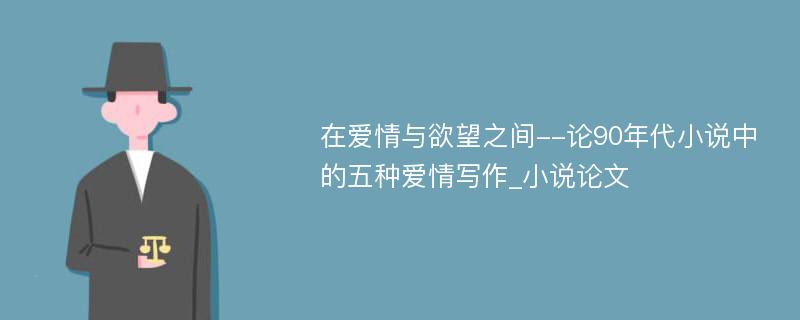
在爱与欲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五种情爱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种论文,情爱论文,爱与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多元文化背景相适应,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表现情爱时显示出了选择的多种可能性,无论是作家的立场、态度、理想,还是具体的表现方式、探索途径,都显示出了迥异其趣的面貌,仅仅用一种模式来概述当下小说中的情爱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当下小说中的情爱书写主要有五种表现方式,即扭曲的欲望书写、赤裸的欲望表达、真诚的精神逃避、无助的揽镜自恋、顺世的情爱合唱。五种截然不同的书写表明了不同的写作群体诠释情爱时所采用的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切入角度,同时也寓示了性别在文学话语中的潜在作用,而我们亦可从这种由作家的独语组成的众声喧哗之中,谛听出某种合唱的旋律与未来情爱的发展方向。
一
要从小说创作中挑选出欲望化书写的典型代表性作家其实是很难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欲望化书写已经由一种个体行为演变为一种群体行为,是当代作家在表达当下现实生活时所无法逃避的书写对象之一。以下的例证其实并不具备绝对的典型意义,而旨在说明这一事相而已。
欲望化书写贯穿于王朔小说的方方面面,《顽主》、《浮出海面》、《动物凶猛》、《许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等等的主人公或者诈骗,或者走私,玩弄感情,欲望直呈,为欲而生,他们丝毫也不隐晦自己的欲望——或者发财或者泡妞。正是这种感情的直接呈现,王朔笔下的这批“末路英雄”、“都市浪人”,才真正获得了生存意义,赢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青睐。其实,王朔的小说在欲望化的书写方面远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粗鄙程度,在他的小说中其实是为纯真预留了一份明静的天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朔的小说所表现出的欲望还是浅层次的、有所保留的、遮蔽的,也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可以在他的小说中读到某种颤栗和焦躁。这种颤栗和焦躁,是在与作品中纯真的人物形象的对读中表现出来的。比如在如下一系列的小说中,都出现了非常纯情的少女形象,如《空中小姐》中的王眉,《橡皮人》中的张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浮出海面》中的于晶,等等。那些堕落中的男人们在面对她们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们,尽量避免伤害她们。在《橡皮人》中,燕生警告“我”说,“别碰她,她不是那种人,不合适”,也许张璐“像小学咱们班的刘良”,“尤其抿嘴一笑”,于是他们陷入了回忆,“我记得当年好特别爱穿墨绿色的灯芯绒衣服”,“老爱哭,算术特别好”,“也不知她现在在哪儿?”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纯真的尊敬。这种对感情“乌托邦”的设置,使得王朔的小说与其它的纯粹欲望化书写区别开来,而没有最终沦落到地摊文学的下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论,原因就在于这部小说对性的大胆、写真、诱惑性的,而其实是很艺术性的描写所致。关于一部小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解是很正常的,反过来说,如果一部小说仅仅只有一种理解,众口一词反而有问题。《废都》的意义我认为正在于他写出了庄之蝶的欲望:生存的,情感的,艺术的,性生活上的,等等。这种欲望其实是很实在的,也是非常具体的,是属于庄之蝶的,而并不是所有人的,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的意义是明显的。我认为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对情爱与性与生存都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而绝非是浅层次的对性的展演。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贾平凹的小说在对欲望的书写过程中,态度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树起了一面正视欲望的写作旗帜。在其后的《白夜》、《土门》、《高老庄》等长篇小说中,他的这种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辩证来看,贾平凹在其欲望化的书写过程中,他的心理上其实是存在着障碍的。我这样说,并非有意贬低他的小说,而是指出这一现象,因为他在对欲望的描写过程中存在着内疚心态,有原罪感。这一点从他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不难见出,在那种放浪形骸的外表之下,其实潜伏着犯罪感,给读者的感觉自然就是颓废、低调的,我们在庄之蝶等人身上体会到的其实很少性的快感,而更多的是负罪的放纵,是必然要后悔的酒后行为。所以说,贾平凹的欲望化书写是有所保留的,是有心理压抑感的。
二
真正能够直面欲望,真正能够将人的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欲望写得像太阳一样明亮,像月色一样美好,而没有丝毫心理障碍的作家要数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了。如何顿的都市题材小说,我们就看不出他在对欲望的书写方面存在什么障碍。发财、女色是都市新生代们的最大愿望,《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是一个典型,他对情爱的理解就是上床。当他向张小英发动攻击而没有成功时,他也还是没事人一般。他对性、钱财的渴望,其实在城市新生代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何顿没有一般作家那样的读书背景,他的生活与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生活距离并不遥远,他了解他们,又没有一般作家那样过分“文化化”后的心理负担。因此,我们从他的小说中不难见出活泼泼的生活原色来。何顿对欲望的肯定化的书写,得益于当下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都市多元化生活情态与读者的阅读期望。
而所谓的晚生代作家们在欲望化书写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邱华栋在《城市的面具·自序》中的一段话,是对这种书写的最好注脚:“对于我,以及像我一样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代人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忆。我们受教育于八十年代,这时候中国开放的程度日趋广大,社会处于相对快速的整体转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社会,经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一切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着,而我们和我的同代人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化的社会中。没有多少文革记忆的我们,当然也就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中了。”正是这种没有思想包袱的创作优势,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学启蒙姿态的失望,晚生代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中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感觉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们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真切,所表达的情感具有真挚与生动,而并不在意所叙写的情节是否曲折与紧张,不在意所表达的思想是否崇高与深刻。朱文将写小说看作是出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认为:“人是一种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他又说:“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这种说法在晚生代作家的创作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他们主张在创作中表现“身体哲学”,直接从身体的感觉出发。通过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来实现其对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的叙述。
在他们笔下,爱情的神圣性被置于可疑的地位,道德伦理更是遭到了嘲笑。无论是朱文的名篇《我爱美元》,还是韩东的小说《障碍》中,读者根本上读不到爱情的影子,有的只是爱情与性错位的游戏,或者只是赤裸裸的性爱场面,主人公之间互相不谈爱情,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性欲的狂热与发泄。
客观地说,晚生代作家们并非为写性而写性,这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实是将“性”当作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来写的。虽然他们自己并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但我们却依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充溢的虚虚实实的性幻想,以及古典意味的浪漫精神中,解读出他们对当下爱情现状的不满与对性乱现实的批判。在他们那里,性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是一种过程而非结果,是一种手段而非全部。
到了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拨,则是直接面对性本身,并且是一种没有方向感和操行感的方式来写作的。他们生活于更本体的感性之中。例如,棉棉的《九个目标的欲望》、《啦啦啦》、《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美丽的羔羊》、《香港情人》、《盐酸情人》,朱文颖的《夜上海》、《霸王别姬》,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魏微的《一个年龄的性意识》,杨蔚的《紊乱》等等,表现出了一种与此前的小说完全两样的“性状态”:更自我,更感性,更随意,纵情、随意、自恋、颠倒、虚无、感伤、紊乱,细节上的绵密细致,透露出冲动的、情欲的、绝望的、迷茫的气息。可以说,这批作家正以其毫无遮蔽的写作形式与表达心态,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另类”写作,欲望化的书写在他们那里表现出了真正的自由精神。当然这批作家远没有到达成熟的境界,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否会顺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或者改弦更张听从阳光的召唤从酒巴中撤退回来,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三
与上述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的欲望直呈不同,另一批富于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的作家,在描写情爱时凡涉及到性爱时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张炜、张承志、邓一光、刘醒龙等等。
张炜的受到评论家们称道的长篇小说《古船》,展览了人性的黑暗、人生的痛苦和历史的无常,意在谋求救渡的希望。他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很容易厌弃人群的喧嚣与浑浊,总喜欢回到真正的自然中呼吸清新的空气,在远离社会的荒原野地守望人类的家园,看护被人事动摇的性灵之根,即人与土地的原始的亲近感觉。在这篇小说中,他明显地把人的天性给压抑下去了。《古船》之后的《九月寓言》,则又造出了一种天地的境界,即将人的活动场所由地面扩展到了天地之间,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之清明,时空顿时开阔无边。张炜热心构筑的理想之境,有人讥之为“文化乌托邦”,虽然批评得过了一些,但是张炜小说对当下现实,尤其是对当下城市文明的反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的确,当下受现代经济挤压和鼓动的人生状态与自然经济时代相比,存在着巨大的恶劣之处。面对这种无序状态,作家采取逃避的立场,企图在另一天地中寻求出生存的意义,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追求的结果,就是作家在客观上对充满人间火味的情爱的逃避,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遗憾。
张承志对凡俗生活的批判是严厉的,无情的。因此,远离现实生活的他,内心里总是非常焦灼、紧张,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宁静的一日,他毫不顾忌地用强悍、狂噪、偏执、激愤,乃至在所不惜的矫情,来向世人倾泄他内心的焦灼不安。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张承志是他自己现实世界中的“漂泊者”,他在自己实际生存的境况中找不到归宿感,而总是渴望着一种在他看来真正充满了深度和质量的绝对的生活。只有在茫茫草原、大坂、高原的广阔之中,他的心灵才能得到安憩,他的沉重的精神压力才能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他醉心于“彼在”的精神世界,因此对“此在”的现实世界失去了忍耐与兴趣,甚至世俗的欲望。张承志就是以这种“荒芜英雄”的浪漫骑士姿态,行走在当下的中国文坛中间。这样我们便多少有些了解《北方的河》中的研究生,为什么离开了可爱的北京姑娘了;也多少可以了解他在《心灵史》里多次宣布,他要“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的沉重心情了。对理想的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的追求,结果必然是对现实琐碎生活当然包括了性爱的逃避。
被视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性作家的刘醒龙,是凭借其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参予而为世人瞩目的,被评论家视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者。而我认为刘醒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者,试想一下,若没有一份理想的浪漫情怀,他是不会在小说中始终给那些有着美好心灵与善良品格的人物,预留下光明的前途的。就是在批评性很强的地方,这种追求与祝愿其实也是存在的。在《挑担茶叶上北京》、《分享艰难》、《凤凰琴》、《村支书》等,小说的主人公面对各种困难时,他总不忘记给他们最终设置一条可行的道路。即使在《秋风醉了》、《菩提醉了》等描写官场的小说中,他也不忘在调侃的戏谑中安排一个合于读者感情之所愿的结局。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刘醒龙是一个内心充满理想主义情感的作者,他分析现实的出发点,很显然与欲望化写作的作家群体迥异其趣。毫无疑问,对性爱的逃避是刘醒龙解析现实生活的一个角度与方式,或者说是一个他选定的切入点与书写姿态。
四
我之所谓的“女性写作者”是指具备女性化写作视角与书写手段的女性作者,那些虽为女性而并不具备上述特色的作者自然不属此列。典型代表有陈染、林白、残雪、徐坤、徐小斌、马丽华等等。她们的名字与作品一再被新时期如“新写实”、“新状态”、“新现实主义”、“先锋文学”、“新生代”、“女权主义写作”等等文学命名中反复例举。由此亦不难见出女性写作的多方位突破和高势位的成绩。
就女性写作而言,从80年代关注与追求两性平等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方舟”、“致橡树”,到90年代开拓与肯定的“与往事干杯”、“致命的飞翔”等等,强调女性“身体语言”的性别经验抒写,再到重新对“黄泥街”、“黑夜意识”颠覆男性霸权话语的确认,最后到“厨房”、“暗示”女性立场的困惑、迷失和展望,关注点的变化,证明着记录着女性文学理论与情怀的发展。而在此中间,对自身身体与内心的迷恋是一条明显的发展路向。
男女两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决定了男女作家在写作同样故事时的不同叙写方式与不同心态的选择。如同样是写“偷情”,在男作家笔下常常成为一次历险式的“艳遇”,一次情感的冒险,一次成功或者并不成功的“回忆”,一次成长的经历,一次“智力游戏”,他总是抱着感激上帝式的心情来书写类似的经历;而女性作家却往往写成为“黑夜”,“创痛”,“撕裂式的痛苦”,“噩梦一样的回忆”。同样是写“婚姻”,男性作家总是将其视为颠沛流离后的归宿,是生活激流中的避风港湾,充满了阳光似的明媚光彩;而在女性作家笔下则成为了“失望”,“最终必然会出走”,“懒得离婚”。这种书写选择上的迥异其趣,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下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通过女性写作者的叙述,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当下的女性的忍耐能力已经失掉了,一去永不回。
当然上述书写的迥异还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诸多原因,我想说的是,女性写作者向内转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既然外部世界是如此的难以把握,既然男性根本上就是一个不可靠的群体,既然市场经济运行下人的冷酷愈来愈明显,那么女性转向于书写更加客观、实在的内心世界与肉体感受便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在《长恨歌》、《情爱画廊》、《玫瑰门》、《一个人的战争》、《双鱼星座》、《私人生活》、《我爱彼尔》、《暗示》、《出售哈欠的女人》、《左手》、《丹青引》等等作品中,我们不难见出女性写作者面对性的态度,充溢的自恋情怀将小说撑得满满当当。自恋式的情爱态度,在小说写作历史上的作用是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即将过去纯粹由男性决定的情爱立场转变为女性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写作者的自恋具备一种写作视角的改变意义,即将读者关注的对象由外在的男女关系,吸引到内在的女性感受上来。而另一方面,自恋化的写作的弊端也同样明显:一是对外在世界的冷漠,使得情感的书写失去了真实的客观依托;二是直接导致了变态心理的产生,如林白在其《一个人的战争》里,坦率地描写到有过接受性文化暗示、渴望被强奸的短暂青春期心理,而一旦将心理兑换成现实之后,却倍觉可笑,而后在这一笑之间将自己的这种心理随手抛弃;三是过分精致、优雅的自恋式书写,距离普通读者的生活相去甚远,没有共鸣的群体基础。
五
张欣与池莉等人的作品在面对情爱时表现出来的态度比较客观、现实,对爱情神话的解构与对现实爱情的肯定,是她们共同的情爱诉求方向。
面对现今社会情感贬值、爱情难觅、婚姻脆弱等等不尽人意的情感困惑难题,池莉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她的《太阳出世》、《不谈爱情》、《你是一条河》、《绿水长流》、《你以为你是谁》、《让梦穿越你的心》、《来来往往》等,一系列涉及男女情感生活及心态小说,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逐一有序地对现代情感生活的各种情态细细地解剖,并力求为现代人的情感生活问题寻求到一条合理的解答方式。纵观池莉的小说创作,我认为她寻求的解谜钥匙就是顺世,即顺应爱情生活的本来面目与实际运作规律,空洞的理想爱情生活模式在她那里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池莉的爱情书写所表现的顺世爱情观,首先是对人们的初恋情结发难。其次则是对现实的认同,即承认爱情与婚姻的难融性,认同世俗性的婚姻形式。面对失去爱情话语的冰冷时代,池莉作品的主人公们并没有惊愕,没有哀怨,而是以平静的心态选定了一种他样的生存方式。再次则是对爱情与情欲的绝对分离,即承认爱情与情欲,“二者不可得兼”的现实情状。张欣在她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等小说中,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顺世观念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其实隐含了这批作家对解答爱与情的困惑难题时所作出的新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还不能尽如人意,尤其是在伦理方面尚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其作为一种选择的努力还是值得重视的。
六
用扭曲的欲望书写、赤裸的欲望表达、真诚的精神逃避、无助的揽镜自恋、顺世的情爱合唱,来概括当下中国小说文本的五种情爱态度,虽然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描述与分类。事实上,在上述各有所属的作家作品分类中,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互相交错的弊端,我们在以倡欲为主的《废都》中,其实亦不难见出作家视肉体之爱为空虚的心态;在自恋式写作中亦不难见出肉体描写的裸呈;在顺世型写作中也有逃避情欲追求精神恋爱的情感向度;在逃避肉欲的纯粹精神生活中亦隐含有自我陶醉式的自恋情结,或者说至少是犯有精神洁癖……因此,上述分类只能说是对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情爱态度的现状进行就事论事式的划分的结果,而我始终相信在类的划分以后的宏观观照,要比单纯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分析的微观观照的意义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