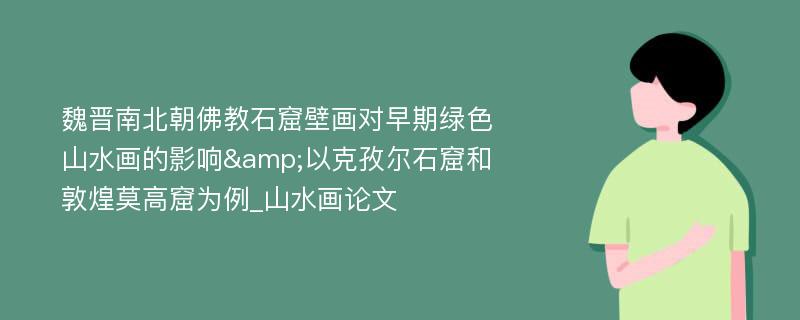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壁画对早期青绿山水画的影响——以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窟论文,莫高窟论文,敦煌论文,佛教论文,青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5)02-0014-03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时期经西域传入中国,在中国真正流传和兴盛是在魏晋六朝。佛教的传播、发展使得各地相继建起大量石窟和寺庙。目前已知的国内主要石窟都兴建于魏晋南北朝。在魏孝文帝时,全国的佛教寺庙、石窟数量多达三万多处。大凡石窟、寺庙之内都会造塑佛像、彩绘壁画。壁画艺术成为宣扬佛教的重要形式。在这些壁画中,北方以石窟壁画为主,画风雄浑富丽,多呈西域风。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大多描绘有精美的壁画。这些石窟壁画受佛教美术和龟兹画风的影响,以石青、石绿等冷色调为主色调,如表现小乘佛教内容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和敦煌早期壁画,展示出一种与中原绘画传统不同的新风貌。蓝绿色也是当时西部壁画的主色调。这些青绿色彩样式对当时的中国绘画造成很大影响,一些魏晋时期的佛教石窟壁画已经出现了青绿山水画的雏形。除此之外,这些壁画用凹凸法染出立体感,也为青绿山水画皴法的出现作了充足准备。同时,由于绘制佛教壁画的需要,画家数量的增多也促进了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总之,魏晋时期佛教壁画为后来青绿山水画的出现奠定了多方面基础。 一、色调的改变 上古绘画别称“丹青”,可见早期的中国画极其重视色彩。中国画色彩在汉以前以青、赤、黑、白、黄五色为主。五色中又以黑、赤色为主。在“丹青”二字中,丹与赤色有关,“青”指黑色。《尚书·禹贡》曰:“(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孔颖达疏:“王肃曰:‘青,黑色’。”可见“丹青”指的就是黑红二色,二者奠定了汉及汉以前绘画的基础色调,现存文物可证实这一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多在烧制成的陶红色胎底上用黑色绘制图案,如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等。这些陶器多以黑、红二色绘制几何花纹与动植物花纹,朴素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渔猎、采集等劳动生活场面。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图》《人物龙凤图》在人物的嘴唇和衣服上施点红色。战国和汉时期彩绘漆画,如湖北荆门包山大冢的楚漆奁外壁所绘《王孙迎亲图》,西汉墓室帛画如马王堆T型帛画也都以黑、红为主色调。汉代的墓室壁画,如林格尔东汉墓的《牧马图》《乐舞百戏图》《夫妇宴饮图》,画面都是先用黑线勾出轮廓,再填染红色或黑色。直到南北朝时期,黑、红色依然是绘画的主色调,如顾恺之的绢本设色长卷《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萧绎《职贡图》,杨子华《北齐校书图》等都以黑、红为主色调。 这一时期西部的石窟壁画呈现出与中原传统不同的新风格。这些石窟壁画受佛教美术及龟兹画风的影响,多以石青、石绿等冷色调为主色调。克孜尔石窟壁画多用石青、石绿等富有装饰性的矿物色,如克孜尔8窟《伎乐飞天》、17窟菱格本生故事画、38窟《伎乐图》等。李广元指出:“以克孜尔壁画为代表的龟兹画风中,在色彩运用方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蓝靛色和石绿组成的冷调倾向。这种色彩特征和西域及印度的建筑色彩有密切关系。”[1](p84)敦煌早期壁画也以石青、石绿构成的冷色调为主,北魏248窟《供养菩萨》,西魏249窟《伎乐飞天》、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北周290窟《佛传之五》等皆有体现。 此时期石窟壁画的色彩样式对当时的中国绘画产生了一定影响。如1987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齐《彩绘石雕释迦立像》,也用石绿、宝蓝、朱砂、赭石等色绘制出田相纹图案。[2](p92)事实上,在魏晋时期的石窟壁画中已经出现了青绿山水画的雏形,如克孜尔212窟主室劵顶在山水、花木、鸟兽之中描绘了僧人坐禅及仙人修行的场景,克孜尔114窟劵顶本生图中,以黑线勾勒山体轮廓,石青填染,并在山上描绘有简单的树形轮廓。敦煌石窟壁画北凉275窟西壁中,山头重染石青,山脚轻染石绿,已有了早期青绿山水画的味道。更典型的是敦煌西魏249窟的《狩猎图》,画面中山峦的色彩呈阶梯变化,如其中一段山头色彩明度自上而下减弱,山头用重色石青,中间是重色石绿,山脚是赭石。这种画法在敦煌壁画中非常常见,与后世青绿山水画的染色技法十分相似。金维诺认为,即使成熟如李思训的青绿山水都可以在敦煌103窟《法华经·化城喻品》、217窟《法华经·化城喻品》上见到。[3](p189)可见,魏晋时期石窟壁画中的青绿色彩样式及其中山水景物图示对早期青绿山水画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从“凹凸法”到山石的皴法 贡布里希说:“佛界的僧侣和居士经常被表现为非常逼真的塑像。”[4](p21)佛教美术注重写实的特性对魏晋时期的人物画和山水画有很大影响。强调立体效果的“天竺晕染法”普遍运用于当时的壁画中。敦煌千佛洞北魏诸窟的壁画人物以及塑像,都是长身细腰,壁画上的人物一律用“凹凸法”来表现立体的感觉。[5](p526)敦煌北魏263窟的《供养菩萨》、北周428窟的《飞天》、北魏254窟的《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等,这些壁画人物肤色多用“凹凸法”染绘而成。428窟塑的佛像先用暗色勾形,用白色画出高光,最后用黑色的线条勾勒出脸与身体的细节,以及骨骼结构,如眼睑、鼻骨、眉弓等。克孜尔石窟壁画也有采用分层次晕染的技法,如第189窟的佛教人物,画面先染淡色,再用重色晕染,晕染层次明显,呈现出立体感,这明显是由佛教美术的传统色彩演变而来的。 受西域绘画技法影响,魏晋时期画家开始重视对形体的塑造和立体感。理论著录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形”的论述。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他认为,“写自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其于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6](p53)。谢赫也同样注重“形”,“六法”中除了第一法“气韵生动”外,其他五法都涉及“形”。魏晋人物画家如曹不兴、卫协、张僧繇、曹仲达、蒋少游、杨子华等也都注重塑“形”。传说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误落墨点,便“点墨成蝇”,孙权信以为真,欲拿手拍,可见其画的逼真程度之高。萧梁时期的张僧繇曾为分散在各地的王子画像,所画肖像亦有“对之如画”的生动效果。传说他曾在金陵(今江苏南京)一寺庙内用天竺画法绘“凹凸花”,远望有凹凸立体之感。“凹凸花”这种绘画手法在中国绘画创作中普遍存在。“凹凸法”对中国画的着色也产生了影响,如后世青绿山水画中的山石,用赭石打底,上绘草绿、石绿,最后用石青点染山头,呈现凹凸感。 在山水画方面,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与王微《叙画》都谈及山水艺术表现的具体经验。宗炳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还提出了山水近大远小的观察原理,以及在画面上表现真实山水空间的方法。他说:“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之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囿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7](p32)可见宗炳已经在探索如写真人物一样写真山水。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用了渲染法,在山、树的画法上甚为明显。其山石的着色方法为:先平染赭石,再罩一遍石绿,最后在山石阳面的顶部染石青。石绿或石青染得厚薄不一,先染过的赭石就忽隐忽现,每块山石产生了微妙的色相对照。这种用色渲染出立体感的画法为青绿山水画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洛神赋图》应用了“色上线”的技法,即画面中染矿物色后,再用墨线勾轮廓。这种技法可能源于西域画法,易使人联想到敦煌壁画中上色后的“定型线”。而在魏晋以前的绘画中,画面都以平涂着色,无渲染之例。在汉代,汉画往往先用墨线表现形体,再将色彩快速地平涂上去,晕染技术很不发达。如汉代马王堆出土的T型帛画便无晕染。这种“凹凸法”也许直接启示了青绿山水的“罩”“染”“提”“填”“衬”等色彩技法。壁画史专家楚启恩认为:“天竺晕染法在当时(魏晋时期)的壁画中被普遍运用,中原地带的唐、宋时期工笔重彩人物、花鸟、山水中的皴法,也是受此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在此以前的时代中,每以纯粹的平涂着色,无渲染之例。”[8](p64) 三、绘画主体的变化 魏晋时期石窟壁画盛行,大批民间画工和士大夫画家都参与佛画绘制。汉画多为画工之作,魏晋时期文人、仕官或文人兼仕官人群的加入,画家人数增多,他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也相互影响。此时期的山水画技法处于探索阶段,正好需要更多的画家参与绘画。但当时多数画家都绘制佛像画,只有少数文人学子以作山水画为乐,并不能使山水画真正发展起来。山水画的进步,需要大量的民间画工和专业画家共同参与,在解决山水画的构图、造型、设色、勾线等问题后,再由文人画家收拾和进一步改造。专业画家和民间画工虽然对早期山水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要想让专业画家和民间画工大量地参与绘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可是六朝和北朝的社会并没有创造这样的条件,而是提供了绘画和雕塑佛像的条件。此时的佛教画发达而山水画初兴,山水画只限于文人自画、自赏,宫廷、寺院、社会并未接纳这些画,所以山水总是依附于人物画。直到唐代,南北统一,给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山水画才成为独立的画种。 从魏晋人们开始重视对山水的描绘到唐代画出现山水的形象,这与当时佛教壁画的兴起和发展有很大关系。山水成为除了佛像和佛教故事之外,魏晋时期壁画研究的另一个主题。但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这些处于背景地位的山水画往往不受重视。对魏晋时期佛教壁画中山水图示的研究是我们探究青绿山水的起源、梳理山水画发展的重要环节,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标签:山水画论文; 壁画论文; 佛教论文; 克孜尔石窟论文; 南北朝论文; 魏晋南北朝绘画论文; 美术论文; 魏晋论文; 艺术论文; 青绿山水论文; 莫高窟论文; 文化论文; 洛神赋图论文; 国画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