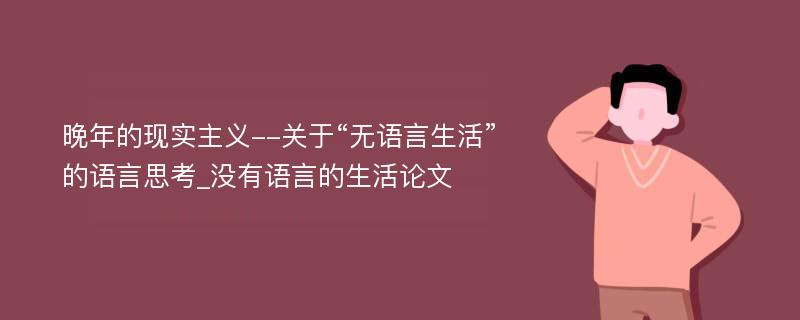
晚生的现实主义——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语言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晚生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生
“晚生代”作为更加晚近的文学后继者,似乎离较为晚近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更加遥远,这不知道是文学历史的一个疏忽,还是“晚生代”自觉的故意谋杀。如果是文学中的自然失误,那就意味着人们无奈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者的结合是“新潮”小说的独特标志)的精致和高级化,倦于艰辛和寻找,厌于“新写实”的粗泛俗浅。如果是“晚生代”对于文学先行者们的不满,自觉地与前不久的文学对抗,反抗和背叛已形成的传统,那意味着文学又一次处于尝试突破困境的时期,他们打出的新旗号是要寻找在高级和低俗之间的中间出路。
对于文学中的“晚生代”,从一部分意义上可以叫作晚生的现实主义或晚近的现实主义,对于传统意识的恢复或可算得一种新的标志。晚生的作家们其实没有统一的旗帜,其创作风格也各得其所,我们暂且把《没有语言的生活》看作一种标志性的例证。它没有古典主义出人意料对现实的规划,没有现代主义超越的理想和怀恋,没有后现代主义的自我嘲讽和对现实的破坏,有的只是一种平易朴实的风格,一个平淡的故事,一支现实的淡淡挽歌,一种没有激动的悲哀。
隔绝
这似乎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命题,在卡夫卡、萨特、加缪那里可以轻易找出来。卡夫卡那个著名的城堡,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永远隔绝。但这个命题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完全被现实化了,它变成了作品中人物具体实在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生命含义和境界。
没有语言的生活是沉默,是隔绝,是与语言世界或他人的隔绝。语言和他人在这里几乎是等同的,它们可以轻易地相互替代。隔绝是这篇小说创造出来的根本生命状态。在沉默而清澈的语调中,这种隔绝一开始就在平静如流的叙述中显露出来,从始至终隐现于故事文本中。这种隔绝从开始的合乎常情走向最后的荒谬绝对、有悖常情:三个分别具有聋、哑、瞎缺陷的人三位一体与世隔绝地生活着。
开始,这种隔绝并不那么触目惊心、超乎想象,所以聋子王家宽虽然听不见,仍能介入他人的世界,仍能在他人中生存,他能明白别人对赤身裸体的父亲隐私处的议论,能明白乡间中医刘顺昌对他的夸奖,能去谢西烛家看别人打麻将,能和别人一起发笑。这种轻松的或麻木的隔绝状态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原因:或许是王家宽的父亲王老炳尚未瞎,介于聋者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之间而加以沟通;或许这是王家宽仅仅作为聋者单独与他人隔绝,不够强大,不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或许是王家宽、王老炳、蔡玉珍尚未形成三位一体的世界、或自我完善的世界;或许是收音机和朱灵尚未出现,或许是语言与非语言混沌未分,语言世界尚未完全分化……。
故事从王老炳被马蜂蜇瞎开始,真正的隔绝状态也从王老炳被马蜂蜇瞎开始。此前王家父子与他人尚在沟通,此后,逐渐进入绝对隔绝状态,哑巴蔡玉珍的出现,既加盟、完善了这个三位一体的世界,又带来了他人或者说语言世界的更多的欺凌和敌意。
聋、瞎、哑三位一体的完成使得与语言世界的隔绝激化、严重,但仍不是隔绝的极端状态,隔绝的极端状态是王胜利作为三位一体的变异物被迫返回自己的堡垒。聋、瞎、哑三个伤残人被迫宣告与他人断绝来往,这已经惨绝人寰,但似乎还可以他们的伤残作为解释。他们的后代小王胜利作为一个生理健全的人,却自动放弃了与语言世界交融的权力,这才是隔绝的极端状态。
双重因素
隔绝具有双重因素:他人的欺凌、排挤、压迫和自我的封闭;语言世界的污浊和非语言世界的自我净化。
作品表现了人具有一种欺凌弱小的恶劣天性。聋、瞎、哑与人世隔绝的状态,是他人对他们的驱赶和压迫造成的。村里的人对于艰难生活的王家三人非但不同情和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他们嘲笑王家宽听不见声音,偷走王家的腊肉、轻薄哑巴姑娘蔡玉珍。甚至一直被王家宽深深爱着、也爱过王家宽的朱灵也把自己的脏水往王家宽身上泼,也欺侮爱着王家宽的蔡玉珍。及至有人趁王家聋、瞎、哑之危,强奸了蔡玉珍,终于使王家悲哀地绝望了:他们拆掉了与村里相通的小桥,以一河之隔与村里人划开界线,表明对语言世界的抗议和失望。
在王家精神意识的深处,蹲伏着一个企图完善的自我,隐藏着一个企图保持净化的世界。聋、瞎、哑的人本来由于听不见、看不见、说不出而比普通人更少一些烦扰,但即使这样的人都无法保持单纯和安宁,外界的不断搅扰和入侵,破坏了他们心灵的平衡,他们不得不撤退到河的另一边。这不仅是躲避,也是防护,用自我封闭的方式将自己企图净化的世界包裹起来,免受外界的诱惑和破坏,以完善一个田园诗般的自我。聋、瞎、哑人之外的世界似乎是一个肮脏的世界,村里人的邪恶和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与王家的单纯善良和毫无进攻能力无法沟通,村里伤害、隔绝这些残疾人的真正原因是不会去理解这些残疾人的心灵。王家人从不伤害别人,作品里出现的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不伤害王家人的:刘挺梁偷王家的腊肉、老黑家将鸡瘟传染给王家、谢西烛嘲笑王家宽听不见声音和不懂性事、张复宝在替王家宽写的情书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让王家宽去传递、朱灵将自己怀的张复宝的孩子说成是王家宽的、朱灵的母亲在桃树下用棍敲打瓷盆以诅咒王家、村里的孩子们教给王胜利唱辱骂王家的歌谣。村里人的所作所为,使王家意识到他们和村里人不是一类人,不得不将自己封闭起来,放弃与语言世界的交流。
因此,这种隔绝也是自我封闭造成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状态。而他人原本就在不断侵入他们的世界,为了保存他们这种世界的纯洁与完整,免于侵入和污染,他们自动放弃了与他人的来往,宁肯孤独而沉闷地生存,不再以语言作为人的标志而自豪。
融和
作品故意描写了与隔绝相反的融合。这种融合只限在王家宽、王老炳、蔡玉珍之间发生,并和他们之外的隔绝形成对比和反证。融合在三个残疾人中发生并且绝不向外蔓延,这是对人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健全的世界的一个明确讽喻和警语式思考。
融合是聋、瞎、哑三位一体的土壤,也是三位一体的天空,它代表了三位一体的准则,也代表了三位一体的必然道路。
融合的过程,也是三位一体的构成过程。融合与隔绝相对抗,必然与隔绝同时发生,隔绝的渐进也是融合的历程,此作品中的融合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封闭、完善的圆圈的:王老炳一开始和儿子并不相融,只是一个外界的中介;蔡玉珍也不是一开始就被王家宽所需要,只有王家宽对朱灵彻底失望后才可能容纳蔡玉珍。
王老炳在瞎眼之前与儿子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只是儿子通向他人和他人通向儿子的一架桥梁,由于有个聋儿子,他不属于任何一方世界,所以他在被蜂蜇时是孤独的,无论他怎么喊叫,儿子都无法援救他,别人也不会援救他。只有在他被马蜂蜇后,他和儿子才能逐渐相互进入对方世界,因为由此他们才有共同的感受和特征。也正因为如此,王家宽只能娶哑巴姑娘蔡玉珍,不可能娶生理健全的朱灵,他和朱灵都不属于对方世界。因此,当朱灵父亲要王家宽承认和朱灵同睡过而愿意把朱灵嫁给王家宽,朱灵又表示愿意嫁给他,王老炳想要朱灵当儿媳妇也让儿子承认和朱灵同睡一夜的事实时,王家宽却因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而理所当然地拼命否认他和朱灵的事。对于王家宽,这是令人惋惜的,却是必然的。只有他们才能融合在一起,即使一个聋,一个瞎,一个哑,也能奇特地交流沟通。他们在正常人的世界中无法生存,正常人也无法进入他们那个融合的世界。
蔡玉珍来到王家,使融合的条件具备,融合的过程接近终点。故事叙述文本临近结尾,三个人发挥各自完好器官的优点进行合作,用语言和手势交流捕捉强奸蔡玉珍的人的特征,是融合的高潮性显现:瞎的问、哑的做手势、聋的用语言将手势传给瞎的……
融合的最终成果是小王胜利的诞生。三个人相得益彰,互相弥补了缺陷,也就失去了缺陷,三个有缺陷的人合在一起实际上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因此产生了王胜利,王胜利不过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代表,他似乎不但在证明三位一体的最终结果,而且在证明三位一体的最终渴望:村里人伤害、驱赶他们,他们却渴望和村里人一样生理健全;他们因残疾而和村里人有所区别,但却渴望消除这种区别,由三个残疾人重新变为一个健全人而回到人群中。然而,这种过程和结果都不能被村里人接受,小王胜利只能被迫象聋、瞎、哑一样,自动不说、不看、不听外面的世界,最终他仍然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一个没有语言的人。融和的结果并不是缺陷的根本消融,而是缺陷的集中化体现。这其实是人类无法实现自身完美的一个寓言表述。
错乱与悲剧
利用聋、瞎、哑者的生理缺陷和人们天生的内心隔绝,小说叙述文本中制造了几次错乱。故事叙述文本的主体依靠几次错乱构成决定性的转移,最终导向王家迁移过河、拆除桥板与人世隔绝状态。
最初的错乱是必然的,成为全部叙述和最终隔绝的起点:王老炳被马蜂蜇而呼救,王家宽没听见,刘顺昌给王老炳治疗蜂伤时说愿收王家宽为徒却似乎被听见了,于是王家宽大声叫了刘顺昌一声师父。这次错乱似乎只在表明:王老炳被马蜂蜇瞎是一种奇怪的必然。
第二次错乱是王家宽弄不懂王老炳要肥皂而误买了收音机,由此听不见声音的王家宽把收音机大开着成天挂在脖子上,终于在一个夜晚带着大响的收音机撞倒了朱灵,当朱灵把收音机声音关闭时,王家宽象打开收音机的声音一样扭开了朱灵胸前的衣扣。这次错乱表明女人朱灵和声音对王家宽一样重要,甚至几乎是一回事,两样中他若拥有一样,就不会有缺少另一样的悲剧,就不会因没有声音而错失朱灵,不会因得不到朱灵而失去全部语言世界,娶了哑巴蔡玉珍为妻,从此彻底与语言世界无法沟通。声音或女人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标志,也是他获得世界、进入世界的保证。而声音和女人在这里微妙地相似和等同,没有声音和女人,他就失去了语言化的世界,他就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就永远被排斥在外。接下来的故事文本叙述,证明了女人和声音对他来说有同样的悲剧性质。
第三次错乱在前两次错乱中已经被安排妥当,它必不可免地发生了,是一种简单而必然的结果。当朱灵的父亲、朱灵、王老炳都希望王家宽承认和朱灵同睡了一夜的事实以便娶朱灵为妻时,王家宽却误解了大家的意思,拼命否认和朱灵同睡一夜的事实。
从现实来讲,聋、盲、哑者都有天生的灵性和极好的后天悟性,王家宽对父亲遇难毫不察觉、对父亲要买肥皂这样的手势不理解、对大家要他娶朱灵的愿望浑沌无知都是违反残疾者的常情的,然而由于他们的生理特性,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作品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现实可能,制造了虚构世界的事实,以典型的语言事实——故事错乱来完成叙述。
有错乱,就有喜剧或悲剧。作为一种悲剧性的错乱,《没有语言的生活》体现了一种悲剧命运,并与古希腊式的悲剧命运相仿。在古希腊悲剧中,错乱是命运的必然表现,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错乱同样是命运的必然表现,在错乱中命运走向悲剧性的三位一体。
隐喻
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我们遇到一些隐喻:声音与女人(朱灵与蔡玉珍)是语言世界的隐喻,聋、盲、哑三位一体是自我完善的世界的隐喻,任胜利是三位一体的隐喻,聋、盲、哑三位一体是对每一个健全人的隐喻,没有语言的世界则是对语言世界的隐喻。
故事叙述文本中的隐喻重叠到最后,在悲剧性的迁移中才开始全部显露出它们隐藏的光芒。
王家离群索居,迁移到河的另一边,在祖坟上重建家园,借祖宗的庇佑以和语言世界对抗。他们悲剧性地拆毁河上的木桥,以河象征性地作为界限,与世间永不来往。这是保持他们的纯净、保证没有语言的世界不受到语言世界的侵犯和污染的一个隐喻,由此,任何与语言世界的通道都被拆毁,任何希望都被规定了失败和悲剧性,所以,当他们藕断丝连地留下了与村庄连接的桥梁时,同时也为语言世界的侵入留下了很便当的通道,蔡玉珍遭到桥上来人的强奸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这促使他们彻底绝望,忍痛拆桥,拆掉外界侵入的通道,也拆掉他们心中语言的诱惑。
拆桥后,王家宽对于对岸的世界仍然依依不舍,隔岸相望,相望的结果只是遥望着朱灵虚空的幽灵,留连忘返于朱灵曾靠过的桃树并趁夜色无人采摘几个鲜桃,此外毫无收获。
作为健全的孩子,王胜利本可以打破隔绝,把无语言的生活最终引向语言世界,并使其消失其中。隔绝一方面是永恒的,一方面是暂时的,三位一体的无语言世界显然不会永久延续下去,它或者消融于语言世界,或者坚持自我封闭而消亡,没有诞生,也没有延续,更没有终结,作为永恒的对立构成因素,它必然是暂时的,但王胜利却单方面地仅仅作为一个永恒的隐喻形象出现,把隔绝推向极端。一旦他过河上学,作为再生的、新形式的聋、盲、哑三位一体试图进入对岸的世界,立即被语言本身挡住了:他学会的最初语言是对无语言世界的亵渎和破坏,这使他立即明白了两种不同世界互不相融的事实,被迫沉默下来:不听、不看、不说,象聋、哑、盲人一样。这种故事事实包含着双重隐喻:一方面只有躲进无语言的世界里才能逃脱语言世界的捕杀,另一方面没有语言的人仍然要归返为语言的人。
王家从聋开始到聚集聋、盲、哑为一体,最终生下没有任何缺陷的王胜利的过程,是个充满隐喻的过程。作为没有语言的人从语言的人中分离出来,又作为语言的人——王胜利返回到语言世界中,最终从语言的人中分离出来,成为没有语言的人,这个由被动地没有语言到自动放弃语言的过程,隐喻了语言世界的残酷规则和自以为是,隐喻了对这个世界的鄙夷不屑和抗拒,隐喻了没有语言的纯净和自我完善。
最终,隐喻的是我们这个有缺陷的世界,隐喻了这个世界的自相矛盾。没有语言是一种缺陷,然而这种缺陷却完成了一种完美的人格和自足的生存。有语言是一种优点,然而语言本身却带来并标志出一种缺陷,因为语言是人类传统与现在并存、文明与原始并存的结果。
在故事中,没有语言的残疾人倒人格完整,有语言的健全人倒人格残缺。由于隐喻,故事最后完成的并非是两个具体世界、两种具体人的隔绝和对抗,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它表明我们自以为是的优点往往是我们的缺陷,而我们的缺陷却有可能保存我们的骄傲和尊严,这就是让我们悲哀的。文明往往是踩过人类的天真和纯洁而前进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虽然令人悲哀,却是一片天真和纯洁的世界;没有语言的人虽然沉默而孤独,却得到了没有语言的宁静和快乐。
叙述
故事文本用一种平静而沉着的叙述语调构成。从本质上说,作者并没有把《没有语言的生活》当作特殊的语言游戏,而是用严肃的态度、平淡客观的叙述语言来叙述故事。我们在作品里找不到荒诞错乱的意识、谜一样的情节、丰满圆润的语言、漂浮不定的叙述,作品明显地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现实主义,用简单而平实的风格叙述。从故事表面看,作品描绘的是弱小人物遭受欺凌的命运,是人类欺凌弱者的劣根性,在精神气质上体现出对弱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同情。这是一个传统化的故事和传统化的主题,与之相适应,是简单而现实化的文本叙述方式。平实朴易的语言、框架式的情节、粗线条的细节、没有个性的人物、不动感情的描绘,都作为这种叙述基调顺流而下的产物融成一体,形成与故事相适应的叙述风格。
但是,在这个具体故事的背后,隐藏着那个悲剧性的寓言命运,聋、盲、哑三位一体的与世隔绝,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隔绝之中,又被别人所隔绝,并去隔绝别人。语言既是我们的延伸和融和,又是我们的困境与缺陷。而我们的健全反而使我们对这种生存状态麻木不觉,自以为是。
这种叙述具有典型的二十世纪风格:表明对现代人的悲哀。卡夫卡的传统或精神如此深入文学的骨髓,以至我们随处可以与它相遇,在这里也可以辨认出它的踪迹。并不是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受了卡夫卡的明显影响或模仿了卡夫卡,而是说一种类似卡夫卡气质的意识在作品中显现出来,在描写人类的隔绝状态时有意无意地与卡夫卡的作品具有相似之处。卡夫卡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现代人的隔绝状态的。与《变形记》中的格里高里在极端状态中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相似,聋、盲、哑三位一体也是人类隔绝状态的变异景观。
悲剧在于,人们必须在这种隔绝状态中生存下去,因此,《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三个人不得不忍受着隔绝,封闭着自己,与村里的人们隔河相望。
富有意味的是,这种隔绝将会代代相传。从这种命题出发,王胜利放弃了语言的权力。他的父辈被迫与他人隔绝,而他却自动走向隔绝,保证这种隔绝的唯一方式是放弃语言。聋、盲、哑人生出了健全的孩子,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也是作品的有意安排。生理健全的人却愿意变聋哑:它同时表明了语言的悲哀和没有语言的悲哀。
收稿日期:1997.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