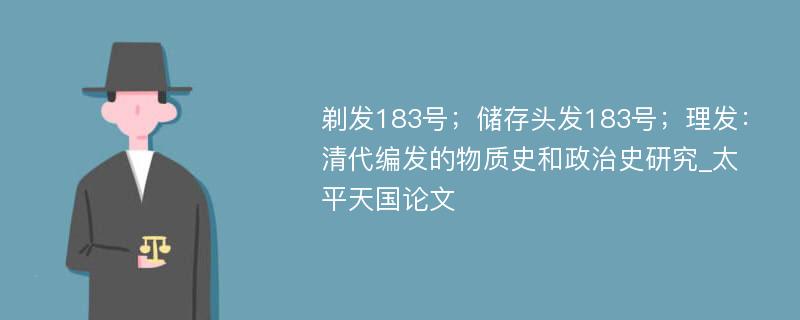
剃发#183;蓄发#183;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蓄发论文,清代论文,史研究论文,身体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是一个与辫发纠缠在一起的朝代。单是男人头上盘旋的一条辫子,其存废留剃就与清王朝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尽管已有学者对于清朝的辫发史作过相关研究(注:研究中国辫发史的成果主要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美国学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学者王冬芳《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等。陈生玺在《明清易代史独见》中的《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剃发令在江南地区的暴行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文,对清初剃发令进行过集中阐释。李文海、刘仰东在《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太平军的蓄发问题。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等书中,深入探讨清末剪发易服等问题。黎志刚在《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中,有《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一文,剖析了近代中国发型变化。张亦工、夏岱岱的《割掉辫子的中国》,集中探讨辫发与时人的心理。),但截至目前还很少有人从身体史的角度切入,将辫发与有清一代历史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展开论述,并且透过“辫发”这一身体符号来对清代政治与文化进行解读。
一、江山易主的“剃”
满族男子剃发留辫,实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风俗习惯。在战争中,辫发渐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投降或归附满族者要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传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轻人必须剃”(注:《满老文档·太祖》卷三十四,辽宁大学1979年译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因为壮丁当兵,要求较严。此时辫发还未完全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多是满族对于投降或归附者发式服饰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极继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就会弃明忠清。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许多被迫剃了发的汉人在从辽西逃至关内的途中,被明军妄杀。有没有剃发,成为区别满汉的首要身体依据。随着满族与明朝之间战争的加剧,“剃发”也开始逐渐上升到有关民族、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发”最终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与文化符号的历程却是相当复杂的。
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注:池内宏:《清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仁祖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发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久, 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多尔衮下令罢除剃发,以收买人心。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注:蒋良骐:《东华录》卷四,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因不用剃发而对清产生某种好感。而清在辫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则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注:七峰樵道人:《七峰遗编》第57回,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一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入南京,多尔衮遂改变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的政策,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在剃发令的罢而复行中,部分降清汉官起了很大作用。清军南下旨在夺取明朝江山,使被统治者从满俗、废汉俗,以免触发人们的故国情思。辫发既然是满汉习俗在身体外观上最显著的差异,又具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内涵,所以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汉官的意见,重新实行强制剃发的政策。至此,辫发完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多尔衮视剃发为征服汉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汉人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突出身体标志。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这样一来,汉人由反对满族的象征——辫发,进而反抗满族统治。所谓“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无奈强令难违,男人从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注:邵廷采:《东南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9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剃发”而发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惨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明、清战争中影响巨大,更成为满汉民族冲突的痛苦的文化记忆,贯穿于有清一代。
在剃发问题上出现如此激烈的冲突,实属罕见,因此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汉人们也许由剃发而联想到阉割。他推断:在旧体制下,男子人格和地位的优越感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而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眼里确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注:孔飞力(Philip A.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of 1768),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月版,第75页。另外,艾德蒙·李奇则提出满人的辫发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他认为:“从礼仪上来说,长发表示不受限制的性征;短发或部分剃发,或紧紧扎住的头发表示受到限制的性征,完全剃光的头表示独身生活。”为强化这一观点,他还征引了17世纪英国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李奇(Leach,Edmund R.):《魔法般的头发》(Magical Hair),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88期(1958年)第153—154页]在他看来,剃发与传统儒家的自律原则格格不入, 这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霍尔帕克(Chyristopher R.Hallpike)认为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相联:“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因而得到征服者的坚持。”[霍尔帕克(Hallpike,Chyristopher R):《社会的头发》(Social Hair),载《人杂志》(Man),第4卷(1969年)第261页])。
笔者以为:满汉民族对头发的认知差异是产生冲突的因素之一,但并非首要因素。首要因素是由满汉对辫发不同政治、文化内涵的解读以及各自所持有的呆板、强硬的态度。
从满族统治者来说,随着对明战争的全面展开,辫发也从民族风俗与服饰上升为赋予政治含义的事件。这可以从满族在辫发问题上对待蒙古、朝鲜和明朝截然不同的态度中看出。蒙古族剃发习俗与满族接近,历史上联系较多,满族统治者便以此拉拢蒙古,强调联合以反对发式和服制不同的明朝。为此,努尔哈赤在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致书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说:“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虽言殊而服发亦相类;……愿同心协力共图有仇之明,如此不亦善乎。”(注:《满洲实录》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因服发的形式问题,满族贵族把蒙古民族视为同类,把汉人和朝鲜人视为异类,突出的是联合蒙古与明敌对。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为笼络朝鲜下令:“自今后朝鲜被掳军卒,更勿剃头,使之长发云。”(注:李民寏:《栅中日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校译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页。) 皇太极两次出征朝鲜,“俱令剃发”(注:《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己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但在大败朝鲜后,则降其为属国,使者进京朝贡,冠戴如故(注:《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十一月甲申,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种针对不同民族而采取不同的发式要求,以及在发式上大做文章的策略,显示了满族统治者赋予发式政治内涵的用意。
拉拢蒙古,是因“发服相类”,视为“同族”;不令朝鲜军卒剃发,缘于朝鲜为“外国”。可见,满族统治者实行剃发制度主要是针对汉人,旨在建立大一统政权。在关外时,满族统治者认为主要敌人是明朝,所谓“七大恨”者是也(注:参见《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七大恨”即: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但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超过了满族,社会制度也较为完备,满族统治者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担心汉人会危及满族政权。当汉化程度较深的满族贵族曾建议全盘汉化,改服汉人衣冠时,皇太极严加训斥。他认为满族的衣冠制度是满人尚骑射、武力精强的保证,金、元入主中原后,皆成汉俗,实后代君主变易祖宗制度,服汉人衣冠,弃本国语言所致。因此,一切制度必须从满,才能保证满族政权的长期稳固。显然,将辫发作为汉人接受满族统治的一种标志,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辫发不仅仅是民族风俗的象征,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注:蒋良骐:《东华录》崇德三,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剃发成为立国之策,不惜以严厉的手段迫使所有臣民遵照执行。辫发既是满族统治者成功征服的标志,也是拥有广大臣服者、长治久安的一种外在体现。
对汉人而言,剃发成为接受异族统治的标志。然而汉人不愿剃发的原因却很多,除了与恪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儒家传统理念密切相关外,还因为剃发同蒙受耻辱、遭到惩罚等有关。例如,在秦代的刑典中,便将剃发同纹面、残肢并列,以羞辱奴仆与已定罪犯人(注:参见霍尔色韦(A.F.P.Hulsewe):《秦律的遗迹》(Remnants of Ch'in Law),E.J.布利尔出版社(E.J.Brill荷兰莱登)1985年版。)。剃发所带来的耻辱感使汉人反抗这一政策,这与部分忠于明朝的汉人反对剃发实质上是在反抗清朝的统治也有所区别。
总之,汉人反抗满族统治者未必都是为明朝而战,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满于让他们感到极为不快的剃发令。在剃发令初罢时,他们甚至盼望新的统治者能将其从沉重的赋役负担中解救出来。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钱谦益派人到苏州进行招抚,“民皆执香以迎,城中大姓有设香案于外者”(注:顾炎武:《圣安本纪》六,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大通书局1984年版。)。而复行的剃发令则逼迫他们奋起反抗。在他们看来,保留以束发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和作为优越“礼仪之邦”臣民的自尊更为重要。曾目击江南人民抗清的一个西方人说:“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檄号为耻辱,曩者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注: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较发达,民族意识也较强烈,长江流域爆发的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就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剃发问题与人的自尊、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注: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Jr):《地方主义与清征服江南时期的效忠思想:江阴的悲剧》(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魏斐德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eds)编:《中国帝制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3—85页。)。辫发本身有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的复杂多样。对辫发的认知差异不但存在于满汉不同民族和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存在于各自民族的内部。
无论如何,剃发令最终使汉人男子发式,从束发向结辫转变。可围绕辫发而引起的矛盾、斗争,则远没有结束。顺治年间,大学士陈明夏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便被处以绞刑,社会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仍抑制不住反抗的浪潮。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与李成栋因反对剃发而起事,掀起清入关后第一次反清高潮。李自成余部因剃发问题降清复叛。从顺治朝到康熙朝,清王朝一直要招抚台湾郑家,因剃发问题致使多次谈判告吹(注: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世界书局1979年版。)。康熙十二年(1672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用束发复衣冠相号召,所过州县俱令剪辫,颇受人们拥护,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半壁河山。此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等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与辫发有关。
综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由满、汉战争而引发的“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但是,在战争中以及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本来为民族风俗的发式成为充满政治符号的身体特征。“剃发”与否成为归顺清朝与否最为显著的身体表现,由此而引发的“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政治事件,不仅将这种身体—政治符号赋予了更多的冲突内涵,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一直贯穿于整个清朝的历史之中。无论是满族统治者还是被征服的汉人,发式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身体标志。
二、揭竿而叛的“蓄”
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蓄全发几乎成为这些起义军的突出标志。然而,每当民众起义失败后,接受清王朝统治者又无一不恢复辫发。这其中,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认,以“复衣冠”的形式来表明对于汉文化的认同。
“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注: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另外还有“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页。) 和“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注:《绍天福朱绦天福陆告四方士民亟早投诚各安生业诲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37页。) 等说。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83页。)、“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228页。)。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
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
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民间以“长毛”、“发逆”来称呼太平军将士,本身就包含了对蓄发的非正统认定。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我们对风俗习惯方面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感到恐惧和害怕,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变化一旦成为传统,就会拥有其他时代的旧模式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注:鲁斯·本尼迪克特(Benedict,Ruth):《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傅铿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这里的“风俗习惯”一词不单指社会习俗,而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等多重涵义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崇经验等,不愿改变。而太平军某些下层兵士的扰民欺民举动也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人们对于禁剃发,并不是全力奉行。柯超曾记述道:“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剃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人照常剃发。”(注:《禁剃发告示》,罗尔纲、罗文起辑录:《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5页。) 海宁冯氏的《花溪日记》中在写到杭州被清收复后:“(同治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杭州府陈姓出示,限三日内皆剃发,民乃欢呼称庆。”(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17页。) 可见,辫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束发倒是显得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
支持蓄发的人们对辫发的认知也并非整齐划一。包括太平军将士在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往往发现所谓“满发老贼”特别勇悍善战,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时间较长的老战士,头发已经长得很长,甚至有“长发尺许”的。而前面头发不长的是新兵,战斗力自然要差得多。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金陵被难记》中载:“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大约皆两湖新裹之众”,所以守城时“每令妇女披发假装男子,上城击鼓鸣锣,呐喊巡视”(注:佚名:《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辑,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第750页。),以此来壮大声势。可见由于政治对抗,辫发与蓄发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不仅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而且还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与资历。另外还有一些人为逢迎太平军而蓄发,甚至还模仿其衣冠。据《自怡日记》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开市颇盛,牌署天朝,掌柜者俱土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1页。)。《花溪日记》甚至说,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677页。)。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对太平军有归降之意,至少是并不把太平军看作“反贼”,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才这样做的,但大部分人主动改变发式,则与其内心的政治倾向变化相关。另外,有些人还对蓄发持保留甚至摇摆的态度,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太平军刚离开,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5页。)。凡此种种,使蓄发与辫发的较量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这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对于违抗蓄发令的人们,太平军处以残酷刑罚,明显地暴露出辫发中所蕴涵的政治含义。这种做法,在百姓看来是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对于主动蓄发者,太平军往往怀柔、安抚有加,无论其蓄发的最初动机如何,一律视为顺民。由发式来简单而绝对地判定其政治倾向,实在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辫发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辫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被特殊化,正是政治斗争激烈化的表现。
然而,有一种人却可以游离于辫发的政治斗争之外,那就是往来于太平天国统治区与清王朝统治区的商人。他们向太平军交费,领一张剃头准许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剃发了。“剃头凭”是太平天国为保护和鼓励商业发展而实行的一项政策。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正式文告中公开宣布的一项重要规定。如海宁的太平军驻军长官就“谕百姓剃头过江贸易,每给剃头凭,须费仅廿六文,剃者甚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5页。)。如此可见,太平天国强令蓄发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是以蓄发取代辫发来挑战清朝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
这场与发式密切相关的战争最后以太平天国的败亡而告终。辫发所代表的清正统地位的再次强化,蓄发人又开始了剃发。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起义战争,将清初以来辫发乃是代表着政治态度、民族情感的身体标志进一步强化了,也随之影响了太平天国之后的历史进程。
三、迈向近代的“剪”
及至近代,辫发问题又因时代的嬗变而成为历史的焦点,相对于既往的历史,辫发问题的背后是更为复杂而隐晦的文化、政治象征意义。
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近代以来却面临着“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而被视为“夷狄”的局面。西方人称中国人为“半开化”,缘于辫发。在国外,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而受辱(注:参见李承基:《第二故乡》,自印1997年版,第91页。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中国留学生的长辫子,被外国人称作“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等等(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62页。),遭到侮辱和耻笑。“国粹”成了“国耻”,于是,一些留学生将垂在脑后的辫子或盘起来,或干脆剪去。
留学生处理辫子的方式有所不同,隐含着对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许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学生就不得不留着辫子,并用帽子盖着,被人们称之为“富士山”。这些人多为保守主义者或想回国后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的人。而剪掉辫子的学生就有所不同了,既有叛逆的“无辫仔”(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页。),也有些人不是。晚清剪辫与剃发、蓄发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不再更多地考虑国内民族、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采取的一种行为。辫发成了“落后”的标志,剪辫就具有弃旧从新的味道。尽管如此,清王朝还是将剪辫子这种大胆行为看成是反叛。所以很多剪了辫子的留学生回国后不得不又装上了假辫子。
专为归国留学生装假辫的专家与清初的理发匠虽然都是为了使男人的脑后有条辫子,但却满足着不同的社会需要。理发匠是为了使辫发代替束发,由此帮助确立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假辫专家则是使象征新时代、新制度到来的短发暂时隐藏起来,向传统的辫发表示屈服。可见辫发作为政治符号,至晚清仍居于发式的主导地位,象征着清王朝统治稳固。
可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也必须现代化,剪辫似乎势在必行。人们越来越感到辫子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争斗时易被捉;行礼时不便脱帽;健身时不便锻炼;勤洗费时间,不洗又不卫生,还会传播疾病。长长的辫子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不利于近代军事的发展,不利于对外交往。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多。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提出了剪辫的主张。
维新派将剪辫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注: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载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可见在维新派的心目中,辫发是一种落后的风俗习惯,既不利于机器生产,又不利于执枪跨马,还会阻碍富国强兵之路,因此需要改良。这反映了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保国、保种的急切心情。辫发与女子的缠足一样成为“落后”与“积弱”的象征,维新派所竭力呼吁的男子剪辫与女子放足,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富强和指向救亡。作为身体标志的辫发承载了强国强种的政治重任,又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革命派提倡剪辫的动机,与维新派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与维新派不同的地方,即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冠服徽识,是民族的外部特征之一,常与民族精神相联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清朝强令汉族和其他民族剃发蓄辫,是满族统治集团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罪行之一,革命要唤起人们对这一罪行的仇恨,以便激发出更大的反满热情。因辫发而腾笑五洲的奇耻大辱,乃是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所造成的,是反清革命的动因之一。于是,剪辫成为争取“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羁”的人们斗争的目标。革命者以此作为激发人民排满情绪,投入反清革命的有力手段。《黄帝魂》中刊载了《论辫发原由》一文,写道:“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注:张枬:《论辫发原由》,原载《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8页。)
显然,时代虽然变化,但是作为民族认同与文化记忆的辫发问题,却贯穿了有清一朝。就像清初剃发是归附清朝的标志一样,清末剪辫与否,也常常成为人们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表现,人们往往“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注:匪石:《野荻一夕话》,《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再版。)。革命党人视剪辫为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而清王朝也竭力反对剪辫,剪辫者即为革命党之流。在1905年,当端方、戴鸿慈等出洋考察宪政官员回国“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宫深滋不悦”(注:《要闻》,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版。)。此后不久,“戴少怀侍郎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注:《要闻》,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更是将剪发同革命谋反联系起来。发辫成了双方尖锐矛盾、斗争的集中的身体体现。不过,剪辫易服之潮流自1910年开始汹涌而来。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而在种种压力面前,武昌起义不久,清政府下达了一道谕旨,承认了剪辫易服运动,谕旨云:“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注:《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使剪辫得以全面开展。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发布《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历数辫发为清罪状之一,并立即颁布禁止蓄辫文(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剪辫与否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身体标志。由于剪辫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对各阶层的要求有所差别。11月上旬,由都督府传谕军、警、政三界人士:“近日剪发者固多,阳奉阴违者实繁有徒。从初十日起,三日之内,由各长官调查,一律除去发辫;否则革除,听其自便。”又规定各机关职员蓄辫者没收证章;军队士兵不剪发辫者不发月饷。有几天还特设检查哨于各城门,蓄辫者不得出入(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对平民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认为“既于商民无碍,而限期在本年之内,尤非操切可比”(注:《内务部关于剪发不易服等奉批议复事申复黎都督文》,《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页。),故一般商民仍多观望。直至1912年1月3日,乃制发国民执照,交保安总社转发各分社,劝令商民一律剪发,听者予执照一张,以免入城门时受军警盘诘,一方严令警士干涉,勒令剪去。为此,“士兵携带剪刀,阻拦行人,强行剪发,所剪下之发仍交还本人”(注:《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58号,《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见,剪辫主要是作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而被推行。距“剃发令”266年,距“蓄发令”60年,又出现的这道影响深远的“剪辫令”,虽然仍很严厉,但没以死相挟,可响应者却较前两次为多。“未及三日,武汉之头颅一新,各属遂以不令而行矣。”(注: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册,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版,第69页。) 通过努力,在首义之区尽管不能断言辫发已肃清,但敢于明目张胆摇着辫子横行街市的人确实少多了。而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数千人集体剪掉发辫的壮观景象(注:《上海时报》,1911年12月17日。)。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准资政院请,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综览晚清时期辫发的发展,可以看到,随着现代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剪辫被逐渐推广开来。这种演变本身就承载着复杂的历史前行,因而剪辫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当辛亥革命使一根根辫子落地后,却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遗老遗少们拖着真辫子与假辫子弹冠相庆;还有人头戴方巾,身穿明代的古装,腰佩龙泉宝剑招摇过市。这些有关发式服饰颇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其实反映的是辛亥之后社会心态、政治态度与文化观念的混杂性。围绕着是否剪发易服的背后其实是身体如何现代化、世界化的问题。遗老遗少则从文化方面考虑,认为辫子乃是中国的“传统”,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割裂的,剪发乃是西式的生活风俗,不足效仿。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清末民初被文化上的遗老遗少所坚持的辫子,在二百多年前正是被明末清初文化“遗民”所激烈反对的。这一历程本身体现的是有清一代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中西二元对立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逐渐得到加强。
由此可见,剪辫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并行。它的每一次发展都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重大进步。由维新变法时期的“奏请断发易服改元”,到革命派“华服剪辫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即是明证。可以说,这种势在必行的改变既是中国与世界外交礼仪从冲突到趋同的进步过程,又是中国半殖民地不断深化的屈辱过程,更是传统中国在世界文明浪潮冲击下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此外,随着革命和时代的变化发式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剪辫运动由全国各地兴起而后推动京畿地区,京畿地区的民众推动清政府。这种由下而上的推进过程,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进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剪辫令所造成的流血牺牲远比剃发令和蓄发令要少得多,也反映民主共和时代政治上的进步性。
从横向来看,剪辫同时也是个人政治态度的反映。湖北新军的官兵在举起武昌起义义旗之前剪了辫子,以无辫为革命标志。章太炎不满于唐才常等人的勤王主张,就用“割辫与绝”的方式表示与改良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都以剪辫为革命的先行。康有为几次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同他在剪辫问题上的摇摆紧密相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请求皇帝率先断发易服,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起点(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369页。)。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袭来时,他成为了保皇党,反对革命。1912年,他给逊帝溥仪上书,追悔戊戌上书时说的话,表明当时想剪辫易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过五年,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暂时“寒流”,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竟想留发重梳辫子了。从剪辫到蓄辫,表现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一种转变。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处在辫子军保护的小朝廷中,蓄着不足六七寸的辫子,已经成为了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守旧派。辫子的去留俨然已经成为政治态度的表现,由此可见辫发在清朝历史中深重的政治意味。
相对而言,民国初年留辫的人多为政治或思想保守者。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以保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怀念与忠诚,他们甚至梦想清室复辟,这可以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为代表。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出于一种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一时看不惯短发。遗老辜鸿铭觉得自己留的那条稀疏的花白头发编成的辫子仿佛是中国几千年道统的象征。还有的人已经把辫子当成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不舍得剪掉。在浙江海宁乡下,“镇上茶馆里,就有五六个年轻朋友,专门乘人不备,代人剪辫,惹起许多口舌。有的人辫子被剪掉了,抱头痛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硬要剪辫子的人赔偿损失”(注:严谔声:《剪辫子》,《新民晚报》1961年10月11日。)。另有一些人怕剪了辫子要穿洋服,“以夷变夏”,所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人怕皇帝再坐龙廷,会杀无辫的人,所以对剪辫和革命持观望的态度。
总体而言,由于辫发在有清一代蕴涵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含义,因而对待剪辫的态度是衡量个人思想态度的外在标志。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辫发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就如多棱镜般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的歧异和对立。然而无论如何,辛亥革命后人们毕竟获得了剪辫的自由,短发逐渐普及。在清末曾因辫子吃过苦头的鲁迅说,他之所以爱护共和制的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是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注: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5页。)。这句话本身除了对于剪辫的欢迎之外,也暗含着文化与政治上的意味。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和观点也会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二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辛亥革命的确使封建伦理道德及其派生出来的许多习俗、理念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观念进一步动摇,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新习尚得以更快传播。但这种社会意识领域内的变化是不均衡的,受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宗法结构、民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种种的差异性在剪辫运动中都得到了深刻反映。
“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注:《论辫发原由》,原载《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8页。)。如同清王朝的覆灭不是导致新王朝的建立,而是中华民国的诞生一样,发辫的肃清也不是重新束发于顶,而是短发的普及。辫发作为一种传统的象征,一种文化记忆和一种政治符号,已然随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加强,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剪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新时代的革命意义,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身体领域的反映。剪辫运动同辛亥革命一样,受到世界变革潮流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结语
从清王朝前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辫发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式风俗问题,而且是涉及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就清初剃发的历史曾说:“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个汉人生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之怪现象。”(注:[日]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而这一所谓“怪现象”正说明发式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满族统治者为确立自己统治权威的一种表现。清王朝一直奉行剃发政策,视百姓剃发为顺从其统治的象征,这就使得辫发与其后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始终密切相关,成为社会运动、政治斗争和移风易俗的冲突焦点。而辫子本身从“剃”到“蓄”再到“剪”的变化过程,也见证了整个清王朝的兴衰和中国逐渐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如同发式的变化需要渐变的过程一样,这段历史也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一种新发式能否最终取代旧发式,也成了政治斗争能否成功的标志。
同一时期的人们对辫发的认识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局面,反映出社会心理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样一条辫子也发生了态度上的转变,又体现了相异的文化和习俗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古语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剧烈的社会转变总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排斥,这是心理定势在发生作用。而这种转变能否最终完成,不仅取决于新事物对固有环境的适应程度,更取决于经济、政治等的发展状况和主导文化的开放、包容程度。而习俗和文化一旦确立为传统,就会有极强的传承性,并往往在下一次新旧交替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尽管也会表现出某种变异性。这些特性在辫发问题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辫发,属于身体,更属于历史。辫发是关系统治权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习尚的大问题,是历史冲突的焦点,更是个人和社会发展轨迹的一份真实记录。
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有清一代发式问题所体现的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和宰制。从剃发到蓄发、剪发,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史成为一部身体史。民族的风俗、文化理念以及政治权力,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并没有选择身体姿态的自由,而是必须受限于外在“权力”的摆布。与此同时,选择何种身体姿态,也就成为表达政治态度、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心态的身体符号。在这种身体文化中,贯穿清朝始终的辫发史,展示的是身体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塑造的历程。
标签:太平天国论文; 太平军论文; 剃发令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满族服饰论文; 历史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专门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