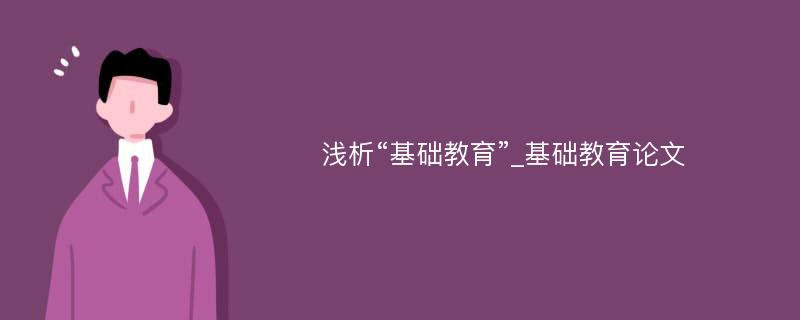
“基础教育”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谓“基础教育”?《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它亦称“国民基础教育”,是对国民实施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质的教育,或者指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有的包括初中教育”。且不说其中表述基础内涵的那一堆判断,到底反映了这种教育的什么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单就其表述的“基础教育”概念的外延来说,它撇开了高级中学教育,不知这是对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基础教育的界定?它至少同中国如今的“基础教育”概念有别。因为我国多年来早就把教育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教育”四个部类,其中“基础教育”不仅把高级中学教育涵盖在内,甚至还包括幼儿教育。恐怕这种界定属于把“基础教育”同我国现行“义务教育”概念混淆之误。这种常识性错误姑且不说,值得讨论的是“基础教育”内涵问题,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长期流行、迄今仍然通行的“基础教育”观念问题。
我国教育界对“基础教育”到底如何理解?其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呢?
一
在中国,尽管谁都不会不知道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并且相信我们在中小学实施的正是“基础教育”;问题是我国中小学教育一直受升学或就业“两种准备”教条支配,或者干脆是“一种准备”。这就是所谓“应试教育”。它表明现有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是高一级学校的预备教育;也许有相当多的中小学还不足以为学生接受高一级教育提供充分的准备,而只是为学生提供一张高一级学校的入场券;其中,等而下之者,甚至就连这种入场券也拿不出来,怎不急煞人也?
正是这种客观现实,使得我们除了这种狭隘的功利考虑以外,很少有心思去考虑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本身有没有价值(工具价值以外的固有价值)?
国家、社会和家长在教育上不吝啬投资,教师们千辛万苦,大抵出于一种共同信念:“培养下一代”,也可以说是追求实现教育的固有价值;问题在于尽管教师面对的是有待培养的活生生的未成年人,而作为高一级学校预备教育的中小学,却难以从学生成长的实际出发,难以顾及他们的自然需求与承受能力。因为这种预备教育不能不受高一级学校的逻辑支配,甚至只受高一级学校招生的行情支配,以致客观上不得不违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以牺牲学生的自然需求为代价换取学校、教师与某些家长的成功。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仿佛把“培养下一代”的期望主要寄托于高一级学校,尤其是大学,而中小学的任务则是带领学生拜领几张纸,证明他们曾经在这里虚耗过自己不少花样的年华。
自然,为了拜领一迭纸而辛劳,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这也是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何况学校中毕竟也还有不少对人生有价值的知识与教育;只是我们一直未分辨基础教育的固有价值与工具价值,以致未把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作为问题提出来,仿佛只要学生能升学或就业就足以证明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性”。
尽管我们一直忙于学生的升学或就业准备,倒也并不把它们视为基础教育的理想状态;虽然没有明确基础教育固有价值问题,我们提出的许多口号,如“教育的人文精神”、“学生主体性”、“培养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等等,倒也表明我们越来越接近于这种思考,只是这堆口号较为空泛。如果说诸如此类的口号能够成立,那么,至少还得考虑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如何体现“人文精神”与“学生主体性”,根据什么确定中小学学生应具备的“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可见这一堆口号还代替不了对中小学教育“基础性”问题的回答。
二
所谓“基础教育”,简单地说,指的是在未成年期为人的一生奠定基础的教育。如此界说,似无新意。不过,由于它着眼于人的一生,也就同限于升学或就业准备的基础教育观念有别,而正是这个人们都懂得的道理,却包涵一条常常被人忽视的衡量中小学教育的标准,即:在中小学教育中,凡是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的障碍都必须解除,以避免使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受挫,凡是对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识、技术以及行为规范,都不可忽视,而不给学生后来的发展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反之,一时一事需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技术、行为规范等)是不是该列入基础教育,不能单以这种东西的绝对价值衡量。由于学生受教育的时间有限,对一时一事需要的内容的取舍,宜以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及他们后来发展的需要为尺度权衡。依此看来,我国以往虽把中小学教育定为“基础教育”,而往往并不把它当作“基础教育”看待。
自然,如此说法仍不免空泛,需要讨论的是中小学到底如何为人生作准备,而不限于为他们的升学或就业作准备?其实这就是同样为人所共知的“普通教育”。
何谓“普通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并无这个词条。大概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无须解释,《辞海·教育学、心理学》解为“实施普通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什么是“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呢?或许同样由于它太“普通”了,也就无须解释。说到“普通教育”,在区别同级其他学校教育时,指的是“一般教养”,而不是特殊教养(如职业教养);它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中的未成年人都共同需要而又不可缺少的教养,也不同于造就专门人才的教育(如高等教育)。那么,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中未成年人共同需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教养是什么呢?要在文化科学知识海洋中选择、提炼出这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识,势必需要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其中包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基本需求和学校原有课程状况、学生心理状况的实证调查,并致力于经得起实践检验与严格论证的试验。如果要从别国举例,不妨以美国的“八年研究”为例。美国进步教育协会为了编制基础教育课程,曾在1934~1942(或说1932~1940)年间,择定30所中学进行试验研究。其中包括对从这30所中学毕业升入高等学校的1475名学生与同样数量的其他学校毕业生的比较研究。此外,各门课程委员会还对数以百计的学校进行广泛的调查;另据课程专家泰勒于1949年称:“在过去的25年里,为了推导教育目标,对当代生活已经做过几百项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对行为的观察,对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前沿思想家对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的分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区研究等(注: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我国以往历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少不了进行调查与试验,并且调查与试验的规模比美国“八年研究”还要庞大。即使就课程开发的经费来说,美国“八年研究”中由基金会提供的经费总额为160多万美元,而我国仅此次课程改革的财政支出即远远超过此数。问题是我国历次课程调查与试验的结果并不可靠,缺乏科学性,经不起实践检验与严格论证,以致终究心中无数,从而使基础教育课程长期处在不断纠正偏向的状态。意味着主要靠尝试错误,才得到一些改进。以往课程调查与试验不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每项调查与试验,总免不了事前确定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本来是要在调查与试验中经受检验的,而我们却往往把这种假设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和课程设计的前提;更由于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情况不断变化,一般价值观念及课程价值观念不免随之变化,从而引起课程的频繁变动。说到课程理念的形成,且不说教育主管当局缺乏课程理论的专业修养,即使是主持与参与课程改革的行政人员与学科专家,他们或许有深厚的学科修养与教学经验,一般尚缺乏足够的课程理论与技术修养。虽也力求借鉴外国课程改革的经验,却未必了解别的国家课程设计所由产生的那种思路与程序。这且不谈,如上所述,在我国就连“基础教育”、“普通教育”固有含义是不是被充分理解,至今仍是问题。
泰勒在论及学科专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建议的价值时,曾经指出:学科专家对基础教育课程问题的提法常常是:将来要在某个学科领域从事更高深研究的学生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基础教育课程。所以,他们的建议往往不尽切合时宜;依他所见,学科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是:某门学科对那些将来也许不会成为这门学科专家的学生可能或应该作出什么贡献,即某门学科对该学科的外行或公民可能或应该作出什么贡献。(注: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这实际上是要求有机会主持或参与基础教育课程设计的学科专家,以“基础教育”、“普通教育”为着眼点。泰勒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问题,在我国是否已经引起注意,尚难断定;不过,从我国2001年公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不难发现,此次课程改革业已开始触及课程体制、课程机制以及课程设计技术之类问题。表明它确已超越了学科专家的视野。至于编写中的课程标准、教材中所体现的“基础教育”、“普通教育”的含量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了。
三
涉及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质问题,除了“普通教育”的内涵以外,就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来说,还存在中小学课程限度问题。这又同“义务教育”观念相关。
义务教育课程要求办学主体所承担的“义务”是否该有个限度,这是人们甚少考虑的问题。不错,所定课程本身就有限;问题在于所定的这些课程及其要求,都属办学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么?都是儿童和少年能够承担的法律义务么?例如,我国学生课业负担长期居高不下,从儿童和少年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角度考虑是否合适?又如家长和社会期待学校使儿童和少年都能顺利地升学或就业,不可谓不合理,而所有学校都单独承担得起这种义务么?学生在学校中发生伤害事故,不问青红皂白,都追究学校责任,学校负得起这种责任么?我们还要求学校发展儿童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在现有教育机制、教学制度与办学条件下,到底有多大可能实现这种目标?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在课程层面该不该体现教育的义务性质,究竟根据什么规定办学主体和学生双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相比之下,有些国家只给义务教育课程确立合格标准(起码的普通教育),而把超越合格标准的追求,看成是办学主体与学生自己的事。这种有限的义务,不仅对于办学主体较为合理,而且对于平均水平以上和平均水平以下的学生也较为公平,况且只有在较为宽松的课程背景下,才更有可能进行有真正教育意义的活动。
法律意义的义务,带有强制性,不能不有一定限度;自然,除此以外,还可诉诸道德义务,激励人们自觉自愿地作超越法律义务的追求,不过,划一而又过高的要求,即使从道德义务看来不也有失公平么?
规定多少课程是一回事,学生经验的课程(他们实际掌握的知识技术和得到的发展即他们的教养),则是另一回事,课程的“过程模式”与“目标模式”代表两种不同的思路,就其实际成效而论,很难论定课程标准的高低。
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课程改革中的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并不期待我国课程很快作改弦易辙之举;只是在同年级所有学生满负荷课业的情况下,解决面向全体学生与照顾学生个性之类历史性的矛盾,要不流于空谈,却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