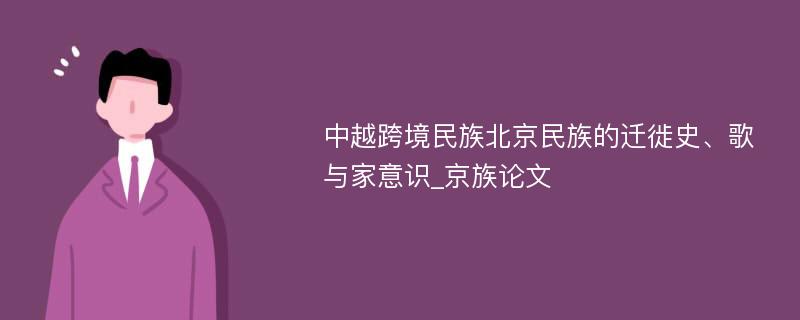
中越跨境民族京族的迁徙史歌与家园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族论文,中越论文,跨境论文,意识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沙白浪、潮涨潮汐,在中国东兴的京族三岛上,一首首悲切而坚韧的迁徙史歌随着海风低徊飘散。这些迁徙史歌唱述着京族祖先由越南迁徙到中国土地后,如何以海为生、开辟家园、歃血为盟、建亭祭祀、固守边疆的历史记忆。同时,地方叙事和民间信仰,与史歌交织融汇,共同为世人理解京族的历史起源、生命记忆、情感心理与族群认同建构出立体多维的文化情境。概言之,京族迁徙史歌,紧紧围绕家园的建立与守护,真切展现了京族从漂移不定转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同时,强烈的“家园意识”作为精神内核,不仅推进了新土地上家户与家户、村落与村落、族群与族群间的契洽与互动,还将不同的迁徙族群吸纳为一个同心圆。那些各自迁徙飘零、游移不定的族群身份也逐渐得以聚拢、凝结,呈现为中越跨境民族——京族这样一个散发着海洋气息与边际色彩的“文化共同体”。 一 史歌叙事:迁徙族群的失忆与记忆 史歌,包含了历史与文学两个叙事维度。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是族群集体对文化渊源与历史记忆的再现与追溯;作为一种文学生活,史歌叙事又带有演述主体鲜明的情感与想象。换言之,史歌叙事是“共同体叙事”和个体情感表达的双重演述、相互渗透。所谓“共同体叙事”,指的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中对“诸如神话、仪式、传说、巫术、魔幻灵异、地方邪技、宗教信仰和民间故事等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时发现,那些以仪式和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叙事类型经常没有作者却有叙事者。”①而一个民族(族群)的史歌唱述,依靠的是族群集体记忆之下个体情感和历史经验的推波助澜,是一代代演述者选择性的失忆与记忆的传承。那么,在史歌叙事中,叙事者的集体记忆如何塑造个体记忆?历史叙事如何与文学生活达成默契,并推动着个体生命与族群文化的互动生长? 在王明珂看来,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族群)史歌,关键在于尝试理解书写者的“情感”与“意图”,及产生如此叙事的各种情境。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在文化实践层面打通一条由集体到个体、经文本到情境的路径,“如此我们才可以对他者所产生的历史产生同情与理解,体会与体悟。”②只有对文化主体建构族群历史的文化实践有所感知与体悟,才有助于我们对史歌叙事的真切聆听,进而去探求一个族群文化传承不息的实践动力。 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下属的东兴市。京族祖先来自越南,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中国的巫头、山心、澫尾三地以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区并定居下来。京族自称为“Kinh”,越南语“Kinh”的发音与“京”相同,因此汉译为“京人”。京族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安南人”“越族”,经国务院批准,1958年5月正式定名为“京族”。在越南,京族占越南总人口的86%,是越南的主体民族。自越南迁徙而来的族群历史,山海相连的生态生计,京族文化呈现出独特多元的文化蕴涵。京族民众对自我文化的热爱坚守与自觉保护,保留下许多生动感人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生活。诚如京族人自己的表述:“凡是历史上用字喃和汉字抄写的碑刻、文书、文献,以及京族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均是京族文化的宝贵资料。”③这些文化遗产的生生不息,在京族人的文化实践中活态传承,成为京族族群认同的精神与动力。 本研究所选择的三个京族迁徙史歌文本取自《京族喃字史歌集》,分别是《澫尾京族简史》《巫头史歌》《山心史歌》。④这三个文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从民间搜集,经整理后编写而成,出版时体现为以京语(国际音标)、喃字、现代拉丁化越南语和汉文四种文字并置的文本形式。这些经由印刷技术呈现的文本,犹如川剧变脸的“脸谱”,为想象京族的族性和文化提供了固化可视的表征,但却无法真切地观照京族驳杂多元的历史本相与文化本性。而这些带着情感温度和生命力度的史歌唱述,则能够带领我们去聆听和体验京族文化的厚度与深度。仔细听来,巫头、山心、澫尾三岛的史歌有着相同的叙事结构又表述不同,呈现了京族祖先是由不同的人群从越南的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来到不同的岛屿上安家落户、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与具体过程。 通常而言,时间作为史歌的纵向线索,贯穿着史歌的叙事进程。综观三首京族迁徙史歌,除了《澫尾京族简史》给我们提供“洪顺三年”这一越南封建王朝的历史纪年之外,其他两首史歌并没有呈现任何具体的年代。澫尾史歌之所以出现“洪顺三年”,据史歌的收集编撰者苏维芳讲述,是哈亭祖传的亭规中有这样的规定:“承先祖父洪顺三年,贯在涂山,漂流出到……立居乡邑,一社二村,各有亭祠。”⑤因此,有可能是编撰者根据这一信息对澫尾史歌进行补充。此后,澫尾史歌的整个叙事也不再出现任何具体的历史年代信息。同时,这些史歌文本虽是当代京族文化精英搜集编撰而成,但从叙事所提及的危机事件只有天灾和盗抢,尚未出现法国殖民者入侵的相关事件,可以推知,这些史歌叙事传承的时间不少于两三百年。纵观这三首京族史歌的叙事过程,均以“代代”“十几代”等家庭代际概念来表述时间,并未采用地契等文书中的越南封建王朝年号的历史时间来表达。“洪顺三年”宛若一个“休止符”,标记京族在越南生活历史的终止。可见,京族史歌叙事中,这些驾着竹舟涉海而来的京族祖先,在脱离越南统治又尚未得到中国接收的情境下,对封建国家王朝历史进行选择性地“失忆”。 反之,京族迁徙史歌则表现出清晰、稳定的空间观念。例如《山心史歌》所唱: 清晨出海晚归来,久住认为好家园。南面一片红树林,退潮海滩似平原。西面相邻是佳邦,西北不远到安良;东北相接贵明村,四周方向已明朗。先人寻得好地方,砍树割草建茅房。 京族史歌迁徙对家园的选址方位、村子的功能布局、空间的地理生态所进行的精细空间描述,体现出迁徙族群对家园之安稳的情感想象。迁徙史歌如此翔实、真切的空间位置和地方感,与京族三岛命运多舛的历史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朝以前,京族三岛地区是中越两个封建王朝权力博弈之地,在国家归属上一直漂移不定,因此有“飞地”之称。⑥由此可见,开创家园的行为实践成为京族人深切感知祖先的关键所在。 京族迁徙史歌之所以能够成为族群叙事与集体记忆,很重要的因素是以“祖先”为史歌的叙事者与主人公。例如: 家家设立祖神堂,村村建起庙亭祠。财物丰盛生活好,人丁兴旺胜往年;每年六月初十始,唱哈祭祀乐数天。沧桑经历十几代,前继后接涂山人,大家同心共发誓,克服困难建家园。(《澫尾京族简史》) 祖先誓言要牢记,齐心协力建家园。(《巫头史歌》) 祖先住此心满意,此处是个好地方。(《山心史歌》) 史歌开篇通过唱述祖先籍贯来展开对祖先的历史追述,结尾又是依托祖先的口吻对后代提出劝谕,可见,“祖先”开创新“家园”的功绩,成为京族集体记忆的深刻烙印。 京族迁徙史歌中的集体记忆,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回忆形象”来串接、勾连和交集。所谓“回忆形象”,指的是每个族群的文化记忆均有自己的“固定点”,它的视野不随时间的向前推进而发生变动。“这些固定点乃是过去的命运性的事件,人们通过文化造型(文字材料、礼仪仪式、文物)和制度化的沟通(朗诵、庆祝、观看)依然保持着对这种过去的回忆。”⑦在三首京族史歌中,以海为生、开创家园、歃血为盟、建亭祭祀成为京族史歌基本的叙事题材与发展结构。可见,迁徙族群的记忆不再飘忽,历史不再单薄,而是以“回忆形象”为依托,在祭祀仪式、庆典展演与个体回忆的集体“狂欢”与众声“喧嚣”中,形成固定的“制度”,构建出活态传承的族群历史。据京族老人所言,“文革”期间,京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哈节被严令禁止,哈亭也遭受破坏;但“文革”之后,在国家恢复民族文化的大语境之下,京族人就是依靠这些史歌一句句的唱述来恢复哈亭的形制构造与唱哈的仪式过程。⑧正是在此种史歌叙事与“回忆形象”的相互沟通与激发,京族重拾了哈节记忆,延续了族群的传统。 综观京族迁徙史歌的叙事,无论是时间标记、空间观念、叙事主人公,还是关乎族群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回忆形象”,均对族群漂移迁徙之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状况不做描述。这对于迁徙族群和史歌文体而言,仿佛一个悖论,是文化主体有意为之的遗忘,还是不想触碰历史伤痛的逃遁?而史歌叙事对从漂移迁徙到安居乐业的变迁过程所作的详尽记述,对地理空间所作的充分渲染,却成为一种强化的集体“记忆”,在一代又一代传述中形塑着京族自我的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 二 家园意识:边缘族群的族性与实践 对越南历史的选择性“失忆”,对“祖先”“家园”和“哈亭”的强调性“记忆”,在京族迁徙史歌叙事结构中形成强烈对照,既反映出京族祖先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的迁徙历史,也凸显出边缘族群在迁入中国海岛后开创新家园的“家园意识”,诚如在《澫尾京族简史》中唱诵的“原来故乡相隔远,如今此地是故乡。”历史的原乡已然不可重返,京族祖先只能将“故乡”的情感移植在新的土地上,并通过辛勤劳动,让漂移的生命落地生根、代代绵延。 就人类发展历史而言,“家”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家”的内涵非常丰富。从人类学的概念和实体而言,“家”首先指的是“家庭”,一般由父母孩子构成的团体,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家”的繁衍与扩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⑨,“家户组织的功能通过社会化创造了稳定性和寻求社会的连续性。”⑩正是京族祖先的英勇开拓、辛勤创造,由核心家庭的人口一代代累积,扩大为有世系关系的家族。从京族史歌的描述中,我们得知,京族祖先最先是打渔漂流到中国的海岛上,依据澫尾当地说法有苏、杜、黄、罗、高、武、龚、孔、裴、阮、梁、吴等十二姓,皆从越南涂山打渔迁来。这十二位祖先被称为“十二家先”,成为京族民众尊崇的共同家神,在哈亭中受到代代子孙的供奉。如《巫头史歌》所唱:“添丁发财家兴旺,建亭立祀安祖灵。纪念前辈却心愿,‘十二家先’建哈亭。姓裴姓陶段黎阮,刘何吴武潘孔黄;十二姓人互相依,巫头岛上聚一堂。” 由此推知,京族祖先迁徙到中国海岛上定居,最初是夫妻组合的核心家庭,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共同劳动生产,共同担负家庭事业,形成和睦相处的家庭规范。如今,京族地区还保存着这一习俗,即家里男子每次出海,老人、妇女、孩子全家人都到海滩送行,并举行海祭活动保佑家人平安归来。京族人对家人与家园的重视在核心家庭的基础上既有纵向延续也有横向拓展。纵向维度上,京族的亲属称谓在以父系称呼为中心的基础上,其基本称谓只有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显示出核心家庭代代呈递的代际关系。横向维度上,京族人还把这套亲属称谓用到了整个社会无血亲、姻亲的关系中。可以想见,京族人对安宁之“家园”怀有的强烈意念,以及在维系家园关系中的地方智慧。 京族迁徙史歌告诉我们,京族祖先是不同的人群、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迁移到京族三岛。进入京族村落我们可以看到,因京族各姓家族的祖先迁来岛上并定居的时间各不相同,京族人家“大多单门独户”,“相同姓氏内部高度聚居,不同姓氏保持一定距离”,构成了京族人家在村落的分布是“零星又相对紧密”的独特空间布局。(11)彭兆荣认为,与汉人村落直系纵线式的祖先祭祀不同,包括巫头、山心和澫尾在内,京族自然村落的家族构成不是单姓、复姓,而是多姓。所以京族更趋向于横向联盟式的共同体认同。如果说汉人村落带有认同中“根基论”的色彩,侧重于根据同一祖先的缘生纽带建立共同体认同,而京族则强调认同的“情境论”,即侧重于根据现实的利益和功能进行共同体认同。在这种情形中,京族的族源认同就带有更多“想象”的特点。京族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首先由核心家庭与核心家庭组合聚居,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人群聚落,之后歃血为盟,同心协力,共同完成族群内部的生产事业和社会事业。可见,史歌的“家园意识”作为京族祖先的族群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着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迁徙族群的“根基历史”,使得在不同岛屿上分散而居的各个族群,形成具有极强凝聚力的文化共同体。 京族迁徙史歌没有王朝历史的时间表述,而是家族代际的传递承继,此种叙事时间的视角反而为讲述者与聆听者创造了一种文化体验的真实。在这样的口传身授中,父辈的历史得以转移到儿孙的记忆与行为中,成为京族人共同的“习性”。“习性”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布迪厄认为,“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12)“习性”作为集体记忆,能够形塑与激发个体生命的思想、表达与行为实践。京族史歌唱述着祖先开创家园的功绩,形成京族集体记忆的“习性”代代相传,逐渐成为后世子孙所共享的爱护与守护家园的信念与实践。 京族迁徙史歌中还有一个重要构成,就是京族祖先如何建立哈亭、祀神祭祖的叙事。如《山心史歌》所唱述: 先人寻得好地方,砍树割草建茅房。为了骨肉不分离,回乡接亲来同堂。居住这里时间长,生儿育女人兴旺。大家杀鸡煮糯饭。歃血为盟互不忘。恰逢良机鱼水情,和睦共处年过年,此处安居有数年,砍树成木建家园。日月如梭时光逝去,巫头有人迁来居,同出同入小村庄,南风送暖夏时至。举目喜看山水奇,日间清幽夜美丽;大家谋生都顺手,仙山琼阁不能比。祖先决心住这里,大家定心来安居。后有盗贼来抢掠,遇见美女便抓去。当时祖先共商量,要立香案聘祖堂。遂派人回故居地,拜别宗灵迎祖香。先祖众人许诺言,建立哈亭迎神灵,拜祭神王建哈亭。 这些叙事呈现出京族民众的信仰观念与家园意识的紧密关系,郑向春认为这是一种“圣俗互渗”(13)的文化结构。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互渗”,毋宁说是京族在“家园意识”之“惯习”的引导下,形成了引神入俗、“家”“神”共在的“信念”,以及祭神护家、酬神娱人的“实践”。鉴此,京族人的文化主体性可见一斑。 田野调查资料也证明,京族的神分为“家神”“庙神”和“哈亭神”。京族人家里供奉的神是“家神”,主要指“祖灵”。在田野调查中笔者看到,京族人家厅堂正壁上都设有神台,上面供着列宗祖灵,神台又称为“祖公”,上写“某(姓)门堂上历代先远宗亲之位”,有些京族人称呼“祖神”为“家神”。京族人家的庭院里,与厅堂门口对着的位置,家家户户都设有一个高约一米的神台,神台上层是天官,神位写着“天官赐福”,下层是“土地”,神位写着“土家土地”和“本家土地”,“土地”为家宅的保护神。此外,“哈亭神”除了护佑家园的神圣,还供奉着本村诸家先灵,村中各祖宗神位,也设在哈亭中,与诸位神圣一起,共享众祭。从京族的信仰观念与祭祀仪式中,认为祖灵能够保佑子孙万代,祈祷神祇护佑家园安宁,处处释放着浓郁的“家园意识”。 诚然,京族强烈的“家园意识”与“家园”来之不易也有很大的关系。京族祖先自16世纪初叶陆续迁到中国,虽然史歌叙事中没有讲述背井离乡的原因,但对应越南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越南正值西山农民起义,后黎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衰落,整个社会战火频仍、政局动荡、民生凋敝。1858年法越战争,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而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位于中越边疆的中国京族被卷入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成为生活在中越两国边疆地带的边缘族群,遭受着家园入侵、国破家亡的家园危机。在这一被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京族民众所传承的“家园意识”,成为其作为边缘族群的精神内核与实践动力。在后来的史歌叙事中,陆续出现了《京族英雄杜光辉》《京族统领苏光清》等英雄史歌,纷纷唱述杜光辉、苏光清等抵御外敌、反抗殖民的英雄叙事,充溢着勇敢守护国家疆土与自我家园相结合的“回忆形象”,激励着京族人在危难中挺身而出、英勇奋战。 可见,史歌作为一种族群记忆与文学想象的叙事类型,不仅记录族群历史、解释文化变迁,也在口传身授的文化实践中对变迁加以主动的推进。这些京族迁徙史歌以“家园意识”为核心精神,讲述了不同地区的京族共同记忆、共同生计、共同地缘与共同命运的叙事,以及京族个体家庭-多姓村落-文化族群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衍生与发展。史歌代代传述,内化于个体,发挥着指导京族及其个体成员积极行动的文化能力。 三 文化认同:跨境族群的边界与互动 京族三岛的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认同,逐渐形成了以海洋民族为族性、以中越跨境民族为族群身份的文化共同体。而跨境族群的身份,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的想象。当我们以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步入京族三岛,以“主位”的视角沉潜于京族的生活,京族的历史起源、生命记忆、情感心理与族群认同就会在想象叙事中渐渐地生动浮现。 如果说京族祖先背井离乡、漂移异域来到中国岛屿上,是在孤寂隔绝的环境中相互抱团取暖;那么,建立家园、劳动协作的联手互助,则是族群之间的互动与壮大。在人类学看来,社会中有两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一种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是同样也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是共生(Symbiosis),后者是契洽(Consensus)。”(14)和谐的人类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契洽”关系,即人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其他人以获得共同的发展。在京族史歌中,京族各个族群之间通过歃血为盟、建亭立祠、家神同在、异祖共祭的形式来达成族群的认同、结盟与互动,从几乎没有血缘联系的零星家庭的居住聚落,发展为一个有着核心精神和族群传统的文化共同体。例如《澫尾京族简史》所唱述的: 大伙会集共商量,决定在此建草房。众心目归一处想,你去砍树我砌墙。大家辛苦日夜干,砍树割草来建房;日月如梭消逝去,光阴似箭时间忘。房屋终于修建成,遮风挡雨有地方。原来故乡相隔远,如今此地是故乡。大家团结如一家,纵然饥馑也不怕;共同发誓相帮助,集中捕捞分鱼虾。 因为文化主体相同的历史命运与现实际遇,不同的京族聚落在史歌叙事中均体现出大致相同的题材要素与发展结构。正如王明珂在对华夏边缘族群文化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文化之模仿、攀附常常发生在亲近人群之间”(15)的看法。无论是族群内部还是同一村寨的各姓氏之间,京族民众形成了团结互助、共同担当的精神。最能体现京族团结互助精神依旧在民间社会通行的是“异祖共祭”习俗,即一些没有后代的老人去世后,同村人也会把这些亡灵牌位请到哈亭中供奉,使其灵魂得以安慰与归属。历史上,京族曾流行一种“寄赖”的习俗,就是赶海归来的劳动收获,与途经遇见者一起分享。笔者在另一个京族村落红坎村的哈节中,看到来自不同村子的京族民众,既有亲朋好友、地方精英,也有游人访客。对于红坎哈亭上所挂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复制品,牌匾最初授予的澫尾哈亭亭长苏春发的解释是,红坎哈节也是京族的节日,“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16)。对于国家所颁发的荣誉,澫尾京族没有垄断独占,而是乐于与其他京族村落共享。可见,京族各村落达成了一种互动与契洽,不仅凝聚为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表征,也达成了各村落的心理沟通与资源共享的动态过程。 如果说在《澫尾京族简史》《巫头史歌》《山心史歌》的叙事中,京族呈现出的还是一个边缘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实践;那么,19世纪后期法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被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把京族这一外迁而来、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边缘的族群纳入了民族-国家的范畴,并推到了国家危难命运的风口浪尖。诚如王明珂指出:“由于资源、国家主权及跨边境交流等因素,国家与民族‘边界’是最神圣也是最危险的,最遥远也是最切身的,最易被忽略也是最受密切关注的”(17)。族群的“边界”不仅指向地理空间,还指向人们的主观意识。人类学家巴斯认为,族群边界是社会边界,族群除了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性,这一人群还有共享的文化与价值,构成联系互动的范围并拥有自我认定与他者认定的成员资格,而恰恰是在联系互动中可能以选择强调族群身份的方式来拓展其新的地位及组织活动模式。(18)可见,“边界”是由族群主体来选择和建构的,虽然有着“祖先来自越南”的身份表述,但国破家亡的共同命运,激发出京族作为中国边疆的国家观念。京族跨中越边境而居,处于国家边界与族群边界“交叠”的矛盾,无疑会形成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错落”。这一复杂问题,笔者另文撰述。但毋庸置疑,恰是在“家园意识”的情感感召与精神凝聚之下,京族各个村落发生着良性的交流与互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营造出边疆和谐、文化共生的良好生态。 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我们规避文化解释过程中的“脸谱化”与“想当然”,对具有独特表征与多元蕴藉的族群叙事给予体贴与尊重。流传在不同地区的京族迁徙史歌,是生命歌吟与生活日常的勾连贯通,以人类学长时段和整体性的理论视域,我们能够还原出京族所经历的个体家庭-多姓村落-文化族群-国家民族的衍化过程,呈现出京族的文化脉络及其社会变迁。坚韧乐观、英勇智慧的京族人,通过史歌叙事的代代传承,讲述着祖先历史、族群关系及文化传统。而京族迁徙史歌作为京族集体记忆的产物,在口传心诵中,丰盈了族群历史,感动着生命叙事,也指引着生活的实践方向。 ①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 ③京族字喃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编《京族社会历史铭刻文书文献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④《澫尾京族简史》《巫头史歌》《山心史歌》均出自陈增瑜主编《京族喃字史歌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下文涉及史歌内容,只标明篇名,不再另注。 ⑤《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⑥在宋代,三岛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明代,因推行里甲制度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明后,越南发生内乱,安南王将这些地区(现广西北仑河以北一直到广西的江平)归还中国;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清朝设防城县,今京族聚居的山心、巫头和澫尾三岛及附近地区,归防城县所辖,属钦州府。参见何思源编著《中国京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⑦转引自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⑧根据笔者2014年8月、2015年3月到京族地区田野调查时,与当地老人和文化精英的访谈所得结论。 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⑩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9页。 (11)何思源编著《中国京族》,第35页。 (12)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13)郑向春、田沐禾:《圣俗互渗:京族文化的行为文本制作》,《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206页。 (1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7页。 (16)笔者2015年3月到京族地区田野调查中对澫尾哈亭亭长苏春发的访谈所得。 (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224页。 (18)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著《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