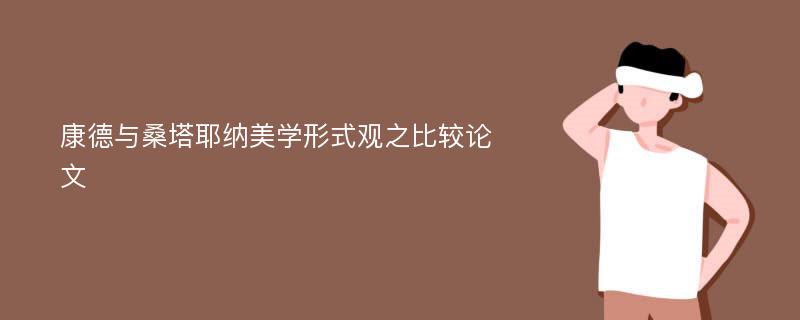
康德与桑塔耶纳美学形式观之比较
张林轩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摘 要: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康德美学中形式观的核心,自然主义美学代表人物桑塔耶纳反对康德从先验角度研究美的做法,而是立足于审美主体的自然经验,借助生理学与心理学去探讨美感与艺术。然而,桑塔耶纳一方面认为形式美服从于“快感的客观化”,即重内形式而轻外形式;另一方面将形式美定位为由单纯感官刺激通往摆脱客观物质的纯粹主观愉悦之间的过渡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康德美学的继承性。以形式观为突破点,可以看到自然主义美学在康德美学基础之上的破旧立新。
关键词: 形式;康德;桑塔耶纳;自然主义
“形式”是美学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尽管在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流派之中,对这一概念的侧重与定位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对立,但终究无法避之不谈。脱离了明确的形式观,我们对美与艺术的认识必然是失衡且不全面的,“‘形式’属于美和艺术总体观念层面上的基本概念”[1]。
远至古希腊时代,诸先哲就开启了西方美学的形式之旅,并自然地将形式定位在本体或本质的高度上。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自然存在物的本质定义为“数理形式”,而美就在于数理关系的“和谐”;柏拉图更进一步,将“理式”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是任何具体事物得以明确自身的超验的摹仿范型。因此,“美的事物”是美的“理式”的“分有”,艺术则是对“理式”摹仿的摹仿,即是对现实事物外形之摹仿。真正理想的美就是绝对“理式”注入具体外部形式之中,即真善美相统一。柏拉图丰富了美学中“形式”概念的内涵,它既有超验的绝对理式之维,又有经验的现实形状之意,而形式自上而下地传递,就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其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说”,首次明确地将“形式因”与“质料因”相对立,而“形式因”又包含着“动力因”与“目的因”,借此,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将本质、创造与价值等维度综合一体,这样的哲学认识也决定了亚氏诗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艺术形式之本质、创造与价值的思想体系。
总之,推进民生水利深入发展,重在深化认识,重在不断实践。应将民生理念贯穿于水利建设、管理、改革各个方面,体现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项目安排、业绩考核等各项工作中,把民生水利发展成效作为水利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标准,努力开创民生水利发展新局面。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为形式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但仍停留在形式的泛化阶段,既是超验的又是经验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形式”仍缺乏自身明确的定位。康德在综合、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以“先验形式”为立足点构建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先验形式”,就是认识主体头脑中先天存在的对物自体所提供的感性材料加以整合的基础,包括作为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与空间以及作为知性形式的四类十二大范畴。在康德先验哲学中,形式居于质料之上,所谓客观现象,所反映的并不是存在本身——“物自体”,而是主观认识形式的反映,因此,“它(感性直观)是一种完全特殊的主观条件,它是一切知觉的先天基础,并且其形式是本源的……物质的可能性是以某种形式直观(时间和空间)作为已被给予的前提的。”[2]而建基于先验哲学之上的康德美学思想,也体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特别是关于“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这一界定,为后来形式美学在多重道路上的开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同时也开启了“艺术自律观”在西方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新时代。
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自然主义美学流派,选择了与“艺术自律”相悖的立场,反对从形而上学体系出发去研究审美现象,反对形式与质料的二元论,突出强调审美经验与自然经验的同质,即将美还原为自然现象:“经验是自然主义美学的出发点,它使自己的注意、思考、推论都围绕着审美的事实和经验,严防先验的、唯理的、形而上方面的闯入。”[3]乔治·桑塔耶纳(又译桑塔耶那、桑塔亚纳等)是自然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广泛借用生理学与心理学方面相关成果,反对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观,以本能、美感、功用、理性等概念,试图打破传统艺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藩篱,建构起独特的自然主义美学体系。桑塔耶纳作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先声之一,其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美学的继承与改造是我们认识其美学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其中“形式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学界在这一方面的深入探讨尚属欠缺,值得我们进行梳理与比较研究,进而更加明确桑塔耶纳的自然主义美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
在鉴赏判断的第三契机中,康德进一步为这种形式做出了规定,即它如何与人的先天能力相适合。在这里,康德要解决一个这样的矛盾:如何做到没有明确目的的同时又体现出合目的性。一般的合目的性概念是指“一个概念从其客体来看的原因性就是合目的性。”[4]42-43而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并不是从因果关系中得来,那样它便势必与概念相联系而成为“意志”,而是与“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的内心状态相联系。就是说,当一个对象与我们的美感相连时,我们似乎要去在对象中找寻到一个概念去支撑我们的美感,但其实美感并不来源于找寻的结果(因为注定是无结果),而取决于找寻(意识)的本身,“并非意识到对象的合目的性就‘引起’快乐,而是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快乐。”[5]因此,尽管在关系契机中,康德强调了审美对象的形式在美感形成中的参与性,这是通过想象力的作用才得以完成的,但同时要实现与知性的和谐,客观的形式要服从于内心主观的诸能力,外形式要服从于内形式。并不是说具备了某种形式就必然引起美感,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刻板的美的规则:“一切刻板地合规则的东西(它接近于数学的合规则性)本身就有违反鉴赏力的成分……想象力可以自得地合目的地与之游戏的东西对于我们是永久长新的,人们对它的观看不会感到厌倦”[4]61,这就是“自由的合规律性”,这反映出康德美学中的浪漫主义维度,同时也预示着康德重自然美轻艺术美的倾向。
在《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论”部分中,康德从质、量、关系、模态四个契机入手对鉴赏判断进行分析。这四个契机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两者主要涉及美感,即“鉴赏判断的愉悦”;而后两者涉及的是美的对象性,也就是美感的先天依据。鉴赏判断四契机的内在逻辑是先有结论,进而为结论的可能性寻求先验理据:“如果这些给予的表象完全是合理的,但在一个判断中却只是与主体(即它的情感)相关的话,那么它们就此而言就总是感性的审美的。”[4]30因此,审美与主体相联系,它根源于人的主观能力。而美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是看似对鉴赏判断的愉悦产生具有意义,而美感本源上是自由生发的。
美的泛化以及对“审美无利害”的批判,意味着对纯粹美的否定,“事物的审美功能均不能与其实用和道德功能相分离。”[7]12这也决定了桑塔耶纳并不可能如康德一样从先验角度去为美寻找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应该立足经验去具体分析美的不同类型。桑塔耶纳从美的材料、形式美与表现美三个角度去构建自己的美学体系。其中,形式美处于一种中间地带,它是对感性材料的组织;同时又暂时悬置着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不需联想的作用就能引起的感性愉悦。桑塔耶纳首先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强调人的形式感的获得来源于外部的刺激,任何外部刺激作用于视网膜会引起肌肉感,一系列有所区别的肌肉感连成一线,进而形成网络,对客观的运动产生感觉,如此便形成了空间概念:“空间感就是这种感觉,其本质是对各种方向和各种可能运动的觉察,借此点与点的对应关系就会得到虽然模糊但却必然地定位。”[6]74空间感是最初级的形式样态,因为它依赖于外部的刺激,因此与美的材料关系密切。而要将形式美完全归于主体的内在感觉,需要“统觉形式”——典型——的作用,“当被感知的对象由于表现出的形式和意义的原因愈多依赖我们的过去经验和想象倾向,同时对外在对象结构的依赖愈少,那么后一种价值根源相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6]85而事物的审美价值的产生就在于典型,即内形式,与特殊多样的外形式相协调,也就是在对外形式的识别过程中内形式的唤醒。而主体对外形式的知觉又来源于生物本能反应,因此,形式美的形成过程同快感的客观化进程一样,是生理向心理过渡的过程。与康德美学中所蕴含的内形式与外形式协调的思想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桑塔耶纳坚守自然主义道路,将形式美完全放置于人的自然机能的演变而非先验能力之下,这也决定了其形式观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鉴赏判断的第一契机,明确了美感的独特性,即将其与快适和善相区别,提出了著名的“审美无利害”:“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4]35“无利害”的原因在于鉴赏判断的愉悦与对象的实存无关,而只涉及对象的形状与自身的情感相对照,这就是“审美静观”。其实,在这里康德便引出了审美活动中“形式”与“质料”的问题,康德的结论是鉴赏判断只与对象的形式有关。而之所以形式能与美感相联系,在于“在一个鉴赏判断中表象方式的主观普遍可传达性由于应当不以某个确定概念为前提而发生,所以它无非是在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中的内心状态”[4]41,这种“内心状态”是对象的形式得以参与到美感形成中的基底,就是说只有与此基底相适应的感官经验,才有资格进入到鉴赏判断的领域。正因为这一先天能力的存在,才为美感过滤掉了“魅力”与“激动”的因素,留存下对象的纯形式因素。也正因如此,鉴赏判断的愉悦才具有无概念的主观的普遍可传达性,因为这是取决于该内心能力在健全人之间的先天存在。
康德美学中形式观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对美所作的如下界定:“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4]56这可以看作是康德形式主义倾向的鲜明体现。理解康德美学的形式观,需要我们理清他如何得出这一界定,并且在这样的结论中,他的“形式”概念究竟指向何方。
基于此,康德区分了纯粹美(自由美)与依存美,区别在于前者不受概念影响,是单纯形式的“审美静观”,而后者则与概念相关。而真正美的理想在于依存美,这是因为它可以作为美与善结合的桥梁,是“部分智性化了的”。康德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美少之又少,审美活动更多地要掺杂进理性的成分。 而以美(判断力)来沟通真(知性)与善(理性),是第三批判的初衷,而纯粹美在一种类比意义上可以与理性形成对照,依存美则是直接沟通起二者。因此,美的理想并非纯粹的形式美,它必然要与道德相联系,可见,康德为美设定了两条路径,而后世“艺术自律”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对康德形式主义路径发展至极端的体现。
二、美感、艺术与形式
“如果没有猜错,两位就是子虚先生与乌有先生吧!纯阳子虚,翠玉白衣,烛花掌天下无对;皇家乌有,李弘之师,一身点穴功夫深不可测,我在长安都听说过的!”袁安说。
①管理无力,水资源统一调度形同虚设。虽然每年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主任与流域各地州师签订年度用水协议,给各地分配限额用水指标,但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难度很大,具体执行不严格。
香夼多金属硫化物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位于胶北隆起区藏格庄凹陷南缘与烟台凸起过渡地带。矿区地层主要为新元古代蓬莱群香夼组以及南庄组(图1),与成矿有关的地层是香夼组,为一套低级变质的碳酸岩建造,分为两个岩性段:一段为泥灰岩、灰岩互层夹薄层板岩,二段为厚层灰岩夹泥质灰岩。断裂构造主要有近EW走向的龙窝铺-翰家疃断裂、NEE走向的蒙家断裂、枣林河断裂。前者与盆缘断裂近于平行,控制了斑岩体的侵入与分布。岩浆岩主要为早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呈岩株、岩枝、岩脉状(图2),为中酸性钙碱性系列浅成—超浅成侵入体,富含Cu,Pb,Zn,Mo等微量元素,为成矿母岩。尚有少量辉绿岩脉等。
桑塔耶纳认为,形式美最理想的状态是“多样性的统一”,他以繁星为例,突出了在繁多之中体现出一致性对于提升形式美的重要性。其中,他这样总结道:“点点繁星没有让我们产生萨费克(Sapphic) 般的联想,反而让我们想到了康德,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事物来比喻所谓的绝对命令,也许因为他觉得这两种事物同样让人感到困惑和不可思议,有着同样强烈的真实性。这种终极情感就是肉体紧张的感觉。”[6]80很显然,桑塔耶纳在此处联想到的是康德那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前者从我在外在的感觉世界所占的位置开始,把我居于其中的联系拓展到世界之外的世界、星系组成的星系以至一望无垠,此外还拓展到它们的周期性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始和持续的无尽时间。”[8]在康德看来,浩瀚的星空带给人们时空的无限感,进而使人心生敬重,这种感觉就是崇高感。同样,桑塔耶纳也将繁星带给人的感受看作崇高。两者崇高观的比较同样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形式观的差异。
(2) 形式与理性 桑塔耶纳美学的形式观同样体现在艺术论的部分。艺术是一种人造的形式,它的功能在于赋予感性材料以形式,这也就决定了艺术必须是物质体现。这从存在论方面对艺术进行了根本限定,但艺术根本上是理性协调本能与功用的产物,而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既包含审美愉悦,也包含道德愉悦)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一方面,艺术根源于本能,是本能的理性化,理性引导生物性的本能走向目的化、功用化。功用既是自然的组织原则,也是艺术的组织原则,功用使对象的形式更容易通往人的快感客观化:“各种形式的出现源于机械的必然性,比如,洞穴和树房都是经过淘汰保存下来的,在不断的选择过程中,建筑结构必须适应的条件是人类的需要和快感。确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后,眼睛就开始逐渐习惯。因受统觉习惯的影响,实用路线改成唯美路线。”[6]121形式习惯——“统觉形式”的确定伴随着生理需要的满足,它进而走向了有意识地去满足审美愉快,艺术因此成了生存之虞解决之后的唯美行动,即将需求得到满足的人生状态进行物质化的体现。艺术之所以能够从本能走向功用进而引起愉悦,所依靠的是以物质手段构形,精神的物质化使精神得以不朽,艺术为精神提供了可传递性:“艺术为人类突破其身体限制追求真正的人类生活提供了工具,并且改造了外在物质世界,从而使其与人的内在价值协调起来,这样,艺术就成为各种价值得以不断产生的基础。”[7]10这样艺术就具有了道德功能,它蕴含着道德的因素:“艺术本应有恰当的(道德)目的,艺术的言说对象本应是完整健康的心灵。”[7]161这些道德因素需要通过艺术批评的方式加以彰显。
(1) 美是客观化的快感 桑塔耶纳的美学,建立在对美感的分析之上,而对美感的分析建立在美感与快感的区分之上。首先,桑塔耶纳反对以“功利性”作为区分美感与一般快感的标准,他指出“每一种真正的快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非功利的”[6]29,然而,他在此处对“功利”的界定是很含糊的,可以与占有欲或者自私感相等同,这显然与康德所说的与对象实存相联系的“利害性”并不是相等的。随后,桑塔耶纳进一步否定了审美快感具有普遍性,认为对其要求是“一种自然的错误”。他针对“共通感”指出:“显然,要求人们获得相同的感受取决于具有同样的能力,但是,绝不存在能力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两个人也绝对不可能对某些事物所持的价值观完全一致。”[6]31他强调每一个体审美快感的专一性与排他性,这显然继承了经验主义“趣味无可争辩”的理论传统,重新拉近了美与趣味之间的距离。
本能和功用作为艺术联结的两端,使艺术一方面植根于人们对享乐的无目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也使艺术与善密不可分,桑塔耶纳将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合同样称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在康德美学中,这一概念是为了突出鉴赏判断的无功利性,即重点在于“无目的”;而桑塔耶纳更侧重于“合目的”,尽管本能是艺术的基础,但在功用性推动下所形成的“统觉形式”——即日常感觉经验——才是艺术得以唤起美感愉悦的关键。“在艺术中,美是机械形式有意适应我们感官和想象已经养成的功能的结果”[6]123,所谓“形式的有意”,就是理性的引导功能。形式的构成来源于自然,既包括自然的物质材料,也包括自然的物质性本能,但理性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使这种形式更加适应人的典型经验,进一步说,也就是更加适应理性自身。然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康德所说的“合目的性”,是与先天知性能力相关,属于先验范畴;而桑塔耶纳的“合目的性”,则是指满足主体的自然本能与经验,属于经验范畴。因此,桑塔耶纳在此处对康德的形式观进行了经验化的改造。在美感论中,形式美作为材料美与表现美的中间地带,所带来的愉悦尽管是直接的,但也与人的典型经验的综合相关,具有激发联想的可能;而在艺术论部分,形式既是一种明确的物质存在方式,但是为精神服务,也是达成功用性的手段。实际上,在艺术论中,形式与材料和表现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在理性光辉的统摄之下,成为理性生活的一部分。
三、崇高之辩
然而,桑塔耶纳认为形式美仍然不是美的极致,因为随着形式美不断向内在感官贴近,也就是随着快感客观化的深入,人的主观能力以综合的方式投射到外物之上时,我们的思维不再满足于构造可见的形式,而试图将它与尚未感知到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联想能力,“客观对象通过联想具备的性质就是我们所谓的表现。”[6]145表现美之所以是美的极致,在于它通过联想连接起了现实的事物与暗示的事物,进而为事物增添更多的美感。 然而,并不是联想到的事物本身增添了愉悦,那样无非就是形式美的叠加;而是联想能力本身就使人愉快,我们甚至可以对“无形式”进行欣赏,这突出体现在桑塔耶纳“崇高”论的部分。
康德的自然美学部分包含着美与崇高两部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在于都体现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原则,是“表现能力或想象力在一个给予的直观上就被看作对理性的促进,而与知性或理性的概念能力协和一致”[4]63,因此也同样具有普遍可传达的性质。而区别在于,美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知性概念的表现,而崇高与理性相关。尽管美属于主观,但仍需要客观形式看似合目的性的存在,而崇高的对象是“无形式”,“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4]64,崇高是从审美静观状态转变为对理性理念的追求,它体现为想象力与知性的不和谐。崇高所带来的愉悦被康德定义为“对想象力的自身扩展的愉悦”[4]67。康德将崇高定义为“绝对的大”,它不同于数学估量中需要通过比较而得来的相对的大,“崇高是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小的那个东西”[4]67。无限的大意味着领会的无限自由,但想象力却很难将领会统摄到一个直观之中,这不是因为感官之于客观对象的渺小,而是因为崇高不该在自然物之中,而只能在我们的理念中去寻找,而理念是超越想象力的东西,想象力所联结的感官的尺度是不适合理念的。因此,崇高的问题不再是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运动,转而成为了想象力与理性关系的问题,想象力在对大小的审美估量中不适合通过理性来估量,进而引起了不愉快感,但这种不愉快感是由于想象力试图去做到理性所能做到事情,从而对想象力的极限做出了判断,这是理性理念得以发挥作用的契机,因此必然又是与理性相协调一致的。因此,在质的契机中,崇高被定义为“对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4]73,使命是要求想象力实现与作为绝对的、整体的、理念的适合性,即想象力超越感官。但是,想象力终究是立足于感官的,因此使命难以达成。正因为这种不适合与未完成,我们才会对使命产生敬重,敬重的实质是对人类自身理性之超越性的认识,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超越自然从而进入自由王国的可能,因此崇高最终是在理念的介入下才达成的。实现这种认识,需要想象力在并不如美的鉴赏中那样自由的状态下与自身抗衡的努力,摆脱知性概念的规导,带着对自身感性定位的否定走向理性理念。想象力与理性的联结产生的崇高感,是审美判断中“被自认为的必然性”[4]81,是崇高的模态,被康德称为判断力批判的主要契机。
在以非常简短的论述对学术史传统进行反思之后,桑塔耶纳提出了自己对于美的定义:“美是通过快感的客观化形成的,是客观化了的快感。”[6]39在他看来,情感同感官印象一样具有客观化的可能,然而这种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唯独体现于美感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快感很容易与知觉相分离,因为客观对象只有作用于人体器官,才能引起快感;但是当感觉活动本身是愉快的时候,感觉的各个要素就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投射到客观对象之上,“产生出该事物的形式与内容的概念”[6]36,由此快感能直接与对象相结合,成为对象的属性,这就是快感的客观化。我们可以将美感看作是快感的一种升华,快感从纯粹的生理机能过渡到与其他心理知觉相结合,共同投射到外物上,进而为外物提供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从这一定义中,桑塔耶纳明确地将美放置于主观之中,就是说美等同于美感。 从被动地接受外物的刺激到快感的主动投射,美感的生成突出了人的主观在愉悦的情感之下去统摄世界的能力。基于此,桑塔耶纳区别了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前者是积极的,而后者是消极的;审美可以在愉悦中达成道德规训的效果,因此:“美是一种终极的善,它会满足某种自然功能,满足我们心灵的基本需求或者能力。”[6]38与康德将美作为真通往善之桥梁的做法不同,桑塔耶纳的美学体现出了泛美感论的特点,美高于与快感相分离的知觉,同时也优于消极的善。
康德看重崇高感,是因为他对人的道德情感提出要求,进而超越了纯粹的形式直观。桑塔耶纳同样看重崇高,将它作为表现美的最佳效果。在他看来,美使人融入世界,因为美必须借助客观对象实现向心灵的内转,外形式是必须存在的;而崇高则使人凌驾于世界,也就是超越客观自然,因为摆脱客观形式而直面内心的,我们无须对对象有明晰的知觉一样可以唤起崇高感。因此,崇高使人达成超越自然的自我解放:“视野的意外扩大,对我们日常利害关系的全然超脱,自我与永恒、超人事物,即我们变幻无常的个性更抽象更不可夺取的事物的融合,所有这一切让我们从眼前的个人悲剧中摆脱出来,然后跃入一种意外的狂喜境界。”[6]182可以看出,桑塔耶纳一直强调美与功用的结合,但也在崇高部分为“审美无利害”保留了一丝余地,这可以明显看出他与康德对“利害”的不同规定。此外,桑塔耶纳对于崇高的限定更集中于康德的“力学的崇高”部分,尽管他也对无限有所说明,但他将星辰归于形式美,将其引起的快感限定为“肉体紧张”,可见在此处他的思想有所矛盾,并对康德进行了误读。然而,桑塔耶纳将形式美看作一个过渡阶段,而将美的理想看作是摆脱客观形式而完全走向内心,这一点是与康德的思路相近的。
绿色金融经过一定的发展,丰富了其金融业务类型和产品的种类。为了实现绿色金融的稳定发展,推动绿色金融全面发展,应该将参与绿色金融的主体多样化,丰富绿色金融的产品类型。在这过程中,甚至发展出了绿色股票和绿色保险。促进绿色金融向着多元化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了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基于我国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我国金融机构陆续对绿色金融业务和领域展开创新和探索,促进绿色金融的全面发展。其中金融行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对绿色金融产品的种类进行开发和研究,对我国的绿色产业投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试验地位于定西市农科院蔬菜展示园,试验地海拔1 920 m,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日照时数2 500 h,降雨量400 mm,年平均气温6.3℃,雨热同季,无霜期140 d。蔬菜展示园土壤类型为黄绵土,肥力中等。
四、结 语
桑塔耶纳在其略显驳杂的美学论述中,所构建出的形式观,与康德时有吻合之处。其根本在于两者都将客观形式看作主观的映照,这也就使得他们都没有满足于形式美,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连接的两头是自然王国(真)与自由王国(善)。如前所述,如果说康德之后的形式主义流派是极端化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所代表的纯粹美的话,桑塔耶纳则选择了继承康德超越纯形式的美学思想。
然而,两者的区别才是更为根本的。两人所立足的哲学基础的不同,导致桑塔耶纳选择无视康德美学的先验理据,而从本能的角度去论述美,这也决定了他的美学整体体现出泛自然论的色彩。其形式观中最突出的是“典型”的思想,“统觉形式”就是审美经验,它来源于本能,但受到功用的牵引,最终表现为客观形式与主观心灵的契合方式。桑塔耶纳将形式从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回归到自然经验。这种经验化走向也影响了杜威,他打破了形式与质料的二元论,而是强调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对形式进行判定:“形式是每个作为一个经验存在的经验的特征”[9],进而沿着桑塔耶纳功用性的道路发展出实用主义美学。
同时,桑塔耶纳美学明显受到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影响,具有科学主义倾向,这影响了新自然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门罗,他以科学的方法对形式进行了细致的解析。以桑塔耶纳、杜威、门罗为线索的美国自然主义美学传统,其对康德美学的继承与背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参考文献:
[1] 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4.
[3] 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20.
[4]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9.
[6] 桑塔耶纳.美感[M].杨向荣,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 桑塔亚纳.艺术中的理性[M].张旭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7.
[9] 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59.
Comparison between Kant and Santayana’s Outlook on the Form in Aesthetics
ZHANG Linxuan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Purposeless purposiveness” is the core of Kant’s outlook on the form in aesthetic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aturalistic aesthetics, Santayana, opposes Kant’s practice of studying beauty from a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 but returns to the natural experience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 using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to explore aesthetics and art. However, on the one hand, Santayana believes that the form of beauty obey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pleasure”, that is, emphasizing the inside form over outside form; on the other hand, formal beauty is positioned as a transitional phase between pure sensory stimuli and pure subjective pleasures that get rid of objective matters, which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of Kant’s aesthetics. Focusing on the outlook on the form, we can find the breakthrough and creation of naturalistic aesthetics based on Kant’s aesthetics.
Key words :form; Kant; Santayana; naturalism
收稿日期: 2018-09-23
作者简介: 张林轩(1995-),男,河北唐山人,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9)04-0035-06
(责任编辑 蒋涛涌)
标签:形式论文; 康德论文; 桑塔耶纳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