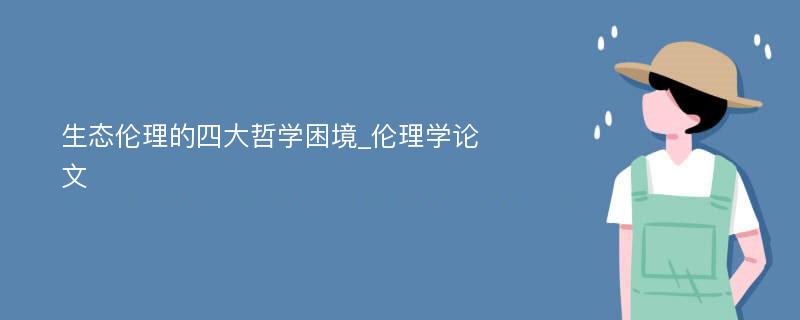
生态伦理学的四大哲学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3-0017-05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与地球绿色运动的蓬勃开展,生态伦理学已成为当今哲学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作为一门新近诞生的边缘性学科,生态伦理学一直面临着诸多的理论困境与逻辑困境。具体表现在:
一、荒野自然观的本体论困境
“荒野”一词是生态伦理学最为青睐、也是生态伦理学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几乎所有的“深层”生态学者都赞美荒野,并以荒野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复杂性“品格”为依据,呼吁人们保持荒野的“完整、稳定与美丽”。罗尔斯顿干脆把他的哲学取名为“走向荒野”的哲学。在他们看来,这个“荒野”不是被人类实践所“中介”过的自然,相反,却是“受人类干扰最小或未经开发的地域和生态系统”,[1] [p.107]即“真实的、原始的自然”。“荒野自然观”,正是生态伦理学的本体论之“根”。①
荒野的上述“品格”不过是自然的自在表现。生态伦理学对荒野的自在性的肯定,本身就是对荒野的自在性的否定。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发生学基础;按照认识发生与发展的逻辑,荒野的先在性、自组织性、系统性等,都不过是人脑通过实践对自然的反映和加工,是人的自为性的产物。如果关于某物的主观映象不是依靠把某物作为对象(认识的或改造的对象)而产生的,那它就是子虚乌有的胡说八道。正如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一文中所批判的那样:“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像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2] [p.161]
1.荒野自然只有成为生态伦理学家们的对象,即成为实践的客体,才能转化为他们的主观映象,才能形成关于它的先在性、自组织性等“观念的形式”。即使这个映象是错误的,但它仍然是以自然作为对象的实践结果。“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3] [p.52]因此,生态伦理学所青睐的“荒野”实质是虚假的荒野,是人化了的“荒野”。
2.生态伦理学关于荒野的“感性确定性”、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的丰富性,也是随着他们对自然的考察与研究而不断产生的。“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 [p.126]
3.生态伦理学本身也是实践的产物。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正是实践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分工造就了生态伦理学家们这样的精神生产者,进而使他们“生产”出生态伦理学这样的伟大思想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实践)分工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他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 [p.35-36]
系统性、自组织性等这些关于荒野的意识是——而且只能是——荒野与生态伦理学家们的“我”发生“关系”后的产物。因此,如果有人问:“你们是如何知道荒野的上述特征或品格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所认识到的吗?”那么,生态伦理学就势必会面临一个罗素式的悖论——陷入回答“是”与“否”的两难境地:如果答案是“是”,那么,他们的荒野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荒野,而是打上了人类实践印记的“人类学的自然”——除非他们和生态学家们都不是人;如果答案是“否”,那么,荒野的自在性品格就成了要么是与上帝一样不证自明的、时间上无限的或自本自因的“阿基米德点”,要么是他们主观的超验玄思或恣意妄为(即便如此,这个“他们”也必须是不属于人类的动物才行)。生态伦理学越凸显荒野的自在性,就越说明了“荒野”的非自在性。这便是荒野自然观的本体论困境。
二、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困境
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这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和灵魂。
主体性是价值范畴最本质的属性。为了证明自然物与人一样具有客观的内在的价值,生态伦理学极力张扬自然的自组织性或自我目的性,企图通过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来证明自然价值的客观性。例如,罗尔斯顿把自然的主体性规定为自然的自我目的性。在《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一文中,罗尔斯顿就不惜笔墨,对蝙蝠的能动性和植物的主动性特征做了生动的描绘:就蝙蝠而言,母蝙蝠能发出超声波、往来穿梭、捕捉小虫带回喂食孩子;就建模生物体的植物而言,植物能够自我繁殖、修复创伤、制造丹宁酸以免受草食动物侵害、制造花蜜以影响传粉昆虫、释放植化相克素以抑制入侵者,等等。这些科学事实都说明了非人类也是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的主体,都具有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能力。[6] [p.42-46]
自然的“主体性”也好,自然的“目的性”也罢,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生态伦理学家们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的外化与确证而已:
1.从认识论维度看,在言论上,他们列举大量的研究资料与科学论据,竭力强调自然的价值能力,强调自然本身就是价值主体,但是,在行动上,他们却把这个“主体”当作他们研究的客体和审视的对象,因为,只有把蝙蝠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才知道蝙蝠的“穿棱”与“捕捉”,也只有把植物作为研究客体,他们才知道植物的“繁殖”与“修复”。
2.从价值论维度看,在言论上,他们强调自然本身就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但在行动上,他们却是把自然当作工具价值加以对待的,即,模仿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然物不过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研究资料)服从于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研究兴趣的需要、完成自己作为学者的本职工作的需要、证明他们对自然奥秘的领悟和对自然的伦理关切的需要、确证他们本质力量的需要。[7] [p.393]
3.从辩证法维度看,肯定“自然即主体”,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然即主体”的否定性理解,即作为“主体”的自然只不过是生态伦理学家们肯定的客体、对象或宾词,也就是说,自然根本不具有主体性。如果自然真的就是主体,那么,这个“主体”根本就不需要生态伦理学家们“肯定”,它自己就会显示自身的能动性,主动向人类展示自身的内在价值,要求得到作为“道德家庭”成员的平等地位,就像黑人或妇女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而主动上街集会游行一样。
于是,生态伦理学不愿看到的一个逻辑困境产生了:他们越阐述自然的主体性与目的性,却反而越说明了自然不具备主体性与目的性。如果有人问:“自然的主体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你们的研究而发现的吗?”那么,生态伦理学同样会陷入回答“是”与“否”的两难窘境:如果答案是“是”,即承认他们是把自然“主体”当作客体而研究和“加工”的,就等于自己揭露自己的口是心非或言行不一;如果答案是“否”,那么,所谓的自然价值能力论就只能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话语,就只能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这便是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论困境。
三、“敬畏生命”的方法论困境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问题上,生态伦理学提倡“顺从命运”、“敬畏生命”。它认为,既然荒野自然是先在的、有机的、自组织的、与人同质同价的,而且这个结论又是具有科学事实严密支撑的,因此,自在的自然就具有了客观性、神圣性或至上性的品格,人类只能尊重它、顺从它、呵护它。
为了保持荒野自然的“真实性”和“原始性”,生态伦理学反对人对自然的干预,包括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干预,反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学转向,认为这些人化过的自然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是心与物、物与我的二元论的产物,都无法比拟自然的原始性、复杂性与真实性。他们还反对《荒野与美国思想》的作者罗德里克·纳什的“输出荒野”(发达国家人们在资源不发达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反对把遭遇人类染指过的自然作为伦理家族中的平等成员。尽管生态伦理学推崇“任何生命体都具有资格成为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但是,这个“生命”在他们看来只是没有打上人类痕迹的生命,是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并不包括如家禽、牲畜等人类所饲养的动物。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相互依存的,在生物之间,每个物种(及其个体)的生存都要以其他生物的死亡为中介。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也无法避免这一规律。生态伦理学无视自然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而提出所谓的“敬畏生命”,其结果必然残害人的生命,使人类成为珍稀动物。理由很简单:“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8] [p.326]由于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因此,为了生存的需要,人必须和动植物一样,以其他生物的“死亡”换取自身的存在。
为了摆脱“生态极权主义”或“反人道主义”的骂名,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阿伦·奈斯将人类的需要划分为“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两类,[9] 认为人类追求“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放弃满足“非基本的需要”(边缘需要或多余的需要)才是自然的。但是,如果人们再进一步追问:将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需要又属于哪类需要呢?那么,深层生态学就势必会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如果答案是“基本需要”,那就犯了同义反复的循环解释错误,而且与事实不符,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类的基本需要只能是解决衣、食、住、行等形而下问题的劳动,而不是诸如划分“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需要、保证代际公平的需要、研究生态伦理学的需要等等形而上的问题;如果答案是“非基本需要”,那就等于自我否定、“自打耳光”。
不仅如此,对于“究竟是人的利益至上还是非人类的利益至上?”的问题,生态伦理学也是很难回答的:如果以牺牲人类的利益而保护非人类的利益,就会落得一个反人类的罪名;反之,如果以牺牲非人类的利益来保护人类的利益,就等于以非人类中心主义话语表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这又是生态伦理学家们不愿承认的。
生态伦理学呼吁人类尊重自然,却否定了人类自身的自然;实践其所谓的“敬畏生命”,必然会扼杀人的生命。正可谓“残酷的慈悲或慈悲的残酷”!因此,当被问及“人的生命是否是自然的生命?”或者“人的生命作为自然的生命是否应该敬畏?”时,生态伦理学又将面临回答“是”与“否”的两难抉择。这便是生态伦理学的方法论困境。
四、“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困境
在认识论上,生态伦理学视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为生态危机的主要罪魁,提倡以整体主义的有机论思维方式取而代之。
有机论的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是认识论中对立的两极。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认为事物间的有机性决定了人对世界的认识只能从整体性、综合型的维度加以“直觉”或“感悟”,而不能把它肢解开来单独观察或实验。后者把世界看成是孤立事物的机械组合,看成是可以用数学或物理方法加以分析和还原的、无生命的物质;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的还原为低级的是它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
有机论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对立决定了“科学的”就不是“有机的”,“有机的”就不是“科学的”。
生态伦理学首先是一门有机论的科学。自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是生态伦理学得以成立“充足理由律”。例如,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会长余谋昌先生就是根据有机论的“真谛”而建构他的《生态哲学》的;泰勒是根据自然界“内在关联的客体和事件”来诉求他的“生物平等主义”的;史怀泽是根据人与自然的“休戚与共”而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主张的;利奥波德是根据“大地共同体”的“综合性”来论证其“大地伦理学”的;奈斯是根据生物圈的“无缝之网”而包裹其“深层生态学”的;等等。生态伦理学的整体主义认识论决定了它必然反对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反对科学。例如,在《深层生态学研究》中,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雷毅就明确反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就明确反对科学,鼓吹科学的“不可知论”:“今天,普通的公民都认为,科学知道是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但科学家始终确信他不知道。科学家懂得,生物系统是如此复杂,以致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了解它的活动情况。”[10] [p.195]
生态伦理学又是一门科学的有机论。为了赋予自身以“科学”的“刚性”与“硬度”,生态伦理学不得不借助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最新研究发现,借助于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其论证手法恰恰是机械论式的、还原论式的。例如,为了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罗尔斯顿用宇宙学家卡尔和瑞恩的解释说明宇宙的形成只不过是“物理常量的偶然配合”;用天文学家洛威尔的惊奇发现说明人的存在与宇宙的初始状态密不可分;用物理学家科温的“从混沌到意识”说明人类的产生得益于自然的复杂与演变;用理论物理学家戴维斯的研究证明自然“搭配得如此天衣无缝”;用热力学家艾根关于物质的自组织与生物大分子的进化论说明生命进化的必然性和地球相对于人类的先在性。不仅如此,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拓展主义也是通过科学主义的主客二分法加以观察和完成的。例如,为证明生态有机性的至上性,罗尔斯顿直接参与了生态系统的科学考察。他以奥克弗诺基沼泽的任何两株枫树与布赖斯峡谷的任何两条郊狼之间的差异对比,说明“生态共同体造就生命有机体的独特性和与其他事物的差别性”;以英国怀汉姆林区栖息着的5000多种动物为例,说明生态共同体通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增加生物多样性;以生态科学的生物进化理论说明“生态系统的一种奇怪的、雍容大度的‘优先性’或‘倾向性’”;等等。[11] [p.253]
可见,在认识论上,生态伦理学一方面强调自然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呼吁人们以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看待并处理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具有强烈的有机论色彩;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自身理论内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它又不得不借助于生态科学的最新发现,借助于机械论的、还原论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因而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色彩。因此,当被问及“你们的生态伦理学究竟是科学的有机论还是有机论的科学呢?”时,生态伦理学将再一次陷入二律背反式的两难选择。这便是生态伦理学的认识论困境。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拙作“荒野自然观: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症结”(《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生态中心主义的隐性逻辑及其批判”(《科学技术哲学》2005年第8期)以及“荒野自然观:人学空场的费尔巴哈自然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