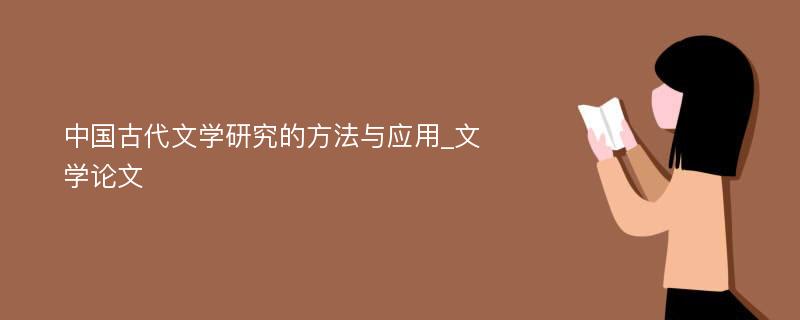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及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分水岭,其意义在于树起了古典时代终结的标尺。在西方 人文理论传入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感悟性的评点(如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或圈点为 主,表现为重体验轻知识的思想特征;进入20世纪后,受西方人文理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文 学 研究摈弃个人体验,关怀“纯理论的知识”(宗白华《形而上——中西哲学之比较》,《宗 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1页)成为一时的风尚,乃至于崇尚理 念重逻辑分析成为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
较早地将西方人文理论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是王国维。在关注西方人文理论的过程中 ,王国维先后写下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 说后》等文章,其思想线路表现出对西方人文理论的热切关注。这里,我们先且不论王国维 对叔本华与尼采作出的分析是否都那么精当,但他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除了 需要重体验外,还应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展开思辨。所以,当王国维运用西方人文理论写下《 人间词话》这部研究古代诗词的著作时,它产生的轰动效应就是向世人证明方法论对于研究 中 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作用。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王国维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依旧为人们所津津 乐道,它的意义就在于,将西方人文理论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给囿于传统的人们打开了新 的天地,使一向重体验轻知识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了新的逻辑起点。
王国维用西方人文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并 不是王国维。较早地运用西方人文理论研治中国古代文学是从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始的。十分 有趣的是,古代中国虽然有丰富的史学著作,乃至形成了后世为前代修史的优良传统,但在 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写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文学史,这种情况的存在恰好 说明了重体验的传统研究方法因轻知识而无法使文学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总揽全局。1923年 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经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 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国人开始了撰 写文学史的历程。今天看来,它所显示的意义不仅仅是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学史,更重要 的是,通过撰写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天地得到了新的拓展。
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刊行于世的中国文学史有日本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富山房发 行,1897年版)、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早稻田大学讲义,1898年版)、英国翟理 斯(又译翟理士)的《中国文学史》(伦敦,1901年版)、德国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莱比 锡,1902年版)。从时间上看,古城贞吉的出版最早,然而,给中国文学史以深刻影响的是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早在1903年,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就由上海 中西书局出版了。国人林传甲撰写其《中国文学史》(京师大学堂讲义,1904年编讫印行)时 说:“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卷首题 记)笹川种郎给林传甲的影响是将文学史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但其主要功绩还在于打 破了研治中国文学的传统方式。从这时起,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史,在西方人文理论的 冲击下,“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也因此发生了动摇。
真正给研治中国文学史带来质的飞跃的是黄人先生。黄人早年任教于东吴大学,自东吴 大学于1905年开设大学课程以后,黄人开始了边写边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历程。据今 人研究,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印行,出版年月未标)完成于1909年前后(参见 高树海《中国文学史初创期的“南黄北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与林 传甲 的相比,这部《中国文学史》主要表现在更为自觉地运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构中国文 学。如黄人认为:“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 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 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黄人《中国文学史 》第二编《略论》)黄人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不但纠正了封建社会时期统治 者将戏曲、小说视为“淫秽之词”的偏颇,而且还以进化论为武器探讨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轨 迹。自黄人以后,中国文学史的研治(包括专门文学史的研治)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然而 就其方法论而言,则是在西方人文理论的引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研究方法的 更新强化了国人“文学史”的意识,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又使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进 入了新的阶段。
总揽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取得的突破,就不能不特别地提一提以顾颉刚为首 的古史辨派。在研究先秦典籍的过程中,顾颉刚发现在春秋时的典籍没有黄帝的记载,只谈 论尧舜之事,又发现战国后期在记录历史时往往追溯到尧舜以前的黄帝。根据这一情况,他 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后,疑古遂成为最流行的风尚。 今天看来,当年被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视为伪书的典籍经过出土文物的证实,其中大部 分是可靠的。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古史辨派在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之处,然而他 们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反拨传统考据学“信古”的作风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古史辨派在方法 论上的更新给当时的考据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人们在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希望用一种 更为科学的方法来澄清传统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足。从表面上看,顾颉刚的疑古主张主要有两 个来源,一是宋代郑樵、晚清姚际恒和崔述等人的疑古思想;二是胡适、钱玄同等人的疑古 主张。甚至顾颉刚曾这样写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 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我是 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同上,第12页)从深层看,顾颉刚的疑古主张虽然与传统的考据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的思想武器却是西方的人文理论。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张发生在新 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在倡导科学和民主的过程中,胡适、钱玄同等人曾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 的人文理论,顾颉刚是胡适和钱玄同等人的弟子,在接受胡适、钱玄同思想主张的同时,接 受西方的人文理论则是必然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顾颉刚的疑古主张与西方人文理 论 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顾颉刚的疑古主张是在胡适“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思想原则 下进行价值评判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作为胡适接受西方人文理论之后提出的方法论 ,不但对顾颉刚的疑古主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还成为了古史辨派重逻辑推理的思想支 柱。
检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如果说将西方人文理论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始于中 国文学史的研究的话,那么,真正把西方人文理论带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则是因新文化 运动而得到充分的强化。发生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 起了最猛烈的冲击,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西方的人文理论为知识界普遍接受。在这样的文 化 势态下,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不仅成为了可能,而且西方人文理论的终极关怀还给人 们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这一内容反映到文学上则是运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研究中国文 学。在这中间,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新青年》杂志起到了不容替代的作用。《新青年 》共十二卷,在这十二卷中,每一卷第一号都有对西方人文理论或思想家的介绍。在介绍西 方人文理论的过程中,人们尝试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学,其 尝试性的探索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更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科学和民主大旗的引导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始了反拨原有的研究秩序和方法的历程 ,具体地讲,这一历程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表现出由重感悟向崇尚理性的方向发展。这 一运动的轨迹,正如宗白华先生描述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时指出的那样:“但如更能超越一 切经验实用之限制,纯抱为真理而求真理之精神,为满足理智好奇之欲,而穷探及于宇宙万 象之普遍法则及一切事物所具变化生灭变化之原因或理由,获到一种纯理论之知识,即为再 高级之科学真知。此为真实智慧之所在。”(宗白华《形而上——中西哲学之比较》,《宗 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页)这一精辟的论述虽说是为勾勒哲学 发展的前景而提出的,用它来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亦同样实用。20世纪的前半叶 涌入中国的西方人文理论是多元的,各种理论的彼消此长,使国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面 临着方法论上的多种选择。今天看来,这些选择多少带有一些尝试的性质,但正是因为有了 这种种尝试,才使西方的人文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出现这样的 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在旧的文化体系倒塌和新的文化体系建构的年代,人们有权力从不同的 方面作出多种多样的选择。
面对多种选择,自20世纪2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又称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开始 在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和运用。一般认为,马克思的 文艺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实,这是不对的。从历史的角度 看,马克思的文艺理论由文学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体系或言说方式, 发端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已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当陈独秀、李 大钊等共产党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文 艺理论的介绍已经为人们认识社会学的批评方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稍后,鲁迅等人对马克 思文艺理论的宣传和运用,一是对普及马克思文艺理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为人们 运用社会学的批评方式从事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之争中,鲁迅曾 这样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 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 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三闲集·序 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这“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是指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鲁迅从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发端于革命文学之争中,这一争论在 推动马克思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同时,对普及社会学的批评方式亦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研究理念上的创新像新文学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深入传播以及30年代左翼作家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自觉宣传和运用,很快,马克思的文学 批评方法就在中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认同。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从社会存在的角 度 解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这一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文艺理 论体系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所以马克思文艺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能得到大多数人的 认同是必然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种强调教化的文学观与社会学的批评方式有 着相通之处,这两者间的契合,使社会学的批评方式由边缘走向话语的中心主要是因为这种 批评方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换言之,社会学的批评方式成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 代文学研究的主流乃是历史的因然。
全面肯定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十七年”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占绝对 统治地位的年代,运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确实使人们发现了许多原先所忽 略的东西,如在分析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解构中国古代文学内在发生的机制方面,分析 文学作品、作家、流派等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方面,用发展的眼光关注文学家在历史中的地 位方面,用辩证的观点来评判文学作品或文学家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于人们 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偏面地将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定位在“人民性”和“阶级性”上,将其作 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结果是导致了用社会批评取代审美评判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存在不 但使研究者在思考文学与知识、主体性和社会规范等内容时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而且 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容易简单地得出“是”或“不是”的结论。
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文学审美价值的淡化或取消曾一度使文学研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 为用单一的方法去研究问题很容易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从另一个层面看,社会学的批评 方 法之所以在新中国一枝独秀,还与权力强化话语——言说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的条 件下,权力可以支配话语和选择话语。如果没有权力的干预,文学研究的方法本应处于多元 的势态,在接受西方话语的基础上如能注意到传统方法的优长,或许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会 看到更多的问题和解决更多的问题。但在这一时期,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乃至在 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出现了用社会学方法取代一切的简单化倾向。这一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 仅是造成了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树立起社会学的批评方式的绝对权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 种思维定势束缚了人文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以及创造能力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新面向世界的时候,人们突然地发现批评方法即言 说形式的单一已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缺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人们开始 对社会学的批评模式提出质疑,与此同时,建立多元化批评模式的主张又再度提出。在新一 轮西方人文思潮再度涌入中国的时候,通过反思“十七年”所走过的弯路,人们终于认识到 研究方法的单一所带来的缺陷。这一时期,视野的空前开阔,不但使先前传入中国的西方人 文理论如精神分析法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而且一些新鲜人文理论也得到了介绍和应 用。如从80年代起,叶舒宪率先向国人介绍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在介绍神话原型批评理论 (参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同时,他又以神话 原型批评为研究方法,先后写下了《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诗 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著作。这些做法不但使神话原型批评成为了当 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而且还对人们以更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 、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比较文学批评理论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回顾20世纪话语体系建立的过程,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已在不经 意中建立起了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式。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首先,国人所提 倡的科学和民主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为构成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人文 知识分子用西方的言说方式来批判封建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其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 需要清算和否定已有的研究秩序,那么,该如何否定呢?其批判的武器只能是西方现成的人 文理论,即用西化的言说方式进行人文学科的研究是人文工作者的必然选择;三是西方人文 理论从话语的边缘走向中心贯串于20世纪国人对人文学科研究的始终,新中国成立以后,虽 然对西方人文理论构成了批判的势态,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西方三大批评理论中的 一种,作为认同西方人文理论的中介,人们选择西方的言说方式是因为有社会学的批评方式 作为话语的言说基础。
言说方式的西化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格局,为批判封建文 化崇尚科学立下了不可埋没的功劳;另一方面言说方式的西化,在树立起西方话语霸权地位 的 同时,还使传统的言说方式出现了危机。事实上,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的中华,其创造的 言说方式是有着博大精深的内容的,纵然这种言说方式有着自身的缺陷,但在运用的过程中 依旧有着其它理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人们对西方人文理论的关怀和尝试,对打破单一的文 学研究模式虽然有重要的作用,但它对传统的否定则忽略了传统言说方式存在的合理价值, 同时也掩盖了西方人文理论的自身缺陷。那么,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该如何面 对这一负面的空间呢?这无疑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以为,在西化与传统化两者之间,我们首先应具有处惊不变的胆量和勇气,一方面我 们要承认西方人文理论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自身理论的长处;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中 还有包容一切的勇气,做到既不厚此也不薄彼,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拿出眼光,敞开胸怀。 未来的世界是多元的,未来的研究方法也将是多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虽有重体验轻知识的一 面,但它对个体经验的强调却有着西方人文理论无法达到的境地;西方的人文理论看重理论 方法在分析问题中的运用,但逻辑推理导致的量化分析未必就能将具有形象思维特征的文学 研究得鞭辟入里。
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和网络化的时代,如果说以前我们进行的研究还可以在 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话,那么从现在起,我们的研究则必须面向整个世界。在未来的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除了应该从理论(这里所说的理论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传统的)的层面来 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外,还应加强文本的训诂、校勘、考订等基础性的研究(包括加强 对作家生平事迹、文学活动、交游的考订,加强文献整理、年谱编撰以及文学编年等)。由 于以上我们在讲方法论时,观照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的,这里有必要专门来谈一谈传统考据学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认为,在走向未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考据学依旧是研究的基础。在考据学的研 究中,文本考证是主要方面。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文本。由于古代书写工具滞后,起初,相当 多的文本是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得到传播的,后来纸张以及印刷术等虽然发明了,但口头传承 形式的存在则造成了文本的相异,再加上印刷术的滞后和错讹,乃至文本在一定的程度上并 不能完整地反映最初文本的面目。如汉代传《诗》者有四家,四家均以《诗》的传人自居, 由于传承的系统不同,文本的相异带来读解的相异则是必然的。这种情况表明,在读解的过 程中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哪一种文本更接近原本?过去,人们对文本进行大量的考辨取得了 突出的成就,但有些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辨伪工作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将可靠的 文献视为伪书的情况。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读解文本的时候首先要思考什么时间的版本最 接近文本的原来面貌。一般地讲,唯远为源,最早的文本当然最为接近文本的原本面貌,但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地简单,因为许多文本根本就不是产生于那一时代的文本。这些都有力地 说明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存在着澄清文本真伪的问题,否则我们的研究 就无法深入地开展。
未来的研究既是多元的,同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能没有理论指导,但 从另一个层面看,理论又是滞后的。这似乎是一对矛盾,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矛盾, 我们的研究才需要不断地开拓进取。在过去20年的研究中,人们为了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导 向深入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尚永亮的贬谪文学研究、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研究, 李浩的关中世族与文学研究,张强的帝王文化与西汉文学研究(以上所讲数种均为博士论文)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既对西方的人文理论和传统的研究方式进行了吸收,同时又从新的视 角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解构,从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在知识全球化 和文学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除了应加 强基础性的研究外,还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更新,必须拓展研究的空间,需要拿出打破现有的 研究秩序的勇气进行新的探索,以适应文化创新的要求,改变原有的研究秩序,使中国古代 文学的研究真正地走向未来。
如果从“诗言志”(《尚书·尧典》)算起的话,古代文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三千个年头 ,在这中间,文学研究不但没有停下它的脚步,相反,一个古老的问题,研究者们还是在不 断地发现新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文学的阐释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 往往因为研究方法的变化而造成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主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根据研 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方法论上作出相应的选择,寻找出一条有利于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向 深入的道路。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顾颉刚论文; 人文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王国维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