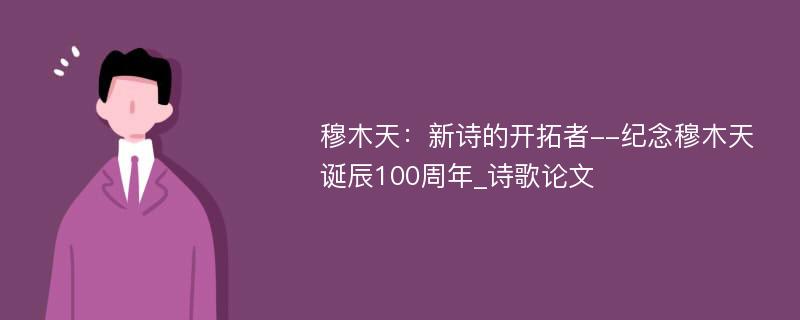
穆木天:新诗先锋性的探索者——纪念穆木天诞辰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索者论文,新诗论文,先锋论文,诞辰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穆木天之前,并不是没有人介绍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当时留法、留日或其他参与启蒙活 动的一些青年文人和知识分子田汉、周无、李璜、刘延陵等人,曾在《少年中国》、《诗》 等杂志上,系统介绍了“恶魔诗人”波特莱尔以及魏尔伦、马拉美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发 展,把它们看成是法国文学进步的一个“新的趋势”。(注:如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3卷第4-5期,1921年2月),周无
《法兰西近世文学之趋势》,(《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李璜《法兰西诗之
格律及其解放》(《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刘延陵《法国之象征主义与自由
诗》(《诗》第1卷第4号,1922年4月15日)等。)周作人曾先后在《新青年》、《语 丝》杂志上译介了被称为“象征派底一个巨子”(注:刘延陵:《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诗》第1卷第4号,1922年4月15日。)果尔蒙《西蒙尼》组诗中的一部分诗篇。 (注: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周作人的《杂译诗二十三首》中,翻译了果
尔蒙《西蒙尼》组诗中的《死叶》;1924年12月15日《语丝》第5期,发表周作人的《田园
》,译介了果尔蒙《西蒙尼》中的《毛发》、《冬青》、《雪》、《死叶》、《河》、《果 树园》等6首诗。)在穆木天介绍法国象征主义的著名论文《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在《创造月刊》发表 的稍后,在清华的朱自清、李健吾二人,还合译了布拉德雷的重要论文,全面介绍法国先锋 性的“纯诗”运动。(注:朱自清、李健吾译:《为诗而诗》,《一般》第3卷第3号,1927年11月5日。)李金发也在早一些时候以自己的实践,第一个将法国象征主义传播到 新诗中来。但是,真正自己由专攻法国文学,对于法国象征派诗人和这一探索性诗潮的发展 作了深入研究,并以自身的诗人素质和审美选择而走近象征主义,自觉地进行新诗理论先锋 性探索的,应当是穆木天。在现代主义潮流已经成为诗歌主要潮流的今天,在纪念穆木天百 年诞辰的时候,回顾他的这种先锋性的艺术探索,对于缅怀诗人的创作道路和思考新诗的发 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924年以前,穆木天虽偶有诗作发表,也还多带唯美的浪漫主义气息。如发表在1922年12 月《创造》季刊上受王尔德影响所写的散文诗《复活日》,即以一个虚幻的故事,传达了以 美与人性战胜宗教精神禁锢的叛逆思想。发表于1923年10月《创造日》上的《心欲》两首诗 ,以化作小孩子、小鸟的心愿,歌唱了充满浪漫情怀的美好人生的追求。他的由王尔德而 转向象征主义的先锋性探索,是1925到1926年间的事。
1924年的暑假里,在东京大学读法国文学的穆木天,带着东京大地震的毁灭感和自我人生 的苦闷与悲哀,到了伊豆半岛的热海,他的艺术接受和艺术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1926年初发表的《谭诗》一文里,他说,1924年6月以前,“我完全住在散文的世界里。 因为我非常爱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思想,而且因我似有点苦闷,在前年的夏期休假中 , 纤丽优美的伊东海岸上,我胡乱的读了那位‘象牙塔’中的预言者的诗集。至今想起来读《 投在海上的浮瓶》(La Bouteille a' lamer),在蜘蛛湖畔还望野犬徘徊在河边幽径上, 甚为有味。但那时究竟是我的ABC。实在我的诗的改宗,自去年二月算一个起头,以前,虽 作 了三二,究竟是尝试中之尝试。”他又说,“去年四月伯奇自京都来东京,我们谈了些诗的 杂话。伯奇于三月底在京都帝大毕业,我曾寄他一本毛利雅斯(Jean Moreas 1850-1910) 的《绝句集》(Les Stances)。……他来的那时,我正嗜谈沙曼(Albert Samain 1859-1900) 。”(注: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 月15日。)过了十年后,他回顾这一段接近和沉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生活,说得更具体了:“伊 东之两个多月,使我感到没落,感到深的悲哀,使我感受了哀歌的素材。同时,在伊东,我 读了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的诗集。那两个月,好象是决定了我的作诗人的运命似的 。”从伊东归来后,在东京大地震“那种凌乱的废墟”中,开始“攻岸着我的诗歌”。“我 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Remy de Gourmont),莎曼(Samain),鲁丹巴哈(Rodenbach), 万·列尔贝尔克(Charles Van Lerberghe),魏尔林(PaulVerlaine),莫里亚斯(More'as), 梅特林(M.Maeterlineck),魏尔哈林(Verhaeren),路易(Perre Lonils),波多莱尔(Baudel aire)诸家的诗作。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当时最不喜欢布尔乔亚的 革 命诗人雨果(Hugo)的诗歌的。特别地令我喜欢的则是莎曼和鲁丹巴哈了。从这种也可以看出 来我那种颓废的情绪罢。我寻找着我的表现的形式。”(注: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现代》第4卷第4期,1
934年2月1日。)这些叙述清楚地说明,从1924年暑 假起到1925年底的穆木天,在自己的阅读中,几乎涉猎了法国自早期象征派到后期象征派的 主要代表诗人,并由于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在自我“表现的形式”的热切“寻找”中,确定 了自己疏离雨果而走向波特莱尔,疏离浪漫主义而走向象征主义的艺术选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穆木天列举的当时自己“耽读”的一串诗人名单里,就有法国诗人 莎曼在。而对莎曼的关注和研究,恰好是他进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论起点。穆木天的《 谭诗》里,在比较杜甫与李白,雨果与维尼,阐述诗的世界与散文世界差异的时候,使用了 “诗的意识良心”这样的概念。如果借用他的这个说法,我们重读穆木天75年前对于诗人莎 曼研究,更可以清楚地发现,他阅读法国诗歌时候这种艺术“寻找”和选择,表现了一个现 代诗人难得的先锋性探索的“诗的意识良心”的自觉。
穆木天1922年初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文科。他完成于1925年12月并于1926年初获得通过的 毕业论文《阿尔贝·莎曼的诗歌》,经过长久的遗忘与淹没,近70年后在日本东京大学被发 现,并由吴岳添先生译成漂亮的中文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注:该论文《阿尔贝·萨曼的诗歌》,一直尘封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大楼地下室档案内的 杂乱文书中,经过近三分之一世纪,一直无人知晓。前些年才由东京大学丸山升教授等先生 发现,特在日本撰文介绍,并将此论文及介绍文章寄赠给穆木天的家属。丸山升先生还盛情 地将穆木天的论文复印件和他的介绍文章寄赠我一份,留做纪念。该论文由法国文学研究专 家
吴岳添先生翻译并加注释,首次全文发表于《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成为中
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穆木天研究的一份宝贵的文献。现收入《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陈惇、刘象愚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这份极为宝贵的资料,为我 们进一步研究早期穆木天的现代诗歌意识和新诗理论先锋性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论文《阿尔贝·萨曼的诗歌》,原稿于1925年用法文写就。全文分五个部分:一、概论, 二、象征主义诗歌,三、浪漫主义诗歌,四,帕尔纳斯派诗歌,五、结束语。全文约23000 余字。后附“参考书目”22种。该文仅涉猎的希腊神话,法国及其他国家的画家、雕塑家、 作家、诗人、哲学家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与其中的主人公,引用的他们(包括萨曼在内)的诗 作,由中文译者一一注释出来的,就有近100种(处)之多。有些法国诗人的名字,至今仍为 国内学人所很少涉猎。论文所显示的学术态度的严肃认真,涉猎知识面的广博多样,与 研究见解的肯綮精到,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就是今天的许多大学生毕业论文,也是无 法与之比拟的。穆木天被认为是中国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研究的理论先驱与20世纪象征诗学 理论的奠基者,由此而更加当之无愧了。
这篇洋溢着25岁的穆木天的诗学理论思想与才华,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精彩的关于莎曼诗 歌的研究的成果,分别细致地考察了这位转折时期中——19世纪抒情诗各种影响的“十字路 口”的诗人所受象征派、浪漫派、巴那斯派诗歌的影响,论述了他的创作与他的前辈诗人们 之间的艺术联系,他如何集三个流派的艺术特色于一身,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独特个性色彩的 象征主义诗人。在论文的《概论》中,穆木天提出了诗人的现代性追求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关 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论文一开头就开宗明义的说: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传统,一位诗人的特色在于其作品 的复杂性,即他把各种不同的潮流结合起来,并把他们与自己的个性融为一体。无论他是传 统主义者还是革新者,他都只是人类运动的长河,即反映人类永恒形象的长河的延续。在与 过去相结合的同时,他提炼着自己的特性,使自己持续的梦幻理想化,从而创造着一个新的 世 界:由此便形成了魔环。无论已经去世还是活着,一位真正的诗人都是这样造就的。因而在 研究他的时候,应该追溯到一切遥远的源头,寻找他诗作的不同起源,从而确定他在总的演 变中的位置。(注:穆木天:《阿尔贝·萨曼的诗歌》,见《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第1页。本文凡引自该论 文者,以下均不再注明出处。)
这个几乎与T.S.艾略特20年代初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那篇“被认为可能是二十世纪 用英语写作的最著名的文章”(注:王恩衷:《艾略特诗学文集》译后记,《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中阐述完全的相同的观点,成为了他论文的理论灵魂。论文 就是在这种观点的统摄下,对于莎曼艺术选择所经历的一个真诚艺术家的痛苦与折磨,进行 了这样的论述:“成为象征主义者还是依然作为浪漫主义者和帕尔纳斯派诗人,与新的运动 结合起来还是恪守传统:这在他初涉文学的时候几乎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他的内心为此备受 折磨。”就他生存的环境与艺术熏陶,他不是革新者而是保守者,不是先驱者而是传统主义 者,这样,“他在理解新的运动时感到非常痛苦,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别于同时代的人, 成为一个独特的作家,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一位古典的象征主义者。”他早期作品受到他 之前的各种流派的影响。他梦想着浪漫主义者的光荣,梦想着帕尔纳斯派的荣耀。他将很多 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大诗人,作为自己的偶像和崇拜者。他向往和梦想过“东方和智慧” ,“空气温馨芬芳、鲜花盛开的海岸”。(《金车》)但是,在自愿成为象征主义诗人之后, 他远离了最初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变得越来越自觉地憎恨这种影响。他从尼采那里获得了 信仰与活力。由此穆木天得出结论说:“在我看来,是帕斯卡尔和维尼的影响与尼采的影响 相结合,使阿尔贝·萨曼信仰人类痛苦的崇高。”“他的非常宗教式和相当病态的气质,把 他和他的同代人联系在一起,使他自觉地成了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一个属于新流派的象征主 义诗人。”在论文的“结束语”中,集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坚持“传统”与“新潮”结合,“ 吸收一切又综合一切”的思想:
萨曼几乎受到了19世纪法国抒情诗的各种相当不同、乃至矛盾的影响。如莱翁·博 凯所说,他是处在这些影响的十字路口。他崇拜传统。他把所有的文学潮流结合在一起。但 是他突然去世,未能完成他梦想的工作。我认为,他的某些作品在召唤着夏尔·盖兰、路易 ·勒卡多梅尔和佛朗西斯·雅姆,其他一些诗篇则启示了费尔南·格雷克和诺阿叶伯爵夫人 的道路。他是一位在象征主义时期保持了安得列·舍尼埃的传统,并且为新古典主义流派作 了准备的作家。如果说颓废诗人是意味着吸收一切又融合一切的话,阿尔贝·莎曼是与这个 动人的名字非常相符的。
穆木天经历了同样“痛苦”与“折磨”。他在莎曼的艺术选择中刺激和启示自己,找到了 在新诗发展中的位置:“把各种不同的潮流融合起来”,“吸收一切又融合一切”,在与传 统紧密联系中坚持与“新的运动结合”,在对于富有先锋精神的象征主义的探索中,成为一 位艺术的“革新者”。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20年代的诗歌理论与诗集《旅心》的实 践所表现的“综合”姿态来看,穆木天是一位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古典的象征主义者”。
从传统与革新选择的痛苦这个角度,重新审视穆木天20年代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与实践, 我们就会在他关于中国初期新诗的先锋性的探索思考中,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获得比 起以前来会是更深层面意义上的理解。
(一)他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认同与建设中,并不完全拒绝浪漫主义的资源。穆木天在论 文中认为,阿尔贝·萨曼的象征主义诗歌见于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公主的花园里》。他的《 瓶边集》、《金车》差不多是浪漫主义诗歌或帕尔纳斯派的诗歌。在《在公主的花园里》这 部诗集中,除了一些属于象征主义的诗歌之外,也杂有一些浪漫主义或帕尔纳斯派的诗歌。 而浪漫主义气息最浓的则是《金车》,尤其是《英雄交响曲》。通过具体的体味分析,论文 明确地指出,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些象征主义大诗人如魏尔伦、马拉美、爱伦·坡、波特莱 尔,乃至埃·德·里尔·亚当的种种影响来。他肯定这样的事实:“莎曼受到了浪漫主义的 巨大影响。有雨果、维尼、拉马丁、缪塞,可能还有圣伯夫的影响。”并且通过萨曼与其他 诗人作品的比较研究,具体探索了这种影响与吸收转化的痕迹,讨论了萨曼诗歌与这些浪漫 主义者之间精神的和艺术的联系。在他稍后发表的《谭诗》、《维尼及其诗歌》等论文里, 他仍然继续了学术论文的这一思路,没有轻易否定中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如在论 述象征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的时候,他所推举的例子,就有拉马丁的《湖水》,维尼的《摩 西》,爱伦·坡的《乌鸦》,毛利亚斯的《绝句集》,杜牧的《秦淮夜泊》等。他由诗人与 时代关系进入“诗人的素质”(Temperament)和“诗的意识良心”确认的时候,就更加肯定 维尼对于雨果,李白对于杜甫的超越性。因为他认为,就一个角度来看,“李白飞翔于天堂 ,杜甫则涉足于人海。读李白的诗,是诗的世界,有一种纯粹诗歌的感(觉),而读杜甫,则 总离不开散文,人的世界。”其他如他提出的“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要求“纯粹的诗 的感兴”(1nspiration),也都包蕴着强调浪漫主义的因素在内。(注: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
月15日。)他介绍维尼的长文里说 ,维尼作拿破仑,或作拜抡,作诗人,或作将军,是诗人维尼一生的最大理想。他作了“不 调和的灵肉的苦斗,开了他的苦闷之花”,这使他成为“法国浪漫时代一个艺术意识最强” 的 诗人。“他是永远的诗的”,追求“内面”、“沉思”、“默想”,“他的沉默的伟大,好 象永久的神秘。他的冷静的外壳里头,确是盛着热滚滚的大海。”但是他的作品,“不是 像一般浪漫诗人似的,表现出一种冲动的感情,他所表现的,是一种思想。他把感情化成一 种思想,他的思想自成一种象征。这是维尼异于一般浪漫作家的。因为维尼虽然生在浪漫主 义的时代,但一方面他却承袭了18世纪的传统,一方面,他却要超脱了浪漫的潮流。”他的 一些诗,可以看出“拜伦式的恶魔的色彩”,同时可以说也“预言了波多列尔(Ch.Baudelae re)的《恶之花》”“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又把他的思想“象征化起来,化成了一个 象征的世界”,维尼是浪漫主义诗人的重镇和代表,同时也是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先驱”和 “预言”。(注:穆木天:《Alfred de Vignyj及其诗歌》,《创造月刊》第1卷第5、7、8、9期,1926 年7月1日-12月15日。)这种沟通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思考,很富有诗歌实践走向的历史感和先锋 探求的超前性。穆木天的诗集《旅心》中的作品,那种“最纤纤的潜在意识”和“若听见若 听不见的声音”的捕捉,那种朦胧而又透明的情调的把握,就是融合浪漫与象征的追求所达 到的境界。后来,到30年代,穆木天论述王独清诗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说了这种思考付诸实 践的可能性:“浪漫的感兴和象征的感兴互相地交流着,但这两种感兴是不相冲突的。”“ 他 有的时候,使用着浪漫的音律,而有的时候,则唱着象征的哀歌。”(注:穆木天:《王独清及其诗歌》,《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1日。)因此,我们在他的 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与实践中,发现很多属于传统同时属于现代的因素,发现了许多浪漫主义 与象征主义交织的现象,就是很自然的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事情了。
(二)在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象征之间寻找平衡,寻找一条国民诗歌与纯粹诗歌结合的道路 。他的《阿尔贝·萨曼的诗歌》这篇论文里,非常清晰的意识到这样一个隐在的事实:萨曼 的 意识里有一种双重痛苦的斗争和对立。一个是,诗歌传统性的魔力与先锋性的新的诗歌运动 ,另一个,是异国情调与外省土气,泛神论与个人主义。他揭示了这种深在的对立与斗争, 而且分析了这两重对立,诗人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就使萨曼有一种热爱生活和热爱 人类的情怀与理想。“他喜爱烟草的烟、茶的热气、鲜花的芳香,然而他也憧憬人类的高尚 。他喜欢在普遍的存在下面看到永恒的象征。……他有着一位杰出的道德家的意识。”这种 高尚热情与道德意识,影响了穆木天。在最沉溺象征诗歌的时候,穆木天显然已经感到自己 理论从外在阐释到内心追求存在的矛盾,便在自己的论文中给予象征主义诗歌美学高度的肯 定与认同之后这样设问:“或者你要问我说:‘你主张国民文学——国民诗歌——你又主张 纯粹诗歌,岂不是矛盾吗?”他用实际是来自萨曼的“生命交响”的理论为此作了回答。他 说:“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不作交响(Correspondance),两者都不能存在,而作交响时 ,二者都存在。”国民文学只不过是交响的一种形式。眷恋故园的荒丘,北国雪野的平原, 南国风光的情调,异国薰香,腐水废船,故国的钟声与悠长的历史,……只要能够引起“内 生命”的交响,就能感觉出它的美来。穆木天看到了,个人内生命的深刻感悟是诗美创造的 关键。“人们达不到内生命的最深的领域没有国民意识”,“国民的历史能为我们暗示最大 的世界,先验的世界”,因此“国民文学的诗,是最诗的诗也未可知”。(注: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
月15日。)他将诗人的内 生命,诗人的灵魂,与现实道德意识以及一切事物的“交响”,即诗人个人生命与现实的感 应,契合,“自我的反映”,看做是国民诗歌与纯粹诗歌“在表现意义范围内”相通的精髓 ,并且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构想出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诗歌之间沟通的理想。这种“交响”与 “沟通”,在实践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如何用创作实绩提供起码的探索文本,当时的穆木天 以及其他诗人都还没有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但他的意愿所提出的方向,却是象征主义 进入中国新诗之后非常值得珍视的一种思考。
为了实现这个沟通的“理想”,他一方面重视内生命包含的现实人生意义的开掘,另一方 面又很重视在写实诗歌中注入主观的因素,以求尽可能达到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代的某种 平衡。在谈到莎曼诗歌对生活的感受时,穆木天就说:萨曼有一种可贵精神,就是他“对生 活的热爱”。“他热爱‘会思想的芦苇’,热爱‘人类痛苦的崇高’。他热爱仁慈,热爱光 明。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人充分体会到他的思想:‘我热爱宽容大度的人生哲学,它是为人类 的痛苦而由慈悲和怜悯构成的。’”他的大部分诗歌,都可以解释为“他感受到人类痛苦的 崇高,以及对人类贫困感到怜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莎曼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除了他萨曼的描写方面的生动诗歌之外,他还是一个心理或哲学上的现实主义者”。这 种对于象征主义的沉溺与对于现实主义的热衷,始终混流在穆木天的血液中。就在发表《谭 诗》之后的仅仅四个月,穆木天发表了一篇论述写实文学的文章。但是与刻板摹写生活的意 见不同,在这篇文章里,他特别强调了写实是人的“内意识”的“要求”与“人间性”关注 的观点。他对写实文学的理解的独特性,闪烁着一个先锋性艺术探索者的清醒。他说,“写 实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是一种真实的态度。必在自我意识最强的时候,必在哲学思索最深的 时候,才会有写实文学的发生。”“写实是一种人的要求。人不住的要认识自己。从要认识 自己的内意识里发生出来的东西就是写实的要求。写实文学就是这种内意识的结晶。”“写 实味毕竟是一种人间味。……懂得真的人生的人们,写实的把它写出来,自然能给我们一种 写实味,令我们感出真的人生滋味”,“自我的一面,是人性的自我,人性的自我创造出来 的东西是写实文学。如说纯粹诗的世界是自我的神性的游离,写实文学的要求,是由于自我 的人性的欲望。由神性的游离生出的纯粹诗歌,是一种超现实的升华,写实是作品是一种现 实的实现。”“写实作者出了自我为得是找到自我,那即是大我;写实作者压下自己浮浅的 感情,为得找着大的感情,那即是人间性的感情”。因此他认为,与偏于写实的帕尔纳斯派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高蹈派的先生比浪漫诗人认识自我认识得多”。(注:木天:《写实文学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日。)稍后他又说:“不 进入内意识的深处,产不出真好的写实作品来。写实味是人间性的认识,写实是人间性的表 现。……写实是认识。人生的一种忠实的态度,是一种大的哲学。”(注:穆木天:《道上的话》,《洪水》第2卷第18期,1926年6月1日。)1928年,他径直把 眼光转向属于“主张文人的社会的使命一派”的法国诗人维勒得拉克(Ch.Vildrac),并专门 撰文加以介绍,对于这位诗人的那些“始终是人生的礼赞”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注:木天:《维勒得拉克》,《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 穆木天的这种美学见解与沟通的努力,显然是想在先锋性的象征主义与传统的写实主义之间 ,也寻找一种诗人的自我生命与现实人生可以跨越的精神和艺术的联系。他的后来扬弃象征 主义,转向写实主义的诗歌和理论批评,固然有许多社会因素支配的作用,有他自身美学观 念转折的动因,但倘若考察了这些理论思考的线索,就不难看到他诗学理想发展过程本身就 存在的一个清晰的内在理路。
(三)初期新诗流弊的反省与民族化现代性新诗的建设。穆木天在新诗发展中倡导象征主义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艺术动因,是他对于五四以后新诗流弊的痛切反省。这种反省里,有倾 心象征诗的情绪带来的对于新诗的“粗糙”和过分“说明”的不满,也有对于新诗民族化追 求如何兑现的焦虑。在《谭诗》中,他已经叙述了在东京与冯乃超讨论“国内的诗坛”和“ 我们所主张的民族彩色”这样颇富使命感的话题。而对国内诗坛这一关注的直接表述,就是 他对于胡适“作诗须得如作文”的理论给新诗带来的弊害进行的严厉批评。这种弊害的主要 后果之一,就是混淆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给散文的思想披上了韵文的衣裳”。(注: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 月15日。)几乎 使新诗陷入无法自容的尴尬境地。这篇责难胡适为中国新诗运动“最大的罪人”的著名文章 ,写于1926年1月4日。四个月后的五月中旬,穆木天乘长崎丸回国。他对于新诗的这种失望 的情绪,在越接近难以言说的现状就越表露得更加激烈了。他说:“这一二天来,我看诗看 的头痛。中国诗人真多啊:真是中华大国!但这些诗人的作品,简直就没有诗意。在感觉感 情想象都没了的中国人里,可也难怪这些可怜的青年!我曾说过,诗有诗的世界,诗有诗的 文法,诗有诗的绝对的存在。诗是内生活的象征啊!攻新诗的青年们呀!请回到自我的国里, 到你们的唯一的爱,——藏在你们心中的唯一的爱的里头,作你们的诗的生活,做你们的诗 的意识,在沉默Silence里歌唱出来,那才是你们的诗。‘作诗如作文’的‘胡适主义’, 别让把中国诗坛害得断子绝孙啊!实在说:中国现在,作诗易于作文。总而言之,在现在中 国里分行写出来,什么都是新诗啊!想作诗的青年们啊!你们各各回到你们的象牙塔里罢!你 们天天作散文的生活,怎么能作出诗来呢?你们的生命力得动!动!动!真的生命的流才是真正 的诗啊!你们没有内意识,’怎能攻文艺,诗更不消说了。”(注:穆木天:《道上的话》,《洪水》第2卷第18期,1926年6月1日。)这些尖锐的批评意见里, 除了他关于象征主义诗歌的表述以外,隐藏了穆木天对于新诗艺术本体与民族色彩的一种焦 虑和茫然。这个话题似乎是隐去了他内心中存在的一个高亢的主调。就在他全神贯注沉溺于 象征主义伊始,潜心钻研莎曼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前夕,1924年10月17日,他写给郑伯奇 的一首诗里,就曾作过这样的内心表白:
什么是真诗人呀!
他是民族的代答,
他是神圣的先知,
他是发扬“民族魂”的天使!
他要告诉民族的理想,
他要放射民族的光芒,
他要腹心是是民族的腹心,
他的肝肠是民族的肝肠。
啊!外来的东西呀!
他们只能慰我们的悲伤,
不能引我们直直前往;
他们只能作我们的药汤,
不能作我们的膏梁。
举起我们象牙的角笛吧!
共唱我们民族的歌曲罢!
啊!伯奇呀!歌!歌!歌!
“民族魂”的真歌,
是永远的青青长长的绿。(注:穆木天:《给伯奇的一封信》,1925年3月6日《京报副刊》第80号。)
如果这些自白,不是看作诗人自作多情的吟咏和自我夸饰的姿态,而是他与冯乃超讨论“ 主张民族彩色”时认真思考的一次真实心境的吐露,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窥见穆木天诗学 思想深层矛盾的一个窗口:在进入象征主义诗歌世界之后,进行中国新诗的流弊反思的结果 ,并没有将他引向对于新诗先锋性与现代性的持续关注,而是匆匆走近而又匆匆放弃了象征 主义,走向了对自我生命意识漠视的唯物史观的现实主义诗学的执迷。这里一个更深层的艺 术原因,说得不客气一点,可能是他对于新诗“民族性”的狭窄观念的潜在迷恋。过分执迷 于自己所理解的民族性导致了穆木天对于“外来的东西”轻易的拒绝和放弃。“他们只能慰 我们的悲伤,/不能引我们直直前往:/他们只能作我们的汤药,/不能作我们的膏梁。”这 种对’“民族魂”与“外来的东西”机械性非常明显的理解,这种“民族的诗歌”与先锋的 诗 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对于穆木天,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展,都带来了窒息性的 压抑与摧残。它所带来的更深的创伤与痛楚,是许多诗人内心最宝贵的先锋性探索精神的丧 失与自我否定。穆木天对于自己倾心研究萨曼的象征主义诗歌,就是如此。他后来甚至有这 样一种负罪的感觉:自己进了大学,“完全入象征主义的世界”,“相当地读了些法国象征 诗人的作品”,“在象征主义的空气中住着,越发与现实隔绝了”,把一些“贵族的浪漫诗 人,世纪末的象征诗人”当作是“我的先生”,这似乎是“犯了不可容赦的错误”。(注:穆木天:《我与文学》,见郑振铎、傅东华主编《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 年。)他 谴责法国以及其他象征主义诗歌,“是恶魔主义,是颓废主义,是唯美主义,是对于一种美 丽的安那其境地的病的印象主义”,“这种回光返照的文学,是退化的人群的最后的点金术 的尝试”,那种“暴发的绝望的表现”,如不象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那样向着新的秩序走去 ,就会是“引着那个主义的依随者达于毁灭的田地的”。(注:穆木天:《什么是象征主义》,郑振铎、傅东华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 5年。
)这种转型留给我们的是可以 理解的心境,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进行反思的资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对于穆木天来说 ,放弃象征主义的探索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先锋性的理论优势。对民族化的过分迷恋的结 果导致了革新意识的磨损。后来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对立起来,视之为“世纪末”的颓废 诗人的精神垃圾,就丢掉了研究萨曼时候获得的“吸收一切又综合一切”的宝贵思想。先驱 者并不一定就是一位永远的探险者和艺术美的创造者。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先锋性最早的探索 者穆木天,后来在另一些方面的更大发展(这当然是历史所需要的一种富有良知的进步的选 择!),而在象征诗艺先锋性探索方面的停滞不前,放弃,忏悔,倒退,甚至简单地责詈,这 是诗人自己新的艺术意识的获得,还是探索中艺术意识的失落?还是别的什么应该思考的更 为复杂的东西?这一点,只能让历史来评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