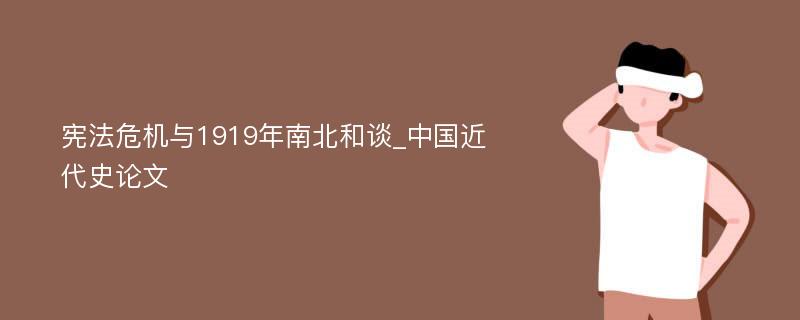
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4—0061—05
1919年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南北和谈,与辛亥年的第一次南北议和相较,固然已经物是人非,双方代表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纷繁复杂远胜当年,然其寻求统一、消除内争的总方向却是一致的。对于其中各个环节的研究,不仅能有助于探寻这次和谈失败的原因,而且对于理解此后国民革命的兴起、国会政治的衰亡或有意义。依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这部分的挖掘尚比较欠缺,仅有台湾学者的一本专著,以及海峡两岸十余篇文章①。总体来看,不仅数量上少,而且在研究角度上也有待扩展。本文将以宪法危机的形成及影响为切入点作一尝试,如稍能拾遗补缺,则幸甚。
一、一部非正式宪法:《临时约法》的困境
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时,人们期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看到一部正式宪法的出台,该约法第53条、54条指出:“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公布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愿望。但人们绝未曾想到这个负载“临时”任务的约法,竟然维持了十年的权威地位!十年后,身为老资格的宪法起草委员汤漪感叹到:“临时云者,革命未了之一别名词而已,以十个月内之临时延为十年之外之临时,是则所谓民国者,始终处于革命未了之环境,而又不能不致谨于法统之维持,其陷于进退失据,皆以宪法不成,阶之厉矣。”②于不经意间道出了民国宪法产出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临时约法》的困境。
以今天的眼光去看,《临时约法》的困境首先是因袁世凯新《约法》的打压,而1916年因国会恢复又得到逆反式强固的一个自然结果。适值袁世凯接手临时大总统之际,《临时约法》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成为临时宪法,总统制一变而为内阁制,在当时颇引起一些“因人立法”的猜疑③,因此招致袁世凯的不满。在反对天坛宪草的通电中,袁世凯说:“综观全文,比照‘约法’皆变本加厉”,已经显露出其对《临时约法》的不满。待成为正式大总统、解散了国民党,既而又解散国会之后,袁世凯开始指责“‘约法’之束缚驰骤”,表示自己隐忍已久,必须重新增修之。于是由政治会议议决,另设约法会议专门修订约法,理由为:《临时约法》“成于南京临时参议院……彼时兵事甫息,民意未申。且起草各员,仓促竣事。既不暇于中国民情国势逐细考求,而于国家机关权限之分割,又不免参以成见”④。按照这样的逻辑定位,正式政府成立后,《临时约法》的任务已完成,正该功成身退,且因其自身的种种不合时势而理所当然地需要被新《约法》取而代之。
尽管新《约法》在精神上大大加强了大总统的权力,但到那时为止,至少在表面上,国家根本尚未脱离法律的轨道,包括袁世凯提出增修约法,其依据也是来自《临时约法》⑤。因此可以说,新《约法》的产生还不足以给《临时约法》创造一个起死回生的口实。也正因为这一点,护国运动中南方的矛头对准的只是帝制,而没有人把新《约法》及袁世凯加强大总统权力的一系列措施明确界定在“帝制”的范围内。在各地发表的反袁通电中,多是对解散国会、颁布新《约法》等集权行动进行谴责,而把其“帝制”自为的起始点定在筹安会的发起上⑥。之后护国军为争取反袁合法性,也是一再指责袁世凯假公济私,四年中所为尽是些“丧权辱国、敛钱害民”之事,而护国军的任务则是“组织个良政府,将袁世凯这四年中所行的害国害民政治从新一一改良”⑦。这些只能说明袁世凯的政府是一个恶政府、袁世凯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总统而已,并不妨碍新《约法》作为国家宪法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署名的政府令发布,公告黎元洪依照(新)《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⑧。6月7日政府发布隆重办理袁世凯丧葬典礼申令,对袁世凯称帝前的成绩予以肯定⑨。这是一种明显的信号,表明政府欲恢复袁世凯称帝前的政治状态——即新《约法》下的民国。而在那种状态下,护国者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将是非法的(参与二次革命者),有一部分人将是被排斥在政治场之外的(旧国会议员)⑩。这种姿态自然会遭到护国运动参与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很快,南方讨伐新《约法》的通电便纷至沓来。
在这些通电中,“帝制”被贬斥为“僭制”、“伪制”(11),新约法则开始被目为“帝制导源”(12),甚至1913年11月4日之后的所有法令变更均被视为“袁世凯自造新制”(13),不能为国会所认同。总之,袁世凯在位时的所有政治行为均跟“帝制”拉上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新约法既然被定位成“胚胎帝制之伪约法”(14),其权威地位自然要受质疑,故惟有恢复旧约法方能“止纷息争”(15)。这样一来,《临时约法》的地位得到空前的上扬,比其刚颁布时犹有过之。一个临时性的宪法被重新强化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负面效应很快就暴露无遗。
新政局建立不久即爆发的内阁大风潮堪称典型的一例(16)。在这次风潮中,人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临时约法》的缺陷。内务总长孙洪伊欲使平政院的地位非法化,但在《临时约法》里的确有关于“平政院”的条文,而平政院则苦于其缺少更加细致的规定,亦无法为自身合法化找到更雄辩的依据。孙洪伊因得不到内阁多数的支持,实行消极抵抗,既不辞职亦不办公,对于命令亦不副署,新政局虽明确为责任内阁制,对此却也是无章可循,大总统又无权随意罢免国务员,这令身为内阁总理的段祺瑞亦感到运用乏术。
同年国会内因省制入宪的问题争执不下,致使宪法流产,无形间突出了《临时约法》的简略与其高居国家根本大法之间的矛盾,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各党派、个人等根据己意解释《临时约法》,分歧严重,宪法危机逐渐形成,其显著表现即是和谈前双方政府在宪法依据上都处于含混不清、自我矛盾的状态。
二、危机的一个体现:1919年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
没有解释权的相关规定,无形中为本就意义多歧的《临时约法》增添了更多纷扰。然而尽管每个人对约法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在1918年前,这种纷扰还只是局限于个别事件中(17)。张勋复辟平定后,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并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准备选举新国会,直接迫使一部分旧议员随孙中山南下,成立了军政府,南北遂成对峙之局。
在感情上,段祺瑞的确有太多理由改造旧国会(18),但段氏毕竟乃一武人,为北京政府作法律辩护的是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国务院为召集临时参议院征集各省意见的通电,据说即为梁氏亲笔,其中“言国会威信已失,再言改选迟重,非计久远,最后言改组……但欲改组,则非先有临时参院不可”(19)。临时参议院并非梁氏臆造,而是来源于《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20)。因此,北京虽言改组,事实上却并未表示完全抛弃《临时约法》。相反,在诸多场合,北京政要出言皆以约法为据。黎元洪退职时即依照《临时约法》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此后段祺瑞继承总理及敦促冯国璋赴京就任均以黎电为前提(21)。而冯国璋于任期届满时发表通电时,表示自己已经竭力“顾念约法精神之所在”,并“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尽管此前就国会问题他也曾公言:“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22)
北方的自相矛盾自然难逃南方的嘲讽,孙中山通电说:“约法之根本,已遭破坏无余,而犹复日依约法某条,其将谁欺。国会本尚存在,何事另行召集,参议院已经消灭,何得重行发生”,旧国会更出釜底抽薪之语:“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实列于第七章附则之内,凡法所具之附则,糜对以适用于一时为限。与法之正文继续有效者迥别,尤不徇妄于比附。”(23) 其实对于这点,梁启超亦心中有数,但是为了“改良组织”,不得不“就广义解释”,“勉强比附”(24)。梁氏如此用心良苦,甚至不惜冒违法之嫌,除旧国会本身因党见纷歧而扰攘不断外,更重要而隐秘的是,此时大局于宪法研究会非常有利,再次燃起了梁氏政党内阁的理想之火(25)。
相较于北方,南方在以往研究中显然享有更多的美誉。但在其政府组成的宪法依据上,是否能够邀得国人的较大认同,却仍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事实上,从军政府的成立直至护法结束,南方从没有对自己的护法行为进行过法律辩护,仿佛打出“护法”旗号本身就证明了自身的合法性。大元帅孙中山为革命元勋,拥有较高的威望与号召力,但从一开始在具体主张上就不欲注重法律轨道,为海军所反对,国会议长吴景濂到沪后,三方专门签订了尊重约法、国会的协议方始南下(26) 。海军虽宣言拥护约法,但并没有提出一个法律范围内的行动方案,而在宪法依据上最有发言权的国会却因人数的关系一直不能正式开会。到1918年6月要开正式常会时,满一个月未到者,参议员51人,众议员147人;满两个月未到者,参议员58人,众议员69人;合计325人(27),这么大的数字差距自然影响到国会的合法性,作为“第一届国会的继续,有关法规当仍适用,但其本身却是特殊的,原法并无依据”(28),故在其宣布召开非常国会及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时,均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通告,未就南方成立政府做任何法律说明(29)。而此前几天国会议员请陆荣廷兴师护法时曾说,“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惟念时局之急,间不容发……用师法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在广州开非常会议”(30),或可作为议员护法却不能依法之尴尬心理的一个注脚。
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直接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同意就职,增强了军政府的实力;另一方面,孙中山从有决议权的大元帅降至七总裁之一,愤而辞职,在通电中,孙慨叹“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国之下”(31),使南方政府在“护法”形象上大受折损。唐、陆虽曾是护国功臣,但对护法都是犹疑不决的。唐于当选元帅后一再辞职,陆则始终与北方联系不断,甚至取消两广自主(32)。而孙中山虽无直属军队指挥,但因其多年革命资历一直受到多方拥戴,此次护法又是首倡之人,故其辞职颇使外人怀疑西南排挤之意(33)。一般人的观感遂渐次变为:“北方的毁法固然不是,南方的护法也未见得尽出于真心”(34),双方并无本质区分。
三、南北和谈的难点之一:回到何处去
到第二次南北和谈在上海开议的时候,中国的法律状况大体是这样的:一方面,权威宪法没有得到更新或者任何的完善,《临时约法》仍然是唯一公认的民国存立之根基;另一方面,政治的运转使超出或偏离《临时约法》的“事实”愈来愈多,1916年护国战争后的新政局就曾对这个问题有过激烈争论,但那时还仅止于一个政府下的“事实”与法律的矛盾,1919年却扩展为南北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了。这两套系统都宣称源自于《临时约法》,而同时有程度不等的变通。因此法律问题,确切地说,回到何处引起的法律争议最少,成为最重要的难点之一(35)。
尽管陆荣廷、唐继尧与段祺瑞、冯国璋等南北武人之间存在许多的利益分歧,但和谈中的利益之争在本质上无非是妥协的多少,其中虽必有一番讨价还价,终究统一起来有路可走。法律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当一度中断了的南北和会开始面对法律问题时,鼓舌辩论的代表们突然噤声,和局顿时陷入一种“不生不死”之状态(36)。其核心难点即:面临着《临时约法》陷入困境而正式宪法迟迟不出台的危机,到底回归到何处,能够既顺乎法理又可以兼容各方面的利益?
南方以护法自居,如在法律上有所退让,无异于自失“人格”,因此唐绍仪一开始即反对预留商量余地,认为“法律问题在和会上让步,负责者固感困难,而流弊亦多”(12),故南方坚持国会自由行使职权的条件,表示对护法主旨决不迁就(13)。而所护之法即《临时约法》,如此势必回到1917年国会解散前的状态。然而这个建议事实上同时受到南北两方的抵制。在北方,安福会正是段祺瑞鉴于旧约法的缺陷改造而成的,与旧国会势不两立;徐世昌虽是主和之人,其总统之位的合法性却与安福系唇齿相依,因此对不能保障己位的复旧亦不能无条件答应。提出条件的南方则面临着另一种尴尬,广州国会虽自称旧会,但因新补入一百多人,与1917年的国会已相去甚远,且此举并没有明确的约法依据,这使南方一方面要坚持复旧,一方面要时时向国会中的新新派解释,旧会系指广东现会,请新补议员不要误会(39)。
1917年既然一去难以复返,1913年能否作为一个替代性的选择(40)?从理论上说,以人们现在的经验重回天坛宪草的制定时期,当可以从文字上纠正这以后几年内由《临时约法》产生的种种混乱,从而从根源上解决现在的宪法危机。然而这四年内已然发生了太多事实上的变化,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都不可能视而不见、一笔抹杀。即使单单考虑议员的流动、政党的变化,1913年也只能成为历史。因此这个建议并没有引起很多共鸣。
岑春煊则提出北京和广州国会同时闭会,双方合作继续:1917年之宪法会议,专门解决宪法危机,然后改选议员(41)。这个提议虽然注重现实,可是对任何一方的国会而言,都含有将来命运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有部分议员表示相互提携之意(42),依然不能得多数同情,而南方反应尤其激烈,甚至要求取消部分议员资格(43)。议长吴景濂更认为“与新国会联合制宪,实荒谬之极”(44)。除此而外,一些议员再次赫然请出约法,“制宪之权,约法规定,岂容任意变更”(45)。多数时候,约法不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是各派人员寻找理由的重要依据。
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这一点南方并非没有觉察,但南方认为,“约法虽未必完备,岂能擅行改毁”(46)。为走出困境,抢得话语权,南方加紧制宪,希望通过正式宪法组织正式政府,与北方相抗(47)。北方对此举亦十分敏感,极力拉拢政学系破坏制宪,而其所用手法竟仍是《临时约法》中最为人诟病的出席人数之规定,正式宪法再次流产(48)。当各派政客利用《约法》之缺陷来制造更深的混乱、以便浑水摸鱼之时,宪法危机随之达到高潮。
小结
约法既名为“临时”,其内容不完备在情理之中,而袁世凯的新约法与护国运动这两个相反的潮流造成的结果,却使这个临时性的约法行正式宪法之实达十年之久。1916年新政局中爆发的内阁大风潮,暴露了《临时约法》的困境,之后旧约法更多成为各派党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其困境遂愈走愈深,在此状态下,国会内部对地方制度等提案争论不休,正式宪法之生成一再流产,宪法危机于焉形成。
虽然各方对宪法危机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但为着不同的利益考虑,《临时约法》仍然被奉为圭臬,而正式宪法却依旧千呼万唤难出来。这使法律问题成为当时各派都不能回避而又无从解决(如果有的话,也只能仰仗约法),这种恶性循环不但给一直打宪法旗帜的武人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也使南北统一失去了一个统摄的中心。李剑农认为,辛亥和议成功,因其有“推倒清廷”一个中心的主义和思想,而1919年的南北和谈则实在找不出一个中心来(49)。如果接受这样的说法,那么宪法危机可以被认为是导致其中心缺失的一个肇因。
注释:
① 参看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段云章:《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范同寿:《1919年的南北议和与南北勾结》,《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3期及《1919年南北议和的前前后后》,《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1期;林明德:《日本与1919年的南北议和》,《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第4期,1976年4月;张北根:《英国与1919年的中国南北议和》,《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等。
②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汤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8辑,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③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235页;顾敦柔:《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第114页;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0页。
④⑤ 顾敦柔:《中国议会史》,第203、201页。
⑥ 见《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称帝罪行通电》、《唐继尧蔡锷等请共兴义举推倒袁氏电》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8页。
⑦ 《护国演说社发表一至十二期演说词》,《护国运动》,第337—357页。
⑧ 《大总统宣布由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告令》,《护国运动》,第740页。
⑨ 《大总统饬隆重办理袁世凯丧葬典礼申令》,《护国运动》,第743页。
⑩ “政治场”一词借自冯筱才著《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参见是著第11页页下注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书主要关注的是商人所受政治场的影响,而本文则关注政治场本身,认为政治场的“磁性”更多地表现在对内部的作用,使所有参与者都不由自主地要受一定规则的制约,使其行为或不能直接表现其真正的内心感受,或为达目的千方百计寻求政治场支持的语言、行为。另外,笔者以为,政治场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使用它能够兼顾早期民国(1912—1927年)约法与派系并存的政治状态。
(11) 见《孙中山请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屏除僭制电》、《吴景濂请恢复约法废除袁氏伪制电》等,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06、716页。
(12) 《胡景伊请恢复临时约法并申斥帝制派阴谋电》,《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770页。
(13)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解散国民党令,国会亦随之解散;《旅沪国会议员请恢复民元约法废止袁氏伪制电》,《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720页。
(14) 《欧阳莘等请取销伪法召集国会组织内阁诛锄逆党电》,《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736页。
(15) 《胡景伊请恢复临时约法并申斥帝制派阴谋电》,《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770页。
(16) 情形大致如下:新任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批裁员引起反弹,被裁人员到平政院控告其违法,但孙氏非但拒不答辩,而且提出平政院的权力来源于新《约法》而非《临时约法》,与平政院大起争执。不久总统府(黎元洪)与内阁(段祺瑞)先后参与进来,复杂的人物关系穿插在各种矛盾之中,使这场阁潮持续了月余方告结束。可参看1916年10月、11月《申报》、《大公报》有关报道。
(17) 比如1916年的内阁大风潮。孙洪伊、周树模、段祺瑞等都利用约法为自己辩护。
(18) 1916年的内阁大风潮给段氏很大打击,参见Allen Yuk-Lun Fung.Struggle over Constitution:Chinese Politics 1917—1919,Harvard Univ.Press,1996,chapter one.作者行文颇有“同情的理解”风格,站在段祺瑞的立场,对其行为有较多维护。
(19)(2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2、839页。
(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1322页。
(22) 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上海书店影印版,第426—427、406页。
(23) 《孙文反对临时参议院电》、《国会非常会议声讨段祺瑞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430页。
(2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31、836、832页。
(25) 此时的情形与1913年二次革命后非常相似,然而余痛未消,梁启超却又满怀希望地与段祺瑞合作了。此次内阁成员中尚有汤化龙、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员,此外范源濂、张国淦、汪大燮等与梁氏均为旧交。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粱启超年谱长编》,第830页。
(26) 《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近代史资料》总107号,第55—56页。
(27) 顾敦柔:《中国议会史》,第317页。
(28)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
(29) 《吴景濂等通知国会非常会议成立电》、《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和选举元帅通电》,《护法运动》,第411—413页。
(30) 《在粤国会议员请陆荣廷等兴师护法电》,《护法运动》,第395页。
(31) 《孙文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通电》,《护法运动》,第510页。
(32) 《孙文为陆荣廷等附北请唐继尧践约就元帅职密电》,《护法运动》,第450页。
(33) 褚辅成曾跟吴景濂商量,为减小形象损失,尽量加以补救。包括以孙中山宣布卸责日宣布为联合军政府,并声明此机关乃孙中山辞职后继承之机关。见《褚辅成就军政府改组应取之补救办法事致吴景濂函》,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34)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450页。
(35) 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284页。
(36) 《本埠新闻·和会正式续开之第廿七日》,《申报》1919年5月6日。
(37) 《唐绍仪就唐继尧电称开议先决条件之法律问题可最后让步为“旧会制宪”事致吴景濂、褚辅成电》,《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册,第142页。
(38) 《本埠新闻·和会正式续开之第廿六日》,《申报》1919年5月5日。
(39) 《罗家衡就法律借款问题交涉事致吴景濂、褚辅成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册,第394页。
(40) 《罗家衡就议和双方代表对宪法制成、总统选举、内阁组织等方面的态度事致吴景濂、褚辅成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册,第379页。
(41) 《林森就抄送岑春煊所拟和议条件事致吴景濂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册,第109页。
(42)(43) 《专电·香港电》,《申报》1919年5月2日、5月7日。
(44) 《吴景濂、褚辅成就所接来电内容与易次干所言不合事致卢信电》,《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册,第862页。此为草稿中内容,不知其正文中缘何删去。
(45) 《国内要闻·旧国会坚持恢复职权》,《申报》1919年5月4日。
(46) 《本埠新闻·三和平会致和议代表函》,《申报》1919年5月4日。
(47) 《吴景濂、褚辅成就议和前途之设想事致唐继尧函》,《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5册,第710页。
(48)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第311—317页。
(49)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450页。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北洋军阀史论文; 历史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段祺瑞论文; 袁世凯论文; 护法运动论文; 申报论文; 护国运动论文; 法律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