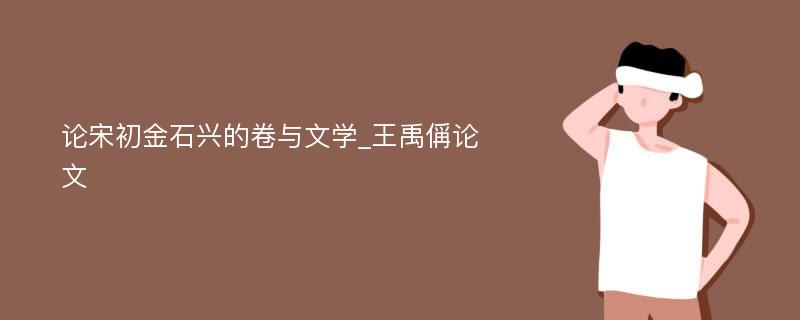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士论文,文学论文,论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2-0106-11
说到唐代的进士“行卷”,人们往往投以欣赏的目光,因为那里蕴藏着太多的人文逸事和文坛佳话。而且据研究,进士行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这是因为,一方面举子们要努力写出最好的“新课”(作品)以为鬻猎之资,另一方面当路者为显示自己慧眼识珠,“为国求贤”,又不得不荐举一些出类拔萃者以应选,于是双向互动,结果既带动了创作水平的提高,也使不少高素质的士子通过此途而荣登金榜。
所谓“行卷”,又叫贽文、投献、投卷等,即举子在科试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贽献给有关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称誉(又称“求知己”),从而提高自己的誉望,以求顺利登科。据研究,唐代行卷并不只限进士科,也包括制科和铨试等,如韩愈进士及第后,于贞元九年(793)应博学宏词科(吏部科目选),即曾行卷,同时作有《应科目与人书》等[1](外集:卷2)。只因有唐(尤其是中唐以后)特重进士科,故人们较多地谈论“进士行卷”。尽管行卷的实质是请托,是作弊,但因它是唐代重“誉望”的科举及铨选制度的产物,虽有时也遭到质疑、反对甚至查处,而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却似乎并不把它看成是严重问题或卑劣行径。
行卷并非唐人的“专利”,宋初也有,只是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且与成熟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牴牾,故很少引起学界的重视并被充分认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只要“采时望”、不依程文定去留的制度存在,就难免有请托,有请托也就可能有行卷。据笔者考察,不仅太祖、太宗两朝,就是真宗之初,行卷也很普遍,只是由于景德科举新制的颁行,到仁宗时期,此风才真正偃息,连宋人都很少提起。本文拟揭示宋初进士(偶也旁及制科等)行卷的史实,并分析行卷风最终止息的原因,以及宋初进士行卷对文学的影响等,以质诸高明。
一、史料文献中的宋人行卷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状元胡旦为举子时曾作《与田锡书》,略曰:“请速来,三月尽约为夏课,三人同志,以振吾道。”[2](卷3·答胡旦书附录)胡旦约田锡来做“夏课”。何谓“夏课”?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曰:“(举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又宋钱易《南部新书》乙卷:“长安举子,自六月以来,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则所谓“夏课”,乃为行卷而准备“新文章”也。这样看来,唐代举子常用的“行卷”,也流行于宋初,否则就无胡旦所谓的“夏课”。
事实正是如此。宋人陈鹄《耆旧续闻》卷8《进士投卷》曰: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湘)、清献(赵抃)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
考赵湘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则其时有进士行卷。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还记载有宋初举子的行卷诗:
王公随雅嗜吟咏,有《宫词》云:“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渔歌唱夕阳。”皆公应举时行卷所作也。
按王随,字子正,真宗咸平五年(1002)登进士第四名,可证真宗初亦存在进士行卷。我们知道对“行卷”有多种称呼,则《青箱杂记》卷7所载侯某向王随献成锐诗,应当也是行卷:
王丞相随刻意于诗,以谓诗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尝有应制科人成锐集诗三篇,国子博士侯君以献于随。随览之,乃亲笔尺牍答侯君,其略曰:“随拜启:伏承贤良成秀才见访不及,裁制三册,文华宏逸,学术该赡。然览《野菊诗》云:‘彩槛应无分,春风不借恩。’又《野花诗》云:‘馨香虽有艳,栽植未逢人。’实皆绮靡不辞,未协荣登之兆。复阅《别随州裴员外嘉》句云:‘凭高看渐远,更上最高楼。’谅惟再举,合践高科。”其好品藻如此。
这是说的制科行卷。既称“王丞相”,时间当在仁宗时(据《宋史》卷311本传,王随仁宗时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谓“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云云,虽是泛论“行卷”,然据上下文,当包括宋人的行卷(详下引)。不过与唐代一样,在宋人文献中直接用“行卷”一词的并不多,而较多地用“献文”、“贽文”。如《邵氏闻见录》卷7载:“李文定公迪为举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将试京师,从明逸求当涂公卿荐书,明逸曰:‘有知滑州柳开仲涂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文定携书见仲涂,以文卷为贽,与谒俱入。久之,仲涂出,曰:‘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因留之门下。”所谓“当涂公卿荐书”,指州郡发解文状;而为求取解,又需向知州“以文卷为贽”,且与“谒”(指书信)一齐进入。又范百禄《文公(同)墓志铭》载:“庆历中,今太师潞公(文彦博)守成都,誉公所贽文,以示府学,学者一时称慕之。再举乡书第一。”[3]又尹洙《谢公(涛)行状》:“(涛)雅善品藻文章,……人有贽文者,必读之终篇,或摘其词之工者称道之,其爱奖士类如此。”[4]又苏颂《孙公墓志铭》:“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孙公讳抃,……尝贽文谒成都尹凌策,将以童子荐之,顾其幼且孤而止。后累举进士,更今讳。”[5]这是行卷求荐举(童子科)。又《青箱杂记》卷2:“(龚)颖自负文学,少许可,又谈论多所折难。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门,独丁谓贽文求见。颖倒屣延迓,酬对终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韩、柳后,今得子矣。’异日,丁献诗于颖,颖次韵和酬曰:‘胆怯何由戴铁冠?祗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从“祝君早得文场隽”句,知丁谓贽文的目的是取进士第。上述都是宋初举子或应进士、诸科,或应制举、童子科时“贽文”亦即行卷的例子。
应当指出,尽管举子以取解、登科为目的的行卷,在北宋中叶以后见不到了,但其它目的的各种行卷并未停止。如《四朝闻见录乙集》:“熊克字子复,建宁人。……暨调馀姚尉,史越王(浩)尝为是官,适以旧学召入相,道出馀姚,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熊克是为得官而行卷,与唐代铨选贽文略同。又如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有“废诗二十馀年矣,忽读来诗眼暂明”句[6](卷10)。他还作有《跋方汝玉行卷》[6](卷106),以及众多的诗卷跋,所跋盖多为“行卷”。又马廷鸾《题周公谨〈弁阳集〉后》,亦有“一日又饷余行卷”句[7]。此类“行卷”,乃江湖诗人相互投赠诗卷,虽形式上与进士投卷相仿,而目的却迥然不同:前者意在蜚声江湖,而后者则志在蟾宫摘桂。
二、宋初进士行卷个案举隅
从上节知宋初的进士行卷,在宋人史料文献中虽记载不多,但并非没有;而欲知宋初行卷之详,我们有必要研究若干个案,以投卷、受卷者自身的材料,证明宋初确实存在着与唐人相似的行卷之风。这类个案,保存在宋初人的别集及宋人所编总集之中。先举投卷个案。
1.柳开(947-1000),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进士。
在柳开的《河东先生集》中,现存《上大名府王祜学士》凡四书[8](卷5),其第一书曰:“自五岁而读书,以至于此,凡十九年矣。当时便诵执事之文章,与夫圣人之言杂而记之。敢望今日亲执事于是邦哉?……敢请见焉。”第二书曰:“当今取士之道,独有礼部焉。每岁秋八月,士由乡县而举于州郡,由州郡而贡于有司。有司试其艺能,择其行义,得中者,后进名于天子,始得为仕也。……幸逢执事之来,故有望于执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书,先斋沐而后请见焉。”第三书则直述投卷情况:
开再拜,谨投所业书、序、疏、箴、论一十七篇,纳其后进进谒之礼,非为文也。开始将见于执事之时,……取旧所著文,写以五通。暨乎得见于执事,执事赐之大恩,不罪狂愚。……
可知“始将见”即投第一书时,已有贽文。四书显然皆柳开为取得州解以贡之礼部,向王祜求知。据《宋史·柳开传》,他向王祜“以文贽,大蒙赏激”。除王祜外,柳开还作有《与范员外书》[8](卷5),自称“东郊柳子”、“穷为一旅人”,则亦在未第之前;并谓“谨以碑、铭、箴、疏、论等杂共一十篇,献于左右”,无疑仍是行卷。他还作有《上窦僖察判书》,曰:“后二月五日,……开本在魏东郊,著书以教门弟子,愿有终焉之志。不幸迩来父兄以家贫,令求禄以养生,……故束带冠发,编修简策,欲陪士君子之下,有冀望于名焉。……开遂北走是来,冀执事之知,进退之间,唯执事之命耳。故以是书,敢为贽业之先容也。”[8](卷7)十馀天后,也就是“后二月十七日”,他又写了《上窦僖察判第二书》,略曰:“开再拜言于执事。……敢望执事以一言而见知,以万力而拔举也,不是虚矣,不是二三其求矣。……事蹙时迫,辞旨恳切,馀其面闻,死罪死罪!”[8](卷7)这就是唐人所谓的“温卷”。柳开在取解之后,又把行卷活动移到京城开封。他在《答梁拾遗改名书》(原注:周翰,开宝壬申岁。按壬申为开宝五年,972)中写道:
四月十五日,乡贡进士柳开再拜。……去秋八月已来,遂有仕进之心,以干于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门下,实为之举进士矣。窃冀于公者,公以言誉之,公以力振之。
这里毫不掩饰行卷的目的。他又作《上主司李学士书》为自己辩谤,有曰:“自去年秋应举在京师间,士大夫或以恶文见誉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间,不复列于此书者,以开所纳文中,有《东郊野夫》及《补亡先生》二传可以观而审之。”[8](卷7)知他曾向“李主司”即李昉纳文,是年李昉知贡举。其《上卢学士书》道:“十一月日,乡贡进士柳开再拜,奉书于执事。……今夫朝廷之贤者,独执事大矣。果将往而卜之,与之进而斯进矣,与之退而斯退矣,是可定于开之利不利也。故夏初求先容以登于执事之门,直以恶文干于左右。洎乎面见执事,果执事不曰汝未可以进矣。……荷执事之恩,宜将何报,姑致谢而进斯言焉。”[8](卷8)所称“卢学士”即卢多逊。张景《柳开行状》曰:“及游场屋,携文诣故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馀年矣。’崖相卢公(多逊)方在翰林,一见公,谓公奇士无敌。”则柳开应还有上杨昭俭书,久已失传。
2.田锡(940-1004),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
田锡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写道:“十一月日,进士田锡谨斋沐拜手,献书于补阙执事。……谨以所编鄙陋之文五十轴,贽于几阁,卜进退于明公也。”[2](卷3)又《上开封府判书》:“十一月日,进士田锡谨斋沐拜手,献于郎中执事。……今皇上嗣守丕图,殆将周岁,……拔解许依于王府。……冀贤王得而荐之,明主得而用之,岂非明公发解之善异乎古人乎,进人之名光于今日乎?”[2](卷4)按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锡)墓志铭》曰:“拔王府荐,有声于京师。太宗皇帝亲策天下进士,擢公第二人,时太平兴国三年秋也。”[9](卷12)则两书显然是为取开封府解“求知己”而作。取解之后,田锡又为省试而忙于行卷,他在《遗中书相公书》中写道:
四月二十三日,乡贡进士田锡谨以长书一通,献于相公黄阁之下。……锡平生所著文约百轴,择其自善者得二十编,虽缮写献投,为举人事业,固不乞用为卖名之资,亦不足为希赏之资;其实邀相公之知、回相公之鉴者,在此一书尔[2](卷2)。
3.王禹偁(954-1001),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
在王禹偁《小畜集》及《小畜外集》残本中,无行卷投书文字,而见于保存在总集中的佚文。《与雷夏柳令书》略曰:
明公……今来宰百里之邑,食五斗之米,非足以申明公之壮图,展明公之大志也。国家并汾已平,则蓟从而可取,是以将求封禅之草,筑太平之基,明公又得以宏略伟才复用于世。……迩来歧路三舍,门墙数仞,命驾之心,朝夕怿怿。是敢辍采兰之役,冒暑而来。……谨以旧史十卷随书上献,视事之暇,光览为幸(注:《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102。是书《二百家名贤文粹》题“雷夏先生”,据该书卷首所列“名贤世次”,“雷夏先生”即王禹偁,盖以其故乡钜野临近雷泽,雷夏即雷泽。)。
文中所谓“柳令”,即著名词人柳永之父雷泽县令柳宜。书谓“国家并汾已平,则蓟从而可取”,按平并汾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即灭北汉,随后太宗进兵幽州,故云“蓟从而可取”。因知是书必作于太平兴国四年夏,与书中“冒暑而来”句正合。王禹偁是年二十六岁。第二年(太平兴国五年),王禹偁省试登甲科,殿试落选;则本年奔走县令之门,当是请求乡贡。
王禹偁还作有《投宋拾遗书》,略曰:“十一月二十日,乡贡进士王某谨斋庄沐浴,裁书百拜于拾遗给事。”其下述自孔子至韩愈之“道”,因云:
顷者明公之典宋、鲁也,某尝策杖辞亲,揭厉行潦,编文著书,求明公之顾,一接威重,属明公有泰山之祷。某以晨羞缺贡,旅火是逼,不果志业,彷徨而归居鲁西。二年间贫病相绊,乞食假衣,以给切累,勉强为文,皆有悲愁寒冻之意。……今年春,始敢囊书笈文,来诣辇毂,登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某辍旨甘之具,为桂玉之费,久留阙下,则身与亲冻馁俱至矣。进之退之,俟明公命[10]。
所投书之“宋拾遗”,即宋白。《宋史》卷439《宋白传》:太宗即位,“擢为左拾遗,权知兖州,岁馀召还。泰山有唐玄宗刻铭,白摹本以献,且述承平东人望幸之意。”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左拾遗、大名宋白献《平晋颂》”,授中书舍人。既知是书乃投宋白,则其写作年代遂可考知。书中自称“乡贡进士”,投书的目的是为了“求誉”并借以“进身”,自然在取解之后、省试之前。王禹偁曾两赴省试,第一次在太平兴国五年,第二次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第一次宋白权同知贡举,第二次为权知贡举。[11]细审书意,既言“顷者明公之典宋、鲁(鲁当指兖州,‘宋、鲁’偏指鲁)”时,尝前往拜见,又谓其因有“泰山之祷”而不值,遂“归居鲁西(指其家乡钜野),二年间贫病相绊”,则书显然作于第一次赴省之前,所谓“十一月二十日”,应是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据前引《宋史》本传,宋白权知兖州在太宗即位之年,即太平兴国元年(976),“岁馀召还”,献泰山唐玄宗刻铭摹本,而禹偁往谒时正值宋白上泰山,当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归居二年,正在太平兴国四年也。若投书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一月,宋白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已五年,不得有两年前典鲁之事。是书既作于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则知王禹偁除本年夏天曾投书柳宜外,又曾于春、冬两次赴京师开封游扬其业。
4.胡宿(996-1067),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
在胡宿的《文恭集》中,保存有他的部分贽文书启。《上谢学士启》曰:“如某者,……屡遘家艰,坐更岁举。叔夜之不堪滋甚,原生之将落可忧。……伏遇大学士辍从周卫,关掌使符。……是用掣铃下馆,曳裾高门,……誓将谫薄,辱在品题。”[12]《上两浙均输徐学士启》曰:“往岁以楚材择秀,鲁席聘珍,妄由穷巷之中,骏奔硗关之下。因缘典谒,获贽编联。……曲敦提耳之私,屡获铸人之问。仍以类优之作,遍加溢美之言。比者国家以裹轮式命,刻鹄旌贤,……未能引退,窃望利宾。……左氏膏肓之疾,倚在一鍼;波臣枯涸之危,系于斗水。誓将白日,庸答所天。”又《上徐监丞启》说得更明白:
如某也,本乏声猷,素无轮咊。……适值国家妙选时英,精抡乡秀。……蟠木轮咊,既绝先容之助;敕字漫灭,徒兴逆旅之嗟。因力缀于编联,偶上尘于视听。……岂谓某官……回月旦之评,曲加品题;传《春秋》之字,遽辱褒称。俾寒灰之复燃,令困兽而思斗。……敢不淬励缣缃,服从名检,上以全公卿之奇遇,次则成父母之荣欢[12]。
从三书中“坐更岁举”、“楚材择秀”、“精抡乡秀”等语看,皆为乡贡取解行卷而作无疑,后两书犹有贽“编联”之语,“编联”即所投诗文卷轴也。
再举受卷个案。这只要研究一下王禹偁就够了。王禹偁是宋初文名最著的作家和诗人,又曾为翰林学士,因此向他行卷的举子特别多,他也指导和荐扬过大批后进。王禹偁曾说:
主上躬耕之岁(指太宗端拱元年,988),仆始自长洲宰被召入见,由大理评事得右正言,分直东观。既岁满,入西掖掌诰,且二年矣。由是今之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朝请之馀,历览忘疲[13](卷19·送丁谓序)。
“举进士者”向一人行卷竟“岁不下数百人”,真令唐人瞠乎其后。即使在王禹偁因延誉孙何等事被贬官滁州时(注:按:王禹偁此次被贬,原因复杂,延誉孙何只是罪状之一。说明一旦出事,延誉举子也会被查处,与唐代相同。),向他行卷的热潮仍不稍减,他在《答郑褒书》中写道:“将理装之官,全有进士林介者,食于吾家七年矣,私谓吾曰:‘今兹诏罢贡举,而足下出郡,进士皆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者。’吾谓介曰:‘为吾谢诸公,慎勿来滁上,吾不复议进士之臧否以贾谤矣。’……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是而非非,造次颠沛,不易其心。吾以一失职而不交贤士,斯自弃也。下车以来,有进士皆接焉。数日前,得生书,因自贺曰:向如谋,则失郑矣。”[13](卷18)秀才黄宗旦,还在王禹偁贬商州时即“走仆赉书”求知;后来贬滁,“复又辱书惠文,以寻前后好”[13](卷18·答黄宗旦第二书)。王禹偁作翰林学士时,“进士钱易数以文相售”。[13](卷20·送江翊黄序)接受进士行卷,似乎已成了王禹偁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寄主客安员外十韵》中,他写道:“寻寺谁同步,留僧自拂床。举公投卷轴,时相觅文章。”[13](卷7)
向王禹偁贽文的众多举子中,最受他器重的是孙何兄弟和丁谓。
王禹偁述其结识孙何(961-1004)的经过时说:“先是,余自东观移直凤阁(指端拱二年由直史馆拜知制诰),同舍紫微郎广平宋公(按指宋白)尝谓余曰:‘子知进士孙何者邪?今之擅场而独步者也。’余因征其文,未获。会有以生之编集惠余者,凡数十篇,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余是以喜识其面而愿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淳化元年,990)冬,生再到阙下,始过我门,博我新文,且先将以书,犹若寻常贡举人,恂恂然执先后礼,何其待我之薄也!”[13](卷19·送孙何序)两人于是乎定交。禹偁复以孙何文章“声于同列间”[13](卷19·送丁谓序)。孙何弟仅(968-1017),字邻几,也深得王禹偁的器重。孙何考中状元后,禹偁即以“小状元”相许[13](卷9·书孙仅《甘棠集》后)。丁谓(966-1037),字谓之,于淳化元年冬携文百篇至京师,引起人们的重视。次年春,又到京师向王禹偁贽文,告归日,禹偁作《送丁谓序》以赠之,叙述相识经过,并评其诗文道:“去年得富春生孙何文数十篇,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仆因声于同列间。或曰:‘有济阳丁谓者,何之同志也。其文与何不相上下。’仆不之信也。会有以生之文示仆者,视之,则前言不诬矣。……今春生果来,益以新文二篇,为书以投我,其间有律诗、今体赋文,非向所号进士者能及也。其诗效杜子美(甫),深入其间;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能辨也。由是两制间咸愿识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贾公(黄中)尤加叹服。”又作《荐丁谓与薛太保(惟吉)书》推举其才[13](卷8)。于是丁谓便与孙何齐名,世称“孙、丁”。王禹偁得此二人,十分满意,赠诗道:“二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14]由于王禹偁等名士的大力吹拂,一时孙何、孙仅、丁谓三人文名大振,“誉望”极高,柳开曾以诗述其盛况道:
今年举进士,必谁登高第?孙传(即孙何,后改名)及孙仅,外复有丁谓。到京见陈访,好尚同韩洎。馆中诸仙郎,纶阁贤三字,翰林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腾走大名,淜轰天色沸。……[8](卷13·赠诸进士诗)
淳化三年(992)春,诸道贡举人一万七千三百,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为主考官,孙何省试、殿试俱第一,丁谓殿试第四。咸平元年(998),孙仅登进士第一,果真成了“小状元”。
三、宋代进士行卷止息的原因
分析上两节所举进士行卷事例,时间都在太祖至仁宗前期,而包括宋人别集、总集在内的宋代文献,几乎没有仁宗以后举子为解试、省试行卷以求公卿“品题”、“延誉”的例子。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说明仁宗后行卷风已经止息。如果考察太祖至仁宗时代科举制度的重大变革,行卷风止息的原因就一清二楚了。
唐代的进士录取,以“采誉望”(即看已有的社会声望)为主,对卷面成绩不甚重视。《文献通考》卷29《选举2》在述唐钱徽、高锴作弊案后,马端临案曰:“唐科目考校,无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取誉望。”由于录取“采誉望”,故举子就把如何得到名人的赏识以提高“誉望”即知名度放到重要位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唐代举子有“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的说法,可见请托已漫然成俗。通过行卷和名士的“激扬声价”,也许可能录取到一些素质较高的进士,但它驱使人们奔竞于势利之途,毒化了社会风气。故南宋人项安世批评唐时“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而为“行卷”忙碌,认为“风俗之弊,至唐极矣”[15]。“采誉望”为权力过多地介入人才选拔开了方便之门,绝非科学、理想的选举模式。宋初,如上引陈鹄所说,“尚有唐人之风”,故那时仍盛行贽文行卷;但随后统治者对隋唐以来的进士考试制度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主要有如下四项,而集中点正是杜绝包括行卷在内的“请托”。
1.取消“公荐”。所谓“公荐”,即当权者或社会名流向主司(知举官)及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推荐进士人选,或用各种方式为举子制造声势。这特别在中唐时代盛行(注:唐代“公荐”情况,可参读《唐摭言》卷6《公荐》。)。所谓“公荐”,实际上是请托,难免流于“私荐”。宋建国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荐”开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2载: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原注:“故事:每岁知举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得公荐所知者,至是禁止之。”
2.实行糊名制。顾炎武《日知录》卷17《糊名》道:“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之。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原注:“此则糊名已用之选人,而未尝用之贡举。”玄宗以后的吏部试,又恢复糊名。糊名用于科举考试,当始于宋初,而最早由殿试开其端。《文献通考》卷30《选举3》载:“(太宗)淳化三年(992),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馀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
礼部试糊名要晚一些。《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8载: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九日(注:原作“景德三年”。考景德三年不闰五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文献通考》卷30《选举3》改。),“帝(真帝)问宰臣等‘天下贡举人几何’?王旦曰:‘万三千有馀人。’帝曰:‘约常例奏名几何?’曰:‘大约十取其一而已。’帝曰:‘当落者不啻万人矣。必慎择其有司。’旦曰:‘至于封印卷首,若朝廷差官,于理亦顺,然须择素有操执者。凡进士诸科试卷,悉纳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校,仍颁其式。知举官考定等级后,复令封之,俟覆考毕,参校其得失。’”是年十二月,令礼部试糊名考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载:
先是,上尝问辅臣以天下贡举人数……(略,大意与上引《宋会要》同)。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审择。晁迥兢畏,当以委之周起,王曾、陈彭年皆可参预。”……于是命翰林学士晁迥、知制诰朱巽、王曾,龙图阁待制陈彭年同知贡举。既受诏,上谕以取士之意,务在至公,擢寒畯有艺者。……又命知制诰周起,京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滕元晏封印举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监封印院门。进士、诸科试卷悉封印卷首,送知举官考校,仍颂其式。知举官既考定等级,复令封之,送复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凡礼部封印卷首及检点程试别命官,皆始于此。
《文献通考》卷30《选举3》亦记此事,曰:“先糊名用之殿试,今复用之礼部也。”礼部糊名考校的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它是指向考官的,目标是追求“至公”。故《燕翼诒谋录》卷5曰:“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
州郡取解试实施糊名制,比殿试、省试更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载: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乃委转运司所部选词学并公勤者为考试监门封弥官”。
3.实行眷录制。虽糊名堵塞了许多漏洞,但仍可用认字迹、留暗号等方式作弊,于是宋人创立了誊录制,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循私舞弊的可能。根据真宗的命令,陈彭年、晁迥等于景德四年(1007)十月呈上所更定的进士考校条制(注:称《考校进士新格》,或《考校进士程式》,见《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宋史·选举志1》。),释文莹《玉壶清话》卷5曰:“陈彭年字永年,……除正言,待制于龙图阁,与晁少保迥、戚密学纶条贡举事,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则礼部试的糊名和誊录两项制度,皆由陈彭年等人所定,而誊录至迟在景德四年已成为法令。事实上,早在景德二年(1005),御试即已用誊录了。《宋会要辑稿·选举》7之9载:真宗景德二年五月十三日,御试,“帝召王钦若等十一人于内阁糊名考校,分为六等,别录本。”“别录本”就是誊录,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誊录的最早记载。
对于糊名、誊录制,宋人曾有不小的争论。《燕翼诒谋录》卷2曰:“虽已弥封,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谬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这是留恋“采誉望”和“行卷”。熙宁二年(1069)正月,针对“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的主张,苏轼在所上《议学校贡举状》中驳斥道:“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服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16]所谓“通榜”,王定保《唐摭言》卷8有《通榜》一节,洪迈《容斋四笔》卷5《韩文公荐士》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有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也就是进士通过行卷得到有力者的推荐,录取时往往就在其中。由此可见,糊名、誊录制正是行卷的最后终结者。
4.取消“公卷”。公卷,唐代又称“省卷”。苏颂曾作《议贡举法》,为我们说明了什么是公卷,以及它的作用:
旧制,秋赋(引者按:即取解试)先纳公卷一副,古律诗、赋、文、论共五卷,预荐者仍亲赴贡院投纳,及于试卷头自写家状。其知举官去试期一月前,差入贡院,先行考校,内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如程试与公卷全异,及书体与家状不同者,并行驳放。……是举人先纳公卷,所以预见其学业趣向如何,亦有助于选择也(注:有人将公卷与举子行卷混为一谈,以为“公卷”即行卷,误。如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第六章《科举考试》曰:“在唐代,举人至京城赴考之际,往往拜访主考官,投呈所作诗文,以求赏识与推荐。……这种请托活动称为‘公卷’。这一习惯,只有在唐代这种社会才有可能。……但是到了宋代,政府为了保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在考试中采取了许多措施,象‘公卷’之类的旧习便不再合适而没落。”(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景颣以前,学者平居必课试杂文、古律诗、赋,以备秋卷,颇有用心于著述者。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惟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诗、赋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岂所以激劝士人笃学业文之意耶(注:《苏魏公文集》卷15。宋代进士科省试前须纳公卷,又见《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7。)?
苏颂认为取消公卷有弊病,但公卷本身,原是为“采誉望”而设,即柳宗元所说的“先声后实”:考官先考校“省卷”,留下第一印象,再读试卷时,“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17]。这不仅为考官作弊预留了通道,也为举子作伪创造了条件。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五日,礼部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行书写,或被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到省,无凭考校。请自今并令亲自投纳。”[18](3之7)更重要的是,考试既实行糊名、誊录制,去取只看卷面成绩,则“先行考校”所纳“公卷”,已失去了意义。于是,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
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
仁宗“从之”[18](15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载此事,文字与此有异,更能说明问题:
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篇试,则公卷为可罢。
以上所有措施,说明自宋初以来,统治者一直在努力革除请托等人为因素对科举考试的干扰,使隋唐以来新兴的科举制度更趋完善和成熟,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有惩于唐代利用科举考试酿成的朋党之祸,以确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但请托既已成俗,涤荡亦非易事,夏竦《议贡举奏》曰:“荐书未达于冕旒,驰声已满于涂路。……祝谒已先秋赋,里选何有至公?”[19]本来真宗景德间立法实行糊名、誊录制后,行卷已没有实际意义,弊风就该立即止息;但仁宗前期仍有记载,一方面是因为州郡取解试到仁宗明道后才普遍实施新制(见前引明道二年诏)(注:按苏轼《题伯父谢启后》曰:“天圣中,伯父中都公始举进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时进士法宽,未有糊名也。”是仁宗初州郡尚未实行糊名制之证。),另一方面则是积习既久的惯性所致。不过统治者消除请托弊风的决心似乎也很大,从真宗时代起,便加大了打击的力度。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真宗“令御史台喻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18](3之7)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五日,又诏榜贡院门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辨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18](3之8)在制度保障和“朝典”震慑之下,官员舞弊虽未必能从此杜绝,但通过行卷请托以制造“誉望”的风气,确乎渐渐偃息了,故贽文投书也逐渐从文献中消失。
四、进士行卷与宋初文学
我们再来讨论宋初的进士行卷。唐代进士行卷,一般是送上文章诗赋若干,而必有书信一封,例为对被投卷者的颂扬乃至肉麻的吹捧,接着是自我介绍,以及所投卷轴类别数量,最后是“进之退之,恭候台命”之类的套话。旬日之后若无反应,犹有“温卷”,又有书信。宋初行卷,大体也不出此。但若遍读现存宋初举子的行卷投书,会发现其内容有不同于唐人的显明特点。
宋初举子行卷,如前面举到的柳开、田锡、王禹偁等,无一不在投书中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柳开向王祜行卷,现存所投四书,均陈述自己对古文、古道的见解。张景《柳开行状》写道:“故阁老王公祜方守魏,公以书谒之。时王公与陶谷、扈载齐名,未尝以文许人。及得公书,谓公曰:‘不意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俨然文学知己。又如上已述及的王禹偁《投宋拾遗书》,在叙述了自孔子至韩愈之“道”后,写道:
下韩氏二百年,世非无其文章,罕能聚徒众于门,张圣贤之道矣。其或者复授于明公乎!明公履孔、孟、扬雄之业,振仲淹(王通)、退之(韩愈)之辞,矧天与之时,则追还唐风,不为难焉。然登明公之门、师明公之道者甚未众,止闻胡、田二君矣。
乃以共同“追还唐风”相期。这类例子甚多。前述王禹偁接受并评论众多举子的行卷,也都集中在文学上,可不再赘。我们还可举孙抃为个案。前引苏颂《孙公墓志铭》,谓孙抃少年时曾向成都尹凌策行卷。孙抃后来举进士,行卷“求知”的书信现存两封,其中《上提点张郎中书》道: 始冠岁,则沿洄经史,秉笔学为文章,凡寓意措辞,必据仁义、蹈礼仪,以求合圣人之旨。……伏闻执事性嗜古道,力提儒术,顷岁魁荐庠序,以文受知于故舍人孙公,倡和大义,斥排异端,琅琅正声,铿越前后。当时缙绅之士,万语一意,咸谓有唐韩文公、牛相之欣会,殆无以过。某窃乐其事,是以拂冠振衣,求进左右,执事得不为之留念乎?……近文一编,谨缮写拜赞,伏冀曲示龟鉴,且加绳墨。……可进可退,恭侯严命[20](卷90)。
其二为《上张太傅书》,自述“累遇贡部”,因故“龃龉”,因求张某“掀援之、鼓吹之”,并以“近文十首,随书拜献”,而开篇即大段评文,自周代直至有唐,像是简略的文学批评史提纲(兹以文多不引),然后说“进士程生,近以执事新文数篇见借”,遂赞扬其文“理粹而古,辞简而达,无气艳,无流韵”云云,然后谓“幼从事于文学,酷嗜典实,颇嫉芜颣”云云[20](卷98),全是以文心契合相许。这表明唐及宋初人的行卷投书,确乎存在显著的差异。
如果深入研究,就会明白上述特点或差异不是偶然的,而有着两代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唐人行卷、受卷双方,往往是一笔现实的或“预支”的政治交易。如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所说: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势,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1](卷18)。
举子行卷的目的,固然首先是登第,而所谓“王公大人”为举子制造“誉望”,则是为了蓄积未来的政治力量,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双方“相须”、“相资”的利害关系。唐代举子行卷特盛于中唐之后,是时统治集团内部党派斗争激烈,“王公大人”往往利用掌贡举的权力或荐举的机会,结成“座主门生”及恩私关系,举子一旦登第,即召致幕中,以扩充政治势力。如《旧唐书》卷176《杨虞卿传》:
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
杨虞卿之所以那么卖劲地为举子“驰走”,目的十分明确。而“门生座主”或恩私关系,更是牢不可破,李德裕当时就有“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的激烈批评[15]。入宋,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和朋党为害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连低级官员也由朝廷任命,同时认识到“恩出私门”的危险,于是取消“公荐”(上已述),又实行“御试”,将进士由“座主门生”转移为“天子门生”,如《燕翼诒谋录》卷1所说:“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谟,可谓知所先务矣!”这就是宋初行卷、受卷双方多以文章相知相许,而不再求政治上“相须”、“相资”的根本原因。
这个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宋初的文学发展。
首先,由于宋初行卷双方都定位在“文学”上,举子投书多选择那些与自己文学思想相同、相近的高官或文学名流,而接受投卷者,也借此机会大力栽培文学新人。如柳开、有张景等众多门人,而向他贽文的,多在古文特别是所谓“古道”方面的志同道合者。他所作《与李宗谔秀才书》曰:“数日前,崔秀才袖足下文一轴及《永泰门义井铭》石本一篇见贶,读之竟日,知称咏足下者不为谬矣。足下之文雅而理明白,气和且清,真可贵也。”[8](卷9)《与任唐征书》亦曰:“辱示诗两轴,辞调颇切于古人,……非雄刚峻逸之材,孰能迨此?”[8](卷9)又《送马应昌序》谓马氏“其文近于古,虽不能全似于我,求之于众,亦不易得也。己酉自京而来,以道德文章期于我与其进也,我岂异哉”?[8](卷12)柳开尝见胥偃所作文章,预料他“异日必得名天下”。[21]崔立长于古文,柳开一见奇之,“于公卿间比比延誉”。[22]李迪曾向柳开贽文,开读之,“未尝不称善,语门人张景、高弁曰:‘复古(李迪字)乎,辅相器也,且陶冶生辈矣。’”[23]如此等等。王禹偁曾接受过大量进士行卷,已详前论。他在读了黄宗旦的文章后,称赞他“辞理雅正”,同时也指出所作《正汉臣对策》之一章持论稍过,并说这是“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13](卷18·答黄宗旦第二书)。按黄宗旦字才叔,泉州惠安(今属福建)人,咸平元年(998)登进士甲科,这与王禹偁的指导不无关系。王禹偁贬滁州时,江翊黄“缝掖而见”,其人“好古乐道,趋向不凡”[13](卷20·送江翊黄序)。同时又指出他“文义尚浅,故答之曰:修之不已,则为完人”[13](卷18·再答张扶书)。王禹偁著名的《答张扶书》、《再答张扶书》,虽是对秀才张扶作文难道难晓的批评,但正见其扶植后进的一片诚心,而不是一味廉价地激扬“声誉”。柳、王二人对待行卷的态度,无疑对宋初文学新人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由于宋初行卷盛行,有志于文学革新的作家遂利用荐扬后进的机会,大力鼓吹文学改革,掀起了诗文革新的第一个浪潮。宋初立志文学革新的作家,仍然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柳开早年曾打出“韩柳”的旗帜,大唱古文,但倾向于“道统”。在上王祜四书中,曾对当时以“刻削为工”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臧丙曾向柳开请教,其《答臧丙第一书》谓“吾子遗我之书,辞意皆是也”;又谓“韩愈氏之书,吾子亦常得而观之耳”;“我之书,吾子亦常得而观之耳”[8](卷6)。臧丙除向柳开学习外,又曾师事于古文家王祜,于是由作四六文字,“变格为韩、柳文,颇近阃阈”[13](卷28谏议大夫臧公(丙)墓志铭)。进士高本“学慕韩愈氏为文”,柳开爱其“难得”,作《名系》贻之[8](卷1)。表彰李宪是“真好于韩文者也”[8](卷11·送李宪序)。赞美韩洎所作古文“颇有吏部(韩愈)之梗概”[8](卷9·再与韩洎书)。等等。王禹偁曾批评“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同样高扬“韩柳”的旗帜,并谓孙何“真韩、柳之徒也”[13](卷19·送孙何序)。又《送丁谓序》曰:“其诗效杜子美,深入其间;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13](卷19)又《送谭尧叟序》,谓谭“师轲、雄、韩、柳之作”。王禹偁曾作《赠朱严》诗,其云:“惟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13](卷19)又作《和朱严留别》诗曰:“师仰惟韩愈,才名压李观。”如此等等。这对于扭转当时文风,扩大学韩队伍,引导宋初文学向诗文革新的方向发展,有着“导夫先路”的意义。
再次,由进士行卷,酿成了宋初文坛的派别化趋势。宋白、李昉诗皆宗白居易(注:田锡《寄宋白拾遗》:“严吾侍从臣,元白才名子。”又《杨文公谈苑》(《类说》引):“李昉为诗慕白居易。”《青箱杂记》卷1:“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而曾向他们行卷的田锡、王禹偁都以白体诗著称,王禹偁是宋初三个主要诗派(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中白体诗派的代表诗人。宋初人又喜利用行卷相标榜。如张景《柳开行状》曰:“故大谏范公杲方好古学,少有大名,特爱公文,常口诵于朝野,为公之誉,世因称为‘柳、范’。”又《渑水燕谈录》卷7:“(范杲)好学有文,时称‘高、梁、柳、范’,谓高弁、梁周翰、柳开与杲也。”(注:《宋史·梁周翰传》谓“高”指高锡。按高弁乃柳开门人,辈份较晚,不得与梁、柳、范并称,《渑水燕谈录》当误。)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曰:“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9](卷6)柳开俨然成了“髦俊”们的领袖。王禹偁诗有“二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之句(已见上引),因此文学史上以“孙丁”并称。他又在《东观集序》中提到赉志以没的古文作者李均、郭昱、董淳、颖贽四人,认为“异日国家召史臣修《文苑传》,此数人者不可遗也”[13](卷19),盖四人也是文章“知己”,除李均外,其馀三人已写入《宋史·文苑传》。于是,以柳开、王禹偁为中心,在宋初形成了两个不同倾向的古文派别:柳开讲“道统”,而辞涩言苦;王禹偁倡“文以明心”,主张为文“易道易晓”[13](卷18·答张扶书)。宋代文苑诗坛,已由进士行卷而初露派别森立的端倪。后来虽行卷之风止息,但由此产生的惯性却影响深远: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或相近结派,而不再象唐代那样由政治上的“相须”、“相资”结党。
综上所述,尽管宋初统治者着力抑制包括行卷在内的请托作弊,但事实上进士行卷风之盛,盖并不逊于有唐;只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才使行卷最终成为历史。又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宋初行卷、受卷双方多以文学观点相同而走到一起,遂使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自太祖到真宗景德科举新制颁行,举子行卷的存在,盖不过四十馀年(景德后至仁宗前期的行卷,当多在州郡,或出于习惯,已是尾声),在有宋历史上时间不长,只可看作是具有宋代特色的科举制度形成之前的序曲,加之请托一直为官府所禁止,故行卷不象唐代那样公开和张扬,这是连宋人也不大提起的原因。但一旦认识了宋初行卷的历史事实之后,就为我们研究宋初乃至整个宋代的科举史、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收稿日期]2002-03-11
标签:王禹偁论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论文; 宋朝论文; 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文献通考论文; 青箱杂记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唐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