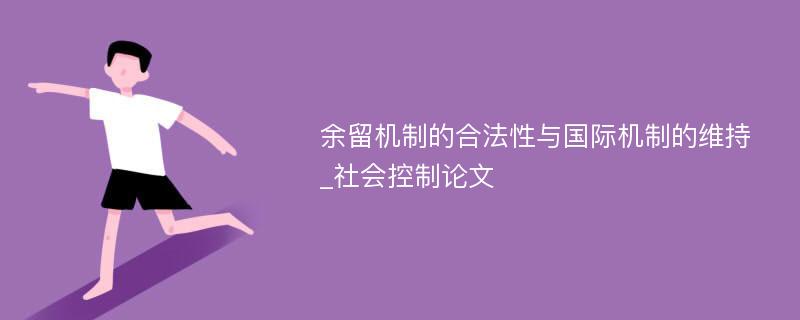
机制合法性与国际机制的维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合法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缺失
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或译作国际体制、国际规制)是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者对某个既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着它们而汇聚(注: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 Ca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n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国际机制可以通过汇聚成员国预期,提供信息,降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来促成国际合作,达到所有成员国的帕累托改进(parato-improvement)(注:[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2001年版,第104-133页。)。因此,国际机制是一种惠及所有成员国的“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在消费过程中,具有排他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vity)。“集体物品”的供给,对于供给者来说,是一种个人受益与集体受益不相平衡的行为。创立国际机制是一种费用高昂的“集体物品”的供给行为,只有经济和政治实力占压倒性优势的霸权国(hegemon)才有积极性提供这种“集体物品”,供所有成员共同消费(注:“大户”对“集体物品”的供给积极性和“小户”的逃避倾向,可以通过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来理解,关于“智猪博弈”可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因此,霸权国的出现,是国际机制创立的必要条件,否则,“集体物品”就会出现供给不足,“国际政治市场”就会失灵。但是,国际机制一旦创立,维持一项国际机制比创立这项国际机制远为容易。只要国际机制的治理绩效能够带来所有成员国的帕累托改进,维持这项国际机制就是一种不论对个体还是集体均为理性的迭抒。因而,即使是霸权国实力有所衰落,但只要其供给能力仍然相对优于其他成员国,衰落的霸权国就仍然有积极性维持这项国际机制,继续承担维持国机制的成本,由于“小户国”的“搭便车”行为而引起的“国际政治市场失灵”也不会发生(注:这是一种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sunk cost)的解释,见[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22-125页。)。所以,国际机制成员国之间的适度权力差距和可以保证足够获益前景的国际机制治理绩效,决定着该项国际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权力分配过度均质化,会使“集体物品”的供给出现困难,国际机制的治理绩效过低,会减少“大户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收益,使“大户国”对国际机制的维护不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经济学逻辑虽然对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战后由美国领导创建的国际机制,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后,仍然保持稳定的现象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基欧汉对“大户国”(美国)护持上述国际机制,保持国际机制稳定的费用,即国际机制维持(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一“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cost of providing collective goods)问题却没有作出充分的分析。显然,“生产成本”是影响维持过程难易程度和维持行动积极性的关键变量,对之避而不谈不能全面地解释和理解国际机制如何能维持,怎样能维持?
国际机制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roles of game),属于规则、制度的范畴。制度具有共同的属性,要弄清维持国际机制的“生产成本”可以通过类比国内制度(规则)的维持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大多数国内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持者都是政府,这种“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即政府维持一种国内制度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权能、制度的绩效和制度的合法性。一项制度要得以延续和稳定,高度的运作绩效和强有力的维护者当属必要,但制度输入过程和制度输出结果是否能够赢得政治系统中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也直接决定着制度的生命力。比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推行的各种制度,既受到英国政府的积极维护,又大大改善了印度的经济福利,但却因其殖民主义的象征意义,在强烈的反抗声中遭到废弃。
可见,将制度的延续与稳定的解释变量,困囿于权力配置结构和制度治理绩效是不够全面的,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机制也有十分类似的现象。“大户国”的积极护持和国际机制本身的治理绩效,是国际机制生命力的两大源泉。但“大户国”的维持成本同样和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即使是在国际机制绩效(regime performance)未受损害,霸权国权势没有明显衰落的情况下,国际机制成员国的不接受或不认同也足以瓦解国际机制。
二、国际机制与社会控制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中,行为体是否稳定、持续地遵守一项规则,会出于三种不同的理由或多种理由的组合:(1)因为行为体害怕规则执行者的惩罚;(2)因为行为体明确地知道遵守规则完全合乎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3)因为行为者内在地感知到这项规则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应该遵守。这正是社会控制的三种方式:强制(coercion)、自我利益(self-interest)和合法性(legitimacy)(注:关于三种社会控制方式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360页。)。
强制的发生基础是行为体之间不对称分布的物质权力,强势行为体能够改变弱势行为者的行为方向,强势行为者可以借助其掌控的权力推行某种规则,强迫弱势行为体遵守。弱势行为体如果不遵守这项规则,将会确切无疑地遭到强势行为体的惩罚。为避免因不遵守规则遭受惩罚而付出额外的代价,弱势行为者会出于畏惧而遵守在它看来并不正当(illegitimate)的规则,在政治生活中,强制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控制作用,但是,一个单纯依赖强制而运转的社会系统,必然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监控、惩罚和威慑其社会成员遵守这种强制性规则,一旦强势集团的权势有所衰落,其社会成员的违规行为就会大量出现并导致强制性规则的崩溃。
自我利益是一种在没有最高权威或强势行为体强力推行的情况下,也能发生作用的社会控制方式。如果遵守规则比不遵守规则能够为所有身处其中的行为体所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那么行为体就会自发地遵守规则。也就是说,行为体通过严格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认识到遵守规则可以为自身带来更多的收益,而不遵守规则却失去获利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创建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对所有理性的行为体都有吸引力的激励结构,制度维护的关键就是如何使制度激励结构与变化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相互适应。基欧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把国际机制维持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权力差距和机制绩效,其逻辑起点正是立基干自我利益的社会控制方式。
强制和自我利益两种社会控制方式都是理性主义的社会控制方式。与这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相比较,合法性是一种不依赖个体理性而发生作用的社会控制方式。它“是一种有关社会实体行为在一些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仰和释义系统中正当、适宜和合宜的总体化的认知和判定”(注:Mark Suchman,"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0,NO.3,Jul,1995,p.574.)。合法性社会控制的发生机理是外在的规则被行为体内化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由此决定的利益构成之中(注:利益与自我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我利益出自理性主义的逻辑范式,而利益则是一个有其社会背景的概念。简单地说,个体的社会身份决定个体利益。建构主义学者将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指出了国家利益的社会性质。参见[美]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1-302页。)。换言之,行为体的行为选择并不单纯地由物质性的自我利益所支配,身份再造和利益实现的内在需要也是其遵守规则的一大动力。规则的合法性被行为体内化到一定程度,将意味着一种独立于被迫遵守和自我利益驱使的内在力量推动行为体自愿、惯常地遵守规则。
作为一种依靠行为体的自愿和忠诚而发生的社会控制方式,合法性在减少社会控制的成本,节约社会控制所消耗的资源上远远优胜于强制和自我利益。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不仅比纯粹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者用最低的政治资源进行管理。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合法性对于所有的社会控制并非必不可少,但是缺少合法性将给控制者带来极其沉重的维持成本,因为合法性为需要热忱、忠诚、分散决策、自行决断和审慎判决的组织运行减少困难”(注:Robert Daul and Charles Lindblom,Politics,Markets and Welfare,New Bre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p.115.)。
同样,国际机制的合法性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即可以降低国际机制维持这一“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因为强制、自我利益和合法性三种社会控制方式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一项国际机制欠缺合法性,大多数成员国都内在地认定这项国际机制并不是足够的“正确”和“合宜”。这样,国际机制的维持就只能凭藉强制和自我利益,而这两种方式都需要投入必需的资源来发生作用,“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也就必然因此而升高。相反,合法的国际机制更能凝聚成员国的信任和忠诚,从而减少控制资源的投入,降低“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此外,对合法性基础薄弱的国际机制的遵守,会给遵守国带来影响其形象和地位的“社会成本”。而对具备较强合法性的国际机制的遵守,则会为遵守国赢得提高其威望和形象的“社会收益”(注:“社会收益”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的改善和威望的提高,“社会成本”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良影响的产生或增加,二者会分别对国家参与或遵守国际机制产生推动和阻碍的影响。参见[加拿大]江忆恩:《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24—26页。)。前一类机制的成员国可能因“社会成本”的增加而放弃对机制的遵守,为保持机制的稳定,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监督和控制成员国的遵守行为,这将提高国际机制的维持成本。后一类机制的成员国面对丰厚的“社会收益”,即使是在物质性收益和选择性激励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可能倾向于遵守国际机制,监督和控制的费用也就因此而降低。所以,具备较强合法性的国际机制的维持成本低于合法性基础薄弱的国际机制。
三、国内社会的制度层级结构
合法性有助于降低维持国际机制的维持成本。那么,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来源何在呢?要弄清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对国内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作一个系统的考察。制度合法性的来源可以是制度的效率。行为体对某种制度的忠诚可以部分地归因于由制度运行带来的现实的或可以预见的福利。同时,行为体没有发现和预期发现更有效率的替代性制度,又能够强化制度的合法性。
制度效率是制度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但却不是惟一的组成要素,制度效率并不是制度合法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民族国家体制,虽然不能满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社会功能性需要,但却能保持良好的政治合法性根基⑩。这从经验上说明,在制度的效率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方面的制度合法性来源。
合法性是一种依靠自愿和忠诚而发生作用的社会控制方式。对于内在地接受制度合法性的行为体来说,忠诚的理由可以类比为一种意识形态。按照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接触,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注:[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页。诺思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许多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因此,发展出一套整合进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是非常必要的。)意识形态可以简化决策过程,它帮助个体进行合宜性行为的评判。同样地,合法性的作用就类似于一种群体性的、共识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合法性要取得内化的共识性的地位,需要一个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之间的合理的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并通过合理的交往取得理解和一致的动态的过程来实现。哈贝马斯认为,合理的交往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可能发生。“生活世界”是合理的交往行为得以进行的界面。“它构成包含着一组社会成员皆视为当然的有关世界、社会等事物的共同的基本信念,以及得到普遍接受的解释,它们促进并形成了构成交往行为的取得理解和一致的过程。”(注:[英]迈克尔·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4页.关于该理论的全面论述,可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生活世界”在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对世界的神秘主义的理解上,即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上。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平台被拉向了理性和公正等基本元价值(meta-value)上(注:[英]迈克尔·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第336页。)。自此,共识从合理的交往行为中产生,又通过合理的交往行为不断地再生。所以,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制度合法性的来源其一为公正和理性支撑的“生活世界”的构造性(generative)元价值,其二为由合理的交往行为形成的衍生性(constructed)社会共识。
构造性元价值和衍生性社会共识,均属于社会共有观念,在社会制度系统中共处在制度系统的最高层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制度服务于其目标并不是靠单独地得到遵守,而是靠其形成相互支持的现象系统[1](P162)。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内,这种相互关联的制度系统构成一种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制度层级结构,国内社会制度中直接指导、约束社会个体行为与互动的是法律细则,行政规章以及在法律框架下达成的私人协议。法律细则、行政规章作为成文法的细化和具体化,依据成文法制订和解释。成文法的母体(generator)则是宪法性规则,而宪法性规则又是社会共有观念的外在体现,内化的抽象性质的社会共有观念统领制度系统中的所有社会制度,是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所有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来源(注:关于国内制度的层级结构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62—167页。)。
社会共有观念不仅从价值上规导各种社会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构成社会制度的价值合法性来源,而且决定着制度生成和制度修正所应当遵循的程序和原则。也即是说,社会共有观念造就和规定着关于制度生成和修正的程序正义原则。高层级的社会制度自我修正的程序要求,受到社会共有观念中程序正义原则的约束。高层级的社会制度形成和阐释低层级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也受到程序正义原则的制约。社会制度的生成和修正程序脱离程序正义原则的内生要求,必然贬损其合法性基础。这种与特定社会系统的共有观念相伴而生的程序正义原则是国内制度的程序合法性(legitimacy of procedure)来源。
四、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来源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制度效率是制度合法性的一大来源,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靠高效的运转来维系成员国的信任和忠诚。低效、无力的国际机制会因成员国的不信任导致违规行为的不可遏止地增加,直至国际机制最终陷入瘫痪。效率固然可以为国际机制打造一个“合法的形象”。但有效率的国际机制并不一定就是足够合法的国际机制。现代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国内社会的制度层级结构。国际社会制度层级结构的最高层级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
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在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看来,数千年以来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转变。(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而事实上,从观念结构考量,国际社会呈现出霍布斯文化体系、洛克文化社会和康德文化社会三种相互区别的理想形态。在霍布斯文化体系中,国家相互之间以敌人来界定对方的角色。这种敌对的主体角色结构意味着,国家互不承认对方和自我的生存权利。在这个完全自助的体系中,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无从发生,社会共有观念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洛克文化的主体角色结构是竞争,而不是敌对。“竞争对手期望相互行为的基础是承认主权、‘生命’和‘自由’是对方的权利,因此不会试图征服或统治对方”。洛克文化并没有消解国家行使暴力的权利,但“战争不会夺取国家的生命,征服性战争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也会由集体行动来恢复原状”。在洛克文化社会中,国家之间对主权的相互承认,赋予了国家,即便是弱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活动和交往的个体性条件(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文化分别代表敌对、竞争和友好三种主体角色结构。详细论述请参见[美]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3-397页。)。这种个体性条件构成了交往行为所必需的基本先决条件,它为“生活世界”的平台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主权制度在现代国际社会的稳固确立,使洛克社会的文化逻辑发生作用,也使国家之间的合理的交往行为具备了基本的个体性条件。另一方面,各种单个国家所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的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又使国家间的合理的交往行为具备了共同的信仰基础。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迫切地需要世界各国对自己生存的环境、条件、危机和未来命运负起责任,实行通力合作。因为,全球公共问题带给人类的灾难,“不仅是指空间意义上的全球困境,更是指构成人类共同体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所面临的生存威胁”[2](P140)。正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一起工作,使用集体的力量之外,别无它择”[3](P18-19)。全球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使国家之间的“全球整体性意识”和“共同命运感”大大加强,而这一“整体性意识”和“共同命运感”又成为了一组国际社会诸成员皆视为当然的有关世界、社会等事物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就为国家之间合理的交往行为创造了赖以发生的“生活世界”。
于是,国家之间合理的交往行为得以围绕“生活世界”的平台而展开。各种构造性共识和作为国家之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产物的衍生性共识(注:非政府组织等沟通行为体(linkage agent)的日益活跃,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国家间合理的交往行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的论述,请参见Thomas Risse,"'let' s Argue!':Communicatiive Action un World Politics",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1,Win.2000,pp.1-39.),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即基础性的国际制度(foundational institutions)(注:这里借鉴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克雷斯蒂安·勒—-斯密特的观点,参见Christian Reu-Smit:"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Autumn,1997,pp.555-589.下文将要提到的基本性国际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s)也出自该文。)。基础性的国际制度以公正、合理地治理和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为精神实质,以实现、维持和促进和平,建设和改进世界秩序为根本目的。这一主导性的共有观念处在国际社会制度层级结构的第一层级,其意义在于提供一个补充已有的国际制度的常在源泉,和判断这些国际制度是否合乎正义和理性的准绳。因此,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是包括国际机制在内的所有国际制度的价值合法性来源。
第二层级的国际制度是国际法,国际惯例等基本性的国际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s)。国际社会的主导性社会共有观念是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建构的结构性基础。在国际法的各种解释之间出现冲突时,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是最后的作出合法性裁定的诉求对象。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承接最高层级的国际制度,同时引导和约束下一层级的国际制度——具体问题领域国际机制的形式和内容。比如,许多传统的旨在管理生物资源(living resources)的消费和使用的保护机制(conservation regime),在国际社会对生物栖息地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观念环境下逐渐废止,并被新的以可持续使用生物资源为目的的国际机制所取代(注:Oran Young,Governance in World Affai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114.)。重新建立的国际机制,体现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主导性共有观念,也体现了相关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塑造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价值合法性。
国际机制的价值合法性植根于国家间合理的交往行为所形成的主导性社会共有观念。程序合法性则来源于洛克文化社会的结构属性。在以洛克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国际社会,国家主权是受到所有国家内在地接受和认可的,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中的任何国家都是对等的实体。主权,即是一种“财产权利”,是对国家可以排他地使用其内部资源权利的共同承认,尊重这种“财产权利”,就需要各国以自由、自愿的契约来解决共同问题。因此,洛克文化社会的文化逻辑内生地决定了主权对等(sovereign reciprocity)和自由契约(liberalcontract)两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程序正义原则,引导国际机制的内部决策和自我修正。
程序正义原则是国际机制的程序合法性来源。在现代国际社会,在主权对等原则和自由契约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机制内部决策和自我修正程序所必须尊重的程序正义原则。作为程序正义原则的多边主义已不简单地是一种制度设计方式,“它更多地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应该在全球的基础上或至少在一个相关的团体之间组织起来,这种信仰也许在存在的意义上是对世界如何运作的诉求,或者在规范的意义上是关于任何事务应该以特定的方式来做”(注:James Caporaso: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in John 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n Interna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54-55.)。正是因为多边主义是一种对维持国际机制具有重要作用的程序合法性资源,所以尽管许多为克服“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而创建的国际机制,单纯从制度效率方面来说少边形式优于多边形式,但实际情况却是它们大多部采取了多边形式[4](P240)。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并非静止不变。它内含有一种随主权国家间的交往行为而可演化,可递嬗的衍生性社会共识。因此,国际机制的合法性也会随主导型共有观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项国际机制在其创建时期具备契合主导性共有观念的价值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而一旦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发生转变或出现转变的趋势。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就会有所动摇,陷入一种危及机制稳定的“合法性危机”,处于“合法性危机”的国际机制走出困境的方法就只能是对机制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使之与转变后的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相适应。相反地,一项国际机制在其创建之时可能面临合法性欠缺的困境而难以维持,而主导性共有观念的转变却使其摆脱困境,稳定而有效地实现“没有政府的治理”。针对捕鲸问题的国际机制的遵守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大幅上升,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注:Oran Young,Governance in World Affairs,1999,p.114.)。
五、结语
国内社会具有一套严整而有机的制度层级结构。居于最高层级的社会共有观念是所有社会制度的价值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来源。价值合法和程序合法的制度可以用低成本的方式持续、稳定地维护社会秩序。霍布斯国际体系是一个以敌人相互认知的自助体系,国家之间“完全的敌意”(sheer hostility)阻碍了合理的交往行为(注:严格地说,它只能称作国际体系。而不是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概念出自英国学派。他们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不止构成了一个体系,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起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详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362-388页。)。洛克文化国际社会的文化逻辑,以及全球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所带来的“全球整体性意识”和“共同命运感”的加强,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之间创造了合理的交往行为所赖以发生的“生活世界”。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得以形成和演化,它是各个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的价值合法性来源。现代国际社会的程序正义原则由洛克文化社会的结构属性内生决定,它是国际机制的程序合法性来源。
国际机制是现代国际社会的特有景观(注:参见陈玉刚:“循环反复…势力均衡…制度合作——国际体系的三大历史景观”,载徐以骅、蒋昌建主编:《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国际机制正常运行产生的制度合作效应可以带来所有成员国的帕累托改进。因此,维持国际机制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欠合法的国际机制的维持费用是相当高昂的。对于国内制度,已有经验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形成自发性服从,政府靠强制在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执行全部法律规范的3%—7%(注:[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67页。)。国际机制要实现自身的稳定,立足于成员国的物质性的自我利益的制度设计当属必要。但即使国际机制的激励结构能够满足成员国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国际机制的稳定和治理绩效的保持也可能因合法性欠缺所造成的控制成本过高而大受影响。
机制合法性有助于降低维持国际机制的“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又有助于解决国际机制维持这一“集体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霸权国的衰落并不必然带来霸权护持下的国际机制的衰败。只要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将其维持成本降低到一个适宜的水平,国际机制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得以维持,为其成员国带来持续而稳定的合作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