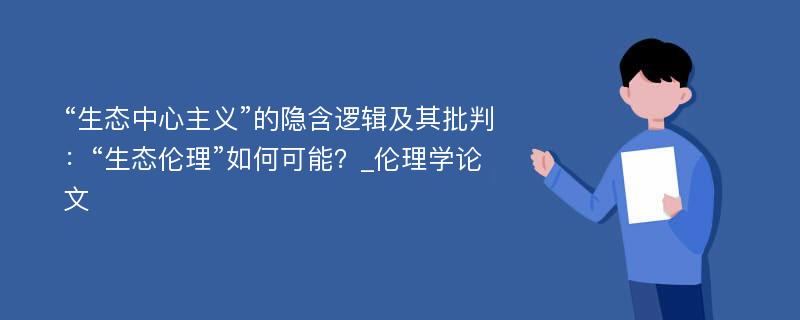
“生态中心主义”的隐性逻辑及其批判——“生态伦理学”如何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伦理学论文,隐性论文,逻辑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5)03-0011-04
费尔巴哈说过,任何哲学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预设作为自身的本体论之“根”。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特别是生态中心主义——同样如此。无论是利奥波德的 “大地伦理学”,还是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抑或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它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预设,这就是“伦理学等于生态学”或“生态学等于伦理学”。 这个逻辑预设的展开与生态学最新研究成果(自然的系统性、先在性、自组织性、复杂 性)的阐发是同一个过程。正如温克勒(E.Winkler)所说:“哲学家们对生态学研究的对 象(即人类和非人类个体、物种、生态系统及整个自然界)各自所有和所处的道德地位问 题各持己见。不过,他们对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即人类与生态规律的联合已成为头条戒 律:生态学是一种伦理学。”[1]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 自然的系统性:伦理学就是生态学
生态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克莱门茨的“巅峰群落”模型和坦斯利的生物群落模 型,说明自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关联”是它最明显的特征。生态中心主义正是 从自然的系统性维度出发而完成它的“伦理拓展主义”的。其逻辑进路是:既然人与自 然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关联就是自然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学关联, 伦理学本身就是生态学了。对此,我们可以以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为证。
奈斯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由各种事物或要素相互连接而成的“无缝之网”,人与非人 类都只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正是这些“纽结”构成了生物圈之“网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深层生态学的中心直觉是,在存在的领域中没有严格的本体论 划分。换言之,世界根本不是分为各自独立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 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分界线,而所有的整体是由它们的关系组成的。……只要我们 看到了界线,我们就没有深层生态意识。”[2]既然人与自然在事实上是相互关联的, 因而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在伦理上也就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生物通过自我的扩大而 亲密相连,伴随这种亲密,就产生了‘认同’的能力,并且作为一种自然结果,也就产 生了非暴力的做法。无需道德,就如同我们无需道德来让我们呼吸一样。”[3]这里, “无需道德”的言外之意不是说要道德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是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 本身就是道德,生态事实的关联就直接意味着伦理学意义上的互助与共生,意味着要实 现我的“好”就必然带动你的“好”与他的“好”的伦理学品质,意味着个体自我的实 现就是“生态自我”即“大地共同体”的实现,包括与小写的“自我”相关联的“本我 ”、他人、鲸、灰熊、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高山河流、土壤中的微生物,等等 。正是生态系统的“关联”决定了生态个体必须不断地扩大自我认同的对象范围,必须 通过否定狭隘的自我来肯定自身存在的意义,通过对对象的关怀而直观自身、确证自己 的本质力量。因此,说白了,生态系统的本质规定——关联——不只是事实与事实之间 的关联,还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生态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联;“生态自我”的自 我实现也不是孤立的价值实现,而是生态学的伦理学转向的实现或伦理学的生态学转向 的实现。奈斯之所以把他的环境伦理学直接命名为“深层生态学”而不是“深层生态伦 理学”,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生态学与伦理学是直接同一的;如果在“深层生态学 ”的名称中间再插入“伦理”二字,那就无异于画蛇添足。
可见,“生态学-关联-伦理学”,这就是奈斯理论的逻辑进路。正是通过“关联”的 中介,“自然主义谬误”这个“休谟难题”便被生态中心主义者们轻而易举地化解,自 然便以一名“平等成员”的角色走入了环境伦理学“大家庭”,“伦理拓展主义”就此 宣告完成。
二 自然的复杂性:生态学就是伦理学
在20世纪60、70年代,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生物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彼此相得益彰 的,因为当一个生物群落的复杂性高时,这个群落内部就存在一个较强大的反馈系统, 对环境的变化和群落内部某些种群的波动,就会有较大的缓冲能力;如果其中的一条能 量流通途径受到干扰或堵塞不通,群落就可能提供其他途径加以补偿。据此,生态中心 主义认为,既然生态学告诉我们自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而复杂性就意味着稳定 性,稳定性就意味着和谐与美丽,就等于价值,因此,生态学就意味着伦理学。关于这 一点,我们可以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为证。
利奥波德认为,生物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有限的认识 能力根本不能通达无限的复杂性事实。他说:“今天,普通的公民都认为,科学知道是 什么在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但科学家始终确信它不知道。科学家懂得,生物系统是如此 复杂,以致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了解它的活动情况。”[4]所以,对于复杂性的生物, 人们要做的不是去认识它,而是去欣赏和保护它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和谐、稳定和美丽。 所谓“和谐”,是指这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复杂——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谓“稳 定”,则是土地的完好无损——维持生物链的复杂结构,以便其能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 更新的作用;所谓“美丽”,则是伦理上的动力——不要仅着眼于经济,还要从更高的 价值观去看问题;和谐、稳定和美丽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在《沙乡年鉴》中,利奥 波德以一种抒情的文学手法和华丽的词藻,按照一年四季的时间顺序,生动地描述了一 个普通农场自然生态的复杂与美丽。从一月份的“冰雪融化”到十二月的“雪山的松树 ”,展现给人们的自然图景是:既有为争夺生存权利的搏斗,也有为维持共同体的和谐 而做出的配合与让步。那些平时被普通人所忽视的自然之美,通过作者深邃的眼睛和富 有鉴赏力的耳朵而变得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如八月里葱翠的荸荠草、倾巢出动的田鼠 、绿毯上漫步的小鹿,等等。据此,利奥波德认为,荒野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拥 有象征价值、审美价值、维护生态稳定的价值。以往人类只从经济学的单向度眼光审视 沼泽的做法是片面的,它不懂得“这些沼泽的最终价值是荒野”。[5]因此,荒野的保 护仅依靠政府行为是永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要转变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把人降格 为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 ,或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大地’。”
可见,“生态学-复杂性-伦理学”,这就是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本体论证明”。 这样,生态学的复杂性之“事实”就意味着价值,就意味着伦理学之“应该”;反之, 伦理学之“应该”也就意味着尊重并保护生态学之“复杂”。通过自然的复杂性之中介 ,生态学就逻辑地推理出了伦理学,简言之,生态学就意味着伦理学。
三 自然的先在性:伦理学属于生态学
生态中心主义的一个价值目标是要祛魅人的主体性,把人还原为自然,因此,它尤其 重视自然的先在性,认为,人所生存于其上的地球只不过是宇宙200亿年来自我演化的 产物,而人又只是地球漫长进化的作品,因而,人是从属于自然的,或直接就是自然本 身;又既然人是属于自然的,那么,属人性的价值范畴就更属于自然、属于生态,也就 是说,价值属于生态事实,伦理学之“应该”也就属于生态学之“是”,伦理学就属于 生态学。这就是罗尔斯顿“价值走向荒野”的逻辑进路。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解读他的 《环境伦理学》而获得证明。
罗尔斯顿认为,地球生态学所揭示的自然的先在性表明,人的产生只是生物进化史上 一个较晚的事件,人类是一个后来者,无论是从人的生理结构还是从他的组织构造看, 他与动物都是直接同一的,“他”和“它”是没有分别的,都服从于自身的物理化学规 律。“如果我们将自然定义为一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总和,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把 人类的能动行为也包含在自然之内。人类动物与其他一切动物一样,都受制于迄今所发 现的所有的自然规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自然规律都在我们身心里起作用。” [6]这就是说,人的生理结构并不比其它非人类的生物特殊,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既然自然的先在性告诉我们人是一个后来者,是自然的生成物,那么,与其说价值是 属人的,是人后天的约定俗成,还不如说它是先在的,是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大自然 是一个完善的进化系统,相比之下,人类却只是一个后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 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价值负载物。”[7]正因为自然界先 天就具有价值,因此,作为母亲,她才把这个财产传承给了自己的子孙——人类。“生 命的出现只不过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假如大自然没有赋予我们任何价值,那么,我们怎 么能够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物而存在呢?”[8]因此,罗尔斯顿断言,人类中心主义把 价值视为人的专利,这在发生学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价值不是人类主观精神的产物, 价值评价也不以人类主体的需要程度为参照,而是先在的、客观的、自然界所固有的; 作为解释这一事实的生态学描述也是优先于人类后天的伦理学规定的,是前者统摄后者 而不是相反。“生态学的描述在逻辑上先于生态系统的评价,前者产生后者。……生态 学描述发现了统一性、和谐、相互依赖、稳定性等等,这些都是在价值上被认可的。… …生态学的描述并不是仅仅肯定了这些价值,而是形成了它们。秩序、和谐、稳定的经 验内容既是给予自然的,也是从自然推导出来的。”[9]
可见,“生态学-先在性-伦理学”,这就是“环境伦理学”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 生态学不仅是事实描述,而且本身就是对价值的解释和规定,也是伦理学之“应该”的 价值向度。这样,与人直接就是自然的观点相对应,伦理学直接就属于生态学,是生态 学的一部分。
四 自然的自组织性:生态学等于伦理学
自然的自组织性一直是生态中心主义所青睐的一个强有力的立论依据。生态中心主义 认为,生态学所揭示的自然的自组织性说明,自然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塑造、自我确 证的独立自存的生态系统;人就是自然“创生性”的产物;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存在 为前提,相反,人的存在倒要以自然的存在为本根。因此,自然的自组织性决定了自然 本身就具有价值评价与判断的能力,并不需要人类的主体性参与。说到底,生态学能够 “自组织”为伦理学。这一结论,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分析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而 作出。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界自己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或不利,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目的和 欲望。他以处于“生物金字塔”低层的植物为例,说明生物具有自我修复、自我保护、 自我评价的价值判断能力。“植物不是主体,但也不像石头那样只是一个没有活性的客 体。它们不是有中枢神经控制的高度统合的有机体,但它们却是建模生物体,只要有空 间和资源,其分生组织就能不断地重复产生新的生长模(新的节与叶),以及新的繁殖模 (果实与种子)。它们能够繁殖;能修复其所受的创伤;能制造丹宁酸和其他毒素,并调 节其浓度,以保护自己少受草食动物的侵害;能制造花蜜以影响传粉昆虫的行为;能释 放外激素,以影响其他植物的反应;能释放植化相克素以抑制侵入其领地者;还能排斥 遗传物质与其不相合的嫁接物。植物与任何其他有感觉或无感觉的生物体一样,都是一 个自发的、自我维持的系统。它体内有着一种信息,能保存植物的同一性。”[10]据此 ,罗尔斯顿认为,创生性是自然共同体具有内在价值的事实根据;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 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荒野,也不是自在的、堕落的和没有价值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美 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自然系统的自组织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 ,就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而言,都是有价值的;生态自然的自组织性事实就是属人 性的价值本身,自组织性的过程就是价值的实现与彰显过程,因而也就应该得到人们的 尊重与呵护。“我们只要拂去了盖在‘事实’上的灰尘,那里的‘价值’似乎就会自然 而然地显现出来。从‘是’到‘应该’是一个瓜熟蒂落的价值飞跃。”[11]
可见,“生态学-自组织性-伦理学”,这就是罗尔斯顿生态学向伦理学的质的“飞跃 ”。这个“飞跃”不需要中介,或者说,它直接就是自然“自组织”而成。因此,如果 说利奥波德与奈斯还算是以理服人的谦谦君子的话,那么,罗尔斯顿则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独断主义者。在他看来,生态学关于自组织性的事实描述就是对伦理学之“应该”的 充分说明,简言之,生态学就等于伦理学。
五 生态学与伦理学:两个异质性的范畴
“生态学就是伦理学”,这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一条隐性逻辑,也是连接其本体论、认 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一条逻辑主线。这条主线抹煞了生态学与伦理学的学科界限, 混淆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本质区别,具有很强的独断论色彩。
生态学是运用分类技术、野外观察、室外或室内试验等自然科学或数学的方法,对自 然有机体之间以及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揭示生态系统自组织过程的 动态平衡规律,为人们认识自然之“他律”而更好地改造自然服务的科学;它是一种关 于生态事实真假的判断,是一种认知意识或理论理性,是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其本质 特征是自然性、自在性、客观性。而伦理学是运用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理 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揭示人类社会道德关系发 展的规律,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更快地促进生产力服务的学问;它是一种关 于行为是否“应该”的判断,是一种实践意识或实践理性,是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其本 质特征是自为性、属人性、主体性。可见,生态学与伦理学、科学与哲学分别属于两种 范式、两种场域:前者属于理论理性,后者属于价值理性。生态学向伦理学的转化过程 至少包括三个方面:①从自然的自在性向社会的自为性转化;②从客观性标准向功利性 标准转化;③从一元性原则向多元性向度的转化。因此,在生态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一 个巨大的从认识论向价值论的跃迁。“是”与“应该”之间的鸿沟决定了生态学知识— —即使是正确的——最多只能算是黑格尔的“不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 真理”,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真理就是有利于人们通过实践的中介实现自身 价值目标的不错的知识;功利性或价值性关联是真理区别于不错的本质特征。例如,“ 这朵花是红色的”就是典型的“不错”而不是真理(这是前些年哲学界经过争论而达成 的共识),因为它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性描述,对人类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性的意义与价 值。环境伦理学所青睐的生态学最新研究成果,都只是符合自然事实的“不错”而已; 只要它不与人们的实践活动挂起钩来,进而通过实践与人的价值目标联系起来,那么, 它就永远只能是“不错”而不是真理,生态学与伦理学也就不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只有当事实判断与主体需要欲望目的发生关系时,从事实判断才能产生出和推导出价值 判断。这样,价值判断便是通过主体判断和事实与主体的关系判断而从一个事实判断中 推导出来的。”[12]“不错”与真理、生态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界限正是由 自然物与人、自然与社会、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界限所决定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与伦理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有联系 的,强调二者的区别就是对这一“联系”的形而上学肢解。
诚然,生态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事实上的联系,对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里说过:“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 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 互制约。”[13]但是,必须指出的是:①马克思这里的“相互制约”正是以自然史和人 类史的相互区别为前提的,因为,“联系”总是两个互相区别、各自独立的实体之间的 联系;如果二者就是不分彼此的完全同一,那么,马克思就完全没必要在这里使用“彼 此”二字,也完全没必要大谈它们的有机联系,否则便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②马 克思这里的“互相制约”是以“只要有人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而人是什么呢?在马克 思看来,人不是别的,人就是实践(马克思有时候称之为“工业”)本身;换句话说,人 是实践的人,实践是人的实践。正因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也 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实践不仅引起了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而且 也引起了自然科学的哲学化或哲学的自然科学化。“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 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 。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 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 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4]如果没有实践的“中介”作 用,那么,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就只能是僵死的、无声的数字或文字砖块。“如果没 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 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至于说生活有 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15]只有穿过实践的桥 梁,从自然的“彼岸世界”来到社会的“此岸世界”,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才能得到整合与融通;自然科学往后才“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 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这样,通过实践的“中介”,人的自然 性和自然的社会性、自然史和人类史才得以“相互制约”和“彼此”联系起来,出现在 人们面前的才不但是“自然的社会”,而且是“社会的自然”;历史才是“自然的历史 ”,自然也才是“历史的自然”。可见,生态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 与统一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生态学不是伦理学,只有与实践联系起来,生态学的“ 生态”与伦理学的“伦理”才能挂起钩来,一句话,生态伦理学才能成为现实的科学。
生态学,无论其发现多么科学、数据多么翔实、描述多么精确,它始终是一门具体的 自然科学,与伦理学永远都是两个异质性的概念。尽管,从哲学史和科学史交叉与融通 的历史走向看,自然科学与哲学是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两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科学就是哲学或哲学就是科学的结论,相应地,我们也就 不能推出生态学就是伦理学的逻辑命题。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过导师肖玲教授和林德宏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收稿日期:2004-12-08
标签:伦理学论文;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 生态科学论文; 生态系统稳定性论文; 伦理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科学论文; 自组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