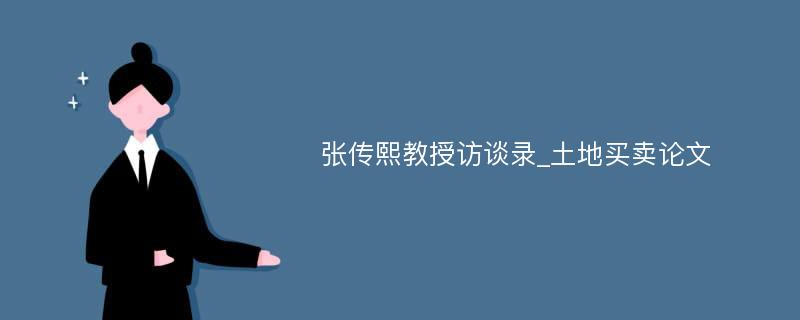
张传玺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张传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2月22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给北京披上了素洁的盛装。我们踏着瑞雪,来到蓝旗营小区,访问了著名历史学家张传玺教授。张教授1927年生于山东日照,1946年7月考入青岛山东大学先修班,次年升入中文系本科,后又转入历史系学习。1951年1月,任私立青岛文德女子中学政治教员,次年该校由政府接管,改名山东省立青岛第八中学,任副教导主任。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攻读秦汉史专业。1961年1月毕业留校,任翦伯赞的助手。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北京市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学术顾问;教育部全国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学科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各类成人高考统一招生考试大纲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兼历史学科组组长;香港珠海书院、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史纲》、《简明中国古代史》、《秦汉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翦伯赞传》以及合著多种,论文200余篇。张教授在书房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中,始终精神饱满,谈吐儒雅,将学术生涯和治学体会娓娓道出,让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
问:张教授,您作为非常有成就的史学家,请先谈谈是怎样走上研究历史学道路的,相信您的成长道路和人生经历,会给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一些教益。
我的学术成就,比较其他同志,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就谈一谈我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吧。
按照过去的基础,解放以前我是上中文系的。由于搞学生运动的关系,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需要学习社会发展史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实际,这就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在向历史学方面靠拢。当时,我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陶大镛的《新民主国家论》,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等,理论著作对我的影响很大。历史著作方面,我读过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印象也很深。1949年6月青岛解放,山东大学成立了历史系,于是我就转入历史系学习。1951年1月,我被派到美国办的教会学校私立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政治教员。因为对历史有感情,就常读历史书,也比较关心史学动态。曾经写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岳飞为什么是民族英雄》,当时国内史学界对岳飞的评价观点不一致,包括艾思奇在内,评价都比较偏激。那时《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副刊归北师大管,白寿彝先生是责编。文章写好后,寄给白先生,他在1951年9月26日的“历史教学”版上发表了。12月,我写了一篇《评宋(云彬)著〈高中本国近代史〉》的论文,寄给白先生,白先生于这月29日又在该刊上发表出来。白先生对于晚辈的提携,我是十分感激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更加激起了我对历史学的兴趣。1952年春,私立文德女子中学由政府接管,改名青岛第八中学,我任副教导主任,分工负责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非常繁忙。尽管如此,我对历史的兴趣仍然不减。1954年,我写了《项羽论评》一文,由山东大学《文史哲》于这年的第10期发表。次年春写成《胡适的反动历史观批判》一文,由《青岛盟讯》于5月20日发表。
1955年冬天,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第二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翦伯赞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幸蒙录取,学制四年。就这样,我离开青岛到了北京。
翦老是有名的史学家,见面后对我的学习提出了三点指示:一是理论方面,要读马列主义著作。给我开了一个书单,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还有《马恩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主要偏重于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史料方面,要认真阅读。文献中的前四史必须要读,《资治通鉴》三国以前的要全读,其他如《汉魏丛书》及文学著作等也要读;考古材料包括金石文字和遗址文物,如铜器铭文、封泥、汉碑、汉简、墓葬、遗址及各种器物等,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如王国维、劳干等人的文章,尽可能多读;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三是信息方面,要关心学术动态。每周至少要去图书馆一次,看看这一周里发表的和秦汉有关的文章,掌握史学前沿情况。根据翦老的指示,我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除了听理论课、外语课,还有教学辅导任务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读书。周一至周六每天要读史料三卷,假如上个星期没看完,星期日补上。翦老要我每两个星期向他汇报一次读书情况。汇报以后,他常常谈一些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或当前的学术界情况,对我很有帮助。
1958年夏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领导全国十六个省(区)市同时开展民族调查,翦老让我参加,组织上把我编到云南组。8月,我任潞西县遮放区傣族调查组组长,率领14个组员对遮放区和瑞丽、陇川两县进行了四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12月又任武定、禄劝两县彝族调查组组长,率领10人调查组到金沙江边进行了七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1959年秋回京以后,已经到研究生三年级,该写论文了。我与翦老商定的题目,内容为“秦汉土地制度”。到毕业时,我被留校,做翦老的助手,于是我从此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
二
问:您的历史研究范围很广,除研究秦汉史专业外,还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中国古代契约史、中国铁器牛耕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请您给我们谈谈这些研究领域在您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之中有什么内在联系。
我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最早的诱因是参加民族调查。我到傣族地区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靠近中缅边界的遮放、瑞丽及陇川傣族地区,在解放以前,土地不许买卖,由土司定时分配耕种,称为澜(水)召(王)领(土)召,意思是水和土地属于王。再往里到芒市一带,土地可以买卖,但不卖死,属于抵押典当性质。田主何时需要,随时可以赎回。这叫做卖马不卖笼,也叫做活卖。这一情况与内地徽州的活卖有些相似,但徽州是正常的抵押典当或买卖关系,普遍存在于民间。傣族是发生在土司与一般贵族或富裕平民之间,是土地买卖关系的萌芽。再往里,即在盏达、勐腊一带,已和内地汉族地区一样,土地自由买卖。同是傣族地区,出现三类情况。就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来说,由内而外,是逐步受汉族影响的结果。后来我又到彝族地区调查,确定以土地所有制作为主要调查课题,从明代后期一直到民国,除口头调查外,凡彝、汉碑刻文字,都拓下来,或拍下来,或抄录下来。只要有史料价值的,全盘收录。最后,我们肯定,武定彝族四百年的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型过程。我对这两处调查,分别写有调查报告,对推动我学习、运用马列有关的理论和研究土地制度的兴趣,都有极大的助益。我回校时,全国史学界正在进行土地制度问题的大讨论,而秦汉土地制度正是讨论的关键阶段。这是我研究土地制度的直接原因。
我在论文题目确定后半个月,写出了一个“序言”,题目是《秦以前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生和确立》。到底土地私有制是怎么发生的?土地私有制的标志是什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都说:土地私有制的标志是土地买卖。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权的体现。贵重财物的买卖,关系双方要立有契约。契约是法律文书,是财产转让的证明。我查史料,例如《周礼·地官·质人》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值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这里讲到奴隶、牛马等私产可以买卖,但要立契约(质剂),可是没有说土地可以买卖。《礼记·王制》曰:“田里不鬻。”后来《唐律疏议》引用这句话说,为什么不许买卖呢?因为唐朝实行均田制,“‘田里不鬻’,谓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但是到西周中后期,贵族之间已经有赠送、赔偿、抵押、典当等土地转让关系,犹如当年芒市地区的傣族那样,出现了土地国有制解体的迹象。春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更频繁。到战国时期,土地买卖已是合法的正常社会现象了。此“序言”被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由翦老推荐到《北大学报》1961年第二期发表。不久,我写出论文的第二部分,题作《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又由学报的第三期发表。两篇文章发表不久,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史学会会长吴晗来北大看望翦老,并说:“张传玺那两篇文章我们研究了,准备由北京史学会组织讨论。”1961年5月,北京史学会果然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地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由吴晗主持,重点讨论我的文章。到会学者、教授100多人,著名的有侯外庐、贺昌群、尹达、邵循正、邓广铭等,发言热烈,分歧很大。总的说来,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教育和推动。1978年和1980年,我在《北大学报》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和《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两文,都是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结合的习作这两篇文章奠定了我对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研究的基础。
我由研究土地私有制问题扩展到研究契约问题,因为土地契约是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证明。我搞民族调查时已接触到契约关系,深深地认识到土地契约的重要性。1959年侯外庐先生在《新建设》发表文章,题目是《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认为中国的土地私有制缺乏法律观念,所谓私有仍然属于国有范畴,因为没有法律认可。贺昌群先生于次年《新建设》2月号上亦著文认为,中国的红契是合法的,因为盖着官府的印;白契没有官印,所以是非法的,从而证明所有权属于国家。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正确。后来我研究契约,从青铜器上具有契约性质的文字开始,一直研究到近现代。我弄明白了,契约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自其产生,就为官府所承认和保护。初无官、私、红、白之说。至少从西周到西晋这1400年间,就是如此。可是在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情况大变。新建国家为增加税收,规定土地牛马买卖,政府收取契税,然后为契约盖上红印。如果漏税,就是白契,属于违法。《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人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文券俗称“红契”。这是红契一名的由来。由此可见,侯、贺两位先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研究契约,写了十余万宇的论文,还编了《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下册,共120余万字。今年6月和12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刊登了我对新发现的契约研究的文章。一篇是关于近年在香港发现的三件吐鲁番契约,文字已残。另一篇是关于今年春天在内蒙古一个山洞里发现的三件元朝契约,文字也已残缺。我相信此两文对契约的研究亦有补益。
我为什么研究铁器牛耕呢?这首先应当感谢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其次,也是我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开始土地国有,后来土地又私有了呢?这都和生产力发展有关系。于是我又研究铁器牛耕。1955年在辽宁辽阳三道壕发现了一件西汉后期的大铁犁,长宽有40多厘米;1958年在山东滕县长城村又发现了比这件大铁犁更大的铁犁。这两件铁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引起争论,有人说能用,曲辕犁能拉动;有人说不能用,曲辕犁也拉不动。我问历史博物馆,他们说可以用,因为“从汉代画像砖中所看到的犁头,似乎也不小”。但我认为画像只是一个参考,真实情况还很难说,就决定亲自实验一下。1980年我三进中国历史博物馆,都是在陈列部和保管部领导和专家协助下量好尺寸,画出图样,反复核对的。学校方面由校工厂制作模型,到海淀翻砂厂复制。至1981年6月,由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李白华教授和阎立忠工程师协助,配制了两件华北传统犁架,一为双手扶,一为单手扶,用福格森165拖拉机牵引,在各种土槽、土壤中共试验了三次。我都拍了照片,记下实验数据,把实验结果写成报告,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由于我的研究,自认为中国古代至春秋中期才出现铁农具,战国中期才有铁犁,西汉前期还是用比较简单的铁口犁,至汉武帝时才出现全铁犁,还使用了翻土的犁壁。这时的铁犁与二牛抬杠结合,已是相当进步的耕作方法了。有人说唐朝出现曲辕犁,给农业带来革命,这话夸大了。我搜集各地壁画和模型等资料,发现自唐初至南宋的16件资料中,只有敦煌445窟牛耕图壁画有一件曲辕犁,其他都是直辕犁。曲辕犁到明清时期才有推广。我研究盐铁问题,是由研究铁农具派生出来的。
关于我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亦和自己的历史观有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研究政治制度有其必然性。现在有些人讲政治制度,谈到民主问题,都说是从雅典开始的。雅典的民主制是贵族民主,奴隶、妇女没有民主。欧洲中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讲:是黑暗时代,哲学是神学的奴婢。有人讲欧洲中世纪只讲后期争取民主,讲近代,则大讲实现了民主制度。如美国独立战争,发表《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发表《人权宣言》,都是大讲民主。后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挽救了民主。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向世界各国推广它的民主。真是资本主义民主“万古长青”。中国则不同,有人讲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以来,后代越来越独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清朝设军机处,更加集权。一直到近代袁世凯、蒋介石,不在话下。两千多年来,专制独裁到底!说来说去,中国不如欧洲,不如美国。
如果是这样,中国古代有没有政治文明呢?难道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吗?在两千多年中,对民族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从来不起积极作用而只是起破坏作用吗?难道只有“专制主义”,就没有一点合理的因素吗?我认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需要,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主要的政治文明。这个文明虽不尽善尽美,至少它的产生、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其前、中期是积极的、进步的。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及有效地管理大一统国家的问题,就应当充分肯定。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时代本部疆域(西域未计在内):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包括了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在内;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秦朝的疆域与西汉接近,人口约为其三分之一强。如果不是秦皇、汉武创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体制度,要想有效地管理这样一个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自然与社会复杂的诺大国家,并推动其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将是很困难的。再如中央之设三公九卿制,是不是反映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九卿中有两个是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其一是典客,“掌归义蛮夷”;其二是典属国,“掌蛮夷降者”。两官之下都有一个庞大的部属官府,基本上不是压迫剥削机构,而是礼宾和管理性质的。《汉书·地理志》中的地方政区,少数民族地区叫道,汉族地区叫县,虽然不是民族区域自治,但具有特殊性质是肯定的。唐朝在北疆和西疆设置的都督府、都护府,都是民族聚集地,实行羁縻政策。辽朝实行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属于原始的一国两制。元明清三代实行土司制度,就是民族头人自治。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几千年来的民族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必由之路。因此,不要把中央集权一下子否定掉。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史,要看见政治文明,懂得政治文明,爱护政治文明。当然,对“文明”要有鉴别,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一分为二,实事求是。
三
问;张教授,您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在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北京史、民族史等方面也有研究成果,撰写过傣族和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合著有《北京史》、《北京历史地图集》等,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通史专家。请您谈谈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断代史研究和通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研究断代史与研究通史是两件大工程,我既不专,又不通,不敢妄言这件大事。我跟着翦老工作,学到了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如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问题,用我的体会,还要左右开弓,上追下连。所谓左右开弓,就是要弄清同一时代相关的重要问题。所谓上追下连,就是要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例如要研究秦汉土地私有制度和土地买卖问题,必须弄清来龙,要读先秦文献。《左传》里就讲到晋大夫魏绛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但这仅是土地买卖的信息,还不是真正买卖。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王登一日而荐二中大夫[于赵襄子],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田耘、卖宅圃而从文学者,邑之半。”这是明确记载了土地买卖。我就把这些问题抓住,弄明白了先秦时期土地买卖产生的时间,再证以战国时期土地买卖的发展,秦汉时期土地买卖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至于西汉以后的土地所有制,如法炮制就可以了。这样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的“专”与“通”问题。至于断代史与通史的关系,也就是较大范围的“专”与“通”的关系。我给翦老当助手,他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主编《中国史纲要》,我就跟着干。我的知识单薄,为了做好工作,要努力学习,这对我很有帮助。“文革”以后,有个出版社要出中国通史少儿读物,想请邓广铭先生当顾问。邓先生说你们如果出宋辽金史,找我当顾问,我一定干;你们出通史系列找顾问,应该去找张传玺先生,他是搞通史的。邓先生说这个话,是对我的栽培和鼓励。至于我本人对于通史,只能说不甚了了。我给翦老当助手,有人不理解,说我那几年没写东西,牺牲那么大。我说:“情况并不如此!我跟翦老十年,受益非常大。”后来我个人写《中国古代史纲》,搞各种研究,都受益于翦老。
四
问:您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不仅硕果累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研究方法。我们想请您谈一谈自己的治学体会,以及对当前历史研究的现状有何看法,给人们学习历史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觉得学理论非常必要。新中国史学的成就是什么?我认为第一个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普及。解放前已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有用的理论,就在偷偷地学习。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讲历史发展原理,发展规律,这是极好的事。当然也有人不满意,甚至抵制,但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是愿意学习的。比如何兹全先生、白寿彝先生,还有四川的徐中舒,上海的束世澂等先生,当时的年龄都很大了。他们都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擦亮了眼睛,学了管用。当然我们年轻人更喜欢学。第二个成果是“五朵金花”大讨论,这不是为讨论而讨论,是历史研究深入的需要。如历史分期问题,是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史论战中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不是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什么是全封建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前面有没有奴隶社会?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历史分期。解放后接着讨论。土地制度问题,是随着讨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问题而提出的,1954年就提出来了。是因为讨论分期问题而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鉴于明清时期欧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到此时已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不是别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都是学术研究深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如果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眼睛不亮,这些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五朵金花”大讨论,不仅推动了众多的史学研究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还锻炼、培养了为数极多的青年史学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有人说:研究历史要自由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是带上紧箍咒。这是大错特错。世界上没有哪一本书没有指导思想。《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这不都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吗!完全中性的自由发挥自己思想的东西并没有,连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认为,历史是通过人的大脑写出来的,包含着作者的思想。每个人都要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讲话,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青年同志想不受外界的影响,发表独立见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你发表的见解有它形成的背景,你要超出这种局限,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进来的思想、学说很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谓“文化冲突论”就很不好。它把世界上重大战争都说成是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比如古代罗马征服地中海,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十字军东征,都说成是文化冲突。其实这些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权益问题。亚历山大东征的口号是:把战争带到东方,把财富拿到希腊!这是破坏和掠夺的,怎么能说是文化冲突呢?有的同志把这种学说作为新观点、新理论引进中国,说汉和匈奴的战争是文化冲突。蒙古和宋朝的战争,也是文化冲突。还说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和基本的方式。那么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屠杀犹太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是文化冲突?是不是实现了文化交流?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不正在为霸权主义、侵略行为作辩护吗?战争还是要讲的,但不能这样讲,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赞成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所以,对于这些外来的理论,青年同志应该注意鉴别。
还有史料问题,现在大家普遍反映念书之风不如过去。年轻的同志缺乏史学功底方面的修养,这也和我们的某些规定有关系。如三年要拿个硕士,三年拿个博士,毕业以后还有提职称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容易误导他们走捷径。过去范文澜先生说:“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要有一种刻苦训练精神。现在我国一年出版的图书很多,大大小小的高等学校都有学报。除学报以外,各省还有各种文史刊物。现在出的东西多,年轻同志发表文章的机会也多,但要注意出高质量的东西,社会需要精品。不要急于成名,更不要为成名而成名。要用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今天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年轻同志要树立雄心壮志,充分利用这样的优越条件,要坚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把中国的新史学研究和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得知,张传玺教授虽然年逾古稀,仍然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编辑10卷本《翦伯赞全集》,已经基本上编完;还参与了北京大学的重点项目4卷本《中华文明史》的编写工作,为四个主编之一。此外,还担任教育部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工作十分繁忙。在此,我们衷心祝愿张教授身体健康,学术事业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