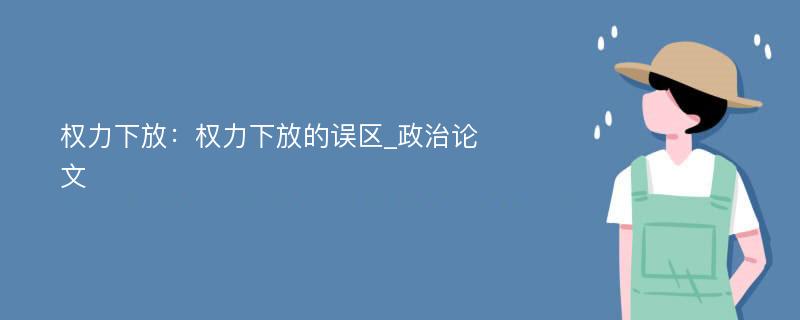
权力分散:分权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散论文,误区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权、分权作为政治权力的存在方式,是政治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政治学家们往往把集权看作是专制制度中的权力存在方式,而把分权看作是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存在方式。所以,“集权”一词在现代政治学中越来越具有否定的含义,并常常被用来描述和指责那些与政治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政治行为。同时,“分权”一词往往与民主化有着同等的含义。因此,在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改革的过程中,往往从分权入手,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权力下放,在同一层级上,也是把权力尽可能地分配到不同的职能部门。但是,由于对分权的问题缺乏科学的理论探讨,以致于分权的实践演变成权力分散,从而造成了与分权的目的相悖的结果,即出现了许许多多小的集权,严重干扰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进程。这种把分权引向歧途的权力分散,是包含着政治危机的因素的,而且从现实表现看,它已经以政治腐败的形式而存在于世界各国。所以,对于急切地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从理论上认识分权与权力分散的区别,是一个关系到民主化进程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
从集权到分权: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从集权开始的。
最初,集权主要是服务于人们征服自然界的需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状态中,强大的自然力量使人的个体力量显得非常渺小,为了生存,人们把个体的力量结成集体的力量,从而产生了权力。“权力”这个概念,最初所意味着的是力量,而且是一种大于个人力量之和的集体力量。
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是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对比力量,是一部分人可以对另一部分人加以支配和制约的力量。从广义上来看,权力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始终的,任何一个社会中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力;狭义的权力是指政治权力,我们在使用权力这个概念时,基本上是指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从政治权力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经历了集权的运动过程和分权的运动过程。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过程,但却记述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轨迹。
政治权力的出现本身就是权力集中的过程,即分散的权力向一个中心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才可能造成一个中心状态的权力——集权。在原始社会末期,集权化的过程成为通向国家之路,创造了中央集权。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一部集权化的历史,一切权力都向某一中心集中,并有中央集权的性质和特征。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集权的规模和程度有所不同,甚至在古希腊也曾出现过奴隶主的民主制度,但从总体上来看,世界上的一切国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都表现为一个不断地集权化和极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过程。即使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并不是在已有中央集权状态下的分权,而是在政治权力诞生的初期阶段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集权方式,是在集权运动中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执掌方式,在本质上它依然属于各种社会权力向中央集中的范畴,只不过它不是集中到某一个君主手中,而是集中在少数奴隶主的手中。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这一权力运动的方向,开始了分权的运动过程。原先积累起来的政治权力被不断地分化和分类,并不断地分配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部门,其结果是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在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分权的方式来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民主制度的。从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这一理论公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集权的挑战,即包含着还权于民的要求。用“契约论”来解释政治发展史,无非是要说明一切政治权力本来是来自于民的,是民权的“出让”和“转移”,并被奴隶主、封建主所攫取而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也正是根据“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理论,集权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恶”。所以,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应当是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重新归还于民。但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又不允许在把权力归还于民的同时出现无政府状态,必须保留国家和政府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因而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就只能通过分权的手段来达到尽可能地使权力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让一部分人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并尽可能地保证政治权力不以人民的异己力量的形式出现。
当然,这只是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设计者们的善良愿望,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现实并未实现这一愿望。其根源就在于分权的实践未能得到理论的指导和支持,或者说在如何分权才是合理的分权这一问题上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因为,“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资产阶级应当通过分权来实现广泛的民主,但是如何分权却一直是理论的盲点。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在近代300 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徘徊在分权与集权的十字路口,当某一党派上台之后,极力地在民主的幌子下推行集权的实践,而在另一党派上台之后,又迫不及待地进行分权。
然而,分权的运动是一个历史趋势,政治文明的标志是民主化,任何一个党派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客观进程。所以,对于政治发展来说,不是要不要分权的问题,而是应如何分权的问题,即如何保证在分权的同时避免造成权力分散的结果。
分权与权力分散:两个不同的概念
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契约论”、“天赋人权论”是分权实践的理论基础,而分权的历史进程也确实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分权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它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中发育,市场就开始把各种各样的集权作为自我成长的障碍,市场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加深,并演化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是独立的人,具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在这个原点上,它必然会不断提出进一步的政治要求,即要求市场行为尽量不受国家权力的干预;要求国家、政治的权力具有确定的规模和范围而不至于被滥用;要求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受到统一的规范而保证市场主体能够平等地进入;等等。总之,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是非常矛盾的,它希望谋求政治权力的保障,又希望政治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它。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它找到了法制的途径。其实,法制无非是权力制约关系的形式化,即借用法律条文及其实施手段这一形式把权力制约关系固定下来。所以,伴随着分权的运动,出现了法制。而法制的现实功能也恰恰是保证了分权的进程不再逆转,也就是说,法制铲除了集权赖以实现的土壤,使分权的运动勇往直前。
在近代史上,分权的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期阶段,所谓分权是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表现为一部分政治权力向非政治权力转化,弱化政权而加强民权。这种分权无疑是政治权力的流失,但却解脱了经济发展的羁绊,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迅速发展。通过这种分权,政府与社会相分离,政府站在市场之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作出一定的规范,而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是被严格地区分开来的,政府基本上不介入到经济行为之中。
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延续了300多年,到了20世纪中期, 国家和政府不再积极地去与社会之间进行分权,而是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分权,即在政府内部进行分权。因为,市场经济自主发展的原动力已经开始枯竭,它开始需要国家更多的支持,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国家从原来的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转化为市场经济的“介入者”。经济学家们把这看作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合理干预,并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这种干预意味着政府为市场经济提供服务的方式和范围发生了改变,特别是服务范围的扩大,使政府的规模也随着增长,因而出现了如何在政府内部分配权力的问题。
在政府内部的分权是沿着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运动的。所谓纵向的运动,是中央权力向地方的转移;而所谓横向的运动,则是权力在每一个层级上的分类化。在习惯上,我们通常把纵向的分权称作权力下放,即政治权力被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放,以便每一个层级的政府都有相对充分的活动自主权,特别是要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在横向的分权中,原来应当属于层级首长的权力被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交由各个职能部门执掌,从而提高权力运用的效率。显然,这种存在于政府内部的分权运动同以往的那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是不同的,但它却同样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作出的分权运动,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从客观结果来看,这种存在于政府内部的分权运动却把原来那种健康的分权变成了畸形的分权,因为它已经陷入到“权力分散”这一分权的误区。
“权力分散”与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权力分散却是在分权运动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政治怪胎。我们看到,在纵向分权的运动中,地方政府诸侯化,即出现了诸侯鼎立、相互封锁等地方保护主义;而在横向分权中,却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可以泛滥的空间。总之,权力被分流或分配之后便失去了控制,从而使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遭到扭曲,执掌权力的人可以在为公的名义下滥用权力,也可以在谋取私利的行为中出租权力。因为,他偷偷地窃取了上级或领导冠冕堂皇的授权,转化成他个人的私有物,任意地支配它。这样一来,分权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变成了集权。当然,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集权不同,首先,这种集权不是一种中央集权,而是分散化、多样性的集权,是用数量上的无数个集权和性质上的多种多样集权来限制和削弱中央权力;其次,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是被公开声明为私有物的,即被声明为权力最高主宰者私有,而这种新的分散化、多样性的集权却是在公共权力的名义下而成为隐蔽的私有物。但是它毕竟是一种集权,是个性化的权力,甚至是一种不道德的、非法的和可能更具有破坏性的集权。这种集权形似分权,而在实质上却是集权,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力分散”状态。
可见,“权力分散”是一种用众多的集权取代单一集权的运动,由于中央集权流失到众多各自为政的小集权者手中,造成了整个社会处处存在着集权,所以这是一种集权的普遍化。整个社会表现为在每一个层级上和每一个部门中都存在着各自的权力中心,每一个以自己的中心为原点而建立起来的集权,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对于社会的整体来说,就像是一块小小的积木,而社会的整体正是由这一块块积木搭成的。所以,在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整体,而实际上是缺乏内在的统一性的。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所进行的分权运动中,法制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权力分散”的现实,人们也求助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因而,近几十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的立法高潮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但总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面对“权力分散”,法制必须通过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维护权力的公共性质。但是,如果这种规范过于慎密,必然会使政府官员丧失运用权力的自由,因而失去任何创造性,也就不可能实现公共权力的使命;相反,如果这种规范过于宽松,就无法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就难以避免公共权力转化为新的集权。所以,在“权力分散”情况下,法制陷入到一个二难的境界。法制是一种能够有效地使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在“权力分散”这种新的集权面前却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所以,70、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空前的政府腐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
权力分散:腐败的结构性根源
同样,在我国,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人们在探讨腐败的根源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从思想上来挖掘腐败的根源,认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是腐败的根源。根据这种看法,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根治腐败,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却忽视了一点,资产阶级自己无论在何时也都未曾希望自己的政府腐败过。有人从体制上来解释腐败的原因,认为新旧体制的转型、法制的不健全,为腐败分子造成了以权谋私的机会。这样一来,随着新旧体制转型期的结束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腐败自然就会消除了,但当代发达国家,有着稳定不变的体制和经常引以为骄傲的法制,为什么依然存在着腐败问题呢?有人则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发展经济,就应当接受腐败的现实,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廉洁不可兼得,在它们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这种观点无疑包含着一个“预言”,那就是人类社会将面临着腐败无限膨胀的未来,因为人类社会必然要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腐败也会越来越泛滥。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多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认识腐败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对腐败根源的揭示,实际上都只能属于一种现象描述,并没有真正揭示腐败的根源。
其实,一切腐败都来自于集权,集权是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在这方面,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论述却包含着更多的真知灼见。比如,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近代社会关于法制建设的主要努力,就在于约束权力, 但“权力分散”所造成的这种新集权却是一种无法受到约束的权力,所以它是一切形式的现代政治腐败的真正根源。由于“权力分散”使集权普遍化了,因而,它也使政治腐败普遍化。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权力分散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动,因此,滋生在现代政治机体上的政治腐败,也只有从权力分散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简政放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旋律。所谓简政放权,在实质上就是分权的运动。而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衍生出了地方保护主义、以权谋私、权力的寻租与出租等腐败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决不是在合理的分权中应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是分权的运动出了偏差,即出现了权力分散的问题。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我们看到一些法学家、政治学家们提出了权力交换的概念,认为政治腐败是权力交换的结果,有些人并因此而断言权力自身就具有可交换的性质。这显然是一种对公共权力的误解,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是它的根本特性,而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共权力决不可以用来交换,一切变相的交换都是与这一根本性质不可调和的。如果说出现了权力交换的问题的话,那么决不是公共权力的交换,而是私权的交换,也就是说,在这种交换发生之前,已经出现了公权向私权的转化,由于权力的抽象性,这种转化在没有造成一定的结果时,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才出现了误以为公共权力具有可交换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公共权力是全体公民平等拥有的权力,是一种永远都不可交换的权力,只有当这种权力被私人占有和被政府官员非法窃取之后,才可能被用来交换。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不会仅仅在权力交换的结果已经出现之后才看到腐败的问题,而是应当把反腐败的重心放在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上面,只有这样,才是廉政建设的正确道路。
政治腐败是权力私有化的结果,而在法律和制度都极力维护一切公共事物的公共性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呢?如上所说,政治权力不是静止的,它要么沿着集权的方向运动,要么沿着分权的方向运动,集权的运动,必然导致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代社会的分权运动中所出现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的情况也应当看作是集权的结果。这种集权具有分权的形式,但这种形式是一种假象,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已有的法律和制度,以致于忽视了它在根本性质和基本内容上的集权。所以说“权力分散”作为一种新的集权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它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破坏民主制度的机体健康。
“权力分散”作为分权运动的畸形结果,背离了分权的正确方向,但是,由于整个政治学界和法学界都对权力分散缺乏认识,以致于没有针对权力分散问题的对策,所以,权力分散已经成为漫布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来说,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着的结构性因素,但却是一个从内部破坏着民主制度的因素,所以,归根到底,现代社会中的腐败是由于权力分散所带来的,权力分散是一切腐败的结构性根源。
可以断言,人类今后的政治是进一步走向文明还是走向野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认识到权力分散的存在,并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它就有可能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寻求合法化的途径,从而成为新的一轮集权的起点。当然,正如现代民主不同于原始共产主义中的民主一样,新的集权也不会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集权形式出现,但可以预言的是,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对人类社会都是一场悲剧。
注释: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标签:政治论文; 公共权力论文; 权力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集权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