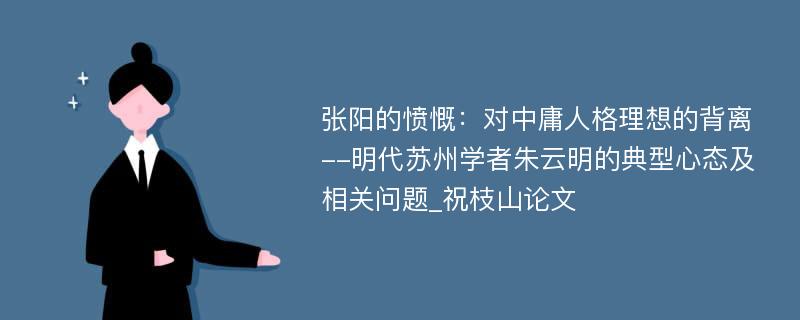
张扬愤激:对中庸人格理想的背离——明代苏州文人祝允明的典型心态及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愤激论文,苏州论文,中庸论文,明代论文,文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4-0141-04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五十八岁的祝允明在《答郑河源敬道书》中写道:“大凡世人莫不有志,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愿遂之,其为邪慝者无论,即为正而良,其负性布行,每恒难乎中庸……以至于遂有若仆者,狂乎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贰且笑焉。”[1](卷12)① 此文虽略带自嘲意味,但毕竟是在坦率地为远离中庸的人格理想辩护,是对明代官方意识形态要求的公开反击。它折射出一种张扬愤激的心态。而考诸史实,此心态实典型体现在这位苏州才子成年后的几十载人生中。祝氏这种心态有怎样的具体表现、其成因何在?把握此心态对于研究明成化至正德间的苏州文人群体又具有哪些意义?本文即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
品读祝允明的作品,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他对自己的心迹,总是习惯于用大胆剖白的方式表露,在表现特征上显得波荡甚至夸张,缺乏精气内敛的老成气息,充满强烈的宣泄感。这恐怕正是其张扬心态的具体外化。他带有心灵独白特征的《丁未年生日序》[1](卷21)、《悲志》[1](卷9)等作品,均是很好的例子。
而对于他来说,随口讲出“人尽克圣,克之者弗为,斯后人之不肖”[1](卷10,《古今论》)或“遐览天地间,何物如我贵”[1](卷3,《和陶渊明饮酒》)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再平常不过之事。至于他屡用俚俗之词来表现名利之欲,就更足以令信奉理学的守道君子们瞠目结舌:
因名为利苦奔驰,换得身痛气似丝。到此都寻参与术,名难将息利难医[2](卷3,《绝句》)。
秽衣宿食宵兴,长路弱脚晓行。归来梦想富贵,困蠢嗟哉书生[2](卷3,《书生戏歌》)。
从上面诸例可见,祝允明的诸多愿望,乃是以一种近乎肆无忌惮的方式呈示出来的。他所谓“人尽克圣”,固然是先秦儒家早已阐发之义,但明白地宣扬此种勇猛精进的精神,在明前中期士林内仍然显得不同凡响。求名逐利,无非人之常情。但祝允明如此公开地歌颂之,确实是显得过分重视个人欲求,远离修齐治平的儒家崇高理想了。
然而仅看到这一层,尚远远不够。对“每恒难乎中庸”之人格持肯定态度的祝允明,绝不回避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而是时时对其激烈攻击。透过相关言论窥探其心态,我们就会不仅见得出其中的“张扬”,更会捕捉到那“愤激”的一面。
今日论祝允明者,每将其视作思想深湛的哲人。不过,思想堪称深湛的祝允明,情感状态却并不平和。读其文集,我们同样不难发现的是,当他向某一对象发表批评意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绝不留余地的攻击态度。他的深刻,也就经常夹杂在这种偏激、有失情绪化的议论中;这种深刻,往往显得锐利,而并不冷静、周全。不妨举其“称诗不可以杜甫为尊”论为例:
甫也果何有哉?其极推者,以为忠义激发,度越诸子,是则未仪辞体,别以礼义论也。然则忠则信有之矣,忠蕴于胸臆,声形于颊舌,固当若是嚣呼诟怼,若捐家委命,强驱赴敌之悍卒然耶?……诗当温,而甫厉;尚柔,而甫猛;宜敦,而甫讦;务厚,而甫露。乃是最不善诗者,何以反推而倒置之与[3](卷9)?
批评杜甫诗歌,在成化正德前后并非空谷足音。可是像祝允明这般不惜以“嚣呼诟怼”、“最不善诗”加诸其上者,毕竟罕见。与此相似,他批评宋学,便一定要说“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1](卷10,《学坏于宋论》);不喜宋诗,就要讲出“诗死于宋”[3](卷9)。如此批评,固然有其深意在,但毕竟会让人觉得:以如此方式发表意见者,其心理状态确乎须以“张扬愤激”来定位。
不过,祝允明的“张扬愤激”,仍最典型地表现于对理学和科举的反击。这种反击从他青年时期就已开始,终其一生均未消歇。
祝允明对理学精神的不满,首先突出表现于对理学人性论的反感。二十六岁时,他就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人之才,有巨者,有细者,有高明者,有沉潜者……必欲其令而不颇,天下之人皆废也。圣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矣!
此段文字并未公开以理学为攻击目标,但是其标举之观念,正好与理学家背道而驰。追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令而不颇”,乃是理学精神要义之一。而祝允明在上面这段话中,恰恰标举人之个性,肯定人性的多样化价值。
除了与理学人性论针锋相对,祝允明还对理学家的诸多作风表现出强烈不满。他特别厌恶因高谈性理而致各立门户、互相攻讦的风气,其晚年作品《答张天赋秀才书》、《祝子罪知录》皆对此予以痛诋。在《祝子罪知录》中,他甚至还质疑程、朱在明代的独尊地位,认为“必以(程朱)为集大成,都废前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百千年,一守不迁,不知可不可也,亦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3](卷5)。如此言论,实际已经是对朝廷思想专制政策的挑战了。
至于祝允明之批判科举,实与其抨击理学相辅相成。明代科举取士,以官方确认的程朱理学精神为准的。而祝允明之反科举,也主要在于反对这种裁断尺度。这集中地体现在其长文《贡举私议》中[1](卷11)。该文一则提出“三试取舍,宜均其力为便”,反对考试仅重“初场”;二则希望在专重“性理”的经义考试中做到“求之宜大,毋拘一律”,“兼习注疏,而宋儒之后为说附和者不必专主”。总体来看,其言论具有如下内核:在经学上,重古注而轻宋儒;在考试整体上,实务、义理兼重;在考试的具体操作上,重灵活而轻教条。这里面无论哪一点,均与明代官方选举制度相应规则背道而驰。当然,在表现方式上,此文比前举那些骂戾之词理性得多。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此议论,若非心中怨愤极为深广,又怎能道出?
二
上述祝允明“张扬愤激”心态的产生原因何在?解释类似问题,今日学者多将其与商品经济对人心的刺激联系于一起。关于这一点,本文并无异议。因为对于成熟于成化以降的江南文人来说,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及相应“重利”人生观,的确可能令他们产生心理波动、引发其基本行为方式的微妙变化。不过应该看到,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不同文人的心态,仍表现出很大差异——在成化至正德间苏州文人群体中,沈周、文徵明虽同样崇尚个性、厌恶科举,但绝非祝允明一样的狂者。因而,我们就须探究:祝允明上述心态的产生,是否还有商品经济刺激之外的因素?这恐怕是深入理解此类心态成因的关键。
祝允明生于显宦家庭,祖父祝颢、外祖父徐有贞皆为著名官僚,且是苏州文艺活动的主要引领者。比起世代隐居的沈周家族,祝允明的家庭不但一样拥有良好的文化环境,更拥有沈氏所不具备的显赫地位。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祝允明在一片鼓励中成长起来。他五岁时就能作径尺大字,九岁便能写诗。虽然年纪幼小,但祖父祝颢却已时时带他参加名士们的诗酒之会。尤其是,当他于二十一岁初入庠序时,仍然堪称幸运。据其友人阎起山记载:
御史山阴司马里按直隶,檄郡学有博学能为古文辞者,免课书,更殊礼遇。郡以允明当。里按吴,允明从诸生中擢行相见礼。侍郎徐公实尝读允明所为文,爱之,数加存问,由是延誉两都,知与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士也[4]。
明代学校教育,一般不提倡古文辞写作。有时碰上态度偏执的学官,好此者甚至有被罢斥的可能。可祝允明的才华,恰恰受到了识才爱才之学官的保护。
通观其早年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他可谓一帆风顺,既不用费神考虑生计问题,又未感觉到科举带来的压力;所作的只是无忧无虑地施展才华。而在相近的年龄,庶民出身的沈周已经代父应粮长之役,直面艰辛的人生;同样出身官宦家庭的文徵明,则正因资质鲁钝而遭人轻慢。而进一步看,在其交游圈中,他因为出众的文艺才能,一直是友人们公认的才子。哪怕科场不顺的苗头已早早露出,此类评价,也没有改变。不妨读一下王铸的这段文字:
希哲作文,杂处众宾之间,哗笑谭辩,饮射博弈,未尝少异。操觚而求者,户外之厅常满。不见其有沉思默构之态,连挥数篇,书必异体。文出丰缛精洁,隐显抑扬,变化枢机,神鬼莫测,而卒皆归于正道,真高出古人者也……所尊而援引者五经、孔氏,所喜者左氏、庄生、班、马数子而已。下视欧、曾数公,蔑然也……希哲方二十九岁,他日庸可量乎[5](P37)?
祝允明二十九岁时,正是弘治元年(1488年)。此前,他已经三次参加乡试,均未得中。可即便如此,在友人笔下,仍满是对他才华的钦慕。祝允明“视欧曾数公,蔑然”的作风,无疑与官方文教精神背道而驰。不过在友人那里,这非但没有被质疑,反而赢得了毫无保留的称颂。不难想见,这类成长环境,很容易令祝允明具备强烈的自信精神,从而发言吐语,皆无忌讳。不过,同时也容易使他对外部世界的复杂缺乏心理准备,将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想象得过于简单。从前面引过的祝允明二十六岁所作《读书笔记》之内容便可看出,他对自我才能,确实毫不怀疑;否则,他不会如此大胆地讲出与官方理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见解。可同样从这个事实中,我们也能看出,祝允明又的确太过天真。他根本认识不到,日后想要在官场显身扬名,就必须适应这些官场尊奉的律令。相比之下,虽然他与沈周皆拥有一颗缘情尚趣之心,但二人的人生理想毕竟有所不同。沈周为自己确定的社会角色相对简单:他不过是要做自得其乐的乡间隐士。而祝允明却不然。从二十一岁初应科举到六十二岁决定退隐,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执著地同时扮演着两个彼此距离甚大的角色:一个是风流自在,率性缘情,不愿忍受专制束缚的才子;一个是七试春闱不售,但又屡败屡战的仕途奔竞者。可以看到,在生命中,他不仅雅好艺文,而且对人生可能完成的一切,都要一概求之。此种对自我极高的期待,多半来自前述的自信。然而支撑着这种自信的,恰恰是天真、简单的才子心态,而非应对外部世界所必须的圆融、事故。我们看到,此种天真,哪怕是在他五十五岁第七次会试失败后,仍然没有消退:
漫读程文,味若咀蜡,拈笔试为,手若操棘,则安能与诸英角遂乎?挟良货而往者,纷纭之场,恒十失九,况枵橐钝手,本无所持,乌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后定也[1](卷12,《答人劝试甲科书》)。
而即便是此后通过谒选,一圆其做官梦,他仍然在发表如下议论:
仆诚不善仕,其故大率不能克己,不能徇人,不能伪,不能忍心。视时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1](卷12,《答张天赋秀才书》)?
人欲在社会中赢得权力与地位,就不能不牺牲个性与社会普遍规则相抵牾之处。尤其在专制时代,文人赢得名利的可靠途径唯有人仕一条。而获得这种权力,更要以付出个人自由,成为专制之奴隶为代价。祝允明投身科场,却偏偏怀着“漫读程文,味若咀蜡”的逆反情绪;已然为官,却时时觉得自己不能因此丧失才子性情。可以说,他既想赢得权力和声名,又质疑为赢得这些所必须采取的方法。这样,他根本不可能融人那个冷酷功利、变诈横生,可又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外部世界。这里,可引祝允明晚年诗文为例:
仆之少也,窃幸生于贤邦仁里而出乎诗礼之庭,当是时也,恬然不知米布之价,况余事乎?日惟从先人求纸笔耳。暗室独坐,每自泰然而喜,以为生得内外尊长之诲迪若是,不二三十,当粗成人也。忽而授室,倏而抱子,曾未转首而继遭大罚,群美顿革,霍然如电掣星过,凡举其所恃以泰然者,邈不知所在矣。自是志趣荒落,履践钩棘,以至于今……其中万分之一犹可以尾君子之末者,则皆昔者之遗也。尝自思之,其所由来固多,大归孤立无援之故矣[1](卷13,《与施别驾书》)。
世棋年矢两相催,绝岭春深与雁回。无限胸中未酬事,蓬窗灯枕酒醒来[1](卷6,《庚辰二月廿七日晓官窑舟中口号》)。
一句“孤立无援”,一句“无限胸中未酬事”,充满浓重的失落感。极力想在官僚世界中出人头地的他,偏无法于此道有所建树。而由于此种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他的心境,也自然就很难平稳。既然终其一生,外部世界均与其格格不入,而他又始终不愿重塑自我形象,那么愤激心态的形成,怎能不是必然之事呢?
三
分析祝允明的心态,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成化至正德间苏州文人群体的某些基本特征。总体而言,这个文人群体的心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一种是以沈周为代表的“恭顺圆通”,另一种就是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张扬愤激”。
对于沈周来说,审美愉悦的实现与生命理想的完成,是在自然而然、不迁不矫的普通人生命中实现的。他放弃政治前途,自认地位的卑微;虽有个性,但绝不因之叛离社会。他并非没有愤激之词,但细究之,他的该方面言辞毕竟为数不多,且即便有之,也从不涉及往圣先贤,更与国家意识形态及科举制度无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种态度,表现出文人尽量在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前提下追求自我人格舒展、自我选择独立的愿望。这是他们对不可动摇之现实体制的让步。此种处世之道,无疑会提升此类文人对社会的适应性;同时,又必然削弱他们对社会的抗争能力。也正因如此,在主动让步后,他们的心态呈现出的不是天真固执,而是恭顺圆通。在这一文人群体里,最有效地继承沈周此种特征的,便是文徵明。对于这位苏州名士“和而介”的品格,今人已有较多分析。官僚绅士的地位,使他不会像沈周那样过分地谦卑。而他也的确屡次发泄对科举规则的不满,且部分言论正是对理学的直接攻击。但归根结底,他的性情因掺入“和”的因素,而不至沿“介”的方向过分发展,所以也就没有走向抗世违俗。明嘉靖初,甫人官场的他便撞上“大礼议”。面对险恶的政治局面,他既未支持“护礼派”,也不拥护“议礼派”,而是称病辞官,返归乡里,迅速结束短暂的仕宦生涯。此后再未出山。在以隐居作画为乐的晚年,他一方面甚为注意自己的生活态度,从不为宦官、诸王、外国使者作画,也从不接受其馈赠;另一方面,又与亲友门生、乡里父老其乐融融地相处终生。这些事迹,当然能说明他行履高洁,不肯与官场群丑同流合污;可同时也确实体现了沿自沈周的生命理念,即立身需端正,行为戒矫激。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说,他的心境,终归是以安时处顺、方外逍遥为归宿,并未进出激烈抗争的火花。
祝允明的情况,显然与沈、文二人大为不同。他一样具有对审美化人生的渴求,但他根本无法如沈周般退避自守,在让步中获得人生的满足和心境的顺遂;同时,又并不具备融入外部社会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因此,他也就无法像沈、文二人那样填平个人理想和生活现实间的沟壑。在此境况下,他不停地向那个令他处处碰壁的外部世界发出猛烈攻击,其心态,也就只能以远离中和状态的张扬愤激为归宿。在这一点上与他接近的,便是唐寅。对于这位知名才子的心态,今人已有多种分析。而此处需指出的是,尽管人生历程与祝允明并不相似,但他那始终如一的才子式天真,却与祝氏别无二致。他始终格外重视外部世界的评价,绝不肯过恭谨和顺的隐居生活。哪怕功名已永不可得,仍要制“龙虎榜中名第一”、“南京解元”之印鉴以求自我满足。与此同时,他又和祝允明一般,永远无法向外部世界作出过多让步,尤其是经历科场案刺激后,其心态中放纵疏狂的一面更被强烈地激发。他狂热的玩世作风,因佞佛而生的幻灭情绪,其实都是他剧烈波荡之心态的外在表现。至于其充满愤世、怨世情绪的诸多诗文,更是直接地呈现着他心中的张扬愤激。可以说,比之沈周一类人物,祝允明、唐寅的这种张扬愤激,其实正是将苏州文化精神中带有抗议性的一面鲜明地表露出来了。
总而言之,以沈周、祝允明等为代表的成化至正德间苏州文人群体,其成员相对远离官僚群体诸多律令限制,有更多机会享受人生情趣,也更为主动地追求着个性的舒展。可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典型的所谓“下层文人”,大多处于国家政治权力系统的边缘。在政治专制社会中,这类人一方面往往在民间化的评价系统中非常知名,但另一方面自身才艺又无法为他们赢得政治地位,从而也就难以使其自我价值真正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承认。在这种困境中,如何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其实也就成为决定其心态特征的关键因素。而选择,无非是“谐世”或“抗世”两种。所以其心态,也就必然出现世人所谓“恭顺圆通”与“张扬愤激”的分化。
[收稿日期]2009-04-20
注释:
① 按:本文所涉祝允明诗文、事迹系年凡未专门标注者,均遵陈麦青《祝允明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