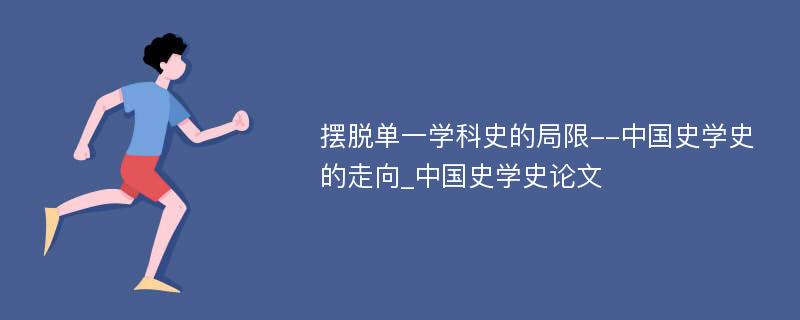
摆脱单一学科史局限——中国史学史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链接
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史学史的做法”(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强调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他还指出“史学史的做法”应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这四项内容,这不仅被认为是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的标志,还被认为是首次规定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展开,相继出现了十余种史学通史性的讲义和著作,以及几百篇相关论文。其中公开出版并产生有较大影响的史学史著作,当属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以及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
多数评论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以梁启超设立的“史学史的做法”的框架为基础,论述方法受到古代目录学的影响,史学史著作更像是史部要籍解题。如金毓黻即直言他的《中国史学史》“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是有其必然性的。问题在于,在以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为主要特点的同时或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还应当关注什么?
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该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影响较大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为倒,书出之后,白寿彝和齐思和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金著对于史学以及史学史自身概念及理论范畴方面认识程度的不足和论述内容的薄弱,这也不仅是这一本著作的问题。而是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走出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必须深化对史学之义和史学史观念的认识。对史学史课题观念的改变,决定了史学史研究及史学史学科的走向。
突出历史、时代视野
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沉寂,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成果还是在学科建设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发展。自1980年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后至21世纪初,大陆出版的各种中国史学史专著有20余种,研究论文则难以计数。
如此多的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重要的是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史学史应如何分期、分期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正是此前以要籍解题为主要特征的史学史研究所亟需充实的“史学之义”之内容。如白寿彝在80年代中期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归纳为:“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将此表述与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形式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并关注史学自身功能及其社会作用的体现。这样的研究趋向,可视为是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向。从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来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促使史学史研究者能够从史家、史书中将研究视野扩展开来,对中国史学的整体脉络、发展节奏与特点作宏观分析,即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40年代到80年代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之课题视野的演变路径是:从中国史学史中的史家与史书,延伸至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学的发展。课题视野的如此变化,理论层次也就相应提高,诸如史学发展与客观历史发展的关系、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脉络、不同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特点、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分期以及分期标准问题等关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受到相应重视。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研究具有了相应的基础,90年代至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拓展的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数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相继出版,其中,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于2006年12月全部出齐,这是迄今部头最大、内容最全面的论述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史》以十卷本的篇幅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还有谢保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必须提及的还有台湾学者杜维运著三卷本《中国史学史》,重视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启迪作用尤深。
突出和强调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拓展和深入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随之而至的问题或许更为复杂。中国史学史研究即使发展到了如此规模,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趋向: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
传统人文学科的独立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就学科史而言,更多地是从学科史较为单一的、纵向性的角度对本学科的自身内容的构建,专门学科的研究在沿着自己关注的问题纵深探讨之时,过分局限于专业视角而忽视了各门学术间的联系,其结果是忽视了学科史与学术史间的渗透关系。学术史着眼于一段时期中学术发展整体性的价值评估、研究方法的归纳、理论体系的总结以及各学科相互间的关系的探究等。这对单独某一门学科史来说,似乎勉为其难。摆脱单一学科史局限的尝试,是将史学与社会时代结合起来。事实上,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将史学史纳入学术史的视角中深入考察史学的自身发展、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而涉及影响史学的诸多学术因素作综合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地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等问题,都更为研究者所重视。
以中国古代史学而言,传统学术之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固然将史部“独立”出来,但古人治学却从未囿此畛域,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无不贯穿经史子集各部。如果以今人专门学科的眼光讨论古代“史学”的内容,诸多含于传统学术中的史学资源或许会被忽视,史学史研究可能就会有不全面、不充分的缺失。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学术史的考察,意在更多地回归于在传统学术诸多因素之中理清史学的发展脉络、探析史学自身的撰述形式和理论内涵等特点、研究史学与经学、文学间的错综关系,揭示那些隐藏在史学发展表面之后的线索。然而,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除在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方面有较突出进展外,纵深式的专题研究似显薄弱。因此,着力向深层次拓展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古代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仍然是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学是近年来史学史研究的热点。其研究的日益深化,却使得该研究领域愈来愈成为中国史学史整体时段中的“专门领域”而存在,换句话说,对所谓中国古代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分野”,固然利于研究上的集中与便利,但却人为地阻隔了二者在实际上的联系。在当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相对充分的情况下,不仅上述在研究时段上的“分工”已无太大必要,而且在研究内容上,更应对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作贯通的考察,将中国古代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视作一个发展整体作全面的梳理与研究。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因‘摒弃’了传统史学才产生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代史学为何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与近代史学的客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
比较中西史学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而且是未来极具潜力的学术研究增长点。如果说研究主体的知识程度是影响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对中西史学的基本认识与价值判断,以及由此涉及到的在比较中西史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则是在史学比较时中外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在起决定因素。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学者的充分的重视,而西方学者鲜有提及。这至少说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家在中国史学的知识背景下是承认并且重视西方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
从比较的对象和内容来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突破之一,是不再局限于中西史学间过分具体的两两对比。以往一说起比较研究,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找出那些中西史学间有相类似的史家、史书等进行比较,诸如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比较、《史记》与《历史》的比较、章学诚与柯林武德的比较。中西古代史学原本是在互不了解、互不交叉的不同的文明渊源中各自发展的,如果过分强调进行具体地两两对比,忽略中西史学间存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往往最终就会出现是否有可比性的疑问。从中西文化传统、中西史学间的理论特点、思维方式的不同、治史旨趣与史学精神的差异进行比较,注重基本结论、思维路径、表述方式的特点之不同,当是中西史学比较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