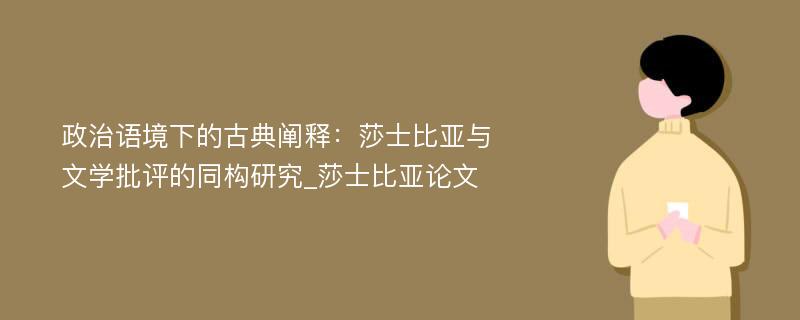
政治化语境中的经典阐释——与文学批评同构的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语境论文,政治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士比亚研究被称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甚至被誉为学术研究中的奥林匹克。在现代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莎作的理解与演出,业已成为国家、民族文学、艺术研究软实力的象征。莎学研究在几代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莎学已经成为一支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力军,在文学批评、世界莎学研究上显示出中国莎学研究的实力。但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相一致,与文学研究、批评领域主流话语的走向同构,中国莎学的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受到以政治标准划线等时代语境的干涉,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中国莎学研究受到了极大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莎学研究被政治化的语境所覆盖,而作品的审美研究、艺术呈现方式、艺术特色研究则被遮蔽。因此,对莎学研究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梳理,可以深化我们对政治化语境中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特殊性的认识。 一 话语权左右下的“靶标” 与1949年以前的莎学研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莎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厚重的成果,但在政治化的语境中,中国的莎学研究较为彻底地摈弃了以西方莎学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评介,将视角转向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莎学理论资源呈现为遵循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一边倒”的研究局面。与文学研究的环境同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主流话语要求莎学研究者的研究,必须将着眼点投射于政治、阶级与阶级分析层面。从事莎学和西方文学教学与研究者要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务必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突出莎作及其人物的阶级属性。要求与国内主流文学话语相一致,莎学研究要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以阶级、阶级属性划线的研究方法获得了主导的研究地位。我们从其研究范式与结论看,可以感受到苏联文艺中“左”的思想,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对莎学研究的全面影响,而且由于研究的惯性和政治语境的特殊需要,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与“修正主义”苏联关系的恶化而有所减弱。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双百方针受到强烈干扰和冲击。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者由于从事的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显赫的文学家的研究,这批莎学家如孙大雨、孙家琇、吴兴华、袁昌英、林同济、张泗洋、刘炳善等,便因其强调研究的特殊性或由于其在莎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被打成右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适应形势,“左”的思想成为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对包括莎作在内的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理论着眼于批判,轻视其经典价值、审美特色和艺术特点,尤其是对一些文艺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如人性、人道主义、写真实、爱情描写、浪漫色彩,甚至现实主义,往往斥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横加挑剔,给予猛烈批判。到了60年代前期,在重点、目的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先以“批资”(即批判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为靶标,后以“批修”(即批判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所谓“修正主义”)为重点,强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使莎学研究沦为了为适应主流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或阶级斗争理论的传声筒。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已经不是探索自身发展规律,而是成为争霸理论话语解释权的宣言,“‘莎士比亚研究’也受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影响,受到政治形式和文艺政策的左右”①。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莎士比亚研究首当其冲地受到波及,成为不断地向“左”的思潮主动靠拢的文学研究。莎学研究必须与政治潮流大方向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化语境中,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外国文学遗产被批评为“对当时社会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不够的”②,为此要在莎作中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为了紧跟时代,这一时期的莎学研究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为楷模,通过对苏联莎学基本观点的学习和模仿,运用于自己的莎学研究中,在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采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通过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莎作产生的时代背景、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上,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莎作中的人物进行分类,以莎剧中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的基础,为证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重在强调莎剧对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有选择的揭露与批判,以及证明某些人物历史与时代的“先进性”,如把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的先进分子,强调莎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伦理观是符合时代的进步潮流的。虽然这些莎学批评中仍然蕴涵了不少真知灼见,远较以往单纯简略的评介深刻,为人们深入理解经典打开了一扇窗户,但由于这些莎评基本上是从政治化语境出发,按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莎作,一味强调莎剧是现实主义杰作,对于莎作中的浪漫主义艺术特点视而不见,甚至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为证明莎作与进步文艺的关系,批评者在肯定其中的人文主义“先进”思想的同时,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出莎作中的阶级局限性,认为莎作必定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外国文学遗产的代表。在这样高度政治化语境中的莎学研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种研究惯性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今天的莎学研究中也没有完全绝迹。 由于受到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文学研究大环境,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与斗争指导方针的影响,莎学研究往往自觉以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切入时代背景、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研究,此时的莎学研究如果不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对莎士比亚、莎作的资产阶级观念给予批判,不对莎作中的人物按照阶级阵线划线、分类,抑或不从阶级分析入手赞扬莎氏本人和莎作反映了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那么这样的研究无疑会被视为对腐朽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批判缺乏力度,甚至研究者本人也存在着立场和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在政治运动风暴中,中国莎学家的命运始终被政治环境所左右。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全国的迅速铺开,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教育领域成为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政治环境显示,只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猖狂进攻,才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胜利。莎士比亚成为政治思想领域斗争中的明显靶标。从事莎学研究本身,也成为决定中国莎学研究者命运和人生沉浮的重要因素。 二 特殊语境中的“资产阶级爱情观” 在政治化语境中,对文学作品中爱情的歌咏,对人道主义的反映与歌颂始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社会和人民的侵蚀。为此,在思想、文化和组织领域内开始了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具有人道主义的爱情描写已经成为创作和研究的禁区。由于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恋爱观,研究莎士比亚也成为具有政治风险的课题。在文学研究领域莎氏被视为“大、洋、古”的代名词,在外国语言文学界,学习、研究被视为经典的莎作是与无产阶级文学有着天壤之别的,如何看待莎氏和莎作中的“爱情”既是感情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因而学习研究莎氏不时遭到质问与批判:“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则认为是人类文化的顶点,读一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胜过生活二十年(这句话和马克思讲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对照一下,会令人发生怎样的感想呢?)”③;其时的思想批判多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甚至与学习、研究者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批判者强调“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爱情观”等新道德观念,拒斥莎作中的男女情爱和人道主义,批判者强调:在莎作研究、学习中,有人“每讲到爱情诗时,就眉飞色舞,赞赏不绝……甚至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人念这些诗以‘自慰’……宣传资产阶级男女关系”④;批判者认为由于立场和感情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们对根据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罗蜜奥与幽丽叶》,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厌,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优秀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击队》则就是不看。这又是一种什么感情?如果真是从心里爱新社会,怎么能不看?如果真是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怎么能不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看社会主义的电影?”⑤批判者所要树立的是集体主义的英雄史观,而非温情脉脉的“资产阶级”爱情观和人道主义。所以,当秦兆阳(何直)提出“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⑥时,当即被定位于“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十足的修正主义”⑦,也就不足为奇了。针对文学经典,即使仅从美学和艺术方向肯定其价值,也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本书可读:一是红楼梦,一是莎氏比亚’……这种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难道是个别的吗?”⑧显然,研究莎氏莎作已经被定位是资产阶级的研究倾向。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纯洁、不朽的爱情悲剧也被视为肮脏、丑恶的“资产阶级男女关系”,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爱情观是背道而驰的,赞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不朽爱情既是感情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具体到研究者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男女关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声浪中,有的莎学家也不断对自己的莎学研究和所谓对资产阶级莎学缺乏批判做出提高认识的检讨:“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英美近来所大吹大擂的‘新目录学’,在其本身就无多大科学性可言,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来提倡它则更是绝大的错误。‘新目录学’自夸在莎士比亚研究上最有功绩,但是鼓吹了半个世纪,莎士比亚全集新版的面目基本上还是1864年‘地球版’的原形,并未向猜测中的莎翁手稿走近半步!”⑨“它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道路,与社会主义的利益根本相反”,对于莎学研究“我们也要问问是些什么东西,对社会主义又有什么用处”⑩。还有文章说,由于莎学所具有的明确的西方学术身份,陈嘉在《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流露的政治见解》一文中还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认识,强调莎氏尽管有反对封建割据和暴君专横的内容,反对唯利是图的思想,但莎氏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映政治问题的。这篇文章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写作,卞之琳等人执笔的,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长篇论文——《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其中该文以陈嘉文章中的只言片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对待人民的感情问题,该文从阶级的角度指出,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陈嘉却“认为劳动人民也受了唯利是图思想的影响”,难道“穷人为了求生而卖命,我们能说他们不顾一切、唯利是图吗?”(11)批判者以阶级划线,以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衡量研究者和论文的政治立场。处于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莎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研究领域——“大、洋、古”中“洋”的总代表,进行莎学研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以人道主义为切入点研究《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爱情悲剧也会被目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显得与无产阶级爱情观南辕北辙,不合时宜,研究者偶有不慎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在这样的政治化语境中,莎士比亚成为与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动人民感情格格不入的文学作品,研究它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被指为与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危险。处于如此敏感的政治化语境中,即使研究者小心翼翼,以谨小慎微的方式解读莎作,也难免会逾越主流意识形态的红线。举例而言,尽管陈嘉在《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章中,以较大的篇幅对莎士比亚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透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恋爱观和人性论进行了批判:他强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位主人公反抗封建恶习冲破爱情障碍的主要动力,他们对不朽爱情的永恒追求,恰好是我们今天要加以批判的资产阶级恋爱观;资产阶级的爱情观与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恋爱,表现了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观点,是掺杂在作品精华中的糟粕;罗密欧、朱丽叶的海誓山盟,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战斗和劳动中产生的爱情,以及持有的爱情观可谓有天壤之别,透过朱、罗之间的爱情,可以看到,作品明显地表现了喜欢玩弄笔墨和感叹风月无常的有闲阶级的思想感情,而无产阶级和从事劳动的青年男女决不会在这些无聊的爱情问题上纠缠不休;归根结底,由于立场和感情问题,更由于莎氏本人的阶级感情和社会经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作家,“他很容易错误地认为在人类社会中有某些永恒不变的和适用于一切人的思想感情”(12)。因此,陈嘉在《论〈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贵族青年男女之间的生死爱情与劳动人民的爱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批判者”的陈嘉在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时,对于莎氏这样著名的外国作家,强调的是应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莎士比亚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描写的爱情,以及所谓的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观点和所谓的爱情的永恒性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提高警惕,给予抨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爱情观对青年思想的侵蚀;更应该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莎氏作品反映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不够深刻,两位悲剧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也根本不能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爱情相比。如此这般的政治化解读在主观上强求古人、洋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演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生死恋,可谓那一时代的莎学研究特色。因此,与文学批评的大环境同步,从时代和意识形态环境来看,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是不适宜“谈情”、“说爱”的,尤其是这种代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爱情描写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同,故而这种达到“情”“爱”最高境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其会被视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爱情观的洪水猛兽了。 三 批判者的工具与被批判者 在20世纪50年代,莎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附庸于政治化语境中,成为图解政治,表明研究者政治立场的工具。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阿垅“对莎士比亚的恶意歪曲”(13),使莎氏成为批判者手中的政治工具。苏联戏剧专家叶·康列斯卡娅用积木教具创造戏剧情景中的“行动”,建立人物感受行为逻辑,使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师资班的70多名学员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在即将结业时,排演了风格较为鲜明的《无事生非》等剧目,而戏剧学院的组织者却将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排演所取得的成功,与反右斗争荒诞地联系在一起,荒谬地宣称“通过伟大的反右派斗争,这系的毕业同学近一百人都表示要坚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右派分子挑拨离间的阴谋”(14)。排演莎剧成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有力配合和对当时政策的坚决支持、响应。为了扩大反右斗争的声势和成果,1957年10月9日至10日,北京话剧界演员、导演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一千多人激情集会,举行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扩大辩论会,在会上,针对右派分子孙家琇等人的所谓“右派分子”言论,以及捕风捉影的所谓“组织活动”进行了上纲上线、声势浩大的批判。指控以孙家琇为首的“中央戏剧学院民盟支部的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地召开反党座谈会,写文章煽动学生反对学院党的领导”,将莎学变成批判莎士比亚研究者的工具。批判者强调,这些右派分子贬损、污蔑社会主义的言行,经过首都话剧界、文学界同志摆事实、讲道理的猛烈批判,已经被批驳得理屈词穷了,他们的右派分子言行也受到了舆论的严正谴责。1957年6月,中央戏剧学院出版的《戏剧学习资料汇编》(创刊号)上孙家琇尚被列为“编辑委员”(15)之一,并且还发表了她的长篇论文《〈大雷雨〉及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报告),但在1957年9月出版的第2期《戏剧学习资料汇编》上孙家琇就被取消了“编辑委员”的资格。而该刊的出版就是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求得“今后文学艺术和科学繁荣发展”(16)。政治运动的突然逆转谁也预料不到,在政治游戏的规则骤然改变以后,中央戏剧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开展起来,因此从思想、艺术创作、办学方针上对孙家琇等所谓的“右派分子”言论进行了猛烈批判。选择莎剧研究、排演已经成为立场问题,“不可否认我们在选择剧目上是有问题的,表现在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内资产阶级专家身上——他们迷信古典、崇拜偶像,和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他们认为古典剧目有‘挖头’‘可以学到东西’,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就需要多排古典剧目……而所谓第一流则只有西洋古典剧目了”。批判者强调莎氏的资产阶级属性是为了达到把孙家琇等人彻底批倒、批臭的目的。选择研究、排演属于资产阶级的莎剧,而不选择无产阶级戏剧是政治立场问题,为此《戏剧报》记者覃柯通过引用戏剧界的著名作家、领导人在批判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对孙家琇进行了猛烈“开火”,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野心家“埃古”的形象作为比附,以正中要害、一追到底的方式批判“孙家琇是穿着裙子的‘埃古’”(17)。这种政治化的猛烈批判,将政治运动中的被批判者与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典型的恶人形象相提并论,成为孙家琇一生为研究莎士比亚所付出的沉重的“政治与人生代价”。同时,这样的政治缧绁,也促使孙家琇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重新焕发出文学研究的巨大热情。但在当时意识形态“左”的大环境中,研究莎士比亚已不现实。批判者强加在孙家琇身上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有着民族灵魂的人,而从感情到立场,表明她确实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上表现了她的“英雄”。显然,批判的调门已经升级,矛盾的性质已经有了重大变化,批判者认为孙家琇写的《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是一份反党宣言。对莎作翻译的不同看法本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批判者认定孙家琇在这篇“宣言”中,篡改了屠岸同志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六十六首,篡改者的目的就是:以莎士比亚三百年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统治进行战斗的诗句,来对照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批判者由此认为挖出了其中的深意,并穷追到底:“我难道碰见了比奥寨(赛)罗更悲剧的悲剧,至少他的苔斯得蒙娜是纯洁的。但是我的理想所寄托的这些党员们并不是纯洁的。”(18)批判者强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唱出的“独立思考”的论调,“实际上在于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孙家琇只是披着莎士比亚专家的外衣进行政治阴谋活动,而这件外衣又是“千疮百孔”的,一眼就会被人识破的。1957年“戏剧学院的‘喀秋莎’集团”也被《人民日报》署名“山柏”的《论小集团》点名,莎学研究成为孙家琇的一桩“罪证”。(19)“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研究莎士比亚更不可能,孙家琇在“文革”中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多年以后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临时总勤务站专案组”的“文革”材料1968年第3号(1968年1月12日下午)和1968年第4号(1968年1月13日)以及“中央戏剧学院联合临时总勤务站专案组”1968年2月3日汇总的《斗争情况简报》里可以印证孙家琇在“文革”中因莎学研究而受到猛烈批判。 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孙大雨成为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遭到严厉批判。自1957年6月8日,《解放日报》以反面教材刊登孙大雨的长篇发言后,上海各大报刊连续发表批判孙大雨的文章,“非但从政治上揭发,而且从生活上进行丑化”。使孙大雨“被剥夺和浪费掉数十年时间”,一生只有11部著译,而梁实秋却在海峡对岸译竣了《莎士比亚全集》。 吴兴华作为一个在莎士比亚翻译和莎学研究上初步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翻译了堪称经典的译作——莎剧《亨利五世》和两篇分量很重的莎学论文。(20)吴兴华的莎学文章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例如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概念中,对资产阶级莎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莎学批评把莎士比亚涂改成了封建制度的拥护者和侵略战争的沙文主义者。显然,吴兴华无法逃脱当时中国特有的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而其死因是“在1957年一次探讨对外语教学方法的发言中,吴兴华表达了与苏联专家不同的观点。这成了他被评为右派的主要依据。他的级别连降两级,被取消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被‘补划’为‘右派’”(21)。 莎学研究专家袁昌英在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后,始终也没有泯灭对莎士比亚研究的信心,在偏僻落后的湖南醴陵乡下她身边带着一本烫金的豪华本《莎士比亚全集》,上面有她用铅笔做的标记和诠释,她一直做着一个美丽而多彩的梦,在自己最后的生命历程中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79年对错划进行改正时,袁昌英这位杰出的文学家、莎学家已经带着无限的遗憾和对人生、对文学、对莎士比亚的眷恋于1974年在家乡醴陵离开了人世。 另一位莎学专家林同济1953年因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讲授莎士比亚、英国戏剧史等课程,作为曾在美国学习比较政治学的“战国策核心成员”,教授、研究政治学已无可能,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麦克白》。林同济的译莎,在正确理解莎作原意的基础上,保留了莎剧的五音步诗形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构成素韵诗基础的莎氏特有的韵律在翻译中流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林同济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虽然这时已经不可能给学生讲授莎士比亚了,但是,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他从未停止过翻译、研究莎士比亚,他翻译了四部莎剧。(22)在“文革”中,林同济因为教授过莎士比亚剧作被红卫兵揪斗了十多次。林同济撰写的《Sullied之辨——〈哈姆雷特〉一词管窥》等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始得发表,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198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莎学研究是整个文学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和莎士比亚联系起来,可谓批判者就地取材借对经典的解读批判被批判者,而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政治语境”映射出的是特殊年代的社会扭曲,以及由此而演绎出的人格变异的悲喜剧。文学、莎学研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联系得如此紧密,这在世界莎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莎士比亚剧作能够与中国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使然,因而彻底改变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者的人生命运和研究方式。研究莎士比亚给中国莎学家带来20年的蹉跎岁月。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莎学研究已经抛弃了政治化思维,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莎学研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折射出文学、莎学批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①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②杨周翰:《批判地对待外国文学遗产》,《光明日报》,1964年6月7日。 ③④⑤⑧编者:《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在西语教学和研究的阵地上!》,《西方语文》1958年第3期。(莎剧名称和人名均以原文为准,本文作者未加改动。) ⑥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⑦姚文元:《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⑨⑩王佐良:《这是什么样的学问》,《西方语文》1958年第5期。 (11)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12)陈嘉:《论〈罗密欧与朱丽叶〉》,《江海学刊》1964年第4期。 (13)孙家琇:《揭穿胡风分子阿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恶意歪曲》,《剧本》1955年第9期。 (14)参见《戏剧报》1957年第16期上刊登的《〈无事生非〉和〈决裂〉将来京公演》。 (15)戏剧学习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205页。(关于编辑委员会的构成可参见该刊第一、二期的版权页。) (16)欧阳予倩:《中央戏剧学院十年》,戏剧学习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戏剧学习资料汇编·中央戏剧学院十周年院庆特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第9期,第22页。 (17)覃柯:《孙家琇、徐步右派小集团现出原形——首都话剧界反右派斗争获得新的战果》,《戏剧报》1957年第17期。 (18)李缀:《反击右派分子孙家琇》,《戏剧报》,1957年第14期。 (19)山柏:《论小集团》,《人民日报》,1957年9月10日。 (20)(21)李伟民:《肠断秋深写歌行——吴兴华与莎士比亚》,《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3年第19辑。 (22)李伟民:《撑住残秋唯此花——林同济与莎士比亚》,《外文研究》2013年第6期。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反右派斗争论文; 政治论文; 右派分子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戏剧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右派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